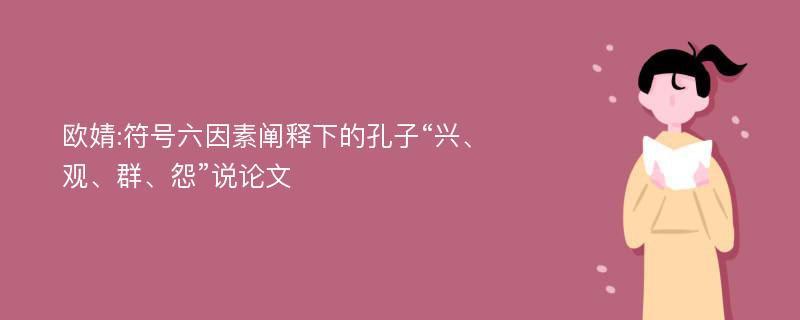
摘 要:“兴、观、群、怨”说,这一儒家话语体系下的文学评价,是《论语·阳货》中孔子就《诗经》现实功用所提出的概念界定。作为符号文本的《诗经》,体现出了“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这几大社会功能,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符号接收者相关阅读体验的产物。运用雅柯布森符号六因素的视角,对《诗经》的相关表意过程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一符号文本受到了具体因素的主导影响,从而生成了不同的意义阐释。借助符号学理论,就“兴、观、群、怨”等一系列概念进行具体阐释,可以有效地就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下的《诗经》文本的解读、传播以及经典化形成的过程展开分析论述,从而为包括诗歌评价与接受在内的传统文学理论提供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符号六因素;《论语》;《诗经》;“兴、观、群、怨”
《论语·阳货》有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P2525)此处的《诗》,即特指编订于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孔子在此处,针对为何需要学习《诗经》这一疑问,提出了其对于人生所产生的指导性影响,即“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这七种概念。如将这几种概念界定视作《诗经》在社会接受过程中所形成的实际功能,就需要对孔子的这一系列评价进行明确的定义。相比于“侍奉长辈、君主”以及“知晓草木鸟兽的名称”等定义明确的社会功用,“兴、观、群、怨”这一组概念,在历代学者对于《论语》的注释中,呈现出侧重不同的多种解释项。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者,对于上述《诗经》的不同功能进行了各自的解读。这种解读上的差异,与注释者们在对《诗经》表意进行理解的过程中,所各自秉持的侧重点密不可分。这种自我认识的侧重,根本上取决于符号表意过程中符号文本所产生的特定意义与目的导向。在特定的传播时期,《诗经》文本自身所携带的文化标记推动了孔子对其社会功用的评价,以及后世儒家学者对于这一评价的再评价。
为了分别对《诗经》表意过程中“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的功能进行有效地分析,本文运用了俄国语言学家雅柯布森所提出的“符号六因素”理论。借助这一方法论,可以对《诗经》表意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本的社会接受与实际运用时的价值取向进行理解。而运用《诗经》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在为符号表意过程的六因素理论寻求阐释案例的同时,也为儒家文论视角下的《诗经》诗教观提供全新的分析视角与解读空间。符号六因素的具体定义,参照赵毅衡教授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即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含“发送者、接收者、对象、文本、媒介、符码”这六个因素,“当文本让其中的一个因素成为主导时,就会期盼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2](P177)所产生的意义性质则与文本的表意现实过程相关。作为符号文本的《诗经》,在表意过程中必然受到上述各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它在先秦社会语境中所形成的不同类别的传播解读。针对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的界定,需在相关儒家学者的注解释义的基础上,结合特定时期下特定因素的主导而加以审视。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1036例中老年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病程≥10年的患者中伴有不同程度脑动脉狭窄病变的939例,阳性率91.64%,行CTA检查诊断检出率为98.41%,MRI结合MRA在诊断海绵状血管瘤及静脉发育畸形准确率要高于CTA,见表1、表2。
一、《诗》可以“兴”
“诗可以兴”作为“兴、观、群、怨”等概念之首,标志着儒家学说范畴的诗歌评论,具备了与社会受众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倾向。在对其进行分析之前,需要明确“兴、观、群、怨”的“兴”与《诗经》六义中的“赋、比、兴”中的“兴”,虽同为一字,却有所区别。“赋、比、兴”的“兴”,是《诗经》的一大写作表现手法。朱熹将“兴”解释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3](P402)即《诗经》篇什的首句,先描写其他与后文诗歌文义无直接联系或联系较为抽象化、意境化的具象物体,再通过此来引发出主要的后文。此处的“兴”,是符号文本自身进行语言组织的一种表现手法,与孔子所提出的现实社会语境下,“《诗》”表意过程中的目的导向有所区别,故在此着重提出,便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界定。
《论语》中“兴、观、群、怨”的一系列属性,与孔子所处春秋时期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群雄割据的诸侯国政治,决定了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对维系诸侯统治的重要性。不同君主、君臣、士大夫相互之间的应酬答对,既是传统礼仪与个人素养的体现,也与一国的国情、风俗等社会、政治情况紧密相连。《诗经》文本能够被运用于实际生活中的语言交流,正是这种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形态的一大体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4]这种赋诗言志的先秦传统,形成了孔子提出儒家文论的一大社会背景,同时决定了当时的接收者对于《诗经》这一符号文本进行理解、评论、传播的主要思想动机。
“诗可以兴”,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何晏引孔安国注释,“兴”为“引譬连类”。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释“兴”为“感发志意”。这两种解释都与《诗经》被主观接受、解读的过程有关。“引譬连类”指通过某一处符号文本,使得读者借助想像而得到与之相联系的、带有普遍性的某种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凝练并升华于文本之上的。例如,《论语·学而》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1](P2458)子贡从孔子所讲述的“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纵”不及“贫穷而安乐,富贵而重礼节”的品格,联想到了《诗经·淇奥》中表述君子的人格应像玉石那样不断被切磋、雕琢的诗句。而孔子就子贡这一表述进行了肯定,认为他具备了可以与之讨论《诗经》的资格,即“告诸往而知来者”,能够由此及彼地从某一个特定的阐释对象联想到另一个对象,重在发掘文本表象之下相互联系的儒家事理。
与“引譬连类”重在思维方式的逻辑联系相比,朱熹提出的“感发志意”则更为强调主观情志的激发。这一概念关注阅读接收者内在思想的启发、感染,侧重于主体接受效果,与上述“引譬连类”的接收方式看似不同,实则是二者间承接连续的关系,因此应在相互区别的基础上,对这两种注释进行共同理解。例如,《论语·八佾》中“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1](P2466)子夏对《诗经·硕人》诗句进行理解,在受到孔子“绘事后素”的启发之后,联想到了个体的礼仪约束应当以个体的品格内在为基础,从而获得孔子“始可与言诗已矣”的肯定。
高居翰认为,“在山水画‘物化’过程中,使山水树木在素绢之上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当这种形式在观者心中能够引起他有异样的情绪,图画就有了取代实景的力量”[6]29。观察自然,宗炳采取“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2]252。不固定视点,以流动目光看待宇宙万物,追求“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4]1517的精神境界,因此,他扶床而卧,观想着无限的山水空间,去感悟内心,神游万象。“卧游”图景和心灵空间图像合二为一,同时互动生辉。可以说,“卧游”和心灵空间之间的联系是互为因果、彼此塑形,“卧游”的心灵空间可以展现出审美创造的生机和自然造化之妙理,使人的情感从中得到解放。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将申包胥向秦哀公请求援兵,哀公起初婉言拒绝,申包胥则“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7](P2137)《无衣》是《诗经·秦风》中的篇章,秦哀公赋《无衣》一诗,旨在通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8](P373)这一传达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战歌,来显示自己同意出兵救援楚国的意向。通过《无衣》而理解到这一点的申包胥则“九顿首而坐”,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由此可见,不同个体通过《诗经》文本来进行交流的过程里,赋诗言志这一表达方式包括了“言志”与“听志”这两个层面。对于赋诗者来说,“《诗》”的作用在于言说自己的志愿,重在表达;对于听诗者来说,“《诗》”的作用在于考察对方的志愿,重在理解,从而构成了“朝聘宴享”等场合的赋诗酬酢行为。
例如2016年广东省中考题第14题,已知了电阻甲和乙的IU,可以得出电阻乙的阻值为6Ω,若把电阻甲和乙并联后接在电压为6V电源两端时,则干路的总电阻为多少?总功率为多少?
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影响下,儒家学说获得了更为深化的尊崇与推广,其社会话语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升。“可以事父、事君”的“《诗》”表意过程,已经逐渐脱离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诗经》形成了在后世朝代更替的纵向线索上得以被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叠加阐释与实践的过程。当“事父、事君”得以促进纵向上表意过程的延续,“《诗》”的经典化进程得以一步步推进,此时的符号文本出现了较强烈的元语言倾向,即《诗经》文本已然形成了解释自身,并对自身进行经典化塑造的文学现象。
二、《诗》可以“观”
在“《诗》可以群”的表意过程里,当这一过程侧重于进行自我表达诉求的赋诗者,即符号文本的“发送者”时,诗句是用来抒发心声、表达主观情绪的工具,符号文本呈现出的是较强烈的情绪性。对于听诗者而言,作为符号文本的《诗经》篇什章句,侧重于其所指称的对象。听诗者需要获取、理解的是赋诗者在诗句中所传达的志向、意愿,例如申包胥通过《秦风·无衣》而直接接收到“秦师乃出”这一信息。这一符号过程以传达赋诗者的内心意愿这一明确意义为目的。文本符号作为“对象”的要素性得以凸显,《诗经》在现实场合中所体现出的语义成为了最为关键的关注点。此时,符号出现的是较强烈的“指称性”。当符号完成了上述表意过程后,就从个体表达上升至群体交流,形成了“群居相切磋”。这一系列表意过程,既关注“自我表达”的输出,也关注“理解他人”的输入。它并不强求作为接收者的听诗者改变自身的内在意愿,就赋诗者的主观志愿、情绪等进行附和奉迎,而是通过交互的切磋、磨合,达到“和而不流”的境界,即儒家所讲求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与此同时“群而不党”的和谐共处、同气相求的交际风貌。
除了“采诗”这一方式,《国语·周语》还记载了“献诗”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5](P11)即先秦以来,存在着公卿、士大夫等百官献诗的传统。《左传》中也有“吴季礼观乐于鲁”的记载。通过各层级的处理、编修、奏颂等传播方式,“《诗》”被传达给君王、贵族等上层阶级,使他们得以借此考察各国的民俗、政教,最终有助于王政得以“事行而不悖”。官员们通过各种灵活的传播方式,将“《诗》”的文本传播到统治阶层的接收视野中,使得君王得以获得有关大众民情的讯息。由此可见,《诗经》在“观”这一语境下所完成的表意过程,侧重于“对象”自身,即“《诗》”的现实社会层面的所指。这一表意过程,以明确地传达各国风俗盛衰、王政之得失为目的。因此,“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所注释的“《诗》可以观”,体现的是“《诗》”这一符号在表意过程中所携带的强烈的“指称性”。
三、《诗》可以“群”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的文本在先秦时期“赋诗言志”这一场合中所出现的沟通、交际的现实作用,影响了“《诗》”同一具体篇章的诗义阐释。在不同的现实场景之中,出现了解释项的不同,即先秦时期赋诗言志时,时常出现的“断章取义”现象。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晋平公囚禁卫献公,卫国派使节前去请求释放,“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7](P1990)再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在场众人赋诗来考察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一首。《将仲子》与《野有蔓草》,原本都是表达男女之情的情诗,并不适用于朝堂上的诸侯国外交情景。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认为子展赋诗选取《将仲子》中“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8](P337)的诗句,是在借此向晋平公进言,暗示他囚禁卫献公的行为不是一国君主应有的风范,意图进谏晋平公应当顾忌周遭舆论对他的谴责。子太叔选取的则是《野有蔓草》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8](P346)这一句,体现的是一种外交场合中对他国使节的欢迎辞令,力图消弭赵孟的戒心。这种有意识地截取、引用《诗经》某一特定章句的行为,改换了它作为符号文本原有的解释项,使其得以表达政治场合中的特定语义。作为《诗经》符号文本的又一表意过程,它的动机在于赋诗者意图通过“《诗》”来达到外交行为的目的。子展需要通过赋诗来促使晋平公释放被囚的卫献公,子太叔需要通过赋诗来表示对赵孟的外交礼节,消除对方的疑虑戒备,此时被置换了解释项的“《诗》”,在表意过程中侧重于符号的接收者,意图促使他们在思想、行为上作出某种期待下的反应,呈现的是较强的“意动性”。
孔子所提出的概念界定,依托于儒家思想话语的特定语境,“兴”这一定义的成立与流变,伴随着“引譬连类”的儒家解读方式的形成。这一符号表意过程,侧重于诗句本身的文义以及孔子对其进行的意义解读,以传达儒家讲求人格修为、礼仪伦常的学说理念为目的。子贡、子夏等接收者能够对《诗经》进行由此及彼、由文及理的联想、阐发,就在于他们理解到了其面对的符号文本的意义所指。这一过程侧重于符号六因素中的“对象”。符号出现的强烈的“指称性”,促使了接收者完成了“兴”的“引譬连类”。接收者们从中领会到了这种文本符号与儒学道义之间的内部思想联结,从而受到了感染与熏陶。这种熏陶同时也是接收者在解读《诗经》过程中所产生的内部主观感受,即符合朱熹对“兴”的“感发志意”的阐释。这一表意过程中,强调了阅读接收者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大程度上基于具有特定导向的、儒家学说的教育、传播方式。在孔子以阐述儒家学说为动机的《论语》语境之中,对《诗经》诗句所进行的阐发,都旨在借此进行儒学理念的教育、传播,目的在于调动接收者,使其产生“贫而乐、富而好礼”“礼后乎”等认知感悟。因此“感发志意”的过程,侧重于诗的接收者,强调能够促使接收者产生与儒学相对应的某种内在反应,此时的“兴”,出现的是较强烈的意动性。
“《诗》可以观”,何晏引郑玄的注释为“观风俗之盛衰”,在正义中解释为“‘可以观’者,《诗》有诸国之风俗,盛衰可以观览知之也。”[1](P2525)分为“周南”“召南”“大雅”“小雅”“颂”的《诗经》,反映了王畿与诸侯各国的风俗人情,接收者可以通过其具体篇章的描写,从而获得对各国风俗盛衰情况的认知。朱熹补充注释为“考见得失”,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4](P1355)由此可见,“考见得失”与“观风俗盛衰”的主体,是运用采诗等手段考察民间风俗的上层阶级。君王与采诗官作为这一表意过程中的接收者,看重的是《诗经》这一符号文本体现出来的各国社会现状,表现了“《诗》”的文本与现实生活实况的紧密相连,因此“《诗》”可以加深君王对自身施政举措得失的认识,从而起到指导上层阶级完善统治的作用。
“《诗》可以群”,何晏引孔安国注释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释为“和而不流”。孔安国借用《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表述“群”的作用在于《诗经》可以使得不同的接收者们,在感发、产生出相同或类似的思想感情这一“感发志意”的前提条件下,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完成思想层面的切磋、碰撞、互补,从而使得各自的思想内蕴最终获得共同的升华。这种接收效果所依托的社会背景,与先秦时期贵族、文人阶层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语言交流中,常引用《诗经》篇什来辅助交流的传统有关。杨树达《论语疏证》中解释“群”:“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6](P456)交际活动中的官僚、文人、贵族统治阶级,通过赋诗来表达内心的情绪、褒贬与志向所在。这种交际行为方式,正是“可以群”最直接的外在显现。“《诗》可以群”的表意过程,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实际发生的社会行为,本质上是不同接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诗经》的具体文本是交流得以形成的重要工具。
四、《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何晏引孔安国注释为“怨刺上政”,邢昺作疏“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这几种解释都表明了《诗经》这一符号文本被用来批评讽刺天子、诸侯在王政统治上的失道,表达的是民情舆论的怨怼。如《邶风·新台》讽刺的是卫宣公为抢占儿媳宣姜而修筑新台的荒淫无道之事;《魏风·硕鼠》则通过比拟手法,将横征暴敛的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危害民生的老鼠;《小雅·雨无正》则是怨刺周幽王昏庸误国的时政,其中“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听言则答,谮言则退”[8](P447)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百官无能、朝中无人能勤政辅国的愤怒与忧虑。这一表意过程中的主体,是“《诗》”的民间创作者与引用者,侧重于符号文本的发送者,展现的是他们内心对时政与统治阶层的讥讽、愤怒之情。“《诗》”这一符号文本呈现的是较强烈的情绪性。
五、《诗》可以“事父、事君”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邢昺的疏解释为:“迩,近也。《诗》有《凯风》《白华》,相戒以养,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颂》君臣之法,是有远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与君,皆有其道也。”[1](P2525)朱熹注释为“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8](P243)这一语境中的“事父、事君”强调的是在家族中可“侍奉父辈、长辈”,出朝堂上可“侍奉君主”等符合儒家伦常教化的行为规范。儒家伦理文化讲求的“三纲”“五伦”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是被列在最首位的伦理道德规范。儒家学说语境下,“父子”“君臣”之间的社会伦常关系被孔子纳入《诗经》的评价话语之中,体现出了儒家注重“《诗》”对接收者的教化作用。从这一评价以及相关注疏中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者们意图通过“《诗》”这一符号文本,向接收者们传递儒家伦理道德的感化、教育。这一表意过程的成立,与“《诗》可以兴、观、群”的现实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只有肯定了《诗经》文本在先秦时期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实际运用,才能有效地将“《诗》”的作用提高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维系的纲常道德层面。
在自身接收、理解“《诗》”的儒家伦理道义的基础上,接收者所产生的自我感情的熏陶、感染,进一步催生了对接收者自身社会行为的指导影响。例如邢昺注疏中提到“《雅》《颂》君臣之法”,得以成就了“远之事君之道”。这与接收者的主体意识密不可分,即“兴、观、群、怨”的第一要义“兴”。朱熹解释的“感发志意”,对这一接收者思想感情得以被陶冶、启发的过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述。这一步骤侧重于“《诗》”的具体接收者,体现的是意图接收者主观反应得以形成的意动性。
从整体的视角考察“可以事父、事君”的表意过程,需要意识到它既是儒家学者们对《诗经》文本进行的评价,同时也是他们对文本接收者所提出的行为规范、道德伦理的要求,意在接收者能够通过《诗经》的文本运用或对其文本义理的理解、学习,获取符合儒家社会伦理规范的思想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指导作为社会个体的接收者在家族、朝堂等场域中的言行举止,完成“事父、事君”的要求。此时,符号表意侧重的是“《诗》”的接收者,“《诗》”这一符号促使接收者做出儒家诗教要求下的反应,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意动性。
从具体实践的视角考察“可以事父、事君”的要求是如何在现实运用中得以成立与实现,则需要分清符号表意过程的具体步骤。在具体的“《诗》”文本阅读接受的情景中,读者得以理解相关文本思想内涵的前提,是他们有效接收到了“《诗》”这一符号文本所传达的君臣伦理信息。可以看出,“《诗》”的符号表意的对象,即“事父、事君”之道,是这一实践得以成立的根本。《诗经》的文本意义明确地指向了实用的外延,并以传达特定讯息为目的。此时,符号出现的是较强的指称性。
选取2016年8月—2017年8月在我院开展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108例作为研究对象。以护理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常规组及护理组,每组各54例。其中,常规组中,男34例、女20例,年龄为29~67岁,平均年龄为(48.0±2.6)岁;病程为6~13个月,平均病程为(9.0±0.8)个月;护理组中,男30例、女24例,年龄为29~69岁,平均年龄为(49.0±2.7)岁;病程为4~13个月,平均病程为(8.5±0.7)个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可以事父、事君”作为儒家学者对《诗经》现实作用的一大概括性评价,建立在“可以兴”的主观基础上,与“可以群,可以怨”的社会交际、舆论反映等现实语境相关联,形成了儒家伦常运作与《诗经》教化作用的结合。儒家学说范畴的道德伦理话语,对《诗经》的阐释形成了定型,从而促使《诗经》在儒家学说的历史沿革里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孔子以及后来学者的评价、解读,对“《诗》”的义理阐释与经典塑造,始终以“事父、事君”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人格、道德等要求为核心。
孔安国的“引譬连类”与朱熹的“感发志意”,同属于对于“诗可以兴”的合理阐释,因此可以将这两种阐释视作接收者在明确诗的指称对象的前提下,得以进行某种特定的、意动的思想情感反应。此二者,既是前后承接的方式与效果,又是在相互生成之中进行统一、交融的抽象思维与主观情致。
《毛诗序》即《诗经》的一种元语言阐释,相传它由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分为大序和小序。《毛诗序》在对《诗经》文本进行整体阐释的同时,对每一篇诗都进行了相关主旨的阐释。此处讨论的《诗经》这一符号文本,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毛诗正义》,即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版本。在它的收录中,把毛诗序和“诗三百”的篇章一起并置,将其共同视作被郑玄、孔颖达解释的正文部分。同时,《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又在文本编排上强调“诗三百”诗句的核心文本地位。诗大序被放置在整部《诗经》正文之前,形式上类似当今书籍出版物的序言;而诗小序,则被放在每一篇具体《诗经》篇章之前,对其诗文进行相关义理的阐发。例如《桃夭》即开篇为“《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的小序,而后接诗句正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8](P279)因此,在《毛诗正义》这一符号文本之中阐发义理的毛诗序,其作用类似于作为“诗三百”的题跋、序言的副文本,它与作为主体的《诗经》具体篇章是不可分割的,它的存在提供了“诗经”得以解释自身的可能。
四川省2015年GDP增速7.9%,2016年增速为7.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势头良好,四川居民消费结构也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是加工转化用粮逐年增加,另一方面是以大米为主的口粮消费呈稳中略降的态势。2011-2014年四川居民口粮的消费量出现小幅度下降,但肉类、禽类、水产品和奶制品的消费量总体上升使得饲料用粮成为全省第二大口粮消费的主要用粮渠道,在口粮小幅度下降和其他食品消费量大幅度上升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预见未来四川省的粮食需求总量将继续增加。(2011-2014年四川全体居民消费结构见表5)
“毛诗序”作为西汉毛亨作传,东汉郑玄作笺的《诗经》版本的“副文本”,为《诗经》自身语义的阐发提供了解读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是《诗经》对自身进行的权威阐释。针对“可以事父、事君”的伦理纲常要求,“诗大序”中评价“《诗》”是“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8](P261)即肯定并推崇了《诗经》对于社会伦常的现实引导作用。又例如,邢昺注疏中“《诗》有《凯风》《白华》,相戒以养,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1](P2525)《邶风·凯风》的“小序”为“《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尔。”[8](P301)小序为这一篇章定下的解释基调是“七子对母亲的孝顺安抚值得肯定”,同时也匡定了子孙对长辈的孝敬、侍奉的正道之所在。这种元语言的倾向,表明了《诗经》在儒家学者的积极阐释之下,其自身已然囊括了由儒家经典话语所构成的内部文本,即毛诗大序与小序。这些时刻传达着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文本,最终形成了对其自身的解释方法,并为“可以事父、事君”的儒家核心伦理服务。
六、《诗》可以“识草木鸟兽之名”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邢昺注疏为“‘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者,言诗人多记鸟兽草木之名以为比兴,则因又多识于此鸟兽草木之名也”。[1](P2525)《诗经》里多出现各种鸟兽草木的名称,接收者可以借此加深并推广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比兴”,这一《诗经》文本所具有的写作表现手法,需要借用自然之物进行创作的比拟、起兴,诗歌的创作者可以通过熟记鸟兽草木之名,来完成这一文学实践;诗歌的阅读者则可以通过鸟兽草木之名的具体所指,加深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扩充自身知识储备。“多识、多记”的这一过程,侧重于接收者,意在使得他们能够通过《诗经》的具体文本,从而完成对自然知识的了解、掌握。而这一过程的前提,在于《诗经》中有关“鸟兽草木”的文本表意是客观成立的,此时符号体现出的是“《诗》”较强烈的“指称性”。这些“鸟兽草木之名”出现在《诗经》具体文本中时,是侧重于对象的,以明确传达某种自然界的所指为目的。正是这种“名”的实用指称性得以成立,才能够建立起表意过程的前提条件,从而使得“多识、多记”的意动性得以成立。
时光飞逝,2018年也迈入了最后一个月份。好在元旦的钟声敲响前,还有一个温暖的圣诞节——这个来自西方的节日同样受到国人的欢迎,大概是因为它让我们可以与相爱的人相聚在一起,彼此交换礼物,回顾这一年携手共度的点点滴滴。
七、结语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文学评价,侧重于指向《诗经》这一符号文本的现实社会作用,并且涉及到了它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意过程。在《十三经注疏》与《四书章句集注》对《论语》注疏释义的基础上,结合雅柯布森的“符号六因素”的理论视角,对“《诗》”这一符号文本在不同语境下的表意过程进行解读分析,从而试图明确符号文本在不同因素占主导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相应意义阐释。这种意义阐释,与儒家学术话语发展历程中的《诗经》,对中华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理论、道德伦理等现实影响密不可分。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视角,对儒学评价体系下的《诗经》符号文本进行解读,有利于深入理解其所承载的儒学理念是如何被具体语境中的广大受众所解读、接收、运用。儒家重要经典“五经”之一的《诗经》,承载着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高度评价,它紧密联系着社会历史、风俗人情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被不断继承、多次解读的经典化过程。这一符号六因素理论视角下的阐释方法,旨在对《诗经》文本的丰富阐释价值进行进一步发掘。借助符号学相关理论方法,对中国传统诗学文论等对象进行阐释,足以提供值得继续关注的广阔学术空间,同时将引导我们继续进行合理有效的思考与解读。
校园情感场生态构建的探索是学校当前工作的“总纲领”,已初步成为全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共识,将覆盖和引领着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深远影响学校未来办学的方向、品位与内涵。我们越发感到,“场”无处不可在,情感的“场”随处皆可创生,大到整个校园,小到班级、小组乃至个人,都可以产生并建起一个个具有情感特质和作用的强大的场,而这种“场”既非简单的空间存在,亦非简单的物理作用。
参考文献:
[1](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南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战国)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The Confucius Ideas of Xing,Guan,QunandYuan Interpreted by the Jacobson’s Six Factors Theory
OU Jing
(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Chongqi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Chongqing400067)
Abstract:The literary evaluation under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four-word system-Xing,Guan,QunandYuan-is the concept defined by Confucius in the “Chapter YangHuo” of TheAnalects on the realistic function of TheBookofPoetry.TheBookofPoetry, as a symbolic text, embodie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Xing,Guan,QunandYuan, serving the father and monarch and getting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name of vegetation, birds and animals.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relevant reading experience of the recipients of symbols under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x factors of symbols by Jacobso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relevant ideographic process of TheBookofPoetr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ymbolic text is dominated by specific factors, thus generating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meaning. With the help of semiotic theory, a series of concepts such as "Xing,” “Guan,” “Qun” and “Yuan” are explained concretely, which can effectively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interpret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text of TheBookofPoe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ethics, thus providing a broader explanatory space for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ies, including poetry evaluation and acceptance.
Key words:Jakobson’s six factors theory; TheAnalects;Thebookofpoetry;Xing; Guan; Qun; Yuan
收稿日期:2019-05-27
作者简介:欧 婧(1990―),女,文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与欧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9)04-0095-07
(责任编辑 王碧瑶)
标签:诗经论文; 这一论文; 儒家论文; 文本论文; 接收者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