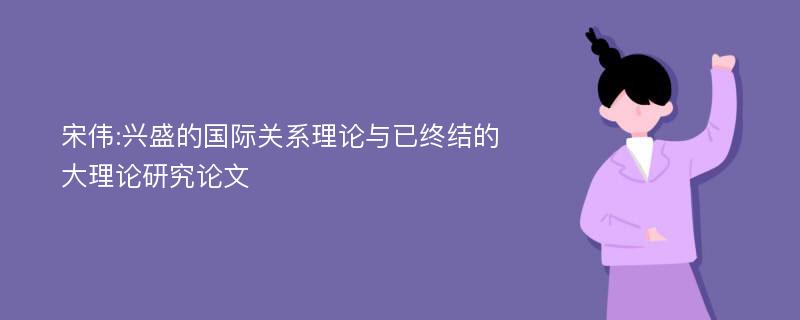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大理论研究;兴盛;终结
[摘 要]虽然过去20年间,国际关系大理论的研究没有出现重大创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的衰落或者终结。理论发展的停滞是因为已有的理论仍然有效并且发展到了一个极限,短时间内难以再出现新的突破。问题导向的研究并不意味着理论被放弃了,而是从大理论转向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建构。问题导向的研究必须在大理论的指导下,最终促进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发展。认为理论已经衰落或者终结的观点很多是不了解理论的解释范围,以及对理论存在的误解。国际关系理论解释的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行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服务于政策制定、因而需要被放弃的观点是一个常见的误解。理论的解释能力、解释范围和理论的发展都有一个极限。目前的科学理论已经穷尽了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范畴内的所有体系结构因素,因此大理论的研究已经终结。接下来我们更多要着眼的是中层和微观的理论发展、规范理论的发展以及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困难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关系大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停滞期,没有出现范式层面有所创新的理论,而人们对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已经感到熟悉和厌倦。(1)所谓的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指的是针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运作及其结果的研究,例如战争为什么反复发生、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更为稳定、什么情况下国家间合作更容易达成。它区别于针对某个现象领域的中层研究——例如对联盟问题的研究,也区别于针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例如大国是否会趋向于采取进攻性的外交政策。但在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时,许多学者将国际关系大理论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部。正如詹姆斯·多尔蒂所形容的,“今天的理论家们面对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好是十年内)创造出一种新范式的压力。”(2)[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质疑呼声,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现实,不具有足够的政策意义,因此是“无用的”“必须被终结的”。“简单化的假设验证”式研究大行其道,在可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居于主流,而理论导向的研究则将继续被边缘化。(3) 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2013,19(3):427-457.
在2013年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组织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这一专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围绕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质疑、焦虑和悲观。但是,目前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终结的讨论,与之前的质疑不同的地方在于,彻底否定现有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将导致这一学科的根基受到动摇。正如三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担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这一命题,将引发对于国际关系学是否终结的疑问。(4)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2013, 19(3): 419.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国际关系学分支是否应该被放弃,其部件是否应被分配给新的分支学科,即冲突、机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行为。”(5) Dan Reiter, “Should We Leave Behind the Sub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 2015, 18(1):482.理论是学科存在的基石,一个学科的理论被彻底否定了,这个学科自然也就离终结不远了。
财税激励政策的落实需要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国资部门等联动,可针对当前影响面广的几大财税激励政策,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等建立相应的协调沟通机制。对这些财税激励政策在落实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梳理、沟通和解决。同时,中央部门和地方应上下联动,加强对地方的指导,形成齐抓共管、层层落实的新局面。此外,还要加大对财税激励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建立科学的监督评估机制,以评估推动加快财税激励政策的落实。
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为了辩护而辩护。现有的对国际关系大理论的许多指责是不合理的,没有搞清楚大理论所要解释的对象,同时也把国际关系大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混为一谈。显然,大理论是学科的主体,但是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发展出许多欣欣向荣的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理论发展的停滞也不意味着理论的无效或者过时,它很可能只是表明该学科的理论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谈不上衰落或者终结;已经终结的只是国际关系大理论的研究,即针对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实力分配、国际制度和政治文化)和结果(体系稳定性)的理论研究。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已经穷尽了科学研究的本体论维度,因此不太可能再发展出来具有新的本体论和范式意义的宏观理论。但是,国际关系大理论仍然是我们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工具,而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发展则方兴未艾。
一、理论停滞不等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衰落
国际关系学起源于对一战和二战巨大灾难的反思。人们迫切需要这样一门知识,来告诉他们为什么战争会反复出现、如何才能有效地制止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国家间军事冲突?因此,战争与和平问题构成了一直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在国际关系学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个过程中,界定该学科的研究领域是最重要的起点,而系统性的、甚至是简明优美的专门理论的出现则是可以算告一段落的终点。用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的话来说,一种理论是对某种行为领域的组织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间相互关系的描述。一种理论要说明某些要素比另外一些要素更为重要,并且要详细阐明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6)[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前言”第15页。一门社会科学总是先界定自己的解释对象,然后提出经过严格锤炼、检验的概念和因果机制假设。这些概念和逻辑就构成了本学科的共同知识。
值得强调的是,国际关系理论解释的对象是国家间的互动结果(冲突或合作,成败输赢),而不是某个国家为什么会采取某项政策。肯尼思·沃尔兹反复强调,国际政治不是外交政策。(14) Kenneth N.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Studies, 1996,6(1): 54-57.原因在于,影响外交政策的不仅有结构性的,还有其他很多的国内政治和个人因素。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对象是有误解的。例如,许多学者认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主要逻辑都是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是在无政府条件下,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类似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建构主义认为政治文化,影响国家行为。这本质上是把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混淆了。正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被混为一谈,国际关系理论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人们指责国际关系理论无法为外交政策服务。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指出了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因素,已经为国家的战略选择指明了方向。但是,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不试图去充分地解释各种丰富多彩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国家对外行为。
人们常说,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它所提供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学生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就应该放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去实施。因此,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积极地在课外搜寻有利于字词学习的探究活动,让学生在探究中学习,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字词之美,感悟中华文化的精髓,从而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激发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衰落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过去十年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步伐似乎陷入了停滞,再没有出现过原来的“范式间大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而学者们进行纯理论研究和理论导向研究的数量也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针对具体案例的假设验证式研究,而这些研究旨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但是,理论发展的停滞并不能等同于理论的衰落,因为这有可能是理论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的缘故。对此,本文的下一节将予以详细的说明。事实上,大理论层次的创新也不是没有,例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试图将量子力学的思想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强调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教授提出了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关系理论”。(7)Alexander Wendt, QuantumMindandSocial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些大理论性质的研究未必比现有的理论更好,但是这至少表明,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滞。
笔者认为热奈特对于戏拟的定义较为准确和全面:“戏拟是对一篇文本改变主题,但保留风格的转换。”(萨莫瓦约,2003:47)戏拟是后现代派作家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他们通过对传统的叙事模式、技巧;历史人物、事件;经典作品中的人物、主题等进行模仿,使其变得荒诞、可笑,以达到对历史、传统、经典进行讽刺和否定的目的。
对国际关系理论自身及其应用范围的误解,是导致许多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死”的主要原因。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国际关系大理论,并不企图解释一切和国际关系有关的问题。相反,国际关系大理论只解释国家间关系中的少数重大问题(或规律性的现象)——如一战和二战为什么会发生、美苏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冷战、势力均衡的游戏为什么会反复发生。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与国际关系有关的重要现象,但这些不是国际关系所要解释的专门领域。
新出现的理论未必就是好的理论,旧的理论未必就是过时的。不同的理论揭示的是现实世界的不同方面,解释力有大有小,不能简单地认为旧的理论就是不好的,新的理论就一定会超越旧的理论。国际关系学者们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种,但是新出现的、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与真实世界的距离更远、更缺乏解释和预测能力。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很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理论的多元化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符合一定的方法论要求,而现实主义仍然可能是未来我们的概念工具箱中最有用的工具。(8)Stephen M.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Policy, 1998,(110):42-43.
莱克支持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的“分析折中主义”,即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应该使用不同的理论,而不是局限于一种理论。(18)David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2013, 19(3): 580,567-587.这一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李少军也持有相同的看法。(19)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页。在解释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要结合几种理论,建立一个针对该问题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假设模型(这些本质上就属于中层理论或者微观理论),但这恰恰说明“主义是有用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曾经指出,“即使人们想从大脑中摈弃理论,这也会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如果没有理论或者某些暗含假设、命题——虽然它们只是理论的粗陋替代品——的帮助,人们根本无法处理世界政治的复杂现实。”“甚至一个有限的、部分的理论——仅仅包含少量命题和一些指导性说明——也是有用的。”(20) Robert Keohane,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5.
二、理论解释力的局限与大理论研究的终结
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国际关系大理论是无用的,因为它们的解释力非常有限,所以应该终结对这些理论的使用。这些批评大多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些指责往往以国际关系大理论来指代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大理论、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第二,这些指责往往批判的是某一种理论的不足,但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某个具体问题时都不可能是完全充分的;第三,指责或者误解了所批评的理论自身,或者误解了该理论所能解释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对国际关系大理论的误解是最为常见的,由于不同学者对理论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对这些误解的澄清变得非常困难。
例如,伊多·奥伦(Ido Oren)指出,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什么是“实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极性”(polarity)、“霸权”(hegemony)这些概念都没有共识,因此,对于19世纪的欧洲到底是霸权体系还是多极体系就看法不一。(11) Ido Oren,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R Theory”, 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 2016, 18(4): 6.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无奈的事情。因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非常清楚。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概念界定使用的是“能力”(capability)这个术语,而不是可以被翻译为实力或者权力的“Power”概念。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但是,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把国际结构的概念界定为“权力的分布”。“权力”要么是“让他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是“一种支配关系”,这两者都不符合沃尔兹所谈到的“能力”概念。(12)宋伟:《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21-26页。对于“极”和“霸权”的概念,如果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也是不存在矛盾的,两者都是基于结构来考量。在冷战时期,这是一个两极结构,苏联的综合实力能够达到美国的70%左右,但是美国比苏联仍然强大很多,所以美国是霸权国;而在19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普鲁士、奥地利、法国、沙俄)综合实力上处于同一层次,意味着这是一个多极体系,但是英国的海军实力和经济实力要强大很多,所以英国能成为19世纪的霸权国。单极、两极和多极结构中都可能存在霸权国。
虽然国际关系理论如此重要,但笔者并不认为,为了捍卫国际关系学科的存在,就需要不顾一切去为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辩护。问题在于,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种种指责,大多是没有准确理解国际关系理论自身论述以及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对象、解释范围的前提下所提出来的。
砖子长松一口气,心说不总结、不讨论、不自打、不被打、不哭叫就好,她想怎么唱怎么表演就演唱吧,我洗耳欣赏罢了,再说赵仙童唱戏也确实百赏不厌的。
这里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和其他许多人(包括温特这样的建构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冷战的终结。加迪斯对沃尔兹的批判是,结构现实主义过于强调两极结构的稳定性,而且强调两极之间会逐步从冲突走向合作,因此不能解释冷战的结束。加迪斯认为,这是由于结构现实主义不考虑结构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导致结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13) John L.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Security, Winter 1992-1993, 17(3):32-34.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和冷战结束的理解都存在问题。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冷战的结束,那么这正是因为美苏两极不断从冲突走向合作的结果;如果说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就是把冷战结束和两极结构的瓦解混为一谈。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两极体系是总体稳定的、可以抑制国家间冲突的发生,但并不认为,两极体系的持续时间就一定会比多极结构要长。一种国际结构持续多长时间,这本身是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结构的变化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大国的兴衰。当然,苏联的解体导致了两极结构的瓦解,但是结构现实主义并不需要解释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联解体是一个内部的进程,其发生与苏联的内政外交都有关系;结构现实主义可以解释一部分,但苏联为何解体本质上是一个内政问题。
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理论的掌握,构成了国际问题研究者们的共同话语和共同知识。当我们分析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时,我们很自然地会使用这些概念和逻辑来帮助我们思考,例如,当我们考察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时,现实主义告诉我们要关注到该进程内的各成员国的实力分配——缺乏具有足够优势的大国主导,是东盟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会从东盟的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以及复杂多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提供分析的思路。尽管持不同理论立场的学者对这些要素重要性的判断不同,但是理论是进行实证研究的指引,它有助于我们去敏锐地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提出分析的框架。这些分析框架就是将各种理论所强调的要素和逻辑应用于具体情境的结果。
同样,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现实世界许多重大发展也是基于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范围的误解——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世界学或者全球学,不致力于解释所有的全球性现象,例如气候变暖。戴维·莱克很动情地谈到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包括全球化撕裂各国社会、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跨国恐怖主义将地方性冲突升级为全球性冲突、气候变化仍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等等。(15)David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2013, 19(3): 580.但问题在于,这些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家间的合作,国际关系理论可以部分解释这些问题的蔓延或者消失,但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提供足够的建议。这些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有赖于不同行为体的共同努力和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合理的;就算国际关系理论告诉国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但现实世界中这些条件并不一定存在或者成熟。
相比于当下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维码,二维码在信息容量上占据极大的优势,其信息容量是一维码的几十倍,通过编码能将文字、图片甚至音频等数据以信息化的方式表示处理;另外,二维码具有超强的纠错功能,即便二维码出现一些局部损坏,比如污染、缺失、穿孔等都能被正常无误的识读,甚至在损坏面积高达50%时还能将译码错误率控制在千分之一内。就目前二维码的应用现状而言,其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相当迅猛,所以综合考虑二维码的应用优势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建议将便捷性更高的智能手机作为移动端,尽量避免使用常用于工业领域的RFID技术。
三、问题导向不等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
的确,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理论疲惫或者说理论厌倦,即十分厌倦“国际关系理论”这个词,很多人都认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例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戴维·莱克(David Lake)就强烈否定所谓的“范式间辩论”,认为这是“宗派性的”“病态的”——每一理论的信奉者都不顾一切为自己信奉的理论辩护,否定其他理论流派,这反而偏离了对真正重要的事务的关注。(16) David A.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2011, 55(2): 465-480.莱克认为,“无须为理论的终结默哀,如果我们所说的理论指的是国际关系的大辩论的话。”(17)David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2013, 19(3): 580,567-587.莱克的观点指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数次大辩论(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一发展历程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即理论家们陷入了各种相互的否定辩论,但却不能有机地使用各种理论来综合分析、应对现实世界中的重大问题。
因此,莱克所谈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其实仅仅指的是“大理论辩论”的终结,因为他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争论是无意义的。事实上,他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没有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它们只有解释力的强弱之分。而过分的“范式间大辩论”却走向了论证理论对与错的死胡同。尽管现实主义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很多具体的案例中,它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例如,单靠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东盟为什么能在没有地区大国提供领导和公共产品的条件下仍然比较顺利地建成了形式上的经济共同体。但是,莱克对于“范式间辩论”的否定也只是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对于理论自身的发展来说,理论之间的互相质疑、对对方逻辑和证据的批判,都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澄清该理论的概念、逻辑、证据和解释范围。“范式间的辩论”从这个意义来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虽然国际关系的大理论研究陷入了相对的停滞,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也在不断取得进展,这些进展主要表现在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等方面。学者们围绕着联盟、威慑、制裁、反恐、和解、国际秩序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这些问题由于与现实外交政策联系紧密,也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9) 例如,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对国家间如何实现和解做了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同时运用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许多研究也值得关注。参见:[美]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宋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的深入发展,需要国际关系理论回答和解释的问题并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多。作为原来旨在解释“少数”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理论,目前面对的重大问题是增加了,例如如何改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规避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欧洲一体化为何停滞不前及其未来的方向何在,等等。国际关系的规范性研究仍然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从国际关系理论向外交政策理论的转向十分明显,也发展出来了许多丰富的研究成果,包括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三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理论流派。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所提出的强调道义重要性的“道义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10)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再一种是“被动形式主义”。不想去干事,只为不出事。因此就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空推”“空动”。工作计划从网上搜索,工作经验从网上复制,工作日志在手机上完成。该说的都说了,该报的都报了,该做的工作却只落实到了纸面上、照片中、圏群里,实际上都是虚的,但无论谁来,也抓不到我什么把柄。
的确,蒂姆·邓恩(Tim Dunne)等三位国际关系学者观察到,范式间的理论争论越来越少,纯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少,但是在过去五年间,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理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属于“理论测试”或者“理论验证”(theory testing)的研究。(21)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2013, 19(3): 406.但这与缺乏理论指引的、纯粹技术性的“假设验证”问题导向研究仍然不同。2001年后,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大量资助在消解国际关系领域理论中心地位的同时,促进了“假设验证型”的实证研究。不过,技术性研究占主流似乎也没有取得丰硕的成果,即美国的顶级安全官员们指责这些更技术性的研究是无关紧要的。(22) Paul C.Avey and Michael C.Desch, “What Do Policymakers Want from Us? Results of a Survey of Current and Former Senior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ers”,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2014,58(4):227-246.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恰恰是因为有些“假设验证型”研究是更偏技术而缺乏理论指导,导致其陷入了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所说的“简单化的假设验证型”研究。一方面,这种“简单化的假设验证型”(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研究导致不同的研究处于一种碎片化的案例研究状态,无法为知识的积累提供帮助;(23) Benjamin J.Cohen, “Are IPE Journals Becoming Boring?”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2010, 54(3): 887-891.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国际关系本质和逻辑的了解,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假设研究往往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并不会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而是应该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反过来,抛弃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纯技术性研究很容易犯常识性的错误,出现破碎化、片面化和彼此自相矛盾的情况。从政策角度来说,将国际关系大理论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出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和吸引力的中层理论与微观理论。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指出,这种简单化的假设验证不承认理论的指导意义,而是通过搜集材料、提出假设进行验证,但是,对理论的轻视导致了对关键概念的误解、对方法的误用以及对于经验模型的错误解读,因此这是“一个错误”。他们举了同一位学者的三个前后自相矛盾的研究来说明。这位学者在2009年的一个研究中发现,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无差别暴力”(indiscriminate violence)手段是反抗减少的原因,而他2010年的第二个研究则发现,车臣本地军队的镇压行动比起俄罗斯军队或者俄罗斯—车臣混合部队的镇压更为有效,原因是车臣本地军队更能有效地区别对待当地的人口。该学者与另外一个学者合作的第三篇论文则认为,依赖于机械化的军队可能增加国家失败的风险,但这一结论又与第一个研究是相矛盾的,因为第一篇文章中,俄罗斯军队是高度机械化的、采用无差别暴力,所以导致了反抗的减少。(24) Jason Lyall, “Does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Incite Insurgent Attacks? Evidence from Chechnya”, 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 2009, 53(3): 331-362; Jason Lyall, “Are Coethnics More Effective Counterinsurgents? Evidence from the Second Chechen War”,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2010, 104(1): 1-20; Jason Lyall, Isaiah Wilson,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s: Explaining Outcomes in Counterinsurgency War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2009, 63(1): 67-106.
四、理论发展的极限与大理论研究的终结
大理论研究为何陷入停滞?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发展出来新的大理论?许多中国学者对此非常关注,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情结,希望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种情结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一定层次的理论研究总是有其极限的。不是理论自身终结了,而是理论研究成熟了、到达了其极限,所以相关的研究就“终结”了。
尽管服务量不断增长,但是因为管理效率提升,医院的检查预约时间逐步实现精准化。过去,患者的候检时间往往是“上午来或下午来”,比较模糊;如今,时间精确到更具体的时间段,患者只需要提前30分钟到医院即可。
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解释对象和解释范围;这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限度或者说极限。理论发展不会是无限的;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基于各种基本的范式条件(哪些是主要行为体,存在哪些基本的结构性制约),出于建立科学理论的目的,理论的发展一定有其限度。这一限度是与物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限度相一致的。例如,相对于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物体质量固定不变的基本前提,指出物体质量随着物体的运动速度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打碎了绝对空间、绝对时间、质量等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这是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未知的物理世界。但是,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而言,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低速运动的世界,物质的质量是确定的,量子力学的基本论断并不适合我们这个世界。物质主义、实证主义仍然是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面对着核武器、监狱这样一些基本的现实,人们的主观观念仍然是有能动性的,但是它必然受到现实世界的制约。
物质主义本体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表明,范式的创新不是无限的。一种关于国际政治的唯心主义学说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如中国古代的预言如《推背图》《烧饼歌》,但是我们不会认为这些是科学知识,因为它们不符合实证主义的要求。我们无法通过具有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的研究对它们进行检验。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三种主流理论,原因在于它们符合了科学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要求,提炼出了三个具有可观察、可测量的体系要素。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它们都属于物质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性力量,物质主义色彩非常强烈;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是国际制度,物质主义色彩一般;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作为社会事实的集体观念,物质主义色彩偏弱。但无论如何,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现有的这三大理论已经穷尽了人类思维所能发现的国际体系要素;如果再往前面走,那么就是后现代主义、唯心主义的地盘了。
政治文本中的隐喻翻译研究——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卫明高,余高峰,乔俊凯 40(2)120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关系大理论的研究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我们很难想象,在当前的条件下,还会出现“范式的革命”。如果有一天上帝被证明存在,那么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的范式。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本质上已经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在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构成的研究领域中,国际关系有没有出现其他的范式变革可能性呢?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事实上,传统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这就是一种不同于现有三大理论的范式。但问题在于,无论跨国公司现在有多么强势,它们似乎还远不足以让我们的国家间政治变成“公司间政治”。
冷战终结了,经济全球化还在继续发展,但国家间政治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从两极结构向单极结构的转换导致了大量国内矛盾和区域性矛盾的凸显,但这恰恰是结构变化的结果。所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张建新和刘丰都认识到,现实世界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难以为知识增长提供足够空间。(25)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27页。尽管一些学者们努力从历史中寻找启迪,但“围绕主权领土国家而出现的概念和问题群已经设置了这样一个特定的议程,以至于难以把其他时代(其构成单位完全不同的时代)里的智慧应用过来。”(26) [美]伊弗·B·诺伊曼、[美]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10页。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强调应该研究阿拉伯之春中的个人的作用,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一场社会运动,并不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我们也无法因此而建立一种国际政治的个人理论。(27) Christine Sylvester, “Experiencing the End and Afterl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2013, 19(3): 620.国际关系理论能够部分解释阿拉伯之春,但绝不是全部。
许多人惊呼特朗普上台后国际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化,其实这些变化只是从过去几十年的自由主义大潮向现实主义回流的一种趋势。对于美国这样的强国来说,它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有利于由政府来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从而会在长期的竞争中丧失自己的霸权地位。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显然更看重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这是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观点。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一直是复合型的,有现实主义的成分,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也有建构主义的成分。世界也许正在变得更加多样,但这种多样性并不能掩盖它内在的一些基本的国际政治规律,反而受制于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说,阿查亚所认为的“我们应该忘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论断显然是误导性的。(28)[美]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16-17页。理论并未终结,但理论发展有其极限。
结 论
尽管国际关系大理论创新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但国际关系理论自身仍然富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表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许多新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不完全属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范畴;这种生命力也表现在,国际关系大理论正在逐步被运用于各种中观层次、微观层次的研究,并得出更多具体的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这种生命力还表现在,国际关系大理论也正在被现实主义学者们转换为外交政策理论和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从而逐步取代原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提出新的规范理论。因此,大理论不仅没有死,反而是不断拓展自己的枝叶、深化理论的研究议程。
“范式间大辩论”的终结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大理论的建构已经基本完成,不再存在明显的瑕疵,接下来的任务,不再是理论之间的相互攻击和否定,而是运用这些经过反复辩论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在现有理论仍然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前提下,“范式创新”的意义似乎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对于许多强烈否定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来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不了解理论的可证伪性(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真理,解释范围都是有限的),或者对这些理论的掌握并不准确。许多人并没有认真读过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就简单认为这种理论是简单的扩张性外交政策理论。事实上,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现实主义;一味地扩张肯定是愚蠢的战略。尽管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强调国家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但并不是主张连续不断的对外扩张。“大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均势以及其他国家对它们行动的反应。它们将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与可能的利益之间的得失。倘若利益不足以抵消危险,它们会按兵不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2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唐小松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页。过度的扩张,恰恰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大国衰落的根源之一。我们无需为国际关系大理论发展停滞或者终结感到悲伤,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对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掌握仍然存在不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剖析工作并没有真的完成。
对于许多希望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来说,也并不需要为难以创造出新的中国特色大理论感到苦恼,因为在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以及在外交政策理论和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等方面,仍然存在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在这些领域,有可能发展出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理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能够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宝贵的指引,因此我们总是期待更有解释力、更简洁优美的理论出现。
TheProspering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theEndofGrandTheoryStudies
Song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Keywor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rand Theory Studies; prosper; end
[Abstract]Although there has been no major innovations in the Grand Theory Stud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in decline or in an end. The stagnation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s because the existing theories are still effective, and mature, and thu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new major innovations. The issue-oriented research tendency does not mean theory has been given up; it means a transfer from grand theory studies to middle level and micro-level theoretical studies. The issue-oriented research must be directed by Grand Theories,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level and micro-level theories. Many viewpoints which think theory has declined or been ended misunderstand the explanation scope of theory and the theory itsel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xplains the interaction outcome of states, not state behavior. It is a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that since Grand Theories could not serve policy making, they should be abandoned. There are limitations for the explanatory power, scope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y. The existing scientific theories have found all systemic factors which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materialism and positivism, and thus the Grand Theory Studies have end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level and micro-level theories, normative theories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作者简介]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刘蔚然]
标签:理论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现实主义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 结构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外交论文; 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0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