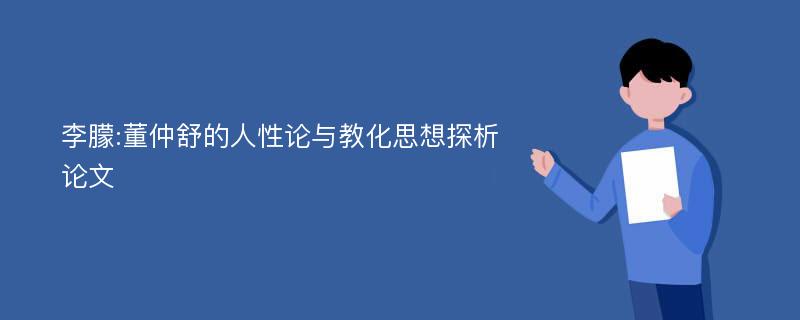
[摘 要]董仲舒作为西汉儒学改造与发展的关键性人物,统合融通了先秦时期的人性同一说,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人性品级说,对之后各家对人性的论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董仲舒“教化思想”以其人性论为理论依据,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体系核心,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迎合了汉初统治者安定民心、巩固政权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人性论;教化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家在论说和阐释自己的教育思想时都离不开谈“人性”,有关人性之说便形成了“人性论”。尽管不同的教育家人性之说各异,但大体上都是对人的本质属性所做的界说,其中一部分包含着对人的品性能力的判断,另一部分则带有对人的道德属性的认知,而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体对教育对象与教育目的等内容的认识,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教育观。
一、性“未善”而分“三品”
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孟子与荀子就人性的论题提出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对立观点,即“性善论”和“性恶论”。孟子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荀子认为人天生就有各种“欲”和“情”,不加引导便滋生暴乱,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董仲舒作为西汉硕儒,对先秦儒学的传承和改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人性论也是对先行的人性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承袭和融通。
就人性的主旨内涵来说,董仲舒有言:“今世闇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反试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1],“性者,天质之朴也”“性者宜知名矣,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1]177,“性者生之质也”[1]306。也就是说,人性是指人生而有之的天然之资,是人天生的本质,不具任何指向性,在范围上具有广泛的普遍适用性。究其善恶,董仲舒提出“仁气”与“贪气”的概念,即“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1]172,所谓“仁气”,是指人天生而有的那些向善的本质,而“贪气”则是有悖于或者不利于封建社会道德、恶性的本质。由此,董仲舒便把善、恶两种倾向同时赋予了人性。之所以说是“倾向”,是因为董仲舒还对“性”与“善”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也就是说,“仁气”与“贪气”并不是人性发展的最终结果,而是人性之始,是人性发展的不同可能性。就性与善的关系而言,“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1]177,性是善的始基,为善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善是“仁气”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而成的结果。所以,性非善或“性未善”,对此,董仲舒以“禾米”为喻,来进一步说明性与善的关系:“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1]176,“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1]172。正是对人性未善的界说,才使得“王教之化”得以存其必要和可能。
董仲舒的人性之说认为,“仁气”为善端,而“贪气”为恶端,人性具有向善或向恶的潜在可能性,但二者在不同个体上的呈现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即不同群体的人性表现也不同。这种论说改造了先秦至汉初人性同一——人非善即恶的观点,开创性地提出了人性品级说,将“性”列为三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和圣人之性。“贪气”主导的人性,难以通过自我制约转而为善,故“斗筲之性不可以名性”[1]177;“仁气”主导的人性,生而向善,即便不经外部的干预或约束也能自而成其善,故“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1]177。因此,董仲舒的人性论所指的“人性”是以贪、仁之气同存,在现实中占大多数的“中人之性”为立论始基:“名性者,中民之性,……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1]177,即“中民”同时具备善与恶的倾向性,只有通过教育、化之王教,才可引中民之性为善,这也正是教育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董仲舒这种对人性分三品的认识打破了人性同一的认知界域,开人性品级学说的先河,对后世王充、韩愈等人性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也曾就人性有所阐释,其人性论由两部分组成。[2]其一,孔子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认为人的天生素质大同小异,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使然;其二,孔子也分人性为三等:上智“生而知之者”,中人“学而知之者”,下愚“困而不学”[3]161。教育只能对“中人”的发展发挥重大作用,这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孔氏的认识侧重于对人的品性能力的判断,而董仲舒的人性论强调对人的道德属性的认知。
二、以“教化”为中心的为政思想
儒家素有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康乐、德治政施的思想传统。《论语》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8,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250。董仲舒结合其人性论,对儒家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1]183,认为国家的治理不能仅靠威慑或刑罚,要依靠教化,以刑罚辅之。
秦王朝的建立与覆灭使汉初统治者们认识到了武力对于政权的夺取与建设所具有的不同意义,秦王朝通过强有力的武力征讨统一六国,政权建立后,接纳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继而推行暴力政治,使得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传袭了仅仅两代之后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武力杀伐可以建立政权,但维护政权的稳定绝不可仅仅依靠严刑峻法,由是便改变秦通过暴力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以巩固政权的策略,转而以“清静无为”、推行教化为治国思想的指导。董仲舒以“教化”为中心的道德教育思想,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理论内核,在汉初统治者欲求巩固新生政权的基础上强调教化,这进一步明确了教化在治国方面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被官方认可并得以推行之后,不仅影响了汉代统治,而且对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权的巩固与更迭也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一)“教化”的人性论依据
我国目前城乡供水体系基本处于一种相互割裂的状态,传统城市供水对象及区域主要针对城区生活及工业用水,其特点表现为自来水厂相对集中,水处理规模较大,水质及水量保证率较高。与城市供水相比较,广大乡镇供水的主要特征为:水厂数量众多,规模小,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和系统协调管理,水质及水量保证率较低,安全隐患较大。
“端具有转而为善的趋向”说明了教化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而教化何以必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指明,斗筲之性与圣人之性皆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主以“贪气”,是至恶之性;圣人之性主以“仁气”,是至善之性,但无论至善还是至恶,这两种人性即便通过外界干预都是难以改变的。此外,这两种人性的呈现主体是现实中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具有“中民之性”的“中民”。与前两者相较而言,中民之性既不是至善,也不是至恶,仁、贪二气兼而有之,并且其性可以通过教化发展为善。反之,这种善端倘不经教育,也难以达成。所谓“性如茧如卵。卵待覆(孵)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1]173,即性不教难为善。综合来看,“中民”在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且“中民之性”不加教化是难以转而为善的,由此,教育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教化”思想,之所以在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有其人性论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迎合了汉初统治阶级休养生息以稳定政权的需要,显现出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教化”的现实意义
(1)Th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level among primary students isvery low.
碎片化学习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微课直播这种教学模式能够将大量分散的、不连续的、碎片状的时间整合起来。定时直播的方式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学习时间,在零碎的空闲时间里进行小的知识点的学习,进行知识整合。即时直播的同时,教师也能够通过学生的评论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便于制订更加合理灵活的教学计划,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教化”思想的核心
儒家伦理道德是董仲舒教化思想体系的核心。在汉武帝举行贤良对策时,他就强调了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重要意义,指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5]210,以道德教化黎民,建立社会秩序,这充分体现了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基于汉代社会的实际需要,他从天人观和人性论出发,统合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使其更加体系化、规范化。“三纲五常”便是对儒家传统道德伦理学说的融通和系统化。通过对一系列道德教育内容的阐释,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以规范,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的终极目的。“三纲五常”强调社会中的等级名分,是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的系统总结,对汉代及其后的封建统治提供了思想精神依据,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传承关键一步。
董仲舒的人性论对“性”与“善”做出了区分,指出“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也就是说,性有善端但并不是善,这种善端具备一种发展成善的趋向,即存在可以通过教育引人性转而为善的空间,这就为教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与重力场特征类似,本区高山岩体和宝山岩体的磁场值相当,均为-140nT左右,亦说明两岩体可能同属深部相连的同一个岩体。此外,北部边界近东西向的半椭圆形负磁异常可能为区域性构造所致。
在确定了社会整体所必需的道德伦常之后,董仲舒还指出了个体应遵循的道德修养规范,即“仁”与“义”:“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1]142,要求大众以“仁者”之心宽容、关爱他人,以“义者”之心规约自己,即以仁待人,以义约己,强调个体对“生命价值与权利的尊重”以及对“社会和其他个体的责任与义务”[2]119。此外,董仲舒倡导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这也是对先秦儒家传统仁政及其所宣扬的理想人格之说的继承与发展。
三、结语
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儒学传衍的关键性人物,对传统儒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人性论统合了先秦时期普遍流行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开“人性品级说”的先河。其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以他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迎合了西汉政权建立之初统治者稳定国势、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从另一层
面上来讲,正是汉王朝国家统一的局面为董仲舒儒学思想的弘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用武之地。由此,董仲舒得以利用孔、孟、荀所不具备的外部环境条件,一举将儒家学说推向了政治地位的高峰,基于此所推行的兴学、养士的文教政策也为汉代文教事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对中国古代教育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三策[M].陈蒲清,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7:171.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
[3]孔丘.论语[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164.
[4]孟轲.孟子[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250.
[5]班固.汉书[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22.
[作者简介]李朦(1995-),男,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8-0085-02
[收稿日期]2019-05-11
[责任编辑:白彩霞]
标签:董仲舒论文; 人性论论文; 人性论文; 儒家论文; 思想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汉代哲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论文;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