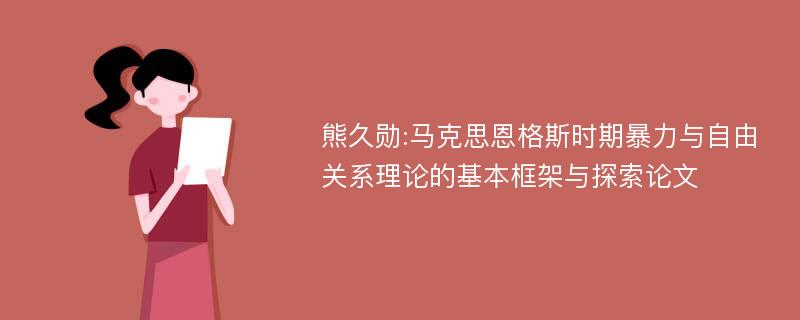
●经典品读
摘 要:暴力与自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十分重要的两个理论维度,一方面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另一方面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所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正是在这一基本理论判断下,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探索逐渐走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变革之路上。马克思主义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的形成和确立,一方面回击了所谓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虚伪自由;另一方面,指明无产阶级在阶级社会历史条件下取得自身解放和自由的根本道路。可以说,剩余价值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则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之基。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基本确立了暴力与自由关系的总体框架和辩证关系,指明作为理念的自由和作为实践的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暴力革命对作为实践的自由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力;自由;辩证法
国际共运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发起的,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持推动的国际性共产主义运动。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第一国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指导建立了第二国际。这些国际性政党组织,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理论指导工人运动实践的重要载体,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中迈出了第一步,走了很多从没有走过的路,在实践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特别要指出的是,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指导了巴黎公社革命,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理论经验和教训。第二国际中,虽然马克思身体状况不好,但仍然坚持对国际的理论思想、组织实践指导。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典型性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血与火中不断夯实理论认识,检验理论科学性,并总结出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来捍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这一重大历史经验及其规律,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为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
1847 年,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阶级在同盟的领导下进行了初步的组织建设,并在组织工人活动中锻炼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同盟的建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当时西欧工人运动的初步实践,标志着国际层面的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组织领导同盟的时候,着力清算驳斥了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夯实了同盟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和指导思想,保证了同盟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人运动和组织斗争工作。在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宣言》作为同盟的正式纲领性文件首次发表问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阐发了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进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和自由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的基础。随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发展了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有着鲜明的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他们对执行暴力的主体、暴力革命的条件、获得解放的途径以及实现最终自由都有十分深刻的论述。
一、暴力革命是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的唯一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议会和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最终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1]302;议会只是证明了阶级对立,它不可能产生“利益和解”。议会这一阶级对立的产物无法消灭自身,只会诱发新的层出不穷的矛盾,阻碍无产阶级解放与自由的实现。消灭这一矛盾根源的方式,就存在于彻底的暴力革命来推翻现存的一切压迫制度。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暴力革命不是布朗基主义。一方面,不盲目采取暴力手段,坚决避免极左派和冒险主义的不自量力,避免无意义的暴力导致的流血牺牲,是站在工人阶级生命安全和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制定的科学革命策略,体现对广大无产阶级和群众自由的根本关切。毫无价值的流血牺牲和投机冒进注定的失败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自由的实现又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一切剥削制度和压迫,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广大劳动者的最终自由,恩格斯指出,“除用暴力的民主革命外,不承认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这些目的”[2]58。
马克思主义强调用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式,而是构建于复杂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规律性认识。暴力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拿起来就能打碎什么,修理什么,建造什么。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命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力与和平选择。对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自由这一终极价值而言,暴力革命“体现了他们(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与传统哲学和传统社会相决裂的决心”[3]15。显然,这一决裂扬弃了以往形而上的自由论调所制造的实践领域对暴力革命的拒斥。也就是说,以往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对“彼岸”世界的反复论证中,是无根的自由;以往的暴力都是为了建立新的压迫剥削制度,几乎没有突破过暴力革命实现自由这一“卡夫丁峡谷”。这中间的鸿沟与断裂正是由马克思主义暴力与自由关系理论来实现弥合的,即经由暴力革命实现政治革命,进而依靠无产阶级的专政进行社会革命来实现人的最终自由。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实践环节就在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统治地位,重塑社会制度,经由社会制度孕育自由之花,进而结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之果。《共产党宣言》也就是在这个理论维度中确证“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4]479。在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改良主义、阶级调和的观点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十分有害,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504。马克思强调,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479,而夺取政权的唯一现实途径就是暴力革命。
3.3.1 性别 国内外对配偶间HIV男女传播概率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男传女高于女传男[11],也有女传男高于男传女[3,20],或HIV 传播与性别间无统计学关联[8],这种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可能与研究对象所处社会环境、个体特征、行为特征或生物学指征不同有关,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
马克思在1852 年一封给约·魏德迈的个人书信中评价自己的贡献时说到,自己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必然性“(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426。这是马克思早期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历史定位的一段论述,从理论上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地位,区分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专政与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本质区别。其中,马克思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地位,并指明只有这一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首先,马克思指出,政权必须交由无产阶级掌握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斗争中,都把国家机器夺到自己的手里,“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并使之不断强化,以便为他们的剥削制度服务,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国家“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6]761。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将政权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6]760,把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摧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铲除一切压迫机构,取消旧官吏,彻底抛弃压迫人民的政治、法律等旧制度。其次,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以往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而需要对这一机器进行无产阶级的改造。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价值取向上。一是阶级属性,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剥削者的专政,而不是对广大劳动者的专政,“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基本形式”[7]28,这种形式在实现无产阶级自由之后也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二是价值取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进而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6]532,最终实现最彻底的社会革命,变革一切生产关系及其产生的整个上层建筑,实现真正的自由。
以往模式中很难对业主的责任进行集中化划分,不能明确地指出。对于EPC工程的总承包模式来说,虽然一直是五方主体的责任不发生变化,总承包的企业还是需要承担总体责任,一旦工程涉及到勘测和设计与采购以及施工的问题,那么总承包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设计施工的过程中会发生扯皮问题,EPC模式基础上的问题扯皮是在总承包的范围中出现的,必须要总承包进行内部把控以及管理,因此,对于总包管理制度和核心能力与人员专业提出较高的要求。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控,所产生的风险就要由总包单位进行负责。此时,就需要分包和分包以及分包和主体施工之间协调管理有效地对接,一旦出现疏忽,势必会造成索赔。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无产阶级充分地享有和实现自己的自由,所以马克思才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民主权利和政治解放的国家制度前提”[7]28,进而在这一基础上实现政治革命范畴的解放,为下一步实现广泛的社会革命范畴的自由创造政治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罗许成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作为手段的阶级专政与作为目的的阶级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了”[7]28,指出阶级自由的实现必须具备阶级暴力的支撑,是相当准确的理论判断,这一判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目的因和动力因的双重属性,其动力因在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推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和自由,由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全人类的自由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自由,也就实现了全人类的自由。
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路易·波拿巴王朝在长年的贪污腐败、战争中早已经风雨飘摇,战争一开始就节节败退。战争的爆发带来无产阶级革命难得的历史机遇,马克思先后起草两份有关普法战争的宣言,指导法、德两国工人在战争期间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迷惑,在共和国这一十分宝贵的自由窗口期“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12]72,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充足的条件。马克思告诫法国无产阶级,在普鲁士即将吞并法国的关键时刻,“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12]71,法国无产阶级要首先捍卫独立的共和政权不至于落入封建势力普鲁士之手,才能有条件实现下一步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向法、德两国无产阶级强调,沙皇俄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时刻觊觎着欧洲的霸权,如果法、德两国两败俱伤,则会给封建的沙俄军队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将会对法、德两国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灭顶之灾。因此,全世界的无产主义者都要共同起来采取行动,尽快使本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捍卫这一民主革命的成果。
三、暴力革命的运用始终存在于革命的具体条件之中
1871 年3 月18 日,巴黎工人阶级在工人武装支持下打败了资产阶级的武装进攻,并夺取了巴黎的政权,但没有对梯也尔进行彻底的清剿,导致其逃到凡尔赛。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之后把政权交给群众选举出来的公社手中。3 月28 日,郑重宣告巴黎公社成立。新成立的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巩固新政权,其中有六条十分重要:一是废除常备军,用人民武装来代替,并宣布国民自卫军是唯一合法的武装力量;二是撤除资产阶级旧制度下的法院、警察厅和监狱,建立了专门的暴力机关;三是规定公社委员的工资、产生方式,实行立法和行政的统一,保证人民选举的权力机构捍卫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四是颁布政教分离法令,宣布国家取消一切宗教开支,取消教会的特权,没收教会财产,推进彻底的政治解放;五是恢复生产,提高工资,没收逃跑的企业主的工厂交给工人合作社开工,并最大限度提高工人工资;六是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提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系列举措开创了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先河,具有十分典型的实践意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真正在实际意义上赋予了劳动群众和人民自由的权利和保障。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组成无产阶级军队来保卫新生的政权。但是逃走的梯也尔政府趁机喘息,再一次勾结德国俾斯麦政府纠集反革命力量,发动武装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内战。由于反革命军队的绝对优势,5月21日,梯也尔反动武装闯进巴黎。5 月27 日,大部分工人住宅落入反革命军队手中,在拉雪兹墓地战斗中,最后一批社员被敌人枪杀,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周”。梯也尔反动武装复辟后,先后有三万多人被杀害,五万多人被捕。马克思对公社的存在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12]126。
面对马克思呼吁的“不要用任何暴力反抗可能按行政方式进行的征税”[1]24,更为激进的哥特沙克等人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相信革命,不相信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9]203。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注工人发动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还对当时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指出发动暴力革命必须要认真研究条件的充分性。这其中有两个层面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结合点:一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落后性,导致工人发动暴力革命后极有可能遭受到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起来的反革命暴力;二是工人阶级发动了准备不充分的暴力革命,将导致本来力量就不足的工人阶级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结果有很大风险会将革命的成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导致革命果实被窃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是在资产阶级完成其民主革命之后,再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而非充当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去反对封建阶级统治,让资产阶级坐享其成。事实证明,1848 年3 月18 日,革命群众在包围王宫后与政府军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迫使德皇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组建新的政府,并释放政治犯和解除城内的政府军。但是,新政府在3 月29 日便拼凑了由大资产阶级代表康普豪森组成的包括容克代表阿尔宁-鲍依森堡、贵族地主施维林、银行家汉塞曼以及资产阶级保守派代表、政客为成员的资产阶级和容克妥协的内阁。在这一临时内阁虚与委蛇的拖延期间,德皇威廉四世早已经在3月底将军队调回柏林,革命力量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对此,马克思指出,广大劳动群众应该置身于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外,“等待资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以便利用它们的结果”[8]535。恩格斯也强调,工人阶级去发动起义,“只是为资产阶级、同时也就是为政府去火中取栗”[1]565,广大无产阶级要坚决避免自己被当作暴力工具利用,否则只会导致本阶级进一步丧失自身各项权利和自由,加剧自身被压迫的处境。通过对工人阶级起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分析,马克思提出“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1]38的总体性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强调革命的暴力要讲策略讲方法,而非冒险主义、投机主义,暴力的运用始终存在于革命的需要之中。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作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自由的最终手段,这既驳斥了将马克思恩格斯污蔑为暴力“拥趸”的布朗基主义论调,也驳斥了将马克思恩格斯曲解为改良主义的和平长入论调。
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马克思创建并实际领导国际工人联合会,简称“第一国际”。第一国际成立后,总委员会中负责纲领和章程起草的包括马克思在内的9 人团发生了意见分歧。英国工联主义者试图将国际变成改良主义的争取工人阶级权利的组织,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试图将国际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国际性合作、信贷组织,意大利的马志尼主义想据国际为己有从而成为欧洲工人的“中央政府”。马克思批判了这些错误的思想,指出国际成立的目的在于组成“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5]496而非发展成为狭隘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义或者半社会主义的宗派。马克思强调,必须“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6]391,首次提出了工人阶级武装力量的概念。但出于维护国际团结的考虑,马克思认为必须要制定一个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能够团结英国工联派、法国蒲鲁东派和德国拉萨尔派等工人阶级力量的纲领。《成立宣言》指出,工人阶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量优势,“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2]10。工人阶级的联合依然是革命最重要的原则,而有效的组织则是保证这种联合的重要手段,彻底的革命性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障。
四、无产阶级政党是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自由的领导核心
德国1848 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回到伦敦重新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恩格斯则和同盟的成员维利希留在德国领导一支武装队伍抵抗反动军队的进攻,同盟的领导人约瑟夫·莫尔在革命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然同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革命的洗礼和十分重要的革命经验同样弥足珍贵。马克思在回到伦敦后,立即着手总结革命的教训。《1848 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是马克思在伦敦重办的理论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连续发表的。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的制度下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马克思庄重地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战斗口号,并用革命的实践经验刺破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虚伪性,强调必须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重新积聚革命力量,发展无产阶级的组织,迎接革命时机的到来。
1850年3月,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同盟和工人阶级必须保持自身在组织上的独立,在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时不忘用斗争巩固联合,以捍卫自己的政治地位。马克思在第二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6 月)中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共产主义者同布朗基主义者所联合建立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根本目的在于“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10]605,并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要求。但是,同盟的组织活动已经引起了德国反动政府的特别注意。德国反动政府指控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革命军团,准备推翻德国政府。反动政府借此大肆搜捕同盟成员,并在科伦审判,这就是著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这一伙反动势力无法拿出所谓的证据支撑他们的指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下毫无依据地宣判同盟成员勒泽尔、诺特荣克和毕尔格尔斯等人犯了侵害资产阶级社会的罪行。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情背后加剧的反动迫害,认为需要组建一个更加坚强成熟的无产阶级组织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52年11月17日,同盟在马克思的提议下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经验表明,必须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来领导进行彻底的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自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亲自领导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效集中的组织生活无法得到保证,并且遍布在各个地方的同盟支部与总部的联系受到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所以,除了在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在德国直接组织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以外,其他时期马克思都在反动势力的驱逐下流亡国外开展理论研究和组织生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终解散,也揭露了反动力量的暴力本质。他们不仅用军队,更利用了一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工具扼杀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的运动和组织。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领导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建设及其革命运动高度评价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11]748。
五、无产阶级武装是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自由的关键力量
明代陈益祥说:“流水之声可以养耳,青禾绿草可以养目,观书绎理可以养心。”“观书绎理可以养心”,就是通过观书绎理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滋补和休息。因为,读书可以让心灵变得宽厚和柔软,让心灵获得快乐和舒畅:读书,心才不慌;不读书,心就荒了。
生活面前,心态平和,不抱怨,不悲观,想得通,看得开,好运自然来。这就是一名运气甚佳的的士司机的处世之道。
战争的发生和大规模军队的作战加剧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复杂形势。巴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的指导下,认识到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不被普鲁士封建军队摧毁,所以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掌握的“国防政府”政权,暂时性地承认资产阶级领导。但是,临时政府企图借“国防政府”之名窃取革命果实,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限制工人阶级自卫军的发展。这一图谋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失败了,巴黎工人阶级抓紧这一难得的自由时期,冲破资产阶级的阻挠,一共建立了194个国民自卫军工人营,有将近30万人,并在20 个区分别组成了区警备委员会,同时还组成了20 个区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组织力量和有生力量。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措施是十分正确而彻底的,由于壮大了自身的武装力量,无产阶级在保证劳动者自由和抵抗普鲁士军队进攻上都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支撑。但也正在此时,资产阶级所谓的“国防政府”暴露出了彻底的反动卖国面目。在20 万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期间,资产阶级秘密勾结俾斯麦,直接与普鲁士政府签订了临时合约,把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全部割让给普鲁士,赔款五十亿法郎,以出卖法国国家利益的条约换取俾斯麦释放资产阶级被俘军人,并提供武器装备协同镇压巴黎公社。马克思后来辛辣讽刺说,“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12]76。
再次,可以利用JSP+HTML+TOMCAT模式与Solr-Cloud技术对所应用的服务其进行布置,并构建起B/S服务环境与适合数据仓库使用的系统。在相关技术的支持下实现对数据的注册、输入以及快速搜索及信息导出等。最后,用户可以利用系统成果数据构建起地理成果数据库、基础数据成果数据库等,并可以通过关键字的输入查询到所需要的地理信息。
1847 年底,德意志各个分裂的邦国遭遇到严重的农业减产和经济危机,导致了四处涌起的罢工潮和饥民暴动。而正在此时,远在巴黎的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德国参加暴动的无产阶级。1848 年4 月初,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到达当时德国的大城市科伦,亲手指导工人阶级发动暴力革命,并通过创建《新莱茵报》进行理论的教育和宣传。马克思根据当时德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条件,指出在德国占据极大优势的力量仍然是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无产阶级革命无法通过一次革命实现,要坚持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清除封建势力,先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而创造更为成熟的条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暴力革命手段的选择上依然是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们强调在无产阶级处于弱势的条件下避免与实力强大的资产阶级暴力机关发生冲突,恩格斯在《科伦在危急中》呼吁不给“拥护旧普鲁士的政党提供任何足以被用来使科伦受到横暴的军事制裁的借口”[8]69-70,马克思随后也在《柏林的反革命》中强调利用“拒绝纳税”[1]20反抗政府的武装镇压。
“为了满足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20世纪50年代要将各种电压等级从最高22千伏统一升至35千伏,每天忙得头疼;六七十年代随着时代发展需要,又逐步升到110千伏和220千伏,只用了十来年甚至就是几年时间,且昆明电网一直保持着西南甚至全国高海拔地区,最早设计投运当时国内最高电压等级的纪录。”回忆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专家覃国成对许多细节记忆犹新,很是自豪。
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组织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真正实现解放和自由。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与威慑力甚至促使资产阶级不惜进行卖国的勾当也要消灭工人阶级的武装。梯也尔控制临时政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防政府”的幌子下遣散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为资产阶级下一步镇压工人、与普鲁士进行媾和创造条件。而巴黎工人的应对则十分正确,就是用革命的暴力打败反革命的暴力,夺取政权并将之改造为工人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巴黎工人用枪杆子保卫了自己的政权和来之不易的解放。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帮共和主义骗子手里”[12]152,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12]1006。恩格斯也指出,公社把“武装人民”这个权威“用得太少”[12]277,正是由于公社没有充分运用革命的暴力,导致反革命的暴力得以死灰复燃,纠集更大的力量,最后倾覆了流血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葬送了流血争取的解放和自由。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掌握自己的武装,以革命暴力消灭反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1872 年9 月,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马克思在会上指出,虽然有些国家的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实现自己的解放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13]179。正如恩格斯说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是用“非常权威的手段”推行阶级的意志,“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2]277。
六、暴力与自由辩证法的核心统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6]527
1848年的德国革命深刻揭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切改良主义者的真实立场和态度。马克思认为,只有不断革命,才能实现广大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消灭一切有产阶级,才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在此基础上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消灭剥削、消灭无产者之间的竞争,掌握决定意义上的生产力。首先,马克思指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建成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必须进行最彻底的暴力革命,“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6]560,消灭阶级和阶级矛盾、建立新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灭暴力根源。方章东认为,虽然“民主改良是社会革命的合法手段”[14]180,但在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手段”[14]185。“不断革命”的思想突出表现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彻底性和先进性。这种彻底性首先要求推翻一切剥削压迫的制度,打碎一切禁锢人的牢笼,实现政治范畴中彻底的解放。其次,推翻一切压迫剥削制度及其统治之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需要进行不间断的革命与自我革命,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就把革命停顿下来,使革命半途而废。最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不是革命的终结。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应该凭借自己手中的政权来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阶级,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恩格斯指出,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通过彻底的暴力革命“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6]595,这样就极大地缩短了无产阶级遭受痛苦奴役的时期,也极大节省了物质生产资料,更极大地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恩格斯在评价1848 革命时指出,法兰克福议会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在它还能左右一切的革命高潮时期,没有一举而坚决地结束同德国各邦政府的不可避免的斗争”[8]265,而正是由于这种犹豫迟缓、拖延不决以及内心中对斗争的害怕,“使1848 年成了空前未有的血迹斑斑的一年,使各个斗争的党派的情况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最后的战斗必然特别残酷和具有毁灭性”[8]483。
1848 年欧洲革命和1871 年的巴黎公社革命都表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不断壮大其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的发展与日益加深的剥削是一卵双生的,积聚的阶级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虽然,反革命的力量可以通过暴力镇压扼杀革命,但同样,逐渐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武装也可以通过彻底的暴力革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是十分昂贵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暴力与自由关系思想,无产阶级军队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自由的最重要的暴力工具。巴黎公社失败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
[3]崔爽.马克思、恩格斯究竟如何理解“暴力革命”?——以《新莱茵报》的时事评论为例[J].理论视野,2014(3):13-1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罗许成.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J].浙江学刊,2009(1):27-3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4]方章东.第二国际思想家若干重大理论争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767(2019)04-008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国民主模式与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研究”(17BZZ084)
作者简介:
熊久勋(1991-),男,河南信阳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高民政(1962-),男,陕西彬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军事政治学。
[责任编辑:姜玲玲]
标签:马克思论文; 恩格斯论文; 无产阶级论文; 暴力论文; 自由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理论建设》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国民主模式与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研究”(17BZZ084)论文;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