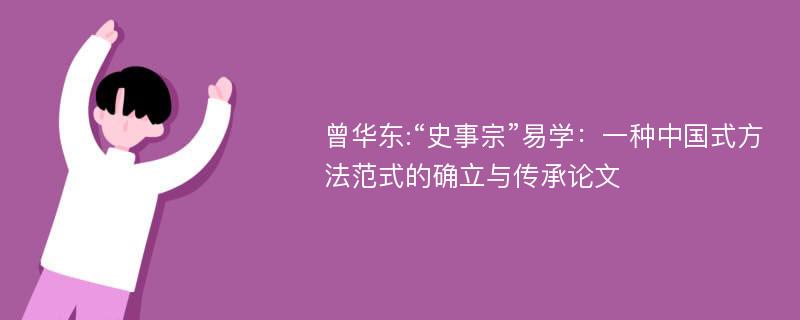
顾炎武《日知录》勾勒了《易》学发展简史,不但泛滥易学的“玄”“理”二家,还清楚看到了“史事宗”这家存在的可能性,并深度揭示了史事“参证”方法在杨万里等《易传》中得到确立,认为“史事宗”《易》学以用《易》为学术趣旨,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高度统一。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但以史证《易》,还由此在其《音论》等著作中推出“广证”“博证”之法,终至形成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疏”“证”相结合的范式。乾嘉学派虽以“复古”“回到汉学”为旗帜,但纯粹“注疏”的方法范式毕竟已成过时的笺注学。后继的乾嘉学者们分别以吴派、皖派大成之作《周易述》《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蔚成了以考据、考证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标示了中国哲学方法范式薪火相传的学术气派。
[关键词]顾炎武;史事宗;乾嘉学派
两宋时期,政治上先后经历了“庆历新政”和“安石变法”,科技上“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发生在宋代。思想、学术上理学昌明,新学、程朱理学、陆学蔚为主流。南宋中兴,首先是文化中兴,大理学家辈出:朱熹、胡宏、杨万里、陆九渊、杨简、叶适、陈傅良等,并产生了易学义理派的第三个学派——由李光、杨万里创立的“史事宗”学派。这个易学义理派的形成,标示了一种中国式“参证”方法范式的最终确立。这位传薪播火者,就是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顾炎武。
研究顾炎武易学早有其人,都为炎武易学做出了有益的学术阐发。本文认为,仍有必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顾炎武虽没有自己的易学专著,但他的《日知录》卷一系统阐述了其易学观点,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易》学发展的简史;第二,顾炎武较早看出《易》学分宗分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甚至为“史事宗”易学这种证、阐与用《易》相结合的范式提出了理论根据。
一、炎武易学与诚斋《易》
《日知录》卷一写了一部易学发展的简史。在这部“易学发展简史”的最后,炎武希冀告诉人们,《易》的源头和归宿均在用《易》或《易》用,当然不是占卜之用,而是教化、人伦之用:“《易》以前民用也,非以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圣人之道也。是以《少仪》之训曰:‘毋测未至’。”[1](P56)
顺着《日知录》卷一的大致目次可以看到,炎武首先关注朱子的《周易本义》,其次关注程子易学和王弼易学,但更看重诚斋易学。顾炎武在《日知录·朱子周易本义》中云:
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1](P4)
在“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1](P9)的讨论中,当谈到“《易》《春秋》尤为缪戾”[1](P9)时,顾炎武归结到“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1](P9)。炎武虽未明确说谁是“后之兴文教者”,但宋代杨万里曾云:
该系统选用GY-MCU90615的红外体温测量模块,该款传感器测量目标范围较大,测量精度以及分辨率较高[5]。Arduino UNO微处理器通过UART串口与该款传感器相连,通过串口实时获取传感器数据,处理后即得到老人的体温值。GY-MCU90615红外体温传感器与Arduino UNO的硬件串口连接,其电路连接如图3所示。
《易》者,箫何之律令,《春秋》者,汉武之决事也。《易》戒其所当然,《春秋》断其所以然。圣人之戒不可违,圣人之断不可犯,故六经唯《易》与《春秋》相表里。[2](第一一六一册,P214)
顾炎武虽言“复程、朱之书以存《易》”,但随后的“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说明他肯定“参证史事”者既在做“存《春秋》”的工作,又在做存《周易》的工作。
顾炎武等乾嘉学派都是排斥图书学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易,逆数也》题下说道:
若如邵子之说,则是羲、文之《易》已判而为二,而又以《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矣。[1](P46)
探寻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开启刊企合作新局面——记2018年《国际石油经济》理事会议暨石油经济信息交流会本刊编辑部 5 98
朱熹是推本图书学的,据顾炎武以上所论,在某些场合顾炎武是疏离朱子的,但对诚斋学的疏离几无。清代全祖望(1705—1755)似遥相呼应,有如下千年一叹:
在《乾·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徳也”条下,程颐进行了折冲和转圜,故有:
顾炎武在其《卦爻外无别象》的讨论中,小结如下:
“史事宗”易学以“参证”方法而赖以存在,乾嘉学派则以“考据、考证”方法而赖以存在。前者对后者有无实质的影响?其实,前面花大篇幅讨论顾炎武的以史证《易》就是要说明这一点。顾炎武不仅在《易》学领域,还率先在其《音论》和其他著作中实践这套方法。延至乾嘉学派其他人物,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周易述》,实际上都是在做“疏证”的考订工作。由此,我们窥见了一条由“史事宗”的“参证”到顾炎武的“旁证、博证”以及稍后的阎若璩等人的“疏证”,再后的惠栋、戴震的学术发展线索。
顾炎武看到了玄、理二家的区别,更看到了诚斋易学的魅力和殊胜之处。诚斋易学的魅力和殊胜之处,说到底,就是基于大量史事“参证”而确立了该方法论范式(显别于其他各家各色参证),并由此建立起了它的易学新形态和新宗派——“史事宗”易学。顾炎武把这种在南宋,甚至在元代都看来很“新奇”①,但也遭到某些人诟议的阐《易》之法,运用到自己对《周易》义理的理解和阐发当中。接下来,《日知录》连续对《周易》的《师出以律》《既雨既处》《自邑告命》三个议题,均“以史证经”。在《师出以律》条下,炎武以“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阐发其“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才是“师出以律”的正判。[1](P15)在《既雨既处》条下,用了隋文帝与独孤后、高宗与武后的故事,来说明“妇制夫,其畜而不和,犹可言也。三之反目……既和而惟其所为,不可言也”[1](P16)的经义。在《自邑告命》条下,用了周桓王中祝聃之矢,唐昭宗用师而犯歧之兵的故事“以史证经”,来说明“保泰者,须豫为之计”[1](P17)。
顾炎武在不到1.5万字篇幅的《日知录》卷一中,直接援引《诚斋易传》的至少有以下几处:
杨氏(万里)曰:“初九动之始,六二动之继,是故初耕之,二获之,初谶之,二畲之。”[1](P21)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安定胡氏改“陆”为“逵”,朱子从之,谓合韵,非也。《诗》“仪”字凡十见,皆音牛何反,不得与“逵”为叶,而云路亦非可翔之地,仍当作“陆”为是。渐至于陵而止矣,不可以更进,故反而之陆。……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与九三同为陆象也。朱子发曰:“上所往进也,所反亦进也。渐至九五极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杨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极;上九,上卦之极,故皆曰陆。自木自陵,而复至于陆,以退为进也。巽为进退,其说并得之。”[1](P33)
疗效评定: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且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完全愈合,被认定为治愈;患者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发生明显改善,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积相比治疗前缩小≥50%,被认定为好转;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未发生明显改善或病情加重,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未缩小或增大。
在《周易·损上九》的解读中,顾炎武更是明确了他的《易》学“厚民”“正民”之旨: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1](P24-25)
如图5所示为正常情况下的回波信号和第一阈值,其中第一阈值与回波信号第1次相交在波峰2,3之间,得到D1点,则TDC-GP22可以分别测得波峰5、波峰6和波峰7的下降沿过零点时间t3、t2和t1,取波峰6的下降沿过零点作为特征点D2,到达特征点时间T为t2。
顾炎武在谈到“厚民之生,正民之德”时,典型地发挥了《诚斋易传·损上九》中的“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实。皆损之上九也”[4](P239)的史事“参证”。与“天下无饥民……天下无冻老……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实”相对应的,是顾炎武的“谷不可胜食也……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进而得出“厚民之生,正民之德”等《易》学观点。而《周易本义》《周易注疏》《周易程氏传》对此几无涉及。《诚斋易传·损上九》曰:
(炎武)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接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9](P12)
《周易本义·损上九》《周易注疏·损上九》《周易程氏传·损上九》均无相关内容,即除诚斋外,各家均没涉及“厚民之生,正民之德”的话题。炎武看到了参证方法在诚斋易学中得到确立,并且,此种易学范式已成为治《易》常态。他认为:治《易》以用《易》为旨,而不是“玄”“无”如王弼学,“天理论”如程子《易》。诚斋治《易》与用《易》的结合,正是炎武信奉的易学趣旨。
下面,我们再看看诚斋易学观与炎武易学观的联系。诚斋说:
古初以迄于今,万事之变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乱。圣人有忧焉,于是幽观其通,而逆绸其图。[4](P1)
炎武说: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之乱。盛治之极,而乱萌焉,此一阴遇五阳之卦也。孔子之门四科十哲,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盛矣,则《老》《庄》之书即出于其时。[1](P26)
此条,炎武与万里的阐《易》几乎亦步亦趋。在《日知录·包无鱼》条下,炎武说:
又说:
万里说:“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时义者也。……初六阴而在下,民之象也。鱼亦阴类,古者以鱼比民。”[4](P256-257)
显见炎武在《日知录·包无鱼》条下的“鱼阴类,民之象”。鱼为民之说来自万里《诚斋易传》,而《周易本义·姤九二》《周易程氏传·姤九二》《周易注疏·姤九二》均未见此说,只有孔疏《周易注疏·姤九四》有“《象》曰远民者,阴为阳之民,为二所据,故曰远民也”[5](P246),《周易程氏传·姤九四》有“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6](P254),但二家均未涉及“鱼”为“民”之说。
无独有偶,“史事宗”另一家——李光在其《读易详说·姤九二》中亦训“鱼”为“民”:“二远君而近民,五阳在上,一阴在下,故初有民之象。”[2](第十册,P391)由此不难窥见,“史事宗”二家有共同的学术趣旨。
顾炎武借说《易》之机,责难晚明心学之流弊,他认为士大夫“存心”,当存于“当用之地”,所以说:
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得乎?此皆足以发明“厉,熏心”之义,乃周公已先系之于《易》矣。[1](P31-32)
在《日知录》卷一的最后,顾炎武请出孔圣。在“孔子论《易》”条下,炎武归本周孔,认为孔子论《易》不但在于用《易》,还在于其用《易》之道有二:一,“庸言、庸行之间”“出入以度”“寡过反身”;二,“体之于身、施之于政”“与民同患”。总之就是人伦日用,用《易》在民,而不是修道、练身,存己为本。[1](P50-51)
杨万里通过他的《诚斋易传》,终于把“以史证经”的参证方法确立下来,其用《易》主旨及其价值和方法论范式也终于引起儒林的重视并得到传承。清人乾嘉学派大家钱大昕在其《跋诚斋先生易传》时谈到:“其说长于以史证经,谈古今治乱安危、贤奸消长之故,反复寓意,有概乎言之。”[7](卷二十七,P434-435)
二、参证与疏证
“史事宗”以其史事“参证”或曰以史证《易》方法见著,并因此而在《易》学领域分宗立派。早有学者称:儒理宗受玄学宗影响,“史事宗”受儒理宗影响,所以这“影响”并不影响其分派立宗。而且,由今看来,“史事宗”遗至清代的影响应该不限于乾嘉学派。我们只要考察从“参证”到“疏证”的形成路径便可知晓。
史事参证这一方法在《易》学方面延伸到清代,甚至近代和民国。黄忠天写于1995年的博士论文《宋代史事易学研究》,详尽地揭示了民国各家从“古史辨”派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到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直至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等,及至李镜池《周易探源》、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均受“史事宗”易学波及。吕绍刚导读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时说过两段话:
综上所述,随着当前医疗水平和技术的进步,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存活率逐渐提高,而术后并发症则成为制约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下肢淋巴水肿,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当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尚不够,有必要开展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全面评估危险因素,制定合理有效的评估标准、预防措施和管理手段,减轻患者负担,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古代有以史证经者,如宋人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李光的《读易详说》。近世以史证经者亦不乏人。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等人从史料考辨的立场着力研究《易》中之史,多少有些进展。至1941年,闻一多在昆明从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8](导读P1-2)
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1](P27)
撰写《周易义证类纂》,闻书钩稽九十条史料,分为经济、社会、心理三类详加辨析,纠正和补充旧注若干,于易学研究实有贡献,但仍是做零碎的史料工作,不以《周易》为史书……到1942年,胡朴安撰成并自行印制200本的《周易古史观》,才全面地,“无一字不解,无一句不说”地解读六十四卦,形成《周易》古史系统。从此,在《周易》卜筮说、《周易》哲理说之外,正式出现了《周易》古史说。[8](P2)
全诗调动多种艺术手法,使叙述、描写、想象、议论等手法水乳交融,以自然界中菟丝和女萝的有情反衬女子遇人不淑、难以白头偕老。文君羁恋旧情的痴心更加重了对男子负心的谴责,篇末借典故哀叹:自古以来,至死不相负的爱情,只有青陵台的韩凭及其妻子何氏,爱情典故也融入了全诗整体的情感中,成为动人的情感意象,让人回味无穷。
这里已明确告诉我们:把《周易》当历史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受到杨万里等人“史事宗”易学的启发。胡朴安在自序中同样谈道:
古来以史证《易》者,以朴安所知,除杨诚斋外,如清章世臣之《周易人事疏证》、查彬之《湘芗漫录》、易顺豫之《易释》,然皆不以《易》之本身即史也。[8](P9)
1.2.1 组织标本采集与处理 EOC组和良性对照组患者均采用手术治疗,在化疗前留取卵巢组织标本,所有标本均采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连续切片,片厚4 μm。EOC组患者的手术方式均为肿瘤细胞减灭术,术后均采用顺铂+紫杉醇的方式进行化疗。
关注我们:(1)打开微信,点击下方“发现”,再点击“扫一扫”,扫描本刊二维码关注即可。(2)打开微信,点击右上方“+”按钮,点击“添加朋友”,输入本刊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搜索后关注即可。
这也告诉我们,胡朴安是受了杨诚斋的影响,只是他感觉杨氏做得还不够,他要直接化易为史、认易为史。当然,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这部书做到了。
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1](P10)
至于什么是“旁证、博证”,二家学术如何发生联系,请看梁任公是怎么说的:
《日知录》为(炎武)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9](P11-12)
(1)布置适量且有梯度的课后练习。布置作业时控制好数量和难度,既能满足学生需求并具有难度,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从而去主动发现学习新知识。
其实,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一说,可视为我们论题所议及的“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由来和出处。但其中的“博证”之法首先绝非来自所谓开“以史证经”先河的干宝、缪和之流,至少在顾炎武的论集中未见提及。与之可圈可点的,倒是其在自己的集子中大力提倡杨万里证经之法和《易》用之道,如前所述。
再看看稍后的乾嘉学另一开山的学术表现。阎若璩(1638—1704)干脆把自己的著作叫《尚书古文疏证》,甚至后来乾嘉学的集大成者戴震(1724—1777)著述《孟子字义疏证》,都绝非偶然。戴震对“疏证”还进一步解释说:
此圣人赞上九不损之损之盛徳也。上九居损之终,位艮之极。居损之终,则必变之以不损。位艮之极,则必止之以不损。当节损之世,下皆损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损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實。皆损之上九也。得臣,谓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谓无自私其家之益。[4](P239)
同样,在这段话中,梁启超说的“固炎武所自创”的“本证、旁证”之法,后来衍成乾嘉学派的主要之法、基本之法,故梁公有“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的话,但梁任公这“皆接近世科学的研究法”却是虚室生白。并且,光一个“固炎武所自创”是说不过去的。杨万里等的“以史证经”说是来自干宝、缪和之辈,炎武所“创”亦必有所出。炎武的“本证、旁证”之法,梁启超说是“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以经证经”,《日知录》已有端倪,而由“以史证《易》”衍生出来的“以经证经”及其证法、证用之道,梁任公自然是没有看到,也就无法分说了。
对乾嘉学派的成因,名家、大家扎堆其中,成绩斐然又众说纷纭。敖光旭认为,“堆马铃薯式”的归纳讨论是有问题的,而“夷夏鼎革”则是乾嘉学的重要成因,恰恰“史事宗”易学的证用、证道、证法之影响再次被全然排除在外。黄克武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分为六类:(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3)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4)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5)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6)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由于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性。[10]
综上所述,有几个问题有讨论的必要。第一,黄克武全没有提到乾嘉学派领袖顾炎武、阎若璩等,可谓至失。恰恰明末前后七子除王廷相是哲学家外,其他都属于文学流派,但王廷相除“气一元论”之外,方法论上实无所创。第二,政治上的“文字狱高压说”颇为盛行,但“文字狱”并没有发生在顾炎武时代,而且该学派门类虽林林总总,但它们共同的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却鲜见提及。第三,经济上的原因即使靠谱,也是要找到方法论范式,学派方可流行。所谓“学派方可流行”,是指大家遵循一定的范式,因而才有大致相同的学术趣旨。何况,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就是“疏证”等。第四,“疏证”之法来自哪里?“史事宗”易学虽然研究者也众多,但实际上处于被边缘化状态。不是顾炎武倡之,谁能想到二家的学术关联?②
微课的呈现形式多样,“Photoshop平面设计”课程内容梯度层次丰富,具有较强的延伸性,由于教师自身水平和软硬件条件限制,拍摄资源种类比较单一,课堂新授型较多,而且方式不够灵活多变,没有做到群体与个体学习相结合,需要发展综合性、实效性更强的微课资源及运用途径。
其实,上述六个原因,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著中亦大致谈到,尤其第五所说“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是较为靠谱的说法,但他也没涉及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疏证”,而且,所谓“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有人说这是在强调二者的疏离,甚至断裂,与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的“清学的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9](P7)相同。弄清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出自哪里,应是重中之重。
梁启超在谈到炎武“博证”之法时,还专门说道:
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而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11](P61)
所谓“疏证”,戴震说是“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还要“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经之大训萃焉”[11](P61)。这实际是把乾嘉之法,兜底归纳展示给我们了。所谓“兜底归纳展示”,是说戴震关于“疏证”的这段说明,实际上也讲清了“旁证”“博证”之法及其功用。戴震作为四库馆臣之一,曾受器重而追随纪晓岚左右。四库馆臣关于《易》学“二派六宗”的“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的话,戴震应该是直接在场、耳有所闻的。何况戴震的直接老师江永(1681—1762)曾受业顾炎武,因此,可以说戴震关于“疏证”的那些解释,正好是顾炎武的“旁证”“博证”的另一种说法,或延展的说法而已。
垃圾产沼气用于发动机发电是很好的节能减排的方法。但发动机发电后产生的烟气温度高达400℃,大量烟气热量排放大气,造成浪费。发动机本身的缸套水温也高达106~108℃,需通过发动机带的风扇冷却后循环利用,造成大量的低温热浪费。多数大型垃圾填埋场一般会配置多台沼气发电机组,如杭州某填埋场,目前已发电的机组就达到8台,根据未来的沼气产量,沼气机组最终可达到16台。如此多的沼气机组,其余热量也是相当大的。如果加以利用,就可以提高机组的效率,获得更多收益。笔者以某生活垃圾填埋场为例,建立了沼气产气模型,提出了利用余热进行发电的方案。
论到“疏”“证”结合,二者应该是先分后合的。然后,才是它们如何走到一起的。“疏”——条疏、疏通,汉代早已有之,并且早已定型,可视为常法。“证”法在汉代甚至更早亦早已有之,但并未定型,可视为非常法。如东晋干宝,甚至更早的缪和。廖名春在《帛书〈谬和〉译文》中指出:《谬和》以此法治《易》,开了以史证《易》先河。[12](P228)关于“疏”“证”,戴震也是先分开说的,所谓“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更有趣的是,顾炎武门人潘耒亦将之分开来说:
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手札记,久而类成此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1](P2)
潘耒在《初刻日知录序》中,也是把“疏”“证”先分开来说,所谓“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这里,实际还有一层意思,梁启超说炎武所谓“旁证”“博证”,其实就是“疏证”之法耳。
尤其顾炎武本人,亦是将“疏”“证”先分开来看的。首先,顾炎武有诗《述古》云:“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赅通,百家亦兼取。”[13](卷四,P384)这诗分明在赞赏汉代经学大成者郑玄及其注疏之法了。但是,炎武对郑玄的态度及其作法又是矛盾的,比如,他在自己的《日知录》卷一中又说道:(《周易》)“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1](P4)这就不难看出,炎武等复古就绝非去完全重走古文经学的老路,而是坚定了炎武及乾嘉学要兼取“证”阐和“疏”通的学术新路。尤其“博证”等,难怪梁启超要说炎武所“自创”证法了。但就“证”法而言,除了前述的在《日知录》卷一中顾炎武赞赏杨万里以史证易,并多处援引杨氏的证案、证法之外,在对《日知录》的提要中,四库馆臣还说道:
虐待老人达到轻伤标准的,可依据“故意伤害罪”追究照护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策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豌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2](卷一百十九,P222)
这里,“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与《四库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的说法何其相似。“参以证佐”与“参证史事”何其相类。《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一文中谈到,顾炎武的考据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一,考辨文字音韵以通经学;二,归纳大量例证;三,验诸实证。[14]这里,“考辨……以通”可理解为“考辨……以疏通”。“验诸实证”表述为“验诸参证”似更恰当。顾炎武开创的乾嘉考据方法,归纳起来还是他的门人潘耒在《初刻日知录序》中说的“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得之。
三、程颐与杨万里的史证
顾炎武是说过“昔日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13](卷三,P384),但不能仅凭这一句话,我们就认定他只认《程传》这一家的阐《易》之法。
程颐阐《易》始以儒理,终以儒理,亦有史证之法,但我们是否可以说,既然顾炎武如此推崇程子《易》,顾炎武“博证”之法就是取自程子证《易》之法呢?显然不能,至少这方面不见顾炎武提及。而且,我们只要看看程、杨二家证法、证道的分殊便知。另,程子说《易》之关注点不在“以史证经”,更未想将此法确立、沉淀而彰显之。前虽有所述,不妨再拿出几条来分析: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程颐释曰:
自古人君至诚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贤,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于梦寐,文王遇于渔钓,皆由是道也。[6](P255)
对结构的扭转效应主要从2个方面加以限制:(1)限制结构的平面布置的不规则性,避免产生过大的偏心而导致结构产生较大的扭转效应;(2)限制结构的抗扭刚度不能太弱,关键是限制结构扭转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T t与平动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T1之比,因为当两者接近时,由于振动耦联的影响,结构的扭转效应明显增大[4]。
这里,程颐只用了史证来说明君求贤的道理,而万里史证却更深入了一层。万里释曰: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刚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刚明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叶之髙而俯包瓜实之美。九二以刚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从天降,而决起盍归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虽壮,何足虑也?尧下逮舜之侧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尧为天人之合,有陨自天之象。何忧欢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4](P258-259)万里史证不但说了“君臣相遇”,还指出了“君臣相遇之盛”有去小人之威势。程子证《易》,言尧、舜处甚多,此处却未逮。
《乾·文言》:“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隠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万里证阐曰:
此一章亦再释爻辞。蹨于身为德,形于事为行。龙德,圣人之事,非贤人事也。初九虽潜,而龙德具矣。潜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横渠张子以颜子行而未成当此一爻,恐颜子不敢当也。程子谓未成者,未着也。以舜之侧微当之,得之矣。[4](P21)
此处,万里直言横渠、程子证《易》之失,一言“颜子行而未成”,一言颜子“未成者”,皆是“颜子不敢当也”,颜子“未着也”,并提出自己的证道“舜之侧微当之,得之矣”。
易至南宋,康节之学盛行,鲜有不眩惑其说。其卓然不惑者,则诚斋之《易传》乎!其于图书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讹,未尝有一语及者。……中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3](卷四十四,P1433)
圣人在下,虽已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学、聚、问、辨,进德也。宽居、仁行,修业也。君德已著,利见大人,而进以行之耳。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傅也。[6](P11)
这里,“君德”可以是“进居其位”的舜、禹,也可以是“进行其道”的伊、傅。此处,将二个证道折中处理得好。
对程、杨二家,潘雨廷在《读易提要》中说得精辟:
夫杨氏精于史,此书之特点即每以史事证经。……观文王系辞而及高宗、箕子,孔子系辞而及汤、武,非明证乎?焦赣以刘邦、项羽当《随》之得失,郑玄以尧末年当《乾》上,可见汉时本有用此法解经者。晋干宝承用之,惜纯以周室事当之,反觉隘矣。《程传》《汉上易传》《读易详说》等用史事之处,亦屡见不鲜,然皆未若此书(《诚斋易传》)之以史事为主也。且此书取材精细,配合恰当,反复引证,曲然有致。[15](P213)
在谈到每自诩“以史证经”的李杞时,潘雨廷也对杨、李二家治《易》进行了比较分殊,他指出:
夫此书(李祀的《周易详解》)与《诚斋易传》同时同类,然内容殊不同。杨氏于《易》义全从《程传》,乃一心致力于史事之配合,故所取之史实极精细,而李氏于《易》义有所自见,其于史事得其概要而己。[15](P209)
杨万里代表“史事宗”易学以史证《易》,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顾炎武及其后继者,推崇杨万里及其证法、证道,正是要彰显和传承其道、其法。
四、结 语
值得说明的是,乾嘉学虽以“复古”为旗号,但却不是简单地回归“以严格笺注为形式”,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的汉学。这里,再回顾一下林忠军的一段话比较有益:
注不破传,疏不破注的局限,显得苍白无力。……这意味着以严格笺注为形式、以追求经文“本义”为目的的经学已没落,“史事宗”以史证的方式完成了义理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16](P262)
从汉学的疏不破注,到清乾嘉的疏以证之,不但发扬“史事宗”的以史证《易》,还以史证经,以经证经。中国自古就有疑经变古的传统,是“史事宗”易学的证《易》阐经在清学中得到弘扬,才使清代众家在“疏破注”“考证经”方面有了可循的章法,直到形成自己的朴学。“史事宗”使“参证史事”方法得到确立、沉淀而彰显,引起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顾炎武等高度重视,并被援引并揭示。经后继者的转圜、实践,四库馆臣的总结、推介,疏证方法在经学中得到普遍应用。乾嘉学术脱离宋明学问的空疏,还以明清尤其清代实学致用的便捷。“史事宗”以“参证”方法影响了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朴学又影响了后面的胡朴安的《周易》古史派,《周易》古史派又影响了后来的古史辨派。薪火相传,蔚为大观。这恐怕就是中国范式、中国哲学的学术气派。
注释:
①说它“新奇”,并不是指它首发“以史证经”,而是说杨万里以醇儒的方式,作了大量的“以史证经”,并将这种方法固定、确立下来。全祖望说诚斋“中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有类此说。
②亦有人认为,考证学当起于宋代,包括朱子,而恰恰是朱熹否认自己的考证、考据一事(见朱熹:《答孙季和》)。说宋代史证者家遍地都是,大史家亦不在少数,如司马光、欧阳修等,这恰恰忘了两点:史家是史家,不是史证家;所有史证者都没有像“史事宗”那样将“参证”一法确立下来,以致有四库馆臣在各家《四库提要》中的不断数落,自是不待赘言,“史事宗”之“参证”一法幸得顾炎武等应用、倡导,也自是不待赘言。中国学术忽视方法范式,与轻视逻辑的习惯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明)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清)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清)纪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3](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清)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宋)杨万里.诚斋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魏)王弼,(晋)韩康伯,(唐)孔颖达.周易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6](宋)程颐.周易程氏传[M].王孝渔,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胡朴安.周易古史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J].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11).
[11](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张涛.周易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3](明)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王俊义.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J].贵州社会科学,1997,(2).
[15]潘雨廷.读易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林忠军.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B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03-001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事宗’易学研究”(14BZX050)
曾华东,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昌大学江西省大学生思想政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29)
杨效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责任编辑:赵 伟】
标签:周易论文; 易学论文; 顾炎武论文; 学派论文; 范式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诸子前哲学论文; 《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事宗’易学研究”(14BZX050)论文;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