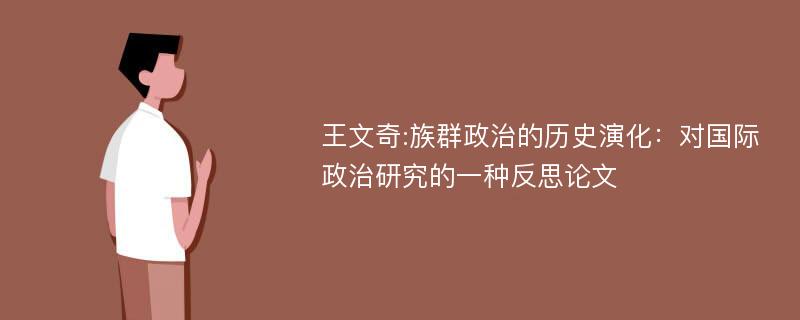
族群政治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并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态势。“过去30多年间,族群政治研究领域已经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注]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在大量研究族群政治的著述中,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族群冲突和族群战争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中东、非洲一些国家,因其内部对部族的认同超越了对主权国家的认同,形成了强社会弱政府的局面,一些学者称之为部族主义国家,[注]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Heribert Adam, Kogila Moodley, “Political Violence, ‘Tribalism’, and Inkatha,” The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 Vol.30, No.3 (Sep.1992), pp.485-510; Ari Sitas, “The New Tribalism: Hostels and Violence,” JournalofSouthernAfricanStudies, Vol.22, No.2 (Jun.1996), pp.235-248; Nile Green eds., Afghanistan’sIslam:FromConversiontotheTaliba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 Westen K.Shilaho, PoliticalPowerandTribalisminKeny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族群问题尤为严重。这些被族群政治困扰的国家,往往没有经过长期的社会文化整合,独立建国时间较短,前现代历史遗留与现代政治建构叠加在一起,使国家内部社会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复杂性。伴随着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混融,族群政治的影响溢出国家层次,成为区域乃至全球需要关注的国际政治现象。而研究族群政治也有助于我们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研究路径和叙事方式展开反思。
第一,社区服刑人员的主观因素。一是存在文化程度差异,量表的表述不能完全理解,工作人员若协助解释则会形成暗示,影响测量效果;二是量表题量多且为客观题,社区服刑人员为节省时间随意填写,造成无效量表过多;三是多数社区服刑人员对心理常识知之甚少,都是“心盲”,主观配合程度差。
其一,研究族群政治,有助于我们更正现行国际政治理论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宏观假定。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还是后来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都存在着某些理论分歧,但它们共享一种叙事方式,即都将视角聚焦在国际体系和结构上,规避对国内政治复杂性的考虑。为了理论的逻辑性和精巧性,两大流派都日益采用科学主义方法,淡化经验研究和历史梳理,结果不仅造成“像加拿大当代著名批判理论家罗伯特·沃克指出的,历史的展示实际上让位于结构解释的展示”,[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而且造成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鸿沟。具体到国际政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之一国家安全上,两大流派都认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国际而不是国内。由于两大理论流派主体理论生成于冷战期间,这种叙事方式的出现便不难理解。但若诉诸经验事实,两大理论流派的宏观假定则大有问题。
实际上,“1945年以来,国内战争比国际战争爆发得更加频繁,也带来了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同时,超过半数的国内战争是由族群问题而非阶级或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注]唐世平、李思缇:《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尤其在后冷战时代,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发展并没有像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将看到“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如何在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 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反倒是族群政治越来越突出,由族群政治所导致的族群冲突与族群战争也更为激烈。1994年爆发的卢旺达大屠杀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也颠覆着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国际而不是国内的认知。进入21世纪后,族群政治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在诸多国家引发了严重的安全问题,苏丹、尼日利亚、马里、阿富汗、伊拉克、缅甸、菲律宾都长期遭受族群问题的困扰。当前,国际政治学者对族群政治研究的升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族群问题诱发国家安全问题的警觉,同时也是对国际政治传统研究路径的一种反思。
柔性资源的运用是企业生产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企业应该投入较大的资金提升柔性资源的使用水平,这就需要企业在投入和产出之间进行权衡,使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有效结合,增加柔性资源的运用,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的附加值,使企业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
真实的历史进程则是,在一些没有历史传统和文化整合的新兴国家中,部族、族群是其重要的认同归属。在认同的序列上,对部族、族群的认同可以压倒对新兴国家的认同。二战之后,一些国家能够走向独立建国而不是分崩离析,源于国家认同的建构不是通过对内整合生成的而是通过对外区别生成的,“不是源自于人们的内部生发,而是在回应外部力量介入时展现出的一种模式”。[注] John L.Comaroff, Paul.C.Stern, “New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TheoryandSociety, Vol.23, No.1 (Feb.1994), p.39.内部可能具有族群多样性,但因为与外部比较具备了较为同一的身份,这才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以菲律宾为例,这个混杂了土著人、梅斯蒂索人、华人等多个族群的区域,在民族主义思潮的熏染下,到1890年时把菲律宾“用作这个家园上全体人民的称谓,他们最终包含了以上所有类别的成员,执拗地归于自身一种共有的菲律宾属性”。[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二战结束后,借助对外而言的身份同一性,菲律宾成为主权国家,但族群冲突一直存在,曾经被遮掩的问题形成了历史反噬,现在族群冲突问题是菲律宾内部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
其二,研究族群政治,有助于我们突破现有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方法论设定。二战结束后,在非殖民化浪潮中,族群政治并没有真正进入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野。族群政治的存在被认为只是全球政治现代化中的一段插曲,是前现代国家或殖民地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国族整合的暂时性问题,通过政策导引族群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形成这种观念的知识基础来自国际政治研究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对欧洲历史经验的认知。欧洲各主要国家,大体上从17世纪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认为是建成民族国家的初始时期。[注]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英]休·希顿-沃森著,吴洪英、黄群译:《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国家组织形态“以民族主义历史代替了宗教‘十戒’和《圣经》;将民族的历史遗迹作为朝圣和膜拜的圣地;以‘无论对与不对,祖国第一’的观念作为转化民族忠诚的道德信条。许多民族主义运动明确地呼吁民众忘记或者超越宗教(教派)差异,以共同的民族性为基础寻求统一”。[注][荷] 叶普·列尔森著,骆海辉、周明圣译:《欧洲民族思想变迁:一部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84-285页。这种类型的叙事认为,在前现代,血缘认同、部族认同、宗教认同等多种认同并存,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尤其是当二战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后,国族认同被认为在认同序列上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擢升,并将血缘、地域、宗教等认同的序列下调,使这些认同成为国族认同之下的亚认同。
族群问题跨越国家边界引发的反思是,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研究主要以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作为起点和终点是否恰当。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开始,主权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强调领土边界。国与国之间的领土边界自此由模糊而清晰,由前现代时期的大体山河分野发展到现代的清晰而垂直的地理分界线,“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图,整个世界都被进行了精确的领土划分”。[注] Michael Billing, Banal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20.由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地缘政治阐释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础设定。但在族群跨境联动的典型案例中,不仅存在着行动层面的族群跨境关联,还存在着对既有主权边界进行政治重构的诉求,一些族群就像曾经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对地理、地图的强调那样,它们也在“把一块地方政治化”,[注][西]胡安·诺格著,徐鹤林、朱伦译:《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这块地方往往就是两国或多国交界处的族群跨境关联所在。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库尔德人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库尔德人逐渐意识到制图学的重要性,他们制定了族群地图和边界地图”。[注] Maria T.O’Shea,TrappedBetweentheMapandReality:GeographyandPerceptionsofKurdist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44.二战结束后,因为诸多因素,库尔德人散居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四国交界处,库尔德人的跨境联动成为四国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但族群问题在溢出国家边界同时,国家边界同样在对族群的跨境联动实现规约,也即意味着主权国家在通过努力将族群问题限制在自己的边界范围内,避免问题更加复杂化。在不同的具体案例中,主权国家的这种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也意味着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政治,国家边界和族群边界互为主体,使族群政治的结果不再是单一向度。而要深入理解、阐释这样一种主体间性政治,突破主权国家思维的束缚是必要的。
其四,研究族群政治,需要我们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引入历史主义视角。族群政治是一种建构性政治,要通过现代历史进程来认知。尽管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认为族群差别是一种久远而古老的现象,这一点是成立的,但是从简单的族群差别走向族群政治,造成族群冲突甚至族群战争,则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或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被建构而成的问题。
[10]Anderson,L.M.,&Pearson,C.M.:Tit for Tat The Spiraling Effects of Incivility in the Workpla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
由于族群政治尤其是其中更为鲜明的部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认同政治,这就造成从国际政治研究视域研讨族群政治问题,不能再依赖于现行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现行国际政治研究方法重点强调对物质因素的重视,对体系或结构的阐释,对囚徒困境的剖解,对博弈效果的衡量(零和博弈与正和博弈,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等),这些看似科学化的方法却无法较好地用于认同政治研究。要展开对认同政治的研究,曾经被国际政治研究所抛弃的思想研究和地方性知识应该实现一定程度的回归。
其三,研究族群政治,有助于我们突破国际政治研究中主权国家思维的束缚。族群冲突除了“会危及所发生国家的领土完整,对它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还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使整个地区不稳定”。[注] Karl Cordell,Stefan Wolff,“TheStudyofEthnicConflict:AnIntroduction,”in Karl Cordell, Stefan Wolff, eds., RoutledgeHandbookofEthnic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1.族群问题会溢出国家边界形成区域乃至全球问题,这是国际政治研究要加大对族群政治研究力度的动因。但这一问题又与同样能够溢出国家边界的环境问题、疾病问题、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重要区别。环境问题等溢出国家边界只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溢出,而族群问题溢出国家边界则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溢出,在一些典型的案例中出现的状况是族群边界与国家地理边界的错位,从而诱发族群的跨境联动。
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的构建,要形成一种国族整合。然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传统上存在着大量部落,如前现代的埃塞俄比亚,不仅部落数量众多,而且“部落群体的组织形式跨度很大,从无政府的裂变结构到卡法(Kaffa)这样的中央集权制的各小邦”。[注][挪威]卡尔·埃里克·科努森:《分化与融合——埃萨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3页。这些拥有大量部落或族群的国家或地区,无论其曾被殖民还是未被殖民,基本上从19世纪末开始都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具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意识。尽管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推动独立建国的崇高意识形态,但在走向民族国家建构的具体过程中,一些部落和族群或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或是因为权利诉求的差异,或是因为对部落或族群地位的异议等原因,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建构了族群政治,从而诱发了族群冲突甚至族群战争。譬如有学者指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争斗不是自古有之的,他们之间的纷争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在殖民时代到来之前,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也是没有族群冲突的。”[注] Errol A.Henderson, “Culture or Contiguity: Ethnic Conflict, the Similarity of States, and the Onset of War, 1820-1989,” Th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 Vol.41, No.5 (Oct.1997), p.651.同样,认为南斯拉夫族群冲突的生成是古老的群际隔阂在现代的重新展现,“在证据上是站不住脚的,南斯拉夫在历史上并没有像西欧和其他南欧国家那样基于宗教差异的族群冲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20世纪之前也并未出现争斗”。[注] V.P.Gagnon,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19, No.3 (Winter 1994-1995), p.133.
族群政治的极端化形态是族群冲突或族群战争,最后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不同族群分离开来,实现各自独立建国。但问题是,族群冲突并不会伴随着分离主义目标的实现而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譬如,2011年南苏丹脱离苏丹实现了独立,但南苏丹内部又迅速出现了部族纷争,时至今日族群政治问题仍然是南苏丹内政中的难题,甚至不排除有进一步分裂南苏丹的危险。其原因便在于族群政治是一种建构性政治,处于历史流变之中。曾经没有衍生出族群政治的部族可能会在历史进程中生发出族群政治,而已受族群政治问题困扰的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国家内部的治理实现族群问题的消弭。要更好地研究这种建构性、流动性的族群政治,现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静态分析模式是不大适用的,需要运用动态的、长时段的分析方法,这正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新时期,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小企业发展也受到影响。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探索中小企业的管理模式,才能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经济法视角下中小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寻求相关的解决措施,从而完善中小企业的管理模式。
综上所述,研究族群政治的历史演化,既是基于对现实国际政治热点、焦点问题的判定,同时也能够对现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些范式、路径、方法进行反思。基于历史经验与事实,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与事实,采用历史主义方法重构国际政治的叙事体系也具有一定意义。
标签:族群论文; 政治论文; 国家论文; 国际论文; 民族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论文;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