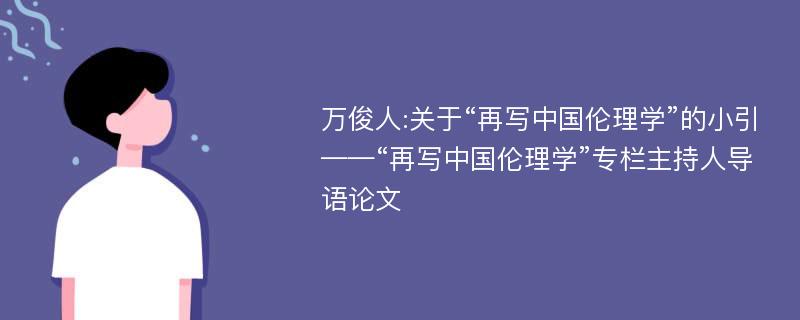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起首专栏一直是极富学术特色和学术声誉的,实非平常主题及一般论文所能荣登。2019新年首期之“再写中国伦理学”专栏更是犹如天边春雷滚动,仿佛预示着某个时刻的来临,抑或,是某一事件即将发生。
本文中我们设计的适用于体域网平台的区块链身份认证系统框架,将传感器、路由器和可信中心构成一个区块网络,如图2所示。由于传感器的资源受限,无法进行数据的计算工作,因此传感器只参与数据的简单加密和传输。然后把数据作为数据交易块发送给路由器,路由器使用验证机制对接受到的数据进行验证。最后,将数据发送给可信中心,可信中心根据共识机制将数据记入帐本。
20余年前,时任《读书》主编汪晖嘱我找几位伦理学同道谈谈中国伦理学的思想状态和学术建构问题,恰好其时我和何怀宏、赵汀阳二友刚刚做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一套名为“道德观点”的小丛书,三人共话,一聚重吟,便借《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组短文。我原本想以此为契机组建一个“北京大学伦理学铁三角”之类的学术团队,展开现代中国伦理学之重建工作,不期诸事坎坷,最终未能如愿。一晃20余年过去了,2018年暮秋时节,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与学报编辑部联合组织了一次以“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为主题的高端论坛,论坛的发起者是伦理学前辈朱贻庭先生和哲学系付长珍教授,此次专栏的三位文论贡献者李建华、邓安庆、杨泽波正是此次高端论坛的代表,而我则成为了两次学术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大概是我被指定为此次专栏主持人的唯一理由。
基于以上对创新领域的发展成效分析,可知美国创新战略具有以下4方面的特点:一是美国致力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推进原始创新带来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美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带来的长期效益,不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三是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再次强调了政府在推动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化了政府创新服务职能;四是美国重视人才培养,大力提倡高校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为何要再写中国伦理学?若离开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这一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再写”的意味究竟是重写,还是续写,抑或是补写?似乎也无定见。无论如何,对于一个诞生过孔子并拥有过“道德文明古国”之荣耀的国度来说,这些说法都近乎废话,甚至荒唐。可是,如果人们不只是沉浸在三千年道德文明古国的历史荣耀或文化回忆之中,而且还能自觉到近代百年中华文明的衰落和传统道德文化所为之承担的责难与苦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尤其是“文革”时期道德伦理文化及其学术研究的劫难和“后文革”40年来伦理学的艰难命运,“再写中国伦理学”的问题便是一个真实而沉重、紧迫而重大的学术问题,甚或足以堪称“中国现代性”中最紧要的思想文化问题之一!因为,古代中国一直都在不断地续写中国伦理学;当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时,便只有中国道德批判而少有中国伦理学,或者再也写不好中国伦理学;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关心政治却忘了道德伦理,等到1960年代吴晗先生等先贤前辈想续接道德伦理的讨论,言始出,便被禁;直到1980年代前后,人们才开始重谈并重写中国伦理学,却又因前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难以走出其笼罩阴影。这就是时至今日我们还在吁求“再写中国伦理学”并将之提升到“做中国伦理学”的学理层面上来的根本缘由。
本专栏的三位论者各取一面,对如何做中国伦理学或者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回应:李建华教授呼吁重返人学,以此为进抵中国伦理学建构之有效进路。其文通过提出并解答“人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人能成为什么?”三大问题,来回应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做中国伦理学?”的主题。其论理结构和形式让人联想到康德的“三大批判”及其内含的“三大问题”,而其实质性主张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80、 90年代曾钊新先生关于“人性是道德的第二土壤”的著名命题。或可将之看作是一种中国儒家本真性德性伦理的回归之努力?吾之臆测而已,不敢妄断矣。杨泽波教授以对儒家生生伦理学中智性之双重功能的诠释学暨东方哲学式探究,重释儒家伦理学及其现代意义,当可看作是氏君对于“如何做中国伦理学?”的一种典型而又深含“创造性转化”努力的传统儒家哲学式解答。
相较而言,邓安庆教授的撰文最为直截了当,“何谓‘做中国伦理学?’”的提问直奔主题,虽然其解答方式是海德格尔式的,但解答本身却又是非常中国的。初读印象似乎是,作者在坦率地警示我们,如若我们不仅想“做”而且想“做好”中国伦理学,必当超越知识建构的“历史性”和“地域性”,“迈向真正哲学性”的理论建构,通过不断地“拷问伦理的伦理性、道德的道德性”,进升到纯粹的哲学思辨层面,从而完成使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的理论建构使命。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借助考察海德格尔为何“不做伦理学”的内在哲学原因,洞见西方哲学因其纯粹哲思永远停滞于以“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而不是或者不能以伦理学为“存在”和“存在论”“奠基”,因之最终无法使“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与之相对,始终坚持以道德伦理为生存和存在“奠基”的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学却可能复可以使“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若如是,不单因此可以解除所谓“中国哲学正当性(合法性)”的(黑格尔式)疑问,而且也可能由此打开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学成功转入现代性语境的充满思想潜能与理论潜力的未来前景。
借本专栏三位作者的雄文高论,我相信并期待,关于“如何做中国伦理学”的探究能够由此渐次敞开,不断精进,俾使中国伦理学和中国道德文化不独摆脱犹豫、诘难、抗争和坎坷,而且得以摆脱单纯“历史性的”自我叙述和狭隘“地域性的”自我独白,进入一种能够到达纯粹哲学之思并拥有普遍性和本真性之“第一哲学”或“世界哲学”的“视阈”(horizon)和“境界”(ambit)。事实上,那才是中国伦理学和中国伦理学人向往并应该到达的理想“视境”,也才是中国现代伦理学的真实时刻!
标签:伦理学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道德论文; 伦理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