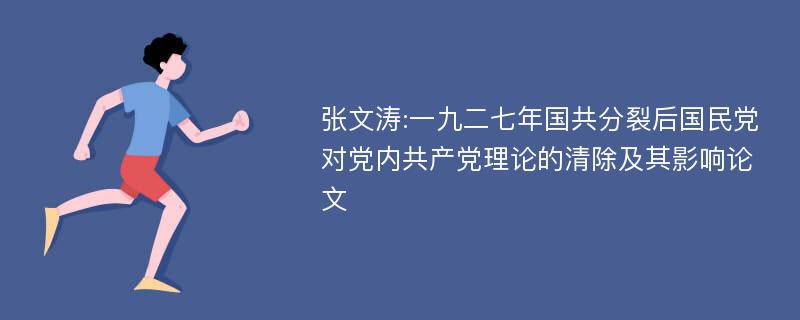
〔摘要〕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继从组织上“清党”反共之后,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中共对国民党理论的影响。国民党将思想“清党”付诸实践后,却陷入极其尴尬的局面——除明确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外,实际上根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思想理论的界限。从思想“清党”的方式来说,无论是蒋介石“一反其义”的训令,还是部分国民党人“拿来主义”的倾向,都无法具体甄别国共两党理论。国民党思想“清党”的本质是否定新三民主义及相关政策,却保留被抽离革命内容的国民革命话语。这种矛盾状态不仅使国民党通过思想“清党”统一自身理论的初衷落空,还进一步加剧国民党内的思想理论纷争。
〔关键词〕国民党;共产党; 思想“清党”; 阶级理论
“清党”,一如其字面意义,指党派为纯洁队伍而采取清除异己的组织措施。在中国革命史论中,“清党”一词作为政治术语,则是特指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大规模的暴力“清共”行为,是为学界共识。多年来,学界对国民党此次“清党”的起因、过程、影响等都有大量研究[注]① 学界有关国民党“清党”的研究较多,代表性论著主要有,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美〕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年,第11—43页;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3—61页;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1期, 2000 年3 月;肖甡:《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张文涛:《〈大公报〉对“清党”前后国民党前途的即时观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研究的推进,国民党“清党”的一些复杂面相也逐渐显露,对以暴力方式将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既有认识有所突破,其中杨奎松、王奇生等的研究已经论及国民党“清党”反共中的思想因素[注]① 杨奎松在重建和讨论1927年国民党暴力“清党”的过程时,论及国民党除在肉体上屠杀中共党员外,更“求根本消弭之方”,试图从思想上彻底根除共产主义。不过,他讨论的依然是传统的组织“清党”,且认定“清党”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即基本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王奇生在讨论国民党“清党”与党内人才的“逆淘汰”时,曾论及国共两党因为“以俄为师”,在理论上有不少相似与相同之处,蒋介石等为奠定反共的“合法性”基础,“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并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从而将三民主义中“左”的成分抛弃。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李红岩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时,曾论及1929年国民党查禁共产党刊物,亦注意到蒋介石曾声称要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全部铲除。他关注的重点是国民党在社会而非党内清除共产党理论。参见李红岩:《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分析》,《文史哲》2008年第6期。。不过,这些研究只是附带言之,并未将其视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所谓的“清党”仍是国民党在组织上清除共产党人。事实上,在1928年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二届五中全会上,清除共产党理论尤其阶级斗争理论影响进而统一国民党自身理论成为会议的重心,在国民党内取得几乎一致认识,影响深远。
国民党“清党”反共,是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和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本文试图在学界既有的主要对组织“清党”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国民党从思想上“清党”这一新的视角,重新发现和理解“清党”的另一面——它与组织“清党”既紧密联系又因侧重点不同而可大致区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国民党思想“清党”,主要指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在党内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由此进而“纯洁”国民党自身理论之举,其清除对象大致指向留存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口号、方法、理论、观念等思想因素。本文希望通过对国民党思想“清党”认识的形成,由思想“清党”而统一自身理论的诉求与困境,思想“清党”初衷的落空及影响等内容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推进对国民党“清党”反共复杂性的认识,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国民党的思想“清党”决策渐次形成
国民党旨在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影响的思想“清党”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以下阶段: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蒋介石等对共产党理论予以国民党理论影响的认识,到七一五政变前后汪精卫明确提出思想“清党”,进而由蒋介石主导在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形成党内共识并付诸实践。
就两党思想理论关系而言,在整个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的确存在一个相互妥协、彼此影响的过程,[注]② 张文涛、姬颜丽:《师其意难去其法: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对阶级斗争的认知》,《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但国民党始终强调三民主义独一无二的指导地位。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江伟藩反对李大钊跨党主张的言辞[注]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页。,以及此后另立中央的“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不计,即使国民党内与共产党合作的主流派的相关论述也不绝如缕。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就曾针对外界“国民党变为共产党”“国民党主义变为共产党主义”等言论进行专门辟谣[注]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四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重申三民主义主张,解释党内外之误会”,强调“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根据”[注]⑤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重要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7月20日。。再以蒋介石为例,1925年3月10日他赴真理学校演讲时被美国记者问到“与俄国有何关系”,他对此明确声称“俄国与本党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目的相同,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自有分别也”[注]⑥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324页。。孙中山逝世之后,随着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国民党人的此类言论更多。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时就有改国民党“成为一个真正不妥协的革命党”“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的想法[注]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第459—460页。。
本文针对评论数据对个性化推荐的影响力,提出基于CNN-SRBM文本分类的评分预测推荐研究算法。从用户对物品的评论内容信息着手,对评论数据进行文本分类,并改进传统RBM评分预测,以解决海量评论文本的情感数据处理复杂性、个性化推荐领域的数据稀疏性以及冷启动问题。
对国民党人而言,承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动摇三民主义对国民革命的唯一指导地位。故而,直到1927年蒋介石“清党”前后,国民党内主流派在陈述缘由、制造“清党”合法性之际,才承认两党合作期间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深刻影响,化思想被动为“清党”之主动。1927年4月16日,为蒋介石“清党”奔走的吴稚晖在陈述“清党”理由时就明确宣称:“总理知共产必不适宜于中国,尤其是阶级争斗之共产主义。故自创三民主义以适合中国,且允许共产党分子之有觉悟者,服从国民党主义,使之隐销其逆谋。”[注]《护党救国运动中之要件:国民党监察委员吴敬恒呈》,《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16日。吴稚晖此举无疑给四一二政变打上“主义之争”的印记,这一点于一周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上的致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蒋介石在致辞中认为,在“这次中国的大改革”中,“国民党的立场至少有三种和共产党根本不同的地方”,其中第一点即为“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社会构成分子)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的阶级(分子)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种残酷压迫的痛苦”[注]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史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20—221页。。蒋介石此番讲话,无疑有将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国共两党主义之争上的考虑。同时,蒋介石欲以“社会构成分子”代替“阶级”也显示他对共产党理论的态度,不过他并未具体论及如何对待共产党理论给予国民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等对“清党”后国民党沿用共产党口号特别忌惮,并有区分和清除共产党口号之举。1927年5月12日,他会同陈铭枢、胡汉民、吴稚晖提议统一政治口号,主张“为防止共产党分化吾党计,非实行整理口号之手续不可”,并责成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所有口号加以审查,其合者存之,不合者取消之”,且“须时时颁布一致之口号”,训令“各级党部各军政治部即各附属机关团体”对之“切实遵守、不得多加一条亦不得减少一条”[注]《中央宣传部关于统一标准语口号以及标语口号等问题的请示报告》(1927年5月—1927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七一一(6)-77。。
No matter English used as the first language in western countries or used second language in Chinese context,a certai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s essential for learning to read.So,in turn,does the progress of reading skills play a role in improving phonological awareness?
当然,网络阅读因为渠道的复杂性,内容还需要谨慎挑选,这方面还需要大量的阅读指导,而不是一味否认。如何就这种情况想出更好的方法宣传深阅读,而不是一味强调深阅读的好处,贬低浅阅读。关键是在引导全民阅读时,如何就阅读内容、阅读目的、阅读过程给予更好的指导。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后,汪精卫在明确共产党对国民党理论影响的基础上进而正式提出思想“清党”问题。1927年7月12日,在与宁方国民党人对峙数月之久后,即将“清党”反共的汪精卫于演讲中公开宣称,“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许”[注]汪精卫:《主义与政策》,《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32页。。7月14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陈述“分共”理由时又强调“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15日会上顾孟余还指出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并主张“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要素”。[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至此,国民党清除党内共产党理论影响的思想“清党”已然箭在弦上。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执信中学演讲《分共以后》时明确提出思想“清党”问题。他说道:
我们所谓分共,不但要将共产党分子,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尤其要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国民党自施行容共政策以来,共产党分子,在国民党名义之下,向农工商学各团体,宣传了不少共产党的理论。如今共产党分子,虽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论,仍然存在于农工商学各团体里……所以国民党当前最急的工作,是将数年以来,国民革命的理论,重新整理一遍。将共产党的理论,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一一剔了出来。[注]汪精卫:《分共以后》,《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41—142页。该文原件见《汪兆铭史料》,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8-010100-0058-002。
11月22日,即十天之后,汪精卫与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张继、李石曾、陈璧君、褚民谊等八人聚于上海李石曾宅“讨论关于党国之一切问题”,其重点就是反共的程度是否止于清除共产党的人。对此,汪精卫明确表示“不但除去共产分子,并须在党内除去共产党之理论”,李石曾继而也称“并须除去共产党存在本党之精神与方法”,其商定结果乃是“凡共产党之理论与方法,绝对不采取”,并决定要让“一般忠实同志,遵循工作”[注]《民党关于党国之四决议》,《大公报》1927年11月30日。。可以说,由汪精卫主导、宁汉双方要人出席的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思想“清党”共识的初步形成。较之蒋介石的“清党”反共,汪精卫确实更为强调中共对国民党理论的影响。中共对此多有讥讽。1927年12月,瞿秋白针对正在上海与蒋介石开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议的汪精卫说道:“汪精卫毕竟是聪明的乖乖,他此次来到上海投降蒋介石,磕头求饶负荆请罪之外,还知道带一个必要的礼物来贡献于豪绅资产阶级。这就是他所谓‘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党里分出去’的工作。”[注]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
汪精卫等人清除国民党内共产党理论的主张,很快成为包括蒋介石在内各派国民党人的共识。1928年2月2日开幕、7日闭幕的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其会议宗旨即为“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同心协力铲除共产党的理论”[注]《国民党大出棺材》,《布尔塞维克》第17期,1928年2月13日。。对国民党而言,这次会议的确是一次因反共而空前“团结”的大会。为召开此次会议,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召开五次预备会、两次谈话会和一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等先后担任筹备会议主席。因为被归罪牵涉中共广州起义等,汪精卫等四人最终未能与会。[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过程相当曲折。参见罗什:《中央执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经过与其价值(上篇)》,《再造》第1期,1928年3月12日。不过思想“清党”的主张却为主导此次会议的蒋介石所反复强调,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1928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上就临时提议“中央全体会议未开会以前所有一切标语暂时停止张贴案”[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六十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记录》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9—310页。,明显有寄希望于二届四中全会厘清国共理论、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影响的用意。1928年2月2日上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开会词中全面回应党内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的呼声。他对此问题的表述如下:
我们不仅反对他(指共产党——引者注)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共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遗害中国。倘若共党仍然存在,他们的理论与方法还未清除,我相信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国民革命仍旧不能成功!所以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对于共党的势力,须要有坚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至于如何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理论与方法,蒋介石明确提出“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方式。他指出:
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席卷哲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后现代”翻译理论趁机蓬勃发展,女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试图从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为译者拨云散雾,并逐渐突破译者以往的“禁忌”与“桎梏”,使译者也开始享有与原文作者一样的“自由”创作权以及作为“作者”应有的平等的主体地位。
国民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对清除国民党内共产党理论和方法的态度可谓决绝,试图通过“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从根本上与共产党思想截然两断。
蒋介石有关思想“清党”的主张,在随后的会议提案和会议宣言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蒋介石本人无疑最为关心思想“清党”,他在多个提案中对此都有涉及。如在《对于党务政治的提案》中,他就认为“今虽清党以后,而余毒鼠伏,尚未净除”,“共产虽去,而共产化之工作,未尽去”,“容共时期之各种口号,至今发现流弊,而袭用如故”,“一切方法策略,犹不免沿袭共党之师承以讹传讹”,致使“社会不安”、对国民党“渐失信仰”。对此,他一方面主张“宜将从前混淆不清之口号,为共产党所遗留而不适用者,概行撤废”,另一方面又要“尽力阐发本党主义”,且认为“阐明本党之理论,乃根本清共之方法”,“否则日言清共,而共何能清!”[注]蒋中正:《对于党务政治之提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346、347页。国民党中其他人也不例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陈果夫五人在所提出的《制止共产党阴谋案》中就声称“所有共党之理论、方法、机构、运动,均应积极铲除”,涉及面更为广泛[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四日议事录》,《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 第269—270页。。此次全会决议审查案则明确规定国民党此前“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撤销”,不仅如此,“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出党籍者”其原决定“一律无效”[注]《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1928年2月6日通过),《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64页。。其后的会议宣言更为集中地表达了国民党思想“清党”的意图,“近数年来,国人受帝国主义与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生之反动的共产主义之流毒,忘却国民革命之整个的责任,于虚无缥缈之间,假设其代表阶级之观念,左倾右倾之流毒,深中于人心”;并主张“自今以后,一切过去之纠纷轧轹,应完全抛弃。全党新旧同志之间,不得再有以派别自居,以派别攻人之谬见,尤不得模效共产党徒暴乱之言行”;且特别强调“自今以后,不特从组织与理论上绝对肃清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尤须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注]《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85、286页。。
二届四中全会上思想“清党”议题的确定对国民党意义重大,蒋介石深信国民党会因此“能团结起来,共同一致来领导国民革命,整理本党的理论与方法,使革命前途放一光明”[注]《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33页。。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等所谓“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说到底就是凡中共的主张一律反其道而行之,其中的核心便是全力清除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会后各地国民党人根据“一反其义”的原则“对症下药”,清除阶级观念。如福州就特派专门人员“分赴各中学校演讲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之优劣,国民党政策与共产党政策之良恶,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之邪正”,其目的在“俾一般青年同趋正轨,不致堕落为赤化所诱惑”[注]《福州反共运动》,《大公报》1928年4月15日。。其时矛盾重重之国民党内各派大员均积极探讨辟“阶级”之法、唯恐人后。1927年6月才“改旗易帜”的阎锡山,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就倡言“清其人尤须清其法”,声称“我同志苟不根本觉悟、涤洗旧污,则虽全国上下一致清共”,然“其人或可以屏诸党外,其方法仍可以煽惑乎人心”,“如彼之利用农民协会与工会,团结农工以袭击非农非工之人,是为马克思之阶级斗争,而非先总理之全民革命。此种方法,万不可行”[注]《阎锡山建议改善农工组织》,《大公报》1928年5月30日。。率先“清党”的桂系自然不愿落后,1928年6月白崇禧在北京女子大学演讲《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其中就有谓:“世界革命之标榜,为共产主义,意将社会一切阶级,尽行推翻,世界资本制度,完全打破”,“国民党容共之时,北方传称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国民革命之成功,乃世界革命之成功。似此谬论,理宜严办”。[注]《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白崇禧在女大演讲》,《大公报》1928年6月28日。这显然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且相当个人化的表述,完全无视国民党主流昔日视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的普遍认知。国民党地方党部也积极响应,如1928年6月由国民党浙江党务指导委员会创刊的《浙江党务》主张:“对于党的理论也想尽量的加以确立与阐发,务使一切庞杂反动的言论,铲除净尽。”[注]① 编者:《编完之后》,《浙江党务》第1期,1928年6月2日。该刊所载的王淑芳《党的改组与党的整理》一文,亦明确指出其时国民党人于理论上“在消极的设法清除共产党的理论及策略,积极的谋建树本党的真正理论和策略”[注]② 王淑芳:《党的改组与党的整理》,《浙江党务》第1期,1928年6月2日。。
二、国民党由思想“清党”而统一自身理论的诉求与困境
同时,也正是因为“清党”后国民党理论被“曲解得莫名其妙”,国民党内遂出现一片“统一党的理论”的呼声。其时的盛况,在《双十月刊》上作者署名“肥遯”的文章《党的理论问题》中得到很好诠释。“肥遯”在这篇文章中绘声绘色地写道:
(一)“一反其义”思想“清党”方式的争议
就事实而言,对于国共分裂后站在反共的“中国国民党立场上的忠实党员”来说,“肃清共产党理论”的确是“个个都觉得必要”,几乎成为“一致的主张”[注]⑤ 李颖才:《肃清共产党理论与取消“打倒基督教”问题》,《新广西旬报》第20期,1928年4月21日。。但是,除了一致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国民党内各方事实上并不知道如何清除共产党理论,又具体清除共产党哪些理论。在此强制却又缺乏确定性的政治舆论语境下,国民党内就出现一方面一致同意清除共产党理论,另一方面却在不自觉中运用共产党理论的局面,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对共产党理论“一反其义”予以清除。因为,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要想彻底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并与之一刀两断,就只有整个抛弃国民革命理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注]⑥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举凡党章、政纲、宣言乃至革命话语都受到共产党影响。陈独秀在讥讽国民党思想“清党”时就有言道:“国民党改组后党章,是共党起草的,是效法共党的,是应该反对的。不但这个,改组后的宣言及政纲,也是共党起草的,更应该废掉。不但这个,连‘反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这类怪话,也不是党国的国货,乃由共产党搬到国民党的……这更是应该急于废掉的,否则不但反共不彻底,而且是胡汉民指斥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点不体面吧。”参见撒翁(陈独秀):《“杀其人而用其法”》,《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也正因为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很快就引发争议,遭到来自党内的挑战。
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国民党主张以“一反其义”的方式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但在实际推进中国民党人却未必如口头上反对阶级斗争般一致。会后不久,汪精卫指派要员陈公博挑起有关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大论战,此正是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等“一反其义”思想“清党”的集中写照。陈公博1928年3月出单行本并引起论战的《中国国民党所代表是什么?》一文,原本写于武汉“分共”时期,本为对抗中共而作,但在思想“清党”的背景下因其自身的阶级分析遭到国民党内“老同志”的特别关注与批判。陈公博以国民党“左”派自居,认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注]⑦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试图通过构建“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对抗中共。但是,其“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的前提是肯定阶级分析的有效性,此与汪精卫本人及改组派内温和派的态度有别[注]⑧ 陈公博回忆称改组派成立前夕他和顾孟余就有辩论:“我主张社会是有阶级的,不过我想以党的力量调和而至消灭阶级的斗争,而孟余则为避免阶级斗争起见,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24页。后来研究者也认为改组派内部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其中主办《革命评论》的陈公博为激进派、主持《前进》的顾孟余为温和派。(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李志毓在,更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背道而驰。不过,陈公博的主张确实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分有激进色彩党人的声音,尤其得到那些希望分共、但更恐怖“分共之后而致开倒车”的党内青年的欢迎。[注]① 陈公博:《苦笑录》,第114页。
1928年5月,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系统阐释其政论,并先后与《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国民党内“老同志”代表吴稚晖等展开为期数月的论战。整个论战内容本身并非本文论述的重点[注]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出版社不详,1928年;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韦夏玲:《1928年国民党理论与主义之争——以陈公博吴稚晖笔战为中心的考察》,《桂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3期。此问题牵涉颇多,既有研究论之较略,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处仅以作为论战落幕篇的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及陈公博的回应,来说明国民党“一反其义”思想“清党”与来自党内挑战间的矛盾与冲突。缪斌此文是为吴稚晖助阵而作,他在文中视思想“清党”为国民党反共合法性的真正来源,称如果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不管”“可以来借用”,那么“清党”“简直是和共产党争权”,“还有什么价值”。[注]③ 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79页。因是之故,缪斌称借用阶级分析的陈公博为国民党内的“共产主义者”,刻意给陈公博论述中的共产党理论算总账。他火药味十足地说道: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深山野林里,生长着一种草本植物,它开着白色的小花,虽然看上去清新可爱,却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下雨之后你再来看,便会发现原先白色的小花变得晶莹剔透,就像精心雕琢后的精美艺术品。你知道这种神奇植物的名字吗?
在陈公博的大著上,经常看到主张国民党要用以党专政的方法来销〔消〕灭阶级,好像俄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所谓销〔消〕灭阶级,而以小资产阶级和农工阶级为联盟的国民党来消灭……陈公博如果是一个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难道总理的大贫、小贫的遗教还没有弄清?现在细看陈先生等的言论,和以前容共时代的共党言论有什么两样?如今共产党的左派主张杀人放火,陈先生等稍温和些,〈亦〉不过是一个共产党的右派而已。这种阶级论调,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便用不着。既要做国民党员,又是信仰共产主义唯物史观,这种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实有肃清的必要。[注]④ 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85—86页。
考虑需求响应不确定性的多时间尺度源荷互动决策方法//孙宇军,王岩,王蓓蓓,李扬,肖勇,李秋硕//(2):106
今日而欲改善本党之理论基础,应一反其义。其(共产党——引者注)为破坏者代以建设,为阶级斗争者代以全民众平等互助,为反科学者代以科学建国,为虚伪不择手段者代以仁爱笃敬,为以民众为工具者代以为民众服役,为三个一民主义者代以一个三民主义,为造成恐怖者代以安生乐业,为使中国破产者代以造产,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平等优裕之机会者代以国际间之平等互助,为打破革命军力量者代以团结革命的武力。[注]蒋中正:《关于党务之提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354页。
至此,双方在理论上的分歧已经凸显无疑,其背后的政治欲求也将图穷匕见。双方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的一致之处始终如一,但彼此的方法却南辕北辙。可以说,陈公博乃是以共产党之法反共产党之人,而国民党内“老同志”则主张“清其人尤须清其法”,且有视“清其法”为“清其人”合法性的倾向。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所确定之思想“清党”,无疑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和助推剂。这一切在9月1日陈公博《答缪斌先生论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一文中得到清晰的呈现。陈公博责问缪斌“是不是替主张继续清党的人打先锋”。至于缪斌因他提倡国民党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而批判他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右派,陈公博则明确表示他从“没有听道〔到〕共产党要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当日在广东以至两湖之共产党都要打击小资产阶级”,他“诚恳奉劝缪先生,多研究些学问,多注意些事实”。[注]⑤ 陈公博:《答缪斌先生论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95—96页。
陈公博反对蒋介石等“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代表其时国民党内相当一批有激进色彩的年轻人主张[注]⑥ 以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一度影响很大,尤其在国民党青年党员中。曾为山东改组派成员的何兹全曾回忆:“改组派在菏泽,在鲁西,势力很大。有思想、有理想的国民党员大多参加了改组派”,“只有一些不学无术或想参加改组派而参加不上的才去参加了CC派”。参见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本文其后所引材料的部分作者如郭春涛、杨玉清等即为改组派成员。。当时一名叫张肇融的国民党青年就认为,“因反共的关系,大家讳言共党所用过的名词,甚至把三民主义里一部分的理论与共产主义有近似的地方,一概清除出去”,乃是“矫枉过正”。他不仅反对二届四中全会上“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方式,还折中陈此基础上更进而指出,温和派《前进》诸人的观点更接近汪精卫本人,他们反对阶级分析法,不赞成《革命评论》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确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用“小市民”的概念来代指“小资产阶级”,较比《革命评论》对“民生”的重视,《前进》对“民主”的诉求更为强烈。参见李志毓:《话语、路线与斗争中的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集团和小资产阶级问题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第226页。
公博“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和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论”,主张“中国国民党应该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来完成国民革命” 。[注] 张肇融:《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双十月刊》第6期, 1928年11月10日。张肇融此例只不过是这场由国民党思想“清党”所引发论战的一个注脚。究其原因,恰如《革命评论》上署名“健”的读者在给陈公博的信中所认为,“有些军阀领袖,利用几个文人,在其管辖区域,办党报,发小册,把三民主义的革命,曲解得莫名其妙”,其结果则“使我们一般青年真是傍彷歧路,莫知适从”,“本党的理论”“有不能统一之势”[注]健:《王恒和王季文的理论》,《革命评论》第15期,1928年。。陈公博言说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莫知适从”的青年,然而就他对谋求统一理论的国民党的客观影响而言,亦与“健”所言的军阀文人相去不远。
国民党力图清除中共理论影响与其谋统一自身理论,乃一体两面之事,同属于思想“清党”的范畴。这也就是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中所说:“自今以后,不特从组织与理论上绝对清除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尤必须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注]③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86页。蒋介石在《革命与不革命》一文中也认定:“把共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了,中国社会稳定了,本党基础巩固了,然后我们就要来实现三民主义最终的步骤。”[注]④ 蒋中正:《革命和不革命》,《新生命》第2卷第3期,1929 年3月1日。不过,无论就事实、还是程序讲,国民党从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到统一自身理论都有一个过程,前者的成效会直接影响到后者的可能。
“建设党的理论”、“统一党的思想”、“整齐理论”、“统一意志”、“清除共产党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这句话好像是共产党常说的,我是引之于再造十三期罗什先生一文,恐遭误会,特此声明。)“如何保障三民主义?”“可在意的农工小资产阶级革命同盟论”。这一大堆的呼喊声,如督战鼓似的一时紧张一时一天紧张一天。的确,没有革命的理论,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没有整齐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尤其不会有整齐统一正确的革命行动。[注]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清党”反共后,国民党对统一理论的渴求,竟然以“没有革命的理论,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这样的共产党理论来论证,且论者明知故犯,这不能不说是对蒋介石等“一反其义”思想“清党”的讽刺。
当然,上述国民党人统一国民党理论的呼声很快形成党内共识。具体地说,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声言清除共产党理论和方法半年之后,统一革命理论即成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中心议题。1928年6月16日的《中央日报》社论《对于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希望》认为:“我们对于这一次中央全体会议,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从前的全体会议,多注重在革命,这次的全体会议,将注重在建设。”[注]雪崖:《对于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希望》,《中央日报》1928年6月16日。在建设的氛围中,统一、建设国民党的理论尤其得到国民党人异乎寻常的关注。蒋介石对此更是积极,他奔走各方、多次发表讲话号召统一思想,其中六七月间最为频繁。6月29日,蒋介石赴武汉,就自谓“余此次提倡思想统一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也”[注]《蒋中正日记》(手稿本),1928年6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又如,1928年7月24日,蒋介石在对北平学界公开讲演时亦称:“思想不统一,诸事是无所宿的,所以现在应当将共产学说及国家主义等,极力排除,将思想统一。”[注]《蒋总司令对北平学界公开讲演》,《中央日报》1928年7月24日。
在施工的过程中,最后的效果是否达标要看质量标准,而质量成本则是指输变电工程施工为了保证质量或者提高施工质量而提供的一切必要的费用,还包括万一质量未达标的情况下所蒙受的损失。
(二)国民党思想“清党”具体对象的确定与困境
“肥遯”上述思想“清党”主张虽属无奈之举,却是国民党在国共两党理论关系问题上的事实反映,国民党中与其持类似观点者不乏其人。国民党浙江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徐文台就是其中之一。徐文台认为,无论说国共合作时期的三民主义主张阶级斗争,还是称国共分裂后的三民主义是在“阶级合作”口号下“欺骗劳工”,都是共产党基于自身阶级观念的认识,他则认定“国民党既不主张阶级斗争,又不主张阶级合作”。事实上,徐文台并不反对诸如“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但是他反对此类口号与阶级理论有直接关系,认为“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是站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上”。[注]文台(徐文台):《阶级斗争呢?阶级合作呢?:共产党的理论与国民党的理论》,《浙江党务》第4期,1928年6月23日。很显然,徐文台意在将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阶级理论切割开来,以三民主义尤其民族主义来解释由阶级理论所派生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口号。这依然是在对待共产党理论时的“拿来主义”态度,只不过比“肥遯”更多些“三民主义”化的努力罢了。
由于浮动核电站运行在海洋环境中,其相关系统运行和设备设计必须考虑海洋运行环境的影响,这就使得现有陆上核电站的核蒸汽供应系统(nuclear steam supply system,NSSS)的控制系统方案并不能完全满足浮动核电站的运行需求,有必要开展相关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ACP100S浮动核电站NSSS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其控制要求进行了分析,给出了相关控制方案,并开展了仿真研究工作.
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实验组的抗卵巢抗体、抗精子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的转阴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
郭春涛等人认为,国民党内上述围绕“国民革命”“民众运动”“党的纪律”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所产生的纠纷,为其时国民党“理论最分歧之点”,“党内派别之发生,未始不基于此,长此以往,危机实甚,究竟孰是孰非,请中央党部根据总理遗教,妥加解释。昭示一般党员俾得有所遵循”[注]《郭春涛等五大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8日。。所谓区分国共两党的理论,必须诉诸具体论题,才能论其异同。显然,国民党人在“国民革命”“民众运动”“党的纪律”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问题上的分歧,都与国民党所受共产党理论影响有关。但郭春涛等仅是陈述事实,并未提出具体的应对之策,一切都在等待中央党部的裁决。相比之下,有类似思路的前述“肥遯”《党的理论问题》一文的讨论明显要深入,且触及国民党人面临的根本问题。
“肥遯”的《党的理论问题》是一篇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文章。作者在解释何为理论何又为国民党理论时,就以为理论“不外是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国民党的理论“无疑的是基于中国革命的客观事实所构成的革命理论”。这显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义上的认识。也正因为基于这种认识,“肥遯”坦然承认国民党内杂有共产党的理论“是一个事实”,认为1924年国民党改组“受了俄国革命的刺激”,“彼时世界发生大变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与西方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几乎因革命的高潮而合流”,国民党于此时“容共与联俄,自然免不了共产党理论的流入”。同样的思路,“肥遯”也可以“因革命环境的变迁”,在“国民党主张清除共产党,清除共产党的理论”时,最先举双手赞成。至于如何具体清除共产党理论,他也面临着前述郭春涛等遭遇的困境:“革命到了今日,对于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清除是应该的,能否清除,却甚为麻烦!”更让他感到失落的是,就连“什么是‘共产党的理论’,什么是‘国民党的理论’”,都“迄今还未看见有一个负责任机关或个人”曾“确然指出”过。“肥遯”自知他更“无此力量来把两者弄得鸿沟划然”,故而他也只能与郭春涛等人一样“选几个零絮问题”来谈。[注]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肥遯”选择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和“以党治国”问题。对主张清除共产党理论的国民党人而言,“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和“以党治国”无疑是两个相当麻烦的理论问题。“肥遯”则将这一麻烦进一步公开化:“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内含〔涵〕实在是具有推翻资本制度,根本改变社会组织的意义”,“的确是第三国际通令各国共产党一律采用的口号”;而“以党治国”“老实说”“也的确是共产党理论的产物”,但这也都是孙中山言之再三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不清除,他〔它〕的确是共产党的理论;你说清除,他〔它〕的确是中国革命客观的事实所反映的需要”,且还是至高无上的“总理遗教”。对此,“肥遯”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到异想天开的解决之道:“本来是共产党的理论,如果经国民党采取以后,我们便应该看做〈是〉国民党理论,而不应复以共产党理论视之。”不过,“肥遯”并不反对思想“清党”,且是“早就赞成清除共产党理论之一人”,他坚决主张:“如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阶级斗争’、什么‘唯物史观’等谬说,都要毫不客气地加以清除,不但清除而已,并且焚其人,火其书,灭其字,毁其版。”[注]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可见,“肥遯”清除共产党理论、建设国民党理论的思路在于:为我所用者,则为建设国民党理论的组成部分;为我所弃者,必是破坏国民党理论的邪说,须加以清除。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并非在理论上区别国共进而“纯洁”国民党理论。
1928年8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国民党人对之寄予厚望,多以为是国民党革命时期结束、建设时代到来的标志。在两个多月的提案期内,各地个人和党部所提与统一国民党理论相关的议案层出不穷。其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整理革命理论案》和《奖励党义著作案》两个相关提案,更有陈嘉祐提出《实行以党治国确定一国一党主义案》。[注]此三案俱可见《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第2张第1面,其中《整理革命理论案》后改名《统一革命理论案》被列入决议案。《整理革命理论案》认为:“数年来,党内纠纷百出,实源于党员对于革命理论不能统一”,党员“以意气而分派别”“对党取批评的态度”“偏重于吹毛求疵的琐屑攻击”,这样下去“必至将整个的党,捣成粉碎”。对此局面,该案认为,先不要问既往国民党人孰对孰错,当务之急是要“及早订出一个言论的标准来,令全体党员遵照标准发表,免得大家凭着意气来做真理”,如此“庶几思想统一,则党的团体容易坚固”。[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整理革命理论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
综上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等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信誓旦旦“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还是上述“肥遯”等倾向“拿来主义”的思想“清党”,都无从确定国民党思想“清党”的具体清除对象。正因为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对上述中央宣传部提出的《统一革命理论案》也无从着手,只能一拖再拖,“决议交常务会议,指定中央委员若干人,组织理论审查委员会,将研究结果,提交下次全体会议通过公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5页。。其后《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宣传大纲》对此案的宣传说明更能说明问题。该宣传大纲一方面再三肯定统一国民党理论的重要,认为“现在解决本党内部纠纷之根本问题,就在统一革命理论,确立中心思想,这在四次全会中既明白宣言,现在更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是此项工作,至繁且重,非特别组织委员会去郑重审查详细研究,不足以得正确的结果;非由下次全会通过公布全党,不足以立同志间的共信”;另一方面则将国民党理论的混乱归咎于共产党理论的遮蔽,“同志们应该注意,革命理论,本党总理,早已详细指导,只因被共产党等捣乱以后,玉洁冰清的革命理论,忽然被粪土淹没了,所谓研究[世]不是另有什么新发明,不过扫除粪土,还我们的冰清玉洁罢了。所以在正式颁〈行〉以前,并不是理论中断,中央尽可随时依遵总理遗教,指导同志”[注]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宣传大纲》,第9—10页。。从二届四中全会到二届五中全会,国民党将区别国共理论、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理论影响,进而统一国民党理论的重任又推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令国民党人遗憾的是,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形成的十一项主要决议案中并没有“统一国民党理论案”来区别国共理论,国民党也自然没有研究出扫除共产党理论“粪土”影响后“玉洁冰清的革命理论”。当然,在此次会议上,国民党人仍偶有承认“共产党之分子虽逐渐驱除,而其遗留于党内之方法态度等,实未湔除”,主张“消极湔除共产党遗留于党内之残毒,积极以总理遗教,培养党员历史的德性”等,[注]《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决案》(1929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3页。但已无实质意义。至此,被国民党赋予极大期望的思想“清党”不了了之。
从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来看,2016年末,河北省31.4%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62.13%的村有休闲健身场所。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人均占有量、规模等还不能与城市相较,特别是博物馆、科技馆等工程量较大的设施目前只出现于城市中。
国民党的理论统一需要制定一个言论标准,其中的关键仍在如何将所谓国民党理论与共产党理论区分开来。换言之,在思想“清党”中清除哪些共产党理论才能有助于国民党统一自身理论,而这是直至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结束都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李宗仁早在给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的提案中就已要求“确定本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之点,发表宣言,与民更始”[注]李宗仁:《党内问题、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98页。。不过这一问题显然没有解决,其中的困难在当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在郭春涛等给二届五中全会的提案中就有全面综述当时国民党人于国共理论莫衷一是的四大问题:“国民革命”“民众运动”“党的纪律”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郭春涛等在该提案中认为,这四大问题相互对立乃至冲突,让国民党人难辨国共。该提案注意到:(一)“国民革命”。就性质而言,有“各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与“全民革命”的对立;就其使命说,有“以民族革命为起点,世界革命为归宿”与“世界革命为共产国际之工作”的对立;就其目的讲,有“国民革命包含社会革命”最终目的“在消灭私有制度”与国民革命成功后“仍承认私有制度”的冲突。(二)“民众运动”。有“总理根据其主义政纲所确定,为本党所应作”与“共产党利用捣乱之唯一根据”的对立;有“依据建国三大纲领”具“破坏与建设”作用和“专为破坏而破坏”的抵牾;有“系社会力量,可以助政府力量所不及”与“系与政府争利益”、“革命政府下,民众无运动之必要”间的冲突。(三)“党的纪律”。有认为“纪律系统一意志”“为革命党所必具”与“纪律系共产党骗人盲从不敢反抗之工具”间的冲突;有谓纪律为牺牲个人自由“服从党的意志,为革命者应有之精神”和主张纪律“束缚个人自由,与‘为自由而革命’相反”等。(四)“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有“我们不及帝国主义势力之大”“应该取消此一口号”与“以此口号唤起民众,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对立;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适以促成他们联合反攻而自取失败”与“三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系处在绝对相反之地位,不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彼亦必联合或单独阻碍革命”的冲突;有“反对共产革命,为我们与帝国主义共同之目标,应与联合为一条战线,不应高呼打倒”与“本党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求世界大同,第三国际及帝国主义均为本党革命之障碍,我们应与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阶级联合一条战线共同消灭他们”间的矛盾等。[注]《郭春涛等五大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8日。
三、国民党思想“清党”初衷的落空与影响
1928年2月6日,即将就任国民党中央民训会干事的杨玉清在日记中写下他对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感想。他称这次会议“是否可以满足人们的希望”,当“以决议案实行到如何的程度为断”,但是同时他又认为,“历来的决议案的实行起来,离决议案太远;不但不能遵照决议案实行,甚至与决议案背道而驰”[注]杨玉清:《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3页。。而事实也证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包含思想“清党”问题在内决议案的实行状况确被杨玉清不幸言中。1935年,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执行委员的吴醒亚在给上海工运学员训话时曾对1927年以来国民党的“清党”及其成效颇多感叹。对此,《申报》记者写道:“吴氏将国民党近十五年来工运政策的阶段详细指出,颇致憾于北伐完成以来,党内虽举行清党,将有形之共产党员清除,但对于无形之共产主义理论之毒剂,则至今一因本党尚未整理自己之理论、使其系统化、详实化,一因工人群众本身所处地位的关系,凡昧于事实与谬执抽象理论的见解者,几向以为阶级斗争为工运理论的正义。”[注]《吴醒亚向工运学员致训救亡图存须劳资协调》,《申报》1935年3月20日。这无疑说明国民党思想“清党”的成效相当有限。
(一)国民党思想“清党”初衷落空的原因
国民党通过思想“清党”进而纯洁三民主义的初衷落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上述国民党思想“清党”具体对象确定的困境是重要原因,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无法脱离主要经共产党阐发而来的国民革命话语以及国民党自身理论本就庞杂并与党内派系斗争互相影响。
国民党的思想“清党”,说到底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新三民主义,否定国共合作及其相关政策。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行国民革命,根本一点即在于他受苏俄及中共的影响,决心将旧三民主义改造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石和国民革命兴起的关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的“清党”,是从反共角度开始进而全面否定新三民主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开始否定新三民主义,但是诚如已有研究者指出,其时国民党中央并没有立即宣布改弦易辙,而是强调自己的“苦衷”,将“清党”反共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并表示联俄及扶助劳工政策不变。直到1927年12月14日,在得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参加广州起义后才宣布与苏俄绝交。至于劳工政策,因忌惮民众运动在道义的正当性,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后才以社会妥协代替了革命的内容。[注]齐春风:《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与消解(1927—1929)》,《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这说明了蒋介石等背离新三民主义的“曲折”与隐秘。
1928年国民党的思想“清党”,是前期组织“清党”在思想上的反映和继续,其本质是打着纯洁三民主义的旗帜否定新三民主主义。对此,其时的共产党人洞若观火,他们对国民党的思想“清党”更多的是不屑。1928年12月8日,郑超麟就认为汪精卫所言国民党“以前只做到从党的组织中清除出共产分子,以后将努力从国民党的理论中清除出共产党的理论”的思想“清党”主张,“恰好表示,中国资产阶级反动以后,现在正要否认其过去的革命的作用,并想建立其纯粹反动的理论”[注]超麟(郑超麟):《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瞿秋白则更是明言:“国民党的反共清党不但是和共产党组织上分裂,并且必然同时是离开三民主义之革命化,而要直接公开地使三民主义反革命化”,他还特意辛辣地讽刺汪精卫一方面高唱“将共产党的理论分出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矛盾”之举。他还提醒汪精卫:“这宣言的初稿是我译的,其中有几段是你改写的”,“那上面说要打倒中国之特殊阶级;你现在却说中国没有阶级,说‘阶级之未发生的从此停止,已发生的也逐渐消融’(狗屁不通的理论!)我劝你们老实些,公开的说取消一切改组后的宣言和政纲等等吧”,“你们要清党清理论,不如老老实实,将共产党所教给你们这班不肖学生的东西,公开的都清出来”。[注]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不难看出,此时对共产党人来说,推动国民革命的理论实为共产党理论,国民党几无革命理论可言。
国民党思想“清党”,否定新三民主义,却无法脱离主要经共产党人阐发而来的国民革命话语。这是国民党的客观需要,也是前述国民党人无法在“国民革命”“民众运动”“打倒帝国主义”等问题上难辨国共的主要原因。武汉“清党”以后,汪精卫率先喊出“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革命里分出去”的口号,国家主义者“平生”称赞汪精卫“也知道国民党的理论和共产党的理论早已混在一起,可谓尚有一线之明”。但谈到所谓国民党的理论却让“平生”犯难,“国民党原来并没有完全的理论作基础,所以究竟什么是真的国民党的理论,恐怕问之国民党老党员也都瞠然无以为答的,现在国民党所仅有的一点理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替他们造的”,他不禁感叹这是国共两党之间没法算清的“一本糊涂账”。[注]平生:《算不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本糊涂账》,《醒狮》第164期,1927年11月26日。国民革命、反帝、扶助农工,这些与共产党牵扯不清的理论问题不仅于客观上难以清除,更在主观上为反共后的国民党所需要,因为舍此难以说明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故而,思想“清党”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国民党蒋介石等打着纯洁三民主义与继承总理遗训的幌子,实际上却是背叛和篡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抽离了其中的革命内容。
国共分裂之后,为巩固国民党统治、彻底清除共产党计,国民党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一致同意清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理论,五中全会上又大倡统一、建设国民党自身理论,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前述“肥遯”的朋友包亦愚就以为,“主张建立国民党的中心理论与清去国民党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者,均为画蛇添足,不独无补于国民党的理论,反足以摇动国民党的理论,分裂党的精灵——三民主义,而引起党内纠纷,更加有使国民党走入歧途的危险”[注]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应该说,包亦愚此论极具洞察力。事实上,国民党思想“清党”不仅未达到清除共产党理论、统一国民党理论的初衷,反而造成共产党人所谓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化”,其重要影响即在于致使相关政策上模棱两可和党人思想上的混乱。
因为国共合作之故,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有所谓新旧之别,其理论来源相当庞杂。《大公报》社论就认为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思想“清党”,是“完全抛弃联俄容共后一切理论,而归于原始的三民主义之下”[注]《宁会宣言之感想》,《大公报》1928年2年9日。。二届五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人黄季陆强调其时“党的纠纷是继续过去三民主义与三民主义两种力量的斗争”,“这纯全是理论的属性不同的问题”,而主张在“纯正三民主义”原则下“贯彻清党”[注]黄季陆:《团结党的内部与贯彻清党》,《建国》第18期,1928年9月15日。。但是,这种将三民主义截然两分而清除为共产党理论所影响的新三民主义,对于理论庞杂的国民党来说显然做不到。前述“肥遯”就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中,有“孔子的片段思想”“林肯的断片思想”“法国革命时的口号”“亨利乔治的单税制”“列宁的东方革命政策”“中国的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以及“瑞士和美国的直接民权,明朝遗老之抗清,太平天国之起义”等等。故而,在清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理论时,如果“先立一原则,必定要总理自己新创的方算为三民主义的理论,国民党的理论,否则要清除出去,那被清除出去的便不只是共产党的理论,此外就还有孔子、林肯、威廉、亨利乔治等的许多理论”,其结果必然是“不但没有三民主义的理论,国民党的理论,简直也就没有总理”。[注]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换言之,理论来源庞杂的三民主义,根本找不到一个恰当标准来寻找纯洁的三民主义。
国民党自身理论不仅庞杂,并与党内派系斗争互相影响,此并非可通过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而能纯洁和统一。1928年8月,《大公报》诸人在读罢陈公博的《重新确立党的基础案》后不由感叹,“中山一生主持革命事业,多历艰苦,精神生活,变化尤剧”,而国民党各派“大率摭拾先生一时代局部的思想而铺叙之,以助其个人主张张目”,“以是〈致〉国民党之理论,直如坚白异同之辩,久而莫之能定”[注]《读了“重新确立党的基础案”之后》,《大公报》1928年8月6日。。蒋介石主要依靠对国民党派系的操控而登台却无法消除派系,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希望通过思想“清党”进而统一国民党理论,于事实上遭到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消解。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与思想不统一彼此影响,这是蒋介石渴望解决却又难以解决之事。更何况,蒋介石本身就是国民党内最大派系的代言人,他与主要竞争者胡汉民、汪精卫相比,并不具备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本身就意味着对通过思想“清党”统一国民党理论诉求的自我消解。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在会晤李石曾等委员时曾表示,“国民党之同志,当依三民主义以革命,而袪除共产党一切阴狠灭裂之策略,在此范围内不可互相猜疑,在此范围外允当互相防制”[注]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31页。。此不过是蒋介石之愿景,因为反共立场一致并不代表各派在国民党自身理论上一致。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是其思想不统一的重要原因。陈公博就形容其时三民主义的乱象,“在今日现象,真是‘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注]陈公博:《〈王恒和王季文的理论〉附后》,《革命评论》第15期,1928年。。
(二)国民党思想“清党”的影响
早春二月,既有春寒料峭,又有无限生机,《二月》书信里的问句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彼时交往理性的某种“早春二月”,情侣之间应该有建立在真诚、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应该符合交往理性,《二月》中的萧涧秋和陶岚之间有建立交往理性的动机,有其萌芽,无奈因为他们自身和环境的局限,未及开花结果。
国民党的思想“清党”清掉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内容,但不得不买椟还珠地留下失去革命内容的国民革命话语。由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民众运动”“打倒帝国主义”等问题上左支右绌,其相应政策也陷入模棱两可之中。譬如,在被公众指为共产党理论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工人罢工等问题上,国民党也在矛盾中坚持。1928年9月11日,《中央日报》社论《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明确宣称,“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根本冲突,因反共产而放弃反帝工作是错误的”[注]《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中央日报》1928年9月11日。。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后认为:“济南事件为空前国耻,在前线亲历之侮辱,非国人能想像于万一,刺心刻骨,留存脑海,虽千万年亦难磨灭。打倒几个军阀,不算什么事,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注]蒋中正:《最近对党国之感想》,《中央日报》1928年9月3日。此外,又如罢工问题,国民党也是左右为难。蒋介石在给上海邮务工人的忠告中就表示:“罢工不适用于公众使用的事业,如甘受共党利用,政府断不姑息。”[注]《蒋中正对上海邮务工友致忠告》,《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6日。如此似乎在“非公众使用事业”中罢工,则为工人应有的权利。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告诫全国工会工人书中又称:“中国如大海〈中〉一孤舟,万不可取阶级斗争手段”,“工人欲为本身争地位,必须先为国家争地位”,“不可贪目前逾量之需求,忘却对于国家之责任”,[注]《中央党部告诫全国工会工友书》,《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又刻意强调阶级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比较对国民党政策上的影响,思想“清党”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冲击更大,其中根本一点在于动摇了此前国民党人在三民主义属于社会主义问题上相对一致的认知[注] 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清党”反共之前也并非所有国民党人都承认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国民党一大时即因其中的关键民生主义就有争议,孙中山也为此多做解释。但是,若着眼于曾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主流派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则称他们视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为相对一致的认知,应无问题。参见《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3页。。1929年3月,蒋介石在《敬告全党诸同志》一文中将国民党因清除共产党理论而带来的理论困境表露无遗。他在文中认为,国民党的根本弱点在于思想不统一,这表现在“左”“右”两种错误的思想上:一方面“有许多人大倡农工小资产阶级,为本党应代表的民众,而自命为革命的分子”,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竟否认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这让蒋介石很不满,他以为“这些思想,我们只要研究总理的三民主义,敢说读完总理遗著,始终找不出这些理论,就可知道这些偏左偏右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蒋介石此处所谓“偏左”的思想,无疑就是前文已述及的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比较之下,他对“否认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偏右”思想的批判,同样足以说明问题。蒋介石坚持认为三民主义乃是社会主义不容否认,故而批评所谓“偏右”思想道:
三民主义之为社会主义,总理在其遗著和讲演中,已经反复说明。因为三民主义的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而且包含社会革命。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就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方法。社会革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中国之不能采取阶级斗争,固由总理再四说明,然而决不能因为三民主义不赞成阶级斗争便说三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有些人竟把三民主义中间的社会革命性抹煞,这也是明白的违反总理的三民主义。[注]蒋中正:《敬告全体党员诸同志》,《中央日报》1929年3月16日。
蒋介石肯定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又为社会革命的方法。这无疑是在祖述孙中山的思想,即在革命党掌握政权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方式,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其明显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因国民党“清党”反共,舆论界对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议论频频而起。
蒋介石的上述言论给“清党”后国民党人的三民主义解读划定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问题在于,“清党”反共后的国民党人因为其“逢共必反”的下意识逻辑,在一些人口中已然发出共产党之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与之敌对的国民党三民主义为资本主义,国民党应代表资产阶级的言论。陈独秀《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一文对此就有评述。他首先肯定“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社会主义性,有非资本主义倾向,在革命进展的策略上,在使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随时代进步上,也未始不可”,继而他对国民党人李权时、谭延闿对三民主义为资产阶级理论的解读加以讥讽:“然而,象〔像〕李权时先生,老老实实把民生主义的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劳力价值论那一类,倒是直捷爽快!所以,谭延闿说:‘近来细读总理的书却实在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注]撒翁(陈独秀):《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布尔塞维克》第2期,1927年10月31日。陈独秀此处肯定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性,与其后蒋介石的上述表述一致,用意在批判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在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革命性。同时,陈独秀文中提到的李权时、谭延闿将民生主义归于资产阶级学说,却与此后共产党批判三民主义的基本逻辑完全一致。瞿秋白就径直称“三民主义就等于资本主义”,因为“纯粹国民党三民主义,反共的三民主义,已经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反工农的反革命理论;所谓三民主义的建设,除屠杀政策以外,丝毫也没有”[注]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清党”反共后的三民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非仅共产党人的一面之词。1932年,国民党人何浩若专文讨论此问题,文章开头就提出“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吗?这问题,从前确实不成问题,现在确实成为问题了”[注]何浩若:《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吗?》,《时代公论》第1卷第4号,1932年4月22日。。
线虫裂解液:10%的次氯酸钠和1 mol/L的氢氧化钠按照1:1的比例混合,摇匀得到裂解液。M9缓冲液:称取KH2PO4粉末3 g、Na2HPO4粉末6 g、NaCl粉末5 g于锥形瓶内,量取1 mL的1 mol/L硫酸镁溶液加入,然后在磁力搅拌器上加水至1 L,高压灭菌后分装使用。油红O染液:油红O储备液与蒸馏水3:2混合,现配现用。上述配制的溶液均需过滤除菌。
同时,因为思想“清党”清掉了共产党给予国民党理论的革命性影响,引发各派政治力量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话语的争夺,致使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走向不明。1930年,梁漱溟就称“自蒋介石于十七年第四中会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凡从前之学于共产党者亦多抛弃”,他并乘机重新以国民党员自居,主张“凡一切在党务上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应“一洗旧染于欧人俄人者之污”而“采取新方针新办法”[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28页。。显然,梁漱溟这种主张虽符合“清党”反共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保守化转向,却并非三民主义之本意,而是他此时立足中国本位所推动乡村建设一脉的真精神。梁漱溟对三民主义的解读只是当时众多对三民主义争夺话语中的一种。更有甚者,因为“清党”反共之后,国民党一方面不肯放弃三民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共产革命方式,其时国际上挂着“社会主义”旗号却疯狂反对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便引起部分国民党人的注意。1929年3月,在陈果夫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提案中,就有国民党党组织的改革应效法意大利法西斯党严密组织的提法,并引起国内媒体的警觉。[注]《法西斯蒂主义与意大利》,《大公报》1929年3月23日。两年之后,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批判世界三大政治思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其中唯有对法西斯称其“统治最有效能”[注]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刘健清主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内部),1985年,第104—105页。。其后,很快就有周毓英在名为《社会主义月刊》的刊物上公开喊出“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蒂为用”的口号,主张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注]参见张文涛:《周毓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第38—44页。。
首先,党校要加大基层宣讲力度,组织一批骨干教师,组建宣讲团,到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次,党校要与其他单位协力合作,通过座谈会、院坝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电视、广播、网络等,多渠道、多形式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力度,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引导和教育,增强人民的环保意识、社会责任、生态责任。再次,党校带头倡导构建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绿色生活理念,让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入脑入心,成为全民共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全民共建共享,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简言之,国民党“清党”反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28年国民党侧重思想理论层面的思想“清党”也是一样。仅以本文论述较多的国民党三民主义是否是社会主义之重要一方面而言,思想“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负面影响尤多。当然,同一“社会主义”名目之下的政治主张可能千差万别,确实存在如胡适所言“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情况[注]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但是在北伐后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国民党的思想“清党”公然违背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的遗教[注]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批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密函》,《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并危及三民主义乃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对国民党而言,这不能不说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否定与退化。
结 语
思想“清党”和组织“清党”一样,是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之后国民党“清党”反共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的重心是从组织上清除共产党人,而1928年国民党的思想“清党”则重在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进而谋求统一国民党理论。这场被阎锡山视为“清其人尤须清其法”的思想“清党”,承载着国民党根除共产党影响进而谋求自身统一的基本诉求,但其效果和影响却反而更加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清党”反共前后的国民党,从强调国共两党理论有别到承认国民党理论受到共产党理论影响再到主张清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理论,这是国民党思想“清党”形成的基本轨迹。1927年11月始由汪精卫明确提出的思想“清党”明显要比从国民党组织中清除共产党人的组织“清党”反共要晚数月之久。在蒋介石的主导之下,思想“清党”成为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的中心议题和主要精神,为国民党内反共各派所认同。国民党之思想“清党”旨在根本上反共,同时也为此前“清党”反共的暴力之举寻求合法性,更试图通过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而统一国民党自身理论,进而统一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的国民党。
国民党虽着力强调“清其人尤须清其法”,但实际上其思想“清党”的效果却相当有限。对经历过国共分裂站在反共的“中国国民党立场上的忠实党员”来说,“肃清共产党理论”的确是“个个都觉得”必要,几为“一致的主张”。这反映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各派在反共问题上的一致之处。但是,一旦诉诸实践,国民党内各方除了一致同意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外,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清除又该清除共产党哪些理论。这在国民党两种思想“清党”的趋向中都能得到印证。为了彻底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以蒋介石为代表主张“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方式,举凡共产党所用之理论、方法、口号等悉数清除。这种主张过于理想,根本无法实行。另外一种是“拿来主义”的态度,为国民党所用的共产党理论即为国民党理论,为国民党所弃的共产党理论则务必清除。此种取向过于现实,其标准难以确立,只能各行其是,适成派系斗争的反映与助推剂。质言之,国民党要有效推行思想“清党”,就得从观念、理论、政策、口号等方面有一个区别于共产党的明确的标准,但这是国民党人所无法提供的。这也反映了共产党理论给予国民党理论的深层次影响。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不统一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党内蒋介石等主流派的思想统一诉求并非可通过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而达到。
国民党思想“清党”不仅未能达到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而统一国民党理论的初衷,反而致使国民党理论更趋混乱多歧。其时共产党人的观察是深刻的,国民党思想“清党”是清除国民党思想中的“革命性”,造成国民党理论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化。国民党理论尤其民生主义虽与共产主义有别,但其为社会主义之一种无疑,这是自清末以来多数国民党人的普遍共识。然而,国民党思想“清党”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共识,并引发各政治势力从己方立场出发对国民党理论的诠释与争夺,国民党理论由此更趋混乱。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在坚决于党内外清除共产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并坚持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无论于思想理论还是政治现实都显得局促不堪。在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业已主导社会主义思潮,而反共势力又多在社会主义名目下积极反共的时代,国民党理论方向的不明随之增加。
进一步讲,国共分裂后的国民党思想“清党”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此时的共产党人也在着手处理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理论对于自身的影响[注]郑超麟在批判汪精卫思想“清党”主张之后接着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时期,也应该有我们的企图,即从过去‘国民党化’的中国革命理论中清除那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然后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理论。”参见超麟:《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换言之,伴随以国民党“清党”反共为标志两党关系的完全破裂,两党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可以说,国共两党清除合作期间对方对自身理论的影响,进而重建自身的思想理论,这是分裂后两党思想理论变动的共相。然而,比较国共双方,共产党虽然在刻意追求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犯过“左”倾的错误,其后却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反观国民党,则始终未能达到其思想“清党”的初衷,且致使党内思想更趋混乱。其中缘由,颇值深思!
(本文作者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扬州 225002)
AStudyontheKuomintang’sEliminationofCPCTheoryfromWithinPartyanditsInfluenceaftertheEndoftheKMT-CPCCooperationin1927
Zhang Wentao
Abstract: The split in KMT-CPC cooperation occurred in 1927, and after the “purges within the party,” elimination of CPC ideology and theory was put on the agenda of the Kuomintang. But when the Kuomintang put the ideological “purge” into practice, it faced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whereby apart from clearly opposing the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it did not discer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oundarie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erms of how the ideological “purge” proceeded, neither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to “deviate from reality” or the inclination of some Kuomintang members to “apply the doctrine” could distinguish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essence of the Kuomintang’s ideological “purge” was to negate the new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related policies bur to reta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which the revolutionary content had been removed. This contradiction not only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Kuomintang’s original intention to unify its theory through an ideological “purge” but it also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disputes within the Kuomintang.
〔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6-0039-16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16FZS029)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薛 承)
标签:国民党论文; 理论论文; 共产党论文; 思想论文; 国民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16FZS029)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