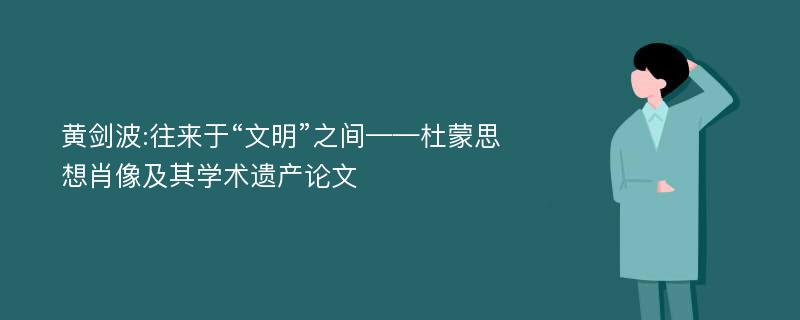
摘 要: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以其印度卡斯特研究名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后期关于欧洲文明的思想史研究。从他学术生涯早期对于物质文化的关注,到后期对近代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研究,其思想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也是杜蒙有多个头衔所在的缘由,如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印度学家、思想史家等等。纵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回到其所处的时代场景,检视其思想理论的生成过程会发现:杜蒙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是超越于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他一方面重视经验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在做全球性的反思,其所关心不仅是印度或西方,乃是整个人类。杜蒙是一个“民族志学者”,一个理论家、人类学家,同时又不仅仅是一位人类学家,他是一个对其所处时代有着深刻忧虑的思想家。
关键词:路易·杜蒙;印度;意识形态;人类学理论;民族学;《阶序人》
引言:为什么要读杜蒙?
20年前(1998年)的11月9日,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在巴黎去世,享年87岁。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大师莫斯(Marcel Mauss)的弟子,同时,他也是一位印度学家,对印度社会学人类学影响重大。1911年,杜蒙出生于希腊的萨洛尼卡(Salonika),父亲是工程师,祖父是画家。这样的家庭背景,对杜蒙一生之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印度人类学家崔洛克·马丹(Triloki Nath Madan)指出,杜蒙将此两种职业(画家与工程师)之素养揉进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里面,即创造性的想象力及对具体之物(the concrete)持久不衰的兴趣[1]195。
概略而言,杜蒙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印度社会研究与近代西方(德法)意识形态研究。我们在21世纪的中国何以要关注这样一位研究印度、欧洲社会的法国人类学家?毋庸置疑,我们关注杜蒙、阅读杜蒙,是希望他的论著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思想资源。作为一个一直在研究、理解、反思“文明社会”的人类学家,我们相信他的思想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带来一些启发。
作为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同时代的学者,杜蒙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盛名之下,往往是被忽略的,这种状况在中文学界尤为明显。2008年,夏希原在一篇评论杜蒙名著《阶序人》的文章中即指出,“杜蒙是一位至今还没有被我国学界所重视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注]夏文(参见夏希原:《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发表之前,国内关注杜蒙较多的是梁永佳,其于2005年在《民俗研究》上发表了《路易·杜蒙论印度种姓制》(参加梁永佳:《路易·杜蒙论印度种姓制》,《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另外2006年他还组织了“在中国阅读杜蒙”的读书会,成果刊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5辑),参见: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5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夏文之后,涉及杜蒙的论述多为《阶序人》一书的评介,除此之外有两篇文章旨在论述杜蒙的学术学思想,是目前笔者看到较为详细的介绍了,具体请参见,张金玲:《杜蒙的人类学思想》,《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王晴锋:《路易·杜蒙的学术肖像:从“阶序人”到“平等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随着2017年简体字版《阶序人》在浙江大学的出版,似乎杜蒙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十年过去,这种情况依然如是。法国著名学者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曾说:“1960年代,在(法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最富盛名的当属列维-斯特劳斯;但是对于我和其他一些人而言,杜蒙的作品则更具决定性的影响。”[2]1法国政治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则直言,在20世纪伟大的人类学家当中,杜蒙和列维-斯特劳斯同等重要[3]。我们引述法国学者对于杜蒙的评价,并不是要在他逝世20年后的今天大肆宣扬或吹捧他,我想他本人也无此意愿。我们只是想说明,杜蒙所留下的学术遗产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思考的。在此诉求之下,对杜蒙进行一个立体式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纵览中文学界对杜蒙的介绍和借鉴,多是通过《阶序人》一书来完成的,或阐述其阶序理论,或借用其“阶序”概念的核心特点“把对立情形含括在内”(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来进行具体的研究。此种情形便造成很多人对杜蒙只是一个切面式的了解,以为杜蒙仅仅是一个研究印度的法国人类学家,因此缺乏对于杜蒙的整体性认识。另外,在介绍其名著《阶序人》时,多数学者将“hierarchy”一词译为“等级”。尽管学者们在理解杜蒙的“hierarchy”一词时并未偏离杜氏的原意,但中文译名“等级”一词却极易对人们理解杜蒙造成误解。因为中文的等级一词即有明显的“高下差别”的含义,而杜蒙的hierarchy并无此意。此种误解往往便成了人们批评杜蒙是在为印度等级制度、不平等辩护的理由。在一篇介绍杜蒙思想的文章中,我们着重强调了“hierarchy”不是等级,而是阶序,重点在于“序”,其核心乃在于对差异的包容[4]。
我们在此指出,中文学界对杜蒙的了解大多是片面的,且在介绍杜蒙时多注重其前期对于印度社会的研究,而忽略了其后期对于近代西方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思考。事实上,杜蒙对西方近代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研究共有三本专著问世,而目前中文世界仅有《个人主义论集》(Essays on Individualism: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一书有译本[注]See Louis Dumont.From Mandeville to Marx: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Essays on Individualism: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German Ideology:From France to Germany and Back.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其中第二本书有中译本,[法]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黄柏棋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桂裕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对比译文,后两个译本应该为同一人所译。。无疑,杜蒙在这方面的影响广泛,且不仅仅止于人类学社会学界[注]如杜蒙对于“个人主义”的研究在法国政治学界产生十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杜蒙对于法国政治学界重大而持续的影响力,请参阅Jacob Collins,“French Liberalism’s ‘India Detour’:Louis Dumont,theIndividual,and 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68 France”一文(Jacob Collins,“French Liberalism’s ‘IndiaDetour’:Louis Dumont,the Individual,and 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68 France”,Modern IntellectualHistory,12,3(2015),pp.685-710)。。故而,我们在今天阅读杜蒙,强调的是对其进行一个整体认识。我们试图以杜蒙个人生命史为主线,从“思想史的高度纵向”把握其个人思想之变化,从“社会史的宽度横向”把握其个人思想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的互动关系[5]。通过这一回溯,我们去追寻杜蒙及其思想理论的“生成过程”[5]7,试图去理解“杜蒙如何成为杜蒙”。
一、杜蒙思想之“谱系”:四个人和四个地方
回顾杜蒙60余年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有很多伟大的思想都对杜蒙产生了影响。阅读杜蒙的作品,检视其思想,我们认为有四位学者对杜蒙影响至深。同样,有四个地方在杜蒙一生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了杜蒙的学术研究。因而,我们将此四人四地视为成就杜蒙之为杜蒙的关键。
莫斯对于杜蒙的影响清晰可见,不管是对于印度的研究,还是对于近代西方意识形态的考察,杜蒙都强调这一切背后的“精神资源”均源自莫斯。在《阶序人》一书的“法文版序言”中,杜蒙说“莫斯的教导愈来愈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导原则”[9]44。而在其《个人主义论集》一书的导论里,杜蒙则直言“他(作品)背后的精神资源是马塞尔·莫斯”[6]1。我们知道杜蒙一生是极强调经验性的,他是一个对“事实与细节的狂热崇拜者”(a devotee facts and details)[2]124。杜蒙对于经验事实的重视正是源自莫斯。这点我们也可以从杜蒙对莫斯的定位上清楚地看到:“莫斯是一位转到具体事实上面来的哲学家,理论者,他知道唯有跟事实作密切的接触,才能让社会学取得进展”[6]278。再者,莫斯所提倡的“整体社会事实”的理念,可以说贯穿于杜蒙整个研究生涯。
1936年,25岁的杜蒙进入传统艺术与民俗博物馆,由此开启了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当然,博物馆不仅仅给了他学习和工作的场所,在研究兴趣和方法上亦对其产生了影响。在博物馆时期,杜蒙关注家具、工具等物质文化的研究,并受到传播论思想的影响(详见后文)。这种影响在杜蒙对印度南部次卡斯特的研究中依然可明显见到,《印度南部的一个次卡斯特》(A South Indian Subcaste)一书的英译者莫法特(Michael Moffatt)提到,“《次卡斯特》一书中包含了很多对于物质文化的细致描述”[7]。罗伯特·帕金(Robert Parkin)同样指出了这一点[8]238[注]See Robert Parkin.“Louis Dumont:From Museology to Structuralism Via India”.In Robert Parkin and Anne de Sales(eds.).Out of The Study and Into The Field:Ethnograph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ench Anthropology,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10,p.238.。除了这一影响,还要强调的是,正是进入博物馆工作使得杜蒙有幸听到莫斯的讲座,并开始跟随莫斯学习。
四个地方分别为:巴黎传统民俗与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德国、印度以及牛津大学。在博物馆,杜蒙得以重返学术,且博物馆同仁们知识共享、亲密无间合作的学术氛围给杜蒙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杜蒙提到人类学这一学科共同体缺乏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昔日博物馆学术研究共同体精神的怀念。德国之于杜蒙的意义,我们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之名便窥其一二。在德国,杜蒙遇到了印度研究专家苏柏林(Walther Schubring),这于他的梵语学习与印度研究有莫大的助力。另外与德国直接相关的是“二战”,杜蒙对近代意识形态进行三十多年的研究和反思无疑与他在德国做战俘的经历有关。杜蒙曾写道:“那段日子在德国人自己和我们的心中都留有伤痕”[6]198。 印度对于杜蒙的重要性则是众所周知的。对印度社会的研究,不仅为杜蒙看清“我们(西方)”提供了一面镜子,而且正是通过印度研究,杜蒙发现了“阶序”这一他倡导和推销的“价值—观念”(Value-ideas)。牛津之于杜蒙也极为关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那里他受到了“第二次学术训练”。
我们谈到莫斯对于杜蒙强调经验性有重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此方面之于杜蒙的影响。杜蒙在牛津四年,不仅与普里查德结下深厚的友谊,更是在其指导下进行了“第二次训练”(详见后文)。在此学术往来之中,埃文斯-普里查德除了在强调经验性方面对杜蒙影响重大之外,他对于非洲努尔人的研究同样深刻影响了杜蒙。这一点我们在杜蒙为《努尔人》法译本写的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0]。杜蒙将印度的卡斯特视为一个体系(system)或结构体系(structural system),他指出“卡斯特从外面看起来是一体的,而其内部则是分化的”[9]96。这与普里查德分析努尔人社会的“裂分-合组”(segmentary)[注]这一概念的译法借用自陈波。特点非常相似。而“裂分-合组”也一直在杜蒙的作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对非近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描述,同样强调其“裂分-合组”特性。杜殴伯(Robert Deliège)在谈到杜蒙的思想时即指出,杜蒙将印度卡斯特体系视为一个“结构体系”,这与普里查德将努尔人描述为一个“裂分-合组”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11]123-124。他强调了杜蒙在牛津期间受到英国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极大影响[11]122。不过,关于这一点需要有所澄清。我们不能否认,牛津四年,杜蒙受到英国学界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特别指出杜蒙一直以来对于所谓“经验主义”(empiricism)与“经验性”(empiricality)之间区别的强调。他指出,“经验性”意指个人经验与田野工作;它同时也要求采取审慎的研究态度,收集尽量多的资料,并在必要的时候对通行的观点提出质疑。“经验主义”则相反,它过分重视自己的范畴概念及其应用技术,因而允许对原始材料进行激烈的肢解,死守不放狭隘的观点;它低估文化环境的重要性,它甚至已开始腐蚀田野工作的首要地位[9]10。因而,我们说杜蒙重视经验事实,我们强调的是其“经验性”,而非“经验主义”。
在大多数学者的眼中,杜蒙除了是莫斯的弟子,通常还被认为是一个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通过阅读杜蒙,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顶“结构主义”的帽子与他的思想并不十分契合,至少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对于杜蒙而言并不完全适用。确实,早在1936年,杜蒙便与列维-斯特劳斯有过会面。那时列维-斯特劳斯刚从南美做完田野回来,时在博物馆工作的杜蒙还帮他整理过一些田野材料。列维-斯特劳斯也是将其《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书的手稿同杜蒙分享。杜蒙在印度田野时,正是因为拜读了该书有关印度部分论述,才完成了《印度南部的阶序与联姻》一书,并将其献给列维斯特劳斯(见后文)。无疑,此时的杜蒙受到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就此断论杜蒙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是不够准确的。细读杜蒙我们就会发现其所强调的结构更多的倾向于价值结构(structure of value),而非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心智结构。而且,其结构的核心特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而是“阶序性对立”(hierarchical opposition)。在这一点上,杜殴伯之说更加合理:称杜蒙为列维-斯特劳斯的门徒无疑是不尽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他毫无疑问是超越于此的;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中至少关于印度的部分,其结构主义特色十分明显[11]122。
确实,莫斯、埃文斯-普里查德、列维-斯特劳斯三人之影响在杜蒙的学术思想脉络里明显可见。这也基本符合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帕金对杜蒙学术生涯的总结,他称其发生了三次“转变”(shifts)。第一次转变是从早期的传播论、文化研究法(习自博物馆)转向莫斯主义社会学(整体论与世界历史的视角)。另外他也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兴趣持续增加,关注简单的二元对立。第二次是从他自己早期的结构主义转变为一种修正的结构主义。随着他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逐步熟悉,以及通过不断的西方与印度之间的比较研究,他发现了“阶序性对立”。第三次,可称之为杜蒙在田野上的转变,从实地观察研究转至思想文献研究,同时在方法上更多地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人类学而非法国人类学的影响[8]251。
同时,进一步阅读杜蒙的作品,我们会在他思想的哲学底色中发现黑格尔的影子。在其所有著作中或隐或显,都可看到黑格尔的留下的痕迹。斯特伦斯(Ivan Strenski)言道:“杜蒙在他的作品中频繁且熟练地提及黑格尔,这表明了他对某种与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思考(方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喜爱,因为在杜蒙看来宏大的愿景即为常态(norm)”[2]124。杜蒙在讨论印度卡斯特作为一个形式体系(formal system)问题时指出,“首先得掌握它们的原则,才能将其化约成一个结构(structure)。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比任何都更早一步看到了体系的原则——抽象的‘差异’”(difference,强调为杜蒙所加)[9]107。另外,若我们熟悉杜蒙阶序概念的核心特征——“把对立情形含括于内”,便会发现其极具黑格尔式的辩证思想。但正如斯特伦斯所言,杜蒙一生从未尝试告诉我们他的哲学偏好,他是一个对于事实和经验极其痴迷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斯特伦斯称他本质上一直是一个人类学家的缘故[2]124。即便是在其后期关注近代西方思想史、观念史时,他都一直强调自己在从事人类学的研究,而其“田野”正是那浩如烟海的文献。无论如何,在讨论杜蒙个人思想的谱系时,我们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黑格尔。我们可以重申:在回溯杜蒙个人思想的“谱系”时,莫斯、埃文斯—普里查德、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黑格尔这四个人始终无法忽略。
我们知道,在考察一个人的思想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纵观杜蒙60余年的学术生涯,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思想都在杜蒙的作品中留有印记。我们强调上述四人的影响,旨在强调这四个人的思想在杜蒙及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诚如艾伦(N.J.Allen)所说,回顾杜蒙的学术生涯,“其最为核心的当被视为自孔德(Comte)、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至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再至莫斯这一思想传统的一个分支,但同时亦不能忽视其他人的影响,这包括韦伯(Max Weber)、埃文斯—普里查德,甚至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2]。详细去考察、梳理杜蒙的思想谱系,应当是一本书的内容。我们通过对杜蒙个人生平与学术全景式的回溯,重新走进和阅读杜蒙,旨在完成文章开头所述之目的——杜蒙何以成为杜蒙。在对杜蒙个人学术思想谱系提纲挈领式的叙述之后,再来走进杜蒙个人生命史、生活史的具体场景,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地看到一个学者思想的生成及其转变。
二、从“青春期叛逆”到“以民族学家为天职”
杜蒙出生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因父亲是工程师的缘故,家人期望他能接受与科学相关的教育,技术或者数学。他选了数学。杜蒙对这种提前规划好的人生极为厌倦,他渴望一种无所顾忌地背离既定规则的生活。当然,他的这一系列的叛逆行为也给其整个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杜蒙自己说,“我的一系列自以为是的越轨行为带来了名符其实的丑闻,我的母亲(当时已成寡妇)原本为了我的教育费尽心思,最后将我逐出家门”[13]。同时,这些青春期的叛逆举动也将杜蒙原本既定有序的生涯规划推入了一片茫然。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整个巴黎都陶醉于其文化与艺术的狂热之中,此时的杜蒙从事着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尽管看起来不是很体面。他沉迷于当时先锋派美学、哲学及社会团体的疯狂的活动中。1930年代早期,杜蒙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文化叛逆的边缘,他与激进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哲学家以及政治思想家交往,也与类似社会学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之类的社团关系密切[注]有关杜蒙早期经历的材料主要引自斯特伦斯的《杜蒙论宗教》一书第一章(see Ivan Strenski.Dumont on Religion.London: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8,pp.5,7.需注意的是社会学学院由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罗杰·加洛瓦(Roger Callois,) 和米歇尔·赖瑞斯(Michel Leiris)于1937年发起成立,故而,此处杜蒙在1930年代早期与此社团关系密切之说有误。杜蒙与此社团之密切关系也是其进入传统民俗与艺术博物馆之后的事,笔者将在后文提到。。
有学者认为早期杜蒙受到神秘主义者、印度学家瑞纳·古埃农(René Guénon)的影响,甚至对此后杜蒙的印度研究影响深远[注]See Roland Lardinois.“The Genesis of Louis Dumont’s Anthropology:The 1930s in France Revisited”.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Vol.XVI No.1,1966,p.27;Jacob Collins.“French Liberalism’s ‘India Detour’:Louis Dumont,the Individual,and 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68 France”.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2015,p687.此处需说明的是,尽管拉蒂诺瓦与柯林斯都述及了古埃农对早期杜蒙的影响,但就其影响程度大小,两位作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主张杜蒙的研究印度的人类学思想深受古氏影响,后者述及影响可能只是研究兴趣方面。斯特伦斯对拉蒂诺瓦的看法进行了尖锐了批评。。伊万·斯特伦斯指出,古埃农可能确实在研究兴趣方面影响了年轻的杜蒙,但拉蒂诺瓦(Roland Lardinois)等人所言之古氏对杜蒙印度社会研究的方法与思想影响深刻的看法是荒谬的[注]伊万的具体批判,see Ivan Strenski.Dumont on Religion.London: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8,p.7-12.。在斯特伦斯看来,莫斯以及涂尔干式的学术圈,似乎决定了杜蒙研究印度社会学(sociology of India)的方法(approach)[2]13。依笔者阅读杜蒙来看,斯特伦斯此说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不仅杜蒙的印度社会研究,乃至杜蒙一生的思想均受惠于莫斯,他自称莫斯为其著作背后的精神资源乃是最直接的证据(见前文)。
记者在某电商购物平台搜索“竹签批发”等关键词发现,只需12-14元就可以买到2000根竹签,平均每根不到1分钱,而卖家们注明了竹签是一次性的,当记者询问卖家竹签是否可以重复使用时,卖家表示:“竹签是一次性消耗品,不建议重复使用。”
杜蒙1935年进入传统民俗与艺术博物馆工作之前已经换过好几份工作,如卖保险、校对员等。于杜蒙而言,进入博物馆是其一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正是进入传统民俗与艺术博物馆工作,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知晓的人类学家杜蒙。杜蒙自己说道:“所有的一切(everything,对社会人类学与印度研究的兴趣)均始于1936、1937年”。他将博物馆称为自己进入民族学(ethnology)的“一扇小门”[注]Christian Delacampagne,“Louis Dumont and the Indian Mirror:An interview with Louis Dumont”(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 Monde,January 25,1981.).RAIN,No.43,1981,p.4;Jean-Claude Galey,“A Conversation with Louis Dumont”.Paris,December 12,1979,P13.。杜蒙说,来博物馆工作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天职”(vocation)可能就是做一名民族志学者(ethnographer)。在博取馆工作期间,他受到馆长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Henri Rivière)的鼓励,并受到博物馆同事们谦逊、投入的工作精神的感染。这一切,尤其是在听了莫斯的讲座之后,均促使他决心重返学术。于是,他重返学校,并跟随莫斯学习。这也使得他接触到一些涂尔干的继承者,如布格列(Céléstin Bouglé)。布格列当时已经完成了一部有关印度卡斯特的研究,而我们知道杜蒙在《阶序人》一书中对于“卡斯特”(caste)的定义就是参考了布格列的定义[9]。斯特伦斯也提到,杜蒙研究的核心“卡斯特”以及“个人主义”很早便是涂尔干及其继承们全部研究兴趣当中的一部分[2]13。在这个意义上,杜蒙无疑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后继者[注]帕金对杜蒙“阶序性对立”(hierarchical opposition)的学术史梳理,以及Celtel对杜蒙个人主义研究谱系的考察,都表明了斯特伦斯此说的合理性。帕金和André Celtel的研究,具体请参见,Robert Parkin,Louis Dumont and Hierarchical Opposition.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03;André Celtel,Categories of Self:Louis Dumont's Theory of the Individual.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05.。
前文提到,杜蒙与“社会学学院”关系密切。这一学习讨论团体是由巴塔耶、加洛瓦及赖瑞斯三人发起成立的。加洛瓦是一位对人类学有浓厚兴趣的古典学者,赖瑞斯是一位在非洲做民族学田野调查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自1937年至1939年,他们每逢双周就进行一次小组讨论,从事神圣经验的研究[14]。这一社团所倡导的研究深受莫斯和黑格尔的影响[15],而正是在该社团举办的讲座上,杜蒙接触到黑格尔哲学,至此之后,黑格尔便一直存在于杜蒙的作品当中,影响其终生[注]See Ivan Strenski,Dumont on Religion.London: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8,p.124;Denis Hollier,The College of Sociology(1937-39).Translated by Betsy Wi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见前文)。
杜蒙研究La Tarasque的专著于1951年出版,题为La Tarasque:Essai de description d’un fait local d’un point de vue ethnographique。杜蒙自评,这是一本奇怪的书(a strange book),其中有诸多不足,但唯一值得他自豪的是其对于细节的描写[16]4-5。马丹对该书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杜蒙自己的说法:在此书中,杜蒙即展示了其对民族志细节的把握和整体取向的研究方法[1]197。1948年底,杜蒙开始其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生涯,即将38岁的他前往印度开始为期两年的田野工作。此次田野能成行,也得力于法国印度学家路易·勒努(Louis Renou)所提供的奖学金。
前文提到,杜蒙在印度田野期间他阅读过斯特劳斯《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书的手稿[注]杜蒙与列维-斯特劳斯首次见面是在1936年,那时列维-斯特劳斯刚从巴西做完田野归来。列维-斯特劳斯给杜蒙分享了他有关亲属制度研究的巨著,即《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这对杜蒙有关印度亲属制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于深入的田野考察,加上系统的文献资料研究,杜蒙完成了两部重要著作:《印度南部的阶序与联姻》(Hierarchy and Marriage Alliance in South India,1957)与《印度南部的一个次卡斯特》(Une Sous-caste de l’Inde du sud:Organisation sociale et religion des Pramalai Kallar,1957)[1]197。稍显遗憾的是,《印度南部的一个次卡斯特》一书直到1986年才有英译本问世[18]。《印度南部的阶序与联姻》以英文出版,是献给列维-斯特劳斯的。列维-施特劳斯对规范性/优先婚姻形式的分析,为杜蒙解释他所收集数据提供了方法。进而,杜蒙认为所谓交表婚在其性质上并非是偶发的,实际是两个父系世系群之间关系持续的纽带[1]197-198。《印度南部的一个次卡斯特》一书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关于印度最为详尽清晰的民族志。他运用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方法,通过Pramalai Kallar次卡斯特这一个案,透视出整个印度社会的构成规则[19]。
1955年,杜蒙回到巴黎,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法国高等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担任教授。在其就职演讲中,杜蒙宣称“印度社会学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学与印度学的结合(confluence of Sociology and Indology)之下”。杜蒙提醒我们要谨记“印度是一个整体”(India is one),这也正是印度学给我们的财富。在此基础之上,印度社会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乃是“作为整体的印度社会”(Indian society as whole)。同时,他也强调了社会人类学“经验性”的重要性。结合此两点,他提倡“描述性社会学”(descriptive sociology)。杜蒙强调,他们所谓的“描述”(description)即“理解”(understanding)。此种社会学表现为三种路径:其一,要用社会学的语言(sociological language)来表述材料;其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孤立的,他们是体系(system)中的一部分;其三,我们研究的首要目标即是“观念体系”(system of ideas),或者是一种“价值社会学”(sociology of values)[注]See Louis Dumont,“ For a Sociology of India”.In Louis Dumont(ed.),Religion,Politics and History in India.Pairs:Mouton Publishers,1970,pp.6-7.杜蒙此次就职讲演后来被波寇克译为英文,以“For a Sociology of India”为题刊在杜蒙和波寇克合编的《印度社会学集刊》(Contributions of Indian Sociology)1957年第1期上刊出。。这种观念贯彻于杜蒙的整个学术生涯,其后期对于近代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研究更是直接体现了这一点。
1938年杜蒙通过了民族学的资格考试。紧接着,杜蒙计划进行一项艺术史的研究,研究当时法国工具中的凯尔特人(Celtic)遗迹,但却因为战争而被迫停止[注]Robert Parkin,“Louis Dumont:From Museology to Structuralism Via India”.In Robert Parkin and Anne de Sales(eds.).Out of The Study and Into The Field:Ethnograph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ench Anthropology,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10,236.。他应征入伍,并很快成为德国的战俘,被留在汉堡郊区的一家工厂干活。在这里杜蒙自学了德语,并翻译两到三本德国关于法国民俗的著作。在此之后,杜蒙感觉自己的德语已然足够,便开始学习梵语。他学习语言的所有材料都是其妻子从法国寄给他的。他决心将自己的研究志趣从法国转向印度。为什么转向印度而非其他地方?杜蒙自己给出了两个原因:其一是他自己一直以来的兴趣,其二便是莫斯(莫斯的作品及其口头典故极大地激起了杜蒙的研究兴趣)[注]Christian Delacampagne,“Louis Dumont and the Indian Mirror:An interview with Louis Dumont”(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 Monde,January 25,1981.).RAIN,No.43,1981,p.4.杜蒙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过有关莫斯的一次演讲,其中他称颂了莫斯的“渊博”。他写道:“莫斯整个人散发出一股令你不由自主便被吸引住的力量……可能他受我们这些学生欢迎的秘密就在于,他跟好多学院派人士不一样,因为只是对他而言不是分隔开来的另一种活动,他的生活已经变成为知识,而他的知识亦即生活了,这点也正是他至少能对某一些人发挥出像宗教师或哲学家的影响力之所在”([法]路易·杜蒙:《马歇·牟斯:处于转变成形过程当中的一门科学》,见《个人主义论集》,黄柏棋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277页)。。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德国耆那教研究专家瓦尔特·苏柏林,并跟随其进行专业的梵语学习,这一切也是得益于监禁他们士兵的宽容。在某种程度上,杜蒙是相当感激这段“囚禁”的生涯:“(你知道)作为莫斯的学生,不懂梵语就开始研究印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正是那段囚禁的岁月促使我去研究印度,那段经历(学习梵语)给了我巨大优势”[注]Christian Delacampagne.Louis Dumont and the Indian Mirror:An interview with Louis Dumont”(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 Monde,January 25,1981.).RAIN,No.43,1981,P.4.[16]4。
回看杜蒙的早期学术生涯,我们可以说,若没有此段进入传统民俗与艺术博物馆工作的经历,或许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人类学家。故而,我们强调博物馆是杜蒙学术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里开启他的民族学人类学之旅,恰如他自称的那样,博物馆是他自己进入民族学的一扇门。从“青春期叛逆的少年”到“以民族志学者为天职”,我们或可说杜蒙的学术之路多少是有些偶然的。或许,没有这种偶然的机遇,杜蒙会像他祖父一样成为一个艺术家。但也正是这种偶然,使得人类学史上多了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思想家。
三、声名鹊起:杜蒙的“印度社会学”
1949—1950年,杜蒙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做调查,其中有八个月是跟Pramalai Kallar(此为由以前的武士和土匪组成的一个卡斯特)在一起的。何以要选择此地作为他的首个田野点?杜蒙解释为,他想去发现古代印度文化与达罗毗荼文化之间“活生生的联系”(living links),他想从当下出发去阐明历史[16]5。杜蒙此说,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古典印度(文化)起源的过程中,底层的达罗毗荼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达罗毗荼文化在由吠陀教转至古典印度教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7]16-17。当然,就这一选择的解释,也符合杜蒙想研究整个印度文明的说法。
西媒一直在使用同南海争端相关的叙事来塑造一个扩张主义中国的形象,因此,在对征兵宣传片的报道中引入南海问题,实际是在引导读者按照他们解读南海争端的方式(规范性解读)来解读解放军征兵宣传。同理,在报道中引入伊斯兰国也是为了“帮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解放军究竟意味着什么——解放军“嗜杀、黩武”,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解放军同伊斯兰国一样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1945年战争结束后,杜蒙重新回到博物馆工作。他主持了博物馆传统家具研究项目的最后一个阶段,并负责《法国民族志月刊》(Mois d’ethnographie Francaise)的出版工作。同时,他准备对La Tarasque(一种传说中的龙)进行研究。杜蒙告诉我们,他在囚禁期间开始对龙感兴趣,并就印度与欧洲的龙进行比较。杜蒙说为此他专门请教过法国比较神话学家乔治·杜梅(Georges Dumez),杜氏建议他进行一项专题性的研究[17]。就此,杜蒙研究了法国南部塔拉斯孔(Tarascon)有关La Tarasque的民间节日。这种比较研究的视角从他的第一本专著开始便显露无疑,且贯穿其一生的研究。杜蒙这种重视比较的研究进路或方法,很多学者将其归为涂尔干、莫斯一系年鉴学派的影响。杜蒙后来回忆此段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光,说道:“那段时间,我着魔一般地工作(我的睡眠时间从未如此之少),完成因战争中断的学位学习,并学习泰米尔语及印地语”[17]14。
1951年1月,杜蒙从印度回到传统民俗与艺术博物馆,并负责了博物馆一个关于布列塔尼(Breton)家具的临时展览[17]17。同年10月杜蒙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在这里做了四年的讲师。在牛津的四年(1951—1955),杜蒙逐渐熟悉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并在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指导下进行“第二次训练”。杜蒙言道,牛津的训练使他养成了一个看问题的“立体视角”(stereoscopic vision)[17]18。也是在牛津期间,杜蒙完成了上文提到的两部著作《次卡斯特》与《阶序与联姻》。在《次卡斯特》一书的写作过程中,杜蒙再一次来到印度(印度北部)做了为期六个月的补充调查。
在中文世界,杜蒙最为知名的作品当属《阶序人》。当然,我们也都清楚杜蒙正是因为此书才使他在整个社会学人类学界、乃至印度学界享有盛誉。《阶序人》一书是杜蒙对于印度卡斯特体系的系统研究。他指出,印度的卡斯特体系是宗教性的(以印度教为核心),其核心特征是洁净与不洁的对立。其表现为“身份”与“权力”的分离。“身份”即“阶序”,是宗教性的,“权力”(政治经济)表现为世俗性的,从属于宗教。在印度社会,阶序的顶峰是婆罗门,即祭司;国王的权力须经婆罗门承认才具有神圣性,如果未经婆罗门的神圣化手续,国王的权力就会沦为完全依赖暴力。婆罗门在精神的或绝对的方面至高无上,但是在物质上则是依附性的;国王在物质上是主宰,但在精神上则是从属的……阶序从来没有和赤裸裸的权力联结在一起,而是一直都与宗教功能相连,因为宗教是普遍真理存在于这些社会中所表现的形式。故而,杜蒙说,“阶序基本并不是一串层层相扣的命令,甚至也不是尊严依次降低的一串存有的锁链,更不是一颗分类树;而是一种关系,一种可以很适切的称为‘把对反含括在内’(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的关系”[9]417-418,441-443。
①三脚架 ②托盘天平 ③瓷坩埚④坩埚钳 ⑤泥三角 ⑥石棉网 ⑦烧杯⑧蒸发皿 ⑨铁坩埚 ⑩干燥器 ⑪酒精灯
50例阴茎鳞状细胞癌患者,均以术后行18F-FDG PET/CT显像检查为起始时间,每隔3个月为随访时间节点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对怀疑复发和转移的病灶行手术切除活检或穿刺活检,病理确诊为阳性的患者结束随访,本研究所选病例均如期完成随访。
A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statement was obtained from each patient prior to study inclusion.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consensus of the local ethical committees of each center and of all the patients.
1957年他与戴维·波寇克(David Pocock)一起创办了《印度社会学集刊》(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之所以用“Contributions”一词,是为了突出他们共同的努力[17]19。帕金指出,该期刊的目的在于将“印度人类学从原来的各种民俗学的、进化论的和功能主义的老路上拉出来从而使其进入到结构主义的轨道上去,这项事业显然是以《社会学年鉴》为蓝本的”[20]。接下来的近十年,杜蒙在该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印度相关的研究,包括村落共同体、卡斯特、婚姻、亲属、遁世修行及民族主义等等。他在《集刊》上所发表的系列论文,都是在为其后来的大作《阶序人》做准备[1]199。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年青学者,并与其他的地方学者进行了合作研究。杜蒙后来回忆,这段时间他在自己的国家,既有了物质上的保障又得到学术上的认可,是他自己做研究的一个理想状态[17]19。1964年,波寇克退出了《集刊》的编辑工作,杜蒙独自坚持了三年之后,于1966年宣告停刊[注]杜蒙在法国主办的《集刊》于1966年停刊。事实上我们知道现在仍有《印度社会学集刊》的存在,现在的期刊其最早历史可追溯至1966年,印度人类学家马丹在印度找到出版杂志的资助上,并征得杜蒙的同意,沿用了原来的名字。新系列的《集刊》第一期于1967年出版(参见T.N.Madan,Sociological Tradition: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dia.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11,p.206,233.)。
1957—1958年,杜蒙来到印度北部的戈勒克布尔地区(Gorakhpur district),在此共做了15个月的调查。尽管此次田野并不比他在印度南部的时间短多少,但杜蒙关于此次调查的作品却少之又少。他曾向马丹抱怨说,戈勒克布尔地区气候干燥,文化复杂(一个村子竟然有众多的卡斯特),且村民远不如泰米尔人有趣、聪明。在1982年时他已然忘记了北部村落的方言,但泰米尔语将会终身留存[17]21,[1]199。尽管如此,北部地区的田野一直以来都为杜蒙的南部研究提供着比较的视角,这点在其后来的名著《阶序人》中清晰可见。
白天和夜间降水量对比(图3b)来看,白天降水明显多于夜间,主要是因为午后降水较多,以及17:00点最大降水出现在白天段(08—20时)。降水随海拔变化,无论白天还是夜间,都呈现出“先增多,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中间3个海拔的降水量明显多于山顶和山脚,尤其是640 m高度降水量最为明显。
1962年,杜蒙受邀于威尼斯东方学院文化与文明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t the Venetian Institute of the Orient)进行了三场有关印度社会的讲座,讲座内容涉及印度的社会、宗教、思想、历史及当代变迁。1964年,讲座内容以《印度文明与我们:比较社会学大纲》(La civilization indienne et nous:Esquisse de sociologie comparée)为题在巴黎出版。1965年该书的意大利语译本问世,遗憾的是这本小书从未有过英译本[1]199。
1967年,《阶序人》法文版出版,这部作品使他声明远播,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如其所言是“毁誉交加”。1970年,该书的英文版问世,期间印度学、社会学、人类学界对杜蒙的《阶序人》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在1980年再版的《阶序人》的英文版中,杜蒙写了一篇长序,对学界的评价与质疑一并做了回答[注]See Louis Dumont,Homo Hierarchicus: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Translated by Mark Saainsbury,Louis Dumont and Basla Gulati,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xi- xlii;中译本,[法]路易·杜蒙:《阶序人》,王志明译,台北:远流事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40页。,具体内容可参阅该文,此处不再赘述。同样是在1967年,杜蒙创建了印度与南亚研究中心(CNRS,the Centre d’Études de l’Inde et de l’Asie du Sud)。1976年,他又创立了ERASME (Équipe de Recherche en Anthropologie Sociale:Morphologie,Échanges),这是CNRS里面一个“以核心价值观念为基础来进行整体比较”研究的小组[注]See Robert Parkin,“Louis Dumont:From Museology to Structuralism Via India”.In Robert Parkin and Anne de Sales(eds.).Out of The Study and Into The Field:Ethnograph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ench Anthropology.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10,p.237.。
1.2.1 调查表 自行设计:①久卧病患照护者一般资料调查表;②久卧病患照护者30°侧卧位翻身护理掌握测评表;③久卧病患压疮分期标准表。调查表以《临床护理技术规范》[1]、《成人压疮预测和预防实践指南》[2]相关防压疮理论为依据。
对文化的准确、成熟的把握,体现着海归新生代企业家的认知与识别能力,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应该充分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相当一部分新生代企业家接受着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在初中、高中时,就离开家乡,独自踏上异国求学之路,因此,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内涵还没有全面把握,又因为在海外求学的过程中,接触到的西方文化是表层的。所以,就目前来说对两种文化都还没有做到深入的了解,容易将两种文化机械地相分离,没有找到如何将两种不同文化相融合的途径,认为两种文化没有办法相互交流。笔者认为中西方文化中,中国文化善于根据当前的现状做出灵活的决定,西方文化倾向于按照既定的目标去完成任务,受周围环境干扰较少。
通过对于印度社会的研究,杜蒙发现了其背后的主导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即为“阶序”。杜蒙的印度社会研究,不仅使杜蒙发现了伴随其学术生涯最为重要的理论概念“阶序”,还使得他透过印度这面镜子,看到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便促使杜蒙转换其研究方向,由关注印度社会转而考察近代西方社会。用杜蒙自己的话来说,从了解“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转而思考“平等人”(Homo aequalis)。
提起杜蒙,人们都会想起他的成名作《阶序人》。我们也知道,确实是印度研究,是《阶序人》使杜蒙成为闻名世界的人类学家。我们在强调“印度社会学”成就杜蒙的同时,更多的是希望他对印度这个“文明体”的研究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方法上的启发。在面对一个有着丰富文献资料的印度文明时,杜蒙强调印度社会的研究必须要结合传统印度学和社会学,要充分利用既有的文献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当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在关注一个社区或一个村庄的同时,要时刻谨记“印度是个整体”或印度乃为“一”(India is a one)。此即要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所关注的村庄或社区是大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借用杜蒙的思路,我们或可以说中国也是“一”(China is one)。我们如此表述,不是说想要去抹杀不同地方、不同区域的多样性。正好相反,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借用史学家的话“中国既是‘一’,又是‘无数’”。“这个‘一’和‘无数’并不对立,而且一并不是从无数中抽象出来的,相反,‘一’只能借助于无数才能呈现自身”[21]。在此思路的导引之下,我们期望能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探寻表述“中国”的方式。这无疑是杜蒙于我们的隐形财富。
四、作为“思想史(观念史)”研究的人类学家
借着西方去描绘印度,杜蒙勾勒出了一幅阶序性社会的风貌(configuration),也正是印度帮他“问题化了西方”[1]202。借着印度去观照西方,由阶序性社会去了解平等性社会,这个思路引导出了杜蒙所言关于“平等人”的研究,促使杜蒙转向了近代西方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研究。
杜蒙言道,“我对近代意识形态的研究始于1964年,此一研究的思想路线很自然地是跟对印度社会所作社会学上的理解研究所需之事倒了过来;我们必须走出近代个人主义式的观念以外,才能对印度方面的材料来作分析,而得以掌握住整体之属的情况与整体社会”[22]14。“人类学的研究观念,可以反过来让给我们更能了解自以为已知怎么一回事的近代思想与价值系统(因为思想和生活于其中)”[22]13。至此,杜蒙由印度社会研究,逐步转向对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考察与反思,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其去世。杜蒙这方面的系列思考与研究,共有三本专著问世:《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胜利》(1977)[注]Louis Dumont,From Mandeville to Marx: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该书的英文版、法文版同年(1977)出版,法文版题为Homo aequalis I:Genèse et épanouissement de l’déologie économique.正是杜蒙所言的“平等人”。、《个人主义论集》(1983,1986)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法国到德国再至法国》(1994)[注]Louis Dumont,German Ideology:From France to Germany and Back.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该书的法文版于1991年出版:Homo aequalis II:L’idéologie allemande,France-Allemagne et retour.。
杜蒙指出,在近代观念的谱系当中,经济曾被含括于政治(道德)之中,如同在印度宗教含括了政治一样。故而《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一书的主题便是去发现“经济”如何逐步独立于“政治”(道德)之外。杜蒙写到,“在多数社会里,主要指高度文明的社会(可称之为‘传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men)要远比人与物的关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things)重要;而此一优先顺序,却在近代型社会中被颠倒过来,于其中人与人的关系臣属于人与物的关系”[23]。与这样一种优先顺序颠倒密切相关的,是近代社会对于财富的一种新观念。在传统社会,动产(土地)与不动产(金银财宝等)区别明显,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往往据于支配他人的地位。这样一种权利或财富的观念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整体主义)。到了近代社会,人们的“财富”观发生了变化,动产的地位上升,因而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财富观念。正是这一独立财富范畴的出现使得“经济”与“政治”界限明晰,也正是对于这样一种财富观追求,一种视“个人”乃一价值拥有者的个人观念(个人主义)出现。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现有临床数据分析,口腔溃疡含片治疗RAU安全有效,分析研究过程严谨,结果可靠,RCT研究也均有明确的纳入标准,但6项研究总样本量均偏少,且均为中文文献,所入选的杂志级别不高,降低了Meta分析的质量;同时随机分配的具体方法,分配方案是否恰当也未表述清楚,故代表性也不高,漏斗图也显示出一定的发表偏倚。因此还需要更大量更严格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的开展,进一步综合评价口腔溃疡含片治疗RAU临床疗效。
《个人主义论集》一书是杜蒙多年以来对于近代西方意识形态即个人主义研究的集结。他就个人主义之历史起源进行了追溯,透过宗教、政治以及经济三个层面,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意义上个人主义的逐步兴起,并成为近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同时,杜蒙关注了近代意识形态与国家相遇之后的“变体”(variants),亦即对德国意识形态(兼与法国之比较)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后来被杜蒙继续扩充成专著),在此基础之上,杜蒙考察了近代意识形态的具体运作,即对于希特勒之极权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主义在近代社会几乎以一种“全球”或“普世”之态势铺展开来,在与不同的国家“传统”相遇之后,亦产生了许多危及人类本身的“主义”,如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等等。如前所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杜蒙对于近代意识形态的“国家变体”(national variants)研究的继续扩展,如书名所示,此书旨在关注“近代意识形态的德国变体(the German variant of modern ideology)”。
杜蒙指出,始于18世纪,特别是在德国狂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期间(主要是1770年—1830年),德国文化在人文学科方面(哲学、美学、文学等等)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这一发展,使得德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到解放,在此之前法国文化在德国居于主导地位,甚至给人一种两国在文化是联成一体的错觉。此一发展,使得德国逐步与法国(及其周边邻邦)“疏离”。而正是这一发展奠定了近代德国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24]17-19。通过研究德国学者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杜蒙指出特洛尔奇笔下德国人看似相悖、矛盾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对于整体的效忠精神;其二是内省式的个人主义。德国人在其血液里有对一件事情、一个观念、一项制度、一种超个人实体的效忠精神。另一方面,德国人又强调内省式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源自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一矛盾、相悖的特色在德国人的Bildung(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这一概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杜蒙笔下,德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形貌被归结为共同体式整体论(community holism)与自我修养式个人主义(self-cultivating individualism)的混合。杜蒙说德国人的认同主要是文化上,而政治方面则为次要(法国则恰恰相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其在政治方面的完全缺席。他提到了德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即“普世主权”(universal sovereignty)。此一思想遗产可追溯至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发展至近代便形成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泛德意志主义[24]21-22,199-200。德国人相信,他们有主宰(支配)世界的天职。故而,杜蒙给德国的意识形态总结出三大特色:(1)整体主义大行其道。(2)路德改革的决定性影响。(3)普世主权幽灵的回荡[24]24。 那么,在此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德国人可如此描述:“我本质乃是一德国人,正因为我是德国人才使得我成为一真正的人”;法国人则与此不同:“我本质上乃为一人,生而为法国人则属巧合”[24]199。
无论是对于近代西方社会个人主义起源的追溯,还是对于德国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些无疑都是杜蒙对于所谓“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是一个亲历战争的人类学家对于他所处时代问题的深刻忧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强调杜蒙是一个从事“思想史(观念史)”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同时,也将其列入伟大的思想家行列。
负重攀越、勇往直前的开磷人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加快步伐迈上了转型升级的新征程。30年前,开磷人排除万难走新路、搞化工,提出了“稳定矿山,发展加工,建设两个基地,开发两类产品”的发展战略,决定依托磷矿石资源优势,发展磷化工,建设磷化工生产基地。从此,黄磷厂、重钙厂相继破土动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混肥等多元化磷化工产品生产装置先后建成投产,开磷在高浓度磷复肥领域逐渐崭露头角。“建设两个基地(磷矿石生产基地和磷化工生产基地),开发两类产品(磷矿石产品和磷化工产品)”的发展战略变成现实。
五、结论与讨论
不管是印度社会还是近代西方(欧洲),杜蒙的研究一直关注所谓的“文明社会”。杜蒙通过印度与西方的互相观照,从其中看到了各自社会中至高无上的价值(value),前者为阶序,后者为平等。以阶序为主导价值的社会,社会乃一整体,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杜蒙称其为整体主义(holism)。以平等为主导价值的社会,“个人”成了整个人类的化身,成了万物的准绳,个人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存在。他称此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通过两种主导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对比,杜蒙指出近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已为个人主义所主导,“唯平等是尚”成了普遍追求。而杜蒙对于近代意识形态所产生之始料未及的后果(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的追踪,旨在反思近代社会个人主义之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学家,也是一位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思想家。杜蒙的这一反思无疑是与他不仅亲历战争且做过德国战俘有关。在一个倡导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何以会出现纳粹主义?这是时代留在杜蒙思想当中的印迹,也是杜蒙他对自己所处时代不满的表达。他时刻提醒我们,“于有些事而言平等可以办到,而对于有些事平等则亦无能为力”[25]。当人们追求极致的无差别的平等时,就将“平等”视为了至高无上的价值,而正义、自由等等其他的价值便已经处于一个较低的层级了。这何其讽刺。西方人极其厌恶hierarchy,却无形中之中处处暗藏着hierarchy。由此,便可以反过来理解杜蒙何以积极推销其在印度发现的“阶序”价值,因为其强调了对于差异的包容,而不是抹杀差异。我们也由此看到了斯特伦斯所说的,在杜蒙的社会宇宙观中深刻的道德关怀,其最为核心者乃为——“对差异的包容与承认”(tolerance and 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2]132-135。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能力的发展是其核心内容。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科教学的过程,而实验又是化学教学的基础,那么究竟什么是化学实验能力?化学实验能力又由哪些要素组成?初中化学课程中的实验能力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在等待我们进行深入了解与探究。
我们对于杜蒙个人学术史的关注,旨在对其整个思想理论有一个更加明晰的认识。同时也如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我们希望阅读杜蒙——这一关注“文明社会”的人类学家的著作,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复杂文明体。杜蒙的整体论思想,他对于社会行为背后价值观念结构的关注,他对于差异性、多样性予以包容的强调,他对于自身所处社会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反思等等,这一切对我们的思考和研究无不有所助益和启发,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深入阅读、理解和思考。在这方面,桑高仁(P.Steven Sangren)、梁永佳等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杜蒙之于中国研究可能的意义[注]桑高仁对于台湾大溪的研究,以及梁永佳对云南喜洲的研究均借鉴了杜蒙氏的“hierarchy”(阶序)概念,重点突出其“把对立情形含括在内”(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的特点,具体请参见P.Steven 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从青春期的叛逆少年,到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我们通过梳理其个人生活史见证了杜蒙的成长和经历。通过此叙述,我们看到了个人经历及其所处时代,在一个学者及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样,我们也在这一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思想不断变化的杜蒙,我们可以称他为“印度学家杜蒙”,或者我们还可以称他为“思想史家杜蒙”。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的记得,杜蒙是一个人类学家,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当然,我们在强调杜蒙是一个人类学家的同时,要不吝言辞地去称赞其思想的超越性。他一方面重视经验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在做全球性的反思,其所关心不仅是印度或西方,乃是整个人类。我们会同很多学者那样称呼杜蒙为一个“民族志学者”,一个理论家,一个人类学家,同时我们还称他是一个“法国式思想家”。
参考文献:
[1]MADAN T.N.Sociological Tradition: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dia[M].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11.
[2]STRENSKI I.Dumont on Religion[M].London: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8.
[3]COLLINS J.“French Liberalism’s ‘India Detour’:Louis Dumont,the Individual,and 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68 France”[J].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2015,12(3):708.
[4]赵亚川,黄剑波.阶序、个人主义与价值——杜蒙及其“文明社会”研究.未刊稿.
[5]黄剑波.人类学理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
[6]杜蒙.个人主义论集[M].黄柏棋,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198.
[7]MOFFATT M.Editor’s Introduction[M]//Louis Dumont.A South Indian Subcaste:Social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Pramalai.Translated by Michael Moffatt and A.Mor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4.
[8]PARKIN R.Louis Dumont:From Museology to Structuralism Via India[M]// Robert Parkin ,Anne de Sales(eds.).Out of The Study and Into The Field:Ethnograph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ench Anthropology.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10.
[9]杜蒙.阶序人[M].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10]BERATTIE J.H.M,LIENHARDT R.G.(eds).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Essays in Memory of E.E.Evans-Pritchar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328-342.
[11]DELIÉGE R.Lévi-Strauss Today:An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 Anthropology[M].Translated by Nora Scott,New York:Berg,2004.
[12]ALLEN N.J.Obituary:Louis Dumont(1911—1998)[J].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Oxford(JASO),1998,29(1):3.
[13]BRUCKNER P.Le Grand comparateur:un entretien avec Louis Dumont[M]// Ivan Strenski.Dumont on Religion.London: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8:7.
[14]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M].辛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24-125.
[15]PAWETT W.Georges Bataille:The sacred and society[M].New York:Routledge,2016:27-28.
[16]DELACAMPAGNE C.Louis Dumont and the Indian Mirror:An interview with Louis Dumont[J].RAIN,1981(43).
[17]GALEY J.C.“A Conversation with Louis Dumont”.Paris,December 12,1979.
[18]DUMONT L.A South Indian Subcaste:Social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Pramalai[M].Translated by Michael Moffatt and A Mort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9]梁永佳.路易·杜蒙论印度种姓制[J].民俗研究,2005(1):49-50.
[20]帕金.法语国家的人类学[M]//帕金.人类学的四大传统.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91.
[21]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111.
[22]杜蒙.个人主义论集:导论[M].王志明,译.台北:远流事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14.
[23]DUMONT L.From Mandeville to Marx: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5.
[24]DUMONT L.German Ideology:From France to Germany and Back[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17-19.
[25]DUMONT L.Essays on Individualism: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265.
Between"Civilizations":LouisDumont'sIntellectualPortraitandAcademicLegacy
HUANG Jian-bo,ZHAO Ya-chuan
(China Modern Urban Research Center and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French anthropologist Louis Dumont is famous for his research on Caste?system?in India,and his late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re also of great concern.Dumont’s thoughts,varying from early concerns on material culture to the study of western ideology(values) later in his academic career,have been in the midst of change.This is why Dumont maintained many titles,such as structuralism anthropologist,Indologist,historian and so on.Looking back at his academic life,especially the "generative process" of his theorie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an apparent conclusion will emerge that Dumont is not only a structuralist who transcends Lévi-Straussian,but also an anthropologist and an thinker as well who concerns deeply about his time.
Keywords:Louis Dumont;India;Ideology;Anthropological theory
收稿日期:2019-03-11
作者简介:黄剑波(1975- ),男,重庆彭水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人类学理论、人类学中国研究、宗教人类学研究;赵亚川(1992- ),男,甘肃渭源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人社会、西北民族研究。
引文格式:黄剑波,赵亚川.往来于“文明”之间——杜蒙思想肖像及其学术遗产[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4):1-13.
① 谨以此文纪念杜蒙逝世20周年。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计划支持,特此致谢。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9)04-0001-13
(责任编辑 张楠)
标签:印度论文; 斯特劳斯论文; 社会论文; 人类学家论文; 法国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人类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