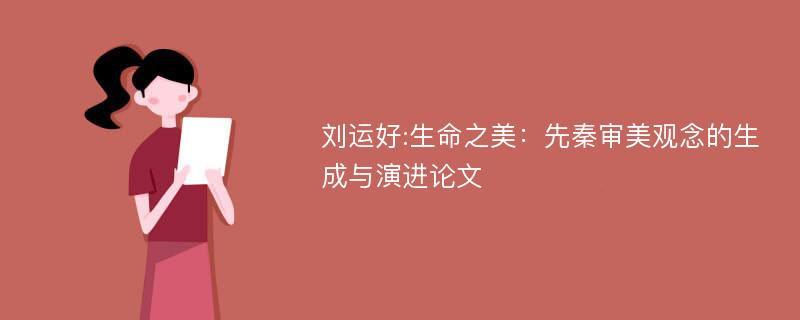
内容提要先秦审美观念以时间人文化为生命起点,礼乐主体化为生命精神,任性逍遥为生命情调,自由自律为生命境界。原始歌舞由狂野的生命宣泄发展为和谐的节奏韵律,并成为某种生命意识的象征,标志着华夏审美观念的萌生;至周孔乃一变,周公创立了系统的礼乐文化,孔子以“游于艺”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本体,“乐以忘忧”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完成了由自觉到自由的审美境界转换;至庄生又一变,庄子以本然之性为核心救赎礼乐文化造成的人性异化,以道德出乎自然重构礼乐文化的内涵,以无待逍遥诗化生命自由的情调;至屈原再一变,屈原辞赋气贯天人、壮浪恣肆的自由境界,与庄子诗化的生命情调形成横向呼应;道德自律、弘毅贞刚的主体人格,与礼乐文化内化的生命精神形成纵向回归。先秦审美观念呈现出生成于一点、发展于两线、又收拢两线集为一点的演进脉络。
关键词先秦审美观念 人文化 主体化 生命精神 审美境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魏佛教诗学研究”(项目号:18AZW006)的阶段性成果。
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厘清审美观念与审美理论的关系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审美观念不能等同于审美理论。观念,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感性的;可能是知性意识,也可能是直觉认知;可能存在于理论体系中,也可能存在于审美行为中。简言之,观念是主体生命的意识存在,以行为、文本为表征;理论是话语体系的物质存在,以概念、范畴为表征,二者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不同。研究审美观念史与研究审美理论史也不尽相同:前者偏重于生命哲学的史的诠释,后者偏重于艺术哲学的史的诠释。只有当审美观念借助话语体系物化为审美理论时,二者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本文正是从生命哲学的史的视角,论述先秦审美观念的生成与演进。
从生命哲学上说,生命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审美观念必然源生于生命意识。贯穿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核心,是生命存在的发现;充实的生命精神和审美的生命境界,是人类文明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明标识。人类在满足了生存和安全需求的基本条件之后,对生命认知的自觉和对主体存在的确认,逐渐发现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律动关系,我与周遭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经过原始的狂放激情之后,逐渐趋于理性的生命精神。在“原始思维”与“玄学思维”的互动、发展、共振的过程中,人类经历了发现生命之美、表现生命之美到创造生命之美的漫长历史进程,审美观念也经历了一个萌生、发展、成熟的历史曲线。先秦,是华夏审美观念从生成到成熟的时期。
华夏审美观念孕育于特定文化的历史土壤,具有传统的连贯性、阶段性和再生性。大致说来,先秦审美观念萌生于原始文明时期,原始歌舞由狂野的生命宣泄,发展为和谐的节奏韵律,并成为某种生命意识的象征,标志着华夏审美观念的萌生。至周孔乃一变,周公创立了系统的礼乐文化;孔子以“游于艺”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本体,“乐以忘忧”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完成了礼乐文化由自觉到自由的境界转换。至庄生又一变,庄子以人的本然之性为核心,救赎礼乐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以道德出乎自然,重构了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以无待逍遥解脱了人生枷锁,诗化了生命自由的情调。至屈原再一变,屈辞气贯天人、壮浪恣肆的自由境界,与庄子诗化的生命情调形成了横向回应;道德自律、弘毅贞刚的主体人格,与礼乐文化内化的生命精神形成了纵向回归——诗性自由和道德自律有机融合,并积淀为生命本体,铸造了审美的人生境界。简言之,生成于一点,发展于两线,又集两线为一点,是先秦审美观念生成演进的基本脉络。
时间与生命:审美观念的起点
生命是人生联结世界的唯一纽带,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从生命存在的感知开始。生命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人文化与生命时间化的二元互动,是一切审美观念发生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与生命,是催生原始文明时期审美观念诞生的两大基本元素。
然而,“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九歌·东君》)。在古人观念中,礼与乐浑然一体,有难以剪断的联系。礼乐的发生,源于对生命的自然本质和本然情性的社会化重塑。也就是说,先王制定礼乐就是为了约束人的情感,故论乐“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⑤;论礼“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⑥。六志即六情,六气即自然;体性中庸谓之中,情发于中谓之和。情生于自然,必审其类型而以乐制之;情发乎体性,必节以中和而以礼制之。礼乐的共同功能就是规范性情,调适心理,使生命的本质由自然化转向社会化,从而完成主体人格的重塑。所以,在西周礼制中,礼与乐是共生的“仪式”,钱穆说:“狭义的礼是指当时(西周)的生活方式,方式中有许多富于礼节性的仪节。执行这些仪节,配合着各种舞蹈和音乐。”⑦一方面,先王制乐以适性为原则,使性合乎礼,“夫乐有适,心亦有适。……适心之务在于胜理”(《吕氏春秋·适音》)。所谓乐适,即韵律和谐,清浊适中;心适,即心境平和,祛恶适性;胜理,即和谐性情,性合于理。乐在于和,和即适性,适性即胜理。另一方面,先王制礼也以适性为原则,使礼合乎性,“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记·乐记》),礼合乎情,乐和其声,才能以礼检情,以乐正性。惟此,礼与乐二元互动,构成统一关系。从个人上说,乐之适性,故能“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吕氏春秋·适音》),即适性之乐可以治身全生;礼之制情,故使“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即制情之礼可以规范行为,乐和礼互补、统一,完成“和心”“成人”即调和心性、重塑人格的过程。从社会上说,礼乐和刑政虽然不同,但是“及其检情归正,同至理极,其道一也”⑧,礼乐和刑政互补、统一,完成国家制度的完善。由适性到胜理,检情到归正,并与国家刑政互补、统一,使礼乐教化成为联系人与国家制度的一根逻辑链条。
其次,在施工前期,管理人员对公路工程的具体施工设计和人员安排无法做到合理调配,导致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岗位不定,现场混乱,工序复杂,工期拖延,最终出现延工、误工的现象[3]。而且部分施工队的进度控制意识薄弱,无法按照施工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施工任务。个别施工队为加快工程进度,随意增加施工人员,而部分施工人员由于没有接受专业岗位培训,匆忙上岗,造成部分已经完工的工程质量不合格,因无法通过质量验收而必须返工,不仅拖延工期更增加了施工成本。
原始生民的生活场景和观念意识,已经掩埋在厚厚的历史尘土之下,既无法还原,也难以描述。我们只能依据人类进化的历史和存世文献的记载,影影绰绰地想象或推断原始生民的可能存在的生活影像和观念意识。
从人类进化的历史和神话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早期人类与鸟兽同群,和动物界并无截然界限。庄子所谓“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实际上正是对原始生民生活状态的想象性描述。人类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时,并没有“万物之灵”的自觉和自负,只是自然生命中的一个种类。神话文献中记载的人类始祖女娲、伏羲、盘古“人面蛇身”或“人首蛇身”,以及诸种神灵“龙身人头”“人面鸟身”之类,纵然如学者所指出的,“实即指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①,那么这些图腾、符号和标志,必然积淀着一种无意识的历史现象,隐约呈现了一种基本事实:原始生民,生活上与鸟兽同群,观念上与鸟兽同质。因此,动物界对待时间与死亡的懵懂无知,也是早期原始生民的基本认知属性。然而,面对蛮荒、狰狞而又神秘的世界,人类基于追求生存的生命本能,在采集过程中,不断经历自然星象和物种的变化,渐渐发现了时间的变化;在渔猎过程中,不断经历突发性灾难和死亡的威胁,又渐渐发现了生命的存在。“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楚辞·天问》)屈原对生命生成、时间变化的追问,或许正是原始生民最初发生的疑问。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这一疑问又逐步诱发了对时间和生命的最初认知。这种认知,或许是直观的、粗糙的、朦胧的、幼稚的,却又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起点。
本方法利用摄像头输入的酶标板目标图像的图像处理方法,通过实验菌体的培养,根据菌体生长时菌液的浑浊度变化计算了不同时期每个培养孔区域的HSV颜色平均值,为酶标板孔菌群浑浊度的检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为后续通过机器视觉对酶标板孔培养孔生长状况符合要求的细菌的筛选提供了一种依据.此外,如果要更好的将此识别系统应用于微生物自动化生产实践中,还需要更多更精确的菌体培养实验得到不同菌体不同生长时期菌液与颜色特征值的关系曲线,获得线性关系,为菌体筛选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
经历了从旧石器渔猎时期到新石器农耕文明时期的漫长历史发展,原始生民对时间和生命的认识,逐渐趋于细密、清晰、理性、成熟。在对自然的观察中,发现时间不再是混沌的整体,而是存在于自然变化的段落之中;在对生命的观察中,发现生命不再是混沌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特定时间的单元之内。宇宙自然的物换星移、季节转换,人类生命的盛衰有时、生死相依,都贯穿着一个无形存在的时间单元。自然的时间被赋予了主观色彩——时间人文化;自然的生命也被赋予了时间标尺——生命时间化。人类在深化时间认知的同时,也深化了生命的认知。然而,在原始思维中,时间的人文化催生了生命的时间化,二者的思维生成存在着因果关联。也就是说,原始生民只有将宇宙自然的变化,定格于确定的时间单元,如四时节气,才可能发现生命是时间单元的存在。而时间和生命认知一旦叠合,就产生了真正意义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的产生,催生了关于生命长度、质量的遐想。于是,原始生民开始幻想“不死之药”“不死之野”的存在,延续生命的长度;开始追逐生命过程中的审美装饰、感官享受,提高生命的质量;开始关注生命终结时的祈祷、祭奠,寄托生命的期待。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淮南子·览冥训》)的美丽而忧伤的神话,而且女性也开始发现了自己的青春,《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女性采摘姑媱山上美丽焉草的花叶果实,装饰自己,以得到“媚于人”的审美效果,其目的乃在于取悦男性,享受两性的欢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想: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其杖“化为邓林”;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灵魂化为精卫,其神话故事的背后,就蕴涵着对逝去生命的祈祷与祭奠。将生命的诗意遐想叠加到时间意识之上,时间不再是一个混沌、自然的客观存在,而是与生命、青春密切关联的心理存在,从而使时间的人文化浸染了浓郁的审美色调。
生命意识的产生,也催生了原始艺术的审美。最初的原始艺术,或许具有记事的意义,如发现位于新疆和田的原始“桑株岩画”,以简约线条刻画人物的不同形状,就是一种原始记事方式。这种记事方式与“结绳而治”并行,就成为“易之书契”——中国文字的最早源头。但是,原始歌舞则是通过表现生活场景的过程,在粗野而热烈、狂放而孔武、壮阔而激情的舞蹈形式、节奏、场景中,宣泄生命的情绪,获得生命的快感,表达生命的期待,蕴涵审美的“意味”。今天依然存在的彝族《十二兽舞》、苗族《水鼓舞》,就是原始生民的生命盛宴的活化石。在文献记载上,《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八曰总禽兽之极。”②《尚书·益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以允谐。”③“操牛尾”粗野、热烈的形式,“投足以歌”“击石拊石”狂放、孔武的节奏,“总禽兽之极”“百兽率舞”壮阔、激情的场景,“载民”“玄鸟”的某种“有意味的形式”,以及“遂草木”“奋五谷”“庶以允谐”的祈祷与期待,与今天保留下来的少数民族原始生态的歌舞,仍然存在着文化上的血脉关系。一切生命的节奏与力量、欢乐与痛苦、祈祷与期待,在这如痴如狂、如火如荼的迷醉场景中,得到了再现、释放和表达。正是在这力量与美感、壮烈与粗野、祈祷与期待的原始艺术中,粗略地勾画了原始生民的生命状态和精神世界,才使具有时间内涵的生命意识进入审美化的状态。
在人类文明的蹒跚脚步中,原始歌舞除了宣泄生命的情绪、获得生命的释放、具有生命的美感之外,其选择的内容孕育着朦胧的价值取向,严整的节奏孕育着萌芽的行为秩序,祈祷的内容孕育着潜在的教化内容,功业的赞美也孕育着英雄的盛德形容,于是,在后代的历史遐想中,原始歌舞与礼乐文化就形成了天然的联系。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种乐器的产生,歌舞创作也进入自觉阶段,原始歌舞更趋于艺术化、审美化,也更趋于理性化、政治化。《吕氏春秋·古乐》记载黄帝令伶伦创作音律,于是伶伦也就成为中国发明律吕、创作音乐、制造乐器的始祖。此后,音乐创作成为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常态,并逐渐丰富,如黄帝之《咸池》、颛顼之《承云》、帝尧之《大章》、帝舜之《九招》《六列》《六英》等。原始社会后期的音乐,已经蕴涵社会教化的内容,上文所引葛天氏之乐就有“敬天常”“依地德”“建帝功”的内容,颛顼之《承云》也有“祭上帝”的功能,帝舜之《九招》《六列》《六英》则完全成为“明帝德”的颂歌。也就是说,传说中五帝时期的歌舞,已经由早期生活场景的直观呈现、生命情绪的放纵宣泄,转向礼敬天地、祭祀上帝、歌颂帝王功德。而且,音乐家通过观察自然物象的形态和声响,又将凤凰之鸣、山林溪谷之音等和谐婉转的审美元素引入乐舞之中,使乐舞由最初的粗犷狂放,也逐渐转向天籁自然。于是,原始歌舞的野蛮、粗犷、强烈的感官刺激,逐渐被得之天籁的乐舞打磨得文雅、圆润、平和,成为一种比较精致的审美了。
原始歌舞在走向精致的审美时,狂野的生命感性逐渐让位于社会的文化理性,教化人心的礼乐文化也在这里萌芽了。
我经常说但凡讲东西通俗易懂的人一定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因为他们善于放下自我,去思考听众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然后根据听众的实际情况去将自己的内容按照听众能接受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其实就是“搭脚手架”。)
本体与精神:礼乐文化的内化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文化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象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原始的巫术礼仪、音乐舞蹈,虽然包含着后代礼乐文化的元素,但是作为一种既定的制度,却在国家诞生之后。因此,真正意义的礼乐文化,萌生于殷商,制定于周公,弘扬于孔门。一旦礼乐文化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就必然与治政手段相辅相成,礼规范行为,乐教化人心;一旦礼乐文化完成了主体的自觉化,就积淀并内化为生命本体和生命精神。礼乐之于人生,正是通过主体内化的过程,由自觉走向自由,逐渐转化为主体的审美境界。
周公制定礼乐,对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影响极为深远,故周公、孔子并称大圣。然而,时代久远,史籍漫灭,难以稽考。今存之“三礼”乃后人所作,真假杂糅,也殊难分辨。然本文所论,唯在于礼乐与人生的关系,从中抽绎出西周至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发展及其对主体人格建构的深刻影响,至于具体礼制则悬置不论。
康、乾二帝特别偏爱杭州的景观。杭州共有19处景观被写仿,位列9府之首。除了南巡诗中提到的西湖、苏堤、柳浪闻莺、云栖洗心亭、孤山放鹤亭、龙井一片云和海宁县陈氏园写仿于清漪园、圆明园、香山和避暑山庄之外,曲院风荷、西湖行宫八景之鹫香庭、万松岭、法云寺华严阁、六和塔、飞来峰、玉泉观鱼、蕉石鸣琴、孤山放鹤亭、龙井龙泓亭、西湖花神庙和海宁县安国寺也都在这4处皇家园林中仿建。
远古洪荒,时间是一个混沌整体,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果说直立行走的发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那么时间和生命的发现,则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认识自身的起点。时间的人文化和生命的时间化,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身的深化;时间的人文化和生命的审美化,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身的升华。从深化到升华,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
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乐舞结合始于原始歌舞与节奏,诗乐结合却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夏后孔甲所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大禹妻涂山女所作之《候人歌》,始为南音;殷整迁徙西河而怀念故土所作之歌,始作西音;有娀氏二女所作之“燕燕往飞”,始为北音。自此之后,诗乐亦不可分,所以《周礼·大司乐》有“以乐语教国子”和“以乐舞教国子”的分别。《诗经》中周歌最盛,风之“二南”、雅与周颂,大约都是周歌。诗乐一体,意义重大。不仅音乐的“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蕴涵伦理秩序、宗法等级的象征意义,“故曰:乐观其深矣”(《礼记·乐记》),而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礼教内容,直接以“言志”方式进入诗歌文本。这样,礼的“程式化”仪式,因为渗透在诗乐舞之中,不仅具有了审美意义,而且与人的情感、心理、价值取向等生命精神,构成了深层联系。因而使刻板的西周礼乐,与生命、审美也有了密切的关联。
孔门儒学基于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精神,弘扬西周礼乐,以礼乐文化的主体内化为路径,完成生命精神和主体人格的社会化重塑。既推进了人类对生命本体的理性认知,又推进了礼乐文化由外在规范向生命精神的审美转换。
积学修身,是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主体的必由之路。《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属于“文”,射御数属于“术”;“游”乃“玩物适情之谓”(朱熹《论语集注》),“玩物”指研习射御数以掌握技艺,“适情”则指浸润礼乐书以怡养性情。《泰伯》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修身、以礼立世、以乐成性,是君子人格重塑的必由之路。孔子所谓的礼乐书属于“文”,诗礼乐也属于“文”,二者意义差近。如果连贯起来理解,礼乐文化是君子积学的核心,也是修身养性的核心。君子必须沉静其性情,通过不断地研习诗书礼乐,将礼乐文化内化为“文质彬彬”的生命本体。《里仁》所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就是外在规范与主体内化的一条分水岭。一是“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一是“知能照识前事,知仁为美,故利而行之”⑨。“仁者安仁”,外在的“仁”已经内化为一种心境,仁爱众生,成为一种自觉行为;“知者利仁”,外在的“仁”依然只是一种规范,以仁作秀,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可见,礼乐文化只有内化为主体的生命精神时,才能真正走向审美人生。
李泽厚指出:“这种‘礼’到殷周,最主要的内容和目的便在于维护已有了尊卑长幼等级制的体制秩序,即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现在汉代的三礼的主要部分正是保留了许多自上古至殷商的所谓‘礼制’——即以祭祀活动为核心的图腾活动、巫术礼仪等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它们正是自上古到殷周的某些‘礼制’的具体遗迹。”礼制与审美的关系,主要在于“礼”的秩序规范,“存在着仪容、动作、程式等感性形式”,故与“美”有关④。实际上这一观点颇值商榷。在时间上,西周礼制,可能保留有夏商两代遗风,所以《论语·为政》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但是,夏商礼制还残存着氏族巫术礼制,以神权天命为核心,故后代文献谓之“夏服天命”(《尚书·召诰》),“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西周虽也有“郊祀”(祭祀上帝)和“宗祀”(祭祀文王),却也有“告朔”(颁布历法)和“朝觐”(朝见诸侯),世俗化色彩十分浓郁,与分封制相呼应的宗法等级也十分森严。所谓“以祭祀活动为核心的图腾活动、巫术礼仪等具体的制度和规范”,主要存在于夏商,而非西周。在内容上,无论是早期的图腾活动、巫术礼仪,还是后来殷商直至周代的“礼制”,在不断重复的“程式化”过程中,已经消解了最初的独特感性形式中所蕴涵的生命意识,转化为积淀着某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庄严抽象的文化符号,反而成为约束个体的感性行为及感官享受的外在锁链。也就是说,礼制的“仪容、动作、程式”,虽也有一定的美感特征存在,却已无法唤起生命审美的联想和想象了。
1964年,我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一家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就在“庐山脚下”。我报了名,第三天就兴冲冲地上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庐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气馁。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可以写诗。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奋笔疾书,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退稿签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终于有一篇我照当地“五句头”山歌写的叙事诗收到了江西省文联文学月刊《星火》一位编辑手写的回信,说: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停刊运动,用稿时间另告。
快乐接受,是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的心理桥梁。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起源于巫术祭祀,“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九歌·东君》),礼乐,是既娱神又娱人的一种形式;自觉于周代礼制,上文所论的乐之适、心之适,就包含审美娱悦,“人心的‘喜乐’,既是音乐的源泉,又是音乐所表现的对象,还是音乐所要达到的目标”⑩;转换于孔门儒学,孔子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为学之道,娱乐接受是为上境。而且,孔子将这种快乐精神推而广之,无论境遇如何坎坷,现实如何难堪,始终坚守“坦荡”的人生襟怀,并且(1)转化为人生的自觉行为,守道不渝,穷且益坚,纵然“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2)渗透于人生的全部过程,不仅厄于陈蔡、困于桓魋,乐观豁达,而且“学而时习之”是乐,“有朋自远方来”是乐,“发愤忘食”更是乐——“乐以忘忧”贯穿于人生的全部;(3)落实在人生的道德实践,“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雍也》),水之流动,如智者乐用其知以治理时世,山之稳固,如仁者乐用其德以化生万物,也就是说,如水之进取为乐,如山之无欲也为乐,这就是以礼乐文化为观照点,在山水的本质对象化中呈现君子的道德实践;(4)升华至人生的审美境界,子在齐闻《韶》,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并慨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这种夸张的描述、深沉的感喟,简直是审美的极致!快乐是君子生命的常态,君子在自觉接受礼乐文化并内化为生命精神的人生历程中,完成了主体人格的社会重塑。
综合模型是整合数据分析观念的外显表现和内隐的认知过程的综合视角建构的,反映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发展.如张丹将数据分析观念的评价框架划分为3个维度9个要素,各要素又划分四个水平,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小学生在教学情境下数据分析观念的发展阶段[11].该框架以数据分析过程为暗线,结合统计意识和随机思维,但未涉及批判思维,且需要更多的样本进行验证.
简要说来,“游于艺”是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本体,“乐以忘忧”是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最终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自由。后来孟子的“吾养吾气”、《易传》的“日新其德”,《中庸》的“慎独”“诚明”和《大学》的“正心”“诚意”,以及理学的“存心去欲”,所强调的人格修养,本质上就是人生的文化砥砺并逐渐内化的功夫。这种内化的生命本体以及最终达到的生命自由,是一种生命精神,也是一种审美境界。
广义的礼乐文化,包括诗礼乐舞,是儒家名教的构成核心。礼乐文化之于人生,正是在主体的不断内化过程中,才逐渐转化为主体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自此,孔门儒学完成了对西周礼乐文化的传承和扬弃。
任性与逍遥:人性异化的救赎
然而,历史与现实并非全然按照先哲所设计的理想蓝图向前发展。任何一种文化的内部都蕴涵着一种“异己”的裂痕,当这种文化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为社会所认同时,这种“异己”的裂痕就可能转化为“异化”的力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礼乐文化内部的“异己”裂痕就逐步转化为“异化”人性的力量。庄子正是围绕人性异化的问题,解构并重构礼乐文化,试图救赎异化的人性。
如果抽去了礼乐文化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那么基于伦理和秩序的礼乐文化,就可能沦落为僵化的等级程式,异化为精神枷锁。子路恪守“君子死冠不免”,结果成为战阵厮杀的屈死冤魂;基于入世与救世的孔门儒学,也可能沦落为“知者利仁”的攫取名利的工具,异化为生命的精神镣铐。如李斯本为儒门荀子弟子,后入秦为客卿,最终成为追逐权贵的精神奴隶。春秋战国的士之阶层尤其是战国辩士,抽去了士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宗教式的救世情怀,汲汲于“势位富贵”,何曾有一点生命的崇高、人生的审美!这种人性的异化,使庄严神圣的生命精神坠落到世俗的尘埃而难以自拔。
2)丽水白云山森林公园降水量日变化,午后至上半夜降水较多,傍晚17:00出现峰值,20:00降水次之。降水峰值出现时段与华东初夏降水的日变化[15]分析中结论一致,丽水降水在午后至傍晚的峰值很明显。降水量年变化,梅雨期雨量集中,6月出现峰值,台汛期多热带气旋的影响,次峰值出现在8—9月。降水量随海拔先增加后减小,最大降水量高度约为700 m左右,在700 m以下降水量随海拔的增加而增大,700 m以上降水量随海拔的增加而减少。
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本是为了匡正世俗人心;结果“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庄子·马蹄》),反而成为异化人性的工具。于是,庄子试图从生命哲学上救赎人性的异化。通过解构与重构,既消解了礼乐文化的刻板程式对人性的桎梏和入世过深对生命的异化,又创造了任性的生命情调和逍遥的审美境界。
众所周知,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天问》固然包含艰涩的探索、深刻的哲思,甚至尖锐的批判,但是诗人对宇宙起源、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的追问,仍然投映着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印记。比如诗人对宇宙、天象、地貌形成的追问:天有九层,造物者谁?天行之纲,安放何处?立地之柱,为何地倾东南?九层之天,如何连接排列?与其说是探究宇宙起源,毋宁说是对神话稚拙而诗意的追问。与庄生《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追问天穹的本来色调、宇宙的辽远深邃,具有相似的审美特质。这种浪漫情调,不仅祭祀鬼神的巫歌——《九歌》表现得特别饶有韵味,如《湘夫人》描写湘君精心准备新房:“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新房地点的选择、厅堂的用料、卧房的装饰,雅洁、芬芳、温馨,构筑了一个人间仙境,昭示了湘君爱情的浪漫;而且抒写情志的篇章——《九章》也充满浪漫遐思,如《涉江》本是叙述诗人流放楚国江南的艰辛历程,然而诗所描写:以青白的飞龙为驾,与帝虞同游瑶圃,登昆仑,餐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壮浪、雄阔、奇诡,化艰辛、晦暗为轻快、明丽。即使抒写悲悯之情的《招魂》,对四方、上天、幽冥阴森恐怖的出人意表的想象,对“魂兮归来”的宫室之华美、内房之瑰丽、后宫之佳丽、行宫之辉煌,以及祭祀物品之丰、歌舞之盛、场面之欢的铺张扬厉,奇谲瑰伟、纷纭挥霍,同样装饰进了浪漫情调。
1.旅行者角度。首先,要有主动了解旅游风险的意识。在选择旅游企业(包括旅行社、旅游景点管理、中介等)时,要注意企业的经营资质认证,企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企业的产品品质以及旅游合同和旅游保险等,对自身出游风险进行预先控制或规避。其次,保持警惕,随时注意旅游企业和相关部门发布的信息,并以正确态度对待。
唯此,庄子试图建构的生命哲学,摆脱了一切礼乐文化的锁链,回归于人的本然之性。因为“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所以庄子强调“至乐”。然而,庄子之乐与孔子之乐不同。孔子是浸润于礼乐文化的“乐以忘忧”,庄子是超越现实的“至乐无乐”。所谓至乐无乐有两层含义:第一,指快乐之乐。《庄子·至乐》批评满足现实欲望的庸俗快乐观,“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在所虚构的髑髅与庄子的对话中,借髑髅之口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这并非礼赞死亡,而是借助“寓言”,礼赞真正的生命快乐。唯有超越君臣秩序的桎梏、四时之事的纷扰,超越“富贵寿善”“味色音声”的贪欲,才能进入“至乐无乐”即虚淡无为、无乐为乐的生命境界。第二,指礼乐之乐。《庄子·骈拇》批评道:“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儒家礼乐,如工匠的钩绳规矩、绳约胶漆,损德去性;虽然曲折备至,以仁义化育抚爱众生,但是“以此伪真,以慰物心,遂使物丧其真,人亡其本,既而弃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也”(成玄英疏),其要害就在于使人丧失了本然的性情。所以《大宗师》又虚构了颜回以“忘仁义”为第一境,以“忘礼乐”为第二境,以“坐忘”为第三境。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即“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郭象注)。一言以蔽之,忘怀现实,心境空明,直达本体之道。无论是快乐之乐,还是礼乐之乐,都必须超越世俗的桎梏,在“坐忘”中,回归于生命的本然状态,才能达到“至乐无乐”的生命情调。
在行为哲学上,救赎人性异化的基本途径,就是“逍遥游”——在无所待的状态下,让精神一无挂碍的自由翱翔。儒家虽然也渴望自由的人生,《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曾点所描述的诗意行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孔子所抒发的牢落不平,都蕴涵着对自由人生的向往,但是儒家入世救世,带有宗教式的悲悯情怀,遮蔽了这种偶然泛起的自由人生的遐想。退一步说,儒家纵然实现了这种人生的自由,也不可能忘怀现实,达到真正逍遥的境界。于是,庄子为儒生虚拟了一条逍遥的路径,这就是颜回“坐忘”的境界。孔子在听了颜回描述的坐忘之后,深有感触地说:万物齐一,则无好恶之心;同乎大道,即不执滞常理。你坐忘如此,定是大贤,从而学之,是我所愿意的呀。其实,庄子“寓言”隐含着一个深层意蕴:即使执著于礼乐文化的儒家,也渴望逍遥人生。也就是说,渴望逍遥人生是人的本性使然。于是,庄子设计了一个“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人生境界。李泽厚描述说:“庄子用自由的飞翔和飞翔的自由来比喻精神的快乐和心灵的解放,是生动而深刻的。之所以生动,因为它以突出的具体形象展示了这种自由;之所以深刻,因为它以对自由飞翔所可能得到的高度的快乐感受,来作为这种精神自由的内容。”表达虽富有诗意,对庄生意旨的理解却不准确。这也难怪,历来对庄子逍遥的理解都有偏差,郭象说“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王先谦说“言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也”,都没有直达庄生文心。在《逍遥游》中,无论是鲲鹏还是蜩与学鸠,是朝菌蟪蛄还是冥灵大椿,是宋荣子“辨乎荣辱之境”还是列子“泠然御风而行”,都因为“有所待”而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才是真正的“逍遥游”。简言之,天地六气是宇宙运化的本然状态,也是万物本然之性的本原。“乘天地之正”,适性而为,为而无为;“御六气之变”,适性而游,游而无待。体之“无己”,用之“无功”,名之“无名”,臻其三境,才能无为无待,得乎逍遥之境矣。
必须说明的是,庄子的逍遥并非现实所能达到的行为状态,而是唯有心灵才能达到的精神状态。所以,即使是“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现实物象的“大树”,也只能生长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虚拟的空间;只有“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齐物论》)——虚拟的行为,才能使心灵得到解脱。唯有身心摆脱桎梏,精神自由翱翔,方可进入无乐而“至乐”的适性逍遥的审美境界。
庄生反复申述“绝圣弃智”,批评“圣人之过”,实际上是从批判现实入手,针对礼乐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以逍遥无待为行为哲学的核心,以本然之性为生命哲学的核心,强调道德生乎本然之性而非外在强加的生命枷锁。从本质上说,庄学是从超越性的视角,试图拯救“礼崩乐坏”的世界,重铸本真的世道人心,对礼乐文化所建构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既是解构又是重构。如果说孟子的经权思想,一面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一面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是对礼乐文化弊端的内部改良,那么庄学的超越思想,一面以本然之性救赎礼乐文化对人性的异化,一面又主张道德出乎自然,是对礼乐文化弊端的外部革命,从而使道与儒在思想上构成涵纳、互摄的关系,既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也在异己力量的撞击下,使礼乐文化逐步地修正、发展、丰富。
自由与自律:境界人生的建构
庄子哲学的内部也仍然蕴涵着一种“异己”的裂痕。庄子的任性与逍遥,对于异化的人性是救赎,是匡正;对社会的秩序是解构,是破坏。社会是一架庞大的运转机器,动态、有序、平衡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秩序原则。秩序原则是社会成员(包括庄子)实现其他一切权利的基本保证,所以任何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社会秩序原则。任性逍遥的本然性只能是有限存在,秩序规范的社会性却是永恒存在。西方基于社会自然结构的社会契约论,东方基于社会宗法结构的名教秩序论,是不同文明类型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存在。无论是诗人有意识的“白日梦”,还是自我无意识的“自由梦”,永远只能存在于审美和梦幻之中。
将梦幻的自由镶嵌到道德的自律上,使本来生命精神中对立的二元存在,转化为统一的人生境界,在先秦时代,唯以屈原为代表。屈原的人生与艺术,既是庄子哲学的诗性延伸——将庄子的虚幻镜像人生,投映到现实人生;又是礼乐文化的审美呈现——将儒家内化的生命精神,铸造为诗性自由。
庄子以基于自然化的“道德”论之矛,猛烈攻击基于社会化的“道德”论之盾,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礼乐观。孔门道德论,以仁义为核心,以忠恕为内涵,以礼乐为手段。庄子道德论,虽然也强调仁义、忠信、礼乐,但是具体内涵却与儒家大相径庭。《庄子·缮性》曰:“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他所说的“道”是治世之道,核心是“理”;德是“以恬养知”之德,核心是“和”。智,明其本然之性而无为,则为“和”;和,生于本然之性而养智,即为“理”。无为顺性之德,包容一切,即为仁;本性恬静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即为义;义理显明,万物亲之,即为忠;仁义发于中而返乎性情,则为乐;行为诚信,容仪自然而合乎规范(文),则为礼。庄子所说的道德,是基于本然之性的生命自觉的行为,以恬静、无为、自然为基本表征。因此,他合理地推断出礼乐的本质应该是顺应自然,本乎性情,认为儒家的礼乐制度违背了本然之性,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规范,造成了秩序与人性的深刻矛盾而使人无可适从,所以礼乐行则天下乱。他提出的解决途径是:推崇真正的圣人之道,是不加诸外在桎梏,使各任其性,各正性命,自养其德。所以郭象《庄子注》序云:“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一切以礼乐为核心的名教都必须符合人的“自性”即本然之性。
随着人们消费意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和利用快递服务这一快速便捷的方式,因而各快递服务企业的业务规模不断提升,社会功能日益显著,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服务消费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浪漫特质上说,屈原与庄生同调。然而,庄子的浪漫是心造的虚幻人生镜像,无论物任其性、逍遥无待的生命情调,齐一万物、均同彼我的价值消解,坐忘物我、外内玄合的道德修养,还是不滞于物、冥情于天的养生方式,随变所适、心斋妙道的应世策略,本质上都是无法付诸人生实践的诗意梦幻。正如苏舆所言:“然其为书,辩多而情激,岂真忘是非者哉!不过空存其理而已。”屈原的浪漫则将庄生虚幻人生镜像,投映到现实世界。《天问》从创世神话到历史传说的追问,再由历史传说到历史事件的追问,经过两次结构的转折之后,使全篇宏大的追问式叙事最终落实到“曾经的现实”之中,与《离骚》以历史为现实镜鉴在意蕴上如出一辙。《九歌》的神灵,或“捐余袂兮江中”(《湘夫人》),“捐余玦兮江中”(《湘君》),满腹凡尘夫妇的嗔怒;或“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充满人间的忧愁哀乐。无论是湘水之神的新房装饰,还是山鬼的精心打扮,都浸润着人间高洁的情怀,与《离骚》中描写诗人自我装饰的象征意义也完全相同。特别是这组祭歌,以为国捐躯的英雄赞歌——《国殇》作为收束,王逸曰:“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讽喻。”显然,在“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哀思中,也寄托屈原忘身殉国的壮烈情怀。《九章》的叙事抒怀,具有强烈的自传体特征,除了《橘颂》外,虽富有浪漫遐思,却也最终落实在叙写流放行进的路线、寥落荒芜的景物以及沉郁复杂的情感上。因此,诗中所创造的诗人自我形象“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甚至“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恰恰在超越尘世的遐思中浸透着缕缕缠绕的入世情怀。这与庄生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词的“寓言”的形式,书写历史传说、现实人物,寄寓“朝彻见独”的形上之道,也大相径庭。唯因将庄子浪漫拉进现实人生,才重铸了生命和审美的境界。
然而,屈原虽身处南方,然一旦将庄子的浪漫拉进现实人生,必然与生长于北国的礼乐文化产生了深层关联。李泽厚认为:“到屈原那个时代,中国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渗透和彼此融合,毕竟已是一种无可阻挡的主流。北国以其文明发达、制度先进的礼乐传统向南方传播蔓延。”其实,除南方地域文化影响外,楚国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同源。大约公元前11世纪,西周成王封熊绎于荆蛮,始有楚国。而后,周天子又派遣太史官入楚教习周代的礼制,遂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干的荆楚文化特色。春秋战国,一方面,诸侯混战,国门洞开,促进了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楚人也主动学习中原礼乐文化,楚人陈良因为“悦周公、仲尼之道”,遂北上学习中原礼乐(《孟子·滕文公上》);楚庄王诏命上亹为太子傅,教授太子《春秋》《诗》《礼》《乐》等周代典籍(《国语·楚语上》),都是典型的例证。1993年出土的郭店战国楚简,不仅证实了楚国接受了中原儒家文化,而且据考证,墓主的活动年代与屈原也十分接近。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屈原自觉接受中原礼乐文化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的辞赋“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如果脱去屈原思想中出身芈姓贵族的宗族情结,其忠君、爱国、民本思想以及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显然与中原儒家礼乐文化血脉相连。王逸直接将《离骚》并称为“经”(《离骚经序》);刘勰又从“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个方面,结论为“同于风雅”(《文心雕龙·辨骚》)。也就是说,汉代以降,《骚》之与《诗》,同成为礼乐文化的载体。
【结论】 乙肝疫苗免疫接种效果显著。做好新生儿乙肝疫苗预防接种,加强中学生及成年人的乙肝疫苗免疫接种。
所以,屈原思想始终执著于庄子所否定的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美丑,表现出强烈自觉的道德自律精神。早年即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作为人生的准则;中年渴望“国富强而法立”,抨击“背法度而心治”(《惜往日》),具有强烈的政治秩序意识。即使是遭谗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王逸《离骚经序》),不惟没有泯灭理想,与世推移,反而深思高举,坚守价值人生。在这首长诗中,诗人系统抒写了政治理想、道德修养和人生追求。从国家层面上说,始终以“圣哲茂行”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以哀予今民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作为“为君之道”的政治标准。从个人层面上说,以儒家的“道德”“仁义”为思想核心,以“内美”“修能”砥砺道德修养,以“依前圣而节中”“伏清白以死直”作为行为准则;试图“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以匡正世俗的道德毁颓;即便因此而“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也不改初心;而“体解未变”“九死未悔”的执著精神,尤其表现出道德自律意识。这种强烈的道德自律,与儒家弘毅贞刚的胸襟气质、浩然之气的人格砥砺、任重道远的社会责任、杀身成仁的坚韧执著,在生命精神上一脉贯通。儒家“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的礼乐文化内化的主体生命精神,也成为屈原人生践履的生命动力,生命境界的思想根基。
然而,屈原辞赋又将儒家礼乐文化内化的生命精神,铸造为诗性自由。既充满人类童年神话的奇诡想象,南国巫筮文化的迷离倘恍,又浸透北国狂狷精神的蹈厉风发,理性觉醒时代的坚韧执著。奇诡想象中融入深沉的情感,“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低佪兮顾怀”(《九歌·东君》),太阳神驾龙车、乘云旗飞升天空时的叹息流连,眷念故居,不正是诗人的情怀么?迷离倘恍中交织执著的追求,“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九章·抽思》),故都道路辽远,却一夕几度梦回;灵魂不辨道路,无法直接归去,只能在星月微光的引导下飞向故都——迷离、凄暗,意旨却是那样坚定!蹈厉风发中也凸显悲壮的情怀,“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宁愿葬身鱼腹,也要坚持高洁的操守,以悲壮人生重新诠释了孔子与其“不得中行”毋宁狂狷的精神。可见,屈原虽以儒家的礼乐文化为思想根基,然而在表现形态上,“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从而使其道德、理想、人生追求以及不满、愤懑、现实批判,表现为奇谲狂放、横而不流甚至惊艳绝伦、壮浪恣肆的诗性自由的审美境界,词烁千古,光被日月,非一代之词人也。
屈原的意义,并不在于自沉汨罗,以身殉道,而在于他浪漫自由而又执著坚韧的精神气质,贯穿于生命的全部过程。即使他的理想走向幻灭,仍然在澄澈的水底化作燃烧的岩浆;生命走向毁灭,仍然在幻想的天宇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因此,屈原的人生不是悲剧,而是壮美;屈原的生命不是流星,而是永恒。他超越了现实的桎梏,又激荡着伟大的理想;这伟大的理想植根于民生的现实,又充满了浪漫的诗性;这浪漫的诗性燃烧着生命的激情,又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这种诗性自由与现实人生的有机交融,将儒家的礼乐文化既内化为生命精神,又融合了庄生恣纵不戃的人性诗意;既消解了礼乐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又将庄生虚幻缥缈的诗意浪漫拉回现实人生,构筑了诗性自由与道德自律有机统一的境界人生,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审美性人格的经典范式。自此,传统的礼乐文化由主体化走向生命化,才真正铸造成一种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并逐渐积淀成为民族文化的潜意识,从而深层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简要地说,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考察,以时间人文化为生命起点,以礼乐主体化为生命精神,以任性逍遥为生命情调,以自由自律为生命境界,是构成先秦审美观念生成与演进的基本轨迹。
①李泽厚:《美的历程》,载《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②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8页。
盐囊细胞(Epidermal bladder cells,EBC)是冰叶日中花的特异细胞,存在于除了根以外的所有组织表面,但在不同组织其形态也各不一样。盐囊细胞是储存NaCl的场所,在受到盐胁迫时,冰叶日中花的地上部分就开始将NaCl储存在各个部位的盐囊细胞中。盐胁迫下的盐囊细胞呈现隆状的凸起[2]。研究显示,EBC 可累积多达 1.2 mol/L 的 Na+, 在离子和水稳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因此,EBC对冰叶日中花的耐盐性起关键作用。
③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④李泽厚:《华夏美学》,载《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93、332、332~333页。
⑤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4页。
⑥⑧《礼记·中庸》,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2、1077页。
⑦钱穆:《黄帝秦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⑨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⑩王齐洲:《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四),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6、138页。
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四),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8页。
在熔炼过程中,炉渣中的ZnO与Fe2O3直接结合形成铁酸锌ZnFe2O4,铁酸锌也成为锌铁尖晶石,其稳定性强,熔点高,使炉渣粘度增大,渣流动性降低,不易被还原分解,炉渣中氧化铅这种渣环境下的还原烟化难度增大,不利于降低炉渣含铅量。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任务绩效容易受到感恩奉献、谦虚沉稳、包容宽恕等人际性心理资本的积极影响,其中任务绩效容易受到尊敬礼让的影响,但是影响不明显;而针对工作奉献来讲,尊敬礼让、包容宽恕、感恩奉献的影响较大;从整体上来看,针对人际促进来讲,人际型心理资本各个维度都能够呈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人际促进影响最大的为感恩奉献[5]。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34页。
作者简介:刘运好,1955年生,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 蔚〕
标签:礼乐论文; 生命论文; 文化论文; 屈原论文; 庄子论文; 《江海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魏佛教诗学研究”(18AZW006)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