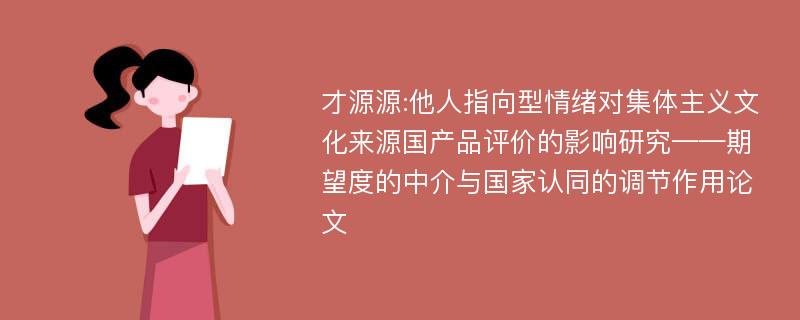
【摘 要】本文提出了他人指向型情绪与集体主义文化来源国之间的匹配关系,通过3个实验研究发现:针对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来源国的产品,消费者在他人指向的平和情绪下较自我指向的高兴情绪下产生更积极的评价;并且,这一匹配关系仅发生在认知参与度高的消费决策情境中。同时,本文通过引入期望度和国家认同变量,探明情绪对来源国产品评价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问题。本文深化了情绪与来源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对非优势来源国的营销策略制定,以及基于文化特征的国家品牌资产提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来源国 他人指向型情绪 深入加工模式 国家认同
1.引言
在品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商业品牌与其来源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在不少国家,企业的品牌战略已逐渐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例如,早在2009年,韩国就成立了国家品牌委员会,专门开展针对“国家作为品牌”的战略和工作。近年来,我国也相继设立了“国家品牌计划”和“中国品牌日”,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和认知度,促进能够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品牌参与到全球商业竞争和文化交流中。与此相对应,在学术领域,研究者们达成共识,认为产品和品牌的来源国家也可以同商业品牌一样,为产品带来附加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资产来源(Pappu & Quester, 2010)。国家品牌在来源国概念的基础上具有更多情感和精神的内涵 (Olin, 2002),其所具备的独特资产也被认为是“消费者对于某一产品或品牌所产生的、仅与特定国家有关的情感”(Iversen & Hem,2001)。
那么,如何建立国家品牌资产、发挥国家品牌的杠杆力呢?国家形象的宣传、文化产品的推广、重大国际会议和赛事的主办等均可能成为提升国家品牌资产的有效方式(Dinnie, 2004)。例如,在中国举办的G20峰会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成为国际会议的亮点,有效凸显了积极而独特的中国国家形象。其实,在文化的传递方式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才源源和何佳讯(2012)的研究曾采用音乐、视频和回忆故事等多种方式启动消费者的“自我指向”型情绪(如高兴情绪)来强化文化特征,发现美国作为产品来源国时其个人主义文化特征在高兴情绪下被激活,从而使美国产品获得更为积极的品牌态度。消费者情绪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也在Maheswaran和Chen(2006)的研究中获得了证明,他们的研究发现生气较悲伤情绪下,消费者更倾向于进行人为归因,而对于某国产品来说,国家即为生产制造者,因此来源国信息在人为归因的条件下会对产品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由此研究者提出:特定情绪可被视为国家品牌资产的一种重要来源,实现改善负面来源国效应的作用。
以往研究尚未证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情绪的影响作用,并且对自我/他人情绪特征影响下的个体认知模式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关注具有文化特征的“他人指向”型情绪,并且在集体主义文化下,针对非优势来源国国家品牌资产的情绪来源进行研究;另外,围绕来源国的问题,本研究将通过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类型以及附加产品信息的引入,探索“他人指向”型情绪对来源国产品评价产生影响的条件。
2.文献综述
2.1 情绪对认知的影响模式
情绪是具有多种认知属性的综合体,除了正负效价、唤醒水平等基本维度特征,还具有关系指向、动机目标、归因控制等更为具体的认知特征(Smith & Ellsworth, 1985)。那么,这些具体特征影响下的认知模式是怎样的呢?Forgas(1995a)的情感注入模型(affect infusion model, AIM)提供了情绪作用于认知过程的全面解释,该模型把具体情绪对个体认知判断的影响归纳为高、低两类情绪浸入类别(high/low infusion strategy)。在低情绪浸入的情况下,个体主要依据已储存的信息和知识经验对认知目标直接进行判断,情绪对认知的影响作用微弱;在高情绪浸入情况下,情绪对认知的影响又可以分为启发式策略(heuristic strategy)以及深入加工策略(substantive strategy)。其中,启发式策略是一种“情感即信息”的认知模式(affect-as-information),即情绪被视为认知线索,直接参与认知过程,个体通过情绪推测出一种判断,实现情绪与认知的一致性(mood-congruent effect)(Bower, 1981)。比如,天气晴朗的日子与阴雨天相比,好心情会让人们感觉生活更加幸福(Schwarz & Clore, 1983),股民也会预测股市投资获得更好的回报(Hirshleifer & Shumway, 2003)。而深入加工策略则以一种“情感启动”的模式运行(affect-priming),这是一种情绪通过唤起、激发个体记忆中已存贮的认知模式,间接影响行为结果的过程。情绪首先激发自我认知、归因以及社会化比较的内部过程,进而对认知产生影响。比如,悲伤的人在进行归因时会更有选择性地注意到情境因素,愤怒的人则会更关注到人为因素(Keltner et al. , 1993)。而何种认知加工方式会发生作用则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参与程度(Forgas,1995a),当认知任务较为简单或熟悉时,情绪对认知的影响表现为启发式策略,即个体不需要过多的认知努力;而当认知任务较为复杂或重要时,深入加工式策略往往会发挥主要作用,即需要个体较多的认知参与。
2.2 情绪的关系指向特征对认知的影响
关系指向(自我/他人)是涉及自我意识倾向的一个具体情绪特征(Salovey, 1992),指向自我(self-focused/self-directed)的情绪来源于个体内部的体验,个体自身的动机和需求是引发情绪的原因,这类情绪包括高兴、骄傲、生气、挫败等;相应的,指向他人(other-focused/other-directed)的情绪建立在自我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个体对自我的评估和情绪的感知常常是参照于他人或者是来源于他人,在这类情绪体验中,个体注重他人的感受,诸如平和、共情、悲伤、愧疚等情绪(Markus & Kitayama, 1991)。围绕情绪关系指向特征对认知的影响问题,以往的研究已证明当自我或他人指向与认知对象特征一致时,会提升认知评价。具体而言,在他人指向的情绪下,关注“家庭需求”的产品或强调“家人健康”的公益广告会获得更好的劝说效果;而在自我指向的情绪下,“个体需求”和“自身健康”的信息表达则会获得更积极的评价(Agrawal et al. , 2007)。在匹配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会将情绪作为一种认知线索,并依据情绪提供的关于自我或他人的信息线索完成后续的认知加工任务(Lerner & Keltner, 2000)。
关系指向型情绪的来源和表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强烈和频繁地报告自我指向的情绪;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他人指向的情绪体验则更占主导(Markus & Kitayama, 1991)。基于文化差异的情绪研究曾提出假设: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美国),个体具有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的认知特征,因而消费者会更偏爱能够唤起关注自我而非他人情绪的广告;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中国),以相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为主导的消费者则会有相反的偏好(Aaker & Williams, 1998)。因此,基于文化差异的自我概念认知系统产生了自我或他人指向(self/other-focused)的情绪,这一具体情绪特征会首先通过启动自我概念,间接影响认知决策,从而进入情绪对认知影响的深入加工模式(Forgas, 1995a)。
绘画语言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既有范式的复制,它的语言价值体现在自然生成的原创性上,也体现在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上。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变革中,中国工笔绘画艺术突破传统审美和表现的藩篱,以当代意识为自觉,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以及工具材料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拓展,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活力,新的审美境界在逐渐形成。罗春辉是中国工笔画坛上的菁英,也是创造这种新的审美境界的积极实践者,他是在工笔画艺术的传统技法与符号程式的基础上,尝试创造多种因素复合的新的表现形式,力求使作品获得崭新审美品质的成功者之一。其成绩斐然,声名远播。
2.3 他人指向型情绪与来源国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匹配关系
在复杂的消费者决策过程中,产品或品牌的来源国常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信息线索,可以激发消费者对产品的兴趣,也可以左右最终的购买决策;尤其是当产品的属性信息(如质量、价格和品牌信誉等)不够清晰时,消费者会更加依赖于对某国的总体性认知做出直接的判断,这即是经典的来源国效应表现(Maheswaran, 1994)。以往的诸多研究表明,产品的来源国常被视为传递质量信息的信号,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消费者对来自该国的产品会产生更为积极的质量感知和整体评价(Chowdhury & Ahmed, 2009)。除了提供产品功能优劣的信息外,来源国信息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Hong & Wyer, 1989)。来源国形象的文化特征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信念或情感,在产品态度形成中发挥间接影响作用(Iyer & Kalita, 1997)。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来源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作为一种信息线索,当消费者的认知对象特征(集体主义来源国)与情绪特征(他人指向)保持一致时,情绪的他人指向特征会通过唤起个体记忆中有关自我与文化的感知,间接影响认知评价,即对集体主义来源国的产品产生更为积极的态度。
One-Way ANOVA检验结果表明,在高兴分数上,高兴组显著高于平和组(M高兴=6.04, SD=0.98; M平和=5.39, SD=1.29; F(1, 76)=6.07, p < 0.05);在平和分数上,平和组显著高于高兴组(M平和=5.99,SD=1.06;M高兴=4.28,SD=1.48;F(1,75)=34.61,p<0.000)。此外,在情绪的积极性维度上,两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M高兴=5.81, SD=1.14; M平和=5.71, SD=1.25; F =(1, 75)=0.128, p=0.72),表明情绪启动成功。
4.1.2 研究结果
H1b:在低认知参与的情境下,情绪的文化特征不会影响消费者对集体主义文化来源国产品的判断。
老贾解释,原来,古董讲究物以稀为贵,如果是举国无双的至宝,价格自然惊人。或者是天下唯二唯三的珍品,当然也是价格不菲。但是如果说到古钱币,因为货币本身就具有易于贮藏和携带的特征,所以保存起来不但方便,而且数量也不少。试想存品超过千,多于万之后,单一钱币的价值自然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古钱币本身的材料多为铜铁,做工也不会太过复杂,所以单纯的艺术价值也不高。少了古董的稀缺性,本身又不值钱,古钱币敢情就变成古董界里后妈养的孩子,和珠宝字画之类亲儿子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
H1a:在高认知参与的情境下,个体在与集体主义文化相匹配的他人指向情绪下,较自我指向情绪或无情绪的条件下会产生更积极的消费者态度。
进一步探索他人指向情绪与来源国集体主义文化匹配效应产生的机制问题,Martin等(1997)提出当个体处于某一情绪状态下时(如悲伤),即会对与情绪特征相匹配的信息产生期待,一旦相匹配的信息出现,就会被优先提取和顺畅加工。Kim 等(2010)在研究关于消费者情绪(兴奋/平和)与旅游产品类型(冒险刺激/悠然安静)的匹配关系时,将“期望度”作为中介变量,并发现消费者在兴奋情绪状态下,对能够体验到兴奋感的冒险刺激型旅游产品产生期待,反之亦然。基于此,本研究将印度和中国确定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作为产品的来源国,以激发集体主义文化特质联想,而当他人指向的情绪(如平和)与之相匹配时,就会产生积极的消费者态度。而在此匹配效应发生的过程中,个体首先对与其情绪指向匹配的集体文化信息产生期待,当期待达成时便会产生更积极的认知评价。由此,针对印度和中国作为来源国的产品,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期望度在他人指向情绪与来源国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匹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2.4 国家认同的调节作用
当消费者在对本国产品进行评价时,由深厚的国家情感产生的民族中心主义、国家认同等因素会对来源国效应产生显著影响(Balabanis & Diamantopoulos, 2004)。例如,Verlegh(2007)将国家认同概念引入产品评价的来源偏差效应中,证明了个体的国家认同感越强烈,对本国产品的感知质量和购买意愿的评价越积极。国家认同即是群体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它代表某一特定文化所包含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多种含义的联结,也可以表达个人对自己所属国家的一种主观的、内在化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Keillor et al. , 1996)。那么,个体越是认同于群体身份,在态度和行为上就会更多表现出对所属群体的偏向(Mackie & Smith, 1998)。
结合本研究中以中国作为产品来源国的实验情境,国家认同高的消费者可能会由于强烈的情感因素而对本国产品做出更为积极的评价,此时情绪的即时影响作用被虚弱,形成低情绪浸入的认知模式。也就是说,国家认同可能会弱化个体依赖情绪与来源国信息的匹配关系进行判断的模式,最终使得情绪通过期望度影响消费者态度的中介关系受到削弱。具体而言,当消费者的国家认同感较低时,期望度在关系指向情绪对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而当消费者的国家认同较高时,情绪的信息性作用被削弱,消费者期望度的中介作用也不再存在。由此,在相对较高的认知参与条件下,针对产品来源国是消费者母国的情境,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 期望度在他人指向情绪与来源国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匹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本国消费者国家认同的负向调节。低国家认同相较于高国家认同,情绪的文化特征通过期望度对消费者态度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研究整体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医院是一个聚集病原微生物的环境,可为疾病传播提供有效条件,继而导致医院感染发生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且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在临床上严格按照医院病区感染管理制度执行尤为重要,有利于减少感染风险[2]。
图1 整体研究模型
3.实验前测
正式实验前,本文首先对来源国的文化特征进行前测,以确定与情绪的关系指向特征相匹配的产品来源国。参考Markus 和Kitayama(1991)的跨文化研究,分别对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描述,并请被试根据自身对美国、中国和印度三个国家的印象,评价各国家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契合程度。结果表明:与中国和印度相比,美国具有显著的个人主义特征(M美国=6.31,SD=1.26;M印度=3.28,SD=1.39;M中国=3.28,SD=1.39);而在集体主义文化方面,与美国相比,中国和印度则具有显著的集体主义文化特点(M美国=2.92,SD=1.54;M印度=4.03,SD=1.44;M中国=6.00, SD=1.35), 配对差异检验(paired-sample T test)结果详见表1。
(2)若CP(a)>1,则P∗(G)的连通分支个数为k(P∗(G))=s1(P)-s1(Φ(P))+1.
表1来源国效应和文化特点的差异检验
美国-印度美国-中国来源国效应差异检验MT(SD)tMT(SD)t笔记本2.83(1.76)9.63†1.00(1.87)3.21**果汁2.14(1.64)7.82†0.56(1.54)2.17*文化特点差异检验MT(SD)tMT(SD)t集体主义文化-1.11(2.05)-3.25**-3.08(2.08)-8.91†个人主义文化3.03(1.63)11.15†3.03(1.72)10.59†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表格中平均数和标准差代表了美国与印度、美国与中国在文化特征和来源国效应上的差异。
其次,确定影响认知参与的因素。以往研究表明产品卷入度通常会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参与(朱丽叶等,2017),对个体重要、相关性较高或存在购买风险的产品,会使消费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进行信息加工(Vaughn, 1986; Maheswaran et al. , 1992)。因此,本研究期望通过产品卷入度的设置来操作不同的认知参与程度,以创造情绪的他人指向特征发挥影响作用的高认知参与条件。本研究选取笔记本电脑和果汁作为高、低不同卷入度的产品类别,邀请20位被试对这两个品类的卷入度进行评价,测量题项参考Zaichkowsky(1994)的研究,包括“同其他产品相比,这一产品对我很重要”“我对这个产品很感兴趣”“购买该产品时,我会很慎重地选择”。结果显示:笔记本电脑产品的认知卷入度(M电脑=4.85, SD=1.86)高于果汁产品(M果汁=3.53,SD=1.16),差异检验达到显著水平(MT=1.32,SD=1.49,t=4.42,p < 0.000)。
进一步的,研究者需要检验在果汁和笔记本两类产品中,来源国的优势或劣势效应。共招募36名非正式实验被试参与该前测,请被试对来自美国、印度和中国的电脑笔记本产品和果汁产品进行1~7分的等级评价(1表示“非常不好”,7表示“非常好”),结果表明:无论是在笔记本电脑产品上(M美国=5.92,SD=1.32;M中国=4.92,SD=1.61;M印度=3.08,SD=1.57),还是在果汁产品上(M美国=5.42,SD=1.20;M中国=4.86,SD=1.38;M印度=3.28,SD=1.60),消费者对美国产品的评价均高于印度和中国产品,配对差异检验(paired-sample T test)结果详见表1。
4.实验1:情绪的他人指向特征与来源国文化的匹配性——基于产品类别的差异
实验1的研究目的是检验他人指向型情绪与集体主义文化来源国之间的匹配关系,以及情绪对认知产生影响的条件。实验1a采用中国笔记本产品,在高卷入度产品类别中验证H1a和H2;实验1b采用中国果汁产品,验证在低卷入度的产品类别中,情绪与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之间的匹配效应不会发生,证明了H1b,从而说明针对来源国的文化特征,情绪对认知产生的影响是一种深入加工的模式(Forgas, 1995a)。
4.1 实验1a
4.1.1 研究过程
实验1a在上海某本科院校进行,通过公开招募,共邀请了77名被试参加实验(女性为66.2%)。本实验采用单因素(情绪:高兴/平和)组间实验设计,所有被试随机分派到两个实验组,分别完成两部分实验内容。第一部分为情绪启动,参考了Tiedens和 Linton(2001)以及 Agrawal 等(2007)的研究,采用故事回忆法来唤起被试高兴或平和的情绪。针对平和情绪,研究者首先介绍“平和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是内心获得的平静与安宁,可能因为你投身大自然,可能因为聆听了一段优美的音乐,也可能因为跟家人、朋友共度的温馨时光等”;之后,被试将有5分钟的时间把自己的情绪故事写下来,随后完成情绪自评任务,即对表达平和情绪的“平和”“宁静”和“安详”,以及表达高兴情绪的“高兴”“欢快”和“喜悦”共6个形容词进行1~7的等级评分(1表示“一点没有感受”,7表示“感受非常强烈”)(Agrawal et al. , 2007)。实验第二部分为产品评价,向被试随机呈现一则虚拟笔记本电脑品牌“瑞升”的广告,包括产品概述和产品图片,并强调“中国”为产品的来源国。邀请20位被试对产品广告进行前测,结果表明:消费者对笔记本电脑广告的总体喜好度处于中等水平(M=3.50, SD=0.80);品牌的熟悉度处于较低水平(M=1.0, SD=1.0)。随后,所有被试完成产品评价测项,产品态度借鉴Swaminathan等(2007)的研究,共四个测项,包括产品质量、品牌评价以及对产品整体喜好度,评价方式为1~7的等级评分,(7表示“非常肯定”,1表示“完全否定”);购买意愿则参考了Laroche等(1996)的研究,测项为:“您愿意购买瑞升笔记本电脑吗?”“如果您恰巧需要购置一台笔记本电脑,您愿意尝试购买瑞升吗?”“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您购买瑞升的可能性有多大?”;产品期望度参考了DeSteno等人(2000)的研究,测项为“您对瑞升电脑有怎样的期望?”和“您认为瑞升可能是一款很好的笔记本产品吗?”。最后,所有被试需要回答个人背景相关的题目,以及对实验目的的猜测。
目前各种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信息的泄露给用户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信息的泄露指的就是用户的一些保密信息被不法分子非法的窃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电子技术与各种高端信息技术的快速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各种信息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出现这种现象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内部的资料被偷窃、存储设备意外丢失等。因此现代人的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信息泄露已经直接损害到用户的利益。
目前大港主力油田均已进入二次开发阶段,再依靠大规模的打新井来提高采收率,效果越来越差,边际效应明显;而三次采油在油田实施规模很小,技术适应性差,还远远不到大规模推广的时候。
(1)情绪启动的检验
脂肪含量,酸水解法;蛋白含量,参照GB 5009.5-2010;水分含量,参照GB 5009.3-2010;灰分,参照GB 5009.4-2010。
基于Forgas(1995a)的情绪注入模型(AIM),当情绪通过激发自我的认知系统影响判断时,通常是一种深入加工的模式,该模式需要个体较多的认知参与(Forgas, 1995b)。因此,我们认为,基于情绪指向与来源国文化特征的匹配效应,应当发生在情绪对认知产生间接影响的高认知参与情境下。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2)因变量及中介作用的检验
因变量包括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首先对产品态度进行One-Way ANOVA分析,结果发现平和组的被试对中国笔记本电脑产品的态度显著高于高兴组的被试(M平和=3.79, SD=0.88; M高兴=3.27, SD=1.10; F(1, 75)=5.31, p=0.024)。当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时,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平和组的购买意愿显著高于高兴组(M平和=2.98, SD=1.32; M高兴=2.32, SD=1.24; F(1, 75)=5.15, p=0.026)。
针对“期望度”的中介效应,按照Zhao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 Hayes(2004)和Hayes(2013)提出的Bootstrap方法(选择模型4,样本量5000,95%的置信度),以情绪为自变量,产品态度为因变量,对期望度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中介检验结果不包含0(LLCI=0.1174, ULCI=0.7415),表明中介作用显著,且效应值为0.3724。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期望度之后,自变量情绪对因变量产品态度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区间(LLCI=-0.5335, ULCI=0.2356)包含0,由此可知期望度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随后,以相同的检验步骤,验证当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时的结果,发现期望度的中介作用仍然显著(LLCI=0.1505, ULCI=0.9507),且为完全中介,效应值大小为0.4782。说明期望度在情绪与产品态度、购买意愿的关系中均发挥了中介作用。由此,H1a和H2在以中国为集体主义文化来源国的高卷入产品中获得证明。
2.2.1 单一对照品贮备液 精密称取淫羊藿属苷A、朝藿定A1、朝藿定A、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苷、鼠李糖基淫羊藿次苷Ⅱ、宝藿苷Ⅰ对照品各适量,分别置于25 mL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0.390、0.282、1.010、1.338、1.792、1.600、0.268、0.908 mg/mL的单一对照品贮备液。
4.2 实验1b
实验1b采用与实验1a相同的实验设计,不同之处是将笔记本产品“瑞升”更换为果汁产品“万奇”,万奇果汁被描述为“含有新鲜水果成分,为身体提供维生素和充沛活力的一款中国果汁产品”。前测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果汁产品广告的总体喜好度处于中等水平(M=4.08,SD=0.79);品牌的熟悉度处于较低水平(M=1.46, SD=0.83)。实验1b同样在上海某本科院校进行,64名学生被试(女性为67.2%)被随机分配到高兴或平和两个实验组,之后完成情绪启动及广告评价任务,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的评价同实验1a。
实验结果表明:在高兴分数上,高兴组显著高于平和组(M高兴=4.95, SD=1.23;M平和=4.28, SD=1.30; F(1, 72)=4.52,p < 0.05);在平和分数上,平和组显著高于高兴组(M平和=5.03,SD=1.18;M高兴=4.27,SD=1.41;F(1, 62)=5.54,p < 0.05),表明情绪启动成功。但是,在产品态度(M平和=3.73, SD=1.25;M高兴=3.72, SD=1.24;F(1, 62)=0.03,p=0.960)及购买意愿(M平和=3.97,SD=1.90;M高兴=4.0,SD=1.67;F(1, 62)=0.05,p=0.944)两个因变量上,高兴和平和组均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在低卷入的果汁产品上,情绪的文化特征没有对来源国效应产生影响,即H1b获得证明。
5.实验2:情绪的他人指向特征与来源国文化匹配性的进一步证明
实验2的研究目的是进一步验证他人指向型情绪与集体主义文化来源国之间的匹配关系。在实验设计上,选择另一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非优势来源国——印度作为产品来源国,并设置无来源国信息的控制组;此外,为了区分“平和”情绪与无情绪状态的差异,设置“日常生活”场景的无情绪控制组,并通过观看视频短片的方式启动即时情绪;依然将笔记本电脑产品作为高认知参与的操纵。由此,实验2采用3(情绪:高兴/平和/控制)×2(来源国信息:有/无)的组间实验设计。
5.1 研究过程
实验2在上海某本科院校进行,共有159名被试参加实验,剔除未完成实验的13位被试的数据,最终获得146个有效数据(女性占57.1%)。所有被试随机分配到六个实验组,分别观看高兴、平和或控制组的视频并完成情绪的自我评定。其中,启动高兴情绪的视频选自一段综艺节目,启动平和情绪的视频为一段风景介绍短片,控制组的视频为一段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剪辑,三段视频时长均为5~6分钟。正式实验前,我们对两个实验组视频的情绪启动效果进行了前测。44名非正式实验的被试随机观看引起高兴或平和情绪的视频,之后回答实验1采用的情绪自评量表(Agrawal et al. , 2007)。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在高兴分量表上(ɑ =0.82),高兴组显著高于平和组(M高兴=5.80, SD=1.19; M平和=4.68, SD=1.30; F(1, 43)=8.77, p<0.01);在平和分量表上(ɑ=0.83),平和组的得分则显著高于高兴组(M高兴=4.35, SD=1.57; M平和=6.27, SD=0.98;F(1, 43)=24.35, p < 0.001),由此表明视频的启动效果良好。实验的第二部分为产品评价,实验材料及产品评价、产品期望的测量同实验1a。
5.2 研究结果
5.2.1 情绪启动的检验
首先,进行3(情绪:高兴/平和/控制)×2(来源国信息:有/无)的交互效应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情绪的主效应显著(F(1, 140)=7.41, p=0.001,ηp2=0.096);有无来源国信息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40)=0.28, p=0.599,ηp2=0.002),情绪×信息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40)=4.96, p=0.008,ηp2=0.066)。进一步针对印度来源国产品进行One-Way ANOVA检验,结果表明:三组消费者在产品态度的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M高兴=2.73,SD=0.88;M平和=4.05, SD=1.04; M控制组=3.11, SD=1.05; F(1, 66)=10.64, p=0.000)。两两比较发现,平和组的产品态度显著高于控制组(F(1, 43)=9.02, p=0.004);高兴组的产品态度虽然低于控制组,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F(1, 45)=1.81,p=0.19)。由此可知,当情绪的关系指向特征与来源国文化相匹配时,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评价,而在不匹配的情况下,产品评价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
5.2.2 因变量的检验
采用One-Way ANOVA检验情绪启动效果,结果表明:高兴组在高兴得分上显著高于平和组(M高兴=5.48,SD=1.07;M平和=4.33,SD=1.28;F(1, 122)=28.92,p < 0.000);在平和分数上,平和组显著高于高兴组(M平和=5.51,SD=0.97;M高兴=4.10,SD=1.33;F(1, 122)=45.53, p<0.000)。
采用One-Way ANOVA的分析结果显示,在高兴分量表上,高兴组的分数显著高于平和组与控制组(M高兴=5.10, SD=1.07;M平和=3.71, SD=1.15;M控制组=3.40, SD=1.45;F(1, 143)=26.21, p < 0.000);在平和分量表上,平和组的分数显著高于高兴组和控制组(M平和组=5.28, SD=1.10;M高兴=3.49, SD=1.03; M控制组=4.70, SD=1.44; F(1, 143)=27.59,p < 0.000),说明情绪启动操作成功。
图2 情绪与来源国信息的交互作用分析
其次,针对高兴与平和两个情绪水平进行ANOVA检验,发现情绪的主效应显著,平和条件下的产品态度评价显著优于高兴条件(M平和=3.71,SD=0.99;M高兴=2.98,SD=0.87;F(1, 92)=16.81, p=0.000,ηp2=0.154),有无来源国信息的主效应不显著(F(1, 92)=0.09,p=0.760,ηp2=0.001),情绪×信息的交互作用显著(F(1, 92)=9.59,p=0.003,ηp2=0.094)。进一步对情绪×信息的交互项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针对以印度为来源国的笔记本电脑产品,消费者在平和情绪下较高兴情绪下有更积极的态度评价(F(1, 92)=24.84, p=0.000,ηp2=0.213),针对无来源国信息的笔记本电脑产品,消费者的态度评价没有受到情绪的影响(F(1, 92)=0.525, p=0.470,ηp2=0.006)。由此,H1a得到再次验证。
5.2.3 中介作用的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情绪指向与来源国文化的匹配性对产品态度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者针对平和组和高兴组,验证“期望度”的中介效应。按照Zhao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Hayes(2004)和Hayes(2013)提出的Bootstrap方法(选择模型7,样本量5000,95%的置信度),以情绪为自变量,来源国信息为调节变量,产品态度为因变量,对期望度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期望度的中介效应显著(LLCI=-1.2970,ULCI=-0.2078),中介效应大小为-0.7230,且控制中介变量期望度之后,自变量情绪(高兴/平和)对因变量产品态度的影响仍显著,区间(LLCI=0.1144,ULCI=0.6654)不包含0,期望度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检验结果还表明,情绪和来源国信息的交互作用显著(LLCI=-2.3247,ULCI=-0.3802,不包含0)。具体而言,针对印度来源国的笔记本电脑,期望度的中介作用显著(LLCI=0.3438,ULCI=1.1165,不包含0),而针对无来源国信息的笔记本电脑,期望度的中介作用不存在(LLCI=-0.3950,ULCI=0.3424,包含0)。由此,H2获得再次证明。
6.实验3:情绪他人指向特征与来源国文化匹配性的影响因素
实验3的研究目的是在低卷入度产品类别下,进一步探索认知参与度的影响作用。我们认为:在实验1b中,果汁产品作为一种快速消费品,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认知参与较低,不会进入深入加工模式,因而导致在低卷入的产品类别中,无法获得情绪与文化的匹配性关系。因此,实验3期望通过引入附加信息的方式,激发消费者不同的认知加工策略,以进一步证明高认知参与是情绪的文化特征产生作用的条件,因为随着信息数量的增多,认知任务的复杂性提高,个体会付出额外的信息加工努力(Petty & Cacioppo, 1984)。我们设置强/弱两类信息组,强信息组为果汁产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是与原产品描述一致的积极信息;而弱信息组则提供了相对负面的论述,与原产品描述产生不一致。我们认为在强化了认知参与的一致性条件下,将产生情绪与来源国文化的匹配效应;而弱信息组虽然也引发了认知参与,但负面不一致信息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可以依据产品属性做出直接判断,而不需要考虑来源国因素,情绪的文化特征也就不会对认知产生影响,即进入了低情绪浸入的模式(Forgas, 1995a)。除此之外,实验3将引入国家认同变量,探索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情感因素是否对“匹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6.1 研究过程
实验3采用2(情绪:高兴/平和)× 2(附加信息:强/弱)的组间实验设计,在上海某本科院校中招募学生被试124名(女性48.4%)。所有被试随机分派到四组并分别完成四部分的实验任务。第一部分为情绪启动和情绪状态的自我评定(同实验1a)。第二部分为阅读虚拟果汁品牌“万奇”的广告以及附加信息材料,附加信息被描述为这款新果汁产品的市场调研结果。附加材料的设计参照Maheswan和 Chen(2006)的研究,选取了口感、维生素含量、纯正度、色泽以及无菌包装五个与果汁相关的产品属性,并邀请了49名非正式实验被试对属性的重要程度进行评分,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口感(M=5.98,SD=1.25)、纯正度(M=5.78,SD=1.38)、无菌包装(M=5.76,SD=1.38)、维生素含量(M=5.59, SD=1.47)和色泽(M=4.07, SD=1.87)。因此,在强附加信息组中,告知被试“万奇”品牌在口感、纯正度和无菌包装三个重要属性上的评价高于另两个品牌,在次重要属性上与另两个品牌有相同的评价,在最不重要的属性上的评价低于另两个品牌;相对地,在弱附加信息组中,则告知被试“万奇”品牌在三个重要属性上的评价低于其他两个品牌,在最不重要属性上优于其他品牌。之后,完成对产品购买意愿的评价,测项为“请预测一下,在未来10次购买果汁饮料产品时,您可能有几次选择万奇”(Laroche et al. ,1996)。实验的第三部分为一个无关测试,请被试用3~5分钟的时间写下本学期的课程表,以消除情绪的后续效应。第四部分为国家认同的测量,四个测项源自Verlegh(2007)的研究,分别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当一个外国人夸赞我的祖国时,就像对我个人的赞美一样”以及反向计分题项“我不觉得自己与中国之间有任何联系”。
5.2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自然天敌,控制使用杀虫谱广的农药,减少果园喷药次数及农药用量;利用微生物农药,如细菌(苏云金杆菌等)、真菌(蚜霉菌、绿僵菌、白僵菌等)、农用抗生素(农抗120、农用链霉素)等;利用昆虫生长调节剂,如抑太保、米螨(虫酰肼)等。
6.2 研究过程
6.2.1 情绪启动的检验
小学英语多媒体资源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构建恰当、合适的小学英语多媒体资源,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积极主动学习。适度整合农村地区零散的小学英语多媒体资源,能够有效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策略,一定程度上促进教研教改,提高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5)海关物流监控中心:负责铅封的发放、注销、核对等管理工作,通过网络与场站计算机进行数据通信[1]。
6.2.2 因变量的检验
针对因变量购买意愿进行2(情绪:高兴/平和)×2(附加信息:强/弱)的ANOVA检验。结果表明:情绪的主效应显著,在平和情绪条件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高于在高兴条件下(M平和=3.14, SD=2.15; M高兴=2.43, SD=1.77; F(1, 120)=4.92, p=0.028,ηp2=0.039); 附加信息的主效应显著,在有强附加信息的条件下,消费者产生了更高的购买意愿(M强=3.73, SD=2.07;M弱=1.85,SD=1.41;F(1, 120)=35.70,p<0.000,ηp2=0.229);情绪与一致性附加信息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120)=3.63,p=0.059,ηp2=0.029)。
进一步对情绪×附加信息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仅在有强附加信息的情况下,中国果汁产品的购买意愿会受到情绪变量的影响,在平和情绪下的购买意愿显著高于在高兴情绪下(M平和=4.34,SD=2.04;M高兴=3.07,SD=1.91;F(1, 120)=8.50,p=0.004,ηp2=0.066)。而在弱附加信息的条件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不受情绪的影响(M平和=1.90,SD=1.47;M高兴=1.81,SD=1.38;F(1, 120)=0.83,p=0.825,ηp2=0.000)。由此可知,附加信息性质影响了情绪对购买意愿的作用(交互作用结果见图3)。
图3 情绪与附加信息的交互作用(果汁产品)
6.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强附加信息的条件下,检验国家认同在情绪指向特征与来源国文化匹配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按照Zhao等(2010)提出的中介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等(2007)和Hayes(2013)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模型(模型7,样本量选择5000,置信区间选择95%)进行Bootstrap检验,自变量采用虚拟编码(平和情绪组编码为0,高兴情绪组编码为1)。结果表明,期望度在情绪和国家认同对产品购买意愿的交互作用中具有中介作用(LLCI=0.0652,ULCI=1.2668,不包含0),作用大小为0.3755。进一步按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分低、中、高三种国家认同水平,分析了不同国家认同水平下情绪对购买意愿影响中期望度的中介效应。条件间接效应的结果显示:针对国家认同较低和中等的消费者,情绪通过期望度对购买意愿的中介作用显著(LLCI=-1.5738,ULCI=-0.2130,不包含0;LLCI=-0.9294,ULCI=-0.0709,不包含0),而对于国家认同较高的消费者,期望度的中介作用不显著(LLCI=-0.5045,ULCI=0.2942,包含0),H3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6.3 结论与讨论
实验3在低卷入度的产品类别中检验了情绪他人指向特征和来源国集体主义文化的匹配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发现引入附加信息引发较高的认知参与时,情绪他人指向特征会对集体主义文化来源国产品的购买意愿产生影响,这也再次证明了情绪他人指向特征与来源国集体主义文化的匹配效应是一种深入加工模式;但当附加信息为负面评价时,消费者会直接对产品做出判断,而并不依据情绪的线索作用。除此之外,实验3还证明了消费者的国家认同在情绪关系指向特征通过期望度影响来源国产品评价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说明情绪与来源国文化特征的匹配作用会受到个体情感因素的影响,当个体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时,情绪的无意识影响作用会受到削弱(Forgas, 1995a)。
其中KC(箱)表示安全库存;V(件/min)为生产线固定时间内消耗的零件个数;T(min)为Milk-run系统的配送周期;u表示每个零件的单箱数量。
7.总体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三个实验研究,验证了他人指向型情绪与来源国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之间的匹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类型以及附加产品信息的引入,进一步探讨这一匹配效应发挥影响作用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当他人指向型情绪(平和)与来源国信息中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相匹配时,消费者会对产品产生更积极的评价,从而获得较为积极的来源国效应,且这一匹配效应存在于高认知参与的情况,比如针对高卷入度的产品,或需要额外认知参与的低卷入产品情境。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针对产品来源国为本国产品的情境,消费者丰富的国家情感卷入,也会削弱情绪关系指向特征的影响作用。
7.1 理论及应用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首先体现在来源国和国家品牌资产的研究领域,针对以往研究未能在以中国为产品来源国的条件下,证明情绪与文化的“一致性效应”问题,本研究通过产品信息和国家情感的控制进行了有效的解释,从而推进了情绪与来源国关系的主题研究。其次,他人指向情绪与集体主义文化来源国之间的匹配关系获得验证,说明即时性的情境因素可以成为影响来源国效应的重要变量,这突破了来源国刻板印象受某国历史、政治和经济发展等长期稳定因素影响的问题(Gürhancanli & Maheswaran, 2000b)。更进一步的,当国家文化特征可以通过消费者的某种特定情绪来表达和传递时,情绪不仅成为识别和判断来自某国的企业、品牌或产品的特殊符号,更丰富了国家品牌资产的文化内涵,使其不仅限于国家品牌感知质量和国家品牌意识等要素(Yoo & Donthu,2001),也可以具备国家的情绪特征联想内容。最后,基于来源国效应的主题,本文揭示了情绪作用于认知加工过程的模式,即自我意识型情绪(如他人指向型)通过深入加工模式影响到来源国效应的问题,从而将情绪影响下的认知机制问题推向深入。
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如何利用情绪对认知的影响作用管理国家、企业和产品品牌,特别是对于他人指向型文化中的非优势来源国效应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针对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来源国,在进行品牌推广和营销时可以充分利用他人指向型情绪,保持国家文化线索与情绪特征之间的一致性,有效提升品牌评价,从而将消费者的情绪情感打造成为国家品牌资产的一个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在具体营销实践中,还应把握产品品类以及产品属性信息方面的特点,使得情绪的他人指向性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充分发挥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采用提供多种积极产品信息的方式,如专家评价、他人推荐、第三方评价机构传播的信息内容等。除此之外,在跨国营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也可以体现本研究的实践价值。比如,在以宣传某国产品或品牌为主旨的展销会或是商业活动中,可以通过营造与该国文化相契合的情绪氛围,获得积极的企业和品牌评价;在宣传国家形象、介绍国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国际活动中,更是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将具有文化意义的情绪元素融入国家形象推广的策略中。
一个生长在杏雨烟柳、六朝金陵的女子,她有太多属于这个城市的性格,极富耐心又极具慧心,将清秀、湿润、温文尔雅,润物无声地渗透进每一丝空气中。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在探讨情绪他人指向特征的影响机制过程中,将“期望度”作为中介变量进行验证,这是相对间接地反映“一致性”效应的指标,今后的研究可以引入测量独立自我或相依自我联想的指标(Agrawal et al., 2007),以获得情绪和来源国文化之间更直接的解释。另外,本文在证明情绪的他人指向特征对认知产生影响时,是通过操作自变量,即产品的卷入度和广告信息的复杂程度来实现的;但是,没有通过因变量的测量来考察深入加工式策略与启发式策略引发的结果差异,比如在Forgas(1995b)的文章中即指出,相较于受情绪直接影响的启发式策略,深入加工式策略下的认知判断时间更长,信息的回忆程度也更高;这两类指标也应当用于检验情绪的文化特征对认知产生影响的深入加工式策略。
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围绕情绪的文化特征主题探索其他的情绪特征,例如情绪在动机倾向上的趋近(approach)和趋避(avoidance)性,已被证明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差异性:在西方文化下,人们表现出追求自主性、取得成就的趋近目标取向;而在东方文化下,人们表现出追求归属、避免潜在危险的趋避目标取向(Aaker & Lee, 2001)。那么,情绪的趋近或趋避特征是否影响涉及来源国问题的消费者认知呢?在未来研究中可以继续围绕情绪的具体特征进行探索,以丰富国家品牌资产的文化内涵,并为国家和企业提供更多提升国家品牌形象,获得积极来源国效应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才源源, 何佳讯. 高兴与平和:积极情绪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J]. 营销科学学报, 2012, 8(3).
[2]朱丽叶, 袁登华, 张静宜. 在线用户评论质量与评论者等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产品卷入度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17, 29(2).
[3]Aaker, J. L., Lee, A. Y. “I” seek pleasures and “we” avoid pains: The role of self-regulatory goal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ersuasion[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2001,28(1): 33-49.
[4]Aaker, J. L., Williams, P. Empathy versus pride: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appeals across cultures[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1998,25(3).
[5]Agrawal, N., Menon, G., Aaker, J. L. Getting emotional about health[J].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 2007, 44(1).
[6]Balabanis, G., Diamantopoulos. Domestic country bias, country-of-origin effects, and consumer ethnocentrism: a multidimensional unfolding approach [J].JournaloftheAcademyofMarketingScience, 2004,32(1).
[7]Bower, G. H. Mood and memory [J].AmericanPsychologist, 1981, 36(2).
[8]Chowdhury, H. K., Ahmed, J. U.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partitioned country of origin on consumer product quality perceptions[J].InternationalJournalofConsumerStudies, 2009, 33(4).
[9]Desteno, D., Petty, R. E., Wegener, D.T., et al. Beyond valence in the perception of likelihood: The role of emotion specificity [J]. 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2000, 78(3).
[10]Dinnie, K. Global Brand strategy: Unlocking brand potential across countries, cultures and markets[J].JournalofBrandManagement, 2004, 12(1).
[11]Forgas, J. P. Mood and judgment: The affect infusion model (AIM)[J]. PsychologicalBulletin, 1995a, 117(1):.
[12]Forgas, J. P. Strange couples: Mood effects on judgments and memory about prototypical and atypical relationships[J].Personality&SocialPsychologyBulletin, 1995, 21(7).
[13]Gürhancanli, Z., Maheswaran, D. Determinants of country-of-origin evaluations[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2000, 27(1).
[14]Hayes, A. F.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2013.
[15]He, J., Wang, C. L.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sumer ethnocentrism impacts on preference and purchase of domestic versus import brand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J]. 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 2015, 68 (6).
[16]Hirshleifer, D., Shumway, T. Good day sunshine: Stock returns and the weather[J].TheJournalofFinance, 2003, 58(3).
[17]Hong, S. T., Wyer, R.S. Effects of country-of-origin and product-attribute in format [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1989, 16(2).
[18]Iversen, N. M., Hem, L. E. Country image in national umbrella branding effects of country associations on similarity judgments [J]. AsiaPacificAdvancesinConsumerResearch, 2001(4).
[19]Iyer, G. R., Kalita, J. K. The impact of country-of-origin and country-of-manufacture cues on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quality and value[J].JournalofGlobalMarketing, 1997, 11(1).
[20]Keillor, B. D., Hult, G. T. M., Erffmeyer, R. C., et al. NATI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measure for us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J]. JournalofInternationalMarketing, 1996, 4(2).
[21]Keltner, D., Ellsworth, P. C., Edwards, K. Beyond simple pessimism: Effects of sadness and anger on social perception[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1993, 64(5).
[22]Kim, H., Park, K., Schwarz, N. Will this trip really be exciting? The role of incidental emotions in product evaluation[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2010, 36(6).
[23]Laroche, M., Kim, C., Zhou, L. X. Brand familiarity and confidence as determinants of purchase intention: An empirical test in a multiple brand context [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 1996, 37(2).
[24]Lerner, J. S., Keltner, D. Beyond valence: Toward a model of motion-specific influences on judgement and choice[J].Cognition&Emotion, 2000, 14(4).
[25]Mackie, D. M., Smith, E. R. Intergroup relations: Insights from a theoretically integrative approach[J].PsychologicalReview, 1998, 105(3).
[26]Maheswaran, D., Chen, C. Y. Nation equity: Incidental emotions in country-of-origin effects[J]. 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2006, 33(3).
[27]Maheswaran, D. Country of origin as a stereotype: Effects of consumer expertise and attribute strength on product evaluations[J]. 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1994, 21(2).
[28]Maheswaran, D., Mackie, D. M., Chaiken, S. Brand name as a heuristic cue: The effects of task importance and expectancy confirmation on consumer judgments[J].JournalofConsumerPsychology, 1992, 1(4).
[29]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Review, 1991, 98(2).
[30]Martin, L. L., Abend, T., Sedikides, C., et al. How would I feel if…? Mood as input to a role fulfillment evaluation process[J].JournalofPersonality&SocialPsychology, 1997, 73(2).
[31]Olins, W. Branding the nati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J].JournalofBrandManagement, 2002, 9(4).
[32]Pappu, R., Quester, P. Country equity: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J].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 2010, 19(3).
[33]Petty, R. E., Cacioppo, J. T. The effects of involvement on responses to argument quantity and quality: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persuasion[J].JournalofPersonality&SocialPsychology, 1984, 46(1).
[34]Preacher, K. J., Hayes, A.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J].BehavioralResearchMethods,InstrumentsandComputers, 2004, 36(4).
[35]Salovey, P. Mood-induced self-focused attention[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1992, 62(4).
[36]Schwarz, N., Clore, G. L. 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ments of well-being: 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1983, 45(3).
[37]Smith, C. A, Ellsworth, P. C. Patterns of cognitive appraisal in emotion[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hycology, 1985, 48(4).
[38]Swaminathan, V., Page, K. L., Gürhan-Canli, Z. “My” brand or “Our” brand: The effects of brand relationship dimensions and self-construal on brand evaluations [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2007, 34(2).
[39]Tiedens, L. Z., Linton, S. Judgment under emotional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The effects of specific emotions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J]. 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2001, 81(6).
[40]Vaughn, R. How advertising works: A planning model revisited[J].JournalofAdvertisingResearch, 1986, 26(1), 57-63.
[41]Verlegh, P. W. J. Home country bias in product evaluation: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economic and socio-psychological motives[J]. 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 2007, 38(3).
[42]Yoo, B., Donthu, N.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sumer-based brand equity scale[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 2001(1).
[43]Zaichkowsky, J. L. The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Reduction, revision, and application to advertising[J].JournalofAdvertising, 1994, 23(4).
[44]Zhao, X. S., Lynch, J. G., Chen, Q. M. 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 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2010, 37(2).
TheImpactofOther-focusedEmotiononEvaluationtowardsProductsOriginatedfromCountriesinCollectivismContext—The Mediation of Expectancy and Moder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Cai Yuanyuan1 Du Qiaoying2 He Jiaxun3,5 Wang Chenglu4,5
(1,2 SHU-UTS SILC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201800; 3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1; 4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New Haven, West Haven, CT 06516;5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Branding Strateg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1)
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other-focused emotion and collective country of origin information. Three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consumers under other-focused emotion (peacefulness) show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 towards products originated from collective countries than those under self-focused emotion (happiness). In addition, cognitive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 behind the compatibility are further explored by combining variables of product category, additional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f country of origin and further provide guidance on developing marketing strategy and promoting national brand equity for countries with less advantaged origin effect but distinc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Country-of-origin; Other-focused emotion; Cognitive model; Nation brand equity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消费者情绪对品牌全球化定位与本土化定位态度评价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716021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品牌与国家的联结:数字化时代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创建全球品牌资产的新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71772066);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消费者情绪的文化特征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14PJC047)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何佳讯,E-mail:jxhe@dbm.ecnu.edu.cn。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专业主编:杜 旌
标签:情绪论文; 来源论文; 认知论文; 产品论文; 平和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珞珈管理评论》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消费者情绪对品牌全球化定位与本土化定位态度评价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716021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品牌与国家的联结:数字化时代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创建全球品牌资产的新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71772066)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消费者情绪的文化特征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14PJC047)阶段性成果论文;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论文; 美国纽黑文大学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