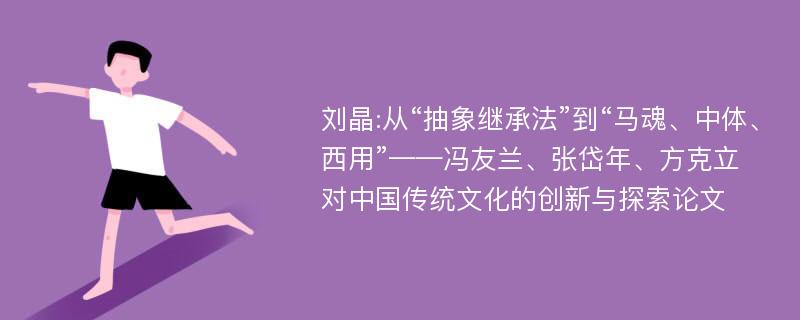
摘 要: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当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无法正确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之路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锁定在文化创新上。从冯友兰“抽象继承法”到张岱年“综合创新”再到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都表明了中国当代学者在传统文化创新之路上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关键词:冯友兰;张岱年;方克立;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创新
五四运动以来,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在近代,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即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其划分标准和争论焦点多集中于中西方文化的优劣和关系等问题上。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和弊病,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以杜亚泉和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只是在物质文明上略逊于西方。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这一阶段,中国知识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日趋客观,许多学者提出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
受社会历史环境等因素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批判的继承”为主,但是关于批判的范围和力度并没有明确界限。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界在重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化的解读方式,使之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契合。本文以冯友兰、张岱年和方克立为代表分析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一、冯友兰:“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十分关注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问题。他曾指出,文化的根本问题并非东西问题,而是古今问题。大家忽视的根本问题在于不是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而是将西方的近代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比较,即用西方近代的工业文明和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相比较。在此基础上,冯友兰提出了“别共殊”的问题。他认为社会类型可以看作是共相,国家或民族可以看作是殊相,同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可能是不同的社会类型,这就是殊相之中有共相。中国文化的问题应该是将其从古代转入到近代,而不是转变成西方文化类型。这种变化从共相层面分析可能让中国和西方各国一样快速发展,步入到富裕强国的队伍中;从殊相层面分析也能够很好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由此可见,冯友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中的一派,而是走中西方思想相结合的道路,属于超越于两派思想的创新之路。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提到“社会上底事情,新底在一方面都是旧底的继续。有继往而不开来者,但没有开来者不在一方面是继往。”[1]此处的“继往开来”既没有激进主义反对传统文化的极端性,也没有保守主义空谈古代文化的不切实际,而是表达出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曾多次检讨和反思自己的哲学思想,对早年的一些学术主张和观点也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对“别共殊”的态度却有所坚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抽象继承法”的主张。20世纪5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一股极“左”思潮,一些学者教条化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学者直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秉持着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从事学术研究。针对这一现象,冯友兰在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提出了如何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方法问题,后被吴传启的《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冯友兰提出,中国哲学的遗产要在区别哲学命题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基础上科学的继承,只片面地关注抽象或具体的意义是错误的。将两者相互区别,并从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方面思考对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才是关键。
受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冯友兰曾调整和修改过“抽象继承法”,甚至进行过全面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他在《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直接表明“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2]冯友兰的这些行为或许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晚年政治环境宽松时期,冯友兰也表示“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当,但是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3]。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才开始逐步接受这一概念,并给予较高的评价。概括来说,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过两次调整,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从1958年左右的几篇文章看来,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的继承”,是继承普遍的思想形式,而不是对具体内容的继承。80年代初期完成的《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调整,这包括“把哲学的继承归结为对于某些命题的继承,这就不妥当。哲学上的继承应该说是对于体系的继承”,“说一个命题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这也是不妥当的……所以一个哲学命题,应该只有抽象的意义。”[3]对于冯友兰这种调整和转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同时也是出于学术考虑,1950年的提法是为纠正当时偏执于“具体意义”的现实,而1980年的转变更多的是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继承本身考虑。冯友兰晚年又再一次将共殊关系问题穿插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中。在他看来,共殊关系不仅仅是哲学问题,也是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古今问题和中西方文化的关键问题。
草33区块被西南部的石村断层及东北部的草25断层所切割,地层向西北倾没,总体构造形态为向东南方向逐渐抬升超覆的平缓鼻状构造,地层倾角为2.0°~3.0°。油藏埋深884.0~1 014.0m。储层为疏松砂砾岩,厚度小于6m,但分布较稳定、连通性好。储层孔隙度一般30%,渗透率变化范围为(1 340~7 752)×10-3μm2。原油密度0.967 1~0.993 4g/cm3,50℃温度条件下,地面脱气原油黏度10~60Pa·s,属特稠油油藏。
二、张岱年:“综合创新”
张岱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观点主要受两个人影响,间接影响来自冯友兰,而直接影响来自兄长张申府。针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问题,张岱年曾写文章《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针对冯友兰提出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内容,提出要从科学性和民主性两个方面继承哲学遗产。“何谓科学性?科学性就是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就是揭示了客观规律的。何谓民主性?民主性就是反映了人民要求的,就是适合人民的需要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思想就是促进历史发展的思想,也就是对于人民有益的思想,在今天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会起积极作用的思想,所以我们要继承。科学性的民主性的思想是哪些思想呢?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辩证法的思想,以及批判专制主义的思想。这里面包括了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正确思想,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学说中的合理因素。”[4]此外,张岱年还强调我们真正应该继承的是思想的精神实质,对于思想的具体内容要进行改造或提高。
1990年,方克立将“综合创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他对此解释:(1)我们学习、借鉴、继承、吸取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全方位开放的,是全面的历史主义的态度。(2)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都是立足于中国今天的现实,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继承、选择的目的和标准,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求。(3)学习、借鉴、继承、选择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批判继承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继承法。把握黑格尔所说的‘扬弃’这个概念,就能了解‘批判继承’的实质。(4)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综合与创新相结合。文化系统的解构与重构是一个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辩证过程。综合本身就是创造,就是创新,就是发展。所以综合创新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9]。“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求我们公正对待优秀的文化成果,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有助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化建设都可以吸收和借鉴。“批判继承”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古今中西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对于合理的精华内容予以改造和继承,对于不合理的糟粕予以批判和抛弃。方克立对于古今文化的根本态度在于“综合创新”,这里的“综合”和“创新”就表明要立足于优秀文化本身,尽可能地创造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新文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反思过往社会历史事件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此次文化热潮更加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以及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如前文所述,张岱年在此次热潮中重新阐述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理论,并得到了学界的不同反应,其中方克立对此抱以极高的关注和认同。他曾著有《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和《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等著作用以阐述自己的文化观点,有学者认为张岱年和方克立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代表。[8]
统观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他从没有如激进主义者一般极端地否定传统文化,也没有如保守主义者过分强调古代文化的巨大价值,而是通过正确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殊关系等方式阐述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思路不仅为当时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后来的学者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二种迹象:微小的日常。一些艺术家已经抛开了所谓宏大叙述,转向了更加贴近自身的、细微的日常景观,展开更加深入、细腻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独特视角。
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新”理论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求。他对文化解析和重构的设想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中事物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原则、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保留了文化中的民族性、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显示了文化所具有的交融性,他强调的综合与改造也体现出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统观张岱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创造的综合”到“综合创新论”的过程,虽然这些理论有传承有差异,但是究其本质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合理解读。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岱年较少提及这一思想和主张,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提出“综合创新论”,即“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6]。主要内容就是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进而创造出全新的中国文化。在张岱年眼中,中国传统思想中优秀的内容不应舍弃,中国近代传入的西方文化也有其发展的合理性,诸多思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方能创造出优秀的成果。张岱年在晚年提出的“综合创新论”是对三十年代“创造的综合”的继承和发展,他在包含内容上从单一的哲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创新论”除中西文化之综合的含义外,同时也包含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7]当然,中国传统学派间的综合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张岱年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点加以区分,批判封建缺点、找寻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点加以保留和发扬;在综合中西方文化和优缺点的基础上创造全新文化。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既代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代表了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三、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
其兄长张申府曾针对中西方哲学及文化问题提出要结合逻辑解析和辩证唯物论的方法,他认为应当是集孔子、罗素和列宁于一体的综合哲学。张申府将这些思想综合的目的在于阐述中国需要新文化建设,即不排斥西方文化、不否定传统文化,对当时中国现有文化加以辩证的综合。张岱年在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提出集唯物、理想和解析于一体的“创造的综合”思想。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的,且有卓越的贡献,我们既生于中国,对于先民此方面的贡献,实不当漠视,而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5]以及“中国过去哲学,更有一根本倾向,即是自然论与理想论之合一。中国哲学家大部分讲自然论的宇宙观,而更讲宏大卓越的理想。西洋人自然与理想主义那种绝然对立的情形,在中国是没有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综合唯物与理想,实正合于中国哲学之根本倾向。”[5]此处的“理想”主要是在强调精神的能动性,张岱年强调理想与唯物的综合,希望借以“理想”成为指导人类进步的思想关键。所谓“解析”主要是指西方实证主义强调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张岱年希望通过明确词句或命题的准确表达,清楚明晰思想中的真实含义。这一理论实际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将中国哲学中的人生理想学说与西方哲学中逻辑解析的方法相结合,形成“创造的综合”理论。张岱年提出这一理论并不是要突出中国传统思想有关理想概念的引导作用,也不是通过分析和推理解决命题的含义问题,而是试图将上述思想和方法相结合,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得到新知识,甚至获得“真知”。
教育学生讲究时机。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用细心去发现时机,用耐心去等待时机,用爱心去创造时机,要了解和研究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抓住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教育,只要时机得当、方法得当,定能很好地促使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y=-143 575.138-227.053x1+1 389.963x2-238.091x3+1 123.636x4+893.114x5-1 047.609x6+1 730.197x7+567.478x8
2006年,方克立在总结“综合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主张。“马魂”即“马学为魂”,“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体”即“中学为体”,“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用”即“西学为用”,“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10]。“马魂、中体、西用”的完整表述应该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过去学者在阐述文化问题时,多采用“中体西用”的方式,究其根本还是停留在体和用的二元层面。方克立有关文化的基本论断,采用了“魂、体、用”的三元结构,涵盖内容更广,结构表述更加清晰。
从“文化综合创新论”到“马魂、中体、西用”,两种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一脉相承。统观方克立有关文化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其理论精髓源自张岱年,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深化和突破。方克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观做出的创造性解读,正是一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同时也可以说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无法正确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解读方式曾出现过极端主义倾向,也经历了短暂的曲折。但是,统观其整体趋势则是坚持了“辩证的否定观”,努力实现批判与继承的辩证统一,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有价值的内容进行适当变革以适应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要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毫无价值的内容进行“决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知识界才会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态度。因此,我们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的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核心内容均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新事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43.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960.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40;243.
[4]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118-119.
[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63;273.
[6]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14.
[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八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628.
[8]洪晓楠.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J].中州学刊,1998(02).
[9]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303.
[10]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44.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9)06-0027-04
收稿日期:2019-03-11
作者简介:刘晶,内蒙古科技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黄晓伟]
标签:文化论文; 思想论文; 中国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张岱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1919年~)论文; 《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6期论文; 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