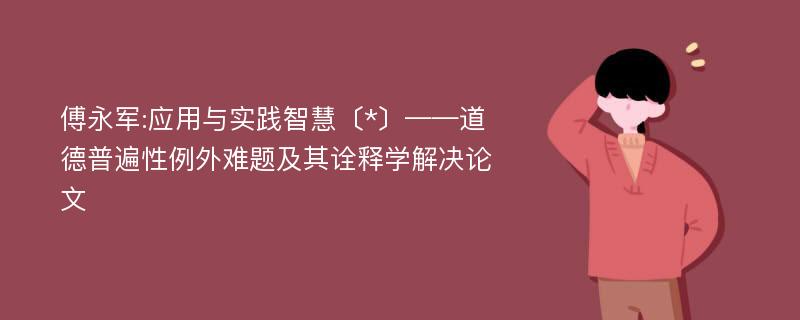
〔摘 要〕道德普遍性例外是康德主义伦理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经由对话伦理学的关注与讨论被归结为“证立”和“应用”之间关系问题。从应用角度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随着哲学诠释学意识在当代的勃兴而成为对话伦理学倡导者的优先选择。对话伦理学借用诠释学的应用原则,通过刻意强调特殊语境下的规范适当性,以解决道德的普遍规范与实践的特殊情形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然而,由于对话伦理学依然将应用理解为道德知识的实际使用,而非在道德行动中实现出来的实践智慧,因而,对话伦理学对诠释学应用问题的借用不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反而使自身落入近代以来理论与实践二元区分之陷阱中。在应用问题上正本清源,回归诠释学的真实洞见,将例外理解为特殊道德语境下不断获得具体化内容的道德行为方式,并以此纾解证立与应用之间的紧张关系,方是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道德普遍性例外;证立;应用;理解
在伦理学发展史上,康德用“绝对命令”的严苛性、非语境性维护了道德意识的纯洁性,也同时维护了道德之崇高地位和由此而来的人之尊严。康德基于摒弃禀赋的善良意志而证成的道德原则在其积极意义之外,也为以道德知识普遍性为诉求的伦理学志向留下一难题,即道德规范的认知上的普遍性与应用上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道德普遍性例外。毫无疑问,作为指导人应当如何行事、调节人与人之间行为期待的道德,不能回避普遍性问题,这是道德得以确立其地位并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但另一方面,道德毕竟与特定的道德情境密切关联,它必然是行动者在一定情境约束下所作出的特殊道德举止。为了与道德的日常直觉相契合,康德所留下的这种张力关系之解决必然是绕不开的问题。然而康德理论的一以贯之特征决定了这是其必然结论,例外问题在他那里也仅仅是道德意识因为恶的倾向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并发挥在冲突中磨砺道德意志并显示其纯粹性的特殊处境。所以该问题的答案显然无法在康德以独白理性为基础的道德理论内部获得,或者说康德伦理学根本上就是排斥道德普遍性例外的。换言之,通过康德绝对命令检验的道德规范,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下都是普遍适用也已应该被行动者无条件遵循的。除此之外,康德似乎还有一个问题未表述清楚,即当以知识形态存在的道德规范进入日常道德实践而被语境特征所限制,并与其它同样具有知识特征的道德规范出现竞争关系时,往往出现另一种认知与应用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不一致并未被背负普遍性论证负担的行动者所排斥,而是一定意义上被接受为合道德的行为(譬如“不应撒谎”在特殊情境下被违背)。面对该问题或困境,对话伦理学〔1〕在当代思想交锋中,形成了哈贝马斯在反思自己道德理论时提出的以“证立(justification)”和“应用(application)”关系为中心问题的学术场域。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此中心问题得以揭示而成为对话伦理学的一个主题,显然是基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应用问题的重新发现,这一点哈贝马斯和君特(Klaus Günther)均有明确表述〔2〕。基于这一层考量,笔者将站在康德伦理学普遍主义立场上,运用诠释学应用概念之于普遍与特殊的相关关系纠正被误解的应用意涵,并探讨加入应用考量的道德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内涵。简言之,以证立与应用关系为表征的道德普遍性例外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通过复归哲学诠释学应用意识而获得合法性解释,是本文所拟解决的问题。
我们赶回河浦时天刚擦黑。路边田里姜月娥在割稻子,她冲我喊道,腊枝你快点儿回去!你伢儿病得么事样的,把百福寺的先生都接来了!我听了心里一紧,拔腿就跑,匆忙赶回屋里。大梁蹲在摇篮边,抬起紧锁的眉头,求救似的望着我。我跑过去,双手扒着摇篮,见大女儿小脸儿潮红,紫色的小嘴儿开张着,透亮的鼻翼费力地翕动,呼呼地直喘气。我把大女儿抱起喂奶,她小脸儿贴在我胸前,嘴巴一动不动!我慌了神,把奶头儿硬往她口里塞。她就那样懒洋洋地噙着,像是噙着一粒石子、一颗土块,无动于衷!
一、道德普遍性例外的两种诠释路径及其问题
如前所述,道德普遍性例外表现为道德认知普遍性和应用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对话伦理学中被揭橥为“证立”与“应用”间的张力关系。为了更好将问题呈现出来,有必要对相关争论进行归结。概而言之,对该问题具有自我反省意识并进行深入讨论者可分为三派:以君特为代表的分离派;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联系派;以及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同一派。但不管归属于那个派别,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都将诠释学意识尤其是应用意识作为解决张力关系的钥匙。基于讨论需要,笔者在这部分将首先探析君特和哈贝马斯观点:前者认为证立与应用是两个平行领域,各有各的逻辑(1);后者认为证立与应用两者并不分立而是存在联系,证立在逻辑上先于应用(2)。
(1) 依据君特,道德规范的证立与应用在道德论证中同等重要,前者属于证立性商谈范畴后者属于应用性商谈范畴,康德在日常道德直觉中遭遇尴尬原因在于道德规范的应用层面被绝对命令边缘化。规范证立和规范应用归属不同的道德商谈(对话)形式:对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之证立,意味着基于公开辩护理由的论证效力;而对于一个在特定道德情境中被实际遵循的规范之应用,“则涉及考察它是否以及如何与该情境相契合”〔3〕。道德规范的证立仅仅涉及这一规范是否能得到合理理由的支撑从而获得知识上的应然有效性,而规范的应用则只是涉及该道德规范是否能够适当地运用于某个道德情境。以绝对命令为例,康德绝对命令在证立意义上发挥的是元规范作用,它只是检验具体道德规范是否具有可普遍化特征的至高原则,只要道德行动者能够意愿该准则成为普遍法则,便可以脱离一切语境限制而是普遍的。但是在实际道德语境中,即使通过绝对命令检验的道德规范仍然存在矛盾冲突的可能,这就需要道德规范的应用性商谈予以解释。依君特所见,如果说证立性商谈的知识原则是可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原则,那么应用性商谈的可应用性原则就是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原则。这一原则的特异性在于,它在考量规范与情境之间的关系与相关情境所涉规范间的关系这种双重关系中确立何者被行动者选择为道德指导规范。由此,证立不存在应用维度,应用不考虑证立维度,如其所言:“证立性商谈必然排除规范冲突这个属性,也必然没有情境依赖这个维度。”〔4〕对于道德规范的证立来说,它可以也必须突破一切语境限制,并保证论证上的知识效力。但是对于道德规范之应用来说,则需审慎衡量特定道德情境中的事实及其相互关系,因为道德规范的证立不能穷尽与情境相关的所有事实,也不可能提前预知该情境中的规范冲突。
注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道德知识的普遍性乃是行为方式的普遍性。为了凸显这一点,我们简单构建一个康德主义伦理学的行动图式:
原则(principle)→规范(norm)→行为方式(way of act)
二、 诠释学应用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启示
道德普遍性例外严格来说具有两种矛盾表现,一种是获得证立的道德规范在不涉及冲突的道德语境中不被遵循,一种是存在规范冲突的语境中哪种规范具有优先性。这两者都与对话伦理学中的证立与应用的张力关系有关,也可以说与伦理学中的知行矛盾有关。通俗地讲,前者面对的质疑是具备道德的知识却不做道德的行为,后者面对的质疑是有道德的知识又有做道德行为的意愿却不知按哪个规范行事。现在的问题是,不论君特赋予证立与应用二者以分立关系还是哈贝马斯将两者建立起关联,都未能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的合理性难题。还有一种可能是诠释学提供的,即构建证立与应用的同一性关系来弥合两者,这一点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有关理解何以可能的理论(证立)向实践哲学(应用)转换的合理性所在,也是我们可以将这一意识运用于解决道德普遍性例外的起点。
道德普遍性例外同时指涉普遍性与特殊性张力关系,这是哲学诠释学同样关心的问题,“如果诠释学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同一个流传物必定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那么,从逻辑上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普遍东西和特殊东西的关系的问题。因此,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9〕伽达默尔这里的意思很明确,诠释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活动,理解活动基于人的历史境遇受前理解结构的限制,所以任何的理解都是理解者在具体情况中进行的特殊理解。可以说,在道德领域,这种特殊境况的理解对应的便是道德普遍性例外。隐含在道德普遍性例外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间的冲突之解决关键在于,作为诠释学的理解究竟如何看待与证立相对的应用,二者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道德规范应用向度的遗忘导致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出现矛盾,诠释学作为从本体论诠释理解的哲学理论总是内在地蕴含着“把理解的本文应用于解释者的目前境况”〔10〕这一任务。理解现象始终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始本文应用到具体境况中这一应用事实。本文向理解者提出理解要求,理解者处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和解释,“那么它一定要在任何时候,即在任何具体境况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被理解。理解在这里总已经是一种应用。”〔11〕按照康德绝对命令,道德规范的证立也即理解目标在于,通过该命令的检验以证成在任何语境下都应毫无例外地被遵循的道德规范,这种证立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即证立需要脱离一切经验干扰去追求适用于一切境况的普遍道德知识。因而,康德主义伦理学都具有道德知识的先验性取向,行动者在已经获得证立的道德规范引导下应用道德知识。
但哲学诠释学理解概念所证成的证立与应用却并不如此看待道德知识。理解与应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为理解本来就是一种应用,或者说是受应用制约的理解。对经过诠释学理解观念改造的道德知识来说,“道德知识决不能具有某种可学知识的先在性”〔12〕,这种知识一旦落入近代知识论转向对知识的理解就会违背道德的实践本性,“只要伦理学被理解为普遍化的知识,他就会出现因道德法则而引发的道德可疑性”〔13〕。换言之,道德知识在本性上就不是只关注证立并将应用视为随之而来的知识使用于具体情况这种自然科学知识意义,而是将道德知识视为“它本身包含完满的应用,并且在所与情况的直接性中去证明它的知识。所以它是一种完成道德认识的具体情况知识,然而也是一种不被感官所看见的知识”〔14〕。显然,按照诠释学理解的道德知识,首先着眼于道德规范的具体应用语境,而这也决定了行动者不是在道德的对面去观看道德知识,也即不是作为道德知识的观察者和发现者去论证道德知识,而是作为知识的参与者和承担者共同创造道德知识。对于绝对命令来说,重要的根本不是用证立方式演绎出普遍化的命令形式,而是命令执行者也即道德自我服从命令并依其而行才称之为命令。当经由纯粹理性证立的绝对命令发出时,这意味着该绝对命令需要应用到它所要应用的具体道德语境。因为道德命令作为被理解的本文,不是一种被感观或理性所客观观察或揭示的东西,命令之被理解为道德命令正在于,其意义在理解者那里被现实实现出来。正因如此,必然存在命令的被遵守和被拒绝这两种情况,但是不论是被遵守还是被拒绝都意味着命令获得了理解。理解命令之人在理解活动之下实际参与了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绝对命令也在这个层面上被有意义地理解和解释,并受理解者应用语境的制约而在其本文意义之外产生了一层适用于特殊语境的意义理解。如果绝对命令停留在证立层面,那么它就仅仅是孤立的没有获得理解的空疏本文,一旦理解者通过自身传统的理解限制赋予其空洞形式于语境中实现内容从而产生出实际道德效果,绝对命令才能作为命令而具有道德意义,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道德“知识不是匿名真理的集合,而是人的一种行为举动”〔15〕。这样,依据诠释学应用意识,道德知识的应用就不复是哈贝马斯所理解的经过理论证立所获得的与事实具有间距的知识,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证立与应用便本然统一在一起,这便是道德知识理解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道德知识由此回归到道德的行动本性,道德作为实践活动重新指向了人的现实具体的活动,这个活动在诠释学视野下属于理解且应用之范畴。
另外,道德普遍性例外还指涉道德历史性和社会性问题,这一点也是康德与哈贝马斯遭批评的核心。理解在哲学诠释学那里具有历史性特征的论证恰恰回应了该问题,理解总是在历史中的理解,这与证立的非历史性特征形成鲜明对照。关于证立与诠释学理解的历史性差异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简单区分:首先,两者对待传统或前见的态度是不同的。证立之所以为证立就在于它破除一切对我们的理解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情感、利益、风俗、生活方式等。证立之普遍性保障恰恰在于它希望将这些对我们的道德规范论证产生影响,从而妨碍获得客观性结果的因素都排除出道德证立实践。康德在论证其道德形而上学思想时明确地将经验而来的禀赋清除出道德领域,也就是道德哲学之作为形而上学必须是纯粹的,“这种形而上学必须谨慎地清除一切经验的东西”〔16〕。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保证了善良意志不受任何经验影响而表现出纯粹的道德内涵,从而也保证了绝对命令仅仅是出于道德理由而被尊为普遍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虽然意图改变康德的证立模式(U原则加入相关者利益之考量),但是他仍然假定了一个有绝对证立能力的被抽象掉一切经验因素的交往者角色,以此保证道德原则的可普遍化特征。而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理解将经验性因素看做是理解者无法清除的背景性前提,“自主的道德理性确实有仅用理智理解的自我决定特征,但这并不排除这样的事实,即人类的行动和决定受经验限制”〔17〕,理解者总是在他所归属的那个特殊的语境中带有前见地进行理解。其次,两者对待语言的态度也存在差别。道德规范的证立在现代语言学转向影响下,从康德的独白式证立转换成对话式证立。通过回归语言的沟通本性发现语言交往中蕴含的有效性要求为道德规范提供合理性说明。为了使对话式证立在一种不受前见干扰的状态下进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假定了一种理想的言谈环境,该环境始终商谈参与者以达至共识为唯一目的,需要摒弃源自于商谈者的特殊经验背景搁置前见以为道德规范找到那个被参与者共同接受的有效性要求。与此相似,诠释学的应用意识最终证成的也是一种基于对话中“你—我”结构的对话式伦理学,并同样将理解的基础归结为语言。但与作证立理解的对话式论证不同,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在语言中进行的理解,但语言发展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得以创造的过程,语言的时间性伴随着语言创造过程也丰富着语言表达,因而这样基础上展开的理解必然不是在假设性的、并且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的理想环境中进行对话。
总之,诠释学的理解在于其本性上包含应用,应用是理解的题中之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道德普遍性例外的例外向度获得在本体论上证立与应用一体两面的同一性结构。证立与应用更像是雅努斯的两副面孔,它归属于同一个体却在不同角度得以展现,并不能把两者单独出来加以运用,“对理解经验的高度理论认知与理解实践也同样是不可分割的”〔18〕。理解含义上的道德知识决不是现代科学中将理论视为实践指导而具有在先性这样一种理论性知识,因而其在逻辑上与时间上亦不具有优先性,“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19〕经过纯粹化和理想化处理的证立,与涉及语境的应用之间天然存在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天然性又必然预示将一种事先理解的普遍东西应用于随后的实际境况这样一层非诠释学意识的应用理解。准确地说,道德规范证立本来就已经是一种应用,“奠基问题具有应用问题的特征;道德商谈关注的是道德的应用,不管是具体社会问题领域还是个体行动的情境。”〔20〕它是受应用引导和制约的证立,甚至反过来说应用也就是一种证立同样成立。职是之故,诠释学的理解能合理解释道德普遍性例外就在于它本性上包含应用,诠释学的任务则在于思考被理解者那里所存在的普遍共同性,以及理解这种共同性必须面对并应用于不断变迁的历史境况中的特殊性关系。目前为止,我们的问题似乎已经论证清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那就是当应用作历史—社会的限制因素引入以说明例外的特殊性时,道德的普遍性如何保障?找出这种诠释学理解不会导致相对主义的理据,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
手持移动设备、传感器网络和射频识别技术的普遍应用积累了大量的移动对象数据,同时遥感卫星和地理信息系统又使得人们获得了大量的气候数据.这些时空数据内嵌于连续空间,其样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很强的自相关性.因此,使用有效的时空数据分析技术对大数据中有关于空气调节的信息进行自动抽取与分析对于空调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三、面向应用的道德何以是普遍的
选用当地优质肉鸡品种矮脚鸡进行养殖,该品种鸡体躯匀称、胫短,体型呈匍匐状,羽色主要有黄、麻和黑色,属于兼用型鸡种,具有较好的生产性能,肉嫩味美,适应性强,抗潮湿,易于饲养管理,是当地群众喜爱的鸡种。
将知识与道德联系起来而强调道德的普遍属性,似乎具有脱离诠释学证立与应用具有同一性的风险,因为伽达默尔曾明确说过诠释学意识并不研讨道德知识。〔25〕但诠释学并非如伽达默尔所言不研讨道德知识,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诠释学是在一种独属于精神科学真理观规导下来探讨道德知识的。伽达默尔只是不是单纯在证立层面上讨论道德知识,也不单纯在方法论上探讨道德知识的普遍性诉求,或者说伽达默尔所谓的道德知识应该是受诠释学应用问题重新发现制约的道德知识。受诠释学应用问题引导的道德知识仍然有普遍性诉求,关于这一点,兹尝试在诠释学视域内提供以下三种理由:
首先,道德意识的普遍性。道德知识的普遍性首要在于道德意识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保障康德是通过善良意志完成并通过自由获得保障的。伽达默尔则从道德历史发展的本性出发为之提供理由,他认为人之所以构建出道德就在于人对自身自然规定之本性的反叛或突破,从而确立起人之为人的精神特质。人类通过教化而实现这一成就,理论性的教化使得我们从具体语境中超脱出来以寻求那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来获得间距性知识,但实践教化则将我们提升为一个对自我有整体性认知并加以精神化诠释的存在者,诚如伽达默尔所言:“向普遍性的提升并不是局限于理论性的教化,而且一般来说,它不仅仅是指一种与实践活动相对立的理论活动,而是在总体上维护人类理性的本质规定。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26〕以实践智慧为根基并把人生在世的属人活动归入其中的道德行动在其本性上就具有普遍性诉求,它通过精神教化将人超拔于那些自然规定性,把人标示为一种道德的存在,这种道德存在应该是具有普遍性自觉且是理性的。只是经由道德教化而得到普遍提升的人之道德决定直接面对的是具体道德语境,“做出道德决定的任务正是在具体情况下做出正当行为的任务”〔27〕,这一点也是实践普遍性区别于理论普遍性的核心所在,但不具有理论知识形态并不是否定其普遍性的理由,在教化意义的精神提升层面上,道德意识同样排斥相对主义。
其次,道德知识是一种有别于逻各斯式知识的普遍知识。亚里士多德对于理性在道德知识中作用的研究表明,道德知识并不是一种可以脱离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而被理性单独规定的东西,而是恰恰相反,它是被人的存在方式所规定并反过来对其进行规定的知识。诚如伽达默尔所言:“道德知识并不是在勇敢、正义等概念的普遍性中,而是在其具体应用中决定了根据这种知识什么是在此时此地应该做的。”〔28〕然而,被如此界定的知识乍看上去似乎是排斥道德的知识化取向也即排斥普遍性的,伽达默尔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提问道:“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有这样一种关于人的道德存在的理论知识,以及知识(即‘逻各斯’)对人的道德存在究竟起什么作用。”〔29〕道德知识不是一种逻各斯的知识,也就是它并不是在道德的对立面去关照道德知识,而是以参与者身份实现道德知识,同时道德知识总是在特殊情况中表达和发现自身。从否定的角度来说,一种无法在具体情况中获得应用的道德知识本身是无用和无意义的,单纯以逻各斯方式进行自我表述的道德知识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否定。证立理论建立在合理性理论基础上,“它从一开始就与实践应用相对立。在这一特定方式下,书本和生活之间必然存在对立。”〔30〕书本代表的是证立,生活代表的应用,但否定这种对立即否定逻各斯式的道德知识不代表必然放弃普遍性诉求。
哈贝马斯与君特在证立与应用问题上显然观点有异,但不管是君特将证立与应用分而论之,还是哈贝马斯将证立视为应用之基础的观点,都未能对道德普遍性例外这一日常道德直觉之合理性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哈贝马斯虽然把应用建立在证立基础上,似乎注意到道德情境对于道德行为的制约作用。但根本上以证立为基础的普遍化原则仍然还在抽象追求道德知识的普遍化,这与其试图解决理论困境所引入的诠释学应用观念背道而驰。道德语境的历史性显现规定没有哪一个道德情境是对现存道德规范体系的简单选择,并依其而行从而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方式。相反,道德规范的应用情境可以是不断出现的带有相似性但又有特殊事实出现的历史情境,也可以是从未出现过的未知情境,这些新情境显然并不为证立和应用所提前预知。证立与应用的分立或联系实际上走向了对道德普遍性例外的自我否定。现在看来,要想为之提供合理性说明,剩下的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从本体论角度论证证立与应用的同一性,这就需要我们回到诠释学意识对应用问题的重新发现,以恢复被哈贝马斯和君特所误解的诠释学应用意识在道德普遍性例外上的展现方式。
高文军[4]等认为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方便、简单、安全、准确,在严格掌握适应证的情况下,可以用于卵巢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本研究在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中有6例穿刺病例病理提示:无法诊断(组织量少或坏死物),并将这6例归为阴性。其中有2例术后证实为畸胎瘤,4例术后证实为恶性卵巢肿瘤。回归分析:这6例盆腔肿块内部回声均以囊性成分为主,肿块较大,穿刺物为:坏死物或纤维组织,存在假阴性。
全球范围内成立了多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要集中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著名的有:麻省理工学院Hyper studio、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人文实验室、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等;并形成国际性组织。哥伦比亚大学位于巴特勒图书馆的数字人文中心,将基于计算机的文本、图像、书目及声音资料与其科研、教学、学习相融合,提供延伸服务支持人文科学领域的科研用户使用数字文本、动态及静态图像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将这些古老的文本和图像转换成数字形式,有助于超越过去限制获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丹麦学者P·肯普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解释学和伦理学的冲突》的论文,肯普认为伦理学与诠释学天然存在矛盾,因为“一个要捍卫人自身和个人的权利,另一个则要捍卫语言、语境或含义的完整性”〔21〕。肯普的具体论证姑且不论,但其确实提出了诠释学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即理解的相对主义。对于道德哲学来说,就像上一部分已经论证过的,道德普遍性例外问题通过回归诠释学意识而获得了合理性。尤其是伽达默尔对于诠释学应用问题的观点,更是使由道德普遍性例外所分离出来的证立与应用间的张力关系得以消弭。道德不再是先验意义上的绝对知识,而是一种非抽象的行动。哲学诠释学的理解即应用理论重新回到了道德的行动本质,当然,仍然有人会怀疑对诠释学意识的回归会导致过分强调特殊性而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这种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就像肯普合理揭示的,现代道德的道德自我理解是个体化的,它基于对整体化的伦理概念与个体化的道德概念之区分来为道德知识的普遍性进行辩护。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通过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为诠释学应用意识提供范例这点毫无疑问表明,伽达默尔是在伦理实体中发现伦理学普遍意义的。但有一点也同样明确,伽达默尔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视为伦理学上同属一脉且具互补关系方能使伦理学走出困境的“哲学伦理学”。而且,伽达默尔在回答杜特是否将自己的矛头指向规范伦理学时,他也只是说规范伦理学“忽视了这样一个解释学问题: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22〕。可以说,诠释学并不站在道德普遍性的对立面,作应用解释的理解活动并未导向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承认,而是相反它依然有理由去维护道德普遍性。伽达默尔明确说过:“理解也是作为一种道德知识德行的变形而被引入的,因为在这里不是关系到要去行动的我本身。所以‘Synesis’(理解)明确地指道德判断的能力。显然,只有当我们在判断中置身于某人借以行动的整个具体情况中时,我们才赞扬某人的理解。”〔23〕哲学诠释学借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作为理解范例去证明理解是指向实践的一种应用活动,它关注的核心并不是行动者所具有的那些内在品性,也并无意建立指导道德行动的规范体系,而是基于品性抑或规范所导向的道德行动。对道德本文的理解恰恰指的是在诸多情况所涉事实和所涉规范进行甄别、比较和选择的能力。诠释学意识下理解的道德“立足点是社会生活,我们生活于由我们的习俗、信念、价值理念所构成的鲜活的关系之中,实践哲学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关系之反思”〔24〕。这种反思虽然以特殊化的生活关系为对象,也尤其强调这种特殊性前理解结构性质,但这不代表诠释学排斥用知识去规定道德这一普遍化诉求。
按照康德主义伦理学,道德行为在道德规范的规导下实现出来,规范因为其自身所包含的实质内容而无法提前构筑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所以为了保证道德的普遍性和强制力康德通过理性自我设定方式揭示出绝对命令这一检验原则。绝对命令不是具体道德规范,它不包含任何具体内容,毋宁说只是从方法和程序上证明了道德的不可避免性。然而,原则的至高性虽然保证了道德的普遍性特征,但却与道德行为之落实产生矛盾。道德知识总是要面对不同的道德情境,因此道德规范之应用也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特征。风俗习惯在不断演变,价值观念在不断更迭,对某种道德行为善恶与否的评价亦随着理解者所处的时代条件而被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理解。很明显,面对这一生活事实,诠释学意识下的道德知识普遍性已经排除了理论知识意义上的道德真理观,更不是如哈贝马斯所论证的那样认为道德知识具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真理观那样的有效性而使自身获得可证立基础。道德知识之普遍性只能是基于语境之规范选择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关注的不是道德知识的超语境化的可证立性特征,而是在相同语境下的相同道德行为的普遍性,也即行为方式的普遍性。伽达默尔认为,“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总是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31〕所以,诠释学意识下的道德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导向的、具有知识可重复特性的普遍性。该普遍性不在于传统意义上我们归之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基础,“实践知识从其本性上来说与行动相关。这一事实提供了一种非对称性的解释,当且仅当它在一种特殊方式下被理解。因为它与行动有关,社会世界中的受历史影响的事情应该如何的知识,与客观世界的事情事实上如何的知识是不同的。”〔32〕总之,诠释学意识下的道德知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识和普遍性特征的德行知识。它关注的只是在诸多给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道德情境中的一般道德选择及由此而来的可普遍化的道德行动方式。这种知识关键在于它区别于动物基于纯粹自然本能而表现出的行为普遍性,而以人的自由选择作为其普遍性根基。
四、结 论
通过诠释学应用意识之回归,道德普遍性例外之证立与应用对峙关系得到解答,也为之做出了说明。应用意识实际上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智慧,也即在这里不再存在近代关于理论与实践二元分裂的道德陷阱,也不存在是与应当的对立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对话伦理学并不因此否定道德的知识性特征,从而未将自己引入道德相对主义。通过将道德认知上的普遍性转换为行为方式的普遍性,从一种弱的意义上保障了道德的行为定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对哲学伦理学之可能性论述中,伽达默尔的伦理学理论更偏向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但我们的立场与此不同,而是站在康德规范伦理学角度解决对话伦理学所招致的与对康德同样的批评。伽达默尔诠释学并未否认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之价值,而是试图勾连两者共同构筑符合现代道德理解的伦理学说明。就康德伦理学来说,其价值有二:其一,保护道德决断的纯洁性。它告诉我们道德乃是与禀赋对立而彰显自己的理性形式;其二,在此基础上内化为一种内在强制力。概言之,康德绝对命令的价值在于彰显道德之崇高和严肃。而诠释学应用则在被康德用来检视道德是否纯洁的冲突中发现道德的本真存在。回到我们曾经提到的“不应该撒谎(N1)”例子。如果N1只是在不存在规范冲突语境中不被遵守,那按照诠释学应用意识道德是在行动中显现自身,未表现出受N1规导的道德行为方式,其根本无所谓知识;如果N1是在规范冲突语境中,比如存在跟“不应该戕害生命(N2)”之冲突,就需要因应语境决定遵循何种规范而行,同时在同样情形下表现出同样行为方式来获得可传授之道德知识的普遍性。所以,经由向诠释学应用意识回归的对话伦理学之规范结构应该是“N1,除非存在N2。”这里,“除非”后面所跟从的事实就是应用包含的语境限制,也是受N1指导的普遍行为方式是否显现的制约语境,反之亦然。关键是,我们是在理解本论上看待其应用指向,而不是作为随之而来的规范使用看待。用颇具诠释学意味的话说,道德真理和道德语境相互规定而显现出普遍性并在此过程中创生道德知识。
〔1〕笔者这里指的对话伦理学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不特指某个哲学家的伦理学思想,虽然不同哲学家对该理论取向的伦理学在具体名称之使用上有所区别,但是围绕着语言的主体间性特征以为伦理学奠定“你—我”结构是其共同诉求。照此理解,对话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形态,在当代至少包括了伽达默尔、阿佩尔、哈贝马斯、君特、韦尔默等人的伦理思想。
(2) 哈贝马斯同样意识到规范应用所显示出的道德普遍性例外之合理性,也赞同君特用应用概念指涉这一问题以及藉此对自己伦理学思想的批评。如有学者指出的,“形式的道德原则必须能够有历史—社会的落实……哈贝马斯发现他的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基础,会有在历史的真实语境中不具有被普遍遵循的可应用性问题。”〔5〕哈贝马斯为此专门写了《证立与应用》一书作为对君特理论的回应和接续。众所周知,哈贝马斯在伦理学上最为其带来盛名的是他承继康德传统,用基于语言的主体间性之“你—我”对话结构代替“我”的独白式言说为道德原则奠定根基,从而将绝对命令改造为普遍化原则(U原则)〔6〕,正是这一原则的证立性质在君特的应用性商谈之讨论中变得可疑。哈贝马斯承认自己的U原则与康德绝对命令一样忽略了道德规范的应用向度,加入这一思考向度的道德规范应该在证立知识上的普遍有效性与应用语境中的具体有效性之间做出区分。道德有效性这里被分成两个维度:“一个是有效的规范所获得的所有潜在的受影响者的理性推动的一致意见,一个是对能在所有可能情况中应用的规范秩序的一致意见。”〔7〕前者追问的是“我应该做什么”,后者追问的则是“在特定语境下什么是正确的行为方式”。依据哈贝马斯,这两个问题并非如君特所言是截然分立的,相反前者乃是后者的基础。因为按照君特适当性原则考量,其必然需要在证立意义上综合各种具有家族相似特征的典型情境,而这一点应用性商谈并不足以胜任。另一方面,相似性情境是社会历史性呈现的,其内部事实不断更新变化,在此意义上适当性原则发挥与普遍化原则相似的检验和甄别任务并背负论证负担,即“在应用性商谈里,适当性原则承担了证立性商谈中普遍化原则的功能”〔8〕。故此,哈贝马斯虽然承认君特的重要发现,但是他在哈贝马斯那里,证立是应用的基础,应用是伴随证立而来的另一个层面。
奇巧生点了点头:“我也早有耳闻,它们个个身手不凡。光是这四个怪物就够吓人了,还不知道其余几个是什么?想想都有点害怕。 ”
〔2〕哈贝马斯明确说过:“应用性商谈受诠释学洞见的影响,在这里,适当的规范在语境的突出特征下获得了具体意义,同时,语境反过来也根据存在于规范中的特殊条件而被表述。”(Habermas,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trans.,Ciaran Croni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4,pp.37-38.)君特亦在其著作中以“应用理解:诠释学”为题专门辟出章节讨论诠释学意识对于道德规范之应用的启发意义。(Klaus Günther, The Sense of Appropriateness: Application Discourse in Morality and Law,trans.,John Farrell,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p.190-202.)
〔3〕〔4〕Klaus Günther, The Sense of Appropriateness: Application Discourse in Morality and Law,trans.,John Farrell,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p.11,239.
〔5〕林远泽:《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做为社会病理学诊断的批判理论》,《哲学与文化》2016年第4期。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先后发表一系列关于青年及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其内涵丰富、逻辑鲜明的青年观,指明了广大青年成长成才的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提出了高校做好新时代青年教育工作的遵循原则与行动指南。
〔6〕哈贝马斯对U原则的表述是:“规范的所有关涉方,都能够接受为了满足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普遍遵守该规范所产生的结果和副作用,并且他们更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而不是其它规则选择的可能性。”(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5,p.120.)U原则归属于道德规范证立范畴,它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脱离一切语境的认知意义上的道德普遍性问题。
〔7〕〔8〕〔32〕Habermas,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trans.,Ciaran Croni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4,pp.36,37,38.
〔9〕〔10〕〔11〕〔12〕〔14〕〔19〕〔23〕〔25〕〔26〕〔27〕〔29〕〔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4、399、400、416、417、420、419、405、14、410、405页。
〔13〕〔15〕〔17〕〔28〕〔30〕Gadamer,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trans.,Joel Weinsheimer,Yale University,1999,pp.21,18,25,29,19.
(4)显著降低土壤有DTPA提取态镉和磷酸盐提取态砷含量,零价铁和腐殖质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抑制镉进入水稻具有协同作用。
〔16〕〔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页。
〔18〕〔31〕〔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99、81页。
〔20〕Wellmer,“Ethics and Dialogue: Elements of Moral Judgement in Kant and Discourse”,in Albrecht Wellmer, 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stmodernism,trans.,David Midgley,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1,pp.113-231,205.
〔21〕〔丹麦〕P·肯普:《解释学和伦理学的冲突》,林雨译,《哲学译丛》1987年第2期。
除此之外,还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元素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因为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是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提升的过程的,也就是说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社会经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偏好,实际上是与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息息相关的,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趣,因此现代服装设计的过程当中,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营养,实际上也是在借鉴传统文化元素当中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是为现代服装设计成果本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
〔22〕〔德〕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4页。
〔24〕潘德荣:《“德行”与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傅永军,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陈太明,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8RWZD01)及山东大学青年团队项目(IFYT1802)的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5.006
〔责任编辑:汪家耀〕
标签:道德论文; 普遍性论文; 知识论文; 康德论文; 伦理学论文; 《学术界》2019年第5期论文;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8RWZD01) 山东大学青年团队项目(IFYT1802)论文;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