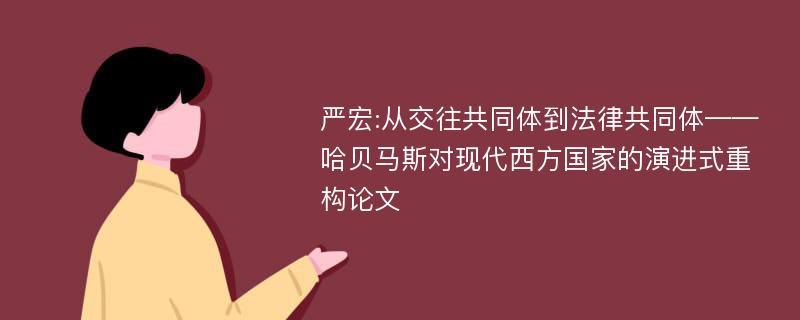
摘要:作为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国家的重构,是建立在其对西方现存国家批判基础之上的。这种批判也经历了从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嬗变。哈贝马斯认为法律是挽救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将生活世界从系统的殖民中解放出来的媒介。这种法律不是现存国家的实证法,而是建立在哈贝马斯重构的法律共同体基础上的法律。虽然法律共同体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最佳的重构方案,但哈贝马斯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从交往共同体到法律共同体的过程。这种法律,是以交往为形式,以商谈为原则,通过对现代西方国家中实用、伦理、道德问题的论辩而产生的。在这一系列商谈过程中,现代西方国家也成为自由而平等公民联合起来的法律共同体。虽然哈贝马斯是基于现代西方国家来构建其法律共同体的,但对当下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 生活世界殖民化; 交往共同体; 商谈; 法律共同体
“法律共同体”概念是哈贝马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并成为其晚期思想中法哲学理论中重要的概念。作为一名对战后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法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前期哲学思想(如交往理论)之上的。但是不同于一般的正统哲学家,哈贝马斯非常关注现代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种种危机。同时,哈贝马斯虽然关注现实问题,但其运用的方法迥异于实证主义的经验分析方法,而是批判-重构方法。当然无论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提出自己的重构方案,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虽然哈贝马斯是基于现代西方国家来构建其法律共同体的,但对当下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从危机到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国家病症的诊断
哈贝马斯的法律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建立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病症诊断的基础之上,正如学者指出,“哈贝马斯的哲学理论绝不是静态的,它是不断演化的”[1]269,他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也是如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用危机理论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病症,并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概念来演绎他的危机理论,一方面把社会系统视为“是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把社会系统理解成“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2]6。在这里,哈贝马斯把系统与生活世界都视作是社会系统,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范式,生活世界是从社会系统内部来理解的,系统是从社会系统外部观察的,他也提到,“面对外部自然,社会系统用(遵循技术规则的)工具行为来捍卫自身,面对内在自然,则用(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来捍卫自身”[2]12。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也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危机呈现出一种演化轨迹。在前一个阶段,危机主要是系统危机,“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2]28。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各类市场的组织化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危机也从单一的系统危机升级为复合的系统危机(经济危机与合理性危机)和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与动机危机)[2]58。安东尼·吉登斯将这两种危机称为客观危机和主观危机[3]。客观危机是指实际发生的危机,即经济危机以及输出危机,国家干预市场的局限性而出现的危机,危及的是系统整合。主观危机主要是政治系统无法“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2]53。在阶级分化的前提下,工人阶级对使用价值的需求与资本家实现对资本的需求产生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使国家行政权力难以控制,资本主义关于“普遍利益”的价值观也被证伪了,于是公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认同危机,即合法性和动机危机,危及的是社会整合。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有“明显瑕疵”[4],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危机理论以及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分法为后来进一步诊断晚期资本主义病症打下了基础。
南北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正如我在高铁上曾遇到的一位来自苏州的老总所说,“有时候南方人过于精明,事情只要与己无关则可以不管不问,于是就‘藏’起内心的那份本有的善良。”当然我相信这位兄台指的是部分南方人。
到了八十年代,在阐述自己“交往行动理论”时,哈贝马斯不仅继续坚持“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分法,而且放在更久远的历史长焦镜下来叙述二者的分化,阐发人类社会的进化。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社会、文化与人格构成的一般性结构。他认为,在部落社会生活世界与系统是同一的,交织在一起[5]155。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生活世界与系统逐渐分化。哈贝马斯把社会进化理解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分化过程以及系统复杂化、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这种分化不是在系统基础上产生生活世界,而是相反,从“生活世界中社会这一成分分化开来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6]48。 但是在整个现代西方社会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生活世界中主体间交往面临巨大压力,使得用“非语言的权力和金钱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5]150。这样人们的交往行动逐渐脱离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取向的生活世界,转向以货币与权力为媒介的系统(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本来“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脱离,是欧洲封建主义等级制社会向现代阶级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以生活世界符号结构的扭曲和物化为标志的,生活世界受制于从金钱和权力中派生的,并变得自主的亚系统的命令”[5]282。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造成了文化的贫困以及本来作为目的——人——的工具化。
那么如何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既要实现人的解放(自主性),也要实现社会团结(整合),维持社会秩序?首先肯定的是社会进化不可逆转,即系统存在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世界与系统合一的时代,那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最好的药方是法律。这主要是因为“法律代码不仅仅同生活世界的旨在社会性整合的理解功能借以实现的日常语言媒介相联系;它还赋予来自生活世界的信息以一种能为权力导控之行政和货币导控之经济的专业代码所理解的形式。就此而言,法律语言,不同于局限于生活世界领域的道德交往,可以起全社会范围内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交往循环之转换器的作用。”[6]98
二、交往共同体的奠基与法律共同体的出场:哈贝马斯的探索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更多的指向的是动态的“法”,即“立法”和“司法”,也就是他所说的法的论证性商谈和运用性商谈。只有在这样的商谈过程中,才既能实现公民的政治自主,又能实现社会团结,形成法律共同体。虽然法律共同体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最佳的重构方案,但哈贝马斯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从交往共同体到法律共同体的过程,“法律共同体”是哈贝马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实与规范》一书中提出的,但是之前的相近提法——交往共同体——与法律共同体密切相关,可以说,哈贝马斯的重构是演进式,即从交往共同体演进到法律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是在交往共同体基础上提出来的,后者为前者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将上述色谱分离制得的色谱峰溶液减压浓缩至干后,配成 4.00 mg/mL 的药液。 参照文献方法[9],按倍比稀释法,用肉汤液体培养基将药液分别稀释为 10 个浓度:1∶2,1∶4,1∶8,1∶16,1∶32,1∶64,1∶128,1∶256,1∶512,1∶102 4。试验用试管分别加入液体培养基 100 μL,试验菌液 20 μL,药液 120 μL,混匀后,置于37℃培养24 h。肉眼观察每支试管的澄清度。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肾组织中p38MAPK、TWEAK mRNA的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的上述指标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环孢素高剂量组小鼠p38MAPK、TWEAK mRNA的表达水平,环孢素低剂量组小鼠TWEAK mRNA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环孢素能抑制SLE模型小鼠肾组织中p38MAPK、TWEAK mRNA的表达。各组小鼠肾组织中p38MAPK、TWEAK mRNA的表达水平柱形图见图2。
在立法过程中,也就是合理的政治意见与政治意志过程中,商谈如何发挥作用?在法律共同体的立法过程中,法律主体之间的争论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问题,一个是道德问题,一个是伦理问题,一个是与利益分歧有关的实用问题。为什么法律共同体会存在上述三类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法律并不是调节一般意义上的互动关系,它起的作用是法律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维持自身——的自我组织之媒介的作用”[6]186。由此他认为政治意志形成不仅与一般意义的道德相关,也与伦理和实用问题联系。他反对将法律商谈看成一个封闭的自组织循环,“法律商谈不能在一个现行规范的密封领域中自足地进行,而必须始终有可能吸纳来自其他来源的论据,尤其是在立法过程中所使用的、在法律规范之合法性主张中捆绑在一起的那些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理由”[6]282。三类问题的立法过程中,商谈原则均发挥作用。但是发挥作用的形式不同,与利益分歧的行动是谈判这种选择,商谈原则,即“确保一种无强制的同意,却只能间接地发生效力,也就是说通过在公平角度下调节谈判的程序来发生效力”[6]204。这里主要是通过道德商谈确保谈判程序的公平,“目的是要确保所有有关利益得到同等考虑,各方都被赋予同样权力,从而,论据之交换的目标,是以尽可能合理的方式来寻求实现自己的偏好”[6]216,也就是说,商谈原则确保了谈判程序得到参与者的同意,保证了公平,但是因为谈判是以成功为取向的策略性行为,“不同实力拥有者之间的程序公正的协议的问题,而不是商谈参与者”的“相互理解”[6]204。所以,同意的效力比较弱,缺乏语内行动的那种行动约束力。但是这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哈贝马斯也认为,现代社会交往自由对法律主体没有义务上的约束性。所以,从解决利益分歧视角来理解立法过程,法律主体只是“私”的角度出发,“公”的意义较弱,因此产生的法律具有强烈的事实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取决于以国家制裁为后盾的法律强制力。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主体重视私人利益的原因,哈贝马斯也给出了解释。但是哈贝马斯认为要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的制度与程序的安排,使得行政决策一直独立于公民的具体动机之外”,“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在一种客观的政治社会中享有的是消极公民的地位”,享有的是主观私人权利[2]41。哈贝马斯反对这种自由主义的消极权利观,他认为,“为反思的自我指涉的公民地位提供根据的,只有政治参与权利”[6]94,因此公民应该从私人主体状态中走出来,参与立法过程,“不能仅仅以取向于成功的法律主体”,“相反必须按照取向于理解的行动主体之间的理解过程的参与者的态度来行使”[6]39。因此,在伦理政治商谈中,主体间可以就共同面临的一种重要的生活问题,所共享的生活形式等进行论辩,并通过普遍化道德商谈,形成共识,经过法律商谈,形成法律。
哈贝马斯把“法律”“理解为现代的实定法,它要求作系统的论证,作有约束力的诠释和执行”[6]96。也就是说,法律既是以参与系统论证各方达成共识的结果,同时也要强制执行。既要有规范性,也要具备事实性。这样的法律能够实现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协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动,以理解为取向的,是交往理性实现的结果。在法律有效性的两个方面中,体现为“法律的合法性或规范有效性,即合理的可接受性”[6]36。在系统中,主体间是以权力或货币为媒介的策略行动,以成功为取向的,是工具理性实现的结果。在法律有效性方面体现的是“社会的或事实的有效性,即得到接受”[6]35-36。那么这样的法律是在什么组织中产生的?很显然,无论是生活世界还是系统中的国家本身还是对其进行改造,都无法产生法律。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贝马斯进行了概念重构,提出了“法律共同体”这一概念,这个“共同体”是“一种高度人为的共同体,更确切些说,是由平等而自由的法律同伴所结成的联合体,他们之结合的基础既是外部制裁的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合理推动的同意的支持”[6]10。
那么哈贝马斯是如何重构他的法律共同体的?他的重构离不开自己的探索,也是建立在前人思想基础之上的,具体说是以交往共同体思想为基础,批判的吸收了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共同体以及卢梭意义上的伦理-政治共同体中的合理成分。交往共同体虽然无法解决现代西方社会的病症,但是它对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前提性作用。这突出体现在法律共同体是交往共同体在时空中的具体化。哈贝马斯指出,“有道德责任能力的主体的理想共同体——从约西亚·罗伊斯到阿帕尔的无限制交往共同体——是通过法律媒介而进入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从而作为法律共同体而具有一种具体的、在空间和时间中有确定位置的形式的”[6]130。但交往共同体毕竟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其过于理想,在现代社会的范围也很小。法律共同体是以法律为媒介整合的社会,也就是整个现代社会,具体包括生活世界与系统。至于商谈与交往的关系,可以说商谈“的基础在于以交往方式构成的生活形式的那些对称的承认关系”[6]134,也就是商谈是以交往为基础的。
但是,哈贝马斯立足于人类学、历史学,认为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程度越高,最初限于种族中心的视野越宽,生活形式多样化和生活历程个体化的程度就越强,它使得生活世界的背景信念的重叠或汇聚的区域越来越小”[6]30。如上文所述,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为交往行动达成共识提供背景知识,但是如果交往主体间的背景知识重叠越来越小,那么规范秩序就失去了交往行动的元社会保障,“即使是生活世界的确定性——它不管怎么样是在发生着多元化、在越来越分化——也无法为这种缺失提供足够补偿”。同时,社会分化也带来“功能上分化的各种任务、社会角色和利益立场的多样性”[6]31,对交往行动产生两个影响,一是交往行动的选择空间更宽,二是在自身基础上产生并与以利益取向的行动的分离。这样,传统社会中对行为期待起稳定作用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混合,也出现了分离。那么到底哪种要素能够处理好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具有合理推动力的信念和外部制裁的强制这双重力量”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伦理和道德都不能很好地处理好上述两种关系。他认为,伦理是关于一个小共同体——“我们”—— 成员所分享和愿意接受的,“似乎我们不应期望伦理问题的答案能够在超过共享相关传统和价值的圈子之外赢得赞同”[11]140。伦理不具有可普遍性,并不适应已经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与伦理规则不同,在现代社会道德是可普遍化的,是“人类,或者所假定的世界共和国构成了对那些基于所有人同等的利益的规则”[11]121,但其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对主体的社会行为的那种约束能力和强制性,因此,无论是伦理还是道德都无法成为治疗现代西方社会病症的药方。那么法律一定就可以吗?哈贝马斯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可以,关键要看是什么法律以及如何产生?在哈贝马斯看来,有两种法律无法承担现代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协调。一是自然法,包括神学自然法与理性自然法,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合理化过程中,作为神学自然法的规范性来源的神灵基础遭到祛魅,神学自然法的效力也受到质疑;近代理性自然法提出不久,就遭到苏格兰学派亚当·弗格森等人的质疑,“他们反对理性法的规范主义,认为它的规范性论证把历史的特殊性和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撇在了一旁”[6]55。对于这一问题,康德进行了补救,强调了情境主义下实证法在社会中的重要功能,但是只不过是“理性法传统的一个形而上学遗产,那就是把实证法置于自然法或道德法之下”[6]106,康德“把法和道德的关系看做是模仿关系”[6]131。哈贝马斯认为,法律的等级化是前现代的特征,已不适应现代社会[6]130。二是实证法。哈贝马斯也认为实证法是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以权力为基础制定的,缺乏作为立法者间共识而形成有效性。如果说自然法规范性太强,而缺少事实性的话,那么实证法则是事实性太强,规范性不足,两者都不可取。
三、商谈原则与法律共同体形成:哈贝马斯的重构
高通量捕获测序提示CLCNKB基因c.1389delA纯合突变。Sanger测序验证父亲携带该位点杂合突变,而母亲未发现该位点突变(图1)。MLPA检测证实先证者与母亲均存在CLCNKB基因1-18号外显子杂合缺失(图2),先证者父亲无片段缺失。明确先证者致病突变及父母来源后分别采用Sanger测序与MLPA检测羊水胎儿DNA,发现胎儿基因型与先证者一致。
因此可见,商谈是法律共同体形成的机制。在哈贝马斯构建的商谈体系中,道德商谈被放在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受程序调控的谈判还是伦理-政治商谈在走向法律商谈之前,都必须经过道德商谈。为什么道德商谈能够成为一种中介,道德商谈起到什么作用?道德能进行商谈吗?在这里哈贝马斯既不完全同意道德认知主义的观点,将道德与科学中的真理等同,也不同意道德相对主义。正如上所述,他认为,在后传统社会,道德是知识系统,是可以进行论证的。通过建制化的道德商谈,主体间可以就道德问题进行论辩,达成共识。那么道德商谈何以达成共识?在这里哈贝马斯遵循的是义务论意义上的道德观。这种道德实际就是道德命令,并认为“正义是表示那表达道德命令的全称规范性句子之有效性的一个谓词”,与“价值要求承认的是相对的有效性,而正义则提出一个绝对的有效性主张:道德命令所主张的,是适用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有效性”[6]187-188。这种义务论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或者道德规范,是现实社会中不同形式商谈达成共识的前提,也只有道德商谈为前提的法律商谈,产生的法律代码才能成为生活世界与系统循环的传感器。这样的法律既具有事实有效性,也具有规范有效性,并成为整个现代西方社会整合的媒介。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都会出现上述三种共同体中的三个问题,即道德的(道德共同体)、伦理-政治的(伦理政治共同体)和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利益联合体)。因此,无论单靠哪一个媒介都无法实现对现代复杂社会的整合。如上所述,哈贝马斯认为法律是实现现代复杂社会整合的唯一媒介。那么这样的法律与法律共同体如何产生?法律与法律共同体是同生同源的,法律是共同体的构成性语言。而商谈是法律及其共同体产生的机制,或者说,哈贝马斯把商谈原则视为法律共同体构成的基本原则,那商谈原则何以成为法律共同体的基本原则?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商谈产生的法律既具有事实有效性,也具有规范有效性或合法性。商谈何以有如此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商谈原则“对于道德和法仍然是中立的,它涉及的是所有行动规范”即“有效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6]132。但是商谈原则比较抽象,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具体化。内在的原则是道德原则,主要对不同利益作同等考虑的行动规范进行论辩;外在的原则是民主原则,其确定的是“合法的立法过程的程序是什么”即“具有合法的有效性的只是这样一些法律规则,它们在各自的以法律形式构成的商谈性立法过程中是能够得到所有法律同伴的同意的”[6]135。而商谈性立法过程需要建制化,即“通过一个权利体系,这些权利确保所有人平等地参与一个其交往预设业已得到保障的立法过程”[6]135,因此,哈贝马斯说,“商谈原则首先应该借助于法律形式的建制化而获得民主原则的内容,而民主原则则进一步赋予立法过程以形成合法性的力量。关键的想法是:民主原则是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这种相互交叠,我把它理解为权利的逻辑起源”[6]148。哈贝马斯反对权利天赋、权利国赋,主张权利互赋。那么法律共同体中同伴间为什么愿意互赋权利?哈贝马斯认为权利涉及是彼此合作的法律主体的相互承认,是一种形式的社会合作。“作为法律秩序的成分,主观权利毋宁说预设了这样一些主体之间的协作,这些主体通过互相关涉的权利和义务彼此承认为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同伴。”[6]111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观受康德的人的自由并存和人是目的论断的影响,每个人都是目的,不能成为他人实现自己的手段,因此在社会世界中人与人要发生联系,彼此之间需要相互承认和合作。不过哈贝马斯对康德的思想进行了转换,即从自然人转换为法权人或者公民。这样康德的普遍主义预设受到情境主义的挑战,即在具体的法律共同体,公民间承认是怎么发生的?这一问题在哈贝马斯的学生霍耐特那里得到系统论证[12]。
作为一个善于运用和借鉴其他学者思想的哲学家,“交往共同体”提法也不是哈贝马斯最早提出的。这一提法来自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哈贝马斯很早就了解了皮尔斯的交往理论,并写过《皮尔斯与交往》一文。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对皮尔斯理论的评价也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认识与兴趣》一书中对皮尔斯的评价不高,到八十年代的肯定与否定并存,再到九十年代的高度评价[7]40-41。笔者认为哈贝马斯对皮尔斯的评价较高,很大程度上是肯定其思想中的两大理论。一是共识真论。“皮尔斯把‘真’解释为合理的可接受性,也就是说解释为对具有可批判性的有效性主张的确认,而这种有效性主张的提出,则需要一种特定的听众群体作为交往条件——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中理想地扩展的有判断能力的听众群体。”[6]19二是交往共同体。哈贝马斯认为,皮尔斯把交往看成语言成就的核心,并用说者、听众以及表述的世界三极概念取代说者与表象世界的两极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皮尔斯的交往共同体有两个特点,首先是理想的或无限交往共同体。“在皮尔斯看来,在时间之中,无限交往共同体的学习过程应该建立起架通所有时空距离的桥梁”[6]19-20。其次是科学家的交往共同体。哈贝马斯指出:“当他提出上述模式时,他想到的可能是一个学者共和国的论辩实践”[6]20。当然,共识真理论与交往共同体理论也是密切联系的。在交往共同体中,学者对可批判主张(可错性知识)进行辩论,最终形成所有人接受的共识,即科学上的真理。
那么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利体系包括哪几个组成部分,从而保障论证性商谈的立法过程?哈贝马斯列出五种基本权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作为法律承受者——法律主体——应该享有的主观私人权利,主要是个人的平等自由权、成员资格权以及受法律保护权;第二类是作为法律创制者——公民——享有的主观公共权利,主要是政治参与权;第三类是无论是法律创制者还是承受者都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权。当然,这些基本权利与商谈过程也是互构的。
哈贝马斯拓展皮尔斯的共识真理观,改造了交往共同体理论。这种拓展表现在皮尔斯的真理主要指的是科学真理,是外在与人的客观世界,而哈贝马斯认为不仅对客观世界能够形成真理认识,对于人与人互动的社会世界,也是认知对象,也能够形成真理。但两种真理的判断标准不同,科学真理主要是真实性,社会真理则是正确性。同时,这种改造体现在,他认为交往共同体不仅仅只有理想类型一种,还有一种现实类型。理想交往共同体关注的是交往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他的普遍语用学就是“人们为了能够进行交往而需要的技巧和能力的理论”[8]188,他提出了言语行动中言者与听者达成理解,形成共识的四个要件。但这毕竟是不带有任何语境的理想意义上的逻辑前提。要想弱化其理想性,必须面向现实。作为一个现实共同体,不仅要重视达成共识的内在构成条件,也不能忽略外在的必要条件,即主体间的共同背景知识。在这里,哈贝马斯引入并改造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提法,并将之作为交往主体形成共识的背景知识。他认为,“适用于一个学者的交往共同体之内的理解的,经过适当修正以后,也适合于日常的交往”。将“有效性谱系置于生活世界之中,使得有必要将皮尔斯的无界限交往共同体的概念加以普遍化,超越科学家对真理的合作寻求”[6]20-21。因此,哈贝马斯将交往共同体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也为交往共同体的维持提供了养分。这表现在交往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前提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在一个主体间共享的生活世界”[6]18,“如果交往行动不根植于提供大规模背景共识之支持的生活世界的语境之中,这样的风险就会使基于交往行动之社会整合变得完全没有可能”[6]26。那么生活世界何以能成为交往行动的共识背景?哈贝马斯认为,这是由生活世界的特征决定的。在交往共同体中,生活世界不是主题知识,而是背景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因为它永远也不会受到偶然经验问题压力的影响”,也“不是供我们随意驱使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置于抽象的怀疑之下”[9]77-78。背景知识不能成为交往主体讨论的主题知识,“一旦成为讨论的主题,一旦卷入了成问题之可能性的漩涡之中,它就分崩离析了”[6]28,主体间的异议的风险增大,取得共识的难度也加大。但生活世界只是为交往共同体提供了背景,主体间的交往还需要一个媒介。哈贝马斯认为,这个媒介就是语言。“人们必须说同样的语言,处身于一个由语言共同体所确立并且具有主体间性结构的生活世界当中,以便真正从对自然语言的反思当中获得好处,并把对言语行为的描述建立在理解这种言语行为内在自我解释的基础上。”[9]55在这里,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语言是自然语言,因为交往是日常生活式。同时他是在语用学意义上使用语言的,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言语行为。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言语行为都是交往行动。哈贝马斯认为并不是这样的,这需要“根据行为的协调机制来加以区别的,而关键的区别标准在于:自然语言是否只是传达信息的一种媒介,或者同时还是社会整合的源泉”[9]59。自然语言能否成为社会整合的源泉,主要是在于“言语行动的语内行动力量承担协调行动的作用”[6]22,那么言语活动为什么能够发挥协调行动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主要是来自于“语言自身的约束力”,也就是说话者与听话者通过言语活动,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将以这种共识指导自己的行动。当然这种言语活动对主体的交往能力或资质提出较高的要求,哈贝马斯认为需要三种能力,一是选择陈述性语句的能力,其功能是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识。二是表达言说者本人的意向的能力,是为使听者能否相信言说者。三是实施言语行为能力,使听者能够在共同具备的价值取向中认同言说者[10]29-30。后来他又认为,交往主体也具有责任能力,“因而预设他们是能够使其行动以有效性主张为取向的”[6]24。
在哈贝马斯看来,不论是利益联合体、道德共同体还是卢梭的伦理-政治共同体都是不切实际的,不适应现代复杂社会。在利益联合体,利益主体只考虑自身利益得失,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其行动也以利益为导向。只不过在霍布斯预设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中,为了自我保存这个根本出发点,他们放弃自然权利,签订契约,建立外在于自身的工具性秩序。哈贝马斯认为,“霍布斯认定自然状态中各方所具有的态度,与私法认定其承受者所具有的态度是一样的,那就是以成功为取向”[6]114。也就是说,法律在利益联合体中只具有事实有效性。在霍布斯这里,建立联合体无非就是实现自身的利益,仅仅是因为明智的理由,而不是因为什么道德,所以康德说这些人是“魔鬼种族”。与霍布斯相反,康德的道德共同体的建立贯彻的是道德原则。共同体中的个人是道德人,其基础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签订社会契约是出于道德理由。作为共同体基础的自主性是道德自主,进行私人的道德判断,行动也是道德的。但是这一构想对现代社会成员的要求极高,哈贝马斯认为,“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的人们”“处于前所未有的(a)认知的,(b)动机的,以及(c)组织的要求的压力之下”[6]140。同时,就后习俗社会而言,道德判断本身也失去了对人的行动的直接影响力。这是因为哈贝马斯所界定的道德是现代社会的道德,用他的话确切地说是“后传统道德”,这是受到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的影响。科尔伯格针对儿童道德发展提出“三阶段六水平”,哈贝马斯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社会学转译,认为现代社会的后传统道德,在失去传统的习俗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规范基础后,其自身也成为反思与论证的对象。后传统道德失去了传统意义上道德对行动的约束功能,仅仅表达一种文化知识[6]131。而卢梭式的伦理-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共同体的福利超越所有公民之上。但这种共同体只适合简单的同质社会,因为它无法解释处于现代复杂的、异质性较强的社会,“公民对共同福利的取向,怎么能够与社会中不同私人的彼此分化的利益相协调”[6]126。
四、对当下中国的意义
哈贝马斯对法律共同体的重构虽然是对现代西方国家为样本的,但是不代表不对当今中国有启示意义。在当下强调重视中国学术话语的同时,也不代表不去了解、关注现代西方国家思想家的思想,特别是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13]关键是如何在基于西方国家产生的理论中提取出对当代中国的有益养分。从这一点来说,哈贝马斯的法律共同体思想对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资源的道德与法律。道德与法律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有其自己的位置,德治与法治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两种基本形式,国家治理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原则,因为道德与法律在功能上具有互补关系,从内外两个方面规范治理主体行为、调节治理主体间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这只是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它们有没有内在构成性关系?即法律与道德的相互渗透,一方面是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在韦伯看来就是形式法的实质化[6]556,这是在西方福利国家背景下产生,这种硬法软化会带来价值司法的问题。道德的法律化是软道德的硬化。因为正如上所述,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后习俗社会,道德认知和道德动机失去对行为的指引和约束功能,成为一个知识符号系统,而法律还是一个行动系统。但是不同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主张的那样道德与法律的彻底分离,道德可以进入法律,问题是如何进入?哈贝马斯认为要经过道德商谈。这种商谈通过使道德通过两个通道实现法律化。一个是立法的道德程序。这里的道德指的是对所有人的利益作同等考量,等同于正义,也就是说,商谈程序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而平等进行论辩。另一个是法律的道德内容。但是道德成为法律,不是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更高意义上原则的法律。法律原则“同时既具有法律性质,也具有道德性质。自然法的道德原则在现代立宪国家中已经成为实证法。”[6]556当然,道德成为法律原则也要经过商谈,并形成共识。哈贝马斯对道德与法律内外关系的阐述,给处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提供了更全面的方案,二者不仅仅是静态、外在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内在构成性关系。特别是道德通过正义程序和内容进入法律,对当代中国的立法过程及结果有一定的启发。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法”是“良法”,最终能够实现“善治”。
第二,提升公民的协商能力与意识。哈贝马斯法律共同体中公民是积极公民,是一种义务论意义上的公民,有着强烈的协商意识,将参与商谈或协商视为自己的义务,应当所做之事,同时这样的公民也具有较强的协商能力。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与参与能力得到较大提高。但是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公民协商意识不足,遇事没有形成协商习惯和思维;一些公民协商动力不足,涉及个人切身利益就积极协商,与个人利益相关较弱的公共事务,往往不愿意协商,公民在协商中表现出“理性经济人”色彩,是功利论意义上的公民;还有一些公民素质不高,协商能力不强,虽愿意协商,但不知如何协商。哈贝马斯的法律共同体中的公民是完美或理想型的公民,对提高我国公民的协商能力与意识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第三,提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商谈是法律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谈是反思性交往行动形式[6]683。他的交往行动是以理性言语情境为基础的,即交往主体在论辩言语行为中可以免于外来的压迫和不平等。在交往或商谈中,主体的更好的理由才具有真正的力量。他还援用阿历克西的观点,认为在商谈中,每个主体允许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疑问、表明他的态度、愿望和需求,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内外或外在的胁迫阻止他的表达[14]89。但是在现实的商谈或协商中,受到各种外部力量干扰的情况不可避免,即便是当下中国也是如此,关键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把这种干扰降低到最小。笔者认为,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外部就是建立一种防护机制,保护整个协商过程免受来自外部的干扰,内部就是建立一种规范机制,主要是规范协商主体的职责、协商议题设置、协商活动开展方式等等,涉及的是程序性制度和实体性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质量,也才能凸显人民民主的真谛,真正实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15]30的良好愿望。
钻井液方面标准化建设工作走上了稳步发展之路,近几年来,一大批钻井液方面的行业标准制订并颁布执行,对钻井工程专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宣传、贯彻、执行标准,规范了钻井液技术行为,推动了我国钻井液处理剂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钻井整体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
[3]Giddens A . “Habermas’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1):198-212.
[4]约瑟夫·希斯:《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 》,张太星译,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5]Habermas J.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Beacon Press, 1987.
[6]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7]童世骏:《批判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8]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朱松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尤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10]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1]芭芭拉·福尔特纳:《哈贝马斯:关键概念》,赵超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2]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第1版。
[14]Habermas J.MoralConsciousnessandCommunicativeAction, 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enhardt, Shierry Weber Nicholsen,The MIT Press,1990.
[1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FromCommunicativeCommunitytoLegalCommunity:Habermas’sEvolutionaryReconstructionofModernWesternCountries
YAN Hong,
AnhuiNormalUniversity
Abstract: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Western society, Habermas has reconstructed the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based on his criticism. This criticism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risis of late capitalism to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 Habermas believes that law is the medium to save the modern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liberate the life world from systematic colonization. This law is not a positive law of the existing country, but a law based on the legal community reconstructed by Habermas. Although the legal community is the best reconstruction plan for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Habermas’s exploration is not an overnight process, but it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a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to a legal community. This kind of law based on communication and is produced through practical, ethical, moral, and legal discourses. In this series of discourses,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have also become a legal community united by free and equal citizens. Although Habermas’s legal community is built based on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it still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day.
Keywords:Habermas;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discourse; legal community
作者简介:严宏,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研究”(14AZD135)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1-10
DOI: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3.08
中图分类号:B516.5; 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9)03-0056-07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马斯论文; 共同体论文; 法律论文; 道德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概况论文;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总论)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研究”(14AZD13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