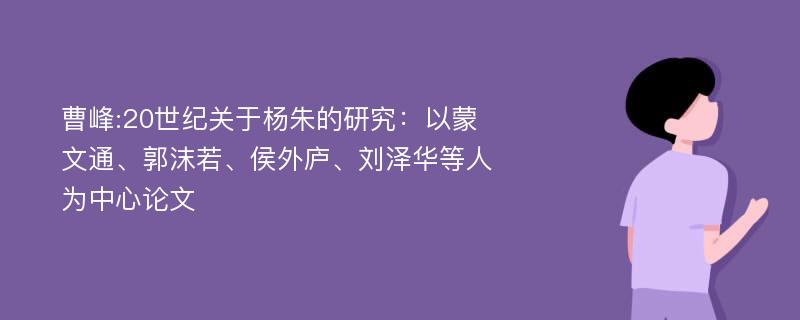
摘 要:20世纪对于杨朱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第一,杨朱学派传承关系的研究,以蒙文通、郭沫若为代表,把詹何、子华子、魏牟、陈仲、彭蒙、田骈、慎到以及宋钘、尹文等人列入杨朱学派,并将其与黄老道家关联起来;第二,对于杨朱思想性质的研究,1949年之后,以侯外庐、刘泽华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把杨朱理论核心定性为强烈的个体意识,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评价和1949年以前胡适等人的评价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与当时儒家思想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理念及其方法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杨朱;蒙文通;郭沫若;胡适;侯外庐;刘泽华
杨朱在《孟子》中,既被评价为思想界的半壁江山,又被描述成不愿牺牲任何个人利益的“一毛不拔”的小人;在《庄子》《韩非子》中,杨朱成了“辩者”“察者”的代表;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那里,杨朱被明确塑造为注重养生的道家人物,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他是道家修养论、工夫论的代表,重视通过养生来体验、实践道家理论;最后到了《列子》的《杨朱》篇,杨朱则成为一个高调纵欲、不合礼法、离经叛道的人物。由于魏晋之后中国社会由儒家主导,因此作为孟子笔下反面人物出现的杨朱,一直备受冷落,在大多数情况下得不到正面的评价和系统的研究。
然而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发生很大的变化。随着儒家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受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理念及其方法的影响,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开始得到比较平等的、客观的考察。20世纪的杨朱研究,在两个方面得到充分展开:一方面是从学术史角度对杨朱展开的梳理,虽然杨朱没有著作存世,但由于杨朱在早期道家思想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杨朱形象在魏晋思想史上也具有巨大影响,因此杨朱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在各种哲学史、思想史尤其道家思想史都有一席之地,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他的影响下是否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派,以蒙文通、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为此做过不少文献整理工作,并梳理出比较明确的线索;另一方面是从思想史角度对杨朱做出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杨朱因为被儒家贴上“为己”的标签或被视为“纵欲”的代表而遭到挞伐,然而到了20世纪,恰恰是这一很少有人具备的惊世骇俗的特征,使杨朱受到今人极大的关注,从梁启超、胡适等人开始,杨朱开始挂上“个人主义”“个体意识”“个人本位”等具有西方思想背景的新标签,对杨朱的评价出现了翻转,杨朱成为中国古代人性解放的标志、个人意识最早觉醒的代表。
本文并不寻求通过文献的再次梳理,从学术史上为杨朱做出新的定位,也不谋求通过哲学分析,从思想史上为杨朱做出新的评价,而是希望借助几位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来考察20世纪学术研究的历程和特征,这个考察集中在两方面:第一,以蒙文通、郭沫若等代表,看看他们如何将詹何、子华子、魏牟、陈仲、彭蒙、田骈、慎到以及宋钘、尹文等人划归于杨朱学派,从而构建出杨朱学派的传承谱系,并将这条谱系和黄老道家关联起来;第二,看看1949年后,以侯外庐、刘泽华为代表的大陆学者如何评价杨朱的“为己”学说,如何把杨朱理论的核心定性为强烈的个体意识,从而给予高度评价的。毋庸置疑,这两条线索都与20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都是20世纪学术史的产物。
在对20世纪杨朱学术史展开考察之前,仍有两个焦点问题,需要表明本文的观点与立场。首先,《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段话中的“利”究竟如何理解?很多学者出于为杨朱辩解,引证大量文献,从语言和思想上论证“利天下不为”应该读为“虽利之以天下而不肯为”。(1)如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原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四期,1932年6月,又见《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520页。笔者认为这种读法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甚至从《列子·杨朱》篇的角度看是正确的。(2)详参刘黛:《“取”“与”皆弃的杨朱生命哲学——从文本、哲学到思想史》,即将刊登于《文史哲》。刘黛认为从《列子·杨朱》看,杨朱根本没有进入“利己”还是“利他”的讨论,他的基本立场在于“利”和“身”之间的权衡,取不为物利而轻身的姿态。笔者表示赞同。但是如冯友兰所言:“与下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同文异解,似不甚妥。利之以天下而欲拔其一毛,杨朱不为;此乃杨朱之学说;拔其一毛可以利天下,而杨朱不为,乃孟子对于杨朱学说之解释;二者不必同。”(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文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9页。确实如冯友兰所言,在同一段话中,对同一个“利”字的性质做两种解释是说不过去的,孟子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修辞的人,与“一毛”相类似的比喻还有“一介”,如《孟子·万章上》有这样一段话:“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是孟子对于伊尹的夸赞之词,说伊尹对于“非其义”“非其道”的事情,即便给他“天下”和“马千驷”,他也视而不见。这里“一介不以与人”可以说就是“一毛不拔”;“一介不以取诸人”就是“一毛”也不想获取,极而言之,就是对“天下”和“马千驷”也不动心,这样就和顾颉刚说的“虽利之以天下而不肯为”相一致了。可见,孟子认为如果与自己的信念相违背,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都不会去做,因此,他完全可以理解杨朱的做法,但是出于对杨朱“为我”观念的痛恨,他却只选择了“一介不以与人”的方式来描述杨朱,显然这是一种偏见。总之,“利之以天下”与“利天下”(4)笔者以为,如果假设老子和杨朱之间存在前后关系,那么“利天下”可以理解为“为天下”,而老子是反对“为天下”的,如王弼本第二十九章云“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文子·道德》也有:“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杨朱正是以“利”的言说方式,重申了“为无为”的思想。两种解释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且各自在历史上发生了巨大影响。我们不仅有必要了解杨朱的本意,也有必要了解被孟子曲解之后产生的历史影响,这两者不必二选一,也不应该混为一谈。
还需一提,2016年给我签发邀请函,现已退休的研究所前所长妮娜·奥其多娃女士,4月23日晚在埃里斯塔酒店设宴款待我们,席间我们有幸认识了研究所已退休的专家,弗拉基米尔·桑奇罗夫(他是兹拉特金的学生),安德列·巴德玛耶夫(1939年出生)等。
第二个焦点是《列子·杨朱》篇是否伪作的问题。受20世纪疑古思潮的影响,20世纪学者基本上将这一篇看作是魏晋时期的伪作而不予采信。但近年来,更多的学者趋向于认为,其中既有传承杨朱本人思想的部分,也有后世的加工和演绎,因此可以作有选择的利用。例如,王威威认为,表面上看,《列子·杨朱》篇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与孟子所述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义相同,但实际含义是对生命的极端重视,而非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同时表面上看,《列子·杨朱》篇的“悉天下奉一身不取”接近《韩非子·显学》所谓“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但实际上,“也包含了《显学》中所没有的、不伤害个体生命而为天下谋利的观点”。所以,“更有可能是此段材料的作者为回应思想界类似孟子的批评而有意识地对杨朱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转化,文中以古人为思想依据,以个体生命解释‘一毛’,以‘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来回答禽滑釐的疑问,突出‘轻物重生’的一面,并以‘天下治’为思想依归,均在去除杨朱思想的自利色彩”(5)王威威:《为我、重生、贵己——先秦思想界对杨朱思想主旨的理解》,《人文杂志》2018年第3期。。笔者赞同王威威的分析,即《列子·杨朱》篇的形成有可能建立在《孟子》和《韩非子》基础上,是对《孟子》和《韩非子》的回应与涵摄。因此有可能形成时间较晚,但也并非全部都是魏晋时候的伪作。
一、蒙文通、郭沫若的学术史研究路径
所谓学术史研究路径,就是并非从观念、概念的角度出发,有目的地选择资料并加以研究,而是在充分收集文献、充分尊重文献的基础之上,对人物及其思想的原貌、背景、影响做出全面地、系统地整理、解读,然后寻绎出线索和脉络来。如前所述,这种理性的研究方式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兴起之后,学界开始对先秦诸子及其思想做出冷静地、全面的梳理,如《古史辨》第四册搜集了多篇关于杨朱的论文,其中有蔡元培的《杨朱即庄周说》、唐钺的《杨朱考》及《杨朱考补》和《杨朱考再补》、郑宾于的《杨朱传略》、高亨的《杨朱学派》、门启明的《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等。(6)参见《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9-609页。同样见于《古史辨》第四册的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也有探索杨朱的内容。因此关于杨朱的学术史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蔚为大观。(7)相关情况还可参刘佩德:《列子学史》(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之附录二《杨朱研究概况及其特点》。但他的总结有很多缺漏,例如对于本文讨论的这四位重要人物全都没有做出考察。在笔者看来,古史辨派的论文虽然汇集了资料、提出了问题,但只是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尚未产生大的影响。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真正对学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学者有两位:蒙文通和郭沫若。他们虽然对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有吸收,研究方法也比较接近,但后出转精,更具有代表性。这里,本文通过对他们学术工作和主要观点的介绍,希望对20世纪学术史研究路径的特征、意义做出回顾和总结。
这样,杨朱就和墨子一样,被抬升为中国古代思想中难得的具有唯物主义意识的思想家,因为它能实现科学上的人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非虚伪的人。他的“个人主义”恰恰和孟子之流虚伪的思想家拉开距离,孟子之流要靠“伦理上的神化”、要靠“假定天志和先王观”才能形成道德论,杨朱的道德论则不加伪饰、充分尊重自己的感觉。这种两军对垒的言说方式,显然背后有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交锋的意识在。(40)侯外庐认为,除了唯物主义意识之外,杨朱派进步意义还在于,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之外,在氏族宗法的人我关系之外,发现了个人的存在。
郭沫若认为宋尹学派的特征在于“救世”,而“田骈、慎到派”和“环渊、老聃派”,前者特征是“尚法”、后者特征是“独善其身”。但除了在时间上将杨朱置于三派之前,他没有进一步将后两派和杨朱做直接的思想关联。另外,郭沫若虽说这三派同起于稷下,但没有交代黄老学派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这样也就难以把握他心目中杨朱和黄老道家的关系。
蒙文通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杨氏之言不多见,后之流变亦不可考,未能如墨氏之显,则安见其言之盈天下?”他发现如果从杨朱“为我”之旨出发,则后来的传承就有迹可循了。他首先通过《吕氏春秋·执一》《庄子·让王》所见詹何“尊生”之义,指出詹何思想主旨合于《吕氏春秋·不二》的“杨生贵己”、《淮南子·汎论》描述杨朱时的“全性保真”,因而推断詹何为杨朱之徒。然后,他又通过《吕氏春秋·贵生》所见子华子“全生”之义,指出与杨朱之说不殊。《吕氏春秋·审为》一篇所述子华子鼓吹身体重于天下的故事,“显为杨朱之义”。蒙文通进而把吕不韦也拉到杨朱思想的延长线上,他引《吕氏春秋》的《尽数》《重己》等篇,指出尊生全性之说虽然与长生久视之术为邻,但“欲之者非有道,故吕氏犹讥之”。即如果以不道的方式追求长生,则不可取。《适音》一篇强调“生全寿长之方,在于胜理”。所以“詹何、杨朱、子华、吕氏之流,持论若一贯,其渊源亦有自也”。
蒙文通接着把话题转到杨朱是否重义的问题上,他先引《吕氏春秋·诬徒》,指出子华子其实既贵生也贵义,而《庄子·胠箧》把“曾、史、杨、墨”排列在一起,说他们都提倡仁义,因此“知杨朱亦为仁义与子华子同”。他再提及孟子与告子关于仁义之辩,《庄子·秋水》所载公孙龙“明仁义之行”的事迹,同时引用《庄子·骈拇》把杨、墨并列当作辩者加以批判的例子,推论说“盖仁义为三古以来之教,杨、墨、孟、荀、公孙龙、告子之徒皆归本于仁义,而义各不同”。从而证明杨朱并非不讲仁义,只不过他的仁义不被孟子认同,所以受到批判。总之,《吕氏春秋》的《适音》《本生》《重己》《贵生》都是杨朱、子华子之说,除倡导养生外,也有自己的仁义观念,这样就和排斥仁义的庄子形成对照。
那么杨朱理论中关于情性、欲望的观念是否有可能走向两个极端呢?蒙文通认为如同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一样,墨、杨的末流分派也会自相攻击。他通过引用《荀子·非十二子》有“纵情性”和“忍情性”之说,结合《管子》之《立政·九败》《立政·九败解》对“全生”之言的批判,《战国策·赵策三》所见公子牟(魏牟)不以富贵累生的事迹,《庄子·让王》所载公子牟和詹何关于“重生而轻利”的对话,指出魏牟乃詹何之徒,他们的行为都接近《荀子·非十二子》所谓“纵情性、安姿睢”一派;(10)“纵情性”一派,蒙文通还举出《庄子·盗跖》所介绍的“夷、齐、鲍、焦、申徒狄、介之推”,也体现于“子张、满苟得之问答”“无足、知和之问答”。同时结合《管子》之《立政·九败》《立政·九败解》对“自贵”之言的批判,《战国策·齐策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孟子·滕文公下》所见陈仲坚守名节、不义不食、刻意避世的事迹,认为他的行为符合《荀子·非十二子》所谓“忍情性”一派。(11)“忍情性”一派学说,蒙文通认为也体现于《庄子·让王》所见“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太王亶父”“王子搜”“颜阖”等人不就王位的故事,以及“北人无择”“卞随”“瞀光”“伯夷、叔齐”等人“迫生不若死”的故事,因此创作《让王》者,“以忍情性损嗜欲为主,而一皆归乎养生完身,则亦杨朱之徒也”。从而论证“杨朱一派显有‘纵情性’、‘忍情性’之二派”,它嚣、魏牟“亦杨朱一系之学”,陈仲、史鱿“亦杨朱之学者”。他还认为,《庄子·盗跖》是詹何、魏牟一派在讥讽陈仲之类人物死守名节的行为。《吕氏春秋·贵生》里面“迫生不若死”的话,又是陈仲一类人物针对詹何“重伤”之说的反论。(12)民国时代学者的文章有时用词过于俭省,缺乏清晰性。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蒙文通有此意。此处原文是“则迫生不若死之说,苟又陈仲子之徒有憾于重伤之论而为之说乎!”“重伤”之说出于《庄子·让王》,指的是既不能约束自己,又要勉强地约束自己,所以是两重之伤害,因此要不受任何束缚地“全生”“重生”,这属于“纵情性”。但在陈仲一类“忍情性”人物看来,“迫生不若死”,如果不得不约束自己,那还不如死,而不是无原则地放纵自己。从《庄子》来看,以《让王》卞随等人为代表“忍情性”一派亦许孔子、不废仁义,(13)蒙文通甚至认为《庄子·让王》等篇可能是杨朱一派的作品,为编者误入。而以《盗跖》为代表的“纵情性”一派则绝仁弃义、诋毁仲尼。(14)蒙文通称其为“杨朱末流”。这是两派的重大区别。《盗跖》鼓吹“纵情性”,《让王》鼓吹“忍情性”。《骈拇》《马蹄》《胠箧》《在宥》诸篇,提倡“无为君子、无为小人”,所以与“魏牟一派为合”,《天地》《天道》《天运》诸篇,“于陈仲一派为近”。他们虽然对孔子态度有别,但都鼓吹“卫生养生”之说。《刻意》《缮性》《至乐》诸篇,“鄙乎长生之为”,就属于庄周之言,而和杨朱有别。
蒙文通因此指出,杨朱一派时而倡导“仁义”,时而参与政治,因而并不像孟子说得那么极端。在对待仁义的态度上,以杨朱为代表的北方道家和与老、庄为代表的南方道家,正好形成对立。因此不能说不反仁义就不是道家。“道家要以北人居多。苟以仁义之说衡之,北方之道家杨朱之徒,不废仁义,斯为正宗。而庄周南方之学,翻为支派也。”这就是他著名的南北道家之说。
第二,此文基本上能把杨朱之学各个侧面、各种特征关联起来,并给予合理地解说。作为杨朱学派的主要思想元素,蒙文通借助与杨朱相关的养生概念,如“本生”“尊生”“全生”“长生”“卫生”“重生”“完身”“为身”“全性”“自贵”“重己”“贵己”“为我”“养年”等,把典籍和人物串联起来,并引申到“仁义”“情性”“因循”“齐物”“清虚”“尚法”等一系列复杂领域。就是说,如果养生是杨朱的据点或出发点,那么其辐射的领域最终极为广泛,和伦理思想、治国理念发生密切关系。
蒙文通进一步指出,田骈、慎到既讲“因循”,又重视“法”,所以《荀子·解蔽》会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吕氏春秋·序意》所见“法天地”之道,“斯亦田骈之道”,“知吕氏以下所谓‘言黄老意’者,皆指田子之术”。这样,通过田骈、慎到,蒙文通就把杨朱学派和黄老之学关联起来了。“晚周以来,黄、老大盛,杂家者起,汇九流而一之,正田骈、慎到之学,乃足以当之。”
然后,蒙文通将视野投向《管子》和《吕氏春秋》,认为《管子》中的《心术》(16)蒙文通不分《心术》上下,这里尊重原文,因此不作区分。《内业》其义合于慎到,《心术》所见因循之说,和《庄子·天下》批评的慎到形象相吻合。而《六帖》《御览》等后世类书所引《慎子》与《吕氏春秋·贵因》有一致之处,可见《贵因》之说本于慎到。《吕氏春秋·察今》在《贵因》之后,《艺文类聚》所引《慎子》与《察今》有一致之处,可见《察今》之说取之慎到。《贵因》之前的《顺说》《不广》都主因循,“似亦慎子一派之说”。《吕氏春秋·慎势》有引《韩非子·难势》所见慎到之文,所以“《慎势》一篇之本于慎到又审矣”。《慎势》前面的《知度》《任数》所见“无先有随”的精神则合于《荀子·非十二子》“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以及《庄子·天下》“推而后行,曳而后往”“缘不得已”的形象。可见《吕氏春秋》几乎是慎到大本营,通过慎到,杨朱之学大为扩展。
蒙文通进而用《管子·白心》中“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盖圣人行其行而百姓被其利,静身以待,物至自治,安用拔一毛以利之,拔毛以利,适为不利也。”用《管子·心术》中“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裁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此殆以天下之自治自利,拔毛以利之,适以乱之。”因此《心术》《白心》的“因循”之道正是对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引申发扬。(17)可见在蒙文通看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指的正是是否利于天下,和孟子的理解一致。但是蒙文通认为杨朱想要表达的是,没有必要去“利”天下,因为“利”天下反而是害了天下。不利天下,这正是杨朱能够“治天下如运诸掌”的缘故。
在此基础上,蒙文通提出《心术》《白心》就是慎到之书,但“足以发杨朱之蕴”,慎到是“上承杨朱而下开申韩”之人。通过对比荀子、庄子评论田骈、慎到的语言,可以确定《管子》的这几篇中田、慎之说有集中体现。
所谓思想史(也包括哲学史)研究路径,是指不把重点放在文本的辨析、材料的确认上,而将目光更多投注于分析概念的意涵、考察思想的脉络,以及对于后人尤其对于今人的影响上。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史研究路径就不尊重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路径就不涉及思想,而是指学者在投身研究时,问题意识以及研究重心上存在差异。
此外,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教授也需要认识到就业现状的严峻性,综合教学的实际,不断地充实自己,并引导学生及时获取信息,将这些信息传授给学生。同时,教师教学中还应该认真分析一些机械零部件的做工,吸取先进的技术,并传授给学生一些相关的知识,让学生在学习中懂得变通,从而提升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通过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理论基础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此外,《白心》之旨“不离乎尊生、贵己之旨”,《内业》和《心术下》“专意于全生之旨”,蒙文通认为这也证明这些文章“循环相通,则并属之杨朱之徒可也”。“墨之学至于宋钘、尹文,杨之学至于田骈、慎到,而义益精”,可以称之为“冰寒于水而青出于蓝”。
接下来蒙文通把目光转向《慎子》一书。他主要以见于《群书治要》的部分来作出论述,认为其中《威德》一篇中的“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则圣人无事矣”正合《管子·心术》“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的精神。“天下自治,非使圣人养己,则安用圣人之利天下哉”,这就又和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关联起来,即不利天下正是不乱天下之意。蒙文通又认为《慎子》书中《因循》一篇所谓“因人之情”的理论和《管子·心术》“人之可杀,以其恶死。其可不利,以其好利”相合,和《尹文子》所引田骈的“自为”之说相合。田骈、慎到出于杨朱,又聚于稷下,“黄老之论于是始倡”。这里,蒙文通再次重申了前面的观点,即杨朱学派和黄老之学有密切关联。
蒙文通还把韩国的申不害也拉了进来,《申子·大体》也主“贵因”之说,同时也讲“势”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都是“申子袭之慎子”。
一是不在群里发广告链接,基本已成为群聊的默认规则;二是群里氛围淡薄了,大家更现实,家长们只是将其当作一个公告牌;三是现在的家长工作繁忙,个人手机或电脑里的各种APP繁多,信息量大,很少有家长愿意花时间关注班级群,更喜欢与老师私聊。
木工机械行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产品个性化,制造商要在和批量生产相同的周转、盈利能力和效率限制下交付定制产品,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汉诺威国际林业木工展览会的参展商将在2019年5月展示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LIGNA展会是国际木工行业的创新市场,此届展会涵盖了以下三大主题:
52例研究对象先行CT扫描,行桡骨远端冠状位和矢状位,确保两层间距2mm,特殊患者可以间隔1mm,有些患者要增加水平位片拍摄。再对52例患者行X线检测,于腕关节正侧位拍摄X线片。
《慎子·民杂》鼓吹“齐物”之论,这个“齐物”显然不是《庄子·齐物论》的整齐物论,而是兼容并包、充分发挥万物不同职能的意思,这就是彭蒙、田骈、慎到的“齐万物以为首”。(18)蒙文通认为《民杂》这段话还只是“齐物论”之用。《庄子·天下》“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是“齐物论”之体。蒙文通历数《尹文子·大道》(19)蒙文通不分《大道》上下,这里尊重原文,因此不作区分。《管子·心术》《管子·白心》《管子·乘马》《慎子·知忠》《吕氏春秋·用众》《庄子·天下》相关言论,认为“贵齐”之说发展到后世,“慎到、尹文有进于田骈、彭蒙者”,“《吕》之所取则精,足以补田、慎之佚说”。即齐物论从彭蒙之师的“舍是与非”“无用圣贤”,一般性地强调平等地对待万物,发展到后来,“是非可不可无所循”(《吕氏春秋·序意》),则是“后师之义,益精更进之说”。从《庄子·天下》所谓“教则不至”发展到《管子·白心》“教可存也、教可亡也”;从《庄子·天下》所谓“选则不遍”发展到《管子·心术》“慕选则不乱”;由《庄子·天下》所谓“莫之是、莫之非”发展到了《论六家要旨》的“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则齐物之论得以消解。
总之,从黄老的角度来看,作者认为“田、慎以清虚无为,名正法备,为黄老之正宗”,“杨朱之学,逮乎田、慎,义益邃而用益宏。黄老既由此出,且以法为邻”。至此,蒙文通最后把列子拉入杨朱体系,因为“列子贵虚”,“黄老一派以虚为贵,当取之列子之言也”,“吕、庄二书皆言‘子列子’,盖列子于黄老一宗所系之重,清虚之说,实始于此”。因此黄老之道,是以列子为先驱的。从谱系上讲,“列子先于杨朱,则杨氏之学,源于《列御寇》,而下开黄老”,“魏牟、陈仲、詹何、子华、田骈、慎到,皆杨朱之流派,而列子者,倘又杨朱之远源也”。
通过以上的概括,可知在《杨朱学派考》这篇大文章里,蒙文通以杨朱为梭子,利用各种零散资料,编织出一张网,这张网之大、之密,作者运用史料之娴熟,串联思想线索技巧之高超,让人叹为观止。无论在蒙文通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无人能编织这样的网。这张网有几个特点:
第一,详细描绘了杨朱学派的谱系,从人物上讲,那就是列子 →杨朱 →詹何、子华子 →魏牟、陈仲 →田骈、慎到。这是他着力考察的几个重点人物,其他与之相关的还有它嚣、史鱿、彭蒙之师、彭蒙、接予、申不害、韩非子、吕不韦、司马谈等。(20)蒙文通并没有绘制这个系列图,是笔者依据他的观点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出来的,因此未必是直线的师承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在《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中曾经绘制过一幅图,在这幅图中,顾颉刚用直线表示詹何、子华子和杨朱有直接师承关系,而用虚线表示庄周、彭蒙、田骈、慎到是受其影响者,这种影响又波及老子(顾认为《老子》晚起)。很可能在蒙文通这里,杨朱与后学的关系,同样既是师承关系,也是影响关系。从文本上讲,主要可以以下文献为代表:《吕氏春秋》中的《本生》《重己》《贵生》《执一》《不二》《审为》《尽数》《诬徒》《适音》《贵因》《用众》等篇;《庄子》中的《盗跖》《让王》等篇;《管子》中的《内业》《心术》《白心》等篇,以及见于《尹文子》《慎子》《申子》《韩非子》《淮南子》《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旨》中的学术史资料。人物极为众多、材料极为复杂,蒙文通却了然于心,如数家珍、旁征博引、无所不窥,从容运用于股掌之中,且精义迭出,为学界全面盘点了资料、梳理了脉络,提供了相对可靠、可用的文献,功莫大焉。
接下来蒙文通转向北方道家,开始整理稷下道家的资料,首先是田骈、慎到,根据《吕氏春秋·执一》所见田骈“因性任物”“变化应求”的主张,他断定“是田骈亦詹何、魏牟全生养年之道也”。而“因性任物”“变化应求”正符“因循”之义,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形容道家的“虚无为本,因循为用”一致。(15)这里,蒙文通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见“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等讨论形神关系的话,“斯皆全生尊生之旨”。观《庄子·天下》批评“彭蒙、田骈、慎到”之言,也均为“因循”之义。《论六家要旨》说道家“有法无法”“有度无度”,正与《荀子·非十二子》批评“慎到、田骈”时说的“尚法而无法”一致。
第三,可能受疑古学派的影响,蒙文通基本上使用的是比较可靠的先秦文献。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与老子的关系,老子没有进入杨朱学派的谱系,也就是说蒙文通切断了传说中老子和杨朱之间的师生关系。在此文中,蒙文通也谈到老子其人及其书,他认为与老子相关者有好几位,他承认有那么一位老聃,但并非《道德经》创作者,《道德经》的作者当为魏国人李耳,创作于《韩非子》之前。(21)顺便指出,蒙文通认为黄帝书的出现在《道德经》之后,《吕氏春秋》之前。在这篇论文中,蒙文通总是老、庄并列,虽然并不清楚这个“老”是与关尹并列的老聃还是《道德经》作者的李耳,但是这位“老”的基本立场和“庄”相同,是极端反仁义的。这样,蒙文通就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和以杨朱为首的道家截然区分开来,成为南北两大道家的象征。至于慎到、尹文、列子则主要使用先秦的记载或者后世类书中辑录的资料,而没有使用今本《慎子》《列子》,对《尹文子》则做了谨慎的使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子·杨朱》的材料,他几乎完全没有提及。
第四,在这篇论文中,蒙文通在构建杨朱学派的同时,几乎同时构建了早期黄老学史。在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以及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还没有出土的时代,要依据零碎的、不被历来重视的材料来构建黄老谱系极为困难,而蒙文通依据他的学识和智慧,在学术史上第一个把黄老道家的重要人物、重要观点、发生地点、发生原因做出了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使杨朱成为黄老道家的鼻祖,这是非常值得敬重的学术贡献。我们注意到,《杨朱学派考》原来是由两篇论文《杨朱考》《黄老考》合成的,因此可以说他在构建杨朱学派的同时,已经有意识地在构建黄老学派了。后来他把黄老学的思考进一步扩大,完成了《略论黄老学》一文。(22)此文收入蒙文通:《先秦诸子与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223页。《略论黄老学》一文较少提到杨朱,但是通过《杨朱学派考》可知,没有对杨朱学派的全面梳理,是不可能推出黄老学派的。今天的黄老学研究借助出土资料已经有飞跃式的进步,但是过分依赖《黄帝四经》等资料,使得黄老学中“从天道到人事”一系的论证日渐丰满,而“养生到治国”一系的研究却显得衰微,当年蒙文通限于资料,只能注重于“养生到治国”一系的研究,而且将其几乎臻于完美,如果他能看到后世的出土文献,相信一定能发出更多精妙言论。我们今天研究黄老之学,如果不能重视杨朱以及杨朱之后的学术演变,如果不能重视蒙文通的研究结论,那是有缺陷的。
当然受到时代的局限,此文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那个时代的学者写作,基本上不用回顾前人研究,不用引用其他学者见解,因此这篇论文的思路、观点哪些是受到古人尤其清代学者的影响,哪些是受到民国学者尤其古史辨学派的影响,我们只能揣测和推理。同时,对于文献名称、人物名称以及原文的引用,作者常常减省,容易给读者造成很多困惑。旁征博引的同时,也难免牵强附会。例如贵因之说,道家典籍中到处可见,全部归于慎到,恐不合适,把《吕氏春秋·贵因》前后各篇均视为慎到之书也未必妥当。总之,作为杨朱学派重点人物的慎到,其材料运用有无限扩大之嫌。此外,论文的叙述,很难锁定和突出主题,仅仅围绕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而显得跳跃和散漫,用今天的话讲,缺乏论文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共有的通病,不能过于苛求。
可能是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作者过分低估《老子》的影响,认为《道德经》出现于战国中晚期、《韩非子》之前。笔者也不认同春秋晚期有那么一位老子,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口气写下了《老子》五千言。郭店《老子》的出现,也给《老子》晚出说带来极大冲击,郭店《老子》并无“绝仁弃义”之语,其中也有养生与政治相关联的思想,因此不得不加以重视。像蒙文通这样,完全无视《老子》中丰富的养生思想,将其完全排斥在讨论范围之外,是不可取的。当然今天很多学者,简单地将《老子》视为道家思想的最高源头,把黄老道家仅仅视为老子思想的转化,我认为也是过于简单化了。
2. 郭沫若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当“亿万富翁”这一标签被媒体使用时,几乎总是意味着对报道对象的贬低和诋毁,但现实是我仍然和以前一样,做着同样的科学和工程业务,只是规模改变了。
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23)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73页。本文所引郭沫若原文,均见此文,不再一一注释。完成于1944年,以《陈侯因敦》铭文为引子,讨论了黄老为何培植于、发育于、昌盛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问题。在此文中,郭沫若提出了道家三派的说法,那就是“宋钘、尹文派”(24)郭沫若认为“宋钘”因为观点与墨子接近,才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与墨翟并举。“田骈、慎到派”“环渊、老聃派”(25)作者认为“环渊”就是“关尹”,两者间存在通假关系。而且“它嚣”“范睢”也是同一人。作者还认为这三派在《天下》篇中的叙述次第及发展次第,大致是宋尹学派在前,环渊、老聃学派在最后。。郭沫若认为这三派都与杨朱有关,杨朱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寓言中的人物,“老聃与杨朱的存在如被抹杀,则彭蒙之师、彭蒙、宋钘、环渊、庄周等派别不同的道家便全无归属” 。(26)他认为“彭蒙之师”或许就是杨朱弟子,但因为他没有专著传世,所以成了无名之辈。他认为老聃确实存在,而“杨朱是他的弟子,大抵略少于孔子而略长于墨子”。作为杨朱的主要学说,他举出了《淮南子·汎论》中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主义;(27)从价值上判断,郭沫若认为这是一种“为我主义”,但“不是世俗的利己主义”。“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韩非子·说林上》)“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庄子·山木》),证明杨朱具有“泯灭小我”的“宽恕”之心。因此他把“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理解为“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说这正是“不以物累形”的夸张说法,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就是他的这种精神的嫡系了”。
前面分析得出了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下面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具体结果见表5。
因此,就杨朱和道家三派关系而言,“宋钘、尹文派”与杨朱关系最近,他引《庄子·徐无鬼》中“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及“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二句,指出“秉”就是“彭蒙”之“彭”的音变。如果说这是庄子当时的学术构图,那么既然“秉是田骈之师彭蒙的彭的音变”,“杨便当于宋钘、尹文一派了”。因此他推出“宋钘”是杨朱的直系。而“宋钘、尹文”的主要著作就是《管子》四篇,该文的一大目的就是要论证《管子》四篇是宋尹学派的专著。(28)这一观点学界争议很大,如冯友兰(《墨家的支与流裔宋钘尹文》,收入《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张岱年(《管子的〈心术〉等篇非宋尹遗著考》,《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祝瑞开(《〈管子〉四篇非宋钘尹文遗著考》,收入《先秦社会与诸子思想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均表示反对。日本学者町田三郎(《管子四篇について》,《文化》25卷1号)、山田统(《宋钘という人间とその思想》,《国学院杂志》63卷12号)、金谷治(《宋钘の思想について》,《中国古典研究》第14号,1966年版,又见金谷治思想论集之中卷《儒家思想と道家思想》,平河出版社1997年版)也表示反对。
这些人都是所谓“避世之士”,有一点地位,也有一点产业,但他们“不愿案牍劳形,或苦于寿命有限,不够满足,而想长生久视,故而采取一种避世的办法以‘全生保真’,而他们的宇宙万物一体观和所谓的‘卫生之经’等便是替这种生活态度找理论依据的”。本来这些人只占少数,又没有大众基础,难以发展,但是因为稷下学宫这个特殊的温床,得到齐国君主的资助,便一下繁盛起来。那时正好秦国做了墨家的保护人,于是就出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逃墨必归杨、逃杨必归墨”的局面。“事实上就是孟子、荀子都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是强半逃儒归杨了。”(29)郭沫若注意到孟子、荀子都尊重宋钘,孟子称其为“先生”,荀子称其为“子宋子”。
而齐国之所以要扶植道家,是因为田氏是“窃国者”,“所以要预为之防,非化除人民的这种异志不可。在这个目标上,杨、老学说是最为适用的武器”。郭沫若虽然没有明讲,但显然认为“全性保真”这类消极避世、自我保护的意识,是有利于田氏统治者消除他人的反叛野心的。
这样郭沫若就把杨朱主要和“宋钘、尹文派”关联起来,他举杨朱临衢而哭等事例,表明杨朱有宽恕之心,而宋钘的特征就是宽恕,所以《韩非子·显学》有“宋荣之宽”“宋荣之恕”的说法。杨朱有“舍者与之争席”(《庄子·寓言》)的故事,郭沫若认为“这是他的无我精神,也就是他的为我主义。道家的无我是认为为我的最好手段,所谓‘无用乃为大用’,泯却了小我乃正保全了大我”。
制定食物中毒应急处理预案。预案应包括领导小组人员、报告处置程序、报告部门、善后处理等内容,保证食物中毒应急处理有效和有序进行,并建立在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的基础上。
在将《管子》四篇定性为宋尹学派的著作后,他开始分析这几篇的主要思想,如作为宇宙本体之“道”、精气、灵气观念、“静因之道”、调和儒墨等。就调和儒墨而言,宋尹学派的“救攻寝兵”,近于墨子非攻;“情欲寡浅、食无求饱”近于墨子节用。而《心术》《内业》各篇“不仅不非毁仁义,不蔑弃礼乐,甚且注重仁义礼乐,这是和儒家通声息的地方”。
侯外庐把杨朱派的道德论与古希腊的伊璧鸠鲁相比拟,然而让他为难的是,伊璧鸠鲁的道德论与自然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伊璧鸠鲁继承了唯物论者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承认物质的、运动的原子为世界的本质,而人的精神则为圆形的、特别活跃的原子构成”。但遗憾的是,从杨朱派向上推,却找不到这样的自然哲学史料。伊璧鸠鲁有建立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关系基础上类似契约论的社会观,从杨朱派向下推,杨朱派虽然也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却找不到类似的观念,“为我”主义发展出来的只是“无君”的思想。因此侯外庐说,由碎片构成的杨朱资料只能构成“中间的一段”,而无法找到上下两段。同时侯外庐又强调,杨朱学派的道德论中,只有“感觉体”意识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而利己主义的“为我”“贵生”思想并不通向唯物主义,恰恰相反,还是杨朱派思想的糟粕。
形成于40年代的蒙文通的《杨朱学派考》(8)此文收入蒙文通:《先秦诸子与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30页。本文所引蒙文通原文,均见此文,不再一一注释。由两篇论文《杨朱考》《黄老考》合编而成,(9)据附记于《杨朱学派考》最后的一段文字可知,这两篇文章原载于1946年10月四川灌县灵岩书院编印的《灵岩学报》创刊号。合编为《杨朱学派考》后载于《图书集刊》第八期,成都,1948年6月。此文对于杨朱相关的资料作了极为详尽的收集与整理,通过绵密的分析,构建起了杨朱学派的谱系,并最终将其和黄老道家联系起来。
总的来看,郭沫若此文借助田氏代齐这一历史事件以及稷下学宫这一历史产物,分析了先秦道家三派的特征,以及杨朱在其中占居的位置,虽然对黄老道家主要思想的定位并不明确,但也将杨朱关联了起来。由于他在学界以及政界的特殊地位,此文对于后世学者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现在研究黄老道家者往往从田氏代齐说起,这和郭沫若的研究应该有密切关系。(30)关于黄老之兴盛,是否与田氏代齐相关,学者现在有不同意见,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作详述。
这样,无论是蒙文通还是郭沫若,都注意到杨朱身上既养生又救民、既避世又入世的色彩,也都将杨朱和黄老道家联系起来。郭沫若没有像蒙文通那样描绘出一张以杨朱为核心的巨大网络,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杨朱和宋钘、尹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杨朱和宋钘、尹文之间建立了学术传承关系。其实郭沫若也提到彭蒙之师是杨朱弟子,但既然彭蒙之师受业杨朱,那为什么彭蒙、田骈、慎到不能和杨朱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注意到,蒙文通恰恰是凸显了杨朱和彭蒙、田骈、慎到一系的关系。在蒙文通的杨朱谱系中,宋钘不在其中,尹文也是间接影响的关系。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恐怕只能说,由于杨朱资料的缺乏,或者由于杨朱思想的多面性,导致了解释的多样性。其实,蒙文通和郭沫若两人还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被郭沫若定义为宋尹学派专著的《管子》四篇,在蒙文通这里,是被当作田骈、慎到学说来看待的。因此,如果以郭沫若的道家三派为讨论基准,那么他们两家其实都注意到前两家关系更为密切,在一些学说上很难完全切分,而和“环渊、老聃派”则有着很大的区别。总的来说,如果以杨朱为论述的核心,那么,蒙文通的材料收集、问题选取、分析路径以及最终结论,似乎比郭沫若更为妥帖、合理一些。
如前所言,出土文献大量问世是在蒙文通、郭沫若身后,这是他们的一大遗憾,他们没有更为丰富的资料可供拓展视野,解放思路。但我们今天不应该轻易忘却他们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对于文献的敏感和熟悉,对于材料的尊重和驾驭,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比他们要差很多,因此细心体会他们的用心,反复揣摩他们的方法,应该是我们经常开展的学术训练之一环。
二、侯外庐、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路径
蒙文通又联系接予的“或使”理论,通过原文作为证据,认为《白心》不少地方正是“或使”之说,而“或使”之说最终导向的是“无损无益”的精神,这一精神恰恰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相吻合。
如前所言,在古代,杨朱因为被孟子贴上“为我”的标签,成为利己的象征,在儒家社会便永世不得翻身,即便在后世道家、道教那里,也没有获得较高的评价。然而到了20世纪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古史辨派学者、蒙文通、郭沫若等人的学术史梳理,杨朱成为早期道家不可忽视的人物,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本来作为批判对象的“为我”,被重新诠释为“为我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之后,反而成为杨朱得以翻案、得以肯定的重要因素(31)20世纪早期的杨朱复活现象,何爱国等学者已做过详细的考察,这里不再重复。参见何爱国:《现代性的本土回响:近代杨墨思潮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中第一章《杨朱学派的近代活化》、第二章《近代杨朱学派新形象的构建》、第三章《事变而学变:梁启超的杨学三变》。。为何会有如此巨大变化?这极为有趣的思想史现象值得我们深究。
膨胀土边坡降雨失稳后的边坡立面图如图4所示。由于发生牵引式滑坡,失稳后的膨胀土边坡表现出了明显的坡顶塌陷和坡脚隆起现象。此时,数值计算结果也同离心模型试验结果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
我们注意到,1916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的作者谢无量,(32)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国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翻印。《杨朱》一节在第134-136页。很可能此前日本人所撰各类《支那哲学史》《支那思想史》已经按照西学标签重新评价杨朱,有待查考。使用“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来概括杨朱,这是用西方人熟用的评价方式来重新裁量中国古人的思想。但在谢无量这本书里,“利己主义”仍不是好的评价,例如他说“要之杨朱所谓利己,限于一己之性分以内,以保全真性,不惟与人无异,且无以自充其性情之欲。虽井然有条,而不可以为国家社会之法。其流弊必至举国家社会而悉绝灭之”(33)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134页。。而“享乐主义”虽不至于那么糟糕,但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其论人生,虽近于厌世之观,而固不至于自杀。惟从自然之大道,守其个人之范围。以生以死、以逸以乐而已”(34)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136页。。
第一位正面评价杨朱,并产生重大影响者,可能是胡适,他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为杨朱设置了专门一章,(3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杨朱》一章在第155-162页。以下引用此文,不再一一注释。在胡适前,严复、梁启超也开始为杨朱翻案,但不似胡适那么有力。虽然他承认《列子》是伪书,但《杨朱》篇“为我”的观点,和先秦时人对他的评价吻合,所以可以使用《杨朱》篇来阐述他的思想。在阐述杨朱人生哲学时,胡适用了“为我主义”。他说自己敢于提出这个观念,是因为以下这段话所蕴含的哲学基础:“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胡适说这指出了“为我主义”的根本观念。即动植物都有存我的天性,生物因为要保护自己,才促进了生物的进化,但人是一种合群的生物,因此除了“存我”观念之外,还有保护家族、社会、国家的爱群主义,由于后世“爱群主义”压倒“为我主义”,才使“存我”成为不道德的观念,“试看社会提倡的‘殉夫’、‘殉君’‘殉社稷’等等风俗,推尊为道的行为,便可见存我主义所以不见容的原因了。其实存我观念本是生物天然的趋向,本身并无什么不道德”。因此,他认为杨朱的为我主义,并不是损人利己的代名词,所以他会一面提倡“存我”,另一面反对“侵物”,一面“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另一面“悉天下奉一身不取”。可以说这都是“为我”思想的完整体现,也是他必然走向“悲观”和“养生”的原因。这样,胡适就通过进化论为杨朱做了辩护,认为他的思想有合理性,因为人作为个体,要自我保存,作为群体的一分子,要维护群体,这些都是合理的。而中国古人将后者大大强化,成为唯一标准,结果造成了“殉夫”“殉君”“殉社稷”等悲剧,杨朱大胆地把人的另一面说出来,其实是勇气的体现,是对个人生命以及感受的尊重。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消化吸收国外援建的中型氮肥厂的基础上,我国建设了多套小型和中型氮肥装置,许多省几乎每县都建有氮肥厂。“心连心1969年建厂,当时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技术。建厂的资金是从老百姓的鸡窝里抠出来的,是老百姓用鸡蛋换来的320万元钱。”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兴旭回忆说。
为杨朱翻案,和胡适提倡个性解放有很大关系。1919年,胡适为一位默默无闻的女生李超写传,引起极大轰动,李超的经历和易卜生描述的“娜拉出走”现象联系起来,她被勾画成“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认为她的一生是挣脱旧的道德束缚、争取个性解放、女子解放的典范。(36)可参颜浩:《胡适为何要为一名民国普通女学生写传记?》,《中国青年报》2015年12月20日。这和“五四”以后,中国人接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急于挣脱封建人身束缚,使国民成为在经济上、思想上、人格上独立的个体,以适应工业社会对于自由人身的要求,有很大关系。因此,反社会、反礼教是值得赞扬的行为。胡适在其《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每个人都要承认自己有独立的价值,要敢于说出自己的主张,要有自由意志,个人要对自己言论、行动负责,这就是“个人主义”。因此,在胡适这里“个人主义”是进步的象征。(37)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在《略谈人生观》的文章中,胡适将王安石和杨朱联系起来,“中国思想上具有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可以与西洋思想相互印证。王安石是个一生自己刻苦,而替国家谋安全之道,为人民谋福利的人,当为非个人主义者。但从他的诗文可以找出他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己的人生观。因为他曾将古代极端为我的杨朱与提倡兼爱的墨子相比。在文章中说‘为己是学者之本也,为人是学者之末也。学者之事必先为己为我,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为自己有余的时候,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因此个人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轻人确立一个人生观,更是需要慎重的把自己这块材料培养、训练、教育成器。”“人最可贵的是个人的个性。这些话,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感情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38)胡适:《略谈人生观》,收入《人生有何意义》,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因此,重新评价杨朱,并将他定义为值得肯定的“个人主义”者,和胡适对于西方理念的接受有关。因为在十八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价值,在西方一直占据着主流意识。胡适这一代的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渴望从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发掘出与西方思想相匹配的内涵时,杨朱的思想就成为很好的材料。同时也和“五四”以后的时代要求、历史使命密切相关。人身的自由、个性的解放是“五四”以后席卷中国的巨大洪流,这股洪流超越了党派意识,因此无论是国民党执政时期还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对于人性的解放,对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强化都持肯定的态度。虽然在1949年之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个人主义有的时候作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对立面,作为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会等同于自私自利、利已主义加以否定,同时因为胡适遭到否定,那么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受到批判,但有趣的是对杨朱的评价却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只不过换了新的标签,重新做了包装而已。以下就以侯外庐、刘泽华为例,描述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下杨朱研究的基本面貌。
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杨朱研究
由侯外庐领衔,赵纪彬、杜国庠等人合作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最初于1957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最新修改版完成于2011年,本文就是以2011年版为依据的。(3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所引候外庐原文,均见此书,不再一一注释。这部书第一卷的作者正是侯外庐,其中的第十章是《杨朱学派的贵生论和宋尹学派的道体观》,侯外庐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杨朱学派和宋尹学派的思想,显然作者认为这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重要侧面,可以看出作者继承了郭沫若的论断,把宋尹学派当作了杨朱学派的继承者。在此笔者不准备对整个第十章作出评判,因为就杨朱学派和宋尹学派的相互关系及其学术思想而言,此书基本上还在胡适、冯友兰、郭沫若等人的框架之下,并无太多新意。笔者打算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此章的第三节《杨朱学派道德论的历史价值》上,因为这一节体现了侯外庐对于杨朱的价值评判。
首先,侯外庐给予杨朱“为我”“贵生”的“利己主义”思想极其高的评价,之所以说极其高,是因为其评价的语气远远超过了前人,侯外庐多次使用了“光辉”这个词汇。例如,在侯外庐看来,“这一理论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背后,隐然潜伏着承认感觉体的光辉!”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感觉体”。他首先引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唯物主义者“事实上是以个体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而“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意思,只是说明了“人是一个感觉体并且只是一个感觉体”的命题。所以“个人利益并不是一条道德诫命,而只是一件科学事实”。他认为杨朱派的理论,恰恰符合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不少地方正是在重复地揭示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是一个感觉体并且只是一个感觉体”的命题。因此,侯外庐指出:“思、孟派的圣人之徒是伦理上神化的人,而杨朱派的圣人则是科学上人化的人,这个科学事实的揭示,正打击了思、孟派圣人头上的神圣的光轮。我们认为,杨朱学派的思想,就现存文献而言,提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人只是一个感觉体,而个人利益只是一件科学事实。这一命题坚持从人本身去说明人,而不人为地附加更多虚假的东西;这一命题坚持从人的感官物质利益去说明道德,而用不到假定天志和先王观作为道德论的奠基石,在这一点上,仅仅在这一点上,杨朱派的‘贵生’论或‘为我’论,在其全篇说教的暗然黑夜里闪出一道光芒,在百家并鸣的诘辩思潮中独树一帜。”
1. 蒙文通的《杨朱学派考》
郭沫若同时依据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说,将告子也归为宋尹学派,因为这“分明就是《内业篇》所说的‘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
我们发现,侯外庐大大高扬的杨朱的“光辉”,只能在尊重“感觉体”这个非常狭隘的话题里找到,而在其他领域,侯外庐感受到的更多是无奈和纠结,他找不到杨朱派唯物主义色彩的渊源和去路,同时还得批判他的利己主义糟粕,也就是说大部分材料并不支持他的结论。在笔者看来,侯外庐观察、分析杨朱的视野,类似胡适,都是希望在中国的材料中找到可以和西方理念相匹配的资源,胡适找到“个人主义”,而侯外庐身处的环境,早已为他规定了可以匹配的框架,那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这是一种教条式的思维,仿佛先设定好一套衣服,然后把身体塞进去。这种思维导向下的研究,既能塑造出杨朱的“光辉”形象,也有可能背离文献原貌越来越远。
2.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杨朱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是刘泽华自己执笔的,在第七章《道家以法自然为中心的政治思想》中,他专门设置了《杨朱贵己及其童子牧羊式的政治主张》一节。(4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朱贵己及其童子牧羊式的政治主张》一节在第378-384页。本文所引刘泽华原文,均见此书,不再一一注释。在研究范围上,刘泽华主要利用的是先秦秦汉古籍中与杨朱相关的资料,而没有把视野扩展到杨朱的后学。
刘泽华认为杨朱思想的核心是“贵己”和“为我”。他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得出了杨朱思想的核心是“个人本位论”。首先他认为“贵己”本于“因自然”,但是“杨朱并不主张把人融化在自然之中,他认为人是独立的实体,人与其他事物相比,人自身是第一位的”。杨朱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为我”,因此刘泽华认为杨朱的“贵己”和“为我”并不是常人所说的低级的自私自利,“他的用意是在说明己是一个自然的独立存在物,己的价值高于一切”。杨朱虽然提倡“贵己”和“为我”,但反对损人利己,“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自立,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列子·杨朱》所谓“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是对不平等交换的反抗,是强调了“人人的平等性和独立性”。
混合式教学使教学过程由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自主学习转变。本文在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网络教学资源建设、计算机仿真技术应用、混合式教学组织,进一步丰富混合式教学的内涵,为实践性强的专业课程实施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教学提供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刘泽华通过《庄子·山木》以及《韩非子·说林上》所见杨朱“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的命题,提出杨朱虽然不反对贤与美,但是反对带有“伤他性的贤与美”,即世俗之贤和世俗之美总表现为对他人的压抑,“真正的贤和美以平等为基础”。刘泽华再通过《说苑·政理》所见杨朱论述的“童子牧羊”式的治理方式,指出这段话的中心是“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思想,与前面讲到的人与人之间不占便宜是一致的,与尊重个人的独立存在也是一致的”。
刘泽华进一步指出,这种强调独立、平等,强调个体价值高于一切并具有不可侵犯性的意识,就是一种可以称之为“个人本位论”的思想,是当时最为激进的思想之一,“是反对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殷周以来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有人都是周天子以及诸侯贵族的附属物,“自己根本没有独立的意义,自己并不是自己存在的目的”。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等级隶属关系开始松动,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一点点活动的场所。杨朱思想由此应运而生,“他提出自己应该是自己的主人,可以说是时代的最强音,最富有解放意义”。
从学脉上讲,刘泽华承认自己属于侯外庐学派。(42)如黄宣民曾提出刘泽华“与他的合作者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可归之于‘侯外庐学派’”,得到了刘泽华的当场首肯,参见刘泽华:《中国儒学发展史》序,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但在杨朱研究上,刘泽华似乎与侯外庐不同。或许因为20世纪90年代,机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有市场,因此,刘泽华著作中没有再出现两军对垒式的简单比附,把杨朱塑造成“科学”的人。不过刘泽华把杨朱思想看作等级社会开始瓦解以后出现的新时代的产物,这一思路依然延续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认为新思想是对旧体制、旧理念的抗争,所以其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不过,把杨朱思想看作是强调独立、平等、具有不可侵犯性的“个人本位论”,虽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不相违背,但其理论内涵和框架又回到了胡适,这和20世纪90年代对于民国学术的评价不再一概否定,而个人主义的禁忌有所消除,可能也有关系。(43)如陈炎《倒霉的杨朱》(《大众日报》2014年4月30日)说:“就拿杨朱所宣扬的‘个人主义’来说吧,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是‘错误’的,需要加以‘批判’的。但是,如果让我们拿出批判的理由,证明其错误的根据,我们却又很难办到。”因此他认为比起虚伪的集体主义,率真的个人主义更为可贵。因此,总体来看,刘泽华的杨朱研究有点调和侯外庐和胡适的味道。经历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杨朱的定位又回到强调个体意识、个人解放的“个人本位”上。
但是,如果我们尊重文本、力图复原杨朱思想的本来面貌,就会发现,所谓“自立”“平等”“解放”“自由”“进步”等概念,都是现代人强加给杨朱的外在标签。把“贵己”“为我”说成“自立”“平等”,把杨朱说成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意识、觉醒意识的“大我”,其实都是偷换了概念,把现代人的理想和信念投影到了杨朱身上。就像20世纪初期为了救亡图存,急于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把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的急切期待投射到公孙龙子、墨家辩者身上一样,都带有太过强烈的时代色彩。
余 言
通过20世纪学术史和思想史两条途径的深入研究,杨朱在历史上的地位被大大强化了。虽然在材料的运用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经过古史辨派学者、蒙文通、郭沫若等学者的努力,有关杨朱的学术资料大为丰富,这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资源、展示了方向,尤其是在黄老道家研究方面,离开杨朱一脉,恐怕难以完善。虽然在杨朱思想性质的辨析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经过思想史(包括哲学史)学者如胡适、侯外庐、刘泽华等学者的努力,杨朱思想的特征,尤其杨朱思想那些在当代还表现出活力的部分被大大发扬出来,对杨朱思想的诠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20世纪思想史的一部分,如何评价这套体系,如何推陈出新,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学术史和思想史两条途径都是20世纪的产物,没有诸子百家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的科学精神,杨朱不可能得到充分地、理性地分析;没有西方价值理念的对照和20世纪时代精神的激发,杨朱不可能被塑造成思想上的伟人,不可能在思想史上站上那么高的位置。但在笔者看来,平心而论,显然20世纪学术史研究途径的成果更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我们做出进一步的消化、修补,在他们基础上做出更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而思想史研究途径的成果带有太强烈的西方色彩和时代色彩,太多“帽子戏法”,观念先行、让材料为观念服务,通过各种曲解,把后人的意志强加到杨朱身上,以至于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简单化、机械化的特征过于明显,因此有必要做出彻底的反思。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并无太大分歧。两者只是从不同的层面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作出了界定。前者观点是从广义的角度对商业贿赂犯罪范围所作的界定,后者则是从狭义的层面对其所作的说明。鉴于以下的论述需要,本文是从狭义层面来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即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种。
压铆件上预置孔的半径应该略大于螺母端部外径C,这样螺母才能放进预置孔内。但是,孔径过大会造成压铆连接的不牢靠。在保证螺母型号、基材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分析不同预置孔的孔径对压铆连接性能的影响。选择型号为S-M4-2的压铆螺纹,压接板孔径D取5种情况,见表2。
总之,20世纪学术史研究途径值得肯定之处更多一些,而思想史研究途径需要反思、修正之处更多一些。不管怎样,尊重文献本身、回到思想本身,不做过度的诠释,应该是两种途径共同的、基本的立场和态度。
ResearchesonYangZhuin20thCentury:CenteredonMengWentong,GuoMoruo,HouWailuandLiuZehua
Cao Fe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orientationson the Yang Zhu stud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the first one is genealogy studies of Yang Zhu school, the well - known exponents Meng Wentong and Guo Moruo include Zhan He, Zi Huazi, Wei Mo, Chen Zhong, Peng Meng, Tian Pian, Shen Dao, Song Xing and Yin Wen in Yang Zhu school, and connect them with the Huanglao Taoist. The second is studies on the features of Yang Zhu’s theory. After 1929, some scholars like Hou Wailu and Liu Zehua try to define the core idea of Yang Zhu as fierce individualism, and they put a premium on it. However, their way of evaluation is in fact similar to Hu Shi from 49 years ago. These two orientations of researches emerged from the 1930s or 1940s to 1990s,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y background of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Yang Zhu; Meng Wentong; Guo Moruo; Hu Shi; Hou Wailu; Liu Zehua
收稿日期:2019-06-15
中图分类号:B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9-0105-13
作者简介:曹 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轻 舟)
标签:杨朱论文; 郭沫若论文; 学派论文; 思想论文; 胡适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