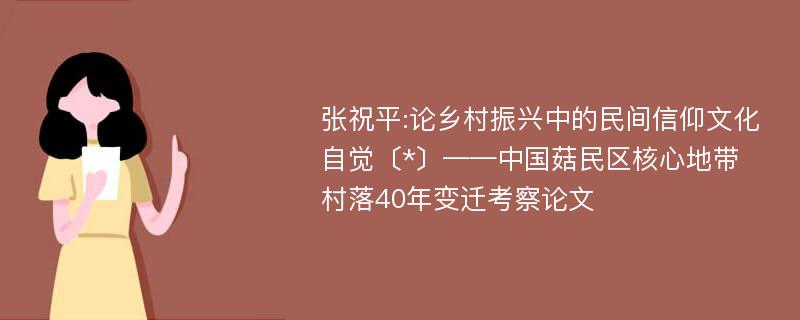
〔摘要〕中国民间信仰的流变与乡村社会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全无教派的宗教文化现象,内蕴着“敬畏自然”“崇德敬祖”“济民利国”的价值取向,一度成为乡村民众文化自觉的重要路径,并与国家意志相协同在总体上形塑着农耕社会的文化品格,在村落共同体联结和激发社会活力中常常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面对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洪流的涤荡,乡村传统文明的物质形态已然处于濒危状态,而传统民间信仰几经沉浮却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复兴景象,与乡村政治、乡村经济交织互渗,依旧叙述着乡土的故事,传播着乡土的情感,持久维系着农耕文明的观念形态,不断为凋敝的乡村生发出文化的想象空间。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发展观,其首要在于对乡村价值的真正理解和认同,关键在于乡村社会精英的培育与再造,背后都离不开乡村文化兴盛的支撑。中国菇民区核心地带村落——X村的乡村建设实践表明,村落保护与建设是从人们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回归和提升农耕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乡村生活方式新样式开始的,其文化实践的方式主要表现在村落传统信仰的复兴上,而这种源于民间生活、祖祖辈辈相承的信仰习俗恰是激发传统村落生机、涵育乡村精英再造机制、助推现代文明反哺和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的一种重要方式。
〔关键词〕民间信仰;村落变迁;文化逻辑;农耕文明;乡村振兴
一、民间信仰复兴:当代中国乡村共同体重建的文化逻辑
民间信仰是发端于人类文明之初的普遍的宗教文化现象,历久弥新,一直是先民们日常生活的思想基础,与血缘、宗族等共同构成了传统村落的基本社会关系,孕育和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村落文明。自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文明的孕育发展,乡村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及其衍生的文明体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新式教育的城市化、工业化取向促进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城市流入,加速了乡村精英的消逝和村落共同体的瓦解,宗族、血缘关系渐趋弱化,村落传统信仰文化得以沿袭之最基础部分逐渐被剥离,加之城市精英的偏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偏差,乡村社会一度陷入文化断裂和“信仰困局”危机之中。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大乡村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策源地,其轰轰烈烈的经济制度变革背后隐寓着深刻的精神危机,而其实质是对自有文化的反思与再造,以及建立于此基础上的乡村社会关系的整合与共同体的重建。回望乡村社会40年的转型变迁,深嵌于其间的民众文化自觉和文化追求生发之轨迹清晰可见。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民间信仰的思想认识逐步从神权迷信观念束缚中摆脱出来,村落传统信仰渐次复苏并成为乡村民众重建社会认同感和信任感的重要桥梁纽带;同时,经由乡村精英的推动,其所附着的乡村社会的价值不断被重新发现、认识和升华。
民间信仰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关系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在吁求思想解放、观念变革渐趋强烈的总体社会环境下,又迅速掀起了一股学术研究的热潮并延续至今,人们试图从各自的学科立场探寻民间信仰之本意、乡村文化之本然,以及其之于乡村社会本体性建构的价值意蕴和实践向度,推动全社会的理性共识,进而在客观上影响和促进传统村落的观念变革与意义再造。经过近30多年来的研究和论证,人们已然感知:(1)民间信仰的生成、演变与创造它的民众的需求息息相关。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乡村民众由“集体人”向“个体人”或“自由人”的转变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原子化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匮乏等是传统民间信仰当代复苏的重要依存理据。〔1〕(2)民间信仰在村落社区整合、村落生活导控、村落情感认同诸方面发挥作用,是理解普通百姓道德情感和生活样态的一种途径,〔2〕可以成为村落共同体内聚的重要力量。〔3〕(3)民间信仰也可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乡村政治因素、市场经济因素与地域信俗文化的互渗交织,是当代民间信仰的真实写照之一,也是它“合理化”嵌入当代乡村社会的一种新方式。〔4〕因此,传统民间信仰的当前复兴,常常受多样思想观念的驱使,人们在相当程度上是把信俗文化作为素材,在国家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自己的文化再生产。〔5〕(4)民间信仰的复兴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新乡贤文化,助推了乡村精英的回归。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基于深厚而朴素的“情感”而非工具理性的传统文化实践,有利于凝聚乡村知识精英,生成新乡贤情感与知识回馈的良性机制,推动知识主导的民俗复兴和地方传统的发明,进而增强乡村民众的主体性以及对乡村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这可能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希望”〔6〕。
诸地乡村建设的实践表明,传统信俗的复兴与重建,不仅成为村落文化活力复兴的动力源,留住了“乡愁”,还丰富了当代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现代性的内涵;人们对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一系列传统文化符号愈加重视,“其实是对其背后的价值与意义的认同”〔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的复兴,不仅是传统村落生活的一种选择性“回归”,更是乡村现代化要素、市场经济要素、地方社会自有要素融合互渗,共同作用于新型乡村共同体塑造的文化整合与培育过程。在这一问题上,过往的研究或者受意识形态的惯性牵制,或者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或者受研究者学科视阈的局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法简单化、目标复古化、思维静态化、手段政治化和价值定位宗教(迷信)化等倾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偏重于现象的描摹和历史性的阐释,对流动着的乡村生活和当代人的心灵世界缺乏深入的观察和体悟,对现时代大背景特别是乡村社会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缺少应有的观照,对于民间信仰复兴之于乡村现代性建设的关系缺少嵌入性的理论思考,容易陷于想象式或自我开导性的意义建构中。本文基于对中国菇民区核心地带村落——X村菇神信仰状况的系统考察,试图充分发挥人类社会学“嵌入式研究”的理论张力,以实证方式解析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及其对传统村落现代性进程和民众现代生活建构的影响,发掘新时代背景下村落传统信仰复兴的特殊性、所隐含的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互构机制,探索生成与传统村落文化共生的乡村振兴之路。
二、中国式乡村文化再造与乡村价值的再发现:一个古村落传统信仰复兴的故事
(一)菇神崇祀——X村的传统信仰
本文研究的个案,是世界最早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之一,当地人因袭历史传统惯称X村,实际上包括两个毗连的有共同历史渊源的行政村,〔8〕现已分别被列入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X村有400多年的建村史,坐落于浙闽赣边境的高海拔山区,远离中心城区,系此一域较具代表性的传统型村落,廊桥、庙宇、祠堂等村落公共建筑及居民住宅、街巷、弄堂都较好地保留了历史的风貌。全村现有住民500多户近2000人,食用菌、高山蔬菜是传统主导产业,中药材、乡村生态游等新兴产业渐成规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加速发展的活力后劲凸显。〔9〕历经当地先民千百年的生产经验累积和生活体验,在村落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文明——菇神信仰,并一直成为维系和滋养香菇文明的纽带和源泉,也因此,X村一域被称为“中华香菇历史与文化第一乡”〔10〕。
溯源菇神信仰,或与香菇栽培同源,在菇民区核心地带已有上千年的生成史。〔11〕所谓菇神,并不是单一的虚幻的对象,而是指在香菇栽培技术创新和菇业发展中发挥过历史突破性作用而为菇民所广泛认同、崇信和景仰的一系列虚实同构的历史人物,其中最核心的有五显大帝、吴三公、刘伯温(刘国师)等。〔12〕先民的崇奉方式主要包括:(1)家庭祭祀,即在家中设置专供家庭成员日常供奉的菇神香火榜;(2)菇山祭祀,凡菇民进山育菇时均携带木刻或泥制的小型菇神像,在山上菇棚中央位置设坛供奉;(3)村庙供奉,为村民共同出资在村里设立的规模大小不一的供奉菇神的庙宇,一般建在村落水口位置,菇民外出,逢村见庙多会跪拜,每年进山育菇和返乡时均需进本村菇神庙祭拜以祈愿(还愿),日常则有留守在村的家人值守庙宇进香祈福;(4)庙会祭祀,主要指每年在大型菇神庙〔13〕举行的大规模进香活动,集祭祀、娱乐于一体,同时为菇民交流商讨菇业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坐落于X村村落中央的“五显庙”是毗邻三县,即菇民区核心地带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远的菇神庙之一。〔14〕据史料载,清雍正元年(1723年),毗邻三县菇帮就商定: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X村五显庙举行菇神庆典活动(菇神庙会),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三县菇民祭祀菇神,祈佑五谷丰登、制菇发财;二是约请地方上的名戏班昼夜演出五天;三是三县菇民交流制菇经验、香菇交易信息、探听菇树资源等。〔15〕凡此其间,商贾云集,以千计的菇民领袖和以万计的菇民汇聚于此,还有十里八乡的民众前来走访亲友、看戏或参与到菇民的体育竞技和民俗表演中,〔16〕造就了一个偏僻山区村落的狂欢盛事。可谓“神”因人而圣、村因“神”而兴。X村一域以其丰富的菇神信仰积淀逐渐成为世界香菇文化中心地之一,成为菇民最集中、香菇经济最发达的村域。有民国时期史料记载:“种菇顶闹跤垟源,常年出门有几千”〔17〕,X村一域外出种植或经营香菇的村民行迹遍及浙、闽、赣、皖、湘、鄂、粤、云、贵、川、陕、甘等13省区250余县市,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屯溪等地还出现了X村菇行一条街,可见菇业之繁盛,村民收入亦极为可观,〔18〕以至于一度出现“村里土地交易价格比县城贵出三倍”的罕见现象。〔19〕1948年,中国第一个香菇职业工会在X村所在乡的中心小学成立,经由230多名菇民代表的举荐和县政府的批准,X村的菇民领袖周仁余当选为理事长。可以说,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与变迁,X村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进入了空前荣盛的时期。同时,村落传统信仰与村落建设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格局也得以形成和巩固。
随着养蜂产业的扩大,砂仁、花椒、魔芋、万寿菊等经济作物收成的增长,曼来村打赢脱贫攻坚战信心满满。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曼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出列35户133人;2018年计划脱贫出列97户341人,2019年计划脱贫出列3户8人,实现整村脱贫。
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乡村社会急剧转型,总体格局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乡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已转变成市民,其主要任务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的问题;一些乡村经过合并,人口迅速集聚,生产形态与生活形态相对分离,其重点是如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建设现代化特色村镇的问题;一些乡村已经消失或正在消亡;还有更多的乡村融生产生活于一体,农业耕作依然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将会成为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记得住传统和乡愁的美丽家园。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加以部署,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42〕,更不能让农村衰败;既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工业化,也要坚持城乡融合,解决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当然,乡村振兴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目标要求,乡风文明是保障、文化复兴是基础。纵观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变迁,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城市消费主义的兴起及“乡村城市化”对乡村原生性文化的肆虐所致乡村生活意义的被消解和乡土文化价值的被抽空,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重要根源。〔43〕因此,乡村振兴,文化要先行、自信是关键,保护传承和创新提升农耕文化遗产是其必然路径选择。而作为农耕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的当代复兴,不仅仅是传统的延续和复兴,更是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国家要素与传统乡村共同体重新整合,市场要素向乡村社会逐步渗透过程的真实写照。〔44〕并且,民间信仰经由创造传承它的乡村民众的创新转化,可以成为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乡村建设的重要资源和提升农民主体性、聚合性的精神力量,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
在传统社会,较之其他区域村落的民间信仰,以X村为代表的中国菇民区核心地带的菇神信仰有着显著的独特性。一是鲜明的社会边界性。从可考史料和田野调查看,菇神信仰多分布于菇民区核心地带,其他区域尚未见有菇神崇信现象;菇民在异地开山育菇设神坛,也仅限于菇民群体祭祀,且菇民返乡即带回神像,不向其他群体扩散。二是紧密的生产关联性。菇神信仰是山区农耕文明发育的产物,是百姓靠山吃山的精神文化源头,因此菇业发展不间断,菇神信仰不间断,香菇种植在哪里,菇神信仰在哪里,菇民进山、返乡都有菇神像随行,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祭祀,属于典型的“口袋信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菇神庙“庙股”〔20〕的设置,将菇民利益与庙宇的荣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菇民与菇神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关者”。三是突出的整体协同性。在这一信仰体系中,无论人际、区际、神际以及人神之际都具有鲜明的共同体特征。比如,信仰者有高度一致的信仰诉求,深山菇寮由诸户共建共设神坛共同祭祀,大型菇神庙则由各地菇帮共同兴建、庙会诸事宜由各地菇帮共同议定,体现了人际、区际间极强的协同性;又如,菇神非一神专属,系多神共享,而这多神之间确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实为一个香菇神灵系统;再如前文所提及的“庙股”的构想与实施,更将人、村、神以及菇业的发展紧密地团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四是明确的价值导向性。崇信菇神既是为了获得神灵庇佑,也是为了启示人们谨循菇业操守、传承香菇栽培技术;建庙既是为了共同祭祀,也是为了创建一个共商议事、共享信息、传授技艺的公共场所;〔21〕每年定期举办的庙会既是为了娱人娱神、和谐乡里,也是为了搭建一个交流制菇技术和菇市行情、商议菇业发展大计的平台,几乎就是一个传统版的香菇产业大会。五是丰富的文化延展性。以菇神信仰为源头,以菇民生存体验为积淀,在菇民核心区地带的民众创造和传承了大量的、多样的民间文化,主要包括(1)武术文化——菇民拳和菇民凳花、扁担功等;(2)戏剧文化——二都戏(菇民戏);〔22〕(3)民间文学——菇山谚语、菇民“山寮白”〔23〕和民间故事;(4)音乐文化——《菇民拜年歌》《菇神颂》等;(5)医药文化——菇山实用中草药等。
(二)X村传统信仰的当代变迁与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制度、新道德、新文化、新秩序的影响和带动下,菇民区核心地带的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权力量强力向村落延伸,改变了传统时期“没有一个朝代的官府衙门能将远离市镇中心的菇民组织起来妥善管理”〔24〕的局面;集体化作业方式,改变了传统时期小生产性家族(庭)模式下个体相对自由的状态;加之,主流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传统信仰受到了深刻的冲击,大多村落的菇神殿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损毁,或改为他用(如村队的工房、灰铺以及乡或村级的办公场所等),神像多被捣毁或被村民“私藏”,〔25〕公共祭祀几无踪影。然而,菇神信仰并无中断,因为新的村落权力结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及新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不能改变这里百姓“菇民”的身份,他们依旧每年秋去春归、别妻离子,如候鸟般分散在边远深山育菇护菇,菇寮神坛依旧、香火依旧,其实,这就是菇民的生活图式,也是他们在公权力所不能及的深山菇寮作业赖以平衡和协调各种关系的唯一依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间民俗文化普遍复苏并广泛地形成了民间信仰的热潮。在菇民区核心地带,传统信仰——菇神崇祀及其相关文化形态再度回归公众视野,由复苏而走向复兴:人们逐渐从神权迷信的观念束缚中摆脱出来,菇神信仰的价值不断“再发现”,实现了由“民间宗教性祭祀活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文化资源”→“文化遗产”的多级提升演替。与之相适应,基层政府的管理方式经历了“强力清除”→“说服制止”→“政策规范”→“价值引导”的转变。总体来看,当代民间信仰的变迁与传统村落的转型发展同频共振,所谓“复兴”,其实就是乡村生活本质的回归和乡村价值的再审视、再发现。以X村为例,以“五显庙”为中心的村落信仰的“复兴”与新型村落共同体建设和村落经济社会全面升级互为助力、紧密关联,大致可从以下三个阶段略加考察。
第一,“五显庙”的恢复与村落共治体系的生成(1982—2000)。这一时期最核心的事件是“公社的退出”与庙宇理事会的重建。因X村五显庙建筑精致、规模宏大、结构合理,人民公社时期一直被征用为公社机构的办公场所,1982年前后,当地人民公社趋于解散,在村内外菇民的强烈吁求和原菇帮骨干的组织策应下,五显庙迅速得以恢复,延续了200多年的“菇民狂欢节”也随即回归。当然,在这过程当中的“各路精英”〔26〕也很快得到了村民的普遍认同,成为应运重生的庙宇理事会的重要成员。庙宇理事会实际发挥着庙宇管理值守、庙会活动组织、“庙股”〔27〕管理使用等作用,以及菇业相关信息联络发布、行业自律管理、菇民利益调处和纷争调和等类似于行业协会的职能,与新生的村民自治委员会相互激励,并行不悖地推动着村落社会新秩序的建构。
甲状腺平扫CT示:甲状腺右侧叶背侧占位,考虑甲状腺腺瘤或甲状旁腺腺瘤,建议进一步行增强CT检查。腹部增强CT示:1.右肾上腺旁团状阴影,考虑肿大淋巴结并钙化;2.考虑右肾盏内小结石;3.双肺下叶坠积效应,肺大泡。上腹部MRI示:胰头、钩突处、胰颈、胰颈胰体交界处多发占位,考虑胰岛细胞瘤。
〔27〕这时候的“庙股”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仍然保留着的大量的“菇寮”开设的庙股;二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村落内部发展出许多大小不一的香菇企业,这些企业也依照菇寮庙股模式,每年按利润的一定比例(一般为5%)无偿上缴到五显庙理事会,供庙宇修缮和举办活动之用。
第三,菇神信仰走出去与传统村落社会的升级(2008—)。近十年来,随着香菇栽培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升级,X村民众进深山育菇的越来越少了,而菇业却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产研销游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格局,村域范围建成了华东地区最大的夏菇生产基地,培育形成了“菇民中草药基地”,村落发展成为菇民区地带最主要的香菇文化旅游基地之一,村民经营的菇行遍布全国各主要食用菌市场,由于经济的活跃和城乡人员的加速流动,特别是一批中高端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流入,〔30〕X村产业兴旺、文化兴盛的态势加速形成,菇神信仰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传播和升华。2008年,因菇神文化的声名远播和共同信仰的情感链接,这个偏远的山村,迎来了台湾菇类发展协会等众多民间组织的慕名来访,并欣然接受了台湾埔里镇菇民拟将五显庙菇神分灵至埔里受奉宫的决议,开启了菇神文化走出去的新起点。此后,每年都有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及日、韩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区)的食用菌专家、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负责人和菇民代表等前来共祭菇神、共商合作发展,为此,X村一域还被命名为“中华香菇科技与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为菇民区继续推进产业转型提升和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动力,也为增进海峡两岸菇民交流沟通搭建了桥梁。〔31〕“以X村为示范,充分发挥生态优势,以传承香菇农耕文化为重点培育绿色产业基地品牌,打造中国古村落升级版”,在2017年菇神庙会暨毗邻三县乡村香菇文化节上,当地党委政府对X村的发展之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被视作应当坚持和广泛推进的方向。
三、“让乡村回归乡村”:现代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与乡村振兴之路
“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32〕纵观近代中国,经济滞后、政治薄弱、内外交困,为图国力尽快复兴,实施“赶超型发展”和“偏向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成为新生政权的重要发展路径选择。由此,国家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化高歌猛进,同时也加速了城乡资源的单向性流动。长期存在的乡村基本生产要素(如劳力、土地、资金等)的净流出,使传统乡村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空心化”“原子化”“荒芜化”,部分乡村公共服务残缺、产业颓废、小官巨腐、文化式微、伦理道德失落等衰败景象不时引起人们的焦虑。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和激进的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国家层面提出并实施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试图和谐城乡关系、改善三农境遇的重大政策举措。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强力推动和主导下,广大乡村的资金输入显著增长、基础面貌明显好转,“道路变宽了”“房子变新了”“村落更整洁有序了”,但传统村落劳动力净流出有增无减,乡村“去精英化”现象凸显,民间文化遗产还在不断被销蚀,新农村建设依然常常陷于“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窘境”之中。谁的新农村?新农村为了谁?主体性不充分的乡村建设必然导致事实与价值的偏离,甚或使人们更趋零散化,“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真切联系,无法将此刻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33〕。
“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34〕其实,每一次社会的巨大转型都是从演绎传统和认识传统开始的,它就像是一次新的生态演替,在社会文化领域都会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35〕深入体察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的变迁,在总体性上,并没有离开乡土文化传统,而是在运用乡土文化传统,也没有离开转型社会中的乡村精英,而是在不断地接纳新型乡村精英,将传统的神圣仪式与当代的生产生活结合,使传统信仰活动既有历史的意蕴,又有当代气息,并广泛渗入现代市场化要素,既包含着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审美需求,也体现了乡村民众的一种文化自信和对待自己文化的情怀,代表着转型中国乡土民众的文化自觉与追求。因此,当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复兴,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累积和个体性多元化需求增长所致,也不能单纯地将它视为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和旧观念的回光返照现象,它或许与中国乡村的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或将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未来趋势。以X村菇神信仰为例,这种趋势初显,路径亦已逐渐清晰,其目标指向即是重建乡村自信,“让乡村回归乡村”。
第一,民间信仰复兴,重建乡村人文系统。乡村是人文的源头,孕育和承载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村落形态以自然生态为核心、以自然过程为重点,是先民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寻求人地协调共生模式的最优路径,协调的自然生态伦理、持续的生产价值伦理、和谐的生活伦理构成了传统村落社会理想型人文生态系统。〔36〕封闭性和内聚性是我们对传统村落的基本印象,也正因此,使得这一理想型人文生态系统长期稳定,而内含于其间的宗族、血缘、信仰是维系其整体性、持久而恒定地发生作用的源动力。近代以降,商品经济的活跃、国家权力的下沉,对传统乡村固有的经济秩序、权力结构、文化形态、社会关系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乡村人文系统不断被解构与重建,民众的文化人格常常无所适从。观照X村的当代转型变迁,唯有传统信仰是维系初级社会关系、调和新社会关系、生成村落文化生态新平衡的内源性基因。它仿佛是一粒不灭的种子,适合乡村的土壤,在不断演替的乡村文明的浇灌下,总是以新的形式重新生长,并成为链接“旧文明”、再造新文明的基础。重要的是,“就像生物学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存留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37〕
第二,民间信仰复兴,促生乡村社会内聚。当下乡村,离散似乎是一种常态,学者们常用“原子化”来形容,并借此表达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忧虑。乡村何以离散?传统人文生态系统的解构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更直接深刻的原因在于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而不在于城乡差异,以至于出现“城不城、乡不乡”的乱象,乡情乡韵远去、乡村品格渐失。所谓和而不同,城乡差异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中文化差异是最大的差异,文化差异也是乡村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古人讲,“礼失求诸野”,而在当下,包括传统信俗在内的中华农耕智慧在城市已经消失殆尽,但在广大的乡村还有或多或少的存留,这就是我们要保护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从乡村建设角度来看,其不仅是遗产,还是实施乡村振兴的资源或基础。〔38〕其实,民间信仰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既是功利的,又是理想的。比如,庙宇是传统村落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建筑,所奉之神灵是与村落公共精神高度契合的产物,祭祀仪式是乡村民众的一种公共表达方式,村庙管理与活动组织则是充满草根智慧的村落公共民主实践,等等,这就意味着作为典型农耕文明形态的传统民间信仰可以成为提升社群凝聚力的一种方式。X村菇神信仰在当代的传承演化进一步表明:某些传统信俗的复兴,可以激发乡愁情结,吸引并留住返乡人口,增强村落内聚力,共同建构具有向外交流能力的特色农耕文明体系,促进生成乡土人才回流与吸纳机制。为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国家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既要切实传承保护好传统信俗等农耕文化遗产,也要推动合理适度利用,“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39〕。
对比表中的数据,还可以发现男单和5人项目在动力性力量难度动作的选择数量上差异较大,因为参加男单的运动员上肢和核心力量等身体各方面素质都比较好,而5人项目为了难度动作的整齐和完成质量,考虑到身体素质的差异,相对来说对难度动作选用会降低一些,因此在动力性力量的选择上会受限。
〔29〕《图式理论》,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5%BC%8F%E7%90%86%E8%AE%BA/9942609?fr=aladdin,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15〕参见《五显庙志》,载龙泉市民宗局编:《龙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工作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5年。
四、小结与反思
2.2 水土流失、地质灾害 水位的周期性涨落对库岸的侵蚀、冲击和浪淘极大地破坏了土壤的结构和稳定性,可能引起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加上雨径流的冲刷,使得表层土壤水土流失严重。
回溯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史,从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计划到乡村振兴战略,始终离不开乡风建设,始终绕不开民间信仰问题。事实表明,如何对待民间信仰,实际上是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农村和农民的问题。百年乡村的兴衰起伏更预示我们,对待自有的文化传统,应当有足够的尊重,要辩证地看待它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既彰显其积极价值,也抑制其消极影响。观照当下,要注重引导、创新载体,弘扬民间信仰复兴正能量,带动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之路。同时,也需要谨防一些不良文化倾向的影响:一是要防止民间信仰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过度渲染民间信仰的原生性氛围和神秘性色彩,固守传统信仰的历史样态,过分夸大传统信俗的社会功能,都可能导致对传统的误解、迷信,容易使人们忽视文化的流动性本质,死守传统规制,形成保守、僵化,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的异质性思维,成为乡村振兴的思想观念障碍。二是要防止民间信仰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一方面,一些文化学者常以精英情怀揣度之,或对一地一域的传统信仰做出合乎理论预设的学术推演,进行臆想的价值评判与意义建构,或借其文化精英优势试图为地方民众提供一套民间信仰活动的“本然图式”,甚或直接参与主导地方民间信仰活动。其实,最真实的民间信仰就根植于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中,简单朴素、并无常态,刻意的阐释、描摹,或规训之、强化之,实与民间信仰的本体性偏离。另一方面,主流精英的偏见,即把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传承作为净化乡村传统文化的过程,以主流文化标准来辨识、评判民间信仰,剔除其间可能存在的“杂质”,这或将导致民间信仰文化的支离破碎。〔45〕三要防止民间信仰文化资本主义倾向。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力,但重要的是,不能以经济资本的方式消耗它。然而,由于经济利益驱使,过度开发和滥用民间信仰文化资源的情形并不鲜见,以至于乡村传统文化经济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甚至崩溃,使一些农耕文明遗存受损耗或损毁。此外,一些民间信仰资源丰富的传统乡村还常常被“成功旅游学”包围,〔46〕“庙宇承包”“香火经济”等,也严重侵蚀传统信仰文化,与保护传承农耕文化遗产渐行渐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道而驰。
注释:
将试验一所得数据制成时间函数和上拉杆角度(如图5所示)、上拉杆垂直力(如图6所示)、上拉杆水平力(如图7所示)、右拉杆垂直力(如图8所示)、右拉杆水平(如图9所示)、左拉杆垂直力(如图10所示)及在拉杆水平力(如图11所示),从上图可以看出,当毒饵喷撒机做提升试验时上拉杆角度在(32°~68°)的范围内。上拉杆垂直力在(0~7 285N)范围内;上拉杆水平力在(0~5 189N)范围内;右拉杆垂直力在(0~5 721N)范围内;右拉杆水平力在(0~5 575N)范围内;左拉杆垂直力在(0~5 238N)范围内;左拉杆水平力在(856~5 863N)范围内。
图4右上表示LNAPI_SA对LNAPI_SA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CPI给农产品价格一个冲击,在第1期时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做出响应,影响为0;之后逐期增大,在第2期与第3期之间达到最大正效应;随后农产品价格对CPI冲击的响应效果逐渐减弱,至第4期(1年)时影响减小到0后继续下跌,产生负效应;在第10期时再次变为0;之后趋于平稳。这说明CPI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响应的时滞为1期(3个月),而CPI的变动需要3个月左右时间后在短期内对农产品价格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很小,在之后第2年、第3年可能会对农产品价格产生负影响。
〔1〕张祝平:《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4-98页。
〔2〕〔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欺凌发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学校老师及家长不易关注的时间段。其中48.4%的学生认为校园欺凌主要发生在课间休息时段,认为发生在上学或放学路上的比例为23.9%;发生在周末或节假日的比例为27.7%。
〔3〕李亦园:《宗教与神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4〕X村五显庙初建于明神宗15年(公元1588年),扩建于清康熙11年,占地面积1087.7平方米,是标准的江南寺院建筑结构,整个建筑整体和谐、设计精巧、造型别致,目前已成世界香菇文化遗迹之一。参见龙泉市民宗局编:《龙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工作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5年,第74页。
〔5〕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宋颖:《民俗主义与学术反哺——以福建外碧村的民俗生活实践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1)测量放样。以施工图纸为基准,计算出放样点的具体参数,并在现场进行定位。应使用红油漆对具体点位进行标识,特殊情况下可以绘制拱部“红线”,以此达到光爆效果。使用钢尺对炮眼孔位进行测量,并以设计图纸为基准做好爆破孔布设工作。适时对断面间距以及断面对应点数进行测量,当出现洞轴线偏离基准水平或顶拱变形等现象时,应对爆破参数做以适度调整。
〔7〕范玉刚:《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核心价值观的润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3期。
〔8〕据当地村干部介绍,民国时期实为一个行政村,即X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村落人口的增长,被划分为两个行政村。为便于整体性分析,本文延用X村称法,所指均涵盖现两村的诸要素。
〔9〕据2017年底当地统计数据,X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000元,同比增幅9.8%,均高于周边三县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和同比增幅7.3%的水平。这对于一个以生态农业为主,交通、资源受限的偏远山村而言,确属不易。
〔10〕著名食用菌专家、香菇文化学者、中国食用菌协会香菇分会名誉会长张寿橙先生认为,X村一域堪称“中华香菇历史与文化第一乡”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菇神庙最集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参见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75-76页。
〔11〕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476页。
〔12〕笔者在X村一域及浙闽交界其他一些香菇栽培主要区域调查时发现,各地菇神庙所奉神灵众多且杂乱,但几乎所有菇神庙都供奉有五显大帝、吴三公、刘伯温,众多庙宇将五显大帝供奉于大殿中位,吴三公和刘伯温供奉于两侧,在二神边上还常见有招财童子、进宝郎君、土地公等诸杂神,各庙供奉情况各异。据地方香菇文化学者介绍,五显大帝传说为春秋时代骆氏五兄弟,被菇民视为香菇人工栽培技术“砍花法”的发明者,也是香菇生产技术的传扬者;吴三公为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人,浙闽交界龙岩村人,是人工栽培香菇特殊生产技艺——惊蕈术的发明者;刘伯温则是为菇民区核心地带,即X村毗邻三县民众讨封到了香菇生产的地域专属权,被当地一些乡土文化学者推塑为“中国香菇专利权创始人与鼻祖”而为菇民崇信。简言之,这些神灵都是为香菇业发展作出贡献者中的突出代表,是农耕文明的实际推动者,经由朝廷敕封或地方文人的描述加工而为百姓惦记、代代相传、不断获得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尹福生:《龙泉龙井五显庙的香菇庙会调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51-53页。
〔13〕指规模远大于村落神庙,辐射范围广泛,由多地菇民合力兴建的信仰场所,既为祭祀之用,又为菇民议事之用。
〔4〕〔44〕杨小柳、詹虚致:《乡村都市化与民间信仰复兴——珠三角民乐地区的国家、市场和村落共同体》,《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
第四,民间信仰复兴,夯实乡村共治基础。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文化现象,具有消融冲突、凝聚人心的潜在功能,敬畏自然、崇德敬祖、协调身心是其与生俱来的核心品质之一,可以成为整合社会秩序的力量。在传统中国,在国家权力少有触及的传统乡村,民间信仰作为非制度化力量往往发挥着制度性权力的作用,村庙管理组织实际上代行着制度化组织的功能,成为村落社会的重要议事机构和决策机构,在调和村落社会矛盾、维护村落共同体利益和规范村落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典型的如上述X村五显庙理事会,集村落政治组织、文化组织、经济组织于一体,其成员多是能够组织乡民生产、协调乡村内外诸关系,在维护和发展社群利益方面有所贡献的领袖型人物。在当代中国社会,乡村民众的诉求日趋多元,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日趋强烈,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交错复杂,现代性的国家力量迅速渗入乡村并对其进行反复的整合、计算、分类、解码和信息标准化处理,〔41〕政府成为了乡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的主导型制度化力量,而民间信仰则遵循自己的文化逻辑,在复兴进程中不断进行着“国家在场”条件下的适应性调适,并行不悖地在新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发挥其非制度化功能。同时,民间信仰的复兴传承了草根自治的文化基因,层累着乡贤文化,厚实了村落共同体与精英再造的文化土壤和经济土壤,催化现代民主国家意义下建构的“村民自治”与在传统农耕文化中孕育生成的“社会自治”寻求并轨相融,既夯实了乡村多元共治的基础,也为村民自治更好落地生根创造了必要条件。
〔16〕因菇民上山种菇,冬去春回,家人分离,缺少传统年节习俗时空条件,每年菇神庙会实际上成为了他们最大的节日,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最好时机。
〔17〕“跤垟源”,指X村一带的村落。参见项吴菊、刘永善等:《触摸世界香菇文化历史源头》,《丽水日报》2009年8月20日。乡土学者尹福生先生研究也指出,自古以来,X村一域每年秋冬有70%左右的劳力赴闽、赣、皖等周边省份深山老林中从事香菇生产。参见尹福生:《龙泉龙井五显庙的香菇庙会调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
〔18〕 据村干部介绍,村民中一直传诵着村里历史上做菇发财的典型故事:“做客鼎好是下田,里村老周发大财,外村老王做好客,请脚每年两百余”。“里村”“外村”,当地人统称下田,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区域,“请脚”就是“请帮工”,主要反映历史上村里香菇种植规模大,发大财的人多,而且乐善好客,村民和谐,其乐融融的情景。另有周氏后裔村民反映,村民传诵的“老周”是其曾祖父,是当时挣钱最多的村民之一,一直到他祖父这一辈,家里还有很多钱。访谈对象:张某,40岁左右,X村干部;周某,40岁左右,X村所在乡卫生院医生;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1日;访谈地点:X村;访谈人:张祝平。
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和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教学教研活动的开展。因此,高校行政管理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笔者访谈笔录。访谈对象:周某,40岁左右,X村所在乡卫生院医生;访谈时间:2018年3月3日;访谈地点:电话访谈;访谈人:张祝平。
〔20〕古时,菇民外出进山种菇通常以菇寮(菇民在山上搭建的简易房子,用于存放香菇并饮食起居和供奉菇神)为生产单位,一个菇寮一般5~6个劳动力。为保证村落菇神庙修造和庙会活动资金使用需要,各菇寮均开设庙股(亦称菇神“干股”),即在收成分配时,菇神庙无偿享有利润分红(半股至一股),由菇神庙董事会代管统一用度。据吴其林先生研究,香菇丰收之年,扣除成本,一个菇寮收入香菇约为10担,按1924年广州香菇收购价,菇神庙股以半股计,“干股”分红计银100圆以上,然集数百上千菇寮之“干股”分配,菇神庙收入极为可观。也因此,菇神庙修缮及庙会活动等,无需民众再另行捐资。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
〔21〕据笔者观察与访谈,新中国成立前,X村毗邻三县大型菇神庙内专门设有“三合堂”“菇帮共厅”等颇具传统政治色彩的议事场所,每年6~7月份,三县菇民领袖常聚合于此,对重大事件进行审议与协商,作出共同行动或一致对外的决定。当然,菇神庙场所宽阔,建有戏台和广场,也成为返乡菇民休闲看戏、分享信息及练拳习武、传授菇山谋生特技和防身技艺的重要场所。
〔22〕发源于X村毗邻三县“二都”一域,形成于明中叶,原为菇民“迎神会”祷告仪式中的演唱小调,后融歌、舞、演、剧为一体,发展成为菇民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独特剧种。参见田中娟:《浙西南菇神庙会的祭祀仪式与仪式音乐》,《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3〕相传,因神之旨意,香菇种植技术专授于X村毗邻三县百姓,菇民为了防止技艺外泄,约定俗成了一种独特而神秘的语言——“山寮白”,亦称“菇山话”(即菇民们在菇山上劳作时交流的语言),它没有文字。据张寿橙先生研究,“山寮白”这种行业暗语,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极其少见,或惟菇民所独有。
〔24〕舒喜春:《香菇 为中华农业文化添光彩》,http://lqnews.zjol.com.cn/lqnews/system/2012/02/13/014737482.s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25〕据笔者调查,其时,偷偷保护或存放菇神庙中神像的村民不在少数,一是基于对菇神的深厚情感;二是确有实际需要,凡菇民入山返乡都要暗自祭拜,在菇民看来,这是基本的“礼数”,不能丢。也可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
〔26〕受访者如是说。主要包括原来的菇帮领袖、乡土知识分子、宗族中的长者、新兴小企业主等在庙宇和庙会恢复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谋划者。
第二,知识精英的反哺与产业文化体系的壮大(2000—2008)。长期以来,菇区民众以自己的质朴、勤劳维系和发展着自有的独特的农耕文明形态,改革开放使乡村再次焕发了生机,山村不断生发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在以工业化、粗放型、快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改革前期,相对于所在省份的平原沿海区域,X村一域的发展已然“滞后”了。〔28〕山门之外的世界给菇乡民众带来了强烈冲击,菇神信仰作为村落文化传统——民众世代践行的文化图式,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外部信息的选择、提取、加工以及最终的行动取向”〔29〕。村落发展很快又回归理性轨道——“靠山吃山”,传承、转化、创新菇神文化成为普遍的行动选择。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发端于农耕文明的非遗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X村厚重的传统信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乡土情感的知识精英的重视,他们或直接参与其中,或为提升其价值、扩大其影响奔走呼号、著书立作,直接推动了菇神庙和菇神庙会的转型升级,五显庙入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菇神庙会及其衍生的诸民俗活动相继列入各级非遗名录。经知识精英的建构与创造,X村的传统信仰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创新性发展之路——集民俗祭祀、文化展示、学术交流、产业推进、生态休闲等于一体,传统与现代相衔接、官民商学互动、大传统与小传统交融,在助推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和文化经济的兴起中作用日渐显现,成为毗邻三县体系最完整、产业融合度最高、最具知名度的乡村文化品牌之一。
〔28〕2000年,X村所在乡镇被列入省“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系所在省份相对贫困的地区。
《淮南子·道应训》中的记录和《列子·说符》中的内容大体一致,只是多了老子的一句评价“故老子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而这段耳熟能详的选千里马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无非是要重视事物内在的本质,也就是原文中说的千里马“其内”(即神韵),而忽略“其外”。刘勰引用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说明在文学创作时也应该注重内在的本质,不能一味注重大文体的创作而忽略了小文体的存在。
第三,民间信仰复兴,催发乡村经济活力。文化也是生产力,传统民间信仰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这是已被人们所广泛认知认同的。或助力经济发展,抑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人们对于传统信仰文化资源的资本化意义,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过。在近40年民间信仰复兴的进程中,大量的民间信仰经济化的探索实践表明,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对于活化生产要素、促进产业发展、活跃乡村经济具有独特功能和积极作用,同时也有益于增进民众对自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丰富多样性的认识、理解和保护。〔40〕尤其如菇神信仰等具有鲜明农耕特色和产业背景的民间信仰,源于乡村民众自我的生产生活体验,与现实村落经济发展契合度高,它的传承复兴实际上已成为厚实传统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底蕴、延续产业文化血脉、传承发展产业经济伦理的内在要求,并在客观上助推了乡村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村落经济的普惠性增长,同时,也在不断唤醒、激活和提升人们的文化主体性与经济主体性,逐步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在地化的生态型经济系统,催生出自己的美丽乡村的“生态经济学”。
〔30〕包括前文所述的香菇技术专家、文化学者、体制内的民俗爱好者,以及来此经营发展乡村生态游的企业主和到X村一域休闲度假的城市知识分子。
〔31〕经双方多次商议,于2011年8月,36位埔里菇民心怀虔诚、千里迢迢专程来到X村五显庙,将菇神分灵至埔里受奉宫,成为在台湾安家落户的第一尊菇菌业神明。参见吴向东:《两岸菇民同庆菇神吴三公宝岛“履新”》,http://lqnews.zjol.com.cn/lqnews/system/2013/10/14/017141119.s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32〕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33〕陈旸:《詹姆逊关于后现代理论的探析及其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5日,第1版。
〔35〕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3)标准先进性欠缺。受生产条件的约束,使得一些材料采用较低的技术标准,无法彻底满足发动机设计、制造和使用的要求。
〔36〕王云才、石忆邵等:《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7〕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式中,n为参数,通常n=3[19]。弹体顶点O的压力可由修正的Bernoulli方程计算得到[19]:
〔38〕方李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39〕《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浏览日期:2018年3月17日。
DEDS的仿真模型主要有面向事件、面向活动和面向进程3种,它们各有不同特点,我们可根据不同需要选择合适的仿真模型。仿真模型实现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建立仿真函数库。它的优点在于建模者可以专注于模型的逻辑关系而不必担心模型实现的细节,因此,仿真函数库的建立需要足够灵活,以保证其适用于各类系统的建模。它的基本功能模块包括:随机数生成、实体建模、运行调度、队列建模、仿真结果收集和分析。仿真函数库首先应有调用子程序或函数的能力,并且是通过参数传递来实现。其次,要有实时生成动态数据对象的能力和能够支持应用预编译模块构成的库[4]。
〔40〕张祝平:《论民间信仰文化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42〕韩长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第7版。
〔43〕沈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困境与重构》,《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4期;李晓明:《城市主义的肆虐与民族乡村原生态文化的际遇》,《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4期。
〔45〕张祝平:《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
〔46〕邱建生:《乡村振兴,别成为新一轮的折腾》,http://www.zgxcfx.com/m/view.php?aid=108161,浏览日期:2018年3月23日。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1.007
作者简介:张祝平(1975—),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民间信仰与农村社会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状况研究”(项目编号:16AZJ007)的成果。
〔责任编辑:刘姝媛〕
标签:乡村论文; 村落论文; 文化论文; 传统论文; 民间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学术界》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状况研究”(项目编号:16AZJ007)的成果论文;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