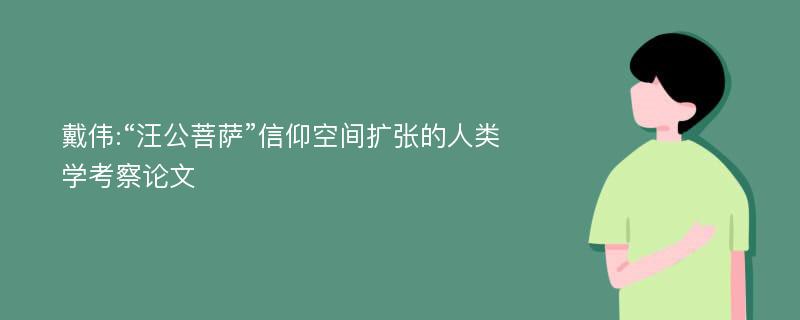
摘 要:从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社会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概念出发,以20 世纪80 年代民间信仰恢复以后的高湖村“汪公信仰”田野资料为基础,将信仰空间从“祭祀圈“到“信仰圈”扩张过程与“汪公信仰”发展历程相关联,通过对汪公出会仪式过程的描述以及对祭祀对象“汪公”从“私家神”到“村落神”再到“区域神”信仰空间格局扩大的研究,阐发地方性神灵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建构的积极意义,为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思考。
关键词:祭祀圈;信仰圈;私家神;村落神;区域神
序 论
要了解“汪公菩萨”信仰空间的产生与发展意义,需追溯到台湾学者对于“祭祀圈”和“信仰圈”概念的研究。最早用“祭祀圈”概念来研究台湾民间社会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他于1938 年在《台湾北部村落生活》一文中将士林地区的祭祀圈描述为“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1],这个概念的提出为后来其他的“祭祀圈”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台湾学者刘枝万、王世庆、许嘉明、施振明、林美容等也相继涉及“祭祀圈”研究。刘枝万在考察台湾“瘟神庙”时,将南鲲鯓代天府池王爷祭祀圈分为三圈:第一圈为核心圈,是信徒分布的主要区域;第二圈为信徒分布的次要区域,其信徒与代天府有分香关系;第三圈为外围圈,虽有王爷庙,但是与代天府没有什么联系。[2]王世庆以“祭祀圈”的概念来探讨树林镇之民间信仰的历史发展。[3]施振明提出“祭祀圈”模式不仅仅涉及宗教信仰的地域范围,而且还包含宗教活动组织。[4]许嘉明以“祭祀圈”概念来研究彰化平原地区名为“福老客”的地域组织,并总结地方性地域组织有3 个要素:移民史、共同的居住范围和共同的祖籍,[5]施振明、许嘉明关于彰化平原(又名浊水溪平原)的“祭祀圈”研究更多偏重于历史取向,他们通过彰化地区的移民史来了解“祭祀圈”的形成。林美容总结以上学者在研究社会组织时,着重从祭祀的地域范围、历史背景研究祭祀圈,或者从外在的政治、经济性因素加以功能性解释,或者从宗教和理念的层次追求象征性意义,忽略了社会组织本身之意义。[6]林美容由此提出“信仰圈”作为“祭祀圈”概念的完善和补充。林美容认为“信仰圈”为某一区域范围内,以某一神明和其分身为信仰中心的信徒之志愿性宗教组织。其以一神为中心,成员资格为志愿性,其成员分布范围超过该神的地方辖区。同时,林美容提出对于任何一个信仰圈而言,其一定是由一个祭祀圈逐渐发展而成的。[7]本文希望借助前面学者对祭祀圈与信仰圈的全面性研究,结合高湖村“汪公菩萨”信仰实际,充分认识高湖村“汪公菩萨”仪式活动恢复以来的信仰空间变化,并探讨地方性“祭祀圈”到区域性“信仰圈”的扩张过程对地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选取我院自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收治的80例宫外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经腹部超声确诊,按照平行对照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参考组各为40例。观察组:年龄23-40岁,平均年龄(36.25±2.52);孕次1-4次,平均孕次(1.76±0.55)次;其中“习惯性”宫外孕15例。参考组:年龄22-40岁,平均年龄(36.19±2.40)岁;孕次1-4次,平均孕次(1.80±0.56)次,其中“习惯性”宫外孕15例。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两组孕妇组间基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一、田野点介绍
高湖村位于皖南山区与长江南岸相接地带的H 县,这一带地势起伏,具有明显山区特点。该村东南部和西南部二处为隆起的高山,其间镶嵌一条濂溪河,该河源于泾旌界边境东流山,出濂长村,流经高湖蜿蜓北去。据《舆地纪胜》记载:东流山在“泾县南五十里,约高数百丈。唐末有逸士隐此称东府君,至此号东流山。”[8]“高湖”是上村“高湖”和下村“下湖田“的合称,因地形得名。上村成串,下村成朵。上村“高湖”,村后有一片高而平的湖地。下村“下湖田”,村边有一山丘,形似鹅鸭,山脚田畴平旷如湖,远观恰似鹅鸭下湖。
设土表覆盖水稻秸秆1 000 kg/667m2(处理1)、1 500 kg/667m2(处理2)2个试验处理,即每箱土表均匀覆盖水稻秸秆300 g、450 g;以不覆盖秸秆处理3为对照(CK),每处理3次重复。
按照2016 年的数据统计,高湖村面积9.6 平方公里,水田24,440 余亩,山场2,800 余亩。共有15 个村民组,总人口1,400 余人。村民姓氏大多为汪、徐、张、李四大姓氏。
同“无糖”一样,“无反式脂肪酸”的食品,要求每100克或l00毫升含量小于0.5克。“因此,‘无反式脂肪酸’产品并不是完全不含。”购买时要仔细检查成分表,若有“氢化油”,那么就说明存在反式脂肪酸。
近几十年来,汪公信仰的信仰空间经历了扩张,其仪式内容也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从以宗族为单位的“私家神”,到以村为范围的“村落神”,然后到跨村的“区域神”,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祭祀组织形成的祭祀场所构成了高湖村的信仰空间。随着仪式时间的延长,汪氏绕境的仪式范围已经到达邻近村落,但是汪华信仰的核心信仰空间依然是以汪氏宗祠为中心的高湖村,而且在今天,汪公会仪式内容中的一些核心环节仍然由汪氏族人所掌握。如为汪公沐浴更衣、祭品“会果”的制作,以及祭拜汪公时汪氏族人的优先顺序等。
在生计模式方面,高湖村山多田少,农业生产历年来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种植茶叶、毛竹,村内的养殖业主要为桑蚕养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高村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这种人口流出的倾向导致高湖村处于一种“空村化”的状态。由于村民的集体生活时间越来越少,所以村里人特别珍视“汪公会”祭祀的机会。用当地的话说,“出会那天才热闹呐”。
在民众信仰方面,高湖村汪氏族人于清朝时建造了宗祠,名为“汪氏宗祠”,当地人称为“汪公庙”。据村民汪洪亮介绍,其祖父曾经是“汪公庙”的管理者,他听其祖父说高湖村汪氏是汪华第八子汪俊①据《汪氏宗谱》,汪华娶有5 位夫人,生有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九子。九子之后发展繁衍,子孙遍及大江南北,成为江南一大望族。汪俊生有5 子:处默、处方、处忠、处思、处静。五支子孙主要分布在今天安徽省歙县、黟县、休宁、旌德、绩溪等地区。的后裔,他们从绩溪县移民至此建立宗祠。在高湖村民中关于汪氏宗祠的来源更具灵异色彩,据村民徐建国口述,绕高坦村而过的濂溪河上游深潭中每年夏天都有恶龙作祟,导致下游的高湖村庄稼颗粒无收,后来汪华神灵显灵,与恶龙在濂溪河畔经历一番大战,将恶龙斩杀于濂溪河旁。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汪华也是为了镇压恶龙,在汪华斩杀恶龙的地方建立了汪氏宗祠。20世纪80 年代,除祭拜汪公之外,出村水口处建有蔡伦祠,在历史上高湖村凭借盛产檀皮和水质优良,兴盛造纸产业,业主在农历九月十八都让纸棚停止生产,设香案祭拜蔡伦,祭毕,备酒食犒赏工人。但是由于造纸行业的国有化和大机器生产,高湖村的造纸棚纷纷倒闭,蔡伦祠由于常年未修,已于上个世纪80 年代末的一场大雨中倒塌。除此以外,土地神是高湖村民普遍供奉的地方保护神灵。在高湖村的每一个村民组,都建造了土地庙。每年农历正月初二、七月十五,高湖村村民都会到各自村民组的土地庙祭拜土地神,向其乞求富康、求学及第、求财求子。与汪公崇拜一起,土地神信仰构成了当前高湖村民俗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
“祭祀圈”向“信仰圈”的过渡是一个“动态”的扩张过程,“村落神”体现出来的信仰空间的特征弥合了扩张过程的特征。村落神是指一个村落的村民进行神灵信仰仪式性活动时而形成的祭祀范围。20 世纪90 年代到21 世纪初,该村的第二大姓氏徐姓、第三大姓氏李姓也加入到汪华信仰的仪式过程中。外姓人不仅可以在汪氏族人跪拜之后进行祭祀祈祷,也可以加入汪公“出会”的队伍,负责举旗、抬轿,扮演出会仪式过程中“护卫”的角色。在汪氏族人跪拜结束以后,外姓的女性和小孩也可以参与到跪拜仪式中。据村中老人回忆,在1995 年的时候,整个村将近270 户人家,其中汪姓占130 多户,徐姓和李姓加起来近110 户,其他姓氏如陆姓、王姓、钟姓加起来近30 户,当时徐姓的一位比较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过年串门的时候向汪氏族长提出申请加入“汪公信仰”的仪式活动,这位汪氏族长掌握了汪氏家族的家谱,而且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是他将汪公菩萨的雕像藏到了邻村山上煤洞里面,汪公菩萨才得以保存。所以他是汪氏家族里面最受敬重的人,扮演了“民间权威”[12]的关键角色。除此之外,在人民公社的时期,在该村的5 个生产队里,汪姓和徐姓经常被分在一起,在长期生产协作过程中,徐家已经成为了汪氏族人的“自己人”。再加上当时打工潮和当兵热现象的影响,很多汪姓的族人都外出打工和当兵,以及当时交通不发达等因素,很多汪氏家族中的青壮年在重阳节那天都赶不回来,在徐姓加入汪华信仰仪式活动之前,汪公会的活动已经停办了3 年。所以在经过短暂的商讨以后,徐姓加入了“汪公信仰”,并被授予请神的资格,在此后信仰空间的扩大过程中,李姓、汪姓、陆姓、钟姓也加入到“汪公信仰”。
综上,以高湖村所处的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区域人文状况为背景,结合“汪公会”具体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其以求吉纳福、驱鬼逐祟为目的的“汪公会”民间俗信之发生、发展,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之双重动因促使其信仰空间由“祭祀圈”向“信仰圈”扩张。
二、高湖村“汪公菩萨”信仰由来
汪华,字国辅,陈至德四年出生于古徽州汪村,贞观二十三年卒于长安。汪华一生最大的功勋在于他以主动归唐的方式化解了隋末混战的局面,六州地区人民都幸免于战乱之苦,使唐王顺利统一中原,客观上推动了中原文化与徽州地域文化的大融合。汪华起义以前,由于徽州地区山多地少,交通不发达,而且位于皇权统治的边陲,中原衣冠贵族在南迁过程中一直视徽州为“未开化之地”,将徽州人称为山野“细民”。同样,徽州原著人也留心提防中原人,域外矛盾也引发了械斗事件,汪氏一族是六州中南迁望族,所以在战乱抗争中汪氏“安民保境”口号深得徽州人心,迅速化解域内域外的双重矛盾,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和谐相处。徽州地域民风得到了亘古未有的统一,当地乡绅等精英人士对儒家礼仪文化的广泛吸纳净化了当地蛮夷风气,推进了中原移民在其他地域的本土化进程。汪华死后,徽州人为纪念汪华,建立社庙祭祀这位英雄伟人,并尊奉他为徽州地区的“保护神”。徽州百姓为纪念汪华的杰出贡献,每年都会举行“汪公会”会祭活动,几千年来,代代赓续,相沿成俗。
游神:重阳节当天上午九时九分,族长宣读祭文,正式出会活动开始,族长将汪公从汪氏宗祠中请出,由4 位族员抬着汪公神舆,其两侧有8 位青年作护卫。另外,在神舆前面,其他村民持“回避”“肃静”的金色仪牌为出会仪队开道。游神的起点为汪氏宗祠,出会过程中到达的第一个分祭台是汪氏族长家。出会队伍临近祭台时,此户人家需鸣炮迎神,并祷告,汪公菩萨到场后与神舆一起置于“八仙桌”上,祭祀家庭的“当家的”点烛焚香,屠宰家禽,并邀请所有亲戚好友一起叩首祭拜,其寓意是:秋收到家,感谢汪公菩萨带来的丰厚年成,并祈祷来年人寿年丰。家中成员在汪公面前依次以磕头、烧香、献酒之礼祈福保佑。汪公宝舆每到一农户家门前,整个出会的队伍会在此稍作停留并绕着这个农户家一圈,以示对这家农户的情况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且“施展法力”保佑这家人平平安安。家祭活动结束后,该户还要鸣炮,告诉下一户准备鸣炮迎神。在出会途中,汪公神舆会在村落学校门前落轿,保佑学子攀蟾折桂。
三、仪式的过程
准备:一般在重阳节前2 周左右,汪氏族长便会召集本村和各个临村的房支,商议筹备“汪公菩萨”出会的相关事宜,包括邀请外地宗亲、募集活动善款、安排出会路线、戏班节目等。近年,村干部也参与到邀请宗亲的过程中。汪氏族长固定担任祭祀的主持,指挥族员准备祭祀道具,包括一座六角香亭、三辆神舆、三面帅旗、三面令旗、三面万岁旗、十六面绣图彩旗、十六顶黄龙伞、三十二副锡制銮驾,还有香盘、花筒、签筒、玺印、令箭等等。
①使用BP神经网络对前三次总体数据进行训练,隐含层采用单层神经元,隐含层神经元的激活函数采用Tansig函数,输出层神经元的激活函数采用Purelin函数,训练方法采用收敛速度较快的Trainlm函数,调整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进行训练,随着神经元个数的增加,训练速度逐渐变慢,训练精度逐渐提高。
帕帕国没有学校,整个帕帕国就是一个大学校。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职业,有的当军人,有的当司机,有的当老师,有的当科学家……完全实行自治。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但是他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比在大人身边生活快乐、自由多了。遇到一些连总统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到“勇敢城”去找一台名叫“三瓣蜗牛”的大计算机。三瓣蜗牛的体积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那么大,外形像三只脑袋挤在一起的大蜗牛。它被放置在一个全是用金刚石做的、透明的、半球形的基地里面。基地的名字叫“三瓣蜗牛基地”。孩子们有了问题找三瓣蜗牛准能解决,另外,三瓣蜗牛还负责了整个帕帕国的安全。
请神:重阳前一天下午三时,请神的第一道仪式沐浴更衣。在沐浴仪式之前,汪氏族长要先请“外屋人”离场,将汪氏宗祠大门锁上。亲手给汪公沐浴的人,一般都是那些“心质好”的人,所谓“心质好”的人是指那些儿女孝顺、夫妻双全、家庭和睦的人。沐浴仪式如同过渡仪式一样,只有沐浴净身的人有权利给汪公菩萨沐浴,进入特纳所说的“阈限”[9]阶段,融入仪式团体中,而不被当作“外屋人”,之后为汪公菩萨换上还愿者送来的新袍。沐浴仪式完成后鸣“山门铳”九响,敞开祠堂大门,“汪家奶奶”会虔诚地把祭神用品放在祠堂中央的“八仙桌”上,恭候汪公菩萨。
祭祀:待族老将汪公抬上莲花宝舆后,全体汪氏族员进入汪公祠堂,开始祭祀仪式。正式祭祀分为“献菩萨”和“拜菩萨”两个流程,“献菩萨”有燃香烛、焚香、献祭品等环节,祭品有“会果”、发米、八宝菜、“欢团”“水晶糕”“九将糕”、蒸米饼、踏煎饼等。“拜菩萨”先由汪氏家员进行跪拜,后由其他村民进行跪拜,跪拜过程中,男女一般分开,男性一般单独跪拜,而女性和小孩一般是以集体的形式跪拜。祭祀完毕,再鸣“山门铳”。
由于史料所限已无法得知高湖村汪氏宗祠建立的具体年代,据村民口述,汪氏宗祠是汪华第八子汪俊的后裔从绩溪移民至此所建。由于“汪公会”停办时间长,很多关于建国之前“汪公会”仪式事项,高湖村绝大部分老人都已经不知晓。据族长汪长青介绍,建国以后,由于国家视民间俗信活动为“封建迷信”,1949 年11 月,由小塘村民组十余名汪氏宗亲将汪公菩萨恭请至小塘学堂,并存放于学堂阁楼处。1966 年下半年,迫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压力,该村民组外姓人提出毁掉菩萨,汪氏族人大多不愿看着菩萨被毁,由汪廷芳、汪廷龙、汪廷虎等十余位宗亲,在一天傍晚六时许将3 座菩萨藏于村后山上一废弃的煤矿洞口,并做了必要的伪装,菩萨才得以逃过一劫。1979 年民间信仰活动恢复,由小塘汪氏为主,恢复了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出会。1985 年左右为防菩萨被盗,村民将菩萨从学堂阁楼请回高坦汪氏宗祠,并坚持每年按时出会至今。
总祭:在分祭台祭拜仪式结束以后,整个出会队伍前往汪氏祠堂旧址举行总祭仪式,祠堂旧址位于村东南部的一块空地,相传汪华在此斩杀作祟恶龙,后人为纪念汪华,也是为镇压邪灵,每年在此进行总祭活动,祈祷风调雨顺,禳病祛灾。
中国竹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集约种植单一竹种,这会带来很大的生态风险,使竹林更容易受到病虫危害。比如在安吉县,由于大部分人主要依靠竹产业,这种状况已很难扭转。在建筑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大量引进不适当的建筑类型和外来材料,从而放弃了传统的建筑形式,使得乡村景观的旅游吸引力大大降低。因此,新的批判性建筑必须考虑当地的历史与气候等条件,但也不能仅仅模仿传统竹建筑,也要满足当地居民的现代生活需求。
私家神是指单氏宗族感谢祖先庇护进行神灵信仰仪式活动而形成的祭祀范围。恢复初的“汪公菩萨”祭祀圈,汪氏宗族通过在村落经济文化资源的优势将信仰空间私有化,彰显其宗族力量。汪氏宗族笃信其祖先神灵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互感,将内在的祖先崇拜外化为具象的祭祀活动。恢复初的“汪公菩萨”祭祀圈与汪氏族员居住地是较为重合的,加上厚重的宗族历史脉络,汪氏族人利用宗祠的空间优势和宗族的历史底蕴,将此时的“祭祀圈”建构成带有家庙性质的信仰空间,实现宗族与庙宇的结合。除了祭祀的范围以外,此时“祭祀圈”内的游神路线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出会的第一个祭台必须是到达最年长的汪姓家,然后随着河流自西向东的方向,依次到达村中汪姓的各个祭台。此时在仪式的参与者构成上也具有明显的宗族色彩,整个仪式过程中的参与者必须是汪氏子孙中的男丁,汪氏妇女也可以参加,但是妇女只能参与制作祭品、祠堂清洁等杂务。此时的汪公会出会仪式体现了地方社区祭祀活动的规则性,也标志着人神互动背景中宗族认同的制度化。除此之外,祭祀时香火只能由汪姓提供,汪姓认为其他姓氏参与祭祀的行为是对汪氏菩萨的“分香”,“好运气会被其他姓的任带走”,所以不允许其他姓氏加入。在笔者的访谈中,许多汪姓访谈者一致认定,“汪公菩萨是汪家的,其他人不能来”。汪氏宗族通过限制其他姓氏的参与等方式树立他们在本村内的象征性权威,这是汪氏领地意识的一种体现,确保他们在地方秩序、地方经济资源的垄断性地位。私家神阶段的“祭祀圈”所形成的象征性权威和利益共享观念仅局限于宗族内部。以上是典型的“私家神”[11]观念的表现。
返位:出会结束后,汪公菩萨要回到祠堂接受供奉,供品有整只的猪、羊和时新瓜果蔬菜以及精心制作的“会果”,摆满祠堂正厅。汪氏族长将轿舆打开“请”汪公“回座”,然后再烧些香蜡纸烛。此时,参与出会仪式的人员享用家宴“十二碗”,家宴的座位依据亲疏、长幼关系排列,出菜的顺序按照地支排列:子—红烧蹄髈、丑—“凉拌”①“凉拌”取“两相伴”谐音,凉菜相拌,两人相伴。、寅—“三章汤”②“三章汤”意为约法三章,各有责任担当。、卯—“常汤”③“常汤”取“肠汤”谐音,意为亲朋好友,常来常往。、辰—粉蒸肉、巳—纯山药、午—糊粉、未—“子孙糕”④“子孙糕”又名“子孙高”,意为祈子祈福,步步高升。、申—红烧鱼块、酉—卤肉、戌—“小吵”⑤“小吵”又名“小炒”,意为生活中吵架拌嘴难免,但不可大吵,只能小吵。、亥—漂圆。宴席结束,族长宣讲汪公事迹和活动中要出演的节目,献戏酬神,此时汪公祠堂成为村落公共活动中心。
四、信仰空间的扩张:私家神-村落神-区域神
在集体化时期,汪公信仰中断。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控制逐渐放松,“汪华信仰”在高湖村也得以慢慢恢复,恢复后的“汪公菩萨”信仰空间,具有义务性、地方性的“祭祀圈特征”,伴随“汪公菩萨”信仰空间经历了一个从私家神-村落神-区域神的扩张,当前的“汪公菩萨”信仰空间具有志愿性、地域性的“信仰圈”形态。“汪公信仰”由“祭祀圈”向“信仰圈”的转变,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父系家族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亲属组织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志愿性地域团体对村落认同感的增强。这种转变不仅是信仰空间的扩展,也是重建后的汪公信仰的仪式内容和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嬗变的过程。
(一)私家神:血缘观念下的义务性与排他性
林美容在《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中指出“祭祀圈”以“祭拜多神、成员的资格为义务性与强迫性、地方性、以及节日性为其主要特征。”[10]林美容认为以祭祀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义务性与志愿性作为划分“信仰圈”与“祭祀圈”的重要标志。根据当时历史阶段下高湖村“汪公会”仪式活动实践,在高湖村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汪公菩萨”之外,“蔡伦神”和“土地神”也是他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祭祀圈概念的义务性体现在整个祭祀仪式对汪氏族员的到场都有严格的规定,任何族员的迟到或者缺席都会受到惩罚(罚款),以及祭祀费用都是由汪氏族员义务性地摊派。以上要素的具备体现了民间信仰恢复之初私家神信仰空间具有“祭祀圈”的特征。
利用现有光学技术、原子和腔场非共振相互作用等,五粒子纠缠态是可以制备[48];除酉变换U1外,本协议中的量子操作都是最基本且简单的酉变换,而U1可以分解为4个二阶酉变换,并且文献[10]已指出二阶酉运算是可以联合操控的,因此我们的方案是易于实验实现的。
江西省的网络教研平台早已经建立,它的目标是在全国实现最优的教研平台。通过该平台以及江西省网络教育资源的多方扶持,从而将信息技术对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为教师开展高效的网络教研提供支持,使教师的教学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系统采用了成熟的平台技术,系统设计采用了“平台+应用”的思想进行建构,从而使得系统具有高效性与灵活性。例如在教师的教研环节,可以设立评比板块,展示教师的教研成果,从而激发教师对于网络空间建设的积极性。
本研究选择采用SPSS26.0进行统计学分析,本研究当中的所有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村落神:血缘共享到地缘共享的变迁
围绕高湖村的汪氏宗祠而形成的信仰空间,从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扩张过程。民间信仰恢复之初“汪公会”信仰空间仍然仅限于本村汪氏族人,具有地方性“祭祀圈”的特征。90 年代以来,村里越来越多的外姓加入到祭祀活动中,祭祀圈得以扩大。近几年来,汪公会出会路线东起濂长村,西至小山村,南至里潭仓,北至上左家,共涉及8 个行政村,构成了“汪公菩萨”区域性“信仰圈”。
初次扩大后的高湖村“汪公菩萨”信仰空间,主要分布在高湖村领域之中,具体出会仪式的组织活动也是扩大到整个村落的范围,而村落内部一些其他姓氏以及作为“国家在场”[13]的村干部的加入,使得此阶段的信仰空间渐渐具有信仰圈“志愿性”特征,汪氏宗族在“汪公信仰”中的权威渐渐受到冲击和挑战,宗族色彩被极大削弱,“汪公信仰”的祭祀空间彰显出整个村落形态的文化象征。
(三)区域神:地域崇拜中的文化认同
林美容认为“信仰圈”是在“祭祀圈”的基础上,更大范围的区域性人群之志愿性的宗教组织,其志愿性为此阶段祭祀空间的显著特征。结合20 世纪以来高湖村“汪公菩萨”信仰的实际,志愿性主要表现在个人意愿而非制度强制已经成为当前民间信仰运行的基本机制,汪公出会的活动费由信众自由乐捐;汪氏族长容忍祭祀活动中的缺席现象;仪式参与“自助化”,祭祀仪式则更为开放包容,只要“心智好”都可以参加到仪式中的大部分环节。同时,林美容认为“信仰空间内的地域性祭典组织只有达到跨乡镇的范围才有可能被界定为信仰圈”,在祭祀时间已经延长到3 天的“汪公会”仪式中,出会路线已经涉及到周边7个行政村,“汪公菩萨”信仰圈中地域性组织也已经超出高湖村,跨越多个乡镇,附近各乡镇皆有人来祭拜,宗祠内挂满了信徒还愿的锦旗。同时,由于“蔡伦会”的多年停办以及各个村民组土地庙无人修缮,汪氏宗祠已经成为高湖村信仰中心,“汪公会”成为高湖村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活动,也正好契合了“以一神为中心”的“信仰圈”特征。此时,区域神所体现出“信仰圈”祭祀空间的存在意义不在于仪式标志实践本身,而是通过仪式活动来联通更大范围的共同信仰人群,这可以视作高湖村民间信仰在空间方面实现其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
区域神是指多个村落进行神灵信仰仪式性活动时而形成的祭祀范围。近几年来,汪华信仰的信仰空间已经扩展到临近的几个村落,区域神的形成使原先单一祭祀单元变得更为多样化。一方面,参加“汪公菩萨”出会仪式的信众越来越多,不但本村村民参与其中,而且附近的村民和其他乡镇的村民也赶来参加;另一方面,在其他村落提前筹备、准备迎神的情况下,汪公出会的队伍也会前往其他村落,使得“出会仪式”的时间一次次地延长,现在的汪公出会的仪式至少历时3 天。区域性“汪公信仰”的祭祀仪式已经成为一个志愿性的开放活动,除了外村的青壮年可以参与出会仪式中的举牌、抬轿等仪式,外村人中妇女和小孩也能参与举旗、分食“会果”等仪式环节。除此之外,祭祀点也发生了变化,在之前出会仪式过程中,准备分祭坛请神迎神的必须是汪姓的人家,但是这两年外姓人也会参与到分祭坛的请神仪式中。外姓人也可以在家准备分祭坛,在汪公出会的过程中迎接汪神。开设分祭坛的外姓人一般都是外出做生意的,家庭条件比较富裕,所以迎接汪公保佑生意兴隆。
从空间分布来看,濂溪河的流向是由东南到西北,在濂溪河的北侧有一条乡间公路,濂溪河的南侧分布着全村近4/5 的住宅,村内的田地紧靠着濂溪河的南侧。汪氏宗祠位于村落的东北部,目前汪氏宗祠是一座县级保护文物,在“文革”中宗祠以及内部木雕、石雕与砖雕被严重破坏。
五、“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扩张的思考
林美容在分析民间信仰的内质时,认为民间信仰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14]高湖村“汪公菩萨”出会仪式所建构的信仰空间的内在社会基础体现出一种乡村自主性发展的力量。所以它的扩张不仅仅表现在祭祀区域的简单扩大和参与祭祀组织的主体多样化,还折射出在新的社会参与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认同空间及村际关系网络的延伸,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再现与村落公共秩序的塑造与维持,另外也是民间信仰的转型的表现,信仰空间的演变使人与神的互动逐渐向人与人的互动转变,神圣化的祭祀变为一种世俗化的展演活动。“祭祀圈”向“信仰圈”的转化过程将古老的民间信仰习俗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在历史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展现出来,通过节日庆典活动来表征民众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精神信仰需求。
(一)秩序性集体生活的延长
人类生活的有序性来源于仪式对社会成员精神世界中情感的调整与加持。仪式不是来自个体行为,而是从集体行为中产生,所以它们必定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5]哈里森指出仪式“源于人类群体对于生活需求和欲望的集体诉求活动”。[16]集体制解体后,村民的精神生活没有了依托,所以信仰空间的扩张是村民为了继续寻找新的村落依托而做出的努力。
“祭祀圈”向“信仰圈”的转变也使越来越多人得以聚集和互动,由于社会文化心理观念上的认同和日常生产生活的实践,促使原来单方面的人神互动转向人与人之间的资源互助。在祭祀圈的变迁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乡民参与到仪式过程中,“汪公会”从单一性质姓氏祭祀的仪式活动发展为周围几个村庄共同祭祀的集体性仪式,邻近几个村落的村民都会参与,他们在汪氏宗祠、分祭坛以及汪氏宗祠的旧址上以共同的方式祭拜着整个区域的保护神。在汪氏族长的带领下,整个仪式队伍迈着相同的步伐,前往一个又一个分祭坛,膜拜共同的对象,进入同一场域。随着分祭坛的增多,集体生活时间得以延长,不同村落成员之间的密切联系唤起神圣的集体情感,人们对区域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强烈。出会仪式时刻保持并提醒着各个分祭台的人们,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将个人命运纳入集体的规则中,有序集体生活时间的延长淡化了日常格局和村际界限,出会仪式所折射出来的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使得沉淀在乡民内心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得到再现,如同宗教仪式常见的规程和内涵一样,展演出社区内部日常生活的规律性,“书写着包括仪式以内的更大社会运作的有序性”。[17]
(二)村际关系网络的扩大
信仰空间的扩张其实也是地域性村际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汪公会”从原来汪氏子孙祭祀扩布到邻近几个村的村民共同祭祀,表明了在“信仰圈”内村际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汪公信仰”作为村际交往的一种介质,拓展了村际信息传播的途径。出会仪式中的祭点的增加,加强不同村落之间的联系。不同村落的合祭也使男女之间的交往有了更多选择,抬汪公神舆路程的延长为那些举帅旗年轻力壮的后生们创造了更多自由活动的机会,为村际之间通婚提供了条件,除此之外,近几年来的献戏娱神节目除了唱一些传统的戏曲之外,还增设了一些情歌对唱的活动,提供了村落领域交流的难得机会。祭祀、娱乐和宴饮在加强人群之间联系的同时,也规范着地方生活节奏和价值系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使村际之间的交往空间更广,村际关系更加紧密。
(三)强制的规训转向内发的志愿参与
恢复后的“祭祀圈”仍然保持着制度性的特征,詹姆斯·沃森认为仪式是“以‘教化’的形式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18]首先,汪公会活动的经费源自汪氏成员的义务捐献,这种捐款完全是义务性质的;其次,不去参加或者在祭祀活动中有迟到行为的,都要受到处罚,罚款的数额有明确规定;再次,在“汪公会”分食祭品活动中,汪氏族长会以汪公的旨意通过赠予“会果”的形式对村里的人表示奖惩,通常是对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对村里面有特殊贡献的人表达对其品性和贡献的嘉奖;最后,汪氏族长也会提前对请神人家的品性进行考察,如果该户人家在村内的声誉不好或者是品性不端,该户会被族长暂停或者取消请神的资格,一方面可以凸显仪式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对社会也起到训诫作用。在“祭祀圈”演化成“信仰圈”以后,个人意愿而非制度强制已经成为当前民间信仰运行的基本机制。一方面,现在汪公会的活动费用不再由汪氏族员义务分摊,而是由信众自愿捐献;另一方面,对于祭祀活动中的缺席现象,不再采用罚款方式,而是一种容忍的态度。除此之外,仪式参与“自助化”,以往祭祀仪式具有一定封闭性,仅限于汪氏成员参加,现在的祭祀仪式则更为开放包容,大部分仪式几乎不设“门槛”,这表明神灵的象征由集体对个体的强制和约束逐渐内化,转变为村社共同体的价值观,祭祀仪式的参与越来越志愿化,自主意识越来越高,祭祀仪式中祖先崇拜的道德教化功能由此转化为一种人文崇拜。当前高湖村汪华信仰的运行机制已经完成了从强制到志愿的转变,“个人而非社区成为当下民间信仰立足的基石”。[19]
(四)社会关系及结构的连续与流变
“汪公菩萨”的祭祀仪式在阶层、性别、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延续着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与结构。高湖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主要体现在参与人员、祭祀范围、仪式内容的变迁。随着区域性“信仰圈”的形成,女性也可以进祠堂进行祭祀、参与举旗等仪式,但是在仪式的核心环节中,还是存在男尊女卑的性别观,这不仅表现在为“汪公”下殿穿新衣只能是男性操作,而且在进行祭拜时,女性的顺序也必须排在男性之后。汪氏族人认为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如果仪式中的所有环节都由外姓人和女性来做,会破坏汪氏在村落中的权威。
彭兆荣认为仪式“具有再生产和再塑造的能力”。[20]变迁后祭祀仪式仍然体现民众在社会关系上的差异,身份和性别上的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仪式表演的环节中,表演者都要为自己的祭祀行为承担一定的职责,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的选择与他在当地生活秩序中所处的地位有关,仪式的环节要求每个人都不能缺席或置换规定的位置,这些仪式的规定均映射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与结构,除此之外,祭祀仪式仍然保持着集体实践的形式,这也是在肯定和巩固传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男性作为祭祀仪式核心环节中的主要参与者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男权语境在乡村社会秩序中一直没有改变,但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祭祀圈扩布过程中又发生了变异,女性可以参与撑旗、分食祭品等环节,女性在祭祀活动中有更多的参与机会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表明传统的祭祀模式内部已经发生流变。
(五)村际对立中的平衡
“汪公会“作为一种仪式表演,虽然它在现代化背景下维系村社结构性秩序,延续其传统的调试乡民精神生活世界平衡的社会功能,但是在各个村落争夺“汪公菩萨”优先“出会权”时,民众的信仰心理不见得更强烈、虔诚,反而在祭祀活动中表现的村社竞争心理更凸显。当汪公菩萨“信仰圈”扩张到邻近几个村的区域时,村庄间的出会仪式先后顺序也体现出村际一定程度的对立关系。高湖村作为信仰空间的核心地带,举行第一天的出会仪式不会引发争议,然而在第二天、第三天到别村的出会仪式的先后顺序往往会引发矛盾。每个村庄的带头人笃信,“汪公菩萨”的优先到来会给该村庄带来一年的“好兆头”。位于汪氏宗祠旧址旁边的南容村,以距离汪氏宗祠最近为由坚持第二个举办仪式,而位于高湖村东面的濂长村以文革时期保管过汪公菩萨神像为由坚持自己村要优先进行出会仪式。“汪公菩萨”出会顺序引起附近村落纠纷,这主要由于村社之间的经济基础、神灵传说等话语的差异,但是最终都会考虑村庄大局和族长压力后妥协。除此之外,南容村、濂长村、小山村每年在年会前的捐款上也不遑多让,因为每年举办出会,每个村捐资数目都会由汪氏族长在祠堂南墙上张贴出来,而通常各个村捐款的数量往往决定了当年出会路线的顺序。近几年,南容村凭借开设拉丝厂、玩具厂受益,往往在捐款数量上拔得头筹,因此获得了高湖村以外的优先出会权。祭祀圈的扩张有着社会关系网作为铺垫,而出会仪式又在强调和强化着这层关系。总之,虽然出会仪式的先后顺序体现村社之间现实生活秩序中利益纠葛的一面,但是仪式提供“一种超越不同经济利益、经济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21],激化利益冲突的同时更多的是平衡村际秩序。
本文运用台湾民间社会流行的“祭祀圈”和“信仰圈”概念对高湖村“汪公菩萨”出会仪式进行解读。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对地方社会的作用,来认识和思考人以及人的行动对高湖村及附近地域存在的影响,传统社会中血缘是人际关系的基石,但是随着信仰空间的衍化和嬗变,人际关系已经超越了血缘因素的界限,汪氏宗族组织的力量明显式微,在现代化背景下应当将地缘条件纳入动态的文化生成过程中。但是信仰空间的变化并不囿于特殊的情境,而是“行动者”与“特殊情境”共生共变的结果。研究发现,当前的“汪公菩萨”信仰空间不仅是基于皖南的村落结构与特殊情境而形成的,还应该考虑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恢复后“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是民众自发性与官方体系的合力产物。虽然“汪公信仰”是皖南村落文化整合的传统资源,但是信仰行为的变化只是信仰空间衍化和嬗变的表层,其背后涉及的是人群结合机制的问题,即高湖村社会存在的模式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笔者认为必须从高湖村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与行动者的心理两个层面入手,才能更好地了解乡村振兴下的新型村落文化生成的过程与公共秩序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冈田谦.台湾北部村落于祭祀圈[J].民族学研究,1938,4(1).
[2]刘万枝.台湾的瘟神庙[J].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22:53-95.
[3]王世庆.民间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乡村之历史[J].台湾文献,1972,23(3):3-38.
[4]施振明.祭祀圈与社会组织——彰化平原聚落发展模式的探讨[J].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3,36:191-208.
[5]许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J].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5,36:165-190.
[6]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地方组织[J].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6,62:58.
[7]林美容.彰化妈祖信仰圈[J].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0,98.
[8]王象.舆地纪胜[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9]特纳.象征之林[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C]//张炎宪.第三届中国海洋发展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1988.
[11]庄英章,林祀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3]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14]林美容.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5]王铭铭,潘忠党.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04.
[16]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134.
[17]陈沛照.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湘西“苗族四月八”的人类学解读[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2):153-159.
[18]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 年)[J].陈仲丹,译.郑和研究,2001(2):47-56.
[19]李翠玲.从结构制约到志愿参与:民间信仰公共性的现代转化——以一个珠三角村庄为例[J].民俗研究,2019(2):136-144+160.
[20]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0.
[21]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An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the Wang Gong Bodhisattva Belief
DAI Wei,LU Wen-pi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601)
Abstract:With the concepts of sacrificial circle and belief circle originated in Taiwan folk society,and based on the field data of Gaohu Village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folk beliefs in the 1980s,this paper relates the expansion of belief space from sacrificial circle to faith circle to the developement of Wanggong belief.Through describing Wang Gong’s exposition ritual,and studying Wang Gong’s transformation from a private god to a village god and to a regional god,the pa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local spiri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and mak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sacrifice circle,belief circle,private god,village god,regional god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9)10-0042-09
收稿日期:2019-06-08
作者简介:戴 伟,女,安徽宣城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硕士研究生。陆文萍,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共同体’观念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7BSH061)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招标课题“现代性语境下的徽州‘家信仰’研究”(HWH009B)
(责任编辑:吴旷子)
标签:祭祀论文; 仪式论文; 菩萨论文; 汪氏论文; 村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共同体’观念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7BSH061)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招标课题“现代性语境下的徽州‘家信仰’研究”(HWH009B)论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