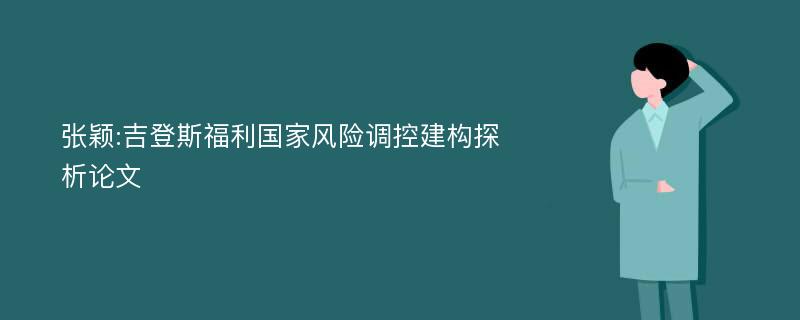
摘要:社会风险是人类无法逃避的重大问题,原因是其未知性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国家干预变得非常必要,但又不能成为不必要的恶。要让个体积极行动起来,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切实参与到现实的生产、分配、生活中去。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作为庞然大物的集体国家实体,任务从解除强大自然力量造成的威胁转向增强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克服个体盲目依赖性和分散性,借由缜密规划和科学控制的理性选择,实现社会有序、团结、融合,达成福利的情感体验化和受益最大公约化。福利国家风险化解倚靠风险解构和福利重构,进而充分发挥国家和个人的潜力实现共同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要大胆借鉴包括吉登斯等西方先进社会风险调控思想,在社会进步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不确定性;情感体验;团结;建构;
一、福利国家社会风险特征:不可知性和破坏性
风险,根据法国人的定义,是指海上贸易和由此造成的损失,有冒险或危险之意,而“风险的概念最为重要的是跟概率与不确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说到风险就是一种没有十分把握的不确定,是要冒一定风险去作出的一种决策”。[1]同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运行也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但其具有最完备的风险调控机能,其阶级本质的暴力性也可有效化解风险,实现阶级统治的目标。国家也具有社会管理的一面,指向性针对社会内部的团结和协调,雷蒙德·威廉斯认为:“现代世界中正在进行的许多事情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凡是能够计划或能够期盼的,都不外是短期的实际效益。”[2]可以说,现代形形色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借用社会主义方法改良的理论,通过“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以便使社会秩序更合理”。[3]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福利国家的出现,正试图努力弥合市场机制和国家强制两者的冲突,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多重修正,也是罗斯福新政和国家主义的复归,“因为它蕴含着生产的不断扩大和财富的不断积累”,[4]伴随着极大的副作用。贝克认为:“西方用市场化的力量疯狂地代替了人类有节制的需要满足,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无节制的特征,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状况是不相容的,生产力的扩张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并最终将导致文明体系的崩溃。”[5]而现代化造成的非现代性,常常造成个人体验的差异,在既有社会形式和技术架构的可靠性信任中,混杂着躁动、预期、失望的情感、焦虑,交织进入自我认知的核心。政府的考验是必须恰当化解这一矛盾,应对和处理个人对资源的占有不足或个人“勤劳”的差别,联合团体和组织的力量对其进行明确的承诺:“愿意工作的人得到工作,不愿工作的人得到惩罚,不能工作的人得到面包。”[4]要对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副产品进行必要的风险管理,在自我制造风险也陷入风险之时,实现从分裂走向联合、从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无力感到实际占有、从社会不确定到新的权威的重新建立,避免“科技和制度等的不断发展使人们陷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6]在发展的不充分显示出两极分化和极端贫困时,完善强化国家福利计划,把个人风险承担纳入政府应对未来不测行为导向的风险管控计划,改善个人生活状况并提升生活品质。虽然福利与国家有着天然联系,但它不是唯一的提供主体,有时可以通过市场化交易满足多样化的个性需要。“在后工业社会,国家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福利。它还必须发挥一种更加广泛又更加松散的调节功能。国家的任务是帮助创造有效的公共领域和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但它远不是唯一的代理人(agent)”。[7]吉登斯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对“福利”认识的两个层面即“给有需要的人提供经济帮助”和“快乐和健康的状态”,认为“福利”是一种康乐状态或者生活目标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保护性风险管理。从中可以窥见,“福利”一词的意涵已经超越基本生活保障、生活水平改善及生活质量提高,而深入到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生活体验的满足。吉登斯后来又对其补充:“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关乎个人的幸福。”[8]
当然,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福利国家风险的张力和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小,可分配的利基比较厚实,普遍纳税人群体规模较大,但要防止少数人对多数人过多剥削,挫伤少数人对社会贡献的积极性。福利国家最难以为继的是被自己的成功所破坏和中产阶级的“纳税人造反”,要防止“不能不加反思地接受把贫困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社会结构本身的那些主张。这种思路等于是说,穷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艰难处境”。[3]国家福利制度的合理设计,正如雷思认为的一样:满足的大多数,满足的选民多数,或者更宽泛地说,满足文化。任何理所当然的享受将带来福利制度的边际效用递减,“福利国家未能把这部分人整合进广大的社会,有时反而促使他们与社会‘疏离’,甚至导致一个所谓的‘下层阶级’的产生。”[9]个人的依赖心理是一种贫穷文化,其强度伴随一定文化背景或强或弱,特别是受习惯、风俗、传统、宗教的影响。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崇尚自由主义的节奏和后工业后现代的生活体验,最终从一种均富滑向另一种均贫,因为“贫困并不只是诸般社会力量作用于消极被动的人口的结果。就算是处于严重劣势的人,也有可能抓住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4]经济上的边缘化在很长时间内会代际传递,最明显的是当下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过程中,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等、靠、要的旧有观念,自我发展意愿淡薄,一代贫困世代贫困和争取贫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代际遗传突出。
二、福利国家社会风险化解:干预主义与行动主义
在流变的现代社会,人类面临各种未知的挑战和困境,内心充满着焦躁和不安,总是想通过理性思维能力化解种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和人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双元革命”的压力,“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于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平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0]这种不可预测,有时单靠个人力量又无法得以解决,只能求助国家的力量和资源,从根本和长远方面获得基本的解决。从国家角度来看,如果社会福利制度只从对“受伤害者”给予补偿的角度思考,恐怕会稍显不足。比如婚姻和家庭的不幸福,夫妻双方要求离婚,国家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保证承担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一方,应该从另一方获得必需的经济物质补偿。
“在多数工业化社会,底层的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福利国家而得到缓解”,[3]国家行动计划中国家权力积极干预能减轻个体应对困难的局限,因为“在人类行为改造能力的意义上,‘权力’是行动者干预一系列事件以改变其进程的能力”,[11]它是进行福利制度设计和风险规避的重要行动力量。国家不能制造问题,更不能对贫困群体进行标签式标识,这是对自尊的忽视,否定人们改善命运的能力和努力,将会导致自我损害或攻击他人的行为发生。国家践行社会责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根据个人工作技能和经验,创造充分就业的环境并保证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同时,又要避免过度供给对公民造成的消极效果及稀缺福利资源浪费,进而产生个体过度的组织依附和团体依赖,福利制度设计应强调帮助人们自助。国家应创造条件,帮助有困难或先天有缺陷的个体恢复应对风险的自信心,改变自我感知和社会体认,寻找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因为风险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可能和机会,人们通过积极创新去把握这种机会,就可能把理想化为现实”。[12]比如,对于肢体残疾的人,除了提供假肢的免费分发等服务外,应该在自主就业和自我创业方面提供必要的指导或减税和免税的支持。吉登斯认为个人行动计划是一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契约,个体意识到要改变并且通过努力也能改变不利的生存状况,就不会转向国家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在个体力所不及时,国家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和就业培训及指导,“个人同意根据再培训和找工作培训所详细说明的方式行动;同时必须给他们提供各种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在不可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个人行动计划的目标则是要稳定个人的生活状况,避免发生异化过程和丧失自尊”。[7]行动主义的另一种理解是社会行动主义,个体必须参与到福利政策的制定过程及福利资源的分配环节中,“福利的分配效果或者民众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成果不仅依赖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取决于国家的制度构造和民众的参与能力”。[13]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政策不再可能只覆盖那些它在传统意义上的实用的领域……它必须与公民自由和文化相对论的讨论相关联”,[7]在强调国家给福利接受者赋予权利的同时,不忽视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承担。
福利社会风险化解的理想路径是:市场的充分竞争、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与福利国家之间有效的协调与平衡。对后两者而言,福利消费者会有更多选择空间,它涉及的领域不仅靠市场原则来组织,相反需要体现团结与和谐的精神。市场过多侵入国家管理和福利场域,必然会造成福利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市场动机替代了公益目标,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就会层出不穷。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从两个大局出发,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大幅度上升,一些公共产品供给明显不足,比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存在差异性、不平衡性及供给矛盾。
三、福利国家社会风险调控目标:秩序与团结
宝宝总有一天是要自立于社会的,如果能从小培养宝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东西自己管、自己的生活自己安排的“自我管理”习惯,就能增强宝宝行动的独立性、目的性和计划性。这对于宝宝今后生活的幸福和成功无疑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福利国家的危机并不纯粹是财政上的,它是一个被新型风险左右的社会中的一场风险管理危机。”[23]在对传统的福利制度再设计时,侧重点和针对性要很明确,“在现代性条件下,与在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许多风险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2]吉登斯认为要在“新福利架构”下,充分考虑国际竞争力、财政紧缩、工作年限的变革、传统家庭护理的弱化、人口老龄化、教育和培训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养老金政策等风险特性而投资,“国家不仅要关注贫困,还要注重教育和技能培训、健康的生活方式、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参与”。[24]妇女在家庭角色扮演上,与男性分担共同的家庭责任,这种革命性转变使她们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全参与变成可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儿童贫困发生率。为了建立友好型的家庭关怀制度,制定人性化的税收政策、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的产假和育儿补贴,能为未来的潜在劳动力(儿童)发展进行长远的投资。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确保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更加持久,阻止学生过早地离开学校和培训机构,促进学生尤其是那些低学历的辍学者从学校过渡到工作岗位。除了继续坚持准终身工作来保护养家糊口的工人外,还要加强对诸如年轻人、妇女、移民和低技能的老年人充足的保障,这种“预防性就业能力”能很好缓解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福利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
近年来,韩国文化的流行与发展推动了韩国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韩语凭借着特有的说话语调以及发音方式使人们对韩国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走进韩国并了解韩国的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化。加之韩国在其旅游方面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致使很多人想观赏韩国一些城市的美丽风景,并且品尝韩国美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最终带动了韩国文化的传播。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外在表现,它不是从来就存在也不会永久存在下去。只不过这一灭亡的过程将伴随生产关系不断修正和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也使得现代国家不能通过其垄断的暴力手段而直接执行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19]又不断陷入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吉登斯认为,阶级划分和社会冲突是福利国家的源起,“通常,对战后福利国家‘安排’的解释是从阶级角度出发的。今天,造成这样一种‘安排’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全球化,不是国家的制度。劳动力流动的实质不是‘阶级冲突制度’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竞争新条件的产物。”[3]这种经济的“安排”是政治和经济风险分化而非分离的结果,仅仅是劳资契约关系摆脱政治的束缚,并非产品只是通过市场生产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另一边是制造出来的贫穷,个体实际购买力的急剧下降。过剩的劳动力保存在“后备库”里,对资本主义来说要吸纳他们,个体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才能满足生产力提高的要求进而避免被边缘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生产目的的人异化成了生产的手段,最终对物的支配变成了被物的支配,精细的分工导致严重的异化效应。它“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个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0]由于阶级利益矛盾的激烈,基于增强劳动阶级的经济发展获得感,国家运用福利分配手段解构个人风险,实现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缓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张力和冲突。在早期,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保证了“有效需求”市场状况,为了应对就业和福利领域的瓶颈问题,需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为劳动力市场准入设置社会壁垒,防止提前退休,降低劳动力市场变迁的不稳定性,以及保证性别平等和机会均等”。[21]到资本主义后期,由于后工业化时代人口结构、出生增长率、资本增值率、投资效益比、经济周期波动,使得北欧等福利发达国家,必须开源节流,转而倚重“有效供给”方面。伴随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挑战,没有成本优势或技术长处的经济模式注定难以为继,伴随国家财富以外汇逆差的方式流向新兴经济体,以往的坐吃山空、寅吃卯粮的福利制度将无以为继。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从适度就业走向充分就业,“实现在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22]
最后,团结的结构维度是指国家、社区、团体的社会联系的融合程度。国家要做的就是促进融合,实现关怀和礼貌嵌入社会有机体,使分化和分裂处于可控和掌握。在后匮乏时代的福利国家,要持续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目的在于防止依赖性的出现,“国家干预模式在全球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效率低下,发挥个人积极性也要有新思维”,[17]结合个人责任和权利、承担和收益综合考虑,“强调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18]在面临空气污染、森林消亡、温室效应等“集体厄运”时,作为外部风险的风险成本,必须由企业和纳税人来共同承担。由于战争、贫穷、饥饿等人为风险出现时,不能简单花钱弥补这种破坏,也不是简单与穷人讨价还价直接转移财富,而是注重就业机会的转移。吉登斯虽然承认向不那么富裕的人提供再分配,但是却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文化差异会挫伤富裕者对扶持贫困者的积极性,后者常常不被认为是同一群体,很难融入到社会体系中。文化多样性使得贫困群体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努力。常常在防患于未然方面国家是失分的甚至是失败的,大部分福利措施只是解决已经发生的事,而不是预防性切断事情发生的根源。福利国家还没有成功地把资源从更加富裕的团体和个体手里转移到穷人手里,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它倾向于制造分裂,“但他们的隔离状况被技术和贫乏的语言知识进一步强化,进而变成一种使自身长久存在的现象,从而激发了本国人的敌视态度。实际上,最危险的是,少数族裔被看作靠福利国家养活的人”。[7]应努力营造能动的平等模式或平等化,为富人和穷人之间达成新的契约提供基础,基于人们变化的生活方式之上的“有组织的讨价还价”。
首先从心理维度看,“有一种关怀他人的普遍态度,包括对待不如自己富有的人。人们可能把这一点称为公民身份的态度维度。关怀可能表现为慷慨,但可以仅指接受纳税的义务,或为提升更大的善的其他义务。”[7]福利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有助于政府和国家建立一个关怀的社会秩序和团结制度,个体利他主义变成国家利民主义就是福利制度安排。除了制度上确保其常态化,也必须通过奖励性鼓励或惩罚性威慑影响某种行为的产生概率。某些以“福利国家”标榜的社会组织强调自我发展和社会关怀,作为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实体,国家根据外部风险,提高解决自我无法实现基本收入和资源标准问题的能力,努力发展二次机会政治,在社会团体和社会职别中建立社会契约和协定,从生产主义到生命主义转变。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14]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叠加,社会风险陡增、社会分化严重、社会整合困难,要维系自然社会和人为社会的相对有序和稳健变得极具挑战,“社会福利制度也必须适应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过去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变为关注人自身、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1)注释:文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专题”,博士生课,ppt,第19页,2018年12月18日晚,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法商北楼509教室。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逐渐意识到,人们相互之间必须加强团结协作,通过组织化或社会化的力量才能存续下去。人们对不可预测的、变化无常的、无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加以认识和改造,通过组织方式和现代手段结合成稳固的共同体,就变成了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公民角度审视,每个公民都希望社会成员联合起来降低个人的风险,美好的愿望是达不成的。从国家层面看,国家介入个人生活越深,个人对国家保护的依赖性越强,个人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就越差。”[15]个体经过理性化思考和选择,积极进取和有效涉入所属的制度并超越个体的限度,与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自我达到更高的层次,否定享乐主义和贪图安逸的生活体验。借由开发技艺的形式,扩展自己的能力并超越自己。理性可以有效规避风险,理性化被植入现代世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一种支配过程中,“世界秩序和权力要求与个体生活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压迫—服从式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人们有一种条理和充满活力的行为驱使下传播理性”。[16]福利国家正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提供者和理性的承载者,在现代理性的支配下,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依赖个体化的集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宗族、地缘等关系,“个体所要单独面对遵从的是充斥风险与不确定因素的社会运动秩序”。[16]
四、福利国家社会风险调控策略:风险解构和福利重构
其次,从团结的行为维度理解礼貌性问题,意味着接受他人或尊重差异,在社会分裂或破碎时首当其冲的是礼貌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破坏殆尽,原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变成了人与制度之间的法律关系。社会的分化减弱了个体之间的相互性,或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恐惧取代了某种舒缓与惬意。莫里认为,与追求幸福紧密相关的是“物质资源、安全以及自尊”。同样“如果一个人要追求幸福,就不需要以物质体现的过多的物质享受”,不能只是物质供应,必须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知,“在跨过了一个相当低的门槛后,收入提高的水平不会导致更大的幸福或者对个人生活的更大满足”。[3]
福利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促进团结或社会凝聚,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和市场交易行为中,要关注个体之间的自由、平等、公平等权利,“公民的社会权利是获得福利的前提,个人享有的实际权利与其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相互关联的”。[10]另一方面又要克服分散的状态,增强社会的整体关联性和协作性。吉登斯认为,团结(又或互动性)有三个维度,即心理的、行为的和结构的。
诈骗罪的行为构成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被骗者陷入认识错误,被骗者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行为人最终取得财物。基于此,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是否让顾客“陷入错误认识”,是区别盗窃和诈骗的关键要素之一。笔者的观点是,表面上看似是顾客在认识上出现偏差,但在整个付款过程中,顾客并没有陷入错误认识。故成立诈骗罪的第一组因果关系不存在。这里所讲的“错误认识”,是指被骗者主观上要认识到其财产发生转移占有,其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两要件:其一,客观上要有处分行为;其二,主观上要有处分意识。即便客观上发生了财产转移,如果不是基于被骗者的处分意识,那么财产转移的原因也不能称为“陷入错误认识”。
在解决劳动力过早退场引起的风险方面,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并加以运用柔性和弹性的措施。离婚、单亲家庭、少子化、老年人护理、加速的老年化等“新社会风险”积聚到年轻人身上,收入在费用清单上平均化发展,导致在每个项目上捉襟见肘,无法保证基本的生活及生存需要,国家行动能力就日益重要,“现代国家的政府能力与它能否成功地维持监控的运作有关,而这种相关性只有在它们允许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方方面面的监控时方可显示出来”。[25]吉登斯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法是鼓励留有余力的老年人兼职和推迟退休年限,开辟新的适应其从事的领域和行业,既能使他们生命处于一种恰到好处的运动状态,又不造成对个人的身心伤害,不至于“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济越多发生道德公害和欺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26]这种晚退休是有效的和有益的,充分体现了灵活性,极大减轻了养老金的负担,出其不意地帮助年轻人分担照顾老人的任务。但如果通过上面的激励措施仍然无法满足家庭的需要,就必须对于极少数的群体辅以短期最低收入补助,帮助其渡过难关。为了防止当前和未来福利匮乏和福利赤字,制定长期的全面提升计划,包括幼儿发展期、人力资本投资、高质量培训、经济参与及文化融合、推迟退休和弹性退休,编织更加牢固的福利网,使真正需要的人获得自力更生的最低标准。
结 语
西方国家风险防范模式和机制走过了缺乏活力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支撑的漫灌式社会福利,目前正处于从“粗放”向“精细”迈进,逐渐从“社会政策的规范性重点从事后再分配转向了预防性的或事前的就业能力”,但是“只有在对不平等的范围加以限制的社会才能实现机会均等”。[21]可以预见,资本主义的调适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抉择,“一个世纪以来,墓仍然没有挖好,而且,资本主义未来的继承人尽管不再像其先祖那样充满活力,但也没有那种死期将至的严重威胁”。[27]在中国当下社会深刻变迁中,各种风险叠加和累加,如何做好风险的规避和防范,显得尤为现实和迫切。如果社会福利制度及政策不能有效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就会威胁到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和新的贫穷群体,从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建构,甚至延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向前推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一揽子的福利选择中,欧洲国家在家政服务、教育和培训、补贴性工作、针对移民的一体化和劳动力市场、合理的基本养老金等方面的结构化安排,以及实施充足的最低收入保障机制,进行了有质量和创造性的社会投资,对我国当前社会福利风险管理和创新,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范式和实践模式,应加强对其社会化进程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学习和经验研究,以资我们社会管理决策之用。
[29]王明生、杨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赵东旭.走出极端政治——吉登斯眼中的中间道路与全球变迁[J].思想战线,2010,(4).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刘岩.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性现代化——贝克和吉登斯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寻及启示[J].江海学刊,2009,(01).
[6]张广利,许丽娜.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4,(02).
[7]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欧洲[M].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8]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
[9]殷序彝.吉登斯《超越左与右》一书评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03).
[10]杨敏,郑杭生.西方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06).
[1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一种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田佑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2]汪建丰.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评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06).
[13]孙晓东.福利制度正当性的根源及其中国意义[J].学习与探索,2015,(11).
[14]陈新光,包宗豪.后现代视域下的社会风险防范——兼与肖瑛和张乐、童星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2,(06).
[15]徐延辉,林群.福利制度运行机制:动力、风险及后果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3,(06).
[16]杨君,茹靖.从孔德到吉登斯——社会秩序思想演化路径[J].理论月刊,2012,(12).
[17]陈德顺,胡同洲.吉登斯的新平等主义:由来、理论指向与反思[J].政治学研究,2012,(03).
[18]陈纪昌.社会变迁与社会福利建设: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探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05).
[19]龙佳解,杨世春.吉登斯论现代国家——兼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J].湖南大学学报,2017,(03).
[20]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21]安东尼·吉登斯,帕德里克·戴蒙德.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M]. 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2]徐平,张文喜.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思想述评[J].学习与探索,2008,(05).
[23]钱雪飞.安东尼·吉登斯社会风险思想初探[J].社会科学家,2004,(04).
[24]阙天舒.欧洲转型的“冰与火之歌”——评安东尼·吉登斯的《动荡却强大的大陆:欧洲的未来走向何方?》[J].国外理论动态,2017,(02).
[2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6]王远.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的理论基础[J].人文杂志2016,(08).
[27]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OntheConstructionofGiddens’sWelfareStateRiskRegulation
ZHANG Y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Social risk is a major problem that human beings can not escape. Because of the great destructive power of the unknown, state intervention becomes very necessary, but it can not become unnecessary evil. We must let the individual take an active part i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life by changing passivity into initiative and disadvantage into advantage. In an increasingly modern society, the task of the collective state entities as behemoths has shifted from removing threats posed by powerful natural forces to strengthening the cohesion of society as a whole and overcoming the blind dependence and fragmentation of individuals through careful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control of rational choice, to achieve social order, unity,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welfare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benefit of the maximum convention. The resolution of welfare state risk depends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risk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lfare,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tential of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to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on the advanced Western ideas of risk control, including those of Giddens,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progress.
Keywords:uncertainty; emotional experience; unity; construction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06)
作者简介:张 颖(1978—),男,贵州毕节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毕节市七星关区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11-0060-06
〔责任编辑:李 官〕
标签:社会论文; 国家论文; 福利论文; 风险论文; 的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论文; 《学术探索》2019年第11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06)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