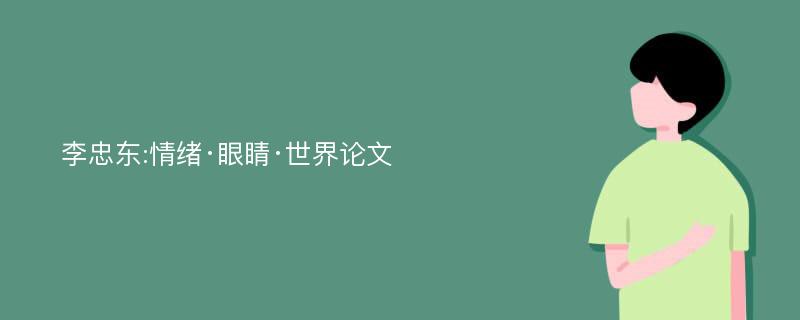
蒙娜丽莎在笑吗?
《蒙娜丽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的油画,它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方向,众多艺术爱好者被《蒙娜丽莎》表面变化的面貌所吸引,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前往卢浮宫鉴赏。据统计,每年的参观人数超过600万。
大多数人认为,蒙娜丽莎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不确定性。在不同的人眼里,或在不同的时间,她的表情看起来都不一样。已故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爵士说看上去“好像她刚刚生病或将要生病”。著名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评价道:“对我来说,《蒙娜丽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情感绘画作品,闪耀的微笑代表着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家唐纳德·沙逊教授则认为,达·芬奇有意隐藏模特的真实情绪,从而给人们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19世纪中期身兼作家和艺术评论家的狄奥菲尔·戈蒂埃以他极具影响力的评论为《蒙娜丽莎》笼罩上一层神秘莫测的光环:“她那弯成弧形的嘴唇,仿佛即刻就要飞出充满优越感的嘲讽、居高临下的讥讽和天使般的嘲弄来。她发自内心的快乐因为其掩盖的秘密深不可测,使得她的嘴唇弯成一道不太分明的曲线了。”
是凝视和微笑?还是恍惚和犹豫?几个世纪以来,艺术爱好者和评论家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争论纷纭。不同的参观者或在不同的时间去看,感受似乎都不同。
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成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由于中国社会体制以及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社工与义工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组织外部以及组织内部间的困境:一是组织间缺乏信任、社会网络支持系统碎片化,服务规范的断裂等;二是组织内部专业化历史短暂,自主性较弱,民间组织发育滞后、资金不足等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组织内部困境有大量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将重点围绕组织间的困境展开。
ICU病房的患者多为免疫功能低下者,其病情危重,常有气管切开或插管,甚至需要机械通气等侵入性操作,容易破坏机体的防御屏障而导致感染[1]。医院感染一旦发生,不仅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加重了病情,增加了经济负担,严重者更导致死亡[2]。肠杆菌科细菌多数为肠道正常菌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致病,为院内感染常见病原菌,近年来多重耐药或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CRE)现象日益普遍。本研究对ICU与其他普通病房肠杆菌科细菌的检出情况与耐药性进行了比较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2.1.3.3 缓冲溶液pH的优化 本方法考察了不同pH对组分迁移时间和分离效率的影响,见图3。最终确认缓冲液优化pH为8.60。
感受产生潜意识
在每次试验结束时,会出现五个面孔(一组),被试验者选择了与他们在试验期间看到的最匹配的面孔。呈现给被试验者主导眼球的脸部总是中性的,但是如果在他们意识之外呈现的图像显示出一个人正在面带微笑,而不是中立或皱眉,他们倾向于选择微笑的面部作为最佳匹配的面孔。
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
我们是自己经验的建筑师,我们的大脑预测了它期望看到的结果,并利用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来更新它期望看到的结果。人们对新面孔的感知,如快乐,悲伤,友善,中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迎接它时所携带的感觉,而不是在那个特定的脸上的表情。这意味着当我们下意识地体验一张笑脸时,我们更可能把一张中性的脸看成是幸福的。“如果你在卢浮宫度过你的生活时光,你会看到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西格尔不无幽默地说,“但是倘若你在与丈夫发生激烈争吵之后再看到她,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画面。”
在第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一种称为“持续闪光抑制”的技术,拍摄了一系列闪图像,能够在43名被试验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刺激。这些图像在像素化图像和中性人脸之间交替显示,呈现给他们的主导眼球。与此同时一张微笑、皱眉的低对比度图像被呈现给他们的非主导眼球,通常该图像将被主眼所提供的刺激压制,参与者不会有意识地去感受它。
从分析结果(见图4)来看:侧壁厚度越接近主壁厚,翘曲变形量越小。整体厚度趋近一致,收缩相对均匀,因此翘曲变形量相对较小。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心理学家埃里卡·西格尔博士和她的团队在研究中,通过模拟人们是如何感觉潜意识的视觉感知的两个实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发现被试验者会认为一张中性面孔(与未看到的正面形象配对时)更像是在微笑。这项研究基于“大脑是预测器官,不是反应性器官”的现代理论,换句话说,人们有人生的经验,用它们来预测接下来要经历的事情,传入的信息实际上只是用来纠正在做出预测时可能出现的错误。
第二个实验包含了一种客观的意识测量,要求被试验者猜测被压抑面部的方向,那些能更正确地猜测方向的人未被包括在随后的分析中。结果再一次表明,看不见的积极面孔改变了被试验者对可见中性面孔的感知。当非主导的眼睛看到一张幸福满满的脸时,他们更可能会认为那张中性脸实际上已经在微笑,而在非主导眼看到了做鬼脸的表情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那张脸实际上是在做鬼脸。由此可见,潜意识对中性表情的脸的察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人体的两个眼睛中,实际上一个是主导眼,另一个是被动的非主导眼。如果每只眼睛都收到不同的信息,人们会有意识地感知到主导眼睛的视觉,但非主导眼睛看到的场景仍然可以渗透到我们的潜意识中,从而产生一种视觉错觉现象。因此洞察表情实际上是一个在人脑中比上面提到的计算程序更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计算过程,我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情绪左右着认知
研究人员做了两组实验,第一组是让 127名被实验者随机观看可以引起人悲伤或愉快心情的两种不同的短片,要求在进入到该情绪当中的情况下短时间内识别连续48个色彩。第二组同样是让研究者观看两种不同的东西,只不过这一次是 130 个人,而且观看的内容由悲伤和愉快两种短片换成了悲伤的短片和没有任何影响的东西。对两组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结果发现观看悲伤短片的人在识别大多数颜色,如红绿色轴的颜色的时候都不会出现问题;而在识别黄蓝色轴的颜色的时候,判断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人在悲伤的时候,看到的世界都是灰色的,原来以为这都是诗意的描述。然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索斯藤森主持的一项研究证实,情绪状态真的会左右我们如何看见周围世界。尤其是在心情抑郁这种情况下,悲伤会影响我们的视觉,损害色彩感知的神经过程,使世界显得更加灰暗。这也表明用颜色来比喻情绪状态是有科学根据的,如“心情忧郁”或是“灰暗的一天”。
早在200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心理学家就将蒙娜丽莎的脸部引入他们设计的情感软件进行分析。根据他们的算法,蒙娜丽莎的表情高兴、厌恶、害怕和愤怒分别占83%、 9% 、 6%和2%。该软件首先根据数据库中年轻女子脸部制出一个“一般表情”模本,再通过与此模本比较嘴唇和眼部周围皱纹的弧度等脸部关键特征,识别人类情绪,目前能识别开心、惊奇、生气、厌恶、恐惧和悲伤6种基本情绪。
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是新课程改革所极力倡导的学习方式。在这种学习方式之下,学生的自主学习是基础。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我们才能很准确地收集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才能为接下来的“以学定教”提供教学决策,使得课堂教与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课堂教学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生的自主学习环节的,因为这样的话学生只是发现了问题,却没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从教学的实际效果上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合作、探究环节才是新课程改革之下一堂课的最主要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教师的教学目标才能实现,课堂教学的重难点才能得到有效突破,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成果也才能有所保障。
之前的研究指出,这有可能是人在悲伤的情况下,导致视觉神经的传递功能受到了影响,造成的原因有可能是视网膜多巴胺的变化损害。至于具体的影响程度和原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现已证明,由脑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多巴胺”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或许与我们悲伤时对颜色的感知有关。作为一种神经递质,“多巴胺”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这种脑内分泌的化学物质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和感觉,将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传递,也与上瘾有关,能帮助控制大脑的“愉悦与奖励中心”。心理学家说,“多巴胺”与蓝黄色轴上的颜色感知存在明确联系,悲伤真的会让世界看起来比平时更灰暗一些。大脑的情感和感知系统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会互相影响,心理学研究也更加注重对感知、认知和情感等过程相互影响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识一个叫英格莱特的印第安纳州人,10年前患了猩红热,康复以后又发现自己得了肾病。他四处求医,找遍了偏方秘方,但谁也无法治好他。不久,英格莱特又得了另外一种并发症。医生说他的血压已经到了最高点,已经无可救药了,离死亡不会太远,建议他最好马上料理后事。
英格莱特只好回到家里,弄清楚所有的保险全都付过后,便向上帝忏悔自己以前所犯过的各种错误,坐下来很难过地默默沉思。家里人看到他那种痛苦的样子,都感到非常难过,自己则更是深深地陷入颓丧中。这样过了一周后,英格莱特心里突然想到,这种样子看上去简直像个傻瓜。既然在一年之内恐怕还不会死,那么为何不趁现在还活着快乐一些呢?于是他挺起胸膛,脸上开始绽放笑容,试着让自己表现出很轻松的样子。刚开始不习惯,但还是强迫自己快乐起来。
这种改进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英格莱特逐渐地发现自己感觉好多了,几乎跟原来装出的一样好。原以为已经该躺在坟墓里几个月后的今天,他不仅活得好好的,感到很健康很快乐,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一直想到会垮会死的话,那位医生的预言就会实现,可是我给了自己身体一个自行康复的机会。”英格莱特自豪地说,“除非我乐观起来,进入良好的情绪状态,使原来面前灰暗的世界看上去斑斓多彩,否则别的什么都没有用,谁也救不了你。”
编辑:夏春晖 386753207@qq.com
标签:蒙娜丽莎论文; 悲伤论文; 情绪论文; 主导论文; 组织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检察风云》2019年第4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