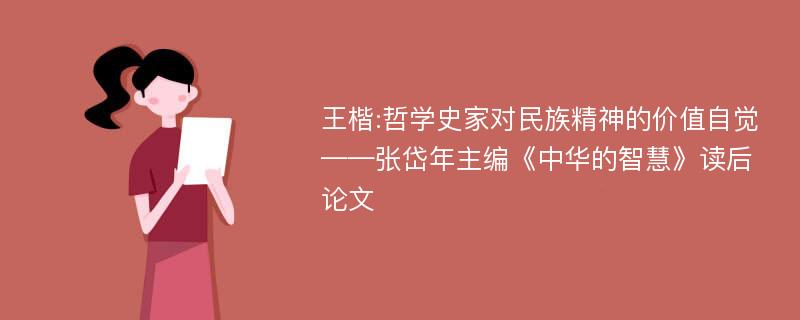
照西方哲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讲法,哲学本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推演开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诗),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沉淀,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亦自当就其哲学中观之。其在中国文化,此一层意思乃可归之于“闻道”,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劝学》)的讲法已然蕴含了此一层意思在其中。明乎此,则不难想见《中华的智慧》(张岱年主编,方立天副主编,程宜山、刘笑敢、陈来撰,中华书局,2017年11月版)一书成之于哲学史家之手实为一件幸事。不如此,则不足以拂其枝叶直探本根而究明其深情底理。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雅非晚近坊间种种弊弊焉以诸凡“品评”/“白话”/“心得”为事的文化读物所可同列者,幸留意焉!
一、思想与学术之间
本书成之于1980年代中后期,一个热闹而短暂的时代。晚近,人文学界习惯于将1980年代称之为思想的时代,而将此后数十年称之为学术的时代。这不仅是着眼于学界风气的转变,更有知识分子价值认同的演进存焉。特别地,此一时代差异由不同的人讲出来,或惋惜、或伤感、或欣慰,或惆怅……其间所蕴含的情感投射不尽相同,甚至于可能相反。偏好“思想”者,往往突出对时代的敏感意识,推崇对社会现实的犀利洞察及表达而倾向于宏大叙事;偏好“学术”者,则强调知识的真,注重规范的训练,追求推理和论证的严密,念念以空疏和独断为大戒。其实,学术与思想之间何曾如此地泾渭分明、画地自限?在理想的情形之下,学术与思想原可相辅相成,融合为一,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
照古人考据、词章、义理三分法的人文知识观,今人所谓哲学者大致对应于义理之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本身就是思想。回到学术史的话头,传统治学方法历来又有汉宋之分。逶迤至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乃有“北大学派”的出现,追求以汉学的精神治宋学,这便是学术与思想的打并归一了。原初,民国年间,清华与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各具特色,一重辨名析理,一重文献考据。1952年,院系调整,随着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诸先生到北大,两种中国哲学研究传统相互融合,于是就有了义理与考据兼重的“北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本书之作,其在当时,正是“北大学派”老、中、青三代杰出学人的联袂之作。如此的机缘,此后是不多见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失为“北大学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岱公乃一代宗师,自不待言。观《序言》一篇文字可知,这既是全书的纲,更是全书的魂。方立天先生平生致力于“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面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由其主笔书中的宗教部分,真可谓得其人矣!程宜山、刘笑敢、陈来三先生,年次略近,俱为岱门高第,其在当时,正当盛年。历经此后三十余年的发展,刘、陈二先生早已成长为各自研究领域中的引领者。唯惜乎宜山先生其寿不永,每每令人扼腕,致有岱门颜子之叹。如此看来,本书由岱公立其纲领、宗旨,岱门高第各以其专门分工协作,从而在整体理论格局和具体问题研究两个层面俱臻上乘,可谓代表了此类著作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学术水准。若就哲学方法上说,本书实现了分析与综合的理想统一。若就知人论世上说,其中又无疑融合了思想的情怀与学术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既属于1980年代,又走出了1980年代。
作为食品安全的技术保障部门,检验检测中心自然是行动的先锋。为做好技术保障,检测中心必须认真组织学习,认真分析食品安全现状,制定详细的抽样计划和检验检测工作方案,科学安排检验工作,尽量缩短检验周期。比如可根据不同食品特性和高风险食品种类,对重点样品做到重点监控、随到随检,提高行政监管的靶向性。
本书既名《中华的智慧》,相信多数的读者如笔者一样,最初是抱着看通识读物的心理预期拿起这本书的。且以寻常情理度之,此类谈智慧的读物即使略略有些浮华在其中也不是不可理解的。然而,本书则不然,通篇彰显出学术著作的谨严和扎实。岱公教人,向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为八字心法,这一点在本书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证。虽则受限于篇幅,每一单元皆要言不烦,不得如专著那样做充分的展开,然观其立意卓尔、持论平正、分析深刻、阐释精微,固非大家手眼不能到此。因此上,本书不仅有助于读者对民族智慧做通识了解,更为专门的学者树立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不特如此,熟悉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学者都晓得,冯友兰先生代表了通史时代,张岱年先生则开辟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此后就大抵进入了专人、专书的个案研究阶段。准此观之,本书另一个特别的意义就在于:在专人、专书的纵深研究有了一定积累的基础之后,重新对整个中国哲学史做一整体的观照和梳理。即此而言,本书亦可视为张岱年先生主导之下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在文化的意义上,这是一部在哲学层面探讨民族智慧的文化著作;在哲学的意义上,这又是一部突出民族智慧问题意识的哲学史,彰显出哲学史家对民族精神的价值自觉,幸留意焉!
二、时风有来去,圣学无古今
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所处的时代风气与1980年代相比已然是大相径庭,更遑论新文化运动时期。此一层意思已论之如左,兹不赘。不消说,时代赋予了国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更多的自信,这固然是我辈的幸运,然而,在当下的文化讨论之中,亦颇有一些学者在文化自信的旗帜之下,恨不能将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涂抹得面目可憎、一无是处,这就不免过了。
综上所述,林业是关乎到我国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工作,其工作效率对于国家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要想使我国生态林业建设效率有较大的提高,就要重视对技术人员的培训,从思想层面、专业技术到监测体系,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位才能够有效地推进林业技术在生态林业建设中的推广工程。就应用林业技术的必要性和作用而言,也要对林业生产手段进行优化,关注林业实践发展中的需求,积极地将相关的科技成果与实践工作进行统一,促进林业技术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时过境迁,历经四十年的“开眼看世界”,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早非昔比。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仍然处在进行时,国人对于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学理讨论也远未尘埃落定,然而,无论如何,那种将民族传统简单地视为现代性障碍的文化观已经不再是知识界的主流了。因此,较之三十年前,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望,本书在今天的再版理应得到更多读者“了解之同情”。这并不是所谓的风水轮流转,而毋宁说只是常态文化观的回归,所谓理有固然者也。当然,“时风有来去,圣学无古今”(王阳明语),一种文化传统固有的价值并不因时人的毁誉而有所增减。古人又云“修辞以立诚”(《周易·乾·文言》),说到底,著书立说唯在求吾心之所安,“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孟子·尽心上》),倘得如此,已称无憾,若有知音会心,又当是份外的幸事!
三、自信与自省
自本书初版以来,屈指已是三十个年头了。当其时也,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化更多地持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冷峻远大于温情,不实的苛责亦复不惜。从社会思潮的演进脉络而言,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主流文化观的接续。照此种文化观,人类文明是线性发展的,故中西文化的差异实为古今差异。从而,中华传统价值被视为与现代性截然对立的物件,不言而喻,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障碍和累赘。不难想见这一文化观所蕴含的结论:传统价值与现代性“二者不可得兼”(《孟子·告子上》),我们须得在其中做出取舍。甚至于,任何对传统价值的留恋即使不是心术上的“坏”,至少也是心智上的“蠢”。
即便在这种时代风气的笼罩之下,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从人数来说未必是主流——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的态度,因而往往被时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当然,这种对传统的同情,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拒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传统价值固然是前现代的,然而,前现代并不就意味着反现代,更遑论现代性自身亦有诸多基本的弊病。一般说来,哲学层面的价值理性是特定文化传统精神气质的观念化,实为一个民族文化认同之所系,容不得虚无化。在学理的层面,这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然而,吊诡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形之下,这种对民族传统“了解之同情”的文化观自身却难以得到“了解之同情”。张岱年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情者”。执笔诸先生怀着深沉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写作此书,观其行文,似冷实热,只是书生情怀已沉淀为一种平静的激情,落笔为文已是客观而理性的学术分析,而不以发思古之幽情自限,流连于小儿女之态的情绪表白。职此之故,将来若有学者考察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观者,于此当大有深意可观,不可草草放过!
首先,曾几何时,西化取向的学者将本民族传统文化妖魔化、污名化的种种做派尚历历如昨,如何又使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岂不愈发坐实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不见长进。夫子有云:“中庸其为至德,民鲜能久矣!”(《中庸》)信夫斯言!若揆之以儒家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一种偏执对待另一种偏执殊不足取。笔者愚见,真正的自信必然包含着自省的意识在其中。在逆境中不妄自菲薄,在顺境下不盲目自大,对自我与他者的优劣长短始终保持清醒而客观的审视才是真正的自信。幸得如此,方不负诸先生著作此书的心意。在此,笔者愿与有心读者共勉焉!
(2) “⟹”对任意x,y∈X,若η(x)=η(y),{x}-={(y}-,由X为T0空间,x=y,故η为单射。
其次,如前所言,对于出自西方文明的现代性,我们需要的是扬弃(aufheben),而非一味的迎合或者拒斥。同样,为着温故知新计,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价值亦当有所损益。“了解之同情”固为“正心”之本,“分析之批评”亦复不容少顷忘焉。要之,信得温情与冷峻相济而成,则庶几思过半矣!不成想,近些时日,听闻学者口中都换了新词,往日“现代转化”的话头已经鲜有提及,传统文化一夕之间又仿佛成了被红尘中人遗忘了的世外仙源——一种较现代性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浑不以近二百年来国族坎坷遭际为镜鉴。若从公而论,这种中西对峙的文明观委实不能不让人深感不安。不消说,现代性有着诸多弊病。然而,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所言,作为“一项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自身尚在演进之中,因其不完善而遽然否定其历史合理性恐怕有失公允。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要克服现代性的弊病,也须得“达后如此”,而非“捨后如此”,此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就中国的当下情形而言,现代性造成的弊病自然不容等闲视之,然而,更基本的弊病乃根源于反现代性,而非现代性,此亦不可不察也。特别地,某些反现代性分明与民族传统无涉,甚至即使在传统中亦为人所不齿,却偏偏施施然以民族传统自居,直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在此背景之下,径而以民族传统否定现代性的想法,无论其动机如何,都绝非国人之幸。职此之故,吾人理应对于那种中西二元对峙的文明观始终保持一种足够的警醒,无论它以何种面目出现。
复次,就缘起而言,《中华的智慧》乃是有鉴于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西方的智慧》而做。笔者浅见,类似这样的书籍,应该是每一个具有基本的国文基础的读者都能够自由阅读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不免过于理想化了。一个大学生阅读此书可能困难不大,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读者恐怕就难免吃力了。委实,诸先生写作此书已经努力做到了深入浅出、平易晓畅。只不过,民族传统文化历经百余年的边缘化,不可避免地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许多常识性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已然成为了专门的学问。吾邦所以称华夏者,文明之谓也。今不意吾辈与先贤礼乐竟疏离至斯,宁不可悲?极而言之,除却血统的意义之外,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还能声称自己是中国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职此之故,在今天重温传统不仅意味着个体性的文化教养,更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再中国化”的过程。就此而言,较之专门性的学术研究,以中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为受众的博雅教育甚至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此,唯愿吾辈深耕社会底层的民族文化教育,如此再过三十年,希望那时的国人阅读此书的时候,笔者今天的忧虑已经是多余的了。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苟子的礼乐修养观及其心性论基础”(18ZXB00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编号】2096-1723(2019)01-0125-04
【作者简介】王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永芝]
标签:本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苟子的礼乐修养观及其心性论基础”(18ZXB005)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