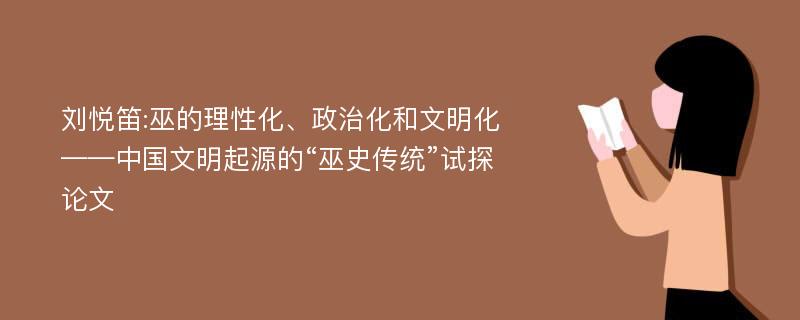
摘 要:所谓“巫史传统”可以被视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之一。然而,巫并不能等同于萨满,巫与萨满之间形成了不即不离的关联。通过“化巫为礼”“化巫为权”和“化巫为史”的历史解析,捕捉中土之巫的理性化、政治化和文明化,这也恰恰是中国文明的特质所在。这是由于与中国文明不同的外部文明一般都走出了巫术阶段,而中国文明却续存了巫史传统,并以自己的智慧将之进行了深度转化。由此,张光直先生的两种文明模式(中国是连续性的而西方是突破性的文明)与李泽厚先生的两种世界模式(中国是一个世界而西方则是两个世界)就可以贯通起来。西方的“突破性”文明走出了巫术却向外寻求另一个世界,而中国“连续性”文明的大智慧就在于走的始终是“一个世界”之途,从而既承继了巫的传统又超越了巫的传统,由此方能形成“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的文明之道。
关键词:巫史传统;化巫为礼;化巫为(王)权;化巫为史;天人合一
在考察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巫史传统”给人以崭新的启示和思路①。本文就以“巫史传统”思想为考察中心,试图来重探中国文明起源之路,并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其他诸文明之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就在于它源于巫又超越巫,“化巫为礼”(巫的理性化)“化巫为权”(巫的政治化)和“化巫为史”(巫的文明化)乃是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根本要义。
一、“巫”与萨满:不即不离的关联
巫,到底如何界定?西方的研究者往往从萨满(Shaman)的角度来观巫,由此认定巫属于萨满的一种类型,或者说,巫就是中土的萨满(当然满族的萨满无疑是典型的萨满,但是在广义的红山文化那里存在的则是典型的巫),甚至将巫与萨满视为同一。萨满这个词,一般认为来自通古斯语而通过俄文得以传播,本来形容一类有特殊能力的人群,该词本有智者与洞彻之意,但其更深远的来源则是巴利语samana,并通过中文萨满(sha-men)对巴利语的转写而得以播撒开来,并在19世纪为大多数东方学者所接受[1]495。萨满主义或萨满教(Shamanism)通常被认为是分布于北亚一代的原始信仰,通过特定的仪式活动而与天地生灵进行身心沟通,甚至可以上天(堂)入地(狱)做时间旅行,以达到控制天气、预言、占星、解梦、治疗、问卜等现世目的,当然这种广为接受的界定,更多把萨满视为一种在宗教产生之前的人类原始文化。
那么,巫与萨满如果不同,它们到底是什么关联呢?如果趋同,两者到底是不是同一的呢?按照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意见,把“巫”译成shaman(萨满)还是合适的,因为他的英文版著作《艺,神与礼:古代中国走向政治权威之路》的第三章就是专写“萨满教与政治”,这章标题在汉译那里却被翻成“巫觋与政治”[2]44-45。张光直先生基本接受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在《九歌:古代中国萨满主义研究》中的意见:“在古代中国,鬼神祭祀时充当中介的人成为巫。可见,中国的巫与西伯利亚和通古斯地区的萨满有着极为相近的功能。因此,把‘巫’译为萨满是……合适的。”②在中文当中,张光直先生还曾使用了“巫教”的说法,但相对应的英文表述仍是Shamanism,他曾论证从祈求对象(鬼神神灵)、媒介人(巫者)、信者及其宗教仪式等角度来观之,巫术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了宗教基本体系的“巫教”[3]1-3。
巫与萨满,因为功能的相近就视为同一,却并没有得到巫术权威研究者们的赞同。著名的罗马尼亚宗教学家米歇尔·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更把萨满视为一种遍及全球的现象,但是他却并不认为巫与萨满是相同的,尽管他也注意到中国的“巫”与满族、通古斯族和西伯利亚萨满主义在“总体上”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巫仪式当中的“性和纵欲要素”方面[1]455,但伊利亚德却忽视了中土之“巫”超越了这些要素的维度,这才使得巫与萨满保持了特定的距离。笔者认同这种观点,巫不同于萨满,尽管两者有着近似与类通之处,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或者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联。
按照伊利亚德的用法,中国“萨满主义”或“萨满教”(Chinese“Shamanism”)称之为“巫主义”或“巫教”(wu-ism)更为准确,他给出这样的判断:萨满是儒教之前的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中国的‘萨满主义’(巫主义,Groot如此称之)在儒家与国家宗教居主导之前,占据了中国人宗教生活的主宰”[1]454。文中“巫主义”的说法,其实就来自于欧洲最早研究中国宗教的这位荷兰人类学和汉学家高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出版的六卷本《中国宗教系统》的居前诸卷里面③,而后曾被西方汉学界所接受。但是在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当中,似乎将巫与萨满视为同一事物却渐成主流。
要做好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是需要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又有关部门制作出多套财务预算方案,在经过企业中的各个部门的认真挑选,选择住一套最合理有效的方案。而这套方案需要企业中的各个部门去完成的。所以说财务预算管理具有系统性。需要企业的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团结协作才能把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完成好。如果有一个部门没有将这个财务预算完成好,将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每个部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完成制定好的企业财务预算计划。企业可以规定相应的奖罚制度。对完成好的给与相应的奖励反之对完成不好的部门加以批评教育。这样可以使各个部门更好的去完成方案。
二、“化巫为礼”:巫的理性化
“化巫为礼”在李泽厚先生那里表述为“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其同名专著《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近期已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正标题则被改为《中国思想的起源》,可以注意到,该书副标题“From Shamanism to Ritual Regulations and Humaneness”被直译出来就是“从萨满教到礼的规定和仁”[5]。西方学界往往从宗教的大视角来看待萨满教,当然人类学家更看重萨满与宗教之间的差异,或者从巫术走向宗教的历史进程,李泽厚先生则更为关注这两者差异的本质。但无论怎样说,中土之巫并不是宗教,起码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李泽厚先生的表述非常明确:“‘巫’的特征是动态、激情、人本和神不分的‘一个世界’。相比较来说,宗教则属于更为静态、理性、主客分明、神人分离的‘两个世界’。与巫术不同,宗教中的崇拜对象(神)多在主体之外、之上,从而宗教中的‘神人合一’的神秘感觉多在某种沉思的彻悟、瞬间的天启等人的静观状态中。”[6]13这意味着,巫所承继的乃是中国“一个世界”的思想之源,而西式宗教则是建基在“两个世界”基础之上的。
显然,王族不仅垄断了祭祀权,只有他们具有祭祀天帝与祖先的权利;而且,也把自身给神化了,他们由此成为天帝、神明在民间的化身。“在‘绝地通天’时期,只有地上人王以全民代表的名义拥有与‘帝’或‘天’直接交通的特权(另一方面,王对于万民则号称他是奉‘帝’或‘天’之‘命’在人间建立并维持秩序的)。但是他不须通过一种特有的神奇法术才能和‘帝’或‘天’取得直接联系,这便是所谓‘巫术’。王或者以‘群巫之长’的身份,或者指派他所信任的巫师主持天人之间的交通。所以我称这种交通为集体方式的‘天人合一’,即由地上的‘余一人’代表人民的集体与‘天’合一。”[12]163余英时先生称这种天人交通方式为“集体的天人合一”,其实并不是全体,而是王代表了民与天地进行沟通。在家为巫史的时期,民众争相为巫,巫的地位下降了,也无需某位领袖代为行之了。后来,“祀与戎已发展为神权和王权。担任祀与戎职责的人已形成为阶层,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社会的权威”[19]246。于是,随着“军巫”地位的抬升,王也是邦国的军事首领,最终,只有君王才能成为群巫之首了。
这就通过“动”与“静”之别,使得巫与宗教得以最简约的分殊,当然李泽厚先生从张光直先生说,认定巫应为 Shaman[6]6。然而,中土的巫与萨满的重要区别在于,巫的活动也并没有去“强迫或压制”神灵,而是通过与神灵的沟通达到自我的目的。按照陈来先生的归纳,这种差异就在于:其一,“中国古巫的活动是以神灵观念为基础的”;其二,中国古巫活动“谄媚和取悦神灵”[10]45-46,这大概更加符合中国人“天人交合”的原始传统。由此,陈来先生认定中土的巫并不属于无神灵的自然萨满那种“原生形态”,而是“神灵观念较为发展时期的次生形态”[10]47,这似乎也预设了巫是发源于萨满,但是巫与萨满却中西分殊。
下面,我们就要给出巫不同于萨满的三个基本面向——“化巫为礼”“化巫为权”“化巫为史”——而这三点恰恰是所谓中国“巫史传统”的基本特质。在这个意义上,将巫史传统定译为“shamanistic-historical tradition”(萨满加上史的传统)[4],也就显得并不那么准确了。还是要翻译成“wu-historical tradition”更为恰适与切合。
巫与政治的关联,应该是“化巫为权”,更准确地说,乃是化为“王权”。巫与王的合一,究竟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李泽厚先生指明了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个关键,“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通天’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即使后来分化出一整套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但自大的‘巫’仍然是‘王’、‘君’、‘天子’”[6]6。这种说法较早来自于陈梦家先生,他认定作为政治领袖的王者即“群巫首”[14],而后这种观点被从李宗侗先生、杨向奎先生到张光直先生等所主张,比如这样的主张:“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15]164,再如“萨满,因而成为每个国家朝廷的核心组成部分;事实上,古代中国研究者们认为,国王实际上就是萨满头领(head shaman)”[2]45,这个萨满头领其实就是“首巫”。不可忽视的是,饶宗颐先生、李零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并不认为巫有如此高的地位。这里面一定有“大巫”与“小巫”的分殊,前一类主张巫被政治化的学者基本持“大巫”说,认定巫曾处于大传统之中,后一类学者基本认为巫尚未被政治化,基本把巫圈定为小传统当中的“小巫”。
治理区属低缓丘陵区,海拔高程30.00~37.00m,相对高差7.00m,地形比较平缓,坡度一般5°~10°。
近些年来,西方研究者开始关注萨满早期形式对于史前时代“认知进化/认知革命”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人类学家维尔兹斯基(A.Wiercin'sk)所提出的萨满起源的复杂模型,它被叫作“维尔兹斯基模型”。按照这种模型,随着“狩猎业的强化”,“狩猎技能的渐进传授和自然环境知识的转移”,这就需要“全面发展人的意志力潜能”,由此形成了“人与世界的萨满模式”;与此同时,“狩猎业的强化”也带来“高效狩猎的准备”,这就需要“感知力和耐力训练”,进而这就关系到萨满的“过关”模型,它需要“禁食,疼痛折磨,遭遇险情,极限跑等”。这就一面“与先天的情绪调节机能脱离,用情感标准培养意志力”,另一面“某种生理机能被剥夺导致的结果:或因机体异常反应产生的变化,或有有意识自我控制和打通潜意识途径训练”,“与环境的自然条件脱离”后,从而都回归到“全面发展人的意志力潜能”。同理可证,“采集业的强化”也是如此,它导致了“致幻剂的发现和使用”,进而通过“(仪式性死亡)开启前世记忆与现世记忆通道”,从而“超越自我—积极参与社会心理活动”,最终从另一条通途形成了“人与世界的萨满模型”[11]。这就从理论模型的建构角度,证明了萨满对于人类认知的促动,李泽厚先生从巫术经由技艺到科学的发展,也是可以由此得到间接明证的。
“亲其师,信其道”,徐老师的学生深感此间的幸福,与他们的老师行走生活和课堂,自由奔放着无限的思绪;“爱其生,悦其心”,这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已然在徐老师的心中成长为十里桃林,灼灼其华地炫美着师生的人生。
与西方从巫术到科学和宗教的理路不同,中国的巫则走了另一条道路,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就是“理性化塑建”之路,外在的塑建就是人文之“礼”,内在的塑造则是人性之“仁”。而且,以“仁”为核心的人性与以“礼”为核心的人文,乃是内外合一的。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呢?这就关乎到李泽厚先生私下常说的所谓中国文明的“两步走”,这也是不同于余英时对中国文明起源描述的关键所在。用李泽厚先生言简意赅的话来说,这两步走就是“周公把巫术外在化为人文制度,孔子把巫内在化为人性情感”[6]112,亦即周公“由巫到礼,政治脱魅”,孔子“建构情理,释礼归仁”[6]142。
巫的政治化,或者说化巫权为“王权”,这对于儒家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由政治领袖的‘王’作为最大的‘巫’,来沟通神界与人世,以最终作出决断,指导行动。这意味着政治领袖在根本上掌握着沟通天人的最高神权”[6]6。更为重要的是,特别是于后世而言,只有实现了这种政治化的巫或者巫的王权化,儒家后世所谓的“内圣外王”才有可能!这是由于,一方面,一般的没有占据君主地位的人,他也并没有“外王”的权利和权力;另一方面,只有王与巫相通,才能有“内圣”的天赋与动力。所以说,巫作为大传统,其实可以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根源,所谓“内圣外王”的思想就是源于“化巫为(王)权”!
其实,无论是外在化,还是内在化,都有理性化在其中起到转化功用。外在化当然是体制化,理性无疑在其中占据绝对主导;内在化则是寻求一种情理平衡,孔子可谓是建构出了中国人的“情理结构”(the emotio-rational structure)。李泽厚先生更多是从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历史学者则给出了近似的结论,按照杨向奎先生从”礼“的角度所做出的同样两步走的分析:第一次是“制礼作乐”的西周周公减轻了礼物的“交易性质”而增加了“德”与“刑”的内容,同时也添加了“乐的成分”;第二次则是“礼云”“乐云”的孔子,他除去了礼的“商业内容”,而以“仁”和“礼”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同时又整顿了趋于紊乱的乐[13]277-440。依据这种说法,周公不仅“定”了礼而且将“礼乐”联姻,而孔子则将这种传统加以合法化和规范化,从而保存和延续了“礼乐相济”的悠久传统。
按照一般的理解,绝地天通就是与天地通嘛!但是历史学者李零先生的反对意见却显得很异端:“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可见‘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18]这就把巫与史的关系,加入了进来,后面我们再详考。这段问的就是:《周书》记载重、黎使得天地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并无此事,那么“民”可否登临天界?这背后预设的问题就是,王族代表了民由此绝地天通?还是民本身就有权绝地天通?
三、“化巫为(王)权”:巫的政治化
巫在中西发展之间实现了不同的发展路数,按照李泽厚先生的宏观视野,“西方由‘巫’脱魅而走向科学(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发展而来)与宗教(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转化而来)的分途。中国则由‘巫’而‘史’,而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6]13当然,这只是个历史大视野的描述,不过李泽厚先生的整体梳理却意味着,西方主流从巫术的发展阶段走了出来,祛魅之后走了认知与情感两条路,科学是认知之路,而宗教是情感之路,两者都蕴藏在巫术当中。从巫术走到宗教,这条感性之路,几成共识,没有问题,但是巫术何以开出科学理性之道呢?
“真”的另一方面是创设情境必须有用。情境创设与新课导入不同,它是教师课堂教学活动的平台,是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有效载体,是贯穿整个课堂的教学主线。因此,情境创设要对整节课堂的教学内容有直接的作用,学生能依据情境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李泽厚先生则认定,“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征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6]10,以对应于小传统中的小巫,也就是延续至今的巫师传统。由此,巫作为大传统在李泽厚先生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发源那里就占有了至高的地位,而且远远高于一般学者的理解。应该说,“王巫”的阶段,在中土一定是曾经存在过的,红山文化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这可以另文详述。
当代学者根据考古资料也提出了巫的历史发展的新看法,那就是发展四段式:“神巫→家为巫史→神巫、军巫→王巫。”[16]124这其实是描述出巫地位的先升而降再而升的历史进程,神巫阶段:巫的崇拜=神的崇拜;家为巫史阶段:人人皆巫不识巫;神巫、军巫阶段:部落首领=大巫;王巫阶段:王=大巫。根据这种更为精细的划分,最终王与巫得以合流,巫权就等于王权,或者说,巫权被上升为王权。按照李宗侗先生在《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当中对中土王权的历史情况的讲述:“王的职务,亦即邦的政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祭祀,一种是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共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实在古邦的政治不过如此……王有护持邦火不灭的职责,他须朝夕祭祀,并时常与族长共同在神前聚餐,名为公餐……祭器及祭品,亦随各邦自己的礼仪而不同,但各邦的皆一成不变,不许稍有改革。”[17]16这种更为具体的描述使得后人可以窥到当时历史的实情。
公平是新时代全球公民的共同追求,各个国家也通过设置各种法律来维护、保证公平。而经济法就在经济体系的运行发展中相对提高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绝地天通”?这就关系到对《国语》当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那段被反复引用的文本的理解:“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此外,李泽厚先生与余英时先生关于中土之巫的根本理解,另一个巨大差异就在于,后者认定巫只是在早期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在“轴心突破”时代之后巫传统就衰落了,“在轴心突破以前,‘天人合一’完全依赖巫作中介,以建立‘人’、‘神’之间的交通管道。但在轴心突破以后,哲学家(或思想家)则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与‘道’合一,在这个新系统中,巫已不能发生任何作用了”[12]171,然而前者认定巫史传统迄今并未中断,反而成为由古至今中国“情理结构”的根基,且经过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倡导而广为接受的“轴心时代”观念是否能成立,也是需要质疑的一种思想界的共识。
英语影视作品的在教学中的应用已经得到了诸多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的重视,其优势在跨文化交际课堂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于巫术与宗教之别,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就已经归纳得相对准确:巫术“强迫或压制”神灵,而宗教则是“取悦或讨好”神祇[7]79;用阐释者的话来说,“据弗雷泽认为,宗教总要涉及求助于神,而巫术与神没有任何联系”[8]153;用更准确的话来阐释,弗雷泽认为“人类开始企图用巫术手段控制环境,后来一旦发现这种控制是不可能的,于是便转向了宗教。宗教之不同于巫术在于:巫术的论据是以不变的法则为基础的,而宗教则以对于控制性力量的信仰为基础”[9]118。这实际上近似于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宗教中的人总是求助于外在于人的那个神,人神即使相通也是静态的冥一,但是在巫当中人与神本然未分,而且是动态的融合为一体。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巫的地位尽管上升到人间的顶端,但是王权与巫权看似合一实乃必有内在争夺:“王要的是发号施令的权利,想的是借助巫来强化统治地位。两者表面上统一,但已渐行渐远。从历史进程的走势看,王权的树立,实乃逐渐开始去巫化的标志。”[16]124这就意味着,随着王权的垄断神权成为既定事实,那么,王权终会压倒神权,历史事实也是后代的王君,也就不再扮演首巫的角色了。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对此有过历史梳理,“王权之前,已存在神权。从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至西周时期,无非是自神、王权并立的社会,演变为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乃至神权成为王权的附庸的历史过程”[19]287,这即为王权对神权“夺权”的历史过程,这个描述也是比较公正的。
总之,在水权初始分配过程中,政府一方面需要为水权初始分配创设合理分配规则;另一方面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调整合理分配规则。问题是,为什么不让市场作为合理分配规则的发现者呢?譬如,拍卖机制或许是判断何为合理用水的最佳选择,因为价格机制是偏好的最佳反映。但是,很少有国家将拍卖机制作为水权合理分配的机制。这或许源于一方面各国长期通过免费分配而非拍卖等价格机制来分配水资源;另一方面拍卖水资源可能会导致水资源垄断,因为出价较高者可能会垄断水资源。
这就是从周公的“制礼作乐”到孔子的“释礼归仁”的发展:第一步,“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不同于西方由巫术礼仪走向宗教和科学的分途”[6]28。西方科学的理性与宗教的感性是割裂的,或者说科学管认知,宗教管情感,理与情本身就是割裂二分的。然而,这种断裂在中国“情理合一”智慧与践行那里却并不存在。第二步,才是孔子的“轴心突破”,假如我们使用“轴心时代”与“哲学突破”这样既有观念的话。余英时先生却没有注意到第一步,包括在他更早的手稿当中(但是余英时先生却开始关注到了“巫—萨满主义”的作用④),周公这一步却被李泽厚先生高举了出来。余英时先生一方面接受了“孔子和儒家不但不是巫,而且尽最大努力与巫传统划清界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定“孔子对于商代几位大巫师的记忆,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他想将天‘道’传播到人间的强烈使命感”[12]135,145。李泽厚先生则没有那么欲说还休,直接就认定“巫史传统”从周公到孔子都被继承了下来,只不过周公将之外在化,孔子将之内在化。
四、“化巫为史”:巫的文明化
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巫史传统”,之所以不叫“巫之传统”,恰在于他非常重视由“巫”到“史”的历史进程,这也是很多历史学者并不赞同的地方。这就又关系到巫与史的基本关联,如果巫彻底转为史,那么巫会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呢?事实上,后代巫与史的职能,的确被分裂与隔离开来,史专注于史本身,巫则衰变为小巫了。
按照通常的解读,“古邦掌祭祀者,亦记载邦中一切史事,亦兼审判,故士亦是史,亦是士师。古代礼记既包括《礼》《易》《春秋》等书,士或史亦兼任后世祝、宗、卜、史的职务”,史书里既有祝宗连用的,也有祝史并用的情况,“由此足见祝与史、祝与宗的职务,分为不甚清楚”[17]46-47。然而,巫与史到底是如何关联的呢?这其实关系到巫的身份演变,历史上巫史的确联系紧密,但是显然史既不是掌权的大巫,也不是后世那种小巫,顶多属于“中巫”类型。但是,历史的记载,很可能就是从记述“巫事”开始的,同时兼及“王事”。这是由于,“以王事为中心的历史形成于记巫事的历史。其开始阶段,王事即巫事,王事活动主要是巫事活动。即使是后来,大量的军事、政治、外交活动,也离不开祭祀、占卜等项”[20]301,这就把史的起源与巫的政治化连纵了起来。或者说,“化巫为史”本就来自于“化巫为(王)权”。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由史到巫,关键也在于理性化,不仅巫可以理性化为礼,而且,史就是巫的理性化。“一方面,‘史’即是‘巫’,是‘巫’的承继,‘祝史巫史皆巫也,而史亦巫也’;另一方面,‘史’又毕竟是‘巫’的理性化的新阶段,特征是对筮——‘数’的掌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史’与‘巫’对天文、历法的掌握,这就是所谓‘识天象’与‘知地理’”[6]18。的确,数字天文地理历史诸类知识掌握,需要的是人类思维的理性化。但是,笔者更想确定的是,这不仅仅是理性化的过程,更是一种“文明化”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各地的萨满传统不同,中国文明恰恰把巫传统得以文明化了,所以才把这种传统包孕在自身文明的内部,一直延续至今。
按照考古学家吴汝祚先生全方位的研究,巫除了扮演祭祀者的角色之外,与此同时,1.“巫是观测天象掌握天文知识者”,仰韶时期的古人就明了日月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联;2.“巫是有地理知识者”,居住与礼仪建筑的地址选定及规划巫者起到重要作用;3.“巫是具有一定数理知识者”,巫者是具有数的知识和几何概念的人;4.“巫是具有一定医药知识者”,巫不仅事神致福而且凭医术救人;5.“巫是重要建筑工程的设计者”,史前重要建筑为巫者所设计;6.“巫是中华古代文化的传播者”[21],这无疑是比较全面的对巫之身份的解析,尽管未突出史作为官职的地位,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些知识的掌握者在后来的历史格局里都变成“专门人才”了。
李零先生在阐释《国语·楚语下》“绝地天通”的故事之时,有着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意见,认定这则所论的不是天人交通进而合一,反而讲的是天人阻断进而分裂,理由就在于:这段文本“以重、黎分司天地讲祝宗卜史一类职官的起源,特别是史官的起源(包括司马迁这一支的来源),因而涉及宗教发生的原理。故事要讲的道理是,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18]。这就意味着,“绝地天通”就是不通天地,因为李零先生侧重于由巫到史的历史角色的转变来加以阐发,他把祝宗卜史视为巫的对立面,这些专业的角色一出,不仅祝宗卜史之间得以专业分工,而且祝宗卜史的出现就直接造成了巫的衰落,因为巫所呈现的理性知识传承的功能,被祝宗卜史所分割了,因而巫只能走向了衰微。
台湾历史学者林富士在《巫者的世界》当中,对于从“古巫”到“今巫”之间的古今之变做了历史梳理。他指出了其中最重要的历史变化,“古代‘国家’(或‘社会’)祭祀鬼神(天神、地只、人鬼“)之事,原由‘巫觋’主掌,东汉末年的‘巫祝’则无法招降或凭降‘正神’(正神不降),只是祭祀一些‘厉鬼’,变成国家‘祀典’之外的‘淫祀’”[22]2,这个历史描述是相当重要的。巫的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起码从先秦时代开始,所谓民巫(民间的职业巫者)与营业之巫就开始出场了。与此同时,禁巫与抑巫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这其实就是在言说一种从“大巫”到“小巫”的历史转变,在中国小巫传统与世界各地萨满传统一样,至今存留下来。然而,大巫的传统仍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明当中得以葆有,这恰恰是中土特色所在。
所以,巫史并称在李泽厚先生那里被凝聚为“巫史传统”,并不是仅仅强调了脱巫而来的“史”的传统,这只是狭义上的价值,更广义的意义在于巫的“文明化”,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所在,这才是广义上的价值:只有把巫之传统得以文明化了,巫才能被文明社会存续和包孕,如此重视天人交合与历史传统的中国,它的“巫史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反而一有恰当的历史境遇就得以勃发出来。
大数据技术是通过一个一个压缩包来对大文件进行压缩,这一做法能够不断地将信息实时地传输到电脑之中,并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对下一个文件进行解压,从而实现视频观看的实时性,只要在前期加载十几秒即可流畅地对整个视频进行观看。这种方式与之前下载后再进行观看的方式相比不仅节约了时间,缩短了延时启动,还降低了缓存要求的空间,并对实时传输协议进行了完善,方便学生进行观看。
五、结论:中国文明源于巫又超越巫
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质,就在于其源于巫又超越巫,李泽厚先生的“巫史传统”说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德国大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将人类的神话思维作为“思想形式”“直觉形式”和“生活形式”来加以看待[23]27,71,153,中土的巫史思维其实也是如此,它既是一种感性的直觉形式,也是一种理性的思想形式,但最终化作了中国人的生活形式,但它终是情理合一的,从而深刻地内在塑造了中国文明传统。如上所述,通过“化巫为礼”“化巫为权”和“化巫为史”的历史解析,本文试图捕捉到巫的理性化、政治化和文明化,恰恰是中土之巫不同于外部萨满之处,也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根本差异所在。这是由于,与中国文明不同的外部文明一般都走出了巫术阶段,而中国文明却续存了巫史传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曾蒙昧未发,而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将之进行了深度转化。这直接涉及张光直的文明比较研究,亦即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转化有“连续性”与“突破性”的两种模式:“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份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24]17-18由此一来,张光直先生的两种文明模式(中国是连续性的而西方是突破性的文明)与李泽厚先生的两种世界模式(中国是一个世界而西方则是两个世界)就可以贯通起来。
质言之,西方的“突破性”文明走出了巫术却向外寻求另一个世界,从而形成了现世界与理念界、此岸与彼岸、现象界与物自体“两个世界”的分殊,然而中国“连续性”文明的大智慧就在于走的始终是“一个世界”之途,从而既承继了巫的传统又超越了巫的传统,由此方能形成“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的文明之道!
注释
①李泽厚:《论巫史传统》(1999)和《“说巫史传统”补》(2005),参见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②参见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静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③Johann Jakob Maria de Groot.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Ⅰ-Ⅵ)[M].Leiden,1892-1910.④ Ying-shih Yü,“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英文打印稿复印件),其中第20页中讲到仁与“shamanistic culture”(萨满文化)相关联的时候,亲笔在打印稿子上增加为“wu-shamanistic culture”(巫—萨满文化),在第59页还写到“古代中国的巫—萨满主义(wu-shamanism)的政治史却并没有被撰写下来”。
4)经验总结。无核白鸡心花前处理,因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气候,处理的浓度有很大不同。应该结合土壤持水量、空气湿度、新梢长势及花序分离时间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Mircea Eliade.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2]K.C.Chang.Art,Myth an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M].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3]张光直.人类历史上的巫教的一个初步定义[J].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93(49).
[4]Paul J.D’Ambrosio,Robert A.Carleo III and Andrew Lambert,On Li Zehou’s Philosophy:An Introduction by Three Translators[J].Philosophy East&West,Volume 66,Number 4,October,2016.
[5] LiZehou.The Origins of Chinese Thought:From Shamanism to Ritual Regulations and Humaneness[M].translated by Robert A.Carleo III,Leiden:Brill Publishers,2018.
[6]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北京:三联书店,2015.
[7]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8]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9]夏普.比较宗教学:一个历史的考察[M].吕大吉,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10]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9.
[11]米哈伊·霍帕尔,梁艳君.萨满与认知的演变[J].世界民族,2017(6):72-78.
[12]余英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3]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4]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J].燕京学报,1936(20):485-576.
[15]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16]张潮.神话·考古·历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7]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 历史的剖面[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8]李零.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EB/OL].(2010/06/05).http://www.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002.
[19]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进程[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20]张紫晨.中国巫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1]吴汝祚.中华古代文明与巫[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2]林富士.巫者的世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23]Ee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
[2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The Rationalization,Politic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of Wu:An Exploration of the“Wu-Historical Tradition”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iu Yuedi
Abstract:The so-called“wu-historical tradition”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However,wu can not be equated with shaman.There is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wu-ism and shamanism.Through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turning wu into rites”,“turning wu into king’s power”and“turning wu into history”,we can catch the rationalization,politic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of wu on Chinese Land,which is exactly the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is is because,unlike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external civilizations had generally came out of the wu-shaman-stage,whil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survived the tradition of wu-history,and had mad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wu in its own wisdom.Thus,Kwang-chih Chang’s the model of Breakout-Continuity in world civilization(China is a mode of continuity while the West is a mode of breakout)and Li Zehou’s two modes of world in world thoughts(China is belong to one-world while the West is belong to two-worlds)can be connected each other.The breakou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ne out of shamanism but sought another world.The great wisdom of continu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always seeking for a path of one-worldness,which not only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wu,but also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 of wu.Only by this way,Chinese civilization could form a road of“heaven and man are united as one”.
Key words:wu-historical tradition;turning wu into rites;turning wu into king’s power;turning wu into history;heaven and man are united as one
中图分类号:B9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9)02-0020-08
收稿日期:2019-01-19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儒家情感哲学研究”(17GCGX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悦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辽宁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比较哲学、情感哲学和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 齐]
标签:中国论文; 萨满论文; 传统论文; 王权论文; 巫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术数论文; 迷信论文; 《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儒家情感哲学研究”(17GCGX14)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