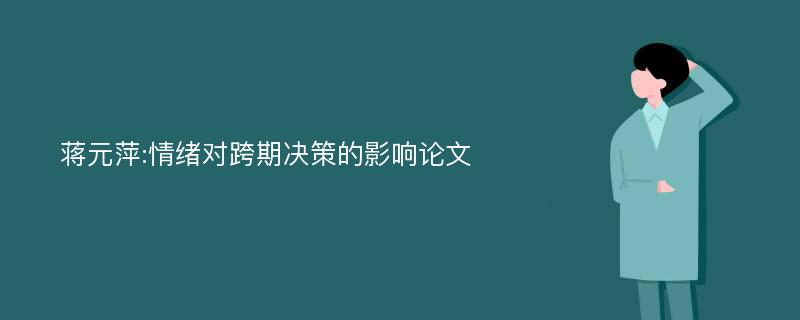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蒋元萍 孙红月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近年来,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根据情绪发生于跨期决策过程中的时间, 可以将其分为决策前情绪、决策中情绪和决策后情绪。目前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的研究, 尤其是决策前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 大多还只是停留在揭示现象的阶段, 较少有研究直接验证其中的影响机制。综合运用行为实验和神经影像学的手段从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揭示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行为机制和神经机制, 将有助于加深对跨期决策心理机制的理解, 并帮助人们更好地利用和控制情绪以做出更满意的决策。未来研究还需加强研究的深度和生态效度, 如考察动态情绪、日常情绪和复杂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并在情绪干预方面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关键词情绪; 跨期决策; 决策前情绪; 决策中情绪; 决策后情绪
1 引言
跨期决策是指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 进而做出选择的过程(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跨期决策需要决策者在眼前的利益得失与将来的利益得失之间做出权衡与取舍, 是既关系人类个体利益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决策。例如, 在投资领域, 投资者会面临选择收益小获利快的投资产品还是符合收益大获利慢的投资产品的跨期决策问题; 在能源开采领域, 决策者面临着“尽量满足当下利益而不顾子孙后代”或“少量开采以使能源持续利用”的跨期决策问题。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 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模型, 以期对跨期决策的行为进行描述。1937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amuelson (1937)首次提出折扣效用模型(Discounted-utility model)。根据该模型, 人们将对未来不同时间点的效用按同一比率(时间折扣率, Discounting rate)进行折扣, 而折扣后的未来各期效用之和, 就是个体对该选项赋予的总效用。但随着折扣效用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异象(Anomalies)不断出现, 研究者通过修正折扣函数等方式发展出不同的折扣模型对异像进行解释(Laibson, 1997; Loewenstein & Prelec, 1992; Mazur, 1984), 如双曲线折扣模型(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和准双曲线折扣模型(Quasi-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等。然而, 单纯的依靠精密的计算思维进行决策似乎总是不太符合实际表现, 人们在不确定世界中不可能时刻以一种高度理性的计算思维去进行决策。因此, 一些学者开始背离主流的理论发展路径, 从有限理性的视角提出了启发式模型, 如属性比较模型(Attribute-comparison model) (Read, 2001)、相似性模型(Similarity model) (Leland, 2010)、齐当别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 (Li, 2004)、权衡模型(Tradeoff model) (Scholten & Read, 2010)等。这些模型认为, 跨期决策过程不是基于折扣求和的最大化规则, 而是通过比较维度之间的差异, 选择比较中占优势的选项。
在这个过程中, 情绪也从最初的被忽视并加以控制, 发展到跨期决策领域中的重要变量。近年来, 在跨期决策领域相继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但由于各个研究中关注的情绪类型或者视角不同, 使得我们在归纳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时, 难免困惑。因此, 本文将从情绪发生于跨期决策过程中的时间维度——决策前情绪、决策中情绪、决策后情绪, 系统梳理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以期通过这样的梳理, 让情绪这一因素在跨期决策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展现更加清晰的脉络, 加深我们对跨期决策心理机制的理解。
2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2.1 决策前情绪
决策前情绪称为背景情绪, 又可以称为偶然情绪, 是由当前决策任务无关的其他因素引起的情绪体验, 它伴随我们日常生活经验质量的好坏而波动。例如:个体的情绪体验会受到看似不相关的天气条件影响, 个体身体状态的好坏也会左右人们的情绪。背景情绪虽然非决策任务所激发, 却始终伴随决策过程, 通过改变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评估而影响后续决策或直接对个体随后的决策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涉及背景情绪的大多数研究中, 研究者通常会在开始进行决策任务之前通过一定的情绪诱发方法来启动被试的情绪状态, 以探讨背景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例如, Pyone和Isen (2011)通过图片和词语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 发现积极情绪会使被试更富有远见, 有更好的自控力和忍耐力。Liu, Feng, Chen和Li (2013)的研究显示, 想象积极情绪事件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奖赏, 而想象消极情绪事件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立即奖赏。目前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研究, 大多数是关于决策前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2.1.1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不同效价的决策前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不同。综合大量研究结果发现, 正性情绪可以降低个体的时间折扣率, 使其更加偏爱长期选项; 负性情绪可以增加个体的时间折扣率, 使其更加偏爱短期选项。例如, Ifcher和Zarghamee (2011)调查了积极情绪是否会影响跨期决策行为, 结果表明, 与中性情绪相比, 轻微的积极情绪显著降低了被试的时间折扣率, 在跨期选择任务中更偏好长远的收益选项; 消极情绪使人变得更加短视, 偏好能够及早兑现的较小奖赏。王鹏和刘永芳(2009)发现, 愉悦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下降,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 而悲伤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增大,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Muraven, Baumeister和Tice (1999)的研究指出, 当个体情绪低落时, 他们倾向于当下吃更多美味的食物或抽更多烟。Gray (2004)的研究表明, 相对于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 人在消极情绪状态下缺乏理性, 目光短浅, 更容易进行冲动选择。陈小玲(2007)研究不同情绪对个体自我控制的影响时发现了一致的研究结果, 与积极情绪组和中性情绪组相比, 消极情绪组被试会出现更多冲动选择。另外, 一些研究发现积极的情感同样会降低个体的时间折扣率, 使其目光更长远。DeSteno, Li, Dickens和Lerner (2014)发现感恩会增加个体在跨期选择中的耐心。Guven (2012) 的研究发现, 由于气候变好幸福感有所提升的居民, 其冲动消费行为有所减少, 而理性储蓄行为有所增加。杨鑫蔚和何贵兵(2015)发现, 幸福感水平较高的个体在跨期决策任务中更加倾向于选择大而远的收益。叶秋伶(2016)研究发现, 希望和权力会影响个体的跨期选择, 高希望或高权力下的个体, 在跨期选择中会变得更有耐心, 更愿意选择等待一段时间后的延迟选项。
登录模块为游客登录APP操作。注册模块是游客注册为会员操作,注册功能和注销功能紧密相连,注销和注册都可以由管理员进行。而注册还可以由游客自行完成。下棋模块是APP的核心模块,通过本模块进行中国象棋游戏,游戏结束后可进行再来一局和返回菜单功能。
目前, 关于决策前不同效价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机制还缺少实证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只是推测机制, 只有少数研究者直接对机制进行了验证。首先, 研究者从认知过程的角度解释情绪对跨期决策行为的影响。Pyone和Isen (2011)通过图片和词语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 发现积极情绪的被试相对于中性情绪的被试在跨期决策中会选择有更大回报的延迟选项。他们同时测量了被试的建构水平和未来取向, 发现积极情绪的被试相对于中性情绪的被试会进行更高水平(forward- looking, high-level)的思考, 并且有更强的未来取向。因此, 他们认为积极情绪会增加被试的认知灵活性, 使其不仅关注眼下的得失, 还会关注长期的结果, 由此被试更加偏爱延迟选项。同样, Ifcher和Zarghamee (2011)虽然没有直接测量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机制, 但他们推测, 轻微的积极情绪通过扩大注意力, 促进信息的开放性以及改善信息整合来提高认知灵活性, 致使被试会更加整合性地考虑和比较现在和未来的总收益, 最终选择有更大收益的延迟选项。
进一步地, 研究者从认知过程角度出发, 深入到从决策过程角度解释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经典的跨期决策选项包含两个维度:时间维度和金钱维度。研究者着眼于情绪是如何影响两种维度各自的显著性(salience)或者两种维度的大小来影响跨期决策行为的。例如, 王鹏和刘永芳(2009)发现, 愉悦组被试比悲伤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更低, 更加偏爱未来选项。他们推测, 积极情绪启动了被试的高水平建构思考, 因此人们更加关注事物的整体意义属性, 即更多关注选项的金钱维度,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 而消极情绪使人们更加关注信息的具体灵活性属性, 即更关注选项的时间维度, 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Guan, Cheng, Fan和Li (2015)则是直接考察了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 相对于正性和中性情绪, 消极情绪使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近期的较小奖赏。他们考察情绪影响跨期选择的内在机制时, 要求被试在情绪启动之后完成时间复制任务和反应抑制任务。结果发现, 被试执行时间复制任务时, 个体在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明显短于正性和中性情绪状态, 意味着消极情绪使得被试的时间感知变长; 与之相对, 情绪效价不影响个体在反应抑制任务中的表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负性情绪状态下目光短浅的冲动决策可能与个体时间感知的改变有关, 情绪是通过影响时间感知的长短进而影响跨期选择的。
杨鑫蔚, 何贵兵. (2015). 主观幸福感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应用心理学, 21(3), 242–248.
一方面,尽管东昌区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支持葫芦文化产业的发展,却没有深刻认识到葫芦文化在乡村旅游中的发展地位,没有充分抓住山东省全面开发乡村旅游的良好机遇,利用本地丰富的葫芦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极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对种植、加工葫芦的收入较为满意,且因文化层次较低,缺少乡村旅游开发经验,从而对开发葫芦文化旅游缺乏足够的信心和热情。
2.1.2 具体情绪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出发, 关注的是一般的、笼统的情绪, 如前文所述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 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已不再是情绪效价上的一概而论, 而是从更加深入、细致的微观层面来探讨同一效价上不同具体情绪的特定影响。正性效价上不同的具体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是比较一致的:如前文所述, 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在面对跨期选择中的延迟收益时, 会变得更有耐心去等待。然而, 负性效价上的不同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Lerner, Li和Weber (2013)发现, 悲伤造成了一种短视悲剧, 使被试关注于立即获得的较小金钱收益而不是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获取更大的金钱收益, 增加了时间折扣率。Lerner等还发现厌恶的参与者并不比中性情绪的参与者更不耐烦, 这意味着不是所有负面情绪都会产生这种短视的影响。由此, 学者们开始在效价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反思, 并提出了基于具体情绪的决策理论——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 从而掀起了具体情绪研究的热潮。ATF理论认为, 情绪具有6个认知评价维度:确定性(未来事件可否预测的程度)、愉悦性(个体感到积极或消极的程度)、注意活动(个体是否关注)、控制性(事件是由个体还是情景控制)、预期努力(需要付出生理或心理上努力的程度)和责任感(他人或自身对事件负责的程度), 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认知评价维度区分不同的情绪, 不同的认知评价维度对每一种情绪的作用不同, 其中对情绪起主导作用的评价维度被称为核心评价主题(core appraisal theme), 核心评价主题可激发个体对未来事件形成一种内隐的认知评价倾向, 因此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是通过认知评价倾向而实现的。由于不同情绪的认知评价倾向不同, 进而决定了其对决策的可能影响也是不同的(Adomdza & Baron, 2013; Lerner & Keltner, 2000, 2001; Lerner, Tiedens, & Gonzalez, 2006; Winterich, Han, & Lerner, 2010)。
Lerner, J. S., Li, Y., & Weber, E. U. (2013). The financial costs of sad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24(1), 72–79.
综上, 目前关于决策前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还不够深入和丰富, 无论是不同效价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还是同一效价不同具体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处于机制的推测阶段。例如, 虽然ATF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大多数同一效价不同情绪对跨期决策的不同影响, 然而却很难实现对机制的真正验证。未来可以综合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眼动追踪等技术, 探讨决策前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 尤其是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入手,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跨期决策这种决策行为。
2.2 决策中情绪
决策中情绪通常是决策过程中由决策情境所激发的情绪体验。根据情绪是否即时体验到, 决策中情绪又分为即时情绪和预期情绪。即时情绪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决策情境所引起并经历到的情绪反应, 影响与决策有关的心理加工。预期情绪又称为结果预期情绪, 是决策者在做出最终决策前, 对发生在将来的、由某种决策所导致的结果可能会带来的情绪反应的一种预期, 现在体验不到(Baumgartner, Pieters, & Bagozzi, 2008; Lowenstein & Lerner, 2003)。即时情绪和预期情绪都会对跨期决策过程和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Estle, S. J., Green, L., Myerson, J., & Holt, D. D. (2007). Discounting of monetary and directly consumable reward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 58–63.
2.2.1 即时情绪
由于决策中的即时情绪难以捕捉和测量, 也容易受其他因素干扰, 目前在研究中多采用神经影像学或眼动追踪的手段测量。在跨期决策中, 研究者发现人们在面对即时收益和未来收益时, 通常更加偏爱即时收益(e.g., Estle, Green, Myerson, & Holt, 2007)。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和Cohen (2004)发现, 当跨期选项包含一个即时收益时, 被试的腹侧纹状体、前扣带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等与情绪相关的多巴胺奖赏区域有更大的激活程度。Albrecht, Volz, Sutter, Laibson和von Cramon (2010)也有同样的发现, 并且指出只有当个体为自我做决策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激活模式。陈海贤和何贵兵(2012)通过自我报告的情绪测量发现, 近期选择情境相比较于远期选择情境激活了更强的冲动情绪, 导致被试倾向于即时满足。虽然目前关于跨期决策过程中, 有多少加工系统参与其中还不是非常明确, 但有研究者认为, 两种加工系统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个体在跨期决策中的表现:冷系统和热系统(刘雷, 赵伟华, 冯廷勇, 2012)。热/冷系统理论认为:热系统与个体的冲动行为有关, 它是情绪驱动的, 表现为简单的条件反射, 反应速度较快; 冷系统则与个体的自我控制有关, 它是认知驱动的, 比较审慎, 所以也比较慢(Metcalfe & Mischel, 1999)。因此, 上述研究结果均支持个体面对即时收益时有更大的情绪激活, 热系统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 情绪可能会削减认知执行功能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例如, Lin和Epstein (2014)考察了未来情景思维(episodic future thinking)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发现积极效价的情景思维使高工作记忆、高抑制控制以及低多巴胺遗传风险个体的时间折扣率升高。
计算结果表明:坝基轻壤土(或砂壤土)在地震烈度7度时,就有开始破坏的可能性,在8度及其以上时地表下砂壤土全部液化及地表下10 m范围内中细砂层开始液化。饱和轻壤土(或砂壤土)抗震稳定性最差,是引起地基液化破坏的主要土层。
然而, 也有研究认为情绪唤起的程度并不在于收益是否即时, 而是在于选择情境。Lempert, Glimcher和Phelps (2015)利用眼动追踪的技术, 测量了代表情绪激活的瞳孔放大程度在跨期选择中的变化规律。结果发现, 被试对于在系列跨期选择中价值变化不大的选项(不论是即时选项还是延迟选项)有更大的瞳孔放大反应, 并且, 对于比过去选择的平均价值更高的选项有更大的瞳孔放大反应, 情绪唤起和其他影响因素一起对跨期决策产生影响。并且, Lempert, Johnson和Phelps (2016)进一步发现, 延迟选项的情绪唤起程度同样可以预测跨期选择结果, 瞳孔放大程度会随着延迟选项主观价值的增大而增大, 伴随延迟选项的瞳孔放大程度越大, 被试越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
以往关于即时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大多集中在收益领域, 较少研究者探究个体面对涉及损失的跨期选项的情绪反应。Xu, Liang, Wang, Li和Jiang (2009)利用事件相关的功能磁共振成像, 使用两个具有对称收益和损失模式的决策任务, 研究了时间贴现的神经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外侧前额叶和后顶叶区域在折扣未来收益和未来损失时被激活, 但是当折扣损失时它们的激活更强。此外, 他们还发现个体在进行涉及损失的跨期选择期间, 岛叶、丘脑和背侧纹状体更加活跃, 而丘脑、岛叶通常被认为与负面情绪有关。这些发现提示我们, 个体对于涉及损失的跨期决策有更强的敏感性, 有更强的负性情绪激活。跨期决策领域的研究发现, 人们对未来获得和未来损失的时间折扣程度并不一致:前者通常大于后者, 称为获得−损失不对称效应(Loewenstein, 1987)。Xu等(2009)的研究为解释获得−损失不对称效应提供了神经影像学基础。
2.2.2 预期情绪
在跨期决策中, 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从根本上偏离时间折扣过程的现象, 称为负折扣现象。按照跨期决策模型的时间折扣假定, 同样大小的损失如果发生在将来, 经过折扣之后其效用小于现在发生损失的效用, 因此人们应该选择将来承受损失而不是现在承受损失, 即出现正折扣。然而研究表明, 当面临现在的损失和将来的损失时, 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现在承受损失, 即出现负折扣现象。比如, Hardisty和Weber (2009)在损失金钱情境中, 让被试想象自己有一个停车罚单, 这个罚单可以选择现在支付也可以选择1年后支付。如果现在支付要支付250元, 如果1年后支付要支付不同数目的钱。如果被试在现在支付250元罚款和1年后支付数额小于250元的罚款之间选择了现在支付250元, 那么被试就出现了负折扣现象。结果发现有28.5%的被试的折扣率为负值, 出现了负折扣现象。van der Pol和Cairns (2000)发现人们更希望病痛快点到来而不是以后到来。Berns等(2006)研究发现, 与延迟电击相比, 被试更喜欢接受立即电击, 甚至有些人更喜欢接受一个强烈的立即电击, 也不喜欢等待一个延迟的微弱电击。Harris (2012)发现, 对于“丢失一张不可替代的照片”, “失去一个好朋友”等负性事件, 被试更愿意这些负性事件现在发生而不是将来发生。
Loewenstein (1987)认为,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情绪将影响当前的选择。具体而言, 当人们面对发生在未来的负性事件时, 预期在等待负性事件的过程中会产生负性情绪(如恐惧, dread), 即人们会预期到等待负性事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预期的消极情绪会致使人们觉得负性事件发生在将来比发生在现在更加令人厌恶, 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现在发生的负性事件, 出现负折扣现象。在此基础上, Sun等(2015)通过实验证明个体之所以出现负折扣现象是因为未来负性事件选项的总负效用不仅来自于负性事件本身的负效用, 还来自于由负性事件产生的预期负性情绪以及在等待负性事件过程中的预期反刍(anticipated rumination,指个体无法停止思考负性事件)所带来的负效用。这是研究者首次尝试通过实验验证负折扣现象的心理机制,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fMRI的手段直接验证个体在面对未来负性事件时是否产生预期负性情绪。
2.3 决策后情绪
决策后的结果会影响人们的情绪, 无可厚非, 好的结果会让人欢欣鼓舞, 坏的结果会令人灰心失望。然而情绪的影响并不是转瞬即逝的, 通常会是一个弥漫持久的过程。决策后情绪反过来也会影响人们对后续乃至今后的相关事件的决策, 使人们倾向于增强令人欢欣鼓舞的选择, 避免令人灰心失望的决定。例如, Zeelenberg和Pieters (2007)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发现, 在第一次任务反馈中经历过后悔的参与者在第二轮游戏中减少了彼此的分配。体验后悔导致连续选择任务中的反转行为。即使后续的决策任务不同于前一个, 经历后悔也会改变被试的决策倾向。在Raeva, Mittone和Schwarzbach (2010)的跨期决策任务情境中, 向参与者展示了一系列涉及做出两个不同决定的实验。第一个决定是一个风险游戏, 在两个风险赌博选项之间选择其一进行赌博; 第二个决定是一个跨期选择。他们测试了对风险游戏的反馈类型是否会影响人们的跨期选择结果。在部分反馈条件下, 仅显示所选赌博的结果, 而在完整反馈条件下, 两个赌博的结果都将被揭示出来。并且, 完整反馈还分为后悔和快乐的反馈。结果表明, 如果参与者在最初的风险选择中经历了后悔, 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在随后的跨期决策中表现出更大的时间折扣率, 倾向于选择短期结果。
2.5 敲低 lncRNA-8439 能降低 nanog 表达水平和肿瘤细胞悬浮球数量 使用 siRNA-2 在 Huh7和 Hep3B 细胞中敲低 lncRNA-8439 的表达后,分别收集细胞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 nanog 的表达量,结果显示干扰组中的 nanog 表达量在 RNA(图5A)和蛋白水平(Huh7 细胞:40.57±1.19 vs 435.81±6.75,Hep3B:18.50±0.75 vs 470.13±2.18;图5B)均降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同时,干扰组的肿瘤细胞悬浮球数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图5C)。
目前关于决策后情绪对跨期决策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并且主要涉及的是后悔和失望, 较少涉及积极情绪, 理论解释也缺乏系统论证, 因此决策后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及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3 研究展望
尽管关于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已经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但在研究深度、生态效度和情绪干预探索方面而言, 均还存在不足之处, 未来研究需要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午餐时,她突然发现她的那份工作餐多了盒草莓,一颗颗拥簇在餐盒之中,鲜嫩欲滴,饱满圆润。这是虚拟零件在头脑反映的假草莓,食用口感、营养成分、香气都通过计算机模拟或转介替代,转移到“草莓”的食物类虚拟零件之中。她用指尖触了一下,草莓表面密密麻麻小粒的凸起上还残留着的细密的水滴。
3.1 研究深度
首先, 目前关于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 尤其是决策前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 大多还只是停留在揭示现象的阶段, 较少有研究从认知过程或者决策过程直接验证其中的影响机制, 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机制探索。其次, 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眼动追踪技术等, 都可以动态地、直接地反映情绪加工和跨期决策的相互作用。目前, 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关系的研究多是行为研究。虽然一些研究运用神经影像学或眼动追踪的手段探究了跨期决策的决策机制(e.g., Albrecht et al., 2010; Lempert, Glimcher, & Phelps, 2015; 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 & Cohen, 2004), 但大多并不是以情绪作为首要出发点进行探讨。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运用这些技术动态地、多模态地考察情绪对跨期决策影响的神经基础。另外, 目前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的研究大多探究的是不同效价的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未来可以深入研究不同唤醒度的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例如, Sohn等(2015)则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考察了高唤醒度正、负性情绪对个体跨期决策的影响。行为结果发现, 与中性情绪状态相比, 个体在高唤醒正性和负性情绪状态下倾向于选择较小的及时奖赏。脑成像结果发现, 个体在高唤醒情绪条件下选择较小的及时奖赏时, 其认知控制相关脑区的激活程度下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高唤醒情绪能增加个体冲动性, 从而抑制个体考虑长远的更大目标。最后,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目前基本上以实验室情绪诱发为主, 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 未来研究可以应用手机程序的即时调查、大数据等手段采集日常情绪, 探究日常情绪如何影响跨期决策行为。
3.2 生态效度
首先, 已有的研究大多仅考察单独一次决策条件下的情绪影响, 然而实际生活中, 人们的选择是时刻在变化的, 而且情绪的影响也不是转瞬即逝的, 往往短暂激发的情绪会对后续的决策产生持久而弥漫的影响。因此, 对动态时间维度上的考察有利于加深理解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其次,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情绪往往不是单一的, 通常是一种或几种情绪占主导地位, 并与其他情绪混合, 因此探讨复杂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也将是未来的一种研究方向。另外, 情绪可以直接作用于跨期决策, 也可以通过影响认知加工间接作用于跨期决策。已有研究表明,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受到其他因素的中介或调节。例如, Guan等(2015)研究负性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内在机制中发现, 情绪很可能是通过影响时间感知进而影响跨期选择。杨鑫蔚和何贵兵(2015)在研究主观幸福感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中发现, 个体的自我增强需求中介了主观幸福感对跨期决策的影响。自我增强需求是一种提升我价值感的内在动机, 是人们强烈地要求获得对于自己的积极反馈或评价的动力趋向(Sedikides & Strube, 1995)。低幸福感的个体拥有较强的自我增强需求, 而较强的自我增强需求会使个体在跨期决策中更加短视, 即倾向于选择能尽快给予的金钱或物品; 高幸福感的个体拥有较弱的自我增强需求, 在跨期选择中倾向于大而远的延迟选项。由此可知, 通过适当引导降低个体的自我增强需求, 可以使人们更着眼于未来。Hirsh, Guindon, Morisano和Peterson (2010)则认为情绪是否影响跨期决策中的折扣率受个体人格特质的调控。结果表明, 外倾性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时比负性情绪状态更偏好立即奖赏。他们认为, 在正性情绪状态下, 外倾性个体更易受到奖励刺激的驱动而产生冲动选择。因此,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未来如果能找到更多情绪与跨期决策任务之间的中介或调节因素, 通过对其进行操纵, 可以有效的控制情绪对跨期决策行为的影响, 帮助人们做出更满意的决策。
3.3 干预探索
对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研究, 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 更重要的是, 希望可以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改善人们的跨期决策, 减少生活中的短视行为。然而, 对于这方面的干预方法与技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Peters和Büchel (2010)的研究表明, 情景预期通过对评估网络和预期网络的调节, 能够有效降低跨期选择中的冲动性。只有加入积极情境的预期想象才能降低个体对立即选项的偏好(Liu, Feng, Chen, & Li, 2013)。Gross (2013)研究发现, 通过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等情绪调节策略, 可以减少负性情绪反应, 激发正性情绪, 从而促进人们的理性选择。Bickel等(2011)研究发现, 通过工作记忆训练提高记忆能力,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药物成瘾者的延迟折扣率。目前, 这些方法和技术都还处于研究阶段, 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实施和临床治疗阶段。因此, 有必要对现有的方法和技术进行改进和延伸, 使其更标准化、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同时, 可以通过探索和发展类似生物反馈训练、神经反馈训练等新的方法和技术, 使情绪与跨期决策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个人和社会。
参考文献
陈海贤, 何贵兵. (2012). 跨期选择中偏好反转的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35(4), 862–867.
陈小玲. (2007). 情绪、情绪调节策略对自我控制的实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刘雷, 赵伟华, 冯廷勇. (2012). 跨期选择的认知机制与神经基础. 心理科学, 35(1), 56–61.
佘升翔, 郑小伟, 周劼, 杨姗姗. (2016). 恐惧降低跨期选择的耐心吗?——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 心理学探新, 36(1), 25–30.
佘升翔, 陈阳, 陈璟, 杨帆. (2017). 恐惧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基于回忆情绪的实验研究. 心理学探新, 37(6), 543–548.
王鹏, 刘永芳. (2009). 情绪对跨时选择的影响. 心理科学,32(6), 1318–1320.
徐富明, 张慧, 吴修良, 李彬, 罗寒冰. (2014). 超越效价的情绪与决策关系的新取向. 心理研究, 7(2), 9–16.
除了从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角度解释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还有少数研究者从情绪管理的角度解释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尤其是消极情绪的影响。根据情绪管理(Affect regulation)理论, 个体具有追求快乐的驱动力, 处于消极情绪的个体会采取能提升情绪的行为(Andrade, 2005), 因此有更强的选择即时收益、获得即时满足的倾向。在对成瘾者和节食者的研究中发现, 消极情绪可以引起“动机转移”, 短暂的享乐需求占据了长远的健康需求, 使得被试更倾向于满足当前的欲望而放弃长远的目标(Elster, 1999; Herman & Polivy, 2003)。然而, 这种机制推测目前还缺乏实证研究的证据。
食品药品检验机构是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保健品检验的法定检验检测机构,其最终产品为检验报告[1]。检验报告数据的真实、可靠事关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和食品药品行政监督管理的顺利实施[2]。检验检测机构的能力建设除了基本设施、环境、检验检测设备之外,人力资源是其强化自身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何加强检验检测人才队伍建设是各检验检测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西8家地市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人力资源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广西市级食品药品检测机构人员状况,发现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
叶秋伶. (2016). 权力和希望对跨期选择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Albrecht, K., Volz, K. G., Sutter, M., Laibson, D. I., & von Cramon, D. Y. (2010). What is for me is not for you: Brain correlates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for self and other.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6(2), 218–225.
招聘需求人数规模度指标用来表征岗位的人数需求紧缺度,即岗位在同行业中的人数需求紧缺情况。计算方法是先对招聘需求实际人数进行修正,修正值为招聘需求人数和发布频率的比值。招聘需求人数规模度指标为岗位招聘需求人数修正值和岗位所在细分领域内招聘需求人数修正值总和的比值。发布频率指标用于表征岗位招聘需求在时间上的紧缺程度,意思是平均每家公司每天发布的岗位需求情况,计算方法是招聘发布公司数量和发布天数的乘积比招聘发布条数。
Andrade, E. B. (2005).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affect: Combining evaluative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32(3), 355–362.
Adomdza, G. K., & Baron, R. A. (2013). The role of affective biasing in commercializing new idea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26(2), 201–217.
Baumgartner, H., Pieters, R., & Bagozzi, R. P. (2008). Future-oriented emotions: Conceptualization and behavioral effec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4), 685–696.
青浦区是全国第三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条例》施行以来,青浦区继续按照《上海市青浦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大纲》及规划,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要求,努力形成水资源管理制度、节水型经济结构、节水型工程技术和节水型行为规范等四大体系,扎实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各项工作。实行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论证制度,开展水平衡测试,实行定额管理,实行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四到位”管理制度。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并于2011年通过了水利部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中期评估,被评为第三批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优秀单位。
Hardisty, D. J., & Weber, E. U. (2009). Discounting future green: money versus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138(3), 329–340.
Bickel, W. K., Landes, R. D., Christensen, D. R., Jackson, L., Jones, B. A., Kurth-Nelson, Z., & Redish, A. D. (2011). Single-and cross-commodity discounting among cocaine addicts: The commodity and its temporal location determine discounting rate. Psychopharmacology,217(2), 177–187.
DeSteno, D., Li, Y., Dickens, L., & Lerner, J. S. (2014). Gratitude: A tool for reducing economic impat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6), 1262–1267.
Elster, J. (1999). Emotion and addiction: Neurobiology, culture, and choice. In: Elster, J. (Ed.), Addiction: Entries and Exit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39–276.
本文中随机选取了某学校某教学班100名同学的相关学籍信息及某学期各门课的平均成绩作为研究数据库,对学生信息成绩表的属性字段“性别”、“上课出勤次数”、“四六级通过”、“生源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优化得到指标值μi:
Frederick, S., Loewenstein, G., & O'donoghue, T. (2002).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0(2), 351–401.
Gray, J. R. (2004).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3(2), 46–48.
Guven, C. (2012). Reversing the question: Does happiness affect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33(4), 701–717.
Raeva, D., Mittone, L., & Schwarzbach, J. (2010). Regret now, take it now: On the role of experienced regret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31(4), 634–642.
图2为少模光纤端面发生横向偏移的耦合示意图.当光学系统存在装调误差时,光斑在两模光纤端面发生横向偏移rb,由于光斑偏移rb实际等效于光纤端面偏移了-rb,则根据式(4)、(5)可推导出在焦平面(r,φ)处其模场分布分别为
采用宽范围IPG(pH值3~10)胶条对凡纳滨对虾血细胞蛋白质的总体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如图2),2-DE凝胶图谱显示凡纳滨对虾的血细胞蛋白质主要分布在pH值4~8之间,中性蛋白质斑点较多,偏酸偏碱的蛋白质斑点非常少,因此在后续的实验中采用窄范围IPG(pH值4~7、pH值5~8)胶条,以提高蛋白质的分辨率。
Guan, S., Cheng, L., Fan, Y., & Li, X. (2015). Myopic decisions under negative emotions correlate with altered time percep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6, 468.
Berns, G. S., Chappelow, J., Cekic, M., Zink, C. F., Pagnoni, G., & Martin-Skurski, M. E. (2006). Neuro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dread. Science,312(5774), 754–758.
Harris, C. R. (2012). Feelings of dread and intertemporal choice.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5(1), 13–28.
模糊语言作为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现实中语言表达不可或缺的必要辅助手段。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可以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人们的交际需要。英文灾难新闻中的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可以使提高新闻报道的可信度,提高报道的可接受性,显示报道的权威性,还可以增加报道中话语表述的灵活性,使话语表述更得体,同时帮助新闻报道者转移责任,自我保护,从而避免负面影响。
Herman, C. P., & Polivy, J. (2003). Dieting as an exercise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G. Loewenstein, D. Read, & R. Baumeister (Eds.), Time and Decision: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pp. 459–48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Hirsh, J. B., Guindon, A., Morisano, D., & Peterson, J. B. (2010). Positive mood effects on delay discounting. Emotion,10(5), 717–721.
Ifcher, J., & Zarghamee, H. (2011). Happiness and time preferenc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affect in a random- assignment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7), 3109–3129.
Laibson, D. (1997). Golden eggs and hyperbolic discoun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2(2), 443–478.
Leland, J. W. (2010). Similarity judgments and anomalies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Economic Inquiry, 40(4), 574–581.
Lempert, K. M., Glimcher, P. W., & Phelps, E. A. (2015). Emotional arousal and discount rat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are reference depend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144(2), 366–373.
Lempert, K. M., Johnson, E., & Phelps, E. A. (2016). Emotional arousal predicts intertemporal choice. Emotion, 16(5), 647–656.
Lempert, K. M., & Phelps, E. A. (2016). The malleability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1), 64–74.
Lerner, J. S., & Keltner, D. (2001). Fear, anger, and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146–159.
Lerner, J. S., & Keltner, D. (2000). Beyond valence: Toward a model of emotion-specific influences on judgement and choice. Cognition & Emotion, 14(4), 473–493.
根据ATF理论, 情绪通过认知评价倾向影响信息加工的内容, 进而影响跨期决策。例如, Lerner等(2013)的研究中, 悲伤组被试更偏爱立即获得的金钱。悲伤的认知评价维度主要是低愉悦性和低控制性, 因此悲伤个体在跨期决策中, 面对即时诱惑, 容易失去自我控制, 并且认为立即获得能够给予即时的安慰。Tice, Bratslavsky和Baumeister (2001)研究也表明, 当人们处于悲伤情绪时, 更容易做出冲动选择。DeSteno等(2014)发现, 感恩增加了个体在跨期选择中的耐心, 使他们更有可能选择长期的优选方案。从ATF理论的角度看, 感恩的认知评价维度主要是高责任感, 感恩的个体认为自身和他人应该对事件积极负责, 卷入程度高、责任心强, 进而在跨期选择中更偏向从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 放弃即时的诱惑而选择长远的较大收益(Lempert & Phelps, 2016)。佘升翔、郑小伟、周劼和杨姗姗(2016)以及佘升翔、陈阳、陈璟和杨帆(2017)分别通过视频和个体回忆诱发被试的恐惧情绪, 发现相对于中性情绪组, 恐惧情绪导致个体在跨期选择中变得更不耐烦, 更倾向于放弃将来更大的回报而选择能立即获得的较小回报, 意味着恐惧者在获取金钱上更加短视。从ATF理论的角度看, 恐惧的认知评价维度主要是不确定性(徐富明, 张慧, 吴修良, 李彬, 罗寒冰, 2014; Lerner & Keltner, 2000), 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 被试倾向于选择时间感知比较近的即时选项(佘升翔等, 2017)。然而, 关于恐惧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结果并不一致。Luo, Ainslie和Monteross (2012)发现, 分别给被试呈现恐惧和中性面孔图片后, 恐惧面孔的被试更加远视, 更加偏爱延迟收益。研究者用“抑制溢出”效应来解释这种现象(Tuk, Trampe, & Warlop, 2011), 即抑制控制不具有领域特异性, 对恐惧情绪的控制有助于抑制跨期决策中的冲动行为。
Lerner, J. S., Tiedens, L. Z., & Gonzalez, R. (2006). Toward a model of emotion-specific influences o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Portrait of the angry decision maker.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19, 115–137.
Li, S. (2004). A behavioral choice model when computational ability matters. Applied Intelligence, 20(2), 147–163.
Lin, H., & Epstein, L. H. (2014). Living in the moment: Effects of time perspective and emotional valence of episodic thinking on delay discounting. Behavioral Neuroscience,128(1), 12–19.
Liu, L., Feng, T. Y., Chen, J., & Li, H. (2013). The value of emotion: How does episodic prospection modulate delay discounting. Plos One, 8(11), e81717.
Loewenstein, G. (1987). Anticipation and the valuation of delayed consump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97(387), 666–684.
Loewenstein, G., & Lerner, J. S. (2003). The role of affect in decision making. In R. J. Davidson, K. R. Scherer, & H. H. Goldsmith (Eds.), Series in affective science.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pp. 619–64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ewenstein, G., & Prelec, D. (1992). Anomalies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Evidence and an interpre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2), 573–597.
Luo, S., Ainslie, G., & Monterosso, J. (2012). The behavioral and neural effect of emotional primes on intertemporal decision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9(3), 283–291.
Mazur, J. E. (1984). Tests of an equivalence rule for fixed and variable reinforcer delay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nimal Behavior Processes,10(4), 426–436.
McClure, S. M., Laibson, D. I., Loewenstein, G., & Cohen, J. D. (2004). Separate neural systems value immediate and delayed monetary rewards. Science, 306(5695), 503–507.
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诗归》一编,易天下之耳目”。[2]816足见竟陵派以新的文学主张,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公安派流于轻率的弊端。但馆臣认为,“公安救历下,至於佻;竟陵救公安,陷於孱”;[2]849同样以幽冷纤巧为宗的竟陵派,“元春之才较惺为劣”,[2]826诡谲荒诞比之有余。明代文学发展到竟陵派,已是病入膏肓,回天乏力了,正如谭元春《岳归堂集》提要中所言:“……有明一代之诗,遂至是而极弊。论者比之诗妖,非过刻也。[2]826”
Metcalfe, J., & Mischel, W. (1999). A hot/cool-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Dynamics of willpower. Psychological Review,106(1), 3–19.
Muraven, M., Baumeister, R. F., & Tice, D. M. (1999). Longitudinal improvement of self-regulation through practice: Building self-control strength through repeated exercis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39(4), 446–457.
Gross, J. J. (Ed.). (2013).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Guilford: Guilford publications.
Read, D. (2001). Is time-discounting hyperbolic or subadditive?. Journal of Risk & Uncertainty, 23(1), 5–32.
Peters, J., & Büchel, C. (2011).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Understanding variabilit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5(5), 227–239.
Pyone, J. S., & Isen, A. M. (2011). Positive affect,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levels of thinking: Increas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wai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48(3), 532–543.
Samuelson, P. A. (1937). A note on measurement of uti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 155–161.
Scholten, M., & Read, D. (2010). The psychology of intertemporal tradeoff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3), 925–944.
Sedikides, C., & Strube, M. J. (1995). The multiply motivated sel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1(12), 1330–1335.
Sohn, J-H., Kim, H-E., Sohn, S., Seok, J-W., Choi, D., & Watanuki, S. (2015). Effect of emotional arousal on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an fMRI study. Journal of Physiological Anthropology, 34(1), 8.
Sun, H-Y., Li, A.-M., Chen, S., Zhao, D., Rao, L-L., Liang, Z-Y., & Li, S. (2015). Pain now or later: An outgrowth account of pain-minimization. PloS One, 10(3), e0119320.
Tice, D. M., Bratslavsky, E., & Baumeister, R. F. (2001). Emotional distress regulation takes precedence over impulse control: If you feel bad, do i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0(1), 53–67.
Tuk, M. A., Trampe, D., & Warlop, L. (2011). Inhibitory spillover: Increased urination urgency facilitates impulse control in unrelated domai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5), 627–633.
van der Pol, M. M., & Cairns, J. A. (2000). Negative and zero time preference for health. Health Economics,9(2), 171–175.
Winterich, K. P., Han, S., & Lerner, J. S. (2010). Now that I’m sad, it’s hard to be mad: The role of cognitive appraisals in emotional blunt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 1467–1483.
Xu, L., Liang, Z-Y., Wang, K., Li, S., & Jiang, T. (2009). Neural mechanism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From discounting future gains to future losses. Brain Research,1261, 65–74.
Zeelenberg, M., & Pieters, R. (2007). A theory of regret regulation 1.0.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17(1), 3–18.
Concept, measurement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effect of emotion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JIANG Yuan-Ping; SUN Hong-Yue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emotion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research trend in recent years. On the basis of the time of occurrenc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emo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emotions before decision-making, emotions in decision-making, and emotions after decision-making. Currently, most of the studies on emotion and intertemporal choice, especially those on emotions before decision-making, mainly focus on revealing the phenomenon other tha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oreover,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emotion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from the cognitive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rough th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and neuroimaging technical would help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in making good decision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emotions. Ultimately, future research must further improve the depth and ecological validity, e.g.,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dynamic emotions, daily emotions, or mixed emotion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pay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emotional interventions.
Key words: emotion; intertemporal choice; emotions before decision-making; emotions in decision-making; emotions after decision-making
分类号B849:C91
DOI:10.3724/SP.J.1042.2019.01622
标签:情绪论文; 个体论文; 选项论文; 发现论文; 认知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决策学论文; 《心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9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601121)资助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