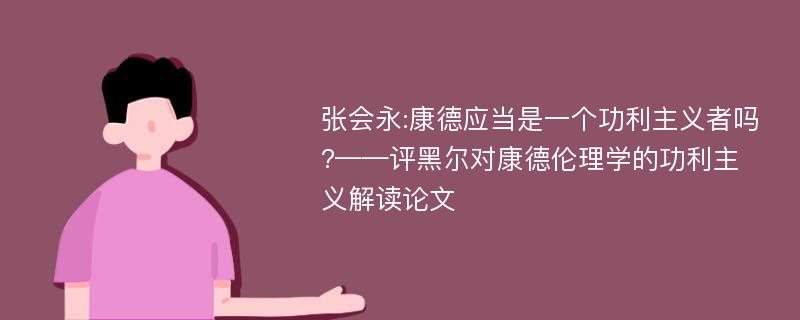
摘 要:针对现代道德哲学盛行的把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黑尔提出了异议。他从元伦理学层面指出康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相容,从规范伦理学层面指出康德伦理学应当导向一种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他因此得出结论,康德可以是也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这种解读仍然坚持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间必然相互对立的教条。实际上,康德不必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他的义务论的立场并不排斥对功利后果的考量。
关键词:康德;黑尔;功利主义;义务论
在现代道德哲学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教条就是,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站在道德哲学对立的两极,前者是义务论的典型代表,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其是否出于对道德义务的尊重,它是先验的、形式性的和普遍主义的;而后者是后果论的典型代表,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其是否促进乃至最大化了善的后果,它是经验的、质料的和具体的。据著名伦理学家黑尔考证,这种对立可以追溯到直觉主义义务论者普理查德和罗斯,他们把康德刻画为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义务论者,而当代自封为康德传人的罗尔斯等人通过援引康德来强调“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又强化了这一对立。
但黑尔否认这种对立。黑尔认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在元伦理学层面上共享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和规定主义的观点,这些主张应当导向一种规范论层面的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而康德在规范论上的义务论观点与其元伦理学的观点是相冲突的。黑尔宣称,从理论的一致性来看,康德不但可以是,而且应当是一个“理性意志的功利主义者”[1]。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和批判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指出康德不必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其义务论的主张能够容纳对功利后果的考量。
2017年,我国数字报纸在探索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在数字报纸传播能力、内容、营销方式以及盈利模式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同时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
在黑尔看来,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康德伦理学,都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元伦理学层面,它考察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行为正当的道德理由或道德判断的特征是什么等问题,黑尔也把它称作“纯粹伦理学”[1]或者“形式的部分”[2];另一个涉及规范论层面,它考察如何实现善、如何道德上正当地行动或普遍规范如何适用于具体情境等问题,黑尔也把它称作“应用伦理学”[1]或者“质料的部分”[2]。黑尔批评道,那种认为康德伦理学是形式的而功利主义是质料的观点,实际上是把这两个层面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分别从这两个层面思考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就会看到,康德伦理学不但与功利主义相容,而且其理论必然指向一种功利主义,因而康德可以是也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中小企业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又称中小型企业,与同行业的大企业相比,具有人员数量、资产规模、经营范围都比较小的特点。资金可以由单独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提供。因其雇用人数与营业额都比较小,所以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经营由业主直接管理,很少受到外界干涉。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下,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我国供给侧改革重要的推动力,是加快经济发展、稳定就业的重要来源。
在纯粹伦理学或者形式方面,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至少共享三个主要观点,即理性主义、规定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点。首先,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是理性主义的。康德伦理学的理性主义表现在,意志的欲求对象作为质料要素,不能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相反,只有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形式性的道德法则,才适合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意志之所以是善良的,不是因为它适宜于达到某种目的或后果,而是因为它能够通过意愿自己主观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从而使自身成为实践理性[3],最终成为行为正当性的基础。黑尔接受了康德的这一观点,认为当功利主义者讨论其偏好概念时,也应当排除偏好的任何具体内容,使自身的规定理性化和普遍化。黑尔说道:“一个人意欲这个或那个,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他偏好这个或那个,同样是一个经验事实。但是,不论其意欲或偏好什么,意志和偏好的形式是相同的。对于绝对命令和道德命令来说,功利主义者和康德都能同意,形式必须是普遍的。对康德和功利主义者来说,对意志只有形式上的限制。”[1]在他看来,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和康德一样,具有一个理性主义的元伦理学理论,“没有什么阻止一个功利主义者以与康德相同的方式分配其探究,正如他清晰做出的,也如我自己所做的。一个功利主义的体系也具有一个纯粹的形式部分,在我看来这只需要依赖道德概念的逻辑特性。它实际上处理偏好概念(它是否不同于意志概念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并不设定偏好具有任何特殊内容。人们偏好什么,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情,一旦我们开始运用我们的推理体系,它必须是确定的,但是,为了建立体系我们不需要假设人们偏好一个或另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在建立体系中,我们仅只看人们偏好的形式,而非内容。”(同上)很明显,黑尔提出的与康德伦理学相容的功利主义,并非如边沁和密尔等经典功利主义者所倡导的奠基于经验的快乐(幸福)之上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功利主义,这种理性偏好功利主义也是哈桑伊等现代功利主义者所倡导的[4]。正如福斯勒所说:“黑尔不是说把康德与一般功利主义理论相连接,而是说康德与一种特殊种类的‘理性目的’功利主义相容,这种功利主义排斥功利计算中的非道德(非理性)目的的满足。康德和黑尔都认为规则必须来自实践理性的需要,二者都被称作‘伦理理性主义’。”[5]
诚然,每个时代文学的发展,都必须也必然会受到前代文学遗产的影响。汤显祖的戏剧“临川四梦”,就是继承与改革魏晋志怪、唐代传奇、元人杂剧和明代话本,并结合他所生活的中晚明时代,所创作出来的划时代杰作。尤其是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一座巍巍高峰,四百年来不绝于舞台。21世纪以来,随着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及“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全世界的巡演,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正在从“美丽的古典”走向“青春的现代”。
黑尔首先指出,元伦理学层面的普遍规定主义必然导向规范论层面的功利主义。因为普遍规定主义要求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既追求平等化,又追求最大化,而这二者正是功利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普遍规定主义意义上的平等化,意味着“对所有情况、各种规则主导下所有利益所有者的平均利益赋予同等权重”[10]。这和边沁的名言“每个人都是一个而不是更多”是一致的。更进一步,黑尔指出,普遍规定主义的平等化必然要求最大化,因为当行动涉及许多团体的利益时,我们能够设想到的具有普遍规定的行动方式必然是使尽可能多的团体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选择,“追求最大多数团体的利益,即最大化所有人群的总体利益,这就是经典的功利主义原理”[10]。黑尔认为,在质料的层面上坚持功利主义,将使得我们不仅思考道德语言的逻辑特性,而且要思考我们的道德行为将会影响到的人们的偏好,而这些偏好是具体的和经验的,它同时使得我们的道德思考更加接近现实世界。因此,功利主义是普遍规定主义的必然结果。也许会有人批评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按照通行的道德义务或规则去行动的,他们并没有进行功利计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按照义务论而非功利主义来行动的。但黑尔认为,义务并不具有最终的解释力,它只有依靠功利原则才能得到正确解释。他说道:“对于我来说,真正的道德思考发生在批判的层面,并且是功利主义的;在直觉层面发生的东西只是帮助我们最大化地和整体地履行我们的功利主义义务的工具,这义务是由批判的思考所决定的。我们使自己变成善良之人,履行我们的义务,并非为了其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这有助于最大的善。”[1]
总之,在黑尔看来,从元伦理学层面看,康德与功利主义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冲突的。黑尔总结道:“关于道德思维的逻辑的概念要点是,道德陈述在其核心使用上是表达规定,并且它们必须是可普遍化的。对这一点的承认导向一种同时承认康德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在做道德判断时,我们对所有相似的情形进行普遍的规定,那么我们将不会为其他人规定那种我们不准备同样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规定的东西。这将引导我们给所有人的偏好以同等的权重,因为我们将给他们的偏好和我们的偏好以同等的权重,并且它当然是实证的。因此,我们将会像功利主义者一样,把每个人都算作一个且没有人算作多于一个,并将会尽力最大化每一个人的偏好的满足,不偏不倚地对待它们。并且,我们也会像康德主义者一样,通过意愿我的准则能够成为普遍法则来行动;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人性和他人的人性看作目的;我们将这样行动,就像我们是目的王国的立法成员一样。”[9]鉴于此,把康德排除在功利主义者之外就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其理论与功利主义是相容的意义上,康德可以是一个功利主义者”[1]。
再次,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是普遍主义的。在康德那里,绝对命令的普遍法则公式,即“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从未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3]这一公式,体现的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黑尔认为,功利主义者与康德一样追求普遍主义。例如,边沁的名言“每个人都算作一个,没有人可以算作多于一个”的主张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就具有“紧密关系”[2]。而密尔也赞赏康德追寻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努力,只是康德在从原则推演具体义务时犯了错误,他要做的是一以贯之地证明功利原则作为普遍原理的正当性[7]。黑尔把普遍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实质的道德原则的可普遍性,就如在康德和密尔那里一样;另一种是关于语言逻辑的可普遍性,即是道德判断和道德语言的可普遍性,这是黑尔所强调的。他认为,当说某人在某种情形下应该做某事时,使用“应当”这一道德词语的人必须承认自己承诺了一个普遍的规定原则。黑尔举例解释道:“当a和b两个个体,如果说a应当在与特殊个体无关的特定情形下把普遍的条款具体化,但b却不应当在相似的情况下这样做,那么这就是逻辑不一致的。这是因为任何‘应当’陈述中都包含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认为陈述精确地应用于所有相似情形。”[6]黑尔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与他自己的普遍主义理论是相容的,虽然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强调道德原则的普遍性而非道德判断和道德语言,但是,如果把它解释为道德陈述的逻辑普遍性,那么康德的公式就与自己的理论一致了,他说道:“如果把康德的普遍命令理解为一个人应当以某种方式去行动,但却说‘其他人不要这样做’,这是一种含有矛盾的罪责,那么康德的原则就是对普遍主义逻辑命题的结果的陈述。在这种解释中,意愿(这是康德最难捉摸的概念之一)被认为大致等于‘对命令的断言’”[8]。因此,在黑尔看来,在寻求普遍规定方面,功利主义完全可以是康德主义的,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康德式的功利主义者”。
二
如果说在元伦理学层面,黑尔只是证明了康德伦理学可以与功利主义相容,或者说不冲突的话,那么在规范论层面,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应当导向规范论上的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
其次,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是规定主义的。所谓规定主义,在黑尔那里,就是说道德语言和道德判断虽然也有描述功能,但他们主要是规定性的,都在表达一种赞成的规定、评价或态度。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明显是规定主义的,他的意志自律概念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这种规定主义。在康德那里,意志自律就意味着意志自己给自己颁布法则,“采纳一种态度、评价或规定,是自律意志的一种功能,用康德的话说,它只受‘使自身适合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所限制”[6]。黑尔认为,康德的自律概念与自己的普遍规定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意志原初自由地欲求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并不因为这个或那个是什么就被限制欲求这个或那个。意志只被康德称作‘适合用作普遍法则的准则’所限制。这就是绝对命令的‘自律’公式所蕴含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想要欲求的东西的普遍形式,而非内容限制我们。内容由意志本身提出。意志只接受其意愿可以被普遍欲求的内容或客体。这与我自己说道德判断必须是普遍规定时所表述的是同一学说”[1]。黑尔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功利主义理论也必定与康德伦理学一样是规定主义的,因为对功利原则来说,必须最大化满足的功利目的必须有理性选择决定,因此我们要有决定标准,而这种标准就是理性的规定。再则,由于功利原则只是最高原则,它必须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则,而在制定具体规则时,真正的功利主义也必须借鉴康德,因为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理论,可以为功利主义提供了理性规定的具体规则。
黑尔进而认为,既然普遍规定主义的元伦理必然导向规范论层面上的功利主义者,那么在元伦理学层面上主张普遍规定主义的康德也不应当例外,他的理性意志和绝对命令的普遍规定主义也将必然导向功利主义,一种理性意志的功利主义[1]。但是,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在规范论层面,康德是义务论者而非后果论者,而功利主义是后果论者,因此,说康德应当是功利主义是错误的。黑尔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不成立的,康德也可以是一个后果论者,只是这个后果论需要被重新建构或解释。黑尔首先指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都既坚持形式的普遍性,又坚持质料的具体性,他们都不否认质料要素对行为的限制。在形式层面上,人们可以与康德一起说,唯一无条件善的事物就是善良意志,这意味着人们是依据其意图而非行动的后果被判断的。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善良意志总是与其欲求对象或者说与其行动的后果相关的,或者说善良意志总是要产生后果的意志。因此,在质料层面上,善良意志之所以是善良的,恰恰是由于后果。所以,后果也是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它在现实层面上规定意志。黑尔说道:“因此,在这种慎思过程中被构成的意志自身,就是一种产生确定后果的意志。它们是被意欲的东西——意愿的客体,如康德所称呼的那样。因此,尽管无条件善的东西是善良意志,但使善良意志善良的东西是被(自律地,普遍低,理性地和公正地)意欲的东西,是想要的后果。”[1]但是,黑尔随即又指出,在这里并非所有后果都应该被考虑在内,因为并非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是与道德有关的,后果与道德的相关性依赖于道德原则的具体运用(相关的后果是那种原则所禁止或要求一个人去实现的后果)[1]。可见,这里黑尔所重构的后果,并非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首先独立于道德原则并进而决定道德原则的后果,而是依赖于道德原则的具体运用的后果。
黑尔进一步指出,康德的这种不一致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对具体义务的划分和解释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四种义务,即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如不能自杀)和不完全义务(如自我完善),对他人的完全义务(如信守承诺)和不完全义务(如帮助他人)。黑尔指出,康德对自我完善、信守承诺和帮助他人的案例与功利主义是相容的,因为功利主义同样赞同这些义务[1]。例如,在讨论完善案例时,黑尔指出,即便康德所谈论的我们追求的完善是一种形式,而非内容,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它,即“善良意志的道德完善是一个形式的完善,这个形式是实践的爱的形式,这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它寻求公正地促进所有目的。图表中的‘质料要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这个源泉”[1]。在黑尔看来,只有第一个案例(自杀)是唯一不能用功利主义方式来处理的案例,也是体现康德的义务论论证明显与其普遍理性主义的元伦理学相冲突的案例。黑尔说道:“但是反对自杀,如果是有效的,也与反对违背承诺和非仁慈不同。把我自己看作由我自己来处置,就是不去挫败我意愿的目的。”[1]也就是说,从康德的自律原则出发,是得不出反对自杀的主张的。他认为,康德之所以反对自杀,不是其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康德幼年时期所受的虔信派教育所致,“或许康德在这里又回到了他年轻时听到的东西,即人之被创造为人,就是去履行上帝赋予的目的,因此不能通过不履行上帝的目的来违背上帝的意志。但是这样论证是依据一个他后来反对的他律原则的论证。这不能通过简单地用‘我自己’代替‘上帝’就变成了自律原则。因为,如果这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我的被命令的意志,那么在一个连续的目的序列中,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下是可以选择自杀的”[1]。因此,黑尔得出结论说,在处理这类案例时,康德是误入歧途的,他试图把自己论证运用于某种超出可普遍化的正当范围之外了。黑尔进一步指出,如果康德反过来从功利主义角度解释其案例,那么他就不会得出不能自杀的结论,因为不能自杀既不符合功利原则,也不符合普遍规定主义的理性要求。黑尔的结论是,如果从功利主义出发,那么康德关于义务的矛盾论述将都会得到解决。
黑尔承认,虽然从理论一致性上来看,康德可以也应当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然而他实际上并不是功利主义者,而是一个义务论者。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首先把义务定义为“出于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而来的行动的必然性”,进而通过区分“出于义务”和“合乎义务”来强化自己的义务论立场。在康德那里,合乎义务的行为可能出自自利的意图,例如一个商人之所以诚实守信,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的诚实守信在康德看来是没有道德价值的。相反,如果一个商人只是出于对诚实守信的义务的尊重,而不管它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如何,那么这就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而后果的好坏并不影响行为的道德价值。黑尔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使得他一方面承认任何具体的行为都包含目的等质料要素,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它出于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而非后果(这是黑尔也承认的)而完全排除了质料要素(这是黑尔不赞同的)。这种义务论自身陷入了无法容纳质料要素的困境之中,因而是不必要的。相反,如果他坚持功利主义,就会发现它与义务论相比,能够更好地解释人们的具体行为。因为功利主义承认,既然没有无目的的行为,那么目的肯定对行为有影响。因此,人们要做的就不是否认这种影响,而是恰当地思考这种影响。在黑尔看来,康德的普遍性理论是能够发展出这种功利主义目的论的,以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为例,他说道:“如果我想普遍化我的准则,就必须寻求使所有让人的目的平等地与我的目的相一致。”[1]
黑尔最终指出,康德之所以成为一个义务论者而非功利主义者,都可以归因于其成长的社会背景。在他看来,康德严格的虔信派的成长背景使他被赋予了一些他不赞成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点。虔信派特别看重信仰者的道德品格,认为德性是人真正有信仰的前提。康德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好像也体现了虔信派的作风。他的生平可以用平淡无奇来形容,尽管家庭生活贫穷、社会地位低下,但像虔信主义者一样,康德高度重视道德操守,年轻时,他是一个勤奋的工作者和品行良好的社交人物。到了老年,康德是一个博学的教授和仁慈的长者,在生活上,他清心寡欲,作息极有规律,一生从不逾越自己的本分。在此基础上,黑尔总结道:“因此,如我开始所说,在其理论与功利主义是相容的意义上,康德可以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是在他的一些实践的道德判断中,他出身的严格主义使他导向了他的理论并不真正支持的论证。”[1]
三
4.人体器官范围急需扩大。条例规定器官移植仅限于摘取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从事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不能适用。而事实上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社会需求十分迫切,我国有大约400万白血病患者等待骨髓移植,而全国骨髓库资料才3万份,大量危重病人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严重的供需失衡必然形成地下贩卖行为猖獗,因此,有必要扩大人体器官范围,将其纳入刑法范畴。
虽然黑尔认为康德可以是,甚至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他仍然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是一个强式的主张,而是一个弱式的主张。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人们完全把康德当作一个功利主义者来对待,或者说从康德的伦理学中得出一套完整的功利主义理论。他要表达的主要意图是,康德的理论并非与功利主义处于对立的两极,二者甚至在许多主要方面都是相容的,他说道:“很明显,我只是粗略地刻画了我的问题。在康德解释中有许多更困难的地方我并没有提出,更别说讨论了。我的有限的意图就是,使那些确信康德和他们站一边反对功利主义的直觉主义者、义务论者和契约论者,更加谨慎地阅读他的(不可否认是费解的)文本。我确信,像我一样,他们至少也将会在其中发现许多功利主义的要素。”[1]
黑尔的这种康德解释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争论。一方面,诸如卡米斯基(Cummiskey)、哈桑伊(Harsanyi)等研究者都认为可以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普遍原则中发展出一种特殊形式的规则后果主义。另一方面,有许多学者反对黑尔的康德解释,例如迪恩(Dean)、诺登斯塔姆(Nordenstam)、特雷多(Terada)、蒂摩尔曼(Timmermann)、魏茵斯托克(Weinstock)都认为,康德和后果论之间有“鸿沟”。
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解释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时,黑尔对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进行了修正。首先,康德伦理学修正了传统的功利主义,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的功利主义都开始于对既定的目的或价值的预定,但在黑尔看来,功利主义也可以像康德伦理学那样,不必事先假设有某种内在的关于幸福或目的的满足的善,进而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最大化地促进这种价值。他反对任何基础的内在的善的理念,而只是认为,我们之所以坚持功利主义,寻求最大化功利的理由在于,它是坚持普遍规定主义的理性行动者可以做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传统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价值完全独立于行为者,只关注行为及其结果,而不关注具体的行为者及其动机。黑尔借鉴康德的义务论,明确反对只关注行为而忽视动机的做法,主张一切伦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动机和后果的。在此基础上,黑尔批判了功利主义者关于“善优先于正当”的信念。当功利主义者这样说的时候,只是表达说善就在那里,直接决定正当,人们是通过善而知道正当的。在黑尔看来,这是对善的一种直觉主义理解,是非理性主义的。与康德一样,他也拒绝这种对善和正当的理解,认为并没有用任何预先给定的目的能够使道德决定优先于推理过程,只有那些通过普遍化检验的才是道德善的,是道德上正当追求的。黑尔借助康德伦理学表明,后果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也可以从意图、规定或者准则领域开始,但后来必须达到各种目的结论,因为目的对于区分行为者的现实状况及其动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黑尔用功利主义修正了康德伦理学,在元伦理学层面,他把康德关于道德原则的理性化和普遍化解释为道德语言和道德判断的理性化和普遍化,把康德那里实质性的道德原则问题转化为语言逻辑问题。在规范伦理学层面,他用功利主义取代康德的义务论,认为康德义务论的规范论主张是与其元伦理学立场相冲突的。相反,功利主义不仅与其普遍理性主义的元伦理学理论相容,而且更能够解释具体现实层面的诸多道德问题。福斯勒简要总结了黑尔的这种主张:“黑尔想反对的是康德的义务论的严格主义的方向,康德的规范主张与规则功利主义的不相容无关于康德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相容。黑尔认为康德义务论并不依据其理性基础,但功利主义原则会依据理性基础。功利主义赞同康德理性主义,而非义务论,康德理性主义应导向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5]
然而,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解释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康德在元伦理学层面的普遍理性主义与其规范论层面的义务论并不冲突。首先,在康德那里,义务体现的是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而道德法则作为实践理性的命令,既是理性的,又是普遍规定的。因此,对义务概念的强调可以说是康德理性普遍主义的元伦理学的必然结果。其次,康德在具体质料层面探讨主观准则和普遍法则的关系时,采用的论证方式(使准则同时成为道德法则)也完全是形式化的,这也是与其元伦理学相一致的。再次,黑尔认为康德的义务论立场并非来自其元伦理学理论,而是来自其幼年所受的虔信派教育,这也只是一种臆测,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不可否认,康德受虔信派影响很大。但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严密的理性论证基础上的,作为其体系的重要环节,他的义务论的伦理学体系是其实践理性批判研究的必然结果。
黑尔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把规范论层面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对立起来了。其实,在规范论的层面,康德义务论也是能够和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相容的。在讨论具体义务时,康德从来没有否认目的或后果,相反,他认为任何具体的行动都包含着目的,而目的就是一个依照其表现而有待去实现的客体的概念[11]。康德明确指出,目的是人类意志和实践理性的必然需要,因为如果不探讨目的问题,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意志和理性。康德说:“因为它(即纯粹实践理性——引者注)就是一种一般的目的能力,所以对这些目的漠不关心,亦即对它们毫无兴趣,就是一个矛盾:因为这样它就不会规定行动的准则(后者在任何时候都包含着一个目的),因此就不会是实践理性了。”[11]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区分了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在他看来,虽然主观目的不能作为道德的客观原则,但是,如果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相一致或者至少不冲突,那么它们都可以纳入“目的王国”的范围,因为目的王国是一个关于目的的整体的概念,它包含(1)作为自在目的的个体的理性存在者,(2)与该个体互为目的和手段以及其他互为目的和手段的理性存在者,(3)每个理性存在者可能为自己设定的特定目的[3]。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进一步提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一概念,并认为这种目的是单纯由理性给出,因而是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目的,例如,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就属于这种目的,它同时也是人们的道德义务[11]。可以确定的是,康德的义务论绝非与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极端对立,它可以容纳人们对后果或功利的考虑[12][13]。
因此,如果在黑尔看来,康德可以是也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康德可以不必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仍然是义务论者,但其义务论的立场却能容纳对功利或后果的考量。
2.2 实验室检查结果 饱和盐水漂浮法、大便潜血试验、贫血检验和嗜酸性粒细胞数或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检测结果见表2。本研究中大便饱和盐水漂浮法找到虫卵共2例,其阳性率极低;贫血表现占50例,其多以轻度贫血为主;大便潜血试验阳性19例;细胞数和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共33例。
参考文献:
[1]Hare.Could Kant be a Utilitarian[J].Utilitas, 1993(5): 4,15,15,13,12,8,10,4,16,15,7,3,9,5,5-6,8,16.
[2]Hare.Moral Thinking: it’s Levels, Method, and Point[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4,4,4.
[3]Kant.Werke IV[M].Walter de Gruyter& Co.Berlin, 1968:412,421,433.
[4]Harsanyi.Morality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M]//In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9-62.
[5]Forschler.Kant and Consequentialist Ethics: The Gap can be Bridged[J].Metaphilosophy, Vol.44, Nos.1-2, Jan.2013:88-104.
[6]Hare.Universal Prescriptivism[M]//A Companion to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451-463.
[7]Mill.Utilitarianism[M]//The Black well Guide to Mill’s Utilitarian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65.
[8]Hare.Freedom and Reason[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34.
[9]Hare.Political Morality[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128-9.
[10]Hare.Ethical Theory and Utilitarianism[M]//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23-38
[11]Kant.Werke VI[M].Walter de Gruyter& Co.Berlin, 1968:384,395,391-4.
[12]Timmermann.Why Kant Could not Have Been a Utilitarian[J].Utilitas, Vol.17, 2005(3):243-264.
[13]翟振明.康德伦理学如何可以接纳对功利的考量[J].哲学研究,2005(5):80-85.
Should Kant be a Utilitarian?——On Hare's Utilitarian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Ethics
ZHANG Huiyong
Abstract:Hare disagrees with the popular view that there is an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Kant's ethics and utilitarianism.He holds that these two are compatible on the level of meta-ethics,but Kant's meta-ethics should lead to utilitarianism instead of deontology the level of normative ethics.Therefore,Kant should be a Utilitarian.Hare's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ethics adheres to the doctrine that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are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In fact, Kant is not necessarily a utilitarianist, but his deontology is compatible with utilitarianism.
Key words:Kant;Hare;utilitarianism;deontology
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4.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德与后果主义伦理学研究”(15BZX098)
作者简介:张会永,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福建厦门361005)
(责任编校:文建)
标签:康德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目的论文; 伦理学论文; 功利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德与后果主义伦理学研究”(15BZX098)论文; 厦门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