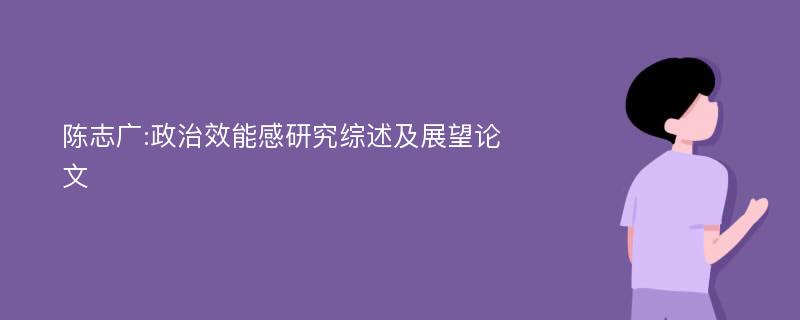
[摘 要]政治效能感是人们对自己对于政治系统影响力的主观判断,是个体与政府、政治关系的主观反映,是预测个体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作为政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概念,政治效能感对于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以政治效能感为研究对象,基于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研究视角的转换,在简要评述政治效能感内涵和测量的基础上,以行政管理学科视角为出发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介绍,并结合已有研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1)重量化研究,轻质性研究;(2)研究群体同质化,缺少多元群体的研究;(3)多为城乡对比,缺乏跨文化、跨地域的研究;(4)研究结构上以双维结构为主,对集体效能感的研究匮乏。后续研究应当跳出问卷调查的研究定势,尝试引入诸如“虚拟情景锚定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挖掘不同群体在政治效能感中呈现的差异性,丰富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对政治效能感进行更系统完善的研究,促进其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运用。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随着各项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阶段,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愈发显得重要。在学术界,个体基于自身能力和感觉对于政府和政治的主观判断和看法被称为政治效能感。深化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研究对于指导改革开放更快、更好向纵深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即是遭受了不公正的命运,认清生活本质后依然能无畏前行。作为一名老师,我感到惭愧,因为我从他身上学到的远比我教给他的要多。
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海外学者在概念上已经形成共识性的研究结论,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多元而丰富的研究成果。反观之,我国在政治效能感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呈现出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对象同质、研究视角狭隘等问题,缺乏与国外研究对话的坚实基础。基于此,对政治效能感这一主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迫在眉睫,通过梳理总结出已有研究的特点、不足和空白,方可为后续研究指明努力方向,推动政治效能感概念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实践。
与政治学、心理学不同,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应用性学科,尤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政治心理的研究范畴,政治效能感在行政管理学上的发展更加强调应用性,由此催生了政治效能感测量的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作为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政治态度变量”[1],政治效能感与人口统计学、政治参与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着力关注目前可着力改善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更是行政管理学的学科特色。
综上,本文从行政管理学的视角出发,梳理政治效能感的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种种规律,分析其在中国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并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群体等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述,以可实践、可操作、可改变为标准,指出目前可着力关注和改善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整理出海内外在政治效能感内涵上的主流观点,从学科视角分析三种观点的特色,并提出其在行政管理学科应用中的不足;第二部分概括出测量政治效能感的三种路径,并结合中国实际,分析其各自的优缺点,提出从诸如“虚拟情景锚定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来测量政治效能感的新思路;第三部分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视角出发,梳理出现有研究在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上存在的共识与冲突,并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研究评述,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为后续研究的完善提供方向。
选取了粗糙表面的金属铝和铜样品,在1 064 nm波长下开展了材料反射特性的测量实验,并利用几何光学近似的方法对测量结果进行了验证。
一、政治效能感的内涵
(一)政治效能感的概念
坤二少爷微微一笑,并不作答,只是低头品了一口龙井,才悠悠说道:“落地八字,富贵天定,祸福都有先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爷家里的公鸡,五更天里只啼半声……”
政治效能感最早由美国学者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在研究美国选举问题时提出。他认为“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是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感觉。”[2]坎贝尔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定义实际上揭示了其两方面内涵:(1)政治效能感的主体是公民,客体是政治或者政治过程;(2)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于自身影响政治的自信程度,是公民对自身政治能力的感觉。由于坎贝尔强调政治效能感是公民自身的一种“感觉”,因而被称为“感觉说”。
值为0 的区域属于非阴影栅格,值为1的区域说明仅在某一个时刻存在阴影;值为2的区域说明某两个时刻存在阴影;值为3 的区域表明该区域在3个时刻都为阴影区域;凡是值大于0 的地方,都是在 12∶00~14∶00 时间内有建筑遮挡的地方。
自坎贝尔之后,“政治效能感”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学者陆续开始就这一概念内涵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政治效能感”内涵丰富化和维度清晰化。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Almond)在其著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中,从“主观政治能力”角度对“政治效能感”的内涵进行界定。他认为,“公民自认为有这种能力的程度具有重要意义。自认为有能力参与政治系统的频率,可能被看作是判断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志……在许多方面,信念在一个人的能力中,是关键性的政治态度。有自信的公民看来是民主的公民。他不仅认为自己能参与,还认为别人也必须参与。他不仅认为自己能参与政治,而且是比较积极的。也许最有意义的是,有自信的公民也是较满意、较忠诚的公民。”[3]阿尔蒙德这一比较模糊的定义,着重描述了政治效能感在个体的“主观政治能力”方面的意涵,因此又被称为定义政治效能感的“主观能力说”。
戴维·伊斯顿(Davis Easton)和杰克·丹尼斯(Jack Dennis)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内涵。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概念,政治效能感是以三个彼此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要素表现出来:即作为规范的政治效能感、作为心理学倾向或者感觉的政治效能感和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4]伊斯顿进一步解释说,作为一种规范,政治效能感蕴含着永恒的理论价值,它是指政治系统中的成员能够且愿意影响政治过程,同时政治系统能够给公民以回应;作为一种心理学倾向,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个体可以在政治过程有所作用”的感觉,是公民感觉个体能够了解和影响政治,同时政治系统会给个体回应的感觉;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实在的政治行为,是个体在政治过程中形成的真正的影响[5]。这种概念界定方式以美国儿童为参照对象,从社会化的视角演绎政治效能感是心理认知——感觉——政治行动的发展过程,从早期的心理认知到感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稳定的过程,而从感觉到采取政治行动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需要一定的触发机制——当个体认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必要时才会将持久的政治态度转化为政治行为[6]。伊斯顿重点阐释政治效能感结构的复杂性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关系,它是以规范、感觉和行为为标准的三维结构,而非由简单的能力或感觉构成的点状式或平面式结构。由于这一界定是伊斯顿和丹尼斯是从儿童政治社会化角度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因而又被称为定义政治效能感的“形成说”。
从发展历程上来看,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呈现出由认识到建构、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规律。其一,面对总统选举活动投票率持续走低的问题,西方学者在反思政治制度设计的同时,也意识到选民心理的变化对于投票率的影响,“试图从探求选民心理的角度入手,寻找解决策略”[7]。沿着这一认知,西方学者开始对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坎贝尔在研究中最早将这种影响政治行为的特殊政治心理称为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用来理解和说明选民在选举参与中卷入程度的差异。在概念建构的过程中,阿尔蒙德则是用“主观政治能力”概念来表达不同的政治效能感,虽然与坎贝尔提出的“政治效能感”在称呼上有所差异,但并不影响学者对概念内涵的探索,学界也未因此掀起一场就这种政治心理应该如何称呼的争论,有趣的是,后来的学者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坎贝尔一方,沿袭“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用法。这一现象一方面与阿尔蒙德因研究主题的原因,未明确阐释其对公民政治态度特征的界定有关,另一方面或许可以从心理学的发展中找到解释——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提出了“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概念,形容自我在完成某项工作时的自信程度,而政治效能感则是形容自我对于影响政治和政府的自信程度,二者是效能感在不同事项上具体应用。基于此,可以猜想,80年代自我效能感的丰富和发展或为政治效能感在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立足提供了某种支撑。其二,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心理态度,政治效能感的实践指导意义重大,是仅次于政党认同的政治研究领域[8]。这一特性决定了政治效能感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指导和预测现实政治的使命。在概念的基础上,西方学者致力于测量量表的开发,将选民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和转变可视化,为政治忠诚、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下降寻求解决路径。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和美国选举中心开发的两套测量量表,以及台湾学者对于西方量表的本土化修正与测试等等,为政治参与的提高及民主体制的完善提供心理层面的路径。
国内对于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上基本采用Likert五点量表来测度政治效能感,也有个别学者采用4级计分[11]、6级计分[12],以及选项问答[13]等方法。在量表使用上大致沿着三条路径发展:中式、西式和中西结合。
至此,海外形成了关于政治效能感认识的三个主流视角——“感觉说”、“主观能力说”和“形成说”,这三种观点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政治效能感的内涵提供了不同的学科视角。“感觉说”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政治效能感更多地从表象和性质上进行定义;“主观能力说”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由表及里,将政治效能感追溯到人的主观能力,主观能力越高,政治效能感也会越高,反之亦然;“形成说”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政治效能感与人的社会化进程联系起来,即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综上,政治效能感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鉴于我国政治制度及政治环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政治效能感在我国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管理实践中会呈现出什么独特的发展规律呢?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未见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而深入的解读,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尝试对政治效能感与西方政治的发展做一简单梳理,期冀为后续研究提供启发。
2016年6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得到国际认可,工程教育迈上新的发展台阶,从而激发了工科专业开展工程教育认证的热情,以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工程教育认证中重点强调科学实践,促使学生在科学探究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中应用和增长科学知识[1]。学生获得学位,学习了科学和工程知识,但通常很少能充分掌握如何有效应用科学与工程知识。当学生在大学里不能有效应用科学与工程知识时,教育模式和未来工作间就会出现关键性的脱节。因此,应推动教学改革,开展工程教育认证,重视科学实践,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政治效能感的维度
罗伯特·莱恩(Robert E·Lane)是第一个对政治效能感的维度展开探索的学者。他认为政治效能感应该具有两方面隐性的意义:第一,在个体层面,个人认为自己具有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第二,在面对政治系统时,个人认为政府会对其有所回应[9]。这样使得政治效能感既包含个体对于自身政治能力的评估,又包含个体对于政府回应性的主观认知。借鉴个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内控与外控,前者称之为内在效能感,后者称之为外在效能感。具体来说,内在效能感指个体认为自身可以影响政治过程的感觉,而外在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政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会回应其要求的主观认知。
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可以被更广泛地定义为“具有影响政府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行为,既包括直接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的行为,也包括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政策抉择的行为”[62],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政治参与行为是影响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63][64][65];第二,高政治效能感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原因;第三,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交叉影响、相互促进[66]。
还有学者提出政治效能感应该具有三个维度,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政治效能感”,即个体在团体中所具有的能够一起组织及采取行动以达成特定目的的信念。但是这种观点目前并未被广泛认可,双维度说是认可度最高的观点,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双维度展开的。
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海外学者对其内涵不断深入探究,目前已经形成了对这一概念比较系统的理解。相较而言,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缺乏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二、政治效能感的测量
政治效能感测量的研究比其基本理论的研究更为丰富[10]。现有测量基本采用问卷量表的形式,其中美国和台湾在量表的使用上已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而大陆地区对于量表的使用则比较混乱。
美国和台湾在政治效能感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这不仅仅体现在概念和内涵的探索上,更体现在对政治效能感的测量上。目前国内外学者使用最多的当属195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开发的量表,该量表最初由5个题目构成:①有时政治和政府看起来很复杂, 不是像我一样的人可以了解;②公民投票是决定国家怎样处理事务的主要方式;③投票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对政府运作发表看法的唯一方式;④像我一样的人根本不会影响政府的做法;⑤我认为政府根本不会顾及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后来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剔除了题目②,①③成为刻画内在效能感的题目,④⑤则是刻画外在效能感的题目,由这4道题目组成的量表成为最经典、最具有影响力的量表。后来,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ES)将量表再度简化,剔除③,只剩下3个题目。
台湾学者在借鉴美国测量方法研究政治选举等问题时,在经典量表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修订为2个问题:您觉得市民对政府施政有没有影响?您觉得政府官员会不会重视市民的想法。后来经由郭秋永和吴重礼、汤京平、黄纪等人的研究,证实NES的标准化题目同样适用台湾。在此基础上,2000年以后针对台湾地区选举与选民的一年一度的“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也采用这套量表。
无论这套量表被后来学者如何精简和修订,承认度最高的依旧是4道题量表。从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出发,结合政治效能感提出的政治背景,SRC提出的四道题目量表经受了信度与效度的种种检验,被认可和推广无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此量表与选举政治密不可分,转换到其他政治文化或政治场景中,一味地照搬这四道题目势必降低量表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以我国为例,首先,“政治”和“政府”在中西方的含义不一致。在西方多党制中,“政治”特指政党政治,“政府”即执政党掌权下的政府,稳定性较差;在我国的政治协商背景下,“政治”和“政府”是同一个含义,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稳定政府。二者之间差异导致“有时政治和政府看起来很复杂”这一问题的表述在我国需要重新演绎。其次,不同政治体制下,投票的方式和影响不同。在西方国家,投票的影响是直接的,国家决定或政策直接反映人民意志,即投票对于政府运作的影响是可视化的。而在中国,人民选举产生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讨论决定法律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群众的投票对于结果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在人大代表到结果产生这一环节,人民群众的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往往会被扭曲和转移,投票与政府运作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基于此,以投票方式作为测量政治效能感的内容不免有失偏颇。最后,对于“政府”的理解亦存在差异。在以三权分立思想指导下的一些西方国家,州政府对于联邦政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地方政府没有自主权,一切受控于中央政府。在此背景下,民众对于测量外在效能感的两道题目的理解亦存在偏差,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需对“政府”加以明确说明,这是提高量表本土化信度的应有之举。
综上,以SRC四道题目量表为蓝本进行借鉴和学习时,除技术性问题外,还应兼顾量表与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的兼容性。
从时间脉络上来看,坎贝尔最早提出“感觉说”,伊斯顿是在反思“感觉说”和“主观能力说”基础上提出“形成说”,政治效能感的内涵的挖掘随着时间发展不断深入,并越来越多地从单纯的理念介绍向实践操作上靠拢。具体来说,感觉和能力将个体视为封闭体,更多的是关注个体自身的内心独白,缺乏从外部探究和改变的途径,而“形成说”则将感觉从个体中解放,放诸社会化的过程,在为二战后美国民众投票率低下现象在寻找政治心理解释视角的同时,也提出了可操作的解决策略。由此,也开启了政治效能感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一,中式量表,即基于政治效能感的内涵,根据研究内容开发出适合研究对象特点的问题,这里又可以细分为自我开发型和学习借鉴型。前者如李蓉蓉[14]针对城市社区居民开发的量表,内在效能感包含社区居民自认为是否熟悉社区的规章管理制度、是否关注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是否了解社区居委会的选举程序、是否认为自己在选举中对选举结果有影响以及是否能影响居委会的决策等5个问题;外在效能感包含居民自认为社区居委会在决策过程中是否会在乎其想法、是否会重视居民提出的建议、社区居委会的决策能否反映出居民的意愿、社区居委会干部是否帮助居民解决困难等4个问题。后者专门是指借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调研问题,因其问题信度高、调查范围广、调研过程严谨、数据连续性好等广受学者青睐。在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上,国内多数学者多采用CGSS中关于政治效能感的问题数据作为自己的数据来源,如胡荣、沈珊[15];范柏乃、徐巍[16];谢秋山、陈世香[17];袁浩、顾洁[18];张蓓[19];丁百仁、王毅杰[20];胡荣、庄思薇[21]等。第二,西式量表,是指套用国外量表的问题来研究中国问题,如熊光清[22]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开发的量表,用“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的行为”、“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三个问题测量内在效能感,用“我认为,政府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来测量外在效能感。再如丁永斌、王文文、孟崇峥[23]借鉴Newhagen的量表,用“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参加政治活动”、“我觉得自己对国家的政治事务有较好的了解”、“我觉得自己在政府机构可以和其他人做得一样好”3个问题测量内在效能感,用“在政府领导下,人民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权”、“如果政府官员对人民的诉求漠不关心,后者也无计可施”、“目前有许多合法途径可供公民影响政府决策”3个问题测量外在效能感。第三,综合量表,即将国外量表与国内情况相结合,或者将中西方已有量表进行综合取舍,修订成为适合研究内容的量表。如周翔、刘欣、程晓璇[24]以Craig[25]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参考蓝本,以班杜拉[26]和Lee[27]为集体效能的参考对象,形成由24个题目组成的政治效能感量表。再如李燕、朱春奎、姜影[28]在研究时,以Balch[29]和 Seligson[30]为内在效能感的题项来源,以王丽萍、方然[31]为外在效能感的题项来源,形成总题数为6项的政治效能感量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种测量路径在中国的发展均遭遇困境(见表1)。在西式量表中,195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开发的量表是目前承认度最高的,后来的量化研究基本都是在这套量表的基础上开展的。然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因海内外在政治制度、社会环境、文化理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西式量表的测量精度大打折扣。中式量表虽方便了研究者对于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测度,然而由于其题目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形成共识性的研究结果。综合量表平衡了中式量表与西式量表的矛盾,试图寻找一条兼具信度与效度的康庄大道,然囿于演绎的科学性,其在实践中依旧举步维艰。
表1 三种测量路径的优缺点对比(来源:作者自制)
中式量表西式量表综合量表相同点多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度不同点以概念演绎为基础,结合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设计题目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开发的经典量表将本土化测量题目与西方经典量表题目相结合,先取舍,后增加优点题目与研究主题的贴合性佳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实现共识基础上的演绎缺点差异性大,研究结论缺乏对话基础水土不服,尺度偏差大本土化过程中的科学性难以控制
在此,我们无法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测量量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无法推进政治效能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采取何种研究方法主要由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决定,就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来说,在西方量表较为成熟的情况下,国内学者在研究时进行借鉴无可厚非,但要兼顾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处理方式,考虑中国情景乃至具体研究事务中独特的内生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降低可能产生的冲突与问题,提高研究结论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现有研究方法中95%的文章均运用问卷和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32],这一压倒性研究趋势导致许多学者将此方法视为研究政治效能感的不二法门,奉为圭臬,导致现有研究在结论上出现相互冲突的混乱局面。事实上,跳出已有研究方法的局限,另辟蹊径,从质性研究的角度入手,探索新的测量方法不失为一种上上之选,例如,刘小青通过对比量表设计和“虚拟情景锚定法”两种方法,发现采用后者的确得到了更好的测量效果,降低了前者在评价尺度偏差上的不足[33]。
④其他部门资料。包括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资料、全国水文地质资料、环保资料等。
无论是量化研究的量表测量法,还是质性研究的虚拟情景锚定法,归根结底都是为政治效能感在行政管理学科的应用服务,我们在进行技术学习或技术移植时,不可忽视行政管理学科的公共性和我国行政管理范式的特殊性。
胖婶看得点头,秀才们也拊掌叫好,吴耕、李离、上官星雨都紧张得站起身不说话,他们的带头小哥哥果然有两下子,力敌贼酋,不只是降猫伏狗的三脚猫把式。如此良夜,山中逆旅,酒酣耳热之余,论刀论剑,由塞外的龙门客栈到山西的灵石旅舍,金香玉、红拂女们,都是这么一个玩法。
Application of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in landslide disaster in Changning County, Yunnan HE Hong-zhi ZHANG Jia-ming(45)
三、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根据行政管理学科中各角色的划分,可以将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具体来说,微观层面是以个人为主体展开的研究;中观层面是对个体所在家庭、家族的研究;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和国家层面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由于行政管理学关注目前实践中可着力改善的影响因素,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重点介绍可实践、可操作、可改变的影响因素。
(一)微观层面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中观层面是一种复杂的身份影响因素,其糅合了政党、种族乃至家族的影响,与此相关的理论有政治赋权论(Political Empower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一个政党或种族的成员会由于所在组织中的领袖获得政治权力而产生或提升相应的主观政治影响力”,即高政治效能感。Lawrence Bobo 和Franklin D. Gilliam的研究发现在黑人担任市长的城市中,黑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高,政治效能感也更高[72];吴重礼对台湾2001年县市长选举与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的研究也发现,当弱势群体中有人进入领导阶层时,此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就会相应提高,佐证了这一论点[73]。将这一理论置于中国特有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的环境中,政治赋权论可以引申为“关系”赋权论,李蓉蓉提出过此想法,但其研究重心是“与村干部有宗族或其他关系的村民的政治效能感”[74]。
年龄。与性别相类似,学界已通过众多实证研究证明年龄与公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负相关性[39][40][41]。
教育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部分学者认为学校教育对公民政治参与有重要的引导作用[42][43];郑永兰、顾艳[44]、丁百仁[45]、李蓉蓉[46]对农民这一身份群体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其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近年来亦有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学校教育与政治选举等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47],魏以宁称之为“倒挂现象”[48]。对此,孙伦轩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通过对“受教育程度——政治关注、政治讨论、政治认知——政治效能感”三种机制对两种政治效能感(内、外在)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了受教育程度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非单向[49]。
收入水平。一般而言,具有较高经济收入的群体在一个组织乃至社会中的受关注程度(外在政治效能感)以及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内在政治效能感)就较大,因此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收入对政治效能感存在正向影响[50][51][52]。国内,无论是对社区居民[53]还是对农民[54]的实证研究均佐证了这一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张雅雯、耿曙[55]在研究中国“村改居”社区的选举时发现,外在物质诱因可能抑制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
信任,分为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前者被Hetherington描述为“一种对基于政府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民众的正常期待做出反应的评价”,后者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人或群体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语承诺是可以依赖的期待”[56]。 陈雪莲对全国24个地区的 720 位地方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地方干部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较高程度信任与高政治效能感同时存在[57]。作为政治信任的一部分,政党认同与政治效能感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Lambert R D使用1984年加拿大全国选举研究的数据对受访者的政党认同进行研究,发现对执政党认同程度高的民众的内外在政治效能感都显著地高于对执政党认同程度低的民众[58];陈陆辉、耿署对 2002 年北高市长选举的案例研究也发现政党认同对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的影响[59];但吴重礼在对新奥尔良市长选举的研究却显示,政党认同与政治效能感的关联性较小[60]。因此政党认同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仍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进行解释。社会信任又可以细分为对家人、亲戚、朋友的“特殊信任”与对一般朋友、同事、领导干部的“普遍信任”,胡荣基于CGSS2010数据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信任的两个因子,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外在政治效能感产生两种相反的显著影响:普遍信任增进外在效能感,而特殊信任却削弱了外在效能感[61]。
CNAS于2017年底和2018年初分别发布了CNAS-TRL-004∶2017《测量设备校准周期的确定和调整方法指南》和CNAS-TRL-006∶2018《轻纺实验室测量设备的计量溯源或核查工作指南》。这2份文件可以给实验室测量设备计量溯源性提供最直接的参考依据。另外,计量标准化部门应不断完善标准化体系,发布和实施更多纺织测量设备的校准规范/规程并与测试标准相适应,满足实验室合格评定和测试的要求。
媒介使用情况。媒介的时政新闻报道是公民获取政治资讯的重要渠道,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更是公民交流不同政治观点、对自己的政治观点进行强化或重塑的重要平台。基于此,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了媒介使用情况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关系的研究。Pinkleton认为,接触报纸、杂志的政治资讯会加深受众对政治过程的理解,因此媒介的接触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67];Aarts和 Semetko通过对荷兰1998年选举的实证研究发现,媒介使用有助于学习,政治参与,信任,效率和动员,进而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68];Kenski 和 Stroud使用2000年全国安纳伯格选举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互联网接入与在线接触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9]。国内近几年亦有相关研究涌现,张蓓基于CGSS2010的数据研究发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不同,前者相对而言正向影响更为显著[70]。目前关于媒介使用/接触和政治效能感关系的研究均从公民视角进行,尚未有基于公务员身份视角的相关研究,但与此相关的研究除了王井对浙江省公务员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发现干部认为媒介对工作的影响(3.47/5)较大外,并无针对性的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研究[71]。
(二)中观层面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性别。Campbell认为,一般来说女性的政治效能感要低于男性[34]。范柏乃、徐巍基于CGSS2010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对于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仅限于内在政治效能感,二者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差异并不显著[35];丁百仁[36]、胡荣[37]、孙伦轩[38]等众多学者均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性别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强相关性。因此,学界对性别因素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基本达成一致结论,故而在后续研究中多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富察氏接过参汤,拿银匙慢慢搅着,神色稳如泰山:“如今进了宫,好歹也是一家人,你就不去看看景仁宫那位吗?”
与微观层面的研究相比,在中观层面对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的挖掘不够深入,家族和家庭在个体政治效能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西方的政治赋权论在中国是否适用?诸多问题亟待相关研究进行解释。
比如电视节目《经典咏流传》,把古典、经典华章与现代音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通过唱歌的方式记住古诗词。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登鹳雀楼》一诗,用了同一首曲子,由不同语言反复吟唱,让一首简单的、只有20字的古代诗歌的魅力,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突破中西文化的壁垒,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三)宏观层面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社会文化。陈炯彤对广州高等院校学生的研究认为被动参与型的社会文化对政治效能感影响明显[75]。无独有偶,陈安繁等人基于CGSS2010的数据,研究认为在现实环境中,政治社会文化相对滞后阻碍了内在效能感的提升[76]。
政府规模。邓燕华和黄健的《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是目前唯一一篇关注政府规模与政治效能感的文章,将个体的心理态度与政府的区域规模相联系,是一项颇为有趣的发现。突破了已有研究对微观因素的过分关注,尝试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上弥补已有研究的空白。研究发现,县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就均值而言,外在效能感随着县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且在其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影响[77]。
政治制度。陈雪莲对地方干部政治效能感的一项调查发现,干部的政治效能感高于普通民众,对此现象她认为主要是由于现有制度给地方干部提供了能动空间[78]。此外,还有学者对政协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研究[79],佐证了政治制度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但是与李雪莲的发现有所不同,李鹏对广东省M市政协委员的研究发现,来自党派的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效能感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高于来自社会团体和社会职业行业的代表,反而是行业职业性界别政协委员参与政治协商的效能感最高。这一结果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与其对自身所在界别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感知有关[80]。虽然研究的对象略有差异,但是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不可忽视,如干部与群众的政治效能感孰高孰低,两者研究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更多具体关系还需后续研究的跟进,为行政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四)总结
文献梳理是研究的第一步,但文献梳理的视角不等于研究的视角。在梳理时,可以将已有研究中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按照视角大小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但是在具体的一项研究中,这三者视角往往是交叉使用的,而非某一单一视角。举个例子,就教育与政治效能感的关系而言,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体政治效能感的直接因素。作为一个社会人,个体不可避免受到家庭或家族的影响,譬如家庭的文化氛围和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成为影响个体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放到更大的视角看,国家的教育政策更是从宏观上决定了个体受教育的内容和程度,从而间接影响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在进行研究时,要兼顾微观、中观和宏观视角下具体变量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减少内生性问题。
四、评述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总体上看,我国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老巴说:“是呀,天寒了,罗爹爹的腿软。早上慢腾腾走到东湖边,别人的拳都打完了。不去吧,他又难过得慌。”
第一,重量化研究,轻质性研究。由于心理态度的模糊性和隐蔽性,在研究之处,海内外学者就试图通过统计工具对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由此造成了在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上呈现量化研究“一家独大”的现象。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九成以上均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其中或使用自制问卷,或使用CGSS数据,对某一群体的政治效能感特征及现状进行研究。鲜有系统的质性研究,对政治效能感的形成路径和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剖析。鉴于前述分析,由于缺乏成熟的本土化量表,量化研究本身存在信度和效度问题,更遑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推广性,这也是近年来政治效能感相关研究数量递增而成果同质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研究群体同质化,缺少多元群体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学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城乡居民、高校大学生、新媒体人、网民等对象,这类群体的共同特征是都为普通公民,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如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既然政治效能感是对个体政治主观态度的测量,政治依托权力运行,为何在研究中单单对权力边缘的普通公民“情有独钟”?而缺少对权力运行主体——政府官员或公务员群体的研究?作为政府体制运行和政策文件执行的核心支持力量,公务员群体对于政府和政治的态度和看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改革成效和分配机制,不容忽视。此外,在中国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作为党的最小细胞,党员的政治效能感同样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未来。对党员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更是该领域本土化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以有意识地增加对多元群体的研究,丰富政治效能感在我国的研究成果。
第三,多为城乡对比,缺乏跨文化、跨地域的研究。从已有研究中,不难发现,半数以上的量化研究都是对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的研究,通过对比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差异,梳理出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相关影响因子。这类的城乡对比研究也集中在同一个区域,缺乏更大视角的现状对比及理论对话。对话是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从大的方面讲,作为一个“舶来品”,政治效能感在我国的发展必然要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与海外研究进行跨文化、跨地区的交流,借鉴有益经验,弥补国内研究的不足;从小的方面讲,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对比,是对政治效能感实证研究的有力补充,可以从更广泛的区域对相关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增强研究的科学性。
第四,研究结构上以双维结构为主,对集体效能感的研究匮乏。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是目前研究政治效能感的两个主要维度,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集体效能感”作为研究的第三维度。集体效能感能否用于个体?集体效能感如何测量?集体效能感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关系是什么?加入集体效能感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如何变化?这一系列问题都是目前集体效能感在研究中难以操作和使用的原因,相关研究非常薄弱,亟待完善。退一步讲,政治效能感的内在和外在划分是否真的能够指导行政管理实践?是否存在更优的划分标准?这些问题都是研究政治效能感主题不可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32]李蓉蓉. 海外政治效能感研究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10(9).
[2][34]Angus Campbell,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M]. New York: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1954:187.
[3]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东方出版社,2008:170.
[4][5][6]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s: Political Efficac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7(1).
[7]孙昕聪.论政治效能感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J].甘肃理论学刊,2017(2).
[8][39]Abramson,P. R.,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M]. W. H. Freeman and Company,1983.
[9]R. E. Lane.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Politics[M].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59:151-154.
[10][33]刘小青.降低评价尺度偏差:一项政治效能感测量的实验[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3).
[11][46][74]李蓉蓉.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2).
[12]朱妍. 中产阶层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评价——比较中国与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J].青年研究,2011(4).
[13][57][78]陈雪莲.地方干部的政治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一项以问卷为基础的研究[J].社会科学,2013(11).
[14][53]李蓉蓉.城市居民社区政治效能感与社区自治[J].中国行政管理,2013(3).
[15]胡荣、沈珊. 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和公众的政治效能感[J].东南学术,2015(3).
[16][35][41]范柏乃,徐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4(11).
[17]谢秋山、陈世香.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3).
[18]袁浩、顾洁. 社会公平感、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2).
[19][70]张蓓.媒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J].学海,2014(5).
[20][36][45][54]丁百仁、王毅杰. 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21]胡荣、庄思薇. 市场化、媒体使用和中国居民的政治效能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22]熊光清. 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五省市的实地调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2).
[23]丁永斌、王文文、孟崇峥. 普通高校研究生政治效能感实证研究[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24]周翔、刘欣、程晓璇. 微博用户公共事件参与的因素探索——基于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的分析[J].江淮论坛,2014(3).
[25]StephenC.Craig, Richard G.Niemi, and Glenn E. Silver,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A Report on the NES Pilot Study Items[J]. Political Behavior, 1990(3).
[26]Bandura,A. Exercise of human agency through collective efficacy[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3).
[27]Lee,F. F.Collective efficacy,support for democratization,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06(3).
[28]李燕、朱春奎、姜影.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6).
[29]Balch, George I. Multiple Indicator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Efficacy[J].Political Methodology,1974(2).
[30]Seligson M A. Trust, efficacy and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Costa Rican peasants[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0(1).
[31]王丽萍、方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0(2).
[37][61][65]胡荣.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5(1).
[38][49]孙伦轩、刘好妤. 教育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研究[J].教育经济评论,2018(4).
[42][50]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华夏出版社,1991:73.
[43][52][60][73]吴重礼、谭寅寅、李世宏.赋权理论与选民投票行为: 以 2001 年县市长选举与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为例[J].台湾政治学刊,2003(1).
[44]郑永兰、顾艳. 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及其调适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对苏南四村365位村民的问卷调查[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47]郑磊, 朱志勇. 教育是否促进了中国公民的政治选举投票参与——来自CGSS2006调查数据的证据[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3(2).
[48]魏以宁. “倒挂”: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的实证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7(17).
[51]Nie,Norman H.,J. Junn and K. Stehlik-Barry,Education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in America[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6: 268.?偊f
[55]张雅雯、耿曙.中国大陆基层选举中的物质诱因与投票动员: 以上海“先进”、“发达”村改居为例[J].东吴政治学报,2008(4).
[56]Hetherington M J.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4).
[58]Lambert R D, Curtis J E, Brown S D, et al. Effect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Governing Parties on Feelings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6(4).
[59]陈陆辉、耿署.政治效能感与政党认同对选民投票抉择的影响——以 2002年北高市长选举为例[J].台湾民主季刊, 2008(1).
[62]Schlozman, Lehman K. Voice and equalit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王靖舆、王德育.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对其政治功效意识之影响:以2004年总统选举为例[J].台湾民主学刊,2007(1).
[64]Ikeda,K.,T. Kobayashi and M. Hoshimoto,Do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ke a differ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hoice,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efficacy[J],Electoral Studies,2008(1).
[66]Stenner Day,K. and M. Fischle,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efficacy: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J],Politics,1992(2).
[67]Bruce E. Pinkleton and Erica Weintraub Austion and Kristine K. J. Fortman. Relationships of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disaffection to political efficacy and voting behavior[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1998(42).
[68]Aarts K, Semetko H A. The Divided Electorat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J],Journal of Politics, 2010(3).
[69]Kenski K, Stroud N J.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06(2).
[71]王井.公务员群体媒介素养的影响因子与差异化分析——以浙江省公务员为例[J].领导科学论坛,2015(11).
[72]Lawrence Bobo and Jr. Franklin D. Gilliam,Rac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Black Empowerment[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0(2).
[75]陈炯彤.广州高校学生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以广州市五所高校为例[J].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4(1).
[76]陈安繁,张慧,方爱华.政治效能感、媒介使用和利益抗争方式——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研究[J].新闻界,2015(22).
[77]邓燕华,黄健. 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6(5).
[79][80]李鹏.人民政协界别设置对界别委员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基于广东省M市政协委员的问卷调查研究[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6(1).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3-0052-10
*[收稿日期]2019-05-06
[作者简介]陈志广(1978-),男,湖南醴陵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魏可可(1991-),女,河南驻马店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政治心理。
(责任编辑:时 间)
标签:效能论文; 政治论文; 量表论文; 测量论文; 这一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