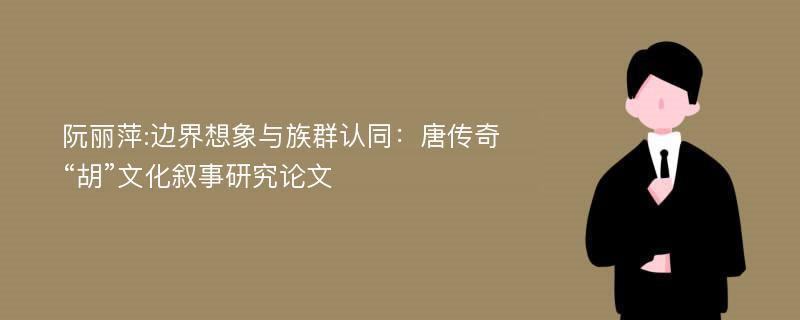
摘 要:李唐一代为胡汉文化交融的繁荣时期。异质文化交流中,胡族迥异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色引起中原汉人的好奇和猜测,因此,“胡”文化叙事形成了唐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唐传奇作者“作意好奇”,对胡族文化特征所呈现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叙事。经过“文化过滤”,传奇作者对胡人胡风的文化叙事中充满了异域想像和边界意识,文士笔下的胡人成为“貌怪”“行异”“类兽”“异心”的集体形象想像物。叙事反映了特定文化群体共享的意义、信仰与价值,作为叙事主体,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流话语人群的传奇作者,在完成对胡人身份叙事与族群认同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作为中原儒家文化代表的集体身份认同,在“边界意识”与儒家话语权的心理机制作用下进行胡族文化的历史抒写。
关键词:胡;边界想象;族界标识;族群认同;儒家话语权
盛唐文化,精彩纷呈,蔚为大观,在诸多促成因素中,民族融合与异质文明跨文化交流是一大关键。陈寅恪有云:“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1]唐时中西交通发达,政治稳定、商业繁荣、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兼之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吸引了大量边地少数民族持续内迁,形成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2]的盛世局面。内迁民族中,以来自西北诸蕃的胡人数量最多,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唐时仅长安一个城市,就有“胡客”四千人。四千“胡客”或为传教、或为经商、或为学习,或为婚配,来华多年之后成为“住唐”胡人,与唐代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即使在唐政府予以遣归的情况下,竟“无一人愿归者。”[3]因此,整个唐朝社会都盛行着“胡风”,在国家政治军事活动、经济商业活动、宗教文化领域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活跃着胡人的身影与胡文化的异域风情,所谓“上至政治文学,下迄阉宦奴婢,在在皆有蕃胡。”[4]
“好奇”是唐人共同的审美心理。在文学领域,诗文既滥,人不欲观,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传奇作者“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5]“胡”所代表的异域文明不仅带给唐人神秘的感官刺激,又给搜“奇”寻“异”的唐传奇作家提供了奇特而丰富的创作素材,唐传奇中所出现的大量胡族文化叙事,正是唐代胡汉文化多层次交融的时代产物。从文化叙事的视角来看,胡人特殊的体质特征与文化差异吸引了传奇作家(叙事主体)的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胡人群体在大唐社会的生活空间,揭示出不同群体的异文化特征。从“身份”出发,传奇作者的文化叙事集中描写了“胡”这一社会群体的文化禀赋。
唐人所谓的“胡”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之“胡”,与“汉”相对,泛指西北各少数民族部族、中西亚甚至欧洲各民族;而狭义之“胡”,在唐代专指西域诸胡。何谓“胡”及“胡人”?这涉及到族群身份的确认问题,唐人称“胡”,是种族的,也是文化的,有三个层次的族界标识:首先是地域上,既指东北部的靺鞨、室韦、契丹、奚,北部的突厥、薛延陀、回纥、鲜卑、黠嘎斯等部族,也指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吐蕃、龟兹、于阗、大宛、楼兰、高昌、波斯、若羌、天竺等西域各民族;其次是种族概念,从肤色、鼻形、发质、身材、嘴唇厚薄等生物性差异现象来划分族群,将具有高鼻、深目、身长、浓须等显性体质特征的外蕃人统称为“胡”;第三个是个文化(族群)概念,在族群接触中,将行为模式上包含特定文化要素(如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宗教、习俗、服饰、审美习惯、价值取向等)的外蕃统称为“胡”。三个层次中,前两个层次是显性的;第三个层次则是隐性的,是族群认同要素中最核心的部分。唐人小说中,胡族文化叙事基本围绕以上三个层次展开;就唐传奇而言,因“作意好奇”,传奇作者作为异文化的“注视者”,意在探“奇”,较为关注胡人显性生物特征,着意刻画胡人“貌怪行异”的异族形象。
胡人的外貌大异于中原汉人,因此受到唐人的广泛关注。唐代文士在族群接触中注意到胡人“貌怪”的特点,文本中多次用“怪”“陋”“寝”等语词描述胡人外貌特征,并根据胡人显性的生物差异对其进行“分类上的授予”。传奇作者对于胡人外貌描摹常常是寥寥数笔,简短而传神地勾勒出“高鼻”“深目”“身长”“浓髯”的胡人形象。《太平广记·诙谐四》“赵小儿”条记载了一胡僧与赵小儿之间的辩论:
(胡)僧语云:“此郎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6]
相对于汉人而言,胡人鼻长而眼深;相对于胡人而言,汉人声高而身小,这是显性的种族生物差异现象。胡人的鼻子与汉人不同,鼻梁高挺而鼻头尖,中唐诗人陆岩梦称胡女鼻子“高于华岳山”(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予女》);又杜甫诗云:“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黄河二首》其一),铁马长鸣,胡兵结队而行,高耸的鼻子成为显著的标志。
国家以改善孤残儿童成长环境、提高孤残儿童生活质量为目标,提出“十一五”[1]和“十二五”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暨儿童福利机构设备配置实施方案[2](以下简称“蓝天计划”)。切实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孤残儿童的集中养护、救治、教育和康复。
安禄山之所以动气,根本原因在于哥舒翰称他为“狐”,从族群上将他排除在汉族文化圈之外,而这一点是安禄山最忌讳的地方。从形象学的角度看,“狐”是胡人形象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胡狐相通套话的建立,事实上就把胡汉文化分了等级,暗含汉人对异族的拒斥、歧视、偏见。
“浓髯”是胡人形象的又一大特点。如《广记》卷256《嘲诮三》“邵景”条载,唐睿宗时,朝散大夫邵景、萧嵩同朝为官,两人“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于庭。铿独廉中窃窥而咏之:‘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11]可见,唐代中原汉人对胡人族群特征认知里面,“须多”“鼻高”是显著特征。不同于汉人黑色胡须,胡人的胡须以紫色为多,而且浓密。有着边塞生活经历的唐诗人岑参,对胡人的浓须有过特写:“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又“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紫髯”是胡族的另一显著族群生理标志。
世界人民在环境危机、战争、饥饿、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问题面前,是利益的共同体。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问题,必须要由全世界各国通过化解彼此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比如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国家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等,是每一个互联网国家都面对的危险。在网络安全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绝对安全,不管它网络技术多么发达。2011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就曾强调:“网络安全威胁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安全挑战。”[2]
再者,胡人举止间带有动物的习性。如前所述,作为中原汉民,传奇作家对胡人的生物性特征进行描述时,受“非我族类”边界意识的驱使,不自觉地将胡人与相关动物进行类比,将胡人习性加以动物化。以兽谤人的写法,在唐代十分盛行。早期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影射初唐书法家欧阳询为白猿之子,作者的创作依据在于欧阳询的长像“耸脖”“埋肩”的特点,像一只大猕猴;《隋唐嘉话》记载了长孙无忌与欧阳询就对方的相貌、血统进行互嘲,针对长孙无忌的发难,欧阳询也不甘示弱,以诗句“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嘲讽长孙无忌相貌丑陋、类猿,当为胡人。
首先,胡人行踪诡异,来无影去无踪。《广记》卷96“韦皋”条载:“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12]这位胡僧不召自至,出现在韦府的行为突兀而失礼,所以引发众怒。又《广记》卷76“李淳风”条[13]载“北斗七星下凡西市饮酒”事:太史令李淳风通晓天文,向唐太宗奏报说北半七星将下界到人间。太宗派遣使者并诏书,如李淳风所示时间、地点前往迎接,结果发现是七个婆罗门僧人(胡僧)。胡僧西市痛饮,饮毕随使者下楼的时候,却毫无征兆地消失了踪影。又“僧伽大师”条记载,[14]一位胡僧大师本已在长安荐福寺圆寂,后来却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临淮化缘,其行迹之诡异,足以令人诧异。
其次,传奇文人笔下的胡人多有迷惑他人的幻术:胡女的魅惑之术、胡商识宝的奇异能力、胡僧的神奇的方术、昆仑奴的驻颜之术等等,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神奇能力使胡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幻术”即为胡人的特异功能,对胡人“幻术”的描写亦符合传奇小说“作意好奇”的创作原则。《广记》卷285“胡僧”条记载,[15]唐贞观中一位“呪术”“能死人,又能生人”的西域胡僧形象;又“梵僧难陀”条记载,[16]记一位擅长“幻术”的梵僧难陀,当众将自己的头割下来,钉在柱子上,此头不但不流血,还能唱歌,不一会儿又回到原处。又“叶法善”条记载,[17]中的“通天狐”,法力高强,是胡神中最具法力者。此外传奇中还出现了具有超常能力的昆仑奴形象,个中既有驻颜幻术者,又有超常水性者,“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18]
1.坚定政治觉悟的强化。信息化调查过程中可能会接触更为隐晦的社会阴暗面,需要调查人员更加具有分辨是非的政治觉悟,必须具有始终如一的忠诚理念。信息化调查工作难以避免、也具有更为便捷的了解案件内外的个人或单位隐秘信息可能,需要调查人员具有更为完善的爱国、爱民政治觉悟。需要按照“如果没有忠诚,能力将无处安身”的信念建设高政治素质人才队伍。
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胡人,行为方式较为诡异,具有神秘性。在传奇叙事过程中,“胡”常常作为一种外在的神秘力量参与叙事,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胡人”在叙事文本中或出现,或隐退,并不需要遵循叙事的逻辑,只是作为一种外在神秘力量存在。
传奇中,胡化狐、胡化虎、胡化猿、胡化狼等“精变”故事俯拾皆是,如《宣室志·杨叟》中的猿精幻化为胡僧事;《宣室志·王含》篇中,王含的母亲由狐精幻化成胡女,继而嫁与中原汉人并生子事;《原化记·柳并》中的虎精化为胡僧事等等。胡人身怀“幻术”,用某种神秘的力量迷惑人,与狐狸精迷惑人的习性相类;“胡”“狐”相通的命题得以佐证。胡化狐,或狐化胡类的故事在唐传奇数量较多:《广记·狐三》“李元恭”条载:“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19]《广记·狐九》“张谨”条记述张谨宿邻村遇胡(狐)女事:“每日昃,辄靓妆盛胡,云召胡郎来,实乃狐魅。”[20]又“叶法善”条以兽谤人,嘲讽胡僧为狐精化身,惯于蛊惑人心,以此抹黑胡人形象。“王含”条记载,[21]王含的母亲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狩猎,在她身上,既有狼的凶残、暴虐、嗜血的一面,又有人的生活伦理,在为家人所不容之时,破户而出不返。他如《古镜记》中的千年老狐狸、《姚坤》中的狐仙夭桃、《任氏传》中的狐妖任氏等,在外貌、语言、思维方式上既有“人”的特点,而在生活习性上又有“狐”的秉性,更有文章指出,《任氏传》中的“狐女”应为“胡女”。[22]
胡人长相奇异,唐人带着新奇的眼光、极度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建构了胡人的形象。法国学者谢和耐说:“(唐人)略带一点讽刺意义和某种嘲弄倾向地保持了对这些民族的充满新鲜的记忆。”[23]“胡”“狐”“精”“怪”等带有歧视性的蔑称,基于一种文化边界意识与族群认同心理,是一种分类上的“授予”,用于辨认成员,证明非成员。《新唐书·哥舒翰传》记载了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关于族群认同的一场对话:
首先,提高农业固碳能力。例如,美国在长期耕作及土壤风化腐蚀的农地采取保护性耕作及休耕方式,并在休耕地表覆盖植被增加土壤有机碳的储存容量的同时减少土壤的物理性扰动来改进土壤有机质的比例。其次,制定低碳农业发展战略。俄罗斯2007年7月颁布了《2008-2012年农业发展,农产品市场调节、农村发展规划》。该规划把改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护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目标之一,对低碳农业的关键环节进行扶持,资助生态农业的相关科技创新。
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曰:“谚语‘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即骂曰:“突厥敢尔!”[24]
胡人眼窝深陷,眼睛多为绿色,如同绿宝石,这让中原人觉得很新奇。《新唐书·西域传》:疏勒“其人文身碧瞳”。《文献通考·四裔考十四·疏勒》卷三三七也说,疏勒、吐火罗一带,“其人文身,碧瞳”“出善马,人碧瞳”。[10]唐代中原汉人对胡人的感知映射着汉人的理念:认为胡人眼睛里有着卑微与悲愁,并将之与鹰眼联系起来,称之为“愁胡”。杜甫《画鹰》:“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又“预哂愁胡面,初调见马鞭”(杜甫《从人觅小胡孙许寄》);又“二鹰猛及徐侯穟,目如愁胡视天地” (杜甫《王兵马使二角鹰》)等等,都是以鹰眼类比胡人之眼睛,状其既绿且深之貌。另外,唐传奇胡化狐、胡化狼之类的故事较多,“胡”“狐”相通、“胡”“狼”相类,其中一个重要的生理依据就在于胡人绿荧荧之窅窅深目与“狐”“狼”相类。
其次,在施工前期,施工企业要对施工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多种原材料进行宏观把控,做好资源管理工作。同时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并制定紧急应对方案,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及时解决,减少损失,维护工程效益。
法国学者莫哈在论及文学形象的研究方法中指出:“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创作出的形象。”[25]他认为文学形象包含三层语义:第一层语义强调的是形象的现实性,关注的是形象中稳定和忠实的成分。第二层语义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关注创造了他者形象的文化。于是,他者形象被纳入了想象的传统之中。第三层语义,我们关注创造形象的作家的特殊感受,即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性在其塑造的形象上的反映。研究唐人传奇中的胡人形象亦可作如是观。胡人“高鼻”“深目”“紫髯”“绿眼”“体臭”是形象的第一层语义,是相对“稳定与忠实”的关于胡人的“套话”;形象的第二个层次——“胡化兽(狐、猿、虎、狼)”命题与“胡精”“胡怪”“胡雏”“胡虏”“杂种”等指称,将胡人形象妖魔化与神秘化,是传奇作家对胡族社会文化整体的阐释与想象,也是一种变异了的形象,形象学上称之为“社会集体想象物”。此时,胡人(他者)形象是在他者缺席状态上虚构的、经过文化过滤的形象,是注视者文化的投射物,变异现象伴随着他者形象塑造与接受的整个流程。传统的形象学研究将重点放在第一层次,而研究“变异”与形象建构及阐释者(作家)的主体性是当代形象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循着这一思路,发掘传奇作家作为一个唐代文人整体的“集体无意识”及主体性,是理解传奇中胡人形象变异与胡族身份建构的关键点。
作为“胡”文化叙事与胡人形象建构的主体,传奇作家的身份理当引起注意。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指出唐代科举中“温卷”“行卷”之风,催生了大量传奇作品,认为“此等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26]即是对传奇作者集史官、诗人身份于一体的士大夫身份肯定。作者的文化身份决定言说立场,传奇作家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决定了其“胡”文化叙事及胡人形象建构的言说立场。从今存唐传奇作品的创作时期分布来看,建中初(780年)至咸通末(873年)近一百年期间,是唐传奇创作的高峰时期,大量的“涉胡”题材叙事也集中于此。安史之乱后,安史叛军的胡族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戎狄乱华、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乱后流弊促使中唐士子重新审视初唐太宗以来“爱之如一”的民族观,社会反思中,“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重新得到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这两股社会思潮也直接影响了传奇的创作,“涉胡”言说中的“边界意识”、胡族叙事中“文化过滤”现象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以天下“复兴”为已任的儒士群体。
至于胡人“身长”的特点,唐传奇中多有描写。传奇《张政》篇记载,唐朝邛州人张政,死后在梦中遇到一位“长八尺余”的胡僧;[7]又《楚州人》篇,以中原汉人的视角描摹胡人,“乃见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长丈余,首出墙头。”[8]可见,身材高大是胡人的特点与指认标识。《太平广记·妖怪八》引《王氏见闻》讲了王宗信识胡僧的故事,他在得知是胡僧提诸妓入火焚炽之事后,“宗信大怒,悉索诸僧立于前,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是此也。’”[9]在诸多僧人之中,王宗信仅凭周姓僧人“身长”的特征,就认定他为胡人,继而以文化经验上的刻板印象认定他为犯罪的胡人。事情的结果是,这位“身长貌胡”的周姓和尚是被冤枉的:“宗信遂鞭之数百,云有幻术。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10]
传奇中“胡”族叙事的“边界意识”,是士人基于戎狄乱华的历史事实,对自己所属族群“华”之主体身份进行审视、探寻、确认的结果。安禄山的身份是昭武九姓之羯胡,胡人乱华的事实在汉人心里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于是迁怒于整个胡人群体,如学者王忠所言:“(安禄山)曾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之善战胡族以增强其武力,故安史乱起,士大夫皆视为胡族乱华,民族意识自觉而亢张,遂有杜少陵诗焉。”[27]安禄山等胡人叛军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包含杜甫在内的中原士人的无比愤怒,面对长安城内“社稷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的现象,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着对胡人的防范与不满,文人创作中“边界意识”成为必然。安史之乱破坏了唐人对异质文化“极恢廓的胸襟”的自信,士人心态由之前的自信昂扬转为内敛哀伤。
高职院校中毕业的学生虽然可以填补社会中某一领域的人才空缺,但在我国逐渐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背景下,这些基础层级的就业市场也逐渐形成了饱和状态。因此高职院校就业难局面便越发凸显。结构性过剩的成因基本都为地域性供需结构失调,故院校在利用师资队伍建设而调整供应力量时,应尽量摆脱人才竞争这一目标,尽量以提升供应质量作为核心视角。
安史之乱后,唐人对胡人由初、盛唐时期的宽容纳异心态,转变为中唐之后的“憎胡地怨胡天”的敌对心理,重新回归到春秋时代的华夷之辨伦理。这股社会思潮也影响到中唐以后胡人形象的文学书写。所以唐传奇作家对胡人形象的建构中,立足于“貌怪行异”之族界标识的抒写,并在胡人生物性体质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等级差异的套话,如《广记》“苏无名”条记载,[28]讲太平公主的宝物被盗,胡人首先成为怀疑对象。又如“王宗信”条记载,[9]宗信根据周姓和尚“身长貌胡”的体质特征,断言周和尚为胡人,进而主观臆断其为犯事的胡僧,鞭打数百之后才发现这位新落发的周姓和尚并非胡人,是被冤枉的。又如“萧颖士”条记载,[29]萧颖士与女子同行,当女子说到姓“胡”时,萧颖士马上联想到“狐”,骂她是勾引人的野狐精,最后才发现是一场误会,原来是店主的女儿。以上多例显示出胡汉多民族融合的艰难,凸显出中唐士人夷夏有别的边界意识。
中药的提取过程是中药质量传递的关键环节,在设计提取工艺时,应考虑到药材所含成分的理化性质及其之间的差异,如分子大小、熔点、沸点、极性、溶解性等[25]。目前,最常用的提取方法是水蒸气蒸馏法,《中国药典》2015年版中规定的中药挥发油提取方法几乎是水蒸气蒸馏法,但水蒸气蒸馏法不适于热敏性、难溶性成分的提取。因此,需加强各种中药挥发油的最佳工艺基础性研究,完善中药挥发油提取技术。提取方法标准化的同时,具体的工艺参数也需明确,如采用有机溶剂萃取法,则需明确说明所用的有机溶剂名称、用量及萃取时间等。中药挥发油的提取过程若能得到有效控制,则其质量的稳定均一性将随之大大提升。
“文化过滤”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范畴,用于解释形象变异现象。文化过滤对他者形象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之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弥漫着“攘夷”“复古”两股思潮,陈寅恪先生将其视为中唐古文运动兴起的内在动因,《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法曲》有言:
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30]
古文运动是安史乱后唐室政治“中兴”在文学上的反映,以韩柳为首的中唐士大夫倡导古文运动的理路是,通过华夷古今之辨,确认汉族“华”文化身份,通过学古文、作古文的文学实践通达“复古道”的思想启蒙,即为韩愈“文以载道”之命题。其最终的文化指向仍在于“复尊儒术”,重新确立儒家伦理的主流地位。唐传奇作为古文运动的“附庸”(郑振铎语),传奇作家笔下的胡人形象是注视者文化的投射物,必定受到儒学复兴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胡族文化叙事中处处体现出士大夫的角色意识。这里涉及到唐传奇的创作动机问题,“立意垂诫”的思想启蒙动机在唐传奇创作中具有普遍性。“垂诫”的内涵当是将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到儒家文化所认可的伦理范围之内,这一点无庸置疑。在涉胡题材的小说叙事中,对胡人行为模式抒写中,儒家伦理文化过滤的痕迹尤为明显。如“胡人买珠”题材,胡人爱珠不爱身的“珠宝崇拜”行为,中原士人并不认可,因为它违背了重义轻利、“问人不问马”的儒家伦理。又《广记》“李勉”条[31]记载了一位波斯胡不远万里来中华寻宝的故事,爱宝而不爱身,以至身死他乡。相比之下,李勉千金在手却不为所动,一介不取。正反对比之中,儒家话语权自在其中。又有“胡变狐”之士子艳遇主题的传奇中,人神相恋型的婚媾题材的结局多半不圆满,以“胡女”(狐女)现出原型逃回山林告终,体现出儒家“鸟兽不可与同群”的文化伦理。传奇作者对狐魅的反感,对胡汉通婚现象的戏谑与拒斥,亦包含着对胡女所从事的色情业及当垆迎送的角色地位的否定,体现出士人对“礼法”“门风”等儒家伦理思想的尊崇,亦是儒家文化过滤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1956.
[2](清)彭定求.全唐诗(卷128)[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493.
[4]冯秉钧.唐代华化蕃胡考[J].东方杂志,27卷17号,1930.
[5](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卷三十五[M].上海书店,2009.
[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诙谐四(卷248“赵小儿”,出《启颜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宋)李昉等.太平广记·报应七金刚经.卷108“张政”条,出《报应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神二十二.卷312“楚州人”条,出《原化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9](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妖怪八.卷366“王宗信”条,出《王氏见闻》[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嘲哨三.卷256“邵景”条,出《御史台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异僧十.卷96“韦皋”条,出《宣室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方士一.卷76“李淳风”条,出《国史异纂》及《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4](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异僧十.卷96“僧伽大师”条,出《本传》及《纪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5](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幻术二.卷285“胡僧“条,出《国朝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幻术二.卷285“梵僧难陀”条,出《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7](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神仙二十六.卷26“叶法善”条,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8](宋)李昉等.太平广记·龙五.卷422“周邯”条,引《传奇》[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9](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狐三.卷449“李元恭”条,出《广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0](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狐九.卷455“张谨”条,出《稽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蓄兽九.卷442“王含”条,出《宣室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2]张军.《任氏传》中的“狐女”应当是胡女[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4).
[23](法)谢和耐,耿昇.中国社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4](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6](宋)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王忠.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8](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精察一.卷171“苏无名”条,出《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9](宋)李昉等.太平广记·谬误.卷243“萧颖士”条,出《辨疑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宝三[M].卷402“李勉”条,出《集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Marginalization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The Study of Ethnic Cultural on the Narration of Tang Dynasty
RUAN Li-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Emperor Li’s Tang Dynasty was a prosperously cultural communicating period for Ethnics and Hans.In this exotically fashioned communication,Hans,dominant habitants of Chinese Middle Plain,were curiously appealed to and mystified by the customs and conventionalities of Ethics.Therefore,Tang’s literature had been featured with the Ethnics’cultural narration since.The authors of Tang’s legendary literature intentionally exerted their curiosity in the narration of life style presented by Ethics with the cultural refinement recomposed to flatter the local popularity.Exoticism and marginalization are thus replete in their legendary stories in which Ethnics are collectively portrayed as fancies such as “abnormalities”,“mimic monsters”or “gentiles”.Shared by certain clans,the meanings,beliefs and values of their narrations are mirrored in their collective culture.As the narrative subject and the main discourse,the authors of legends,represented by the leveled scholars accomplished their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s the Confucius discourse of Chinese Middle Plain by historically narra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Ethnics in the way fused by their creative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their identity of Confucian discourse.
Key words:Ethnics;Marginalization;Ethnics symbol;clan/Ethnics identification;Confucian discourse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9)03-0110-06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3.024
收稿日期:2018-07-19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2018年度科研立项“传统与现代之间:陈寅恪‘新宋学’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项目编号:sisu2018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阮丽萍(1978-),女,湖北咸宁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传播。
(责任编辑:辛丽平)
(责任校对:李永皇)
标签:胡人论文; 太平广记论文; 形象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文化论文; 《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四川外国语大学2018年度科研立项“传统与现代之间:陈寅恪‘新宋学’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项目编号:sisu201803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西南大学文学院论文;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