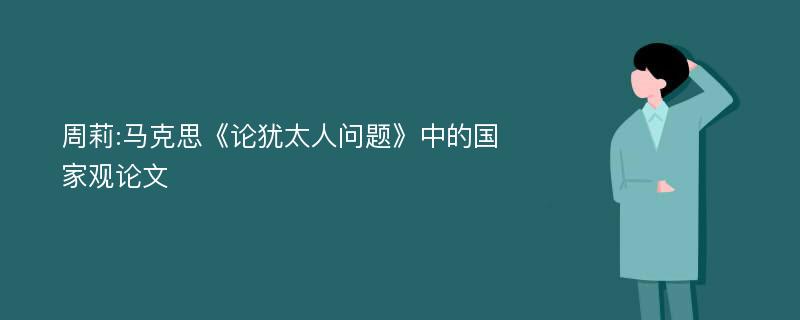
摘 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里明确指出,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国家的问题。针对鲍威尔只批判基督教国家而不批判“国家本身”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从基督教国家到现代政治国家凸显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充分肯定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同时也看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这种限度导致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内在缺陷,即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实质是真正意义上的的基督教国家。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政治国家必然会沦为市民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现代政治国家并成为现代政治国家的目的。于是,马克思从对现代政治国家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进一步引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一定程度上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关键词:基督教国家;政治解放;现代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犹太精神
19世纪早期,德国社会的核心话题之一集中在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上。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而此时鲍威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提出了政治解放与现代政治国家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看法有失偏颇,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作了《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国家的问题,并随后对现代政治国家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与鲍威尔以及黑格尔不同的国家观,应该“承认马克思有着更深远的眼光和更宽阔的视野”。[1]从人类精神发展史的角度,马克思揭示了从基督教国家过渡到现代政治国家的必然性,认为政治解放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有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导致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内在缺陷,即它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从此,人被迫过上了双重生活,政治国家反而成为超越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存在,现代政治国家的实质进而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伴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壮大发展,现代政治国家逐渐沦为其统治的工具,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现代政治国家而上升为其目的。于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政治国家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理性精神转向了现实和物质利益关系,从政治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后来成为马克思一生关注的重点。
1 从基督教国家到现代政治国家
马克思和鲍威尔当时所处的德国,其政治制度相比较同时期的英国、法国来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以至于马克思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处在当代的焦点”。[2]5德国的犹太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鲍威尔看来,当时的德国本质上是基督教国家,仍然以宗教为前提,还没有完成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因此,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首要条件是必须实现彻底的政治解放,使德国成为现代政治国家,而犹太人则必须放弃他们信仰的宗教。对于政治解放,鲍威尔指出,要实现真正的现实的现代政治国家,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是实现现代政治国家的最后手段和必要途径。同时,鲍威尔把宗教的对立看做是“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2]23而犹太教是特权的狭隘的宗教,远远没有达到人的精神发展的自我意识阶段。他希望借助国家取消宗教的特权,唯有如此才能达成政治上的解放。因此,他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2]25
马克思不同意鲍威尔的这种观点,他并不否认普鲁士国家的基督教性质,也不否认在落后的普鲁士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国家必须实行政治解放的途径,更不否认政治解放的进步性,而是认为是否存在宗教并不是现代政治国家实现与否的前提。马克思通过对德国、法国、北美各州具体情况的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地区虽然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是宗教并没有被完全废除,依然得到了留存和发展。因此,马克思认为,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现代国家里依然保留宗教,一方面揭露出这些国家的软弱无能,仍然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代政治国家本身依然存在问题和缺陷,这恰恰暴露了政治解放的限度。政治解放只是让国家挣脱了宗教的束缚,但是国家中的人并没有挣脱宗教的束缚。换言之,无论国家中的人是否信奉宗教,政治解放并不是国家解放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国家是否得以解放的前提条件,更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因此,这种解放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解放。从这种政治解放中建立的现代政治国家本身也是抽象的有限的国家,依然存在种种缺陷和问题,人依然受到宗教的束缚,它仅仅通过间接的方法承认人,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媒介。换句话说,政治解放仅仅使国家挣脱了宗教的束缚,将国家领域(公共领域)的宗教变成了市民社会领域(私人领域)的宗教。这一切表明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从而也带来了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
2 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
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前,又被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当时并没有国家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是一个政治权力为主体的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在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没有清楚或严格的边界和界限,以至于二者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换言之,政治性不仅是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本质属性,也是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直接属性。直到近代社会,由于近代思想家们的启蒙使得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深入人心,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开始不断尝试冲破共同体本位社会的藩篱。在“时代错乱”的德国,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马克思认为这种制度的性质是封建主义)更是招致了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强烈不满,在近代启蒙思想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影响下,政治解放成了包括鲍威尔等在内的新兴市民阶级实现现代政治国家的必要途径。
铷是一种非常活泼的稀有碱金属,不仅在传统的电子器件、催化剂及特种玻璃等领域应用广泛,而且在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显示出极大的应用前景[1-3]。铷作为分散元素,至今仍未发现单纯的铷矿,而是以伴生状态赋存于锂云母、铯榴石、铯锂云母、光卤石、钾长石、盐湖卤水、地热水及海水中[4-5]。由于没有独立的铷矿可以直接利用,从浸出液和卤水中回收是获取铷的主要方式。从溶液中分离提纯铷的关键是去除其中性质极为相似的锂、钾、钠元素[6]。
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以偏概全,只看到政治解放的积极性作用,却忽视了其带来的消极结果: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胜利之后,人民推翻了同自身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建立了现代政治国家,如何管理现代政治国家成为人民的事务。因此,“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2]44政治国家成为人民的普遍事务,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解脱出来,政治性不再是其直接属性。可见,政治国家的政治属性不但没有被清除,反而得到了强化,而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却最终被祛除。于是,政治属性得到强化的政治国家与没有了政治属性的市民社会开始明确区分开来,并逐步导致了二者的分离和对立。具体来说,在现代政治国家中,政治国家负责管理人们公共领域的事务,市民社会则负责人们私人领域的事务。因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者之间界限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来说,二者的分离和对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质和表现。
从“远远落后于时代”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全球坐标在变化。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发展,世界从未如此聚焦中国。今天的改革,必须在百年未有的国际大变局中,经受各种风浪的洗礼。
3 现代政治国家的本质是真正意义的基督教国家
随着政治解放的完成,宗教被驱逐到市民社会领域,市民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犹太精神(货币拜物教)也逐步蔓延并风靡一时。犹太精神的风靡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市民社会逐步把现代政治国家视为其手段和工具,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政治国家的目的。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的发源地和舞台”。[5]
但是,伴随政治解放带来的这种后果,人也被迫面临着双重生活的境遇:一方面是政治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成员,另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个体。“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2]30于是,政治国家中的生活和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彼此处于相互区别、对立的状态。政治国家中的生活实质上是人们不懈追求的普遍性的公共生活,人是作为抽象的普遍的类存在物而存在的;而市民社会中的生活是不具有政治性的私人生活,人是作为现实的特殊的个体而存在的。因此,市民社会是人现实生存的私人领域,政治国家是人追求的普遍的抽象的公共生活领域。但是人们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体生活是不真实的,国家中的公共生活才是人的本质。于是,政治国家成为超越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存在,它成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和目的。“正因为人们有如此的认定,政治国家才获得了相对于市民社会的超越性,才能被作为普遍性而发展起来。”[3]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对现代政治国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了其本质是基督教国家的结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论断,也是因为宗教在现代政治国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看到,一些国家虽然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是宗教并没有被完全废除,依然得到了留存和发展。这充分表明:一方面,政治解放虽然使现代政治国家不需要借助宗教这种形式来充实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它并没有取消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也不要求人们完全排除对宗教的虔诚。换言之,政治国家已经强大到有足够的能力去管理公共事务,不需要再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宗教在公共事务中已失去用武之地,只能从这一领域迁移到市民社会。宗教虽然被下放到市民社会中,不再与普遍性的政治国家发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它对人们在理解、认同现代政治国家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市民社会精神的宗教与现代政治国家的政治意识和公民精神,在超越精神和抽象普遍性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不只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宗教甚至担当起了现代政治国家的政治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作用。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 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 而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 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 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其出发点和结果。”[4]于是,人们认为政治共同体的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类的普遍性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市民社会的生活虽然是现实的生活,但却是不真实的现象。正如在宗教中,人们认为天国的生活是真正的普遍的生活,宗教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促使它力图超越个体的有限性(世俗生活)而达到普遍性(天国)。现代政治国家也和宗教超越世俗生活的有限性的方式相同,力求超越市民社会这个不真实的现象而达到政治共同体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奉宗教的国家成员所具有的宗教意识,使他们更容易理解、认同现代政治国家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现代政治国家基于自己本身的缺陷更需要借助宗教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来维系自身的存在。正是基于宗教在现代政治国家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现代政治国家的实质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
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论断,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现代政治国家和宗教的相似之处。现代政治国家和基督教一样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承认人,都通过一个媒介,只不过后者的媒介是基督,而前者的媒介是国家。在宗教生活中,人们借助基督这个媒介连接着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把处于世俗生活彼岸的天国的神圣生活看作是真正的生活,希望能摆脱世俗生活的苦难而通往天国;在现代政治国家中,人们以国家本身为中介连接着政治共同体和市民社会的生活,把处于现实的市民社会生活彼岸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看作是真正的生活,借以实现人和人之间的普遍自由。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理论范式。基督教作为人的精神发展过程的一个低级阶段,它用天国的、宗教的途径彰显了人的普遍自由,而现代政治国家作为紧接着基督教的下一个阶段,则用世俗的、政治的方式实现了基督教的这一真理——人的普遍自由。因此,现代政治国家是对基督教的继承和超越,同时用世俗的、政治的方式取代了非世俗的、宗教的方式,从而实现了基督教的人的基础——人的普遍自由。可见,在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方面,现代政治国家和基督教是殊途同归的,现代政治国家是类似基督教一样的抽象的存在。所以,基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现代政治国家界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
4 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
通过前面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了这一结论:现代政治国家的本质是真正意义的基督教国家。这个结论是对鲍威尔“基督教国家”观念的驳斥和反击。鲍威尔所说的“基督教国家”,指的是落后的普鲁士国家,这种国家以基督教为前提,政教不分,是一个实行普遍奴役制的特权国家。鲍威尔驳斥了普鲁士的这种国家形式,主张实行彻底的政治解放。他认为政治解放可以解决国家的一切问题,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是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完善的国家。但是,鲍威尔只批判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并不批判“国家本身”,即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包括黑格尔主张的现代政治国家制度,认为现代政治国家是德国政治解放的最高目的。但是,马克思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鲍威尔的“基督教国家”虽仍然以基督教为前提,但还是没有完成的基督教国家,而通过政治解放建立的毫无缺陷的完美的现代政治国家,实质上才是真正意义的基督教国家。
除了印刷技术方面,在环保方面,利丰雅高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进行环保生产。公司在空气治理方面投入400万安装了VOCs末端催化燃烧装置;积极做好源头控制,禁用含酒精的异丙醇洗车水;严格进行过程管控,比如将擦拭布放在密封箱里等。末端治理方面,利丰雅高安装了废水净化装置,保证排出的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废水。对于废固,其按照规定码放、建立台账、交由资质公司处置。可以说,利丰雅高在环保的路上真正做到了源头控制、过程管控、末端治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思想。按照他们的观点,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赋有一切自然的权利,并且可以任意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为了让人类更好地实现自我保存,人们借助理性相互约定,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转让出来组成公共权力,转让出来的权利形成了公共权力领域即现代政治国家,没有转让出来、依然留存的权利形成了私人领域即市民社会。可见,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现代政治国家是基于人的自然权利之上的公共的普遍的权力机构,现代政治国家不仅高于市民社会,而且是市民社会的目的。那么,市民社会则是现代政治国家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一思想后来被黑格尔和鲍威尔所认同和继承。随着政治解放的完成,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逐渐割裂并对峙起来。因此,马克思认为,对于生活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人来说,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重生活——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即人一方面是政治国家的成员,另一方面则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人在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在这里,即在把自己并把别人看作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做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是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2]31于是,现代政治国家成了非现实的类存在物,代表了人的普遍利益,是市民社会的目的;而市民社会则被看做代表私人利益的不真实的现实的个体存在,是现代政治国家的前提。于是,人们总是不断地克服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从而达到现代政治国家的普遍性,这成了现代人普遍追求的理想和目的。
接着,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市民社会是代表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不再直接具有政治性,在这个领域中,人的行动完全是基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的私人化的活动。一句话,市民社会中的人实质上是自私自利的人,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准则。“金钱”是他们世俗的神,“自私自利”就是他们行动的精神准则。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自私自利”的精神准则并不只是某些个别群体的精神,而是成为市民社会普遍信奉的精神准则。于是,这种精神准则逐渐普遍渗透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需要,不断地把他人和自己看作是手段和工具,造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现代政治国家——先前作为市民社会的理想和目的的普遍性的现代政治国家——逐渐沦为市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最终不得不服从于市民社会的统治。至此,一直被人们奉为理想的普遍的现代政治国家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尊严,市民社会则成为了现代政治国家的目的。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于是,马克思批判的焦点从现代政治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从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
尿失禁的严重等级根据简表(ICI-Q-SF)的3个计分题得分情况进行划分[7],具体情况为轻度(1~5分),中度(6~12分),重度(13~18分),极重度(19~21分)。
总之,马克思透过对犹太人问题的现实关注,解答了政治解放的限度问题,看到了现代政治国家自身的缺陷,进而揭露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实质,并进一步分析出市民社会必然取代现代政治国家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虽然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国家观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是他已经认识到黑格尔国家观的缺陷:不是现代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现代政治国家。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益于他对社会现实保持着热烈而长期的关注和研究,抛弃了鲍威尔以及黑格尔只注重从精神、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政治国家问题的观点。也正是从《论犹太人问题》开始,马克思批判现代政治国家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理性精神转向了现实和物质利益关系,从政治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可见,《论犹太人的问题》中的国家观,不仅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更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一方面,马克思对现代政治国家的批判,为彻底清算和驳斥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及其整个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做了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马克思注重现实社会、物质关系的哲学方法,为后期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确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能够实现两个重大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他的新世界观、新哲学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参考文献:
[1] 张学鹏.理论逻辑与问题意识:马克思国家观革命[J].北京:哲学动态,2017(4):30-36.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张双利.马克思论宗教与现代政治[J] .上海:复旦大学学报,2016(1):54-61.
[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254.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7.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6.
OnMarx'sViewofStatein“OnJewishIssues”
ZHOU Li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On Jewish Issues” is a controversial work of Marx and Powell. In this article, Marx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Jewish problem is the one of the modern state. As for Powell’s view that he only criticized the Christian state but not the “state” itself, Marx deeply criticized the modern state. He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countries into modern ones wa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fully affirming the progress of political liberation, but also witnessed its limits. This limitation leads to the inherent defect of modern state, that is, the separation and opposition of moder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On this basis, Marx revealed that the essence of modern state was a Christian state in the true sens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modern state would inevitably become the means and tools of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would eventually replace modern state and become its purpose. Thus, Marx turned from criticizing the modern state to criticizing the civil society, which further led to the study and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task gradually became the focus of Marx’s later work after “On Jewish Issues”.
Key words:Christian country;political liberation; modern state; civil society; Jewish spirit
收稿日期:2018-12-07
修回日期:2019-0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语境中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BKS010)资助。
作者简介: 周 莉(1977— ),女,汉族,安徽淮北人,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371(2019)03-0001-05
[责任编辑:李玉年]
标签:国家论文; 政治论文; 马克思论文; 社会论文; 市民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