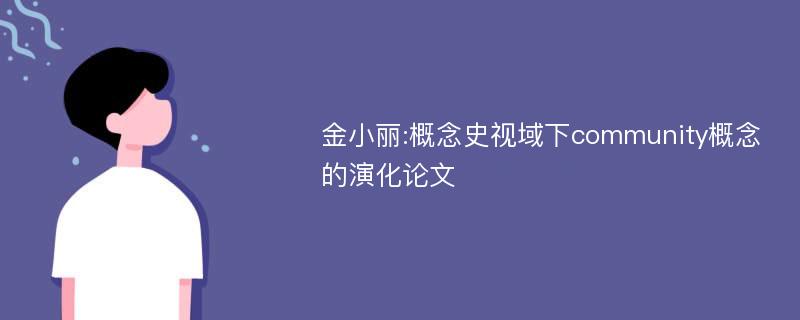
摘要:Community,汉语译为“社区”“社群”。其作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在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就引发了学者对其涵义的探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群/社区兴起,对于它们的研究也逐年增多,在满屏充斥着“社群”“社区”这样的关键词时,人们发现虽然许多学者都宣称在进行相关研究,但许多学者没有厘清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都还将社区等同于社群。文章拟结合相关文献,梳理社群与社区的历史脉络,力求可以准确、完整地阐明两者的演变与发展,为今后的社区研究和社群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概念史;community;社区;社群;演变与发展
“社群/社区”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有将近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学者对其概念的界定一直争议不断。不同学科在面对不同问题时,往往会不断翻新对“社群/社区”的认识,并对其进行再定义,因此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社群/社区”的概念千差万别。比如,学者吕燕平在《社群与族群》中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三个学科层面阐释社群的定义,认为“由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利,因此对社群的定义强调社群的政治性;社会学核心概念是组织,对社群概念侧重从社群的结构、功能考虑;人类学的角度看社群,既要体现文化性,同时应该有一个综合的观照”。[1]毋庸置疑,从学科差异性的角度出发,每一个定义都符合相关学科的特性,但学科之间又是相通的,这种对定义的过度细分与解读,是否会让研究深陷于界定定义的泥沼而导致概念的碎化呢?这恐怕是学界不希望看到的。因此,本文旨在概念史的视域下梳理community这个词语的演变,希望能为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个共同的参考。
一、概念史方法对于研究community概念的价值
大多数概念史学家认为,“概念史”一词最早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20世纪中叶,《概念史文库》的创办以及《哲学历史词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本》的出版,标志着概念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兴起。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里特尔(Joachim Ritter)、科雷塞尔(Reinhart Koselleck)和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科赛尔认为概念史专注于“重大概念”(亦即“基本概念”)之长时段的语义发展史,考察的是背后的整个历史脉络。之后,它由方维规、李宏图等学者引入中国,近年来,被较多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李宏图认为,概念史考察的是“在不同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的。同时,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被新的概念所取代”。[2]概念史关注概念的延续、革新以及再定义,同时透过概念的演变去观察历史变迁以及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周保巍学者指出,“‘概念史’强调‘概念’的历史性、偶然性和易变性,也强调歧义性、竞争性和政治性。”[2](5-8)
Community概念有其历史缘起,不同国家在引入该概念时,结合了本国国情对其进行解读,又由于概念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相关学科对其涵义进行争夺,概念的指涉范围多次发生变化。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会发现很多学者没有厘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生搬硬套,导致文章的脱节。因此,通过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梳理community概念的发展脉络,有利于为今后的社群研究与社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工业社会时期community概念的提出
1871年,英国学者梅因(H.S.Maine)在《东西方村落社区》中首次使用community一词,他将村落视为社区。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J.Tonnies)出版了一本名为《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书,其中Gemeinschaft被译为community,这里的community更偏向于“共同体”的意思。作者认为共同体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关系,代表着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成员们相互之间有共同的信念作为支撑、有默认一致的价值观,集体观念会形成约束成员行为的力量,成员统一的行为是为了显示统一体的精神和意志。他还将共同体分为三类,分别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精神共同体是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意味着心灵上的相互联系。Gesellschaft则被译为society(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像在共同体里一样,是以和平共处的方式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呈现分离的状态。在共同体里,虽然有种种分离,但成员仍然保持着结合,而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成员仍然保持着分离。并且成员的社会行为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体现出一种利己主义。[3]
从以上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滕尼斯的视野中,共同体描述了一种社会关系,人们通过相互间的来往和直接间接的结合来增加彼此的亲密感,体现了浓厚的人情味。他们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对共同体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滕尼斯对于共同体的向往与渴望,就像他在文中所称赞的“完美的共同体”。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个概念,其实是对工业社会忽视人类情感需求现象的反思与批判。
三、现代化社会建构下西方学者对community概念的重构
(一)Community概念的“空间转向”
滕尼斯(F.J.Tonnies)的书《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后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C.P.Loomis)翻译成英文,译为《Community and Society》。1915年,威斯康辛大学的学者Charles T.Galpin在《The Social Anatomy of an Agricultural Community》中通过研究农村社区,从而给其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交易中心和其周围散居的农家合成的,[4]这里的community偏向于社区的意思。之后一些文献也强调了社区的地域特征,认为community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共同生活了一群人。后来,美国芝加哥学派兴起,社区研究更是成为重点,“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区研究中,‘社区’有着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是文化生态学中,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生物群体,彼此生活在一个共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并对这一地域范围内的资源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指城市移民或贫民的社会实体,如犹太人社区或贫民社区。”[5]第一方面直接凸显地域特性,第二方面,其实说的是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这些群体受到排挤,移民或贫民被迫在仅有的几片区域互动,与同类型的人产生联系,于是城市就分化为一个个小社区,这些社区会带有当地居民的特性。正如帕克所说,“原来只不过是几何图形式的平面划分形式,现在转化为社区,即是说,转化为有自身情感、传统,有自身历史的小地区。”[6]由此可见两种表述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空间场域的色彩,这与滕尼斯(F.J.Tonnies)提出的community已有了出入。
原因可能在于community从欧洲传入美国需要,适应美国的社会土壤。美国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移民大量涌入城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得以解决,而以地域划分的社区给肤色、种族、价值观不同的国民提供一个“归属地”,让他们得以栖居,从而为他们的身心提供了归所。
(二)Community概念的“脱域”
中国人对于土地有一种很深的依恋感,“落叶归根”“安土重迁”都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居住的那块区域的珍视。而中国社区研究最早的研究对象“乡村中国”,正是牢牢依附在地域上的共同体。
本研究通过2‐DG联合Met作用于人肝癌HepG2细胞,考察二者的协同抗肿瘤作用,同时对AMPK及mTOR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2‐DG联合Met可以降低细胞线粒体膜电位,增加细胞内活性氧的产生,诱导细胞发生凋亡,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说明在HepG2细胞中,针对肿瘤细胞的能量代谢特点,利用糖酵解过程中己糖激酶的竞争性抑制剂2‐DG抑制肿瘤细胞过度依赖的糖酵解的产能方式,同时联合氧化磷酸化过程中复合体I的抑制剂Met防止氧化磷酸化的产能方式重启,具有可行性。
Fischer以及前人的观点使得Wellman意识到重新修正社区的定义已迫在眉睫,于是他整理了当时学界对于社区关系的三种看法。
19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Park)来华讲学,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吴文藻先生及他的学生费孝通等人把community译为社区。可以说中国的“社区”概念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的烙印,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学者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社会学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括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12]而这种对于社区概念的实体性以及空间性的强调,一直延续至今,从各种社会学教材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到(见下表)。
1.社区消亡论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家国同构”,家庭、家族、国家之间有共同性,即以宗法关系来统领,家族成员对于“抽象缥缈”的国家的认同主要是通过对家族的认同来实现,家族作为中介。近代之后,作为中介的家族消失。新中国成立以后,单位取代了原先家族的位置。在农村,曾经的单位就是人民公社,由它维系着国家与家庭,在城市,单位则是政治性机关、经济型企业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制”开始松动,而为了安置那些原本为单位效力的员工,社区应运而生,这时“单位人”就变成了“社会人”。而且,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语境下,社区包含着“法定社区”,而不仅仅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国家其实也非常重视对社区的建设管理,希望通过社区来推进基层民主的建设。
有机肥施用对玉米生长发育及水分利用的影响………… 刁生鹏,高 宇,张 雄,任永峰,赵沛义,贾有余,聂 晶,骆 洪(58)
社区消亡论在北美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区研究及大众社会研究中都占据重要的位置。Wellman认为这个理论预设了只有在紧密联系的有边界的社区,亲密的初级关系才有可能自然出现,却忽略了如何去建构这种初级关系的问题。由此,他认为,有可能这种初级关系只是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并没有在城市中消亡。
2.社区继存论
从静态看盘去分析个股有没机构活动?或有没新资金进怎么看。1、看多日K线看量能变化;2、看分时走势表现;3、看盘中成交明细;4、多日分时走势连贯分析。
很多城市社会学者在社区消亡论提出后倍感失落,作为对消亡论的回应,他们在之后的30年间,一直强调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下,社区也仍然存在并繁荣地发展着。从经验层面来看,社区仍持续为人们提供着社交的机会,拥有非正式控制的权利。从理论上来讲,人类在本质上是合群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组建社区。
要想有效的解决评审人员职责不明确的问题,可以指定标准化的制度,将各个参与对象的工作职责明确的进行标注,具体如下:
由此可见,在国外,community的概念从共同体到社区,再延伸到既包含社区又包含社群,学者是立足于时代背景在不断修正概念中不合理的限定性因素,力求可以比较完整、准确地界定community。正如学者高鉴国所说,目前学术界定义社区的通常做法是使用最简要的语言,描述其最主要的特征,避免将某些排他性要素(如地域)置于定义之中。[10]如塞文·布林特(S.Brint)提出,应当从最普遍意义上提出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一个“一般概念”:社区是“具有共同活动和(或)信念的,主要由情感、忠诚、共同价值和(或)个人感情(如相互性格和生活事件中的兴趣)关系相联接的一群人”。[11]这个定义没有把地域作为限定性因素,仅包含了人际互动与情感联系等最基本的要素。
3.社区解放论
如表1中依次给出了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和循环结构的控制流程图和控制依赖图的结构。为了方便表示,可以对程序的节点用0到n的自然数表示。其中程序的入口节点记作0节点,依次标号。
社区解放论肯定了初级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但认为这种联系其实已经不完全存在于有边界的社区了。由于居住地、工作场所的分散以及与亲人的分离导致多种社会网络凝聚力的减弱,而廉价高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降低了空间距离的社会成本,使人们很容易维持分散的初级关系,城市的规模、人口密度、多样性以及遍布的互动设施,为人们形成多元松散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这个理论放弃了把物理空间作为分析社区问题的起点,而是直接去探寻初级社会关系的结构。[9]
社区解放论把社区从地域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地缘关系去研究社区。这是对社区概念的一次重新再定义,即社区不再仅仅是在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更是突破了地理限制,有着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追求的一群人。
2.历史层面
Wellman认为,虽然继存论从两方面驳斥了消亡论,但它不幸地回避了消亡论最重要的观点——现代劳动分工可能会对初级关系产生强烈的影响。继存论的学者一直在探讨的是邻里关系、亲属关系是否存在,外部的亲密关系是否可以从有边界的社区辐射到更宽广的范围,却没有分析团结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位置。
四、中国学者对community概念的本土化解读
(一)中国语境下的社区
本文研究成果可为协同产品创新的成员管理及知识管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可为CPIKN稳定性监控及预警系统的开发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与方法参考。然而,本文主要研究了CPIKN内部关联关系为对等互惠关系的情况,即没有考虑网络节点间关联关系的有向性,因此,非对等互惠关系下的CPIKN稳定性问题将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另一方面,本文研究中尚有一些因素没有涉及,如协同产品创新知识的特性(隐性化特征、复杂性等)、协同成员及创新知识的增加与更新等问题在文中均未深入探讨,这些都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探究的重要方向。
如何看待曾树生离开家庭去兰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如何评价曾树生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当战争逼近曾树生所生活的城市时,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的氛围。
不同社会学教材对“社区”概念的界定
书 名社 区 定 义《社会学概论新修》郑杭生主编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社会学导论》风笑天主编社区是由若干个社会群体在一特定区域内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社会学教程》王思斌主编社区是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
Community表达本土化的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1.学术层面
首先,作为中国社区概念的引入者,吴文藻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认为滕尼斯在使用社区概念时,虽没有提及地域特征,但他将社区概念降至社会之下,已具有地域性意义。[13]为了使中国学者信服,他有意识地引进了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观点,“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有两个特点:一、功能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在理论上的关系最为密切;二、功能观点与社区观点在实地研究的方法上完全相同。”[14]确实,该学派的奠基人马林诺斯基认为,只有在一个边界清晰、自成一体的社会单位里,才可以研究整个文化中各个要素的功能。20世纪60至70年代,国外学者正在进行“社区消亡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的讨论,他们针对当时主导的community的概念进行探讨、修正,而那时中国正处在一段较为停滞、封闭的时期。1950年6月8日,在第一次中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的专家提出了“苏联模式”,极大地贬低了文科的价值。之后,中国开始进行院系调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许多文科专业被直接砍掉。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科才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研究被长期搁置,因此中国学界并没有参与那次讨论。
(2) 将从GIS中导出的预处理后的模型数据导入HEC-RAS软件,以实现河网的几何属性编辑。这些属性主要包括:河网形状、河流走向、河道断面、研究区曼宁系数。根据需要,还可以添加水工建筑物,例如堤防、水坝、桥梁、堰、孔口等。
从上文可以看出,美国学者的社区研究是把社区作为一个地域实体,而滕尼斯的设想其实没有框定区域与形态,因此学者们也开始反思是否可以把地域作为排他性要素置于定义中。学者Colin Bell 和Howard Newby认为社区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即使是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也仍然是一个不太明晰但暗含价值,需要持续研究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很多研究涉及特定的地理位置或是社会区域,好处显而易见,就是有一个实体的研究对象,确保研究的可行性,但是这样的研究也会遗漏很多东西。[7]Fischer则指出社会学关注的是在某一个地点、位置、栖息地、领地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总体来说是关注人的“聚落形态”,以及这种“聚落形态”如何决定社区和个人的特性,城市社区的研究也不例外。但他不是很赞同这样的研究,因为他认为“地理位置”并不是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虽然它的变化展现了社会变迁,对于某些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它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并不重要,因为社会生活是在微观的个人领域中进行的。并且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局限于邻近的地域。由此,他提出应该以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来定义社区,而不是通过地域范围来界定。[8]
2.2.2 8%炔草酯对小麦的安全性评价 施药后观察各处理的小麦叶色、株高与空白对照一样,未发现畸形、黄化、死苗等药害症状。收获时测产,各药剂处理下小麦产量分别为7 218.7,7 267.8,7 488.2,7 504.3 kg/hm2,各处理与空白对照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增产率分别是5.3%,6.1%,9.3%,9.5%(表7)。
3.地理层面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分布在国内的不同角落,形成不同的区块,随着人们的交往互动和历史变迁,各个区域产生了各具自身特色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多元化,要求划分区域以窥全貌。正如学者丁元竹所说,“要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分区域进行社区研究,以社区研究来把握各区域中的社区类型,是全面真实地把握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15]
4.政治层面
社区消亡的论断其实是城市社会学理论对滕尼斯理论的首次回应,而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困扰着许多人。社区消亡论认为劳动的分工削弱了社区的凝聚力,城市化导致社区的解体与个人的异化,初级的社会关系变得“疏远、短暂、割裂”。市民们不再充分融入单个紧密的社区,而是成为多元的社会网络的成员,稀疏地分布、松散地联结。
北美刺龙葵结实量巨大,每株每年可产生 1 500~7 200粒种子,种子可随风力、水流、动物、交通工具等途径进行自然和人为因素主导的扩散蔓延[10,12],种子扩散到新地区后,其休眠特性(休眠期可达10年)能极大地提高其定殖能力[13]。
(二)中国语境下的社群
community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出现了断裂,分裂为社区与社群两个概念。从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社群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而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关于社区的概念,笔者在上文详细地阐述过,接下来笔者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以“社群”为关键词,搜索探讨社群概念的论文,通过分析这些论文来观察社群概念是否也经过了本土化的再创造。
学者李万全在《社群的概念—滕尼斯与贝尔之比较》一文中,首先展现了滕尼斯与丹尼尔.A.贝尔对于社群的界定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再从历史背景、理论的建构方法两个角度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16]
学者廖杨在《民族·族群·社群·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关联分析》中认为,社群概念起源于政治哲学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所提到的“城邦”。之后,他又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出发列举了社群主义者迈克尔·桑德尔、戴维·米勒对于社群概念的界定,最后归纳了社群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享有完整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分享利益而组合的;二是社群的参与者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三是社群是其成员自我认同的核心,社群的关系、义务、习俗、规范和传统对成员有着决定的意义。实际上,社群主义者心目中的社群,即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了达到最大和最高的善而组成的人类团体或人类关系。[17]
学者吴玉军在《现代社会观的批判和重建—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社群”观念的一种考察》中梳理了自古希腊以来众多思想家对于社群涵义所做的不同界定。思想家有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滕尼斯、桑德尔、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通过对社群主义社群观的分析,作者认为社群观展现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的社会观或国家观。社群主义者将社群看作构成性的存在,有利于人们建立稳固的关系、增进归属感。[18]
(三)中国语境下社区与社群的分野
通过对以上三篇论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大多是从社群主义的视角出发,按照时间轴去展示不同西方学者对于社群的界定,并没有对国外的概念进行补充或者修正。由此可见,西方的community在指代社群意义时与中国语境下的社群概念是一致的,但中国语境下的社区与社群概念存在着明显差异。
首先,中国的社区强调了物理空间上的接近和联系,是在特定区域里的生活共同体,是一群人的集合,甚至还是个有形的实体。而社群没有场域的限制,它的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因为无论是滕尼斯还是丹尼尔.A.贝尔对社群的归类都包含了地缘社群。
其次,政治行政力量进入了中国社区,使得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比如社区居委会、社区管理,而社群会以情感联系取代强制话语的表达,有意识地隐匿权力的分配和管理阶层。
最后,社区是作为一种弱联系的存在,它强调社区成员的参与感,成员们仅仅只是进入这个社区,维持基本的社会互动,不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但社群就不一样,在成员眼中,个人要退居于社群之后,每个成员都愿意忠于自己的社群并顺从共同的利益。在社群中,人与人是强联系的存在,它是可以给成员提供情感支持的。
五、网络时代下传统社群向网络社群/社区的延伸
随着网络的崛起,网络社群/社区开始出现。研究发现,尽管在中国语境下,学者们会去区分社区与社群,却并没有特地去区分网络社群与网络社区。在笔者看来,由于“脱域机制”的存在以及政治力量相对较少的介入,两者其实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多措并举 创新土地集约利用(黄小珊) ........................................................................................................ 6-50
网络社群(Internet Community),又称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或在线社群(Online Community)。首次提出网络社群定义的是Howard Rheingold,他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虚拟社群:电子疆域的家园》(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an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中写到,“虚拟社群是基于网络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体,一定数量的人们怀揣着充沛的感情在这个平台上进行长时间、充分的公开讨论,从而建立起网络空间中的人际关系。”[19]Schubert在论文中从社交驱动的角度来看待虚拟社群,他把虚拟社群定义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个人或组织共享语义空间,并利用电子媒介进行经常性交流,从而形成的集合体”。[20]
网络社群之所以产生,在归功于互联网技术的同时,也离不开传统社群的衰落。传统社群由于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得人们很难与距离遥远的人产生紧密的联系,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更是让人们尝遍了世间的冷漠与无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渴望在超越现实联系的基础上可以建构一个虚拟空间,缓解紧张感。正如涂尔干所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个公社或省份,但连结我们的纽带却一天天地变得脆弱松弛了。这种地理上的划分纯粹是人为的,根本无法唤起我们内心中的深厚感情,那种所谓的地方精神也已经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我们已经不再关心和纠缠于本地和本省的事情,除非这些事情与我们的职业有关。我们的行动已经远远超过了群体范围,我们对群体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也反应冷淡,一切都因为群体的范围太狭窄了。”[21]
正好网络社群出现了,网络是没有边界的,人们的交往不再受时空限制。网络的匿名性一方面隐藏了现实生活中明显的等级秩序,使得人们在网络社群中享受相对纯粹的平等;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摆脱现实的枷锁、还原本真的自我提供了机会,他们得以建构自我认同。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界定认同时说,“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我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的。”[22]网络的流动性也给人们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可以根据兴趣进入不同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游走,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抽离,而在所属的网络社群中,则寄托了自己更多的私人情感,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传统社群由于人们大多是面对面的交流,无形中就会给想要离群的成员以压力。网络社群同样还保留着传统社群的一些传统,比如网络社群也有为了增加社群凝聚力所举办的线上活动,有群体的规则限制,还是有权力的分层,但它可能是把情感的联结发挥到了极致,回归到了精神共同体的范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社群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对于传统社群的情感上的回归呢?
参考文献:
[1]吕燕平.社群与族群[A].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贵州民族学院.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人类学高级论坛2008卷[C].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008:34.
[2]李宏图,周保巍,孙云龙,张智,谈丽.概念史笔谈[J].史学理论研究,2012(1):4-21.
[3][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96.
[4]C.J.Galpin.The social anatomy of an agricultural community.Madison,Wis.: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15):34.
[5]陈美萍.共同体(Community):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6][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
[7]Colin Bell,Howard Newby.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Frank Cass,London,1974:355.
[8]Fischer,Claude S.The Study of Urban Community and Personalit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75:67-89.
[9]Barry Wellman.The Community Question: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9:1201-1231.
[10]高鉴国.社区的理论概念与研究视角[J].学习与实践,2006(10).
[11]Brint.S.Gemeinschaft revisited: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Socio-logical Theory,2001:8.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94.
[13]胡鸿保,姜振华.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J].学术论坛,2002(5).
[14]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122.
[15]丁元竹,江汛清.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区”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1991(3).
[16]李万全.社群的概念——滕尼斯与贝尔之比较[J].社会科学论坛,2006(6).
[17]廖杨.民族·族群·社群·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关联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8(2).
[18]吴玉军.现代社会观的批判和重建——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社群”观念的一种考察[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9]Rheingold H.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IT press,1993.
[20]Schubert and Ginsburg.Virtual communities of transaction:The role of personalization in electronic commerce .Electronic markets, 2000,10(1).
[21][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40.
[22][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0.
作者简介:金小丽,女,硕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9)01-0102-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研究”(16BXW04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高辛凡]
标签:社群论文; 社区论文; 概念论文; 共同体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研究"; (16BXW042)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