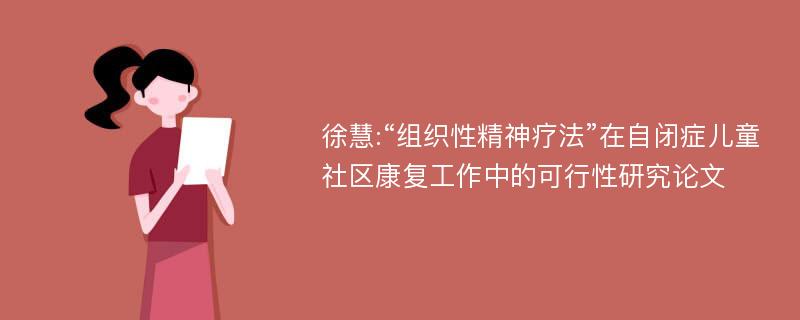
【摘要】针对我国目前自闭症患儿及其家庭因各种原因在社区往往处于孤立封闭状态的现状,我们参考“组织性精神疗法”在法国儿童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工作中的应用,先后在广州市两个不同社区组建了“亲子空间”,融合接待包括自闭症在内的学龄前儿童及其家庭。本文从“亲子空间”近一年的实践经历出发,探讨“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工作设置及原理,并考察该疗法在我国自闭症儿童社区康复工作中的可行性,进行实践研究。
【关键字】组织性精神疗法;儿童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学龄前自闭症患儿
“组织性精神疗法”是指“利用社群生活来帮助精神障碍患者重建社会关系,并重新找到与现实富有活力的接触方式”的一种临床治疗思想及技术。该疗法发端于二战期间法国圣-阿尔拜(Saint-Alban)精神病院,于20世纪60年代促成法国实现了“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并随之被广泛应用于精神病院及社区精神康复服务机构,如白日医院、社区医学心理中心(CMP)、治疗性工作坊等[1]。通常来说,在社区运用“组织性精神疗法”接待精神障碍患儿的康复机构包括政府设置于每个社区医学心理中心,非全日制治疗活动中心(CATTP),以及受某些市政府及福利组织资助的“孩子与父母接待中心”“绿房子”项目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法国以“组织性精神疗法”为基础而开展的儿童精神障碍的社区康复及教育工作都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此外,由于本文作者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在两家“孩子与父母接待中心”实习工作过三年,较为熟悉“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具体执行原理及干预技巧,为我们参考该疗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开展精神障碍患儿的教育及康复工作提供了可在实践层面探索的可能性。
1.研究背景及方案
1.1 研究背景
自2017年6月开始,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曾先后在广州市两个不同社区(L社区和C社区)开展了长达一年的社区营造工作。最初,当我们在L社区筹划社区营造的工作内容时,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该社区有一家自闭症儿童公益机构经常组织一些群体内的活动,但很少与外部有交流接触。
事实上,此地的现状并非个案,李乐乐等人在《中国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一文中已指出,当前很多自闭症患儿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不一样,更愿意让自闭症孩子留在特殊学校或康复机构”,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对“融合教育有一定的了解, 明白融合教育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缓解交流和沟通障碍,促进自闭症儿童社会化的发展”[2],因此会为孩子积极争取融合教育的资源或创建条件促成融合教育。目前,我国开展融合教育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幼儿园及小学这类教育机构。
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将眼光拓展到社区,认为在自闭症患儿及其家庭居住生活的社区拓展融合教育及康复服务可以有效改善现有工作的不足,这样既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参与患儿的教育及康复工作,同时又能帮助患儿重返社会,获得较好的康复效果[3]。然而,较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以自闭症为代表的患儿的社区康复及教育工作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倡导阶段,鲜有基于实践探索的研究报道。因此,有关该项工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用以参考的执行方案、干预理论及方法、组织管理原则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及探讨。
建议对外观异常的膀胱黏膜进行选择性活检。当尿细胞学检查阳性,或存在高风险外生性(非乳头状)肿瘤时,建议对外观正常的膀胱黏膜进行随机多点活检,活检部位包括膀胱三角区、膀胱顶以及膀胱各壁。若条件允许,建议在荧光膀胱镜或NBI引导下完成多点活检。
因此,为满足L社区里现有的自闭症患儿及其家庭的潜在需求,我们参考“组织性精神疗法”的理论及技术要求,并结合L社区及我们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研究条件,在该地组建“亲子空间”,融合接待包括自闭症小孩在内的学龄前儿童及其家庭。半年后,来访者越来越多,为寻求更大的接待空间,我们于2018年3月搬迁到了C社区。
1.2 “亲子空间”接待概况及研究方案
“在照料病人之前,应先照料医院”,这是“组织性精神疗法”最具标志性的言论主张。该疗法早期的开拓者及实践者,如托斯盖尔(François Tosquelles)、让·欧利(Jean Oury)等,均认为“在机构本身有病的情况下来治疗住院病人是可笑的”。这些论断看似夸张,但并非哗众取宠的浮夸之词,事实上,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改革派精神病科医生面对精神病人在传统精神卫生制度下只能陷入被隔离、被监禁、被遗弃的残酷现实时,运用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等对传统医疗机构进行剖析并试图对其改造的结论及主张。
不过,受租用场地面积的限制,在L社区,我们每次只能接待10名左右的儿童,而在C社区的“亲子空间”里,我们则可接待25—30名儿童。此外,由于L社区是两家自闭症儿童公益机构的驻地,因此,自闭症患儿在该地“亲子空间”的融合比例要高于C社区,约为20%—30%,而后者则为15%—20%左右。至2018年底,我们在L及C社区共开展了四十多次活动,接待了近两千人次的孩童及其父母。为较为客观地检验“亲子空间”的工作成效,验证“组织性精神疗法”对于我国城市社区自闭症患儿康复工作的效用,我们在搬到C小区之后,运用《0—6岁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评估量表》[4]对前来参与“亲子空间”活动的自闭症及疑似自闭症患儿进行跟踪记录,分别在他们到访的初期、2—3个月之后的中期及活动末期做评估。
第一,正如上文3.1部分所折射的,在组建团队、挑选工作人员时,看重候选人作为个体而非作为机构性功能角色而表达出来的对亲子话题的兴趣。这也是“组织性精神疗法”要求工作人员具有的东西,即“具有个体独特性的主体性、积极性及创意,并非是听从他人指派或参与审核过的‘治疗计划’而表现出来的所谓的主动性[13]”,因为“这是一条较为容易激发工作人员治疗潜能的通道”[12]。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管理者Y能够在监督管理“亲子空间”运营的同时,又能对其给予适当的人文关怀。
在本文中,我们将在追溯总结“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内涵及其应用的基础上,结合“亲子空间”的实践经历探讨“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工作设置及逻辑,借助量表统计结果分析总结该疗法对于我国城市自闭症儿童社区康复工作的效用及相应的实施条件。希望通过这项探索性研究抛砖引玉,为我国儿童精神障碍社区教育及康复工作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参考及思路。
2.“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内涵及其应用
2.1 “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内涵
无论是在L社区,还是在C社区,我们均参照“组织性精神疗法”在法国“孩子与父母接待中心”的工作模式,通过组建“亲子空间”接待6岁以下由成年人陪同的孩子,其中包括自闭症在内的有心理及行为障碍的儿童及其家庭。接待频次为一周一次,时间均为每周六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倡导者们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实则遭受着社会及病理的双重异化。前者是因传统的医疗机构继承了资本主义工厂管理机制而导致的,因为在一个“分工、专业化、对工作人员去技能化、权力集中、监控措施完备[5]的机构里,医生与病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交流,治疗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还应包括对机构组织的改造。至于后者,借助精神分析,改革派精神病科医生们赞同主体是通过在社会中的异化而自我构建的,因此精神病实则“是一种防御机制”,因为病人懂得“词语意味着事物的缺席,而缺席是令人痛苦的。他放弃了词语所运载的意义……以抗议立即摧毁的感觉”[5]。
作为一项既参照了国外理论技术又涉及公共服务的在地项目,“亲子空间”的组织管理似乎最初便暗含着技术目标与行政管理之间的潜在矛盾。但“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先行者托斯盖尔曾通过对“组织”及“机构”的区分强调“‘机构’是国家为了解决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创建的……但这不应意味‘机构’仅仅只需要完成这些任务;而‘组织’是职业团队依照他们所处的环境入住机构的方式……团队可以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及需求自由地部署,以提供最为合适的服务[12]”。这成为我们对“亲子空间”的工作进行组织管理及架构的参照。
采空区垂直投影的平面范围界线根据调查资料、物探解译资料与验证资料综合分析适当外推,圈定采空区垂直投影总面积约4341m2,采空区容积约19793m3,见图2。
2.2 “组织性精神疗法”在法国儿童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中的应用
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及的那样,“组织性精神疗法”自20世纪60年代便被法国政府以法令的形式推广应用于精神病院及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中。但该疗法以预防及社会化的目的被应用于法国儿童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中则是1979年精神分析家多尔多女士(Françoise Dolto)创建“绿房子(Maison Verte)”之后。
基于多年的临床经验,多尔多及其同行好友发现“等到孩子的诊断结论下来再做干预是不明智的。很多时候,当躯体或性格障碍已经出现,或学业困难不断加重的时候(再做干预),其实往往已经有点迟了……最珍贵的时机已经错失。较好的做法是当早期的嫉妒开始激烈表达、孩子为早期的分离而焦虑时便进行干预”[9]。同时,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儿童及家庭在社会变迁中所遭受的冲击,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家庭分散、住所变小、亲人之间的分离、离婚等原因,家庭链接已被打散,在个体之间创建其他的链接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同时,也应该促进孩子自主性的发展、帮助他们融入社区但又无须与其父母、亲人分离开来。”[10]因此,在“预防”及“为幼龄儿童提供社会化场所”的现实需求中,“绿房子”应运而生,仅接待4岁以下由成年人陪同的幼童。
关于“绿房子”与“组织性精神疗法”的渊源,欧乐嘎(Olga)博士曾明确指出: 由于“绿房子”小组成员的“职业背景及经历为他们带来了被时代所标记的关于‘组织’的思考”,“绿房子”的工作也因此“构建了一些方法,它们既对离心及同质倾向进行分析,又能对解决方案中关于僵化处理的活动进行思考”[10],而这正是“组织性精神疗法”所要抵达的目的。
受“绿房子”所获得的成功及所传递的人文关怀的影响,在社区开展精神卫生预防及康复工作的公共卫生机构(如精神病院设置于社区的医学心理中心、妇幼保健站等)便纷纷仿效“绿房子”的做法,接待4岁或6岁以下由成年人陪同的学龄前儿童,其目的在于促进亲子之间的关系连接,预防儿童早期关系障碍,并为其提供社会化场所。截至2011年,法国已建立了1192个“孩子与父母接待中心”,但这离法国政府的目标——每4000个6岁以下的孩子可拥有一个“孩子与父母接待中心”——还有一些距离,因此该类中心近年来也一直呈增长趋势[11]。
单一的相似度评价难以全面地反映不同产地橘叶药材的差异性,指纹图谱和化学计量学的结合可以整体地评价各个产地橘叶的质量。目前,化学计量学在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中应用广泛,主要利用其信息化技术将指纹图谱丰富的信息量进行降维,以低维变量代替原始高维变量,建立分类模型,从而有效评价指纹图谱中各信息的贡献影响力[11]。本研究采用IBM SPSS 22.0软件和SIMCA 13.0软件对不同批次橘叶药材的指纹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3.“组织性精神疗法”在“亲子空间”中的应用
总之,以“亲子空间”为载体,通过以上工作设置,我们实验性地将“组织性精神疗法”应用在自闭症儿童的社区融合教育及康复工作中。
3.1 与上级管理部门的关系
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组织性精神疗法”主张应通过一系列举措或设置来挫败传统医疗机构对治疗者及病人的结构性异化作用,将其改造成“心理(精神)病理痛楚接待中心”。同时,该疗法吸收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技术来开展具体的临床接待工作,强调“仔细倾听精神病人所说话语的重要性,尽管这些话里有一些谵妄,但并非没有意义[6]”,主张“应该允许病人‘表达冲突’,并给予‘涵盖认同及移情的时刻’”[7]。此外,托斯盖尔、让·欧利等人对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拓展,证明精神病人的“移情”具有“分裂性”特征,即“一个经历分裂感的精神病人不能将他的移情投注到单独的某个精神分析师身上……对于他来说,与机构里的不同人物建立多角度的移情更为容易,而这些人包括精神病科医生、咨询师、护士,以及其他病人等”[8],这些认识及主张为“组织性精神疗法”的一些具体措施及设置提供了理论基础及临床依据。
2.加强管理者法律责任意识,切实发挥防控制度体系的有效性。管理者在油田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中处于主导者的地位,对于法律风险防控制度体系建设及其有效性的发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加强管理者的法律责任意识,强化管理者在应对突发性法律风险时运用法律手段、依托防控制度体系加以解决的法律思维模式,达到切实发挥防控制度体系有效性的目的。
事实证明,Y带着个人兴趣对我们工作的监督管理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开了一些可能促成官僚化管理的要素,并为“亲子空间”的工作增添了不少人性化素材。在整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除去例行的检查管理外,Y偶尔也会带孩子参与“亲子空间”的活动,并会以家长的身份给我们一些建议,譬如建议我们设置路标、分享新的游戏等。
对宗教界的教徒群众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通过广泛的、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教育,“发动了群众,打击了敌人,团结与争取了绝大多数教徒群众,巩固与扩大了爱国势力,打击与孤立了敌对势力”。如在对天主教界教徒群众进行的“反帝爱国”教育过程中,贯彻了“团结、教育、争取”虔诚教徒的方针,最大范围地发动了教徒群众。广大天主教教徒群众普遍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解除了思想顾虑,进一步了解、信任了国家的宗教政策,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这在事实上巩固、扩大了天主教内的反帝爱国势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了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3.2 团队工作组织架构
为了践行“组织性精神疗法”,还需要在机构内部做一些必要的组织架构,以消除传统机构中常见的金字塔等级结构,避免机构异化。治疗性俱乐部、“工作坊”等都是一些常用的让机构承载治疗功能的工具。
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二十一日,又有逃向库尔喀喇乌苏西湖一带的200余名回民中的数十骑逃向塔尔巴哈台,[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中华书局,1996年,第367页。这将是在塔尔巴哈台活动的最后一批回民。锡纶派兵驻扎博罗塔拉,扼防塔尔巴哈台西南边境,同时,兼护伊犁所属察哈尔游牧,以期有备无患。[注]《清德宗实录》卷221,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戊辰条。十二月,塔尔巴哈台境内“贼匪擒斩殆尽”。[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中华书局,1996年,第287页。
首先,就“工作坊”来说,其功能在于通过促进个体关系的建立与交流而让机构摆脱异化。在“亲子空间”,我们以玩具、绘本、游戏等为媒介构建了一些小型的工作坊。然后参照儿童年龄,以互不妨碍,又不相互隔离为原则将它们安放在空间的不同角落,形成差异化分区布置。譬如,在不到一周岁的幼龄儿童区,放上爬行垫、小的布绒玩具;在其旁边,放上沙发或椅子以方便父母们在照看孩子的同时能一起交流和讨论。这些以玩具、书籍、绘画或游戏等为媒介的不同场景为个体的相遇提供了可能性要素或条件。
可以说,小虫的这次行动计划非常缜密。在姑妈进了水池后,玉敏迅速给小虫发了信息,告诉他钻戒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小虫早就到了姑妈家的小区,候在大门外。接到了信息,小虫才进去。小虫知道姑父肯定不在家,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编好借口,然后才上了电梯。敲了半天的门,确认姑父家里没人了,小虫又向对门看了看,然后开门进去了。进了屋,小虫叫了声姑父,无人回应。小虫直接进了卧室,小心地取出钻戒,放在兜里。出门时见对门的门仍关着,小虫放心地进了电梯,下了楼,骑上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走了。
其次,“组织性精神疗法”认为相异性在有效的组织下既能促进创意,也能让团队工作更为完备,因此它倡导组建具有多学科专业背景的工作团队。参照这一主张,最终组建了一支具有心理咨询、精神分析、社会工作、艺术等专业背景的工作团队。
3.3 工作原则及技术要求
为了让组织管理层面的设置具有治疗的功能,工作人员及团队需遵循“组织性精神疗法”所倡导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及技术要求。这些旨在尊重个体主体性的工作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各层次、各专业的职业教育均是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并按照核心岗位的需求来构建课程体系,[2]这就要求中高职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统筹专业课程。但当前中高职衔接过程中关于课程设置的问题较为突出。文化课方面,中职坚持“简单、够用”,高职则强调“深度、广度”。因此,中职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学习文化课普遍感到吃力,尤其在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方面的能力较差,较难完成专业培养目标要求。②专业课程方面。中高职在专业课程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课程重复现象严重、课程先后顺序不合理、课程内容层次不分明。
第二,在以“工作坊”为媒介而开展的接待工作中,为了促成个体关系的建立和交流,还需要引入“流动自由”的原则:所有来到“亲子空间”的人,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来访者,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活动内容及场地,且在整个活动期间,所有的人都能在不同的场景中穿梭流动。如此设置是因为“组织性精神疗法”强调“真正的相遇发生于偶然之中,不能对相遇做一些规划或预计”[13]。因此,“流动的自由”本质上所涉及的是关于内在的“主体性自由”。
那么,对于还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自闭症患儿来说,他们的主体性又如何得到尊重?通常来说,这需要工作人员的仔细观察、与父母等抚育者的交流来了解孩子通过行为、情绪等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交流兴趣及需要,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给予相应且合适的回应。譬如,一位叫H的自闭症患儿曾长期参与Y村“亲子空间”的活动,但他在此地却只喜欢做两件事情,一是躲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画画,二是蜷缩在大厅的沙发上用布将自己裹起来。在他的“小画室”里,他拒绝工作人员的介入,但却能接受与一个叫T的同龄男孩共享空间。只有当他躺在沙发上时,才乐意让工作人员用布套将其裹起来并玩“躲猫猫”的游戏。依照H通过行为传递的交流兴趣及对空间距离的要求,我们都给予尊重并相应地做出合适的回应。
第三,“组织性精神疗法”显然是一种有赖于集体协作的干预方法,而参与的各方既包括团队内部成员,也涉及机构外的其他组织,甚至包括通常被看作被照料者的来访者们。为了让协作成为可能,该疗法认为工作人员需要放弃一些偏见。这些偏见一方面包括某些想象性竞争、对个人仪表和机构赋予的职业形象的想象等,同时还包含对来访者的一些偏见,譬如将病人或来访者看作被照料对象,但却忘了他们也可以照料别人。对于前者,“组织性精神疗法”认为“放下自己的身份架子是治疗者能力的一部分,因为通过这种放弃,治疗者的某些偏见才能得以停止,这是能够接纳新事物,保证现场积极工作的一项必要条件”[15];而后者则是源于“照料者与被照料者”的角色划分而促成的偏见,因此该疗法主张通过让来访者承担责任而尊重每个人的能力。
3.4 团队建设及督导
正如前文2.1介绍的那样,受精神分析的影响,“组织性精神疗法”将临床工作中发生在精神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的移情拓展为治疗机构与病人之间的“聚合性移情”,并运用“工作坊”“治疗性俱乐部”等工具“编织交互性关系以创建一种生活氛围……让社会的、有意义的场域以及补充性关系等都能出现,从而能够构建多重焦点的移情场域”[16]。但在构建移情场域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在“(与)病人或来访者的接触将使治疗者浸润在与对方的移情中,并成为前者心理痛楚的支撑者:(扮演着)信号的功能……而这个过程和工作对于治疗者心理并非没有影响[14]”。为了避免或降低被托斯盖尔称为“机构性反移情”的东西给治疗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组织具有治疗性功能的聚合性小组会议。
纵观3个学段,6个版本教材中都出现了“平行四边形的概念”知识点.在第二和第三学段,除北师版外,其它5个版本均出现了“性质1(对边相等)”知识点;冀教版和青岛版都出现了“性质2(对角相等)”知识点.“高”“底”和“性质5(是中心对称图形)”等知识点与相关知识点组合情况在不同版本有较大差异.
而话语及交流的自由是让会议具有治疗功能的条件,这意味着在这类会议中,应侧重强调工作人员与来访者之间的治疗关系、他们作为主体的相互交流,并警惕机构所赋予的身份地位、职业形象带给治疗关系的损害,需要注意“裁定话语价值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贴切,而非说话者的等级地位[17]”。同时,引入精神分析的视角也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帮助工作人员树立尊重他者话语的意识,构造一个接纳主体的空间,让小组会议成为机构的分析工具。正如菲德尔(François Feder)所认为的,精神分析在聚合性集体会议中的作用在于通过团队分享建立二次性转化的工作框架,从而构建“一个让小组非常满意的交流空间,在这样一个相互认同的地方,工作人员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既被重视,也有价值[18]”。
“亲子空间”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会举办一个持续30分钟左右的小组会议,谈论在接待工作中的情感体验,包括那些让自己觉得为难、尴尬或愤怒的事件。在分享的过程中,参照罗杰·米塞斯的建议,避免分享的材料是分散或零碎的以至于形成对来访者的碎片化认识,而是注意分享内容的连贯性、一致性及严密性,以便让每个工作人员都能通过会议对孩子及其家庭形成整体的认识,从而保证工作的延续性[18]。
所以,我们首先向相关部门及组织承诺满足他们的管理要求及条件,但同时建议管理方安排一位对亲子关系感兴趣的工作人员监督管理我们的工作,因为参照“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建议,对于构建人性化治疗空间的组织来说,需要机构消除金字塔等级结构并引入对主体的尊重,其中尤其应包含对工作人员作为“主体”的尊重。最终,我们迎来了管理人员Y,她除了“××主管”职位之外,还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因此较为关注亲子议题。
正如法国卫生部门所建议的,“在组织集体性会议或讨论时应安排团队支持,定期接受来自外部第三方的调整”,以“避免专业上的孤立,并让工作能够呈献给同行、负责人及督导[18]”。为此,邀请一位具有多年“组织性精神疗法”工作经验的法国精神分析家作为“亲子空间”的督导,每月开展一次视频督导会议,讨论在接待工作中遇到的疑问及困难。
依照上文所介绍的“组织性精神疗法”的内涵要求,即需要从组织管理及个体层面的接纳互动两方面着手来构建人性化治疗空间,在参考法国“孩子与父母接待中心”工作设置的基础上,我们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开展“亲子空间”的接待工作。
4.研究结果及讨论
按照前文所介绍的研究计划及方案,我们运用《0—6岁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评估量表》对参与了C社区“亲子空间”活动的自闭症患儿做了全程(项目持续总时间长度为7个月)跟踪记录,现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4.1 “亲子空间”对自闭症患儿的干预效果统计分析
在C社区的“亲子空间”里,共融合接待7名自闭症及2名疑似自闭症患儿。前者是经医生诊断的患儿,而后者还未去医院做诊断,但工作人员依据经验观察,认为孩子可能是自闭症。
统计信息表明,在接待的9名儿童中,能保持到中期及末期的持续来访率分别为44.44% 和22.22%。但在讨论患儿及其父母中断来访的原因之前,先介绍患儿们在“亲子空间”所获得的变化及进展。
通过对这9名自闭症及疑似自闭症患儿在“亲子空间”的活动做跟踪记录,得到如下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表明,尽管只有44.44%的患儿能够坚持参加活动至中后期,但几乎每位能够持续参加活动的孩子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譬如,小男孩Y、JH及EN在活动初期的得分分别为7、9、11分,但到了活动中后期,得分均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JH及EN,分别获得了29及30分。
通过量表分数的增长而呈现的进步也反映在所观察到的现象中。以JH为例,在他刚来“亲子空间”时,已经2岁半的他还不会说话,脾气也非常暴躁,在“亲子空间”横冲直撞,甚至暴力攻击8个月大的婴儿。但持续参加几个月的活动后,JH变得不再那么暴力,甚至能加入其他小朋友的游戏中。当为期近7个月的活动快结束时,JH已经开始非常积极地用语言表达,他母亲说“JH最近很喜欢跟着我们学说话……自从他能够用语言表达后,他的情绪好了很多,没有以前那么暴躁了”。
文献[1,2]提出了具有谐振直流环节软开关拓扑结构的三电平逆变器,但是因为直流母线之间设置了4个分压电容,在分压不均时,软开关的实现条件影响会受到影响.文献[3~5]提出了具有谐振极软开关拓扑结构的有源三电平逆变器,但是如果该拓扑结构应用到单相全桥三电平逆变器中,辅助开关数将多达8个,控制相对繁琐.文献[6]提出了具有谐振极软开关拓扑结构的无源三电平逆变器,辅助电路无辅助开关器件,控制相对简单,但是直接串接在逆变器桥臂上的无源辅助器件的通态损耗会阻碍逆变器效率提高.
总之,无论是量表的统计数据,还是所观察到的言行变化,都显示,凡是能够持续参与“亲子空间”活动的自闭症患儿,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和变化,甚至有一名儿童(JH)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获得了语言表达能力。
4.2 问题及不足
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有55.55%的问题儿童及父母在初期来访之后便不再来“亲子空间”。通过我们的调研走访,原因有二, 一是这些孩子及家长们的居住地较远,往来一次“亲子空间”费时费力;二是较普通孩子来说,问题孩子的言行较为怪异,同时也容易与其他孩子发生冲突,在“亲子空间”这样一个较为社会化的场所,家长们承受着很多来自公众对自己教育能力及父母角色评判的压力,往往在自己孩子与其他孩子发生强烈的肢体冲突后,便不再来“亲子空间”。譬如上文所说的JH的母亲曾在JH与其他小朋友发生肢体冲突后中断过参与“亲子空间”的活动。
畜禽粪便中四环素类抗生素的残留及危害……………………………………………………………………… 于晓雯,索全义(83)
这些问题及不足是社区“亲子空间”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结论
“组织性精神疗法”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社区里自闭症患儿的社区融合教育及康复工作,在预防及改善幼龄儿童的早期关系障碍、提升其主动性和社会化程度方面,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自闭症患儿及其父母持续参与活动,且父母能积极配合并努力反思和改善亲子关系的前提下,部分孩子可以获得语言使用能力。此外,对自闭症患儿的康复工作来说,父母的配合程度会给康复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亲子空间”的工作也能给父母带来一些影响,我们曾用量表对参与活动的父母与从未参与的父母做过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亲子空间”的工作能够提升父母效能感、降低亲子关系中的焦虑及紧张。正如4.2所提及的问题表明,在“亲子空间”的活动之外,还需要对自闭症患儿的父母给予额外的支持及干预。
当然,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一是所列出的样本量不大,二是项目持续的时间不长。在扩大样本量并增加项目时长的条件下,研究结论或许会有变化。
参考文献:
[1]徐慧,朱健刚.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的发展与启示.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10- 2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337.c.20181025.1507.001.html.
[2]李乐乐,李苗.中国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绥化学院学报, 2015,35(10):94-98.
[3]王建芳,李永生.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与社区孤独症儿童康复的联动机制.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5:1100-1105.
[4]于新宇.0-6岁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评估系统的研发与应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8:22-42+86.
[5]JAMET J-M.De l'asile à la psychotherapie institutionnelle.Soin Etude et Recherche en PSYchiatrie.(2004) [2017-04-04].http://ancien.serpsy.org/histoire/jamet.html.
[6]DUPREZ M.Réhabilitation psychosociale et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L'information psychiatrique, 2008, 84 (10): 910.
[7]HENCKES N.Le nouveau monde de la psychiatrie française: Les psychiatries, l'État et laréforme des hôpitaux Psychiatriques de l'après-guerre aux années 1970[D].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EHESS), 2007: 214.
[8]CHICHE S.La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 de Jean Oury.Le cercle psy.(2014-05-16) [2018-3-4].https://le-cerclepsy.scienceshumaines.com/la-psychotherapie-institutionnelle-dejean-oury_sh_32472.
[9]AUBOURG F, TROTOBAS P.L'Accueil au risque de la psychanalyse.Paris: Le Harmattan, 2016: 32.
[10]Olga S.La possibilité d'une Ile Verte - Histoire de la Maison Verte de Paris à Saint-Pétersbourg: création et transmission d'un dispositif.Paris: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Paris 7, 2015:105,188.
[11]Bénédicte J-V, Michel R.Évaluation de la politique de soutien à la parentalité.(2013-02) [2018-7- 23].http://www.ladocumentationfrancaise.fr/var/storage/rapports-publics/134000110.pdf.
[12]DELION P.La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 : d'où vient-elle et où va-t-elle?.Empan, 2014, 96(4):109, 110.
[13]OURY J.Transfert, multireferenctianite et vie quotidienne dans l'approche thérapeutique de la psychose.Cahiers de psychologie clinique.Cahier de psychologie clinique, 2003, 21(2) :161,159.
[14]DELION P.Thérapeutiques intentionnelles.Croix Marine Normandie.(2015-07) [2018-7-10].http://www.croixmarinenormandie.com/wp-content/uploads/2015/07/therapeutiquesinstitution.pdf: 18.
[15]LUCA-BERNIER C.Transformation du soin et logique des groupes...en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J].Revue de psychothérapie psychanalytique de groupe, 2013, 61(2):115.
[16]BERNARD R-P.Du “nous” au “je”: la posture de l'infirmier en psychiatrie.Information sociales, 2008, 145(1): 74-75.
[17]CHAPEROT C.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 à l'hôpital général: négativité et continuité.L'information psychiatrique,2008, 84(5): 447.
[18]BUFERNE R, JOUSSELME C.La cure en institution.Un outil recommandable de prévention contre la maltraitance institutionnelle?.VST-Vie sociale et traitement, 2015, 127(3):78.
Feasibility Study of “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 in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Work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XU Hui, ZHU Jian-gang, WANG Hai-yan
【Abstract】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heir families are often isolated and closed in the community for various reasons, we have established two “Child-parent Homes” in two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to receive the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cluding children with mental disorder represented by autism⋅ With reference to hold the application of “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 in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work of children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France, we organize our reception work in the “Child-parent Home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iscuss the work setting and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 from our one-year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Child-parent Homes” for one year, and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therapy in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for Chinese urban children with autism⋅
【Keywords】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 Children with mental disorder;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autism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10(2019)34-0056-07
* 基金项目:2018年度广东省残疾人事业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012018100904v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一般课题(2018GZY98)
作者单位:1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州 510275 2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3 广东警官学院 广州 510300
作者简介:
徐 慧 博士后;研究方向:社区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在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中的应用
2.1介入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腹腔镜组,各观察指标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朱健刚 教授 博导;研究方向:社区发展、公益慈善
王海燕 副教授;研究方向:心理学
标签:自闭症论文; 组织性论文; 疗法论文; 精神论文; 亲子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残疾人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2018年度广东省残疾人事业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012018100904v1)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一般课题(2018GZY98)论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广东警官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