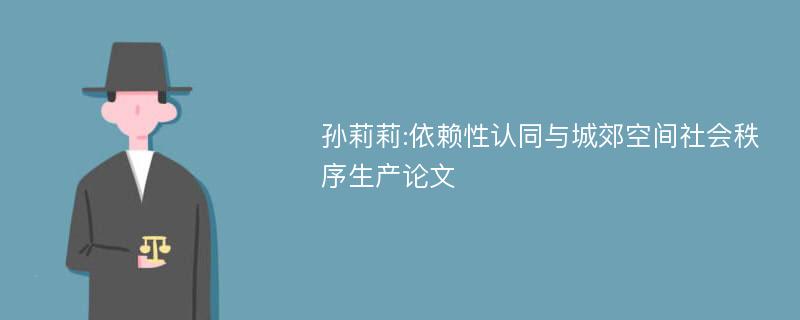
[摘 要]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空间治理的诉求,也是空间研究的核心关注议题。城市空间的分工与更新,使得郊区空间具备了一定的“地方性”特征,要求治理者因地制宜生产与空间生活相适宜的社会秩序。研究发现,依赖性认同构成了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一种机制,即住房属性引起的“政府对我负责”的认同、户口差别导致的“只有政府能做到”的认同和文化冲突诱发的“只有政府能改变”的认同,形成了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生产中相关行动者力量的不均衡,社会秩序面临维系之难。面向美好生活的社会秩序生产应凝聚空间共识和提升合作能力,以形成各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秩序生产格局。
[关 键 词]城市郊区空间;社会秩序;生产机制;依赖性认同
一、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研究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理念和实践推动了我国城市社会的快速转型,城市空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相应的社会秩序遭遇空间流动的解构与重构。一方面是城市中心的日常生活被解构,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政治权力组织和商业功能所消解;另一方面是城市郊区的新空间获得重组,一种新社会秩序的生产正在进行。两个方面政策叠加的效应就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越来越向城市的外围边缘地区置换,城郊空间容纳了从城市中心的旧城改造项目中动迁的市民和附近征地拆迁的农民,空间行动者身份的特殊性构成了社会秩序生产所面临的独特“民情”。从历时性上看,近几年城郊空间现象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社会秩序的生产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从横向比较上看,我国的城郊空间与发达国家“郊区化”的形成机制不同,发达国家的城郊比较多的是中产阶层田园诗式的“后现代主义生活”,而我国城郊空间更多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动聚集。在此意义上,以美好生活为旨向的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成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并检验着城市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政策设置及其效应。
(一)空间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城市规划学、地理学领域的学者把空间研究聚焦于土地、建筑、景观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发现在关注空间物理形态的基础上,更要深刻洞察社会实践或者说社会生活对空间的巨大形塑力,[1]因此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和视角。在此脉络下,城市的空间秩序与空间的社会性生产高度叠加在一起,包括资本、权力、文化等在内的要素影响了空间的结构,并成为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主要参与力量。空间本身形成于对社会生活的回应过程,且从实践上呈现了一种生活的形态,同时,空间结构又折射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在不同空间的沉淀,充分彰显了空间的社会建构。经济与社会因素的投射所引发的城郊空间快速变革让社会成员对新空间的认同存在或多或少的“堕距”,社会成员在新空间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因此,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需要洞察这一实践基础,使空间社会成员成为空间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生产者。
(二)城郊空间的社会结构特征
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进入的“郊区化”阶段不同,我国城市郊区空间的形成并非市场机制的推动和社会成员的主动迁徙,而更多地是行政力量主导下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被动迁居。与其他空间相比较,城郊空间的居民身份更加多元,既有来自城市中心的市民,也有城郊附近的农民,一方面这些社会成员的总体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在民生话语和安居工程下,这些社会成员身上带着政治的标签,整体上看,城郊空间居民的身份内隐着一定的张力,主要表现为居住资格与便利的公共服务之间的紧张感。除此之外,城郊空间居民的社会网络呈现出群体差异,农民群体的邻里关系和组织关系较其他群体紧密和封闭,是空间整体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城市发展政策的裹挟之下,这些社会成员实现了空间的流动,然而,对于城市政府和迁移居民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建构空间的集体认同,凝聚美好生活的共识,进而生产有序的社会秩序。
二、空间与秩序:有序社会的探寻
现代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却又追求着相对稳定的秩序。帕森斯把“秩序问题”定义为整合问题,有序的秩序能使社会成为有机团结的一个整体。马克思在考察空间的社会逻辑时,依据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解析了空间实践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而社会关系正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呈现。当现代性与空间连接在一起,秩序问题被看成是时间-空间伸延的问题,有序的社会秩序能够适应时间-空间的变化。因此,在变动的空间中如何建立有序的秩序,是空间研究的重要旨向。
(一)空间分工与秩序分化
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宏观意义上最大的一次空间分工,其带来精神劳动在城市的集中和大机器生产的科学化,空间分工与秩序分化由此拉开了大幕。由资本、人口等要素推动形成的“大工业城市”改变了传统乡村和自然城市的功能和分工,生产实践中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如商人阶层,商人阶层的崛起直接推动了新兴城市的勃发,而新兴城市内部的空间秩序也因现代文明要素的聚集而发生着分化。[2]104-107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的居住区域日益凝固,工人阶级简陋的蜗居条件和资产阶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区隔”的城市空间中并存,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居住的空间中资本聚集,是消费和文化的城市“中心”。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空间权益关系、空间生活品质等方面存在的严格壁垒的记录,是对社会秩序分化的录制。[1]
现代性语境中,现代社会秩序需要在与传统社会秩序发生断裂的过程中完成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形式的重新建构,然而该制度目标的实现受到社会体系的挑战。现代性的降临带来的是快速的变迁和大范围的断裂,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不再受“在场”的地域性活动支配,“缺场”的各种其他社会要素能够穿透面对面互动复合建构出秩序。[7]12空间与时间的伸延开启了社会秩序变迁的多种可能性,“脱域”机制使社会秩序能够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要素连接起来,“嵌入”空间中去影响社会生活。而对空间行动者来说,则面临着与惯常的分离,对缺乏完整信息的他人给予合适的信任等风险,秩序的稳定感降低。此外,如何认识个体化与标准化、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秩序,如何应对制度性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自发形成的有效的社会秩序间的对立,都是空间更新中秩序的迷思所在。[8]95,277不确定性和风险随着空间的扩展和要素的流动而成为社会秩序生产需要考虑的基本要素,契约、公意等是走出社会秩序迷思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从物业管理的困境和维系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城郊空间的社会秩序生产中,政府起到了核心作用,尤其是面对市场缺位、社会弥散的结构基础,政府具有对话市场、协商社会的资源动员能力,使X社区的物业管理重返轨道,居民获得了有保障的社会秩序。
(二)空间更新与秩序迷思
G镇是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创新工作(保障房安居工程)试点镇,位于城市郊区,居民由中心城区动迁户和周边农民拆迁户组成。G镇X社区是上海市首个建成并交付使用的大型居住社区,该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推进受到市、区、镇多层面的高度关注。与其他空间类似,该空间的物业管理状况①集中体现了社会秩序生产的情况,是研究空间社会秩序的一个恰当切入点。
马克思开展的空间分工与秩序分化研究得到一些学者的继承和发展。列斐伏尔关注城市空间内的日常生活,发现城市及其居民遭遇外在力量如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的单方面控制,逐步失去了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无法围绕日常生活建构一种自由和有差异的秩序。[3]序言7-9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的社会秩序生产没有关照到不同阶层不同主体的特征,而是在全球化的主导话语下趋于同质化。压制了差异性和个体性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激起了空间的矛盾,制度性的规划没有建立在空间的不平衡之上,其结果就是日常生活中人被城市空间所异化,比如底层的和边缘社会群体的声音常常在城市空间中被支配性话语体系遮蔽,无法参与到空间秩序的生产中。因此,他认为应该由人民大众来管理空间,并让空间为人民大众服务。基于此,他提出了“自治”的秩序生产策略。[4]越来越多的堡垒型社区、排外聚居区及贫民窟的出现,引起了学者对空间异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哈维提出“空间修复”(spatial fix)以解决城市增长的空间障碍,苏贾在城市权利的议题下分析寻求空间正义的路径。他认为,正义或者不正义是城市空间问题的关键性指标。重建城市、发展城市、改造城市涉及到是否获得城市空间、参与城市管理、拥有城市生活的权利。[5]序言4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的空间分工与秩序分化的本质是权利关系,没有城市主体之间基本协调的权利关系,就不会有城市正义和社会正义,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美好生活就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空间正义不仅要求社会成员有居住之所,还要能够相对自由而理想地进行居住空间生产和消费,建构适宜“空间性”要求的社会秩序。
三、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特征:以物业管理实践为例
城市的扩展和更新中,不同的空间因各自的资源禀赋而聚集了特征比较明显的群体,空间也因此被区分出来,被赋予了各自特有的功能。在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苏贾等的视野中,城市郊区空间在“中心-边缘结构”的空间形式中处于边缘位置,是远离社会生活重心的区域。城郊这一特定的位置对应着特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城郊空间的社会秩序生产也呈现着独特的面向。
如马克思所发现的,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社会群体,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使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商人通商的扩大,使城市郊区也成为生产和交往的重要地域,并在流通中打破了与城市其他区域的限制,城市获得了更新。城市的地域更加宽广、功能更加明晰、人口更加集聚,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连接纽带的重建。涂尔干认为不断发展的分工成为影响团结的主导性因素,集体意识的平均程度和强度已经式微,社会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如果集体印象有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对象,那么集体意识便具有了确切的特征,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大,尤其是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之后,共同意识的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种可能的变化是共同意识不得不被迫超越所有地方差异,驾驭更大的空间,以避免“失范”。[6]244
(一)资本的撤离与社会秩序的困境
住房体制改革之后,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这“三驾马车”是社区社会秩序生产的重要组织力量,[9]这三个组织中,物业管理公司是市场组织,有着资本的逐利性。社会秩序井然的社区,其物业管理应该是健全的。X社区物业管理经历过一段实践的困境,导致空间的安全、洁净受到威胁,居民的不安感和无助感累积,空间社会秩序一度陷入不佳的境地。该空间物业管理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物业管理费用收支倒挂。在不能降低服务标准、无法收缴约定物业管理费的情况下,物业管理公司入不敷出,无法维持现有的管理,只好向政府表达撤离的意向。这样一来,X社区空间的现有社会秩序遇到挑战。
X社区的物业管理并未遵循市场逻辑。受限定政策②影响,X社区最先投入使用的两个小区里,各项服务和收费标准都定位在二级。虽然限定政策于2011年9月取消,但由于受到之前两个小区影响,2011年以后接管的各小区的各项物业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大多为二级。实际运行中,B企业往往要提供高于二级标准的物业服务,成本更高。因为X社区在民生话语中的特殊定位,经常承担来自于各方面的视察、考察和检查任务,这对物业企业在管理服务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企业在人员配套、服务质量等方面比普通商品房要求更高。然而,恰恰因为X社区是动迁配套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的房屋属性,其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低于普通商品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不相对应,导致B公司的物业服务难以为继。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B公司提出撤离该社区的想法。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自然离开那些没有利益可图的空间,而空间因为缺乏市场回报而无法吸引资本的到来,X社区的社会秩序生产因缺少“一架马车”而无法有效运转。
(二)社会力量的弥散与社会秩序的沉重
有序社会秩序的探寻不仅考察空间结构特征如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位置,还要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源关系、社会认同等对社会秩序生产发生作用的能动因素。[13]认同宣告了一位行动者的存在,表明“我是谁”以及“我怎样与你有所关联”[14]235,认同、空间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关联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城郊空间的物业管理实践中,在权力的呵护之下,资本得以驻留、社会力量找到了功能发挥的方式,空间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组织和社会成员的不安感、焦虑感得到缓解。诚然,政府的资金补偿机制弥补了资本在该空间中的利益,那么是什么机制使得城郊空间中的社会力量对权力从外部供给社会秩序给予认可呢?基于城郊空间的社会结构特征,笔者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依赖性认同,构成了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一种机制,即住房属性引起的“政府对我负责”的认同、户口差别导致的“只有政府能做到”的认同和文化冲突诱发的“只有政府能改变”的认同,形成了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困境、沉重与维系之难,需要空间治理者加以分析。
空间居民合作意愿低,自发秩序难以生产。长期以来,X社区的物业费收缴率低于50%,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拒绝缴纳物业管理费。一是该空间内配套矛盾突出。商业网点、菜场、交通、就学、就医等配套设施要么尚未投入运行,要么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导致入住居民日常生活不便,居民将不满情绪转嫁到物业企业身上,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不缴纳物业管理费。二是该空间的群体为相对弱势群体。X社区导入群体主要是低收入阶层,其中一部分人群长期居住生活在高度商业化的中心城区。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管理和生活服务质量有着较高的期望和要求,当现实不理想时,这部分居民要么选择居住在别处,把房子租出去,对物业不予理睬,要么以物业服务差为说辞,当面拒缴;另一方面,物业管理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少交或者不交的心态比较普遍。这些有着同样经历的居民集中居住后又产生群体效应,相互影响,导致物业费收缴率常年不高。三是本地区的动迁安置户祖祖辈辈居住在乡村,长期无拘无束的农民宅基地生活,导致这类群体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住着自己的房子还要交费”,对物业管理十分排斥,对居委会的劝说不放在心上。面对这些情况,G镇和X居委会从“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提倡多与居民沟通的工作方式,并不倡导B公司把欠缴物业费的居民告上法庭。因此,居民感受不到来自法律的威慑,也不认可居委会的说辞,物业管理费的收缴陷入僵局。因此,居民的不理解、不合作使得有序社会秩序的生产步履维艰。
(三)权力的呵护与社会秩序的维系
当市场无意继续参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而社会力量无力生产适宜的社会秩序时,政府如何运用权力维系该空间的社会秩序,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在体制转型、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城市空间经历了显著的重构,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受到资本逻辑、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逻辑的形塑。[12]
为了找到新的物业管理公司,镇政府和居委会一起找到几家物业管理公司进行商谈,了解到X社区物业管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基础之后,这几家企业表示“很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但是实在没办法做”。市场机制走不通时,镇政府把情况汇报给区政府,请求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决。区层面高度重视X社区的社会秩序状况,相关部门出面与前期物业(B公司)坐下来详谈,希望该企业能够继续在X社区的物业管理活动。B物业管理公司是该区区属国有企业,知道X社区的物业管理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也能够意会政治话语,于是,双方开始围绕物业管理的具体政策支撑展开讨论。在区里主要领导的推动下,区政府制订了B公司在X社区承担物业管理的详细扶持方案:区政府对B物业当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确认当年的亏损额,然后对物业费欠缴部分予以全额补足,将物业管理实际成本与物业管理应收额的差额(收支倒挂)部分作为政府对企业扶持的考核基数,根据考核情况予以拨付。同时,镇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对物业管理情况和收缴率情况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给予物业管理公司财政资金扶持和奖励。
分析: 第(1)问检测的是遗传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概念。生物体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的特征就是所谓性状,而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类型称之为相对性状。判断显性个体是否为纯合子的方法通常有: ①自交: 如果是纯合子,自交子代不出现性状分离;如果是杂合子,自交子代会出现性状分离;②测交: 如果是纯合子,测交子代只表现为显性;如果是杂合子,测交子代既有显性也有隐性。
住房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影响着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政治取向,同时,住房也是政治不平等或者合法化的来源。[15]在市场逐利性的驱使下,由许多保障性住房构成的城郊空间被认定为住宅质量和社会环境差的地方,并因此与其他空间“区隔”开来。城郊空间中居民行动资源的缺乏和身份的福利性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居民对政府秩序供给的高度认同。城郊空间居民经济地位处于劣势,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弱,尤其是动迁农民,虽然拥有了城市身份,却难以获得职业角色,本质上依然是城市边缘人,依赖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改善他们的现状。在一些社会保障滞后的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无力感更加明显。同时,无论是动迁农民还是拆迁市民,身份中的福利标签伴随着他们的房屋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空间资源。针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撤离,G镇X社区业主委员会不得不寻求镇政府的帮助而没有诉诸于市场渠道,体现了空间居民对自身住房特殊性的理解,以及由此特殊性而产生的对政府的依赖。城郊空间居住的动迁农民和拆迁市民绝大多数为行政推动下的被动迁居,空间的住房也由政府规划和主导修建,当围绕着房屋而产生的物业管理这一重要的服务陷入困境时,居民认为“政府对我负责”理所当然。这种依赖,可以看作是个人和家庭面对“现代性”袭来之时,还没做好充分准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或者是“抗拒”。而政府在民生话语下,肩负着保障生活、改善公共服务的行政责任,因此,其无论如何也要维持一种最基础的社会秩序。面对着城郊空间居民的依赖性认同,政府探索自上而下地从外部向社区供给秩序,并努力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可以视为一段时间内政府的权宜之举。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为应对工业4.0而出台的、具有我国国情特点的行动纲领。职业教育主要是服务产业发展的,当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渐到来之际,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由此,传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将不能适应未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为此,职业教育界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本课题在一线教学的基础上,提出“拓基础、强根基、淡专业、重运用、灵考核”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可以为未来职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一条思路。■
四、依赖性认同: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机制
缺少经济资本的驻足,如果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空间仍然可以实现有序。一些小区在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的情况下,居民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业主自管的方式成功处理物业事务。[10]当然,自发秩序的形成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比如空间行动者有对共同利益的认知,有互惠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有对集体行动“搭便车”现象的预防和惩罚。这种秩序接近于帕森斯所讲的“规范性秩序”,是在政治机会恰当、社会参与充分、协商途径畅通等诸条件皆具备的情况下,社区中各种力量长期互动形成的具有规范意义的社会秩序。[11]81-84相反,如果社会力量利益分化大、群体共识少,则无法依靠社会力量的团结形成自发秩序。
(一)住房属性与空间认同
除以上直接扶持外,G镇和X社区居委会专门组建了一支由党员、退休工人组成的社区巡逻队,及时发现社区安防死角和预防邻里纠纷。在此契机下,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物业管理,是期望增强居民和物业管理人员的互相谅解,提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一种自发秩序的形成培育相应的社会资本。
(二)户口管理与空间认同
目前,户口仍是我国许多城市的重要治理手段,户口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包含着分化、监控和计算等,以达到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目的。[16]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公共服务仍是按照户籍人口进行配置的。那些户口留在市中心的拆迁市民,即使居住在城郊,仍要到户口所在地接受相应服务,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利。尤其是残障人士、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需要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异地配置的探索。也就是说,流动性快速增加的背景下,公共服务配置与空间需求之间的张力在增大,城郊空间中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凸显。物业管理案例中,B公司决定撤离后,X社区物业管理遭遇无人问津的现状,没有物业管理公司愿意提供服务,这与中心城区物业管理市场的活跃形成对比。同样是城市户口,但城郊空间很大一部分居民仍保留乡村居住生活习惯。对物业管理持抵触心理,让物业管理公司望而却步。当市场机制失效后,政府选择使用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这部分居民相对缺乏公共空间意识,与一部分非本地户籍白领群体追求较高质量居住体验的需求形成反差,同一空间中需求的显著差异,市场难以细分,只能期待政府更精准地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对于居住在城郊的外地白领来说,虽然通过自身的努力拥有了住房,但要想获得城市户口,却不是那么容易。而户口往往与公共服务捆绑在一起,成为不同人群能否触及公共服务的门槛。这种制度设置造成人群之间人为的区分,影响该空间居民的公平感获得,而该空间中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缺乏,意味着公共服务很大程度上仍需要政府的主导。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养老、教育、医疗等,紧密关系到居民的生活体验感,考验着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在这样的困境中,居民会选择依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形成“只有政府能做到”的认同,而服务型的政府也会动员不同的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以期弥补这部分居民由于户口障碍而无法获得的服务。
比喻要新颖别致,才能让人难以忘怀。《压力气球》一课中,马老师让学生用吹气球的方式把自己的思绪理一理,觉得有压力的事儿,就往气球里吹一口气:带给你的压力大,就吹猛一点;压力小,就吹轻一点;如果没有什么压力,可以不吹。这样的活动吸引了学生,大家纷纷投入其中。接下来的分享交流让学生明了:大家都有压力,压力是可以承受的,压力的释放很重要。在紧张的高三学习中,有这样一个温馨别致的活动,心情会好许多。这一课将成为学生高三生涯的驿站,让大家调整后再出发。
(三)文化冲突与空间认同
文化的冲突导致空间的内部整合困难,难以形成一种被不同群体广泛接纳的自发秩序,需要政府从外部进行干预。这种文化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动迁农民和拆迁市民之间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思想观念上,征地农民来自同一片区域,相互之间自然的亲近感使他们很快在新空间中重拾了之前的社会网络,原来的思想观念籍由延续下来的社会网络得以维持,并没有加入新的元素。当他们与拆迁市民居住在一起时,产生对“外来户”的排斥。相对封闭的思想观念或许为该群体提供了暂时的庇护,营造了舒适的小群体自发秩序,却与城市生活要求的“现代性”不相吻合,同时,拆迁市民也会视该群体为“乡下人”,认为这种小群体自发秩序是落后的、守旧的。然而,思想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在管理和服务中进行长期引导和培育。生活方式上,主要表现为乡村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存在较多碰撞。动迁农民缺乏在注重“公共空间”的城市社区进行恰当行为的经验,当他们以自己所熟悉和掌握的方式开展社区生活时,常常出现“文化堕距”,与城市生活和社区治理目标格格不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动迁农民的一些行为习惯被“凝视”,被从市中心迁来的居民视为“不文明”的、“自私”的。于是,两个群体的隔阂加深,社会秩序生产的工作难度加大。X社区物业管理中出现的管理费收缴难、行为习惯养成难等问题,实质上已经超越了物业管理本身,反映了空间中不同群体的观念、习惯等文化冲突,需要有效的力量来进行引导、培育。当弥散的力量不能通过群体间的互动达到融合,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共识时,就需要外在的力量来出面协调。空间内的群体不约而同地把对文化冲突的不满投射到政府那里,形成“只有政府能改变”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在政府的动员之下来到这里的,并非主动选择迁徙并有意融入一种文化,理应由政府想办法来解决。政府的社会秩序建构就面临着整合不同群体文化的重要任务,既要在包容中尊重多元文化,又要融合不同文化,将小群体的自发秩序和普遍接受的人为秩序贯通。
五、讨论: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秩序格局
已有的空间研究成果表明,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在资本和权力的相互嵌入之下,存在同一性的特征,不同空间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地方性、差异性常常被忽视,导致这些地方的社会秩序生产不够有效。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等多种逻辑的影响之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空间而言,城市已经成为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国家控制与社会成员自主性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17]但当我们进行细致的实地研究时发现,在一些空间,由于力量的不均衡,国家的扶持与呵护却显得必不可少,权力并没有裹挟着资本去凌驾于社会力量之上,相反,权力成为了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保护力量。案例中物业管理服务得以保持,该空间基本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关键在于政府的及时回应、呵护。因此,面向美好生活的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需要从地方性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的正义和空间结构的差异。
(2)下部注入管,将喷嘴降低到设计深度,并确定喷射方向和摆动角,以确保凝结体的有效连接。应防止喷嘴堵塞,可采用低压给水、气、浆时放低管道的方法,或采用塑料布或胶布缠绕的临时防护措施。
城郊空间中,社会成员在城市经营者的政策设置中处在了一种相对脆弱无助的位置,他们在新空间生活体系尚未建立时仍需要传统支持机制的保护功能。研究表明,在一些国家,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有所增加,一是由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对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形成了挑战,二是由于那些合作的传统和互助的形式已经消失,个体成员找不到达成目标的组织依托。[18]14,15本文通过对城市郊区空间的研究,发现空间行动者的依赖性认同构成了空间社会秩序生产的一种机制,并分析了城郊空间中住房、户口、文化等是依赖性认同机制产生的关键因素。同时,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面临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单一依靠政府资源投入的现状,制约着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秩序格局的形成,需要培育该空间中的社会力量建构自治秩序,塑造合作性的认同,推动空间的社会秩序生产从权宜性逐渐走向制度化。
《羊齿山》是自传体诗,迪伦·托马斯在此诗中回忆了自己在羊齿山安妮婶母的乡间宅院度过的愉快时光。第一、二诗节展现儿童时代的托马斯悠闲地在苹果树下玩耍的情景,描述了童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美好时光。第三、四诗节写诗人入眠后的梦想和觉醒的经历,完成了从童年到成年的蜕变。第五、六诗节诗人以老者 的口吻叹息时光短暂,时光让人年轻又让人衰老,完成从童年到老年的生命轮回。
政府仍需要继续完善城郊空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增加生活配套设施,优化商业布局,兑现其对空间居民的承诺,最大程度地缩小城郊空间与其他区域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与政府的外在秩序供给同步,空间的内部自发秩序也面临着如何培育和激发的问题。一方面,凝聚空间不同群体的共识,通过互助服务增强信任与获得感。政府提供平台,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一起主动发现居民需求,共同运作自治项目,使社会成员在空间参与过程中加强互动沟通,形成对空间利益、空间行为等的共识。另一方面,增强空间不同群体的团结,提升空间社会合作能力。引导小群体的团结融入到空间的整体社会秩序中,增加不同群体围绕空间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对话的机会,使空间社会成员具备和市场合作、与政府合作的能力。具备了共识与合作能力,空间自治秩序的生产才有可能性,城郊空间社会秩序的生产才会获得内生动力而得以持续开展。
(5)医院医疗经费使用限定范围,医疗业务中的每一笔款项用途应详细列出,全面加强对成本核算工作的监督。各医院主管部门以及医院自身必须要提高对医疗成本使用过程的监督力度,整治目前医院医疗经费使用与记录弄虚作假的问题,建立严厉的奖惩制度,让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得到相应的惩处。与此同时,为了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和提高医院资金利用效率,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医院还应健全医疗成本评价体系,为保证医院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注释:
会哭的孩子更容易快乐。有的孩子“会哭”,而有的孩子“不会哭”。会哭的孩子哭得痛快,负面心情宣泄也快,事后很快就心情晴朗起来,性格也更加开朗愉快。而不会哭的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感情,哭起来抽抽啼啼,甚至会伴随咳嗽、呕吐等现象。事后要过大半天才能恢复过来,情绪转换慢,对身体也不好。
①以下对物业管理过程的记录来源于笔者在G镇X社区挂职锻炼期间的实地跟踪调查。
王海平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2002),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本质、特点、类型、过程和机制等做了探讨;王敏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2002),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立体地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机理;张世欣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2005),概括了古今中外,人们对思想接受所做的思考,对接受的内涵、特征、机理、接受者进行了分析;近年来有冯颖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心理研究》(2007)、徐永赞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研究》(2006)、赵继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2009)、刘丽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接受论》(2009)等。
②限定政策主要指的是《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分等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沪价商〔2005〕011号)和《关于本市新建配套商品房前期物业服务和收费的若干意见》(沪房地资物〔2006〕583号)。
参考文献:
[1]胡潇.空间的社会逻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3(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及其中国意义[J].社会,2008(2).
[5][美]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9]李友梅.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J].社会学研究,2002(4).
[10]一个小区业主自管物业的案例[N].人民日报,2017-05-19.
[11][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2]钟晓华.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转型期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13(2).
[13]钟晓华.社会实践的空间分析路径:兼论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生产[J].南京社会科学,2016(1).
[14][美]查尔斯·蒂利,塔罗.抗争政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5]Zavisca, Jane R., and T.P.Gerber.2016.The Social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Hous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2):347-367.
[16]Fenglong Wang and Yungang Liu.2016.Interpreting Chinese Hukou System from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J].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16):1-15.
[17][英]曼纽尔·卡斯特,刘益诚.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J].国外城市规划,2006(5).
[18][英]保罗·霍普.个体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Dependence Ident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in Urban Suburban Space
SUN Lili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Good social order is the pursuit of space governance, and also the core issue of space research.The division and renewal of urban space make the suburban space have a certain “local” characteristic, which requires the governors to produce the social order suitable for the space life in the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The paper 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in G town in Shanghai,the author found that dependence identity constitutes a mechanism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suburban space social order, that is, the ident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me” caused by the housing property, the identity of“only the government can do” caused by the “hukou” institu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only the government could change the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cultural conflict, which together form the disequilibrium of the forces of the related actors,then the space social order faces the difficulty of maintenance.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for a better life examines the consequ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to achieve the goal, the actors should refine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spaces, focus on space consensus and cooperation ability, so as to form a social order production pattern based on collaboration,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Keywords:Urban Suburban Space; Social Order;Production Mechanism; Dependence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1003-5479(2019)01-0110-08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1.016
[收稿日期]2018-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差异及分类治理研究”(16CSH061)。
[作者简介]孙莉莉(1982-),女,社会学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宋海洋
标签:空间论文; 社会论文; 秩序论文; 城郊论文; 城市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长白学刊》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差异及分类治理研究”(16CSH061)论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