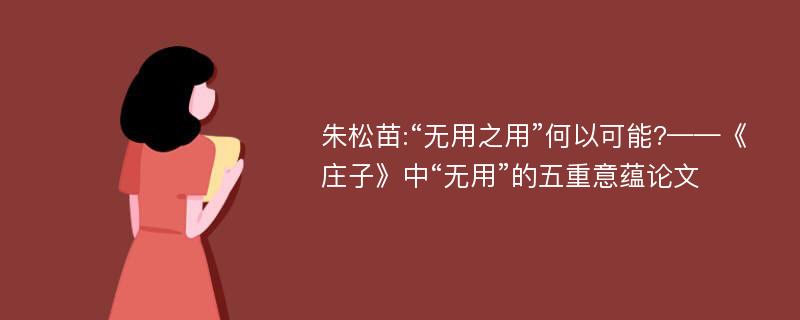
[摘 要]庄子阐释了“有用”的无用性以及“无用”的有用性,其“无用”有五种含义:一是对人为之用的否定,它让人和物都保持在各自边界之内而成为自身;二是与“有用”共在、共生的“无用”,它为“有用”腾出空间、让其实现自身,并和“有用”共同构成统一的世界;三是“有用”自身所包含的“无用”,它显现了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显现了物之存在的边界性;四是道之“无用”,它不仅是对世俗之用的否定,更是对原初世界的复返,在此本源的“无用”中,世界归于自身;五是绝对的“无用”,它是道之“无用”的实现和本真形态,它避免了“无用”的世俗化,使“丧我”的世界不断地复返于道,使本源的世界不断地敞开自身。总之,庄子所寻求的不是事物的“有用”与“无用”,而是事物本性的实现与完成,它昭示了生活世界的真实与真相。
[关键词]无用;无;自然;无用之用
一、“无用”的缘起
和庄子的其他思想一样,其“无用”思想并不是来源于他的纯粹理性思辨,而是来自他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观察与沉思,即世人过度崇尚、追求物的“有用”性,而轻视、规避物的“无用”性——这具体表现为世人因为追求“有用”,而“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1](《庚桑楚》);正是因为规避“无用”,所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庄子阐释了“有用”的无用性,以及“无用”的有用性:对人“有用”之物,对物则无所谓“有用”或“无用”,相反此“用”还会分裂乃至伤害物自身;而对人“无用”之物,对物自身则“有用”,因为正是这种“无用”守护了物的本性,使其免受人的伤害。基于此,《庄子》展开了对世之“有用”的否定和对世之“无用”的肯定。
(一)对世之“有用”的否定
“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移是,今之人也,是蜩与学鸠同于同也”(《庚桑楚》),“今之人”以擅长“用”为“智者”,以不擅长“用”为“愚者”,但在庄子看来这实际上是颠倒了是非,因此他将“今之人”比作浅薄无知的“蜩与学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们只看到了物所呈现出来的表面功用,却看不到这种功用给物所带来的深层危险——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浅薄和无知,其视野的局限性和思想能力的缺失使它们丧失了获得事情真相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狭隘和自私,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需要能否被满足,而不是物自身的实现。在这种境遇中,物不再归属于自身,并因此不再完整,它成了供世人使用的工具和满足世人欲望的对象。其最终的结果是“有用”与“无用”成为世人判断物的价值的唯一或最高的标准,以至于物成了人之物,而人则成了物之人,人不人化,物不物化,人为物役,物为人役。
基于此,庄子对世之“有用”和擅长“用”物的人进行了批判。在世人看来,木之有用性在于它可以用来做船、棺椁、户枢、屋柱等器具,而这些器具又可以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与之相对的就是“散木”“不材之木”,它们因为其材质旋散而不能被做成任何器具,所以不能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因此它们是无用之木。但是对于庄子而言,那些对人有用之木,对其自身却是一种灾难,因为在它非常小的时候就会被人砍去做系猴子的木栓,即便能逃过这一劫的“木”也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继续被人砍去做棺椁、屋柱横梁等。
因此庄子认为“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人间世》),所谓“材之患”就是“有用”之患,这种有用性不仅不会给物自身带来利,反而会给它带来害。这种伤害一方面来自人对物的使用,因为它实际上是以消耗物为前提的,物就在这种消耗中夭折,即便不是如此,物也会因此而失去其原初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来自物对其自身的“有用”的炫耀和展示,“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人间世》),物因为显露自己的“有用”而招来危险,所以“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人间世》)。
概言之,庄子不仅否定了世俗意义上的有用性,而且否定物(人)以这种有用性自居的态度。
综上所述,紫杉醇+奈达铂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治疗中晚期鼻咽癌疗效确切,可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二)对世之“无用”的肯定
如果说庄子的思想一方面是否定,即否定了世之“有用”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则是肯定,即肯定了世之“无用”,认为“无用”对于物自身而言才是真正的“有用”,这种“无用”甚至成了物的本性和物的意义。
这幅图事实上很好理解:x1~xn可以看作不同的输入,而w1~wn是这些输入的权重。1则是用于调整的偏置值,一般记为b但可以看作一个输入永远为1的带权值的向量,此时b =w0。Σ是加权的不同输入的和(就是简单的和),而这一值最终由一个“激活函数”处理,也就是我们说的阀门。整个结构被称为一个“神经元”(感知器),包含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但从这一点来看,它与普通的数学函数无异。但在一个神经元的内部可以看到,除了输入值不可控和激活函数被预先给定以外,不论是任何一个输入值的权重,以及偏置值都是可以任意更改的,这也是神经元的灵活性之所在。
概言之,世之有用与无用是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的,而庄子的有用与无用是从物自身出发、以物自身为重心的。前者从主观出发,以主体的需要和意愿为中心,试图占物为己,而后者则从事情本身出发,以物的本性为重心,试图回到事情本身。所以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对立:在世人看来是“无用”的物,对于物自身而言却是“有用”的;在世人看来是“有用”的物,对于物自身而言却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对立表明,此时的人与物是分离的,原因在于作为自然的人没能超越自己——或者说没能实现自己,而只是以纯粹欲望和充满偏见的眼光看待物,只是将物作为欲望和意愿的对象,这不仅导致了物自身的分离,而且导致了人与物的分离。
二、“无用”的意蕴
庄子对于“无用”的思考虽源于现实,却不局限于现实,而是对其进行了不同层级的思考,所以在《庄子》文本中,“无用”实际上是一个意蕴丰富的语词,它除了作为不同意味的名词出现以外,还以不同层级的动词短语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它将“无用”作为“无”的一个维度,融入了其“无”之思想的整体中——具体而言,《庄子》之“无”至少含有五层含义:一是作为否定的“无”,即对人为之“有”的否定;二是“有”之外的“无”;三是“有”之中的“无”;四是“无”自身;五是绝对之“无”[3]。基于此,“无用”和“无用之用”在《庄子》的上下文语境中也相应地具有五重意蕴。
(一)否定人为之“用”
物既然为物,那么它就是存在的,而且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即物都是有用的。当人面对这种“用”时,就有自然之用和人为之用之别。自然之用尊重自然、顺物自然——“因物尽用”[4],人为之用则以人为中心,破坏物的自然;自然之用是客观的使用,而人为之用是主观的使用;自然之用被用来实现人的自然的欲望,人为之用则被用来满足人的非自然的欲望;自然之用的主体对物自身的认识是完整、全面的,人为之用的主体则可能是狭隘、片面的——“任何物……其存在价值、具体的使用价值、功能与用途则是多方面的。当人们着眼于某物的某种具体用途时,此物的其他用途、其他使用价值是被忽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5]
正是基于此,《庄子》的“无用”首先意味着要否定人为之“用”。一方面,人为之“用”掩盖、割裂、破坏了外物;另一方面,人为之“用”也会伤害作为特别之物的人的身体自身。“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德充符》)”,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可以有两种使用:一是随顺身体自身的需要,按照身体自身的能力,自然而然地去使用身体;二是超出身体自身的需要,逾越身体自身的能力,人为地去使用身体——这种“人为”又表现为两个极端,即“轻用”和“重用”,如果说“重用”是极端重视自己的身体,而导致谨小慎微一事无成的话,那么“轻用”则正好相反,轻率地使用自己的身体而导致自己的身体受损——叔山无趾因为自己的轻率,结果使自己失去了脚。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以自己的欲望和意志为中心,而没有客观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因而偏离了身体自身,最终伤害了身体。而人为之“用”不仅会伤害人的外在身体,也会伤害人的内在性情,“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齐物论》),庄子以猴子为喻,说明世人往往因为不了解事情本身的真相(“名实未亏”),而妄用自己的情绪(“喜怒为用”),这种“用”最终会伤害自己。那么,这种人为之“用”所产生的原因何在?
对于世人而言,细枝弯曲之木是无用的,因为它不能做栋梁;花纹旋散之木是无用的,因为它不能做棺椁;有毒有异味之木是无用的,因为它们容易伤身。但正是因为它们的“无用”,才让它们能够自然生长,而不受人为之砍伐,“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散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树木如果不能成为栋梁,那么它就“无用”。但是以“道”的眼光来看,树木还有更高的“用”,树木不是用来满足人的贪欲的,而只是实现、完成自身,并且依靠其自身的统一来显现人的统一和世界的统一。所以对于树木而言,它首先是要保存自身,然后才能实现自身。而它要保存自身,所需要的就不是对于他物的“有用”性,而是其“无用”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林希逸认为“以无用为大用也”[2](p79)。
一方面来自人的贪欲。在世人那里,物之“用”与“无用”实际上只是来源于人的主观标准,即能否满足个人的欲望,而与事情本身无关——对于他们而言,能够满足人的欲望的物是“有用”的,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物则是“无用”的;能够满足人之大欲的物,它是有大用的,能够满足人之小欲的物,它是有小用的。然而,在庄子看来,人并不需要超出自然本性的“用”,“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逍遥游》)对于小鸟和偃鼠而言,真正对其有用的只是一枝和满腹,这符合它们的自然本性,所以是恰到好处的“用”,相反深林和江河对于它们而言则是多余的,对于人也是如此,人的自然需要是有限度的,在此范围内,物是“有用”的,但是当人试图超出这个限度去追求更大的“有用”时,就可能会伤害到人自身,所以庄子“不用”“天下”,马不用“义台路寝”——“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马蹄》)。
另一方面来自人的主观意愿和成见。“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逍遥游》),宋人以己度人,结果越人因为无发而“无所用之”。这种偏见和成见在蜩与学鸠那里也被突出了出来,它们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出发,嘲笑了鲲鹏的世界,认为鲲鹏的高飞和远游是无“用”的——“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逍遥游》),但正是这种偏见显现了蜩与学鸠的狭隘和无知,“他们(蜩与学鸠)安住在常识的价值和规范世界,以那个世界为它的全部,而被埋没在那些世界。他们,对于他们本来是怎么样的存在,对于人们的真正意义的‘应该怎么样’是什么,人们的根源的真实生活方式是什么的种种问题,是无缘的……”[6](p160)蜩与学鸠所强调“无用”的,却是鲲鹏所认为“有用”的;它们所强调“有用”的,却是鲲鹏所认为“无用”的,这是两种视野、心胸和境界的差异,也是两个世界的差异。
基于此,正是“无用”让物保持在自身的边界之内,从而守护、保存了物。同时,它不仅守护了物,而且守护了人,它让人也持守在人的边界之内。这是“无用之用”的第一层含义。
总之,在“用”的问题上,庄子试图回到自然之“用”,并以此为准绳,对人为之用进行了否定:(1)人为之用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事物本身为标准,它不能如实观照;(2)这种主观判断受限于人的局限性;(3)这种局限性会伤害事物本身;(4)物不物化,人不人化,物和人都丧失自己;(5)物自身并不追求“用”,它只是要实现自身。
2017年,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提高其整体水平,更好地宣传和利用我国的优秀学术成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中国正式出版的各学科6154种中英文期刊进行综合科学评价,遴选出新的300种以中文出版的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其中《冶金分析》杂志有幸入选“第4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的基础上,择优遴选顶尖学术论文,建设了“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F5000)平台”,集中对外展示和交流我国的优秀科技论文,《冶金分析》同时为“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项目来源期刊。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难怪阿花要我过来呢,原来是看中了我手里的客户。而阿花在说这番话时,完全是老板式的口吻,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严肃得像不认识我似的。我简直怀疑我们是否缠绵过。老板本是无情物,美女老板更无情。我早就知道老板是无情的,可我不知道美女老板竟也这么无情。
因为人的偏见、成见及其由以形成的视野、心胸和境界的差异,也会导致人的能力的差异。同一种药,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功用,同一个大瓠,在不同的人手中,有不同的结局,这是由人的能力所决定的。因为物本身是敞开的,关键在于人如何去“用”它:有的人能顺物自然,发挥物的物性,发掘出物的最大潜能,这就是“大用”;有的人则只能利用物,将物作为某种工具,这样虽然也是“用”物,但只是“小用”;有的人则只能破坏物,因为在他的眼里,物不利己,所以“无用而掊之”。
(二)与“有用”共在共生的“无用”
在此意义上,“有用”与它之外的“无用”共同构成了物的世界,所以“无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无用”让“有用”成了“有用”——“无用”为“有用”腾出空间,让“有用”实现自己,完成自己,即“无用支撑着有用,且包容着它”[7](p96)。这就是“无用之用”的第二层含义。
显而易见,每个事物都有其“有用”之处,也有其“无用”之处。“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天运》)。舟对于水行是有用的,对于陆行则无用;车对于陆行是有用的,对于水行则无用。所以舟只能行于水上,车只能行于路上,否则就行之不远。这意味着舟有舟的“有用”之处,也有其“无用”之处;车有其“有用”之处,也有其“无用”之处。因此,对于事物本身而言,“无用”就是其一种存在状态,这是它的一种必然性。
科学合理的管理可使中水系统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及效果[6-7],经过研究和实践,南山终端探索出了1套高效的运行管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无糖不一定就说明它所含的热量就少。我国现行的无糖食品标准规定,每100克或l00毫升固体或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0.5克即是“无糖”。
不仅于此,这种“有用”和“无用”之间不仅仅是共存的关系,更是共生或相互补充的关系。“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外物》)。对于脚(世人)而言,足之所立之地是“有用”的,所立之外的地方则是“无用”的。但是对于庄子而言,如果我们挖去了“无用”之地,仅靠“有用”之地,脚依然是无法行走的,因为如果“有用”之地失去了其依靠,“有用”之地也就不成其为“有用”之地了。推论之,如果没有“无用”,“有用”将失去其依靠;反之,如果没有“有用”,“无用”也将失去其意义。
庄子的“无用”除了表示对于人为之用的否定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以名词形态存在着的与“有用”相对待的“无用”。这种“无用”既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可能性,也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必然性。
(三)“有用”自身所包含的“无用”
不仅“有用”之外存在着与之共存、共生的“无用”,而且“有用”之内或“有用”自身,也含藏着“无用”——即“有用”自身所包含的可能性的“有”与“无”。
文献[21]提到了蓄热换向流动过程中抽取烟气型的取热方式相比中心布置换热器的取热方式更易获得温度分布的对称性,而中心布置换热器的反应器结构及带冷却夹套的反应器结构均易出现温度分布不对称的现象,并针对热不对称情况提出了改善的控制策略。
首先,“有用”自身存在着显(显现)和隐(隐藏)的问题,当“有用”被隐藏时,它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无用”,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无用”——即“有用”的隐藏。这种隐藏之所以能够存在,既可能源于人,也可能源于物自身,所以隐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人隐藏了物之“用”,即人由于自己的贪欲、偏见和能力的原因而不能发现这种“用”;二是物自身隐藏了物之“用”,“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逍遥游》)。对于有发之人而言,帽子是“有用”的——这时帽子的价值是显现的;对于无发之人而言,它却是“无用”的——帽子的价值是隐藏的。这意味着帽子的“有用”是存在的,但它可能显现自己,也可能隐藏自己。当物之“有用”被隐藏时,物就呈现为一种“无用”。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无用”。
其次,“有用”除了被隐藏,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被消耗,当这种用被消耗殆尽时,“有用”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无用”,这种“无用”就不是可能性的“无用”,而是必然性的“无用”;它不是“表现”为一种“无用”,而是真正、彻底的“无用”。当然这种“消耗”也可以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的消耗,另外一种是自然的消耗,前者会导致物的“中道夭折”,后者会导致物的“终其天年”;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要否定,因为它是对物的伤害,对于后者,我们则不能否定,因为它是物的天命和自然之途,是物的实现和完成。
基于此,正是“无用”完整地显现了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昭示了物之存在的边界性,并让物的存在和价值得以实现和完成。这是“无用之用”的第三层含义。
(四)“道”之“无用”
如果说以上所讨论的是与“有用”相对的“无用”,我们统称之为物之“无用”的话,还有一种更为本源的“无用”——道之“无用”。“道”之所以“无用”,是因为“道”本身是被“无”所规定的——“夫道……无为无形”(《大宗师》)、“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天道》)……
从主观方面而言,道是无为的,它反对人为的行为,强调不干涉万物,因此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它对万物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它仿佛是“无用”的;同时道也是“不仁”“无情”“无知”“无言”的,它不会主观地去爱、去思考、去言说,这都表明了其世俗的“无用”性。
从客观方面而言,如果说“物”因为其现实的存在性而可以被人或他物所用的话,那么“道”是不能被人或物所用的,究其根源,“道”并不是现实之“有”,而是“无形”的,“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天运》),因此它不可能被用来“献”“进”“告”“与”于他人,从而给自己及亲近的人带来利益。在此意义上,道也是无用的。
图1示,阳性淋巴结中PLAGL2高表达,其染色强度高于相应的PCa原发灶组织,其中在PCa组织中弱阳性5例,阳性4例,强阳性6例,在转移淋巴结组织中,弱阳性2例,阳性6例,强阳性12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686,P=0.039。
因为道在根本上是“无用”的,这也意味着万物在本性上是“无用”的,所以“无用”就成了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身,“物的意义就是其无用性”,而“物的有用性”则“遮蔽了物自身的意义”[8]。
所以,物既不是为了“用”而存在,也不是因为“用”而存在,而是原本就存在的。相反,为了守护它的存在,它需要反对它的有用性。所以有用之山木、桂树、漆树、果实因为其有用性,而遭到人的砍伐、伤害。相反,那些无用之山木、支离者、痔病者等却因为它们的无用性,而得以全身养性,所以对于物自身而言,这种无用就是其最大的用,即无用之用。
而真正能做到彻底的无用,不被外物所伤害的,就是“无”或接近于“无”的人和物,如“骷髅”——“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至乐》)。一方面,对于他人而言,路边的“骷髅”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以至于人不会去关心、理睬它,所以“骷髅”不会受到人的打扰,更不会受到人的压制、伤害,因此它能持守自身;另一方面,“骷髅”因为原本空无一物,所以它不会失去自己,“它的枯干,是出于它完全没有东西在内,它是最空洞不过的,然而它还是我自己。这是最空虚、最低层的我,我(它)没人可再压制了。我(它)是无敌可畏了”[9](p22)。在此意义上,只有“无用”才能保持物自身的坚固性、完整性和统一性。这不是“骷髅”自身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其存在自身的真相,也就是它的本性。它只是顺从了自己的本性,从而获得了自身的统一。
虽说不期待浪漫的发展,也不该在巨大升学压力下节外生枝认识女孩,但如果在清晨的公车上遇见她,起码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好吧。
两人重新站位。天问大师道:“无回掌有三招,三少准备好了。第一招,‘我佛普渡有缘人’!”他交待无回掌三招又叫出招式的名称是以为祭出无回掌会只赢不输,但由于输了一场,萧飞羽又送一场,所以就该赢得磊落,赢得萧飞羽无话可说。他身上的黄色僧衣无风自动,双手指东打西,倏然幻化出满天掌影,掌影如莲花在幻动中沉浮。果然绝学,未行接触就已声威逼人。
称(S(ξ),I(ξ))是系统(1)的行波解,其中若(S(ξ),I(ξ)) 非负 、非平凡且满足系统(1)以及下述边界条件:
本文使用TI公司的DM368作为主处理器,DM368采用ARM926EJ-S内核,工作频率最高可达432 MHz,芯片内部集成有两个视频图像协处理器引擎HDVICP和JPCP、Voice Codec模块。DM368还提供丰富的外设接口,如USB2.0、SDIO、EMIF、EMAC、I2C和SPI等。
综上所述,对于庄子而言,万物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其无用,而这又在于其本性——“道”是“无用”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复返于“道”,就需要复返于“无用”。在此意义上,“无用”不仅是对世俗之用的反驳,更是对原初世界的复返。因为正是在本源的“无用”中,世界才归于世界自身,“大树只是生长在自然之野中,而自然才是大树所归属的世界。在这样的自然的世界里,大树就是大树,它作为其自身是其自身。因此它是真正的物自身”[8]。这是“无用之用”的第四层含义。
(五)绝对的“无用”
然而“无用”自身也需要不断的自我否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无用”之“用”向人们显现时,“无用”也可能会成为人们所追求的对象,这时“无用”就不再是“无用”自身,而是成了一种新的“有用”。因此,“道”之“无用”本身需要不断的自我否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将“无用”有用化,即避免“无用”的世俗化;另一方面是为了“无用”自身的生成,只有当“无用”不断地自我否定时,它才能与自身分离,从而不断地自新与生成。这意味着,“无用”中的“无”在这里是作为动词使用的,当它的对象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时,它不仅否定“用”,而且否定“无用”,甚至也否定“无无用”乃至无穷,即绝对的“无用”。
《人间世》中的栎社树及其背后的匠石就是这样一种求取“无用”的典型。栎社树因为材质不好而成为无用之木,但正因为这种“无用”,才使它免受匠石的砍伐,得以长寿。问题在于,这种“无用”却成了栎社树所追求的对象,“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只是当栎社树在追求“无用”之时,危险同样紧随其后——“几死”。以至于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最终使它得以保全自身的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无用”,恰恰是它的“有用”,即成为社树。因此,栎社所求的“无用”仍然是一种“有用”,它之所以能够保全自身,只不过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其他欲望,只是方法上的与众不同而已——“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匠石的弟子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如果栎社树追求“无用”,那么它为什么还要成为社树呢?对此,匠石也只能左右为难地承认,“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匠石之所以左右为难,是因为他在前面肯定了栎社树的“无用”,而在此他又必须肯定它的“有用”。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人对于无用者无须担忧。凭借其无用性,它具有了不可触犯性和坚固性。因此以有用性的标准来衡量无用者是错误的。此无用者正是通过让无物从自身制作而出,而拥有它本己的伟大和规定的力量。以此方式,无用乃是物的意义。”[8]
事实上,匠石的“为难”并非来源于事情本身,而是来源于他的主观成见,他过于在意物的“无用”,以至于把“无用”当成所追求的对象。实际上“无用”的有用性主要是对于物自身而言的,在一个风险社会里,人类对于“无用”之物的态度却不可捉摸。对于无道之人而言,他所否定的正是“无用”之物。所以当我们去追求物之“无用”时,也是“无用”的危险之时——这也是栎社树在追求“无用”时,屡屡处于“几死”处境的原因。
“无用”并不是我们躲避危险的避风港——因为在有道的社会,“无用”是有用的;在无道的社会,“无用”是无用的。无独有偶,在《逍遥游》中,庄子也强调了这种“无用”的危险性,“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五石之瓠虽然可以被庄子用来“浮乎江湖”,但是在惠子那里,它却因为“无用”而被打碎了。
所以“无用”是无须追求的,在风险社会里,“有用”“无用”都有其风险,“无用”并不能保证其不受伤害。更重要的是,“无用”也不能被追求,否则它会偏离乃至伤害事情本身。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山木》)。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故事。山中之木因为其“无用”而得以全身,山外不鸣之雁却因为其“无用”而最终殒命,同是“无用”之物,却命运迥异。这证明了在风险社会中,物之命运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所以我们无须去追求“无用”。
爱莲心对这个故事则提出了第二种解释,表明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能去追求物之“无用”。因为这种追求是人为而不是自然的,人为会破坏物的自然。“不鸣之雁,刻意遵循庄子的思想而误解了它的思想。它因其刻意而误解。在其竭力坚持无目的的目的(宁可不鸣)的过程中,它犯了错误。”[10]188在这里,她将雁的“不鸣”理解为一种刻意的行为,也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是一种富有创见性的解释。她可能注意到了植物和动物的区别:植物虽有生命,却无意识;动物则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和行为。所以对于植物而言,它的生命本身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着非自然;但是对于动物而言,则具有了两种可能性——自然和非自然。在爱莲心看来,不鸣之雁选择了后者,它非自然地“遵循一种预先的计划,刻意遵循庄子为雁设立的规则”[10](p188),正是这种“刻意”和“追求”断送了它的性命。
由此可见,庄子一方面反对世俗的“有用”;另一方面也反对非自然的、人为的“无用”;最后它还反对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介于“有用”与“无用”之间,即“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因为这同样是人为的设计和安排——“将处乎”,它不符合事情本身,所以“未免乎累”。
概言之,绝对的“无用”才是真正的“无用”,与其说它是对“道”之“无用”的否定,不如说它是“道”之“无用”的真正完成,是“道”之“无用”的真正存在形态。在此过程中,因为绝对的“无用”避免了“无用”的世俗化,并且使之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显现、生成自身,从而使本源的世界不断地显现出来,使“丧我”的世界不断地复返自身。这是“无用之用”的第五层含义。
三、无用与自然
那么,庄子对于“有用”和“无用”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如果说不鸣之雁是因为“非自然”而牺牲的话,那么鸣之雁之所以能够躲过这场劫难,则是因为它的“自然”,它遵循了自己的本性。
这意味着,我们所要遵循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人为的标准,而是事物自身的本性;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事物的“有用”与“无用”,而是事物本性的实现和完成,并通过这种实现和完成来昭示自己,同时昭示世界的真实、真理和真相。所以无论是“有用之用”,还是“无用之用”,都不是庄子追求的最高目标。天地万物如果因为追求“有用”而丧失本性,那么这个“用”就应该被否定;反过来,当天地万物因为追求“无用”而丧失本性,那么这个“无用”也应该被否定。
所以,庄子最终选择的方法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所谓“道德”就是得之于道的自然本性,林希逸解释为“顺自然”[2](p300),“万物之祖”即万物的本性、本源,是“万物之始也”[2]301,没有人为的赞誉或诋毁(“无誉无訾”),没有人为的执着之心(“无肯专为”),而只是顺物自然(“与时俱化”“以和为量”),这样就能“物物而不物于物”①关于这句话的翻译,历代译注多有不同,陈鼓应翻译为“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1](p501);曹础基翻译为“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主宰”[11](p167);王先谦则将其翻译为“视外物为世之一物,而我不为外物之所物”[12](p286)。从中可以发现,大家对于“不物于物”的理解是大体一致的,但是对于“物物”的理解则产生了分歧。陈鼓应和曹础基认为“物物”就是人要主宰外物,问题在于,就庄子的思想而言,人和物都是“道”的显现,他们之间并不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平等齐一的,人不物于物,物也不物于人。所以“物物”的真正含义应该是:以物为物,把物当成物自身,人和物一样,都是“世之一物”,人是人,物是物,人不主宰物,物也不主宰人。。
因此庄子在这里所强调的也许并不是要对某种外在的威胁给出一个万全之策,这不是人所能把握的,所以他强调要“安之若命”;他所强调的是人不要刻意而为,既不要刻意追求有用,也不要刻意追求无用,因为追求对象虽然不同,但是追求这个行为本身是相同的,它表现了人的心灵的偏执——偏执于世界的某一点,而忘记了其他,所以这种偏执是片面的、狭隘的,是一种有限的“有”;而人的心灵所追求的应该是全而不是偏,是无限而不是有限,是宽广而不是狭隘。
综上所述,庄子的“无用”思想并不完全是基于对现实的情感性批判,也不是基于纯粹的逻辑思辨,而是基于对“物”之本性的沉思,最终他所获得的是对于物之本性地揭示。在此意义上,庄子对于物的“有用”和“无用”的认识超越了历史和现实,进而展示了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纯粹性。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周啓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朱松苗.论《庄子》之“无”的三重意蕴[J].海南大学学报,2016(5).
[4]朱哲.老、庄“无用之用”思想析论[J].宗教学研究,1996(4).
[5]罗安宪.“有用之用”“无用之用”以及“无用”——庄子对外物态度的分析[J].哲学研究,2015(7).
[6][日]福永光司.庄子:古代中国存在主义[M].李君奭,译.台北:专心企业有限公司出版社,1978.
[7][日]金谷治.“无”的思想之展开——从老子到王弼[M]//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彭富春.什么是物的意义?——庄子、海德格尔与我们的对话[J].哲学研究,2002(3).
[9]吴光明.庄子[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
[10][美]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1]曹础基.庄子浅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6.006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6-004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庄子》之‘无’的美学精神研究”(17YJC720044);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265)。
作者简介:朱松苗(1980—),男,湖北宜昌人,哲学博士,运城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有用论文; 庄子论文; 之用论文; 自己的论文; 自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理论月刊》2019年第6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庄子》之‘无’的美学精神研究”(17YJC720044)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265)论文; 运城学院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