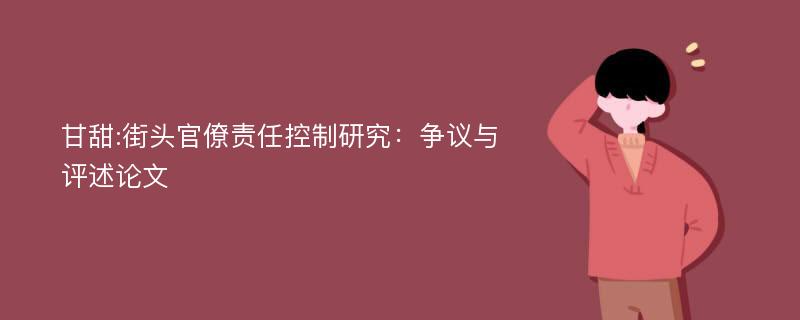
理论述评
【摘要】街头官僚因其自由裁量权而引发学界对其责任控制问题的持续关注。论文分析了街头官僚责任体系与控制机制、责任控制的研究起点与争议焦点、责任控制程度论争、责任控制路径论争、责任控制转向等问题。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已超越了单纯的政策研究领域,但仍缺乏共识。因此未来发展需在四个方面发力:街头官僚责任控制机制及方式整合研究;屏幕官僚和系统官僚的责任控制;治理理论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影响;街头官僚理论的本土适用性与责任控制研究。
【关键词】街头官僚 自由裁量权 责任控制
一、引言
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作为政策执行的末端,因其“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政策再制定能力”(Lipsky,1977,1980)为责任控制设置了难题,备受学界关注。在现代媒体的推动下,执法一线频发的冲突与矛盾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和政府权威,街头官僚责任控制因此成为更加重要的公共话题和研究主题(韩志明,2011;尹文嘉,2009)。
当前,街头官僚责任控制议题基本围绕街头官僚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展开(Scott,1997;Vinzant et al.,1998;Brodkin,2008;Hughes & Condon,2016),但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究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增加还是减少甚至彻底消失?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该分歧所引发的如何实现对其责任控制成为争论的焦点(陈那波、卢施羽,2013;Maier & Winkel,2017),并形成了“国家代理人”范式下的“惩罚-规制”型(Lipsky,1977,1980;Hadley & Clough,1998;Bovens & Zouridis,2002;Baviskar & Winter,2017)和“公众代理人”范式下的“激励-引导”型(Brodkin,2008;Tummers & Bekkers,2014)两条截然对立的责任控制路径。
尽管街头官僚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但其核心关切往往不是责任控制,而是政策执行与自由裁量权问题(Weatherley & Lipsky,1977;董伟玮,2018)。究其原因,其背后的逻辑是上述二者可等同于责任控制问题(韩志明,2008,2011)。这实际模糊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与责任控制之间的界限。诚然,街头官僚责任控制问题由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引发,但二者属于“因果关系”而非“等价关系”。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街头官僚的责任体系、自由裁量权与责任控制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应有关注。同时,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居于研究的焦点,该理论创立者迈克尔·李普斯基(Michael Lipsky)(Lipsky 1980)并未专门探讨其含义,而是通过描述街头官僚的工作环境与特点来表现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后续学者基本沿袭该传统,往往把“自由裁量权”视为先验的假设(Assumption)或者常识(Commonsense)而对其理论内涵等讨论较少。鉴于此,本文试图摆脱传统的以自由裁量权为核心的研究视角,转而以街头官僚责任控制为核心,在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以述评的方式建构起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体系,即责任控制的“体系与机制—起点与焦点—程度与路径”。
胃肠道微生态参与胰腺癌发病的可能机制目前尚未阐明。学者们认为,病原菌、年龄、环境、代谢、遗传等因素导致胃肠道微生态失衡,失衡可能经由模式识别受体、炎症复合体以及NF-κB、环氧化酶2、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树突状细胞、调节性T细胞等细胞分子引起肿瘤相关性炎症、感染、代谢失衡、免疫紊乱,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15-17]。这些机制是肿瘤普遍发生的过程,找到其与胰腺癌发病机制的特异关系将有益于揭示胰腺癌发生的本质,因此尚有许多的研究要做。
为此,本文的论述结构与章节安排如下:首先,第二部分阐明街头官僚责任控制体系与机制的内涵,具体包括责任控制体系中的“方向”与“对象”和责任控制机制中的“类型”与“特征”。其次,第三部分通过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起点——自由裁量权的述评,明晰其内涵与特点、产生、本质及表现形式,进而阐明责任控制的争议焦点在于对自由裁量权控制的程度与路径。再次,第四部分围绕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应该有多少”引发的责任控制程度之争分三个历史时期展开述评。复次,第五部分围绕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及如何予以控制”引发的责任控制路径之争从自由裁量权的“魔鬼”与“天使”形象出发,分三个历史时期展开述评。最后,第六部分总结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现状与不足,指出新时期街头官僚理论责任控制研究的四大方向:街头官僚责任控制机制及方式整合研究;屏幕官僚和系统官僚的责任控制;治理理论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影响;街头官僚理论的本土适用性与责任控制研究。
二、街头官僚责任体系与控制机制
第二,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究竟是积极的(“天使”)还是消极的(“魔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路径,即责任控制制度设计中,究竟是鼓励还是压制其自由裁量权?
(一)街头官僚责任体系:方向与对象
定时。种苗培育饲料投喂是关键,严格按照固定的时间投喂有利于鱼类尽快形成摄食习惯,便于鱼群集中等候。要求少量多餐,一般推荐一天投喂次数不少于四餐。即早上第一次投喂8:00-9:00,第二次10:00-11:00;下午第一次投喂14:00-15:00,第二次17:00-18:00。
(二)街头官僚责任控制机制:类型与特征
对宽带IP网络的全部流量进行采集,考虑到每个城市有多个区县,所有业务流量均要经过城市出口路由器,建议将采集系统设置在城市出口路由器侧,如下图:
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特征则在于“一个中心”与“多元并举”。“一个中心”即在控制逻辑上紧扣自由裁量权,并遵循“由影响因素确定控制方式”的理念;“多元并举”则是在控制方式上呈现多元化特征,形成诸如制度控制、组织控制、技术控制、文化与伦理控制、公共服务动机塑造、外部环境优化等多元控制方式(韩志明,2008;Hupe & Hill,2007;Brodkin,2008;Busch & Henriksen,2018;Loyens & Maesschalck,2010;Moynihan & Pandey,2007;Scott,1997)。总体而言,学界为街头官僚责任控制设置了多重机制和多种具体方式,但不同控制机制对应于存在张力且逻辑相异的“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体系,不同机制之间会否相互影响乃至阻碍,进而导致控制机制失效?同时,究竟如何匹配上述多种控制方式,从而实现责任控制的最佳效果?这些问题尚无定论。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学界普遍认为街头官僚既受所在政府组织的委托,又受社会公众的委托,因而其责任包含两个方向:科层制中的“对上负责”(Lipsky,1977,1980)和民主政治中的“对下负责”(Harrits & Møller,2014)。具言之,一方面,街头官僚作为“国家代理人”,须通过完成政策执行任务对所在的基层政府负责——这实质是科层制中的“对上负责”逻辑。通过组织控制的强化,“能够强制基层官僚,使他们的行为更加符合组织的正式规则和期望。这些指标能更确切地指导基层行政人员应该做些什么事,这样会有助于回应”(罗森布鲁姆等,200 387)。另一方面,街头官僚作为“公众代理人”,须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对社会公众负责(Weatherley & Lipsky,1977;周定财,2010),即遵循“对下负责”的逻辑(Maynard-Moody & Musheno,2000;Sager et al.,2014)。当前学界普遍认可街头官僚责任体系内蕴双重方向(对上与对下)和两类对象(政府与公众),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往往偏于从政府(Weatherley & Lipsky,1977)或公民(Scholz et al.,1991)中的某一方论证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缺乏对两者的整合。此外,科层制与民主政治天然存在张力,如何平衡“上”“下”责任体系,学界并未进行更多探讨。
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起点在于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这为责任控制设置了难题(Brodkin,2008),而争议焦点则在于其自由裁量权应控制在什么范围内以及如何实现控制。现有研究与实践中,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议题围绕其自由裁量权展开(胡怀亮,2005;韩志明,2008;Weatherley & Lipsky,1977;Hupe & Hill,2007;Bovens & Zouridis,2002),其内在逻辑在于:自由裁量权引发责任控制难题,约束与控制自由裁量权是实现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钥匙”。
三、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起点与争议焦点
如上所述,街头官僚责任体系与控制机制的研究未能回答“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张力、多种控制机制如何匹配等难题,但目前的共识在于街头官僚的双重责任体系由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引发,责任控制机制的设置以“控制自由裁量权”为目标。因此,有必要回顾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起点——自由裁量权及争议焦点——自由裁量权控制路径和程度。
(一)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起点:自由裁量权
李普斯基认为“拥有自由裁量权的一线执法者”(Lipsky,1983)是街头官僚的核心特征,而自由裁量权导致街头官僚在执行政策时会“再决策”,从而影响执行效果。围绕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学界从其内涵、产生、表现形式和本质等方面展开研究。
1.内涵: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空间
早在街头官僚理论正式提出之前,肯尼斯·戴维斯(Kenneth C.Davis)(Davis 1969)便对自由裁量权下了经典定义,他认为“对一位政府官员而言,只要对权力的有效限制给予他在作为与不作为的可能的行动方式中做出选择的空间,他就拥有自由裁量权”。亨利·韦德(Henry W. R. Wade)和克里斯托弗·福塞斯(Christopher F.Forsyth)(Wade & Forsyth 200 35)更为简练地表述为自由裁量权就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而李普斯基(Lipsky,1980;Weatherley & Lipsky,1977)基于政策执行的视角,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出发,认为自由裁量权就是街头官僚在制度、组织和环境等约束条件下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由此,街头官僚实际成为“政策再制定”的主体。此后40余年,学界基本沿用其定义,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是街头官僚执行时“一定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空间”(崔卓兰、刘福元,2009;Scott,1997;Brodkin,2008)。尽管取得一定共识,但学界对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侧重于描述性定义,而非严格的学术定义,因而未对其伸缩空间和价值、性质等作出判断。这不利于厘清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与责任控制之间的界限,也为日后关于其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程度和路径之争埋下了伏笔。
2.产生:街头工作特性抑或制度、组织约束不足
李普斯基(Lipsky,1980)着眼于街头官僚的工作环境和特点,认为街头官僚居于一线,与具有不同服务需求的公众面对面接触,工作环境极为复杂,须时常即时作出判断和决定,由此便产生了自由裁量权。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对象是个人,“和大多数组织中的低层职员不同,街头官僚在决定他们的机构供给的利益和惩罚的性质、数量和质量时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Lipsky,198 13)。换言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来源有二:一方面源于政策执行任务繁重而执行资源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源于政策制定不可能兼顾所有情况,街头官僚须对具体情况予以判断。珍妮特·温赞特(Janet C.Vinzant)等(Vinzant et al., 1998)赞同上述观点,指出一线官僚的决策总是在特定环境之中,这种环境迫使他们自主决策,从而提供相应的工作解决方案。进而言之,基层一线官员必然拥有自由裁量权,并藉此作出临时性的判断与决定(Brehm & Gates,1999)。与此相反,另一派学者反对自由裁量权产生的必然性,坚持认为这是制度约束失效、组织监控不足的结果(Koch,1986;Jones,1999;Lymbery,2000)。换言之,只要加强组织控制,明晰政策目标和内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减少乃至消失(Howe,1991;Harris,1996,1998)。综上,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产生到底源于工作特殊性还是制度、组织因素,抑或兼而有之?学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如果是前者,则其自由裁量权必然存在;如果是后者,则其自由裁量权可以消除。正是由于上述分歧,影响了学界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流变的判断,特别是治理转向和技术应用后,其自由裁量权是否压缩乃至消失的争论也与此相关,并引发了关于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程度的争论。
坚持“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随着时代发展而扩张”的学者则强调强化责任控制程度。尽管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街头官僚受到了更多监控,但不少学者从实证角度否定了其自由裁量权受压缩的观点。例如,约翰·威尔士(John S. G. Wells)(Wells,1997)通过对社区心理卫生政策的执行情况调查后发现,居于较高地位的政策执行者和组织管理者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会故意放松对街头官僚执法的监督与控制,其后果是扩大了其自由裁量权。伊夫林·布罗德金(Evelyn Z. Brodkin)(Brodkin 1997)指出社会福利分配与公共服务领域天然存在自由裁量权,组织规则再全面,也不能预知政策执行中的所有情况。张力伟(2018)指出街头官僚在部门冲突中往往更善于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完成任务。概而言之,这部分学者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并不会随着组织控制技术的完善而缩小,相反,在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过程中,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实际存在扩大趋势。因此,需要采用更加严苛的责任控制手段加强对其自由裁量权的监控和抑制(Brodkin,1997,Maynard-Moody et al.,2000)。
本质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是“约束条件下的自主选择权”(Davis 1969;Lipsky,1977,1980;Brodkin,2008)。这一约束条件既可能是工作性质、环境导致的资源不足(Lipsky,1980),又可能是制度缺陷、组织能力欠缺导致的监督不足(Koch,1986;Howe,1991)。在表现形式上,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最主要表现在其“再决策”权力上(Lipsky,1977,1980),即街头官僚在服务分配和社会管理时,他们实际在制定谁可以获得服务以及谁应当被管理的政策(叶娟丽、马骏,2003)。具言之,其表现形式有:(1)选择行政处罚幅度与种类,即街头官僚可在规则范围内,对管理对象的违法行为决定处罚的幅度及种类(Lipsky,1980;韩志明,2008);(2)选择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即在提供服务或管理社会时,他们可自由选择作为或不作为(Wade & Forsyth,2000;Dunér & Nordström,2006;Dorch,2009);(3)事实性质及情节轻重的认定,即他们可自主对服务和管理对象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予以认定(Westley,1970;Van Maanen,1973)。
综上,学界普遍赞同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但对其内涵的界定以描述为主,并未在性质及价值判断、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方面达成共识。由此,围绕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责任控制问题便产生了控制程度与路径之争。
街头官僚责任控制机制分为“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两种类型。内部控制遵循科层制中的“命令-控制”模式,通过组织目标、行为标准和绩效考核等方式达成责任控制目标(Sabatier & Mazmanian,1979;Edwards,1980;Linder & Peters,1987),契合街头官僚在科层制中“对上负责”的逻辑。外部监督因监督主体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遵循民主政治的逻辑,通过扩大公民参与、媒体监督等方式规范街头官僚行为(Scholz et al.,1991;Hupe & Hill,2007);另一类则遵循政府体系中的分工原则,通过立法监督(如完善立法)和司法监督(如法律制裁)等方式保证街头官僚忠实履职(Lipsky,1980;Bovens & Zouridis,2002)。无论是对公众负责还是对立法机关负责,外部监督机制都契合民主政治中的“对下负责”的逻辑。
(二)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争议焦点:程度与路径
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问题尽管始终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Evans,2010;Scott,1997),但学者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始终存在交锋,由此,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程度和路径产生巨大分野。
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导力量,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教师有些行为不合适,也容易引起学生课堂问题行为(见表2)。
第一,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应该有多少?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是否随着时代,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压缩乃至消失?对该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程度,即责任控制制度设计中,究竟施加多大力度、配置多少资源对其自由裁量权予以控制?
在当前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环境和条件下,医院各层领导者在经营意识和成本理念中仍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普遍存在着重医疗而轻管理、重收入而轻支出和重投入而轻效益等问题。医院现在都在实行预算会计的相关制度,而财务人员却缺乏有关成本核算的知识和理念,体现在管理机制和模式上就是比较重视业务部门的成本核算,而忽视了管理部门的成本核算。在管理部门或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粗放式的成本核算管理制度,使管理者在成本核算时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和偏差,最终导致管理者在管理决策上出现失误,从而影响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在民主国家,责任控制是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街头官僚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界处,面临来自科层组织的压力和社会公民的要求,因而承担双重责任。对其责任控制自然存在着来自科层组织的“内部控制”和来自社会公众等“外部监督”两类机制。
电商(商务秘书)场景实验室教学有效地建立起了课堂与岗位间的密切联系,提高了学习的实用性和学生的岗位实践能力。教学中,教师以电商场景实验室或企业真实场景为平台,通过完成场景任务将理论知识与岗位实践有机联系起来,为学生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电商(商务秘书)场景实验室教学中,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也得到了逐步提升。
四、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程度论争
街头官僚理论提出至今已有40余年,但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应该有多少,是否产生时代流变,即自由裁量权是扩张抑或压缩存在巨大分歧,由此引发的街头责任控制程度议题成为学界持续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自由裁量权稳定期与责任控制程度
街头官僚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80年代,解释当时一线官员政策执行的情况,因而无所谓自由裁量权的时代流变。总体上,当时学界普遍认可街头官僚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多数研究者指出,街头官僚受到组织规则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其自由裁量权的减少乃至消失(Prottas,1978;Brintnall,1981)。查尔斯·科赫(Charles H. Koch)(Koch 1986)不仅指出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时存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还认为对官僚决策缺乏实时监督是这一现象的根源,这与李普斯基(Lipsky,1980)认为的“工作环境与性质产生自由裁量权”存在分歧。尽管如此,他们共同承认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于组织能力控制不足,基层政府无法实时监督其政策执行过程。因此,在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议题上,主流声音是必须强化对街头官僚的约束与控制,并力主遵循“加强组织控制—自由裁量权受约束—实现责任控制”的逻辑。然而,上述观点存在理想成分,因为规则和条例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自由裁量权受到更大控制(Evans & Harris,2004),相反,增加的规则和程序等组织控制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街头官僚反而会利用规则间的张力扩大其自由裁量权(Maynard-Moody et al.,1990)。
(二)自由裁量权压缩与责任控制程度
持有“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随着时代发展而压缩”观点的学者总体建议适当放松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程度。20世纪80—90年代,西方掀起了以管理主义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此时,一派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极大推动了公共部门绩效测量与考核的应用,“控制型”文化占据主导,因此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被压缩甚至消失(Howe,1991;Harris,1996,1998;Hadley & Clough,1998)。若这一结论成立,则街头官僚责任控制问题将不再值得特别关注。在此基础上,这部分学者认为,街头官僚控制无须施加过大力度,也无需配置过多资源,只需维持原有组织的责任控制机制即可(Harris,1996,1998)。
其次,教师要尊重、信任学生,做到高度尊重学生。这种尊重和信任更多的是对于学生人格的尊重和学生能力的认可。在进行教学评价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学生的主观感受,更加注重鼓励和肯定学生,进而引导学生更有效地进行语文学习。这样才不会打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影响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学生才不会出现厌学的情绪。以生本教育理念为指导进行教学评价,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语文课堂教学策略才能发挥效用。
进入21世纪,公共组织设定了更多责任控制机制,这实际是为了回应民主需求和提高整体治理能力。这一时期,尽管不占主流,但一派学者仍然坚持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缩小乃至消亡的观点。托尼·埃文斯(Tony Evans)和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Evans & Harris 2004)在研究社会工作中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后指出,自由裁量权本身没有“好”或者“坏”的属性,它应当被视为不同程度和级别的决策自由,因此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受制于具体情境,并存在缩小趋势。朱亚鹏和刘云香(2014)指出,街头官僚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执行制度环境等,只具有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此外,不少学者强调管理主义下,社会工作领域中的街头官僚受到了管理权力和制度机制的强烈约束,其自由裁量权不断削减(Jones,1999;Lymbery,2000)。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认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程度应当予以适当放松,因为过多的规则和制度反而会扩大本已被压缩的自由裁量权(Evans & Harris,2004)。此外,一部分学者注意到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电子政务的普及,部分街头官僚逐步走向网络这一虚拟空间,成为屏幕官僚和系统官僚(Bovens et al.,2002;Wastell et al.,2010)。对此,一派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加强对街头官僚实时、实地监控提供了可能,这直接压缩了其自由裁量权(Bovens & Zouridis,2002;Busch & Henriksen,2018)。
综上,20世纪9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在管理主义的影响下逐步缩小。然而,这一观点忽视了新公共管理运动造成政府部门“碎片化”的后果,即不同部门在政策制定时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性——这导致处于执行末端的街头官僚时常面临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Hjörne et al.,2010),增强了他们运用自由裁量权化解工作困境的意愿。进入21世纪,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公众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具有更大话语权,因而公众参与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Sager et al.,2014;Abbo et al.,2015)。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参与并不必然压缩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公众与他们实际并不对等,公众往往无法选择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线官僚。究竟如何解决二者间的 “不对等性”,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此外,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街头官僚的实时、实地监控提供了可能,从而压缩了其自由裁量权(Bovens & Zouridis,2002)。
(三)自由裁量权扩张与责任控制程度
3.本质及表现形式:自主选择权及政策再制定
21世纪以来,尽管公共部门愈来愈强调回应性和治理能力,但大部分学者强调这并没有压缩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有研究认为居于一线的街头官僚尽管受到组织规则约束与控制,但工作的环境与特点使得他们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Maynard-Moody et al.,2000)。他们还发现,随着组织的规则与程序日趋增加,规则之间、程序之间可能产生冲突,而街头官僚必须实时做出判断与选择,这意味着自由裁量权成为必须。有学者进一步强调新公共管理运动导致规则目标的模糊,街头官僚在矛盾的目标间进行选择与判断时,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即自由裁量权(Hjörne et al.,2010)。因此,加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程度是公共管理改革的方向。由于信息技术在政府中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工作“场域”,使实际处于一线的街头官僚走向了电子屏幕和操作系统之后,其可能利用专业技术逃避公众和主管部门的监督,并有可能通过操纵系统“隐蔽”地为自己牟利——这意味着街头官僚的自身自由裁量权不减反增(Wastell et al.,2010;Hansen et al.,2018)。
概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尽管主流声音是“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因管理主义而被压缩,可放松对其责任控制的程度”。然而,仍然有不少学者从实证的角度予以反驳。遗憾的是,尽管实证上多有成果,但在街头责任控制理论建构上少有突破。进入21世纪后,随着“屏幕官僚”和“系统官僚”的产生,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屏幕和系统操控的隐蔽性,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扩张,因此强调对其责任控制程度的加强。然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减少了基层政府与街头官僚、街头官僚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且实现了对街头官僚“随时随地”监控,因而其自由裁量权可能受到压缩(Busch & Henriksen,2018)。面对上述两种可能性,学界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方可确证。
(四)责任控制程度论争小结
纵观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时代流变及其引发的责任控制程度之争,学界普遍认同街头官僚的核心特征是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同时,街头官僚基于自身利益和生存策略,具有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街头官僚是独一无二的”(Scott,1997),街头官僚工作在第一线,连接着国家、社会与市场,掌握着民众所需要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代表着政府,极大地影响着政府合法性的构建,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责任控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外,街头官僚直接参与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又是政策再制定的“始发处”,政策能否高效、准确地执行事关政策本身的成败,加强对其责任控制是保证政策通畅执行的必要手段。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存在时代流变存在争论,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管理主义压缩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过于理想化,且忽视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部门“碎片化”问题;第二,依托实证研究证明自由裁量权扩大的学者少有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建构;第三,街头官僚与公众之间“不对等性”问题如何解决、信息技术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到底如何作用,仍然有待研究。总之,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程度论争尽管持续不断,但其中的研究脉轮相对清晰。就是否加强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研究上,呈现“加强控制为主导—适当放松控制出现—二者并立”的特点(见表1)。
表1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程度研究脉络表
自由裁量权流变方向自由裁量权流变原因责任控制程度的主张传统公共行政时期(1955—1990)①相对稳定,无流变组织控制能力不足加强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1990—2000)“自由裁量权逐渐缩小”占主流管理主义强化组织控制能力“适当放松控制”占主流①街头官僚理论产生于1977年,但早在1955年,彼得·布劳(Peter M. Blau)(Blau,1955)已开始对相关议题展开研究,只是当时布劳把街头官僚称为“政府一线工作者”。故本研究把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议题的起始时间定为1955年。
自由裁量权流变方向自由裁量权流变原因责任控制程度的主张治理理论兴起与扩展时期(2000—)“自由裁量权缩小与扩大”的观点并行信息技术改变街头官僚工作的“场域”加强控制与适度放松并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街头官僚责任控制:路径论争
相比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时代流变及其引发的责任控制程度之争,关于其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和如何予以控制而引发的责任控制路径论争在学界产生了更为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学界普遍承认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但不代表在合法性上达成共识。在探讨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实现议题上,自由裁量权的褒贬之争成为核心:若忧虑自由裁量权的负效应,研究者则主张“惩罚-规制”型控制的路径;若认可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价值,研究者倾向于采取“激励-引导”型控制的路径。
(一)自由裁量权的“魔鬼”形象与责任控制路径
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为“魔鬼”的研究者主要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指出作为代理人的街头官僚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会利用自由裁量权扭曲政策,为自身牟利(Lipsky,1980;Koch,1986;Meyers et al.,1998;Corazzini,2000;Smart,2018)。从研究脉络看,20世纪70—8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街头官僚往往依赖自由裁量权满足自利需要:应对压力的生存和自保策略,即通过选择服务对象和公共服务种类,规避风险(Satyamuri,1981);牟利行为,即对委托人和公众需求进行“分类”,从而重点完成可以带来预期收益的任务(Brintnall,1981;Mladenka,1981)。20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通过案例研究证实他们对自由裁量权忧虑的必要性(Fineman,1998;Mayers et al.,1998)。例如,威尔士 (Wells,1997)指出,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英国的社区政策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会选择性执行易于满足考核指标的任务和政策,在表面上形成高效为民的效果。2000年以来,不少学者延续了李普斯基的基本认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负面效应占主导。具言之,街头官僚通过自由裁量权或随意增减公民服务需求(Corazzini,2000),或选择性提供服务(Dunér & Nordström,2006;Dorch,2009),或扭曲政策目标和对上级“抗命”(Kaler,2001;张力伟,2018;朱亚鹏、刘云香,2014),或勾结罪犯(Smart,2018),或操纵程序与系统(Bovens & Zouridis,2002;Wastell et al.,2010;刘祺、朱林彬,2018)。
基于此,在责任控制的议题上,这一派学者主张“惩罚-规制”型控制的路径,即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管理自由裁量权是街头官僚问题的核心所在”(Lipsky,198 11)。理查德·威瑟利(Richard Weatherley)和李普斯基(Weatherley & Lipsky,1977)在指出管理者与街头官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认为增加工作人员能够“分解”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减少他们的对抗行为。然而,他后来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工作人员的增加永远赶不上顾客需求的增加”(Lipsky,198 11)。受传统“命令-控制”模式的影响,强调严格的层级控制和加强组织控制成为众多学者的选择(Sabatier & Mazmanian,1979;Edwards,1980;Linder & Peters,1987)。受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研究者和实践者倾向于通过严格的绩效指标和考核系统加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Howe,1991;Harris,1998;Hadley & Clough,1998)。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推广与电子政务的普及,严密的技术监控手段加强了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Harris,1998;Bovens & Zouridis,2002)。马克·鲍文斯(Mark Bovens)和史达罗斯·邹里迪斯(Stavros Zouridis)(Bovens & Zouridis 2002)认为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得街头官僚“与公民直接接触”的特征消失,他们的个人偏好对政策执行产生的影响被压缩,进而加强了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
综上,基于自由裁量权的“魔鬼”形象,学者们总结出街头官僚滥用权力的诸多表现,并指出必须通过“惩罚-规制”型责任控制路径予以解决。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派学者过分强调街头官僚的“经济理性人”的面向,忽视了街头官僚作为政府人员所具备的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否定了自由裁量权促进其履行职责的功能。同时,依赖“惩罚-规制”型控制路径,必然需要增设更多规则和程序。若这些程序和规则缺乏协调与统一,反而会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提供条件(Maynard-Moody et al.,1990)。
第五,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受到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因素的影响。各类外围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技术等)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酵产生作用,从而使得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受到各类外围因素的影响。
(二)自由裁量权的“天使”形象与责任控制
坚持自由裁量权“天使”形象的学者也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强调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对政策顺利执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Elmore,1979;Goodsell,1981)。从研究进程看,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派学者强调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实际受到诸多限制,被滥用的空间并不大(Goodsell,1981)。20世纪90年代,部分学者开始警惕管理主义过分强调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并认可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价值:提升政策执行效果和政府回应性(Maynard-Moody et al.,1990;Maupin,1993;刘升,2018);提升组织活力,实现组织变革((Maynard-Moody et al.,1990;Maynard-Moody & Leland,2000);提升履职积极性,实现组织和个人价值(Mayers,1998)。21世纪以来,研究者对传统街头官僚理论展开批判,其批判点有二:过分强调街头官僚的“国家代理人”角色;把街头官僚视为无差别的个体。由此,学者们着重从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层面证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积极价值:“公众代理人”范式转换,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其成为基于委托人服务需求进行公正判断并优化服务的负责任官员(Maynard-Moody & Musheno,2000);街头官僚间存在巨大个体差异,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其挑战自我,履职担责,获得认可(Maynard-Moody & Musheno,2000;Hagelund,2010;Harrits & Møller,2014);维护法律和秩序(Akosa & Asare,2017)。更进一步,有学者指出当前研究并没有发展出自由裁量权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他们因此构建了客户意义(Client Meaningfulness)和执行意愿(Willingness to Implement)二维框架,通过对1 300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实证调查证明了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意义(Tummers & Bekkers,2014)。
基于此,研究者认为“激励-引导”型控制路径是实现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有效形式。早期研究者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责任控制路径,但是对“惩罚-规制”型控制路径予以了批判(Lipsky,1977,1980)。不少学者指出,企图以加强组织控制来防范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切实际,这将迫使街头官僚的“再决策”行为由公开走向秘密,反而加大责任控制的难度(Brown,1988;Hill,2003;Tummers & Bekkers,2014)。科赫(Koch,1986)率先提出官僚机构制定执法行为手册和规范,引导街头官僚发挥自由裁量权的积极作用。20世纪90年代,部分学者主张权力下放,扩大街头官僚在政府绩效指标设定的话语权,将他们纳入政策制定的议程中,从而规规避权力滥用问题(Maynard-Moody et al.,1990;Maupin,1993)。进入21世纪,研究者一方面对管理主义主张的对街头官僚“授权”进行验证(Eisinger,2002),另一方面反思李普斯基“国家代理人”模式的街头官僚理论,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采用的“命令-控制”模式压抑了街头官僚的积极性,反而不利于塑造其责任意识(Brodkin,2008)。因此,学者建议通过立法保障街头官僚“公众代理人”的身份(Maynard-Moody & Musheno,2000),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提供咨询的方式引导其正确行使权力,实现对其责任控制 (Hill,2003)。随着治理理论的扩展,公民权和公民主体地位被视为规范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依托(Sager et al.,2014;Abbo et al.,2015)。传统的公民非自愿性的观点开始被摒弃,信息不对称问题也由广泛的公众参与监督得到缓解,自由裁量权将很有可能由“魔鬼”转变为“天使”(Tummers & Bekkers,2014;Bartels,2017)。
二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总体数量不高,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审理难点问题没有改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难以获得支持,新的争议领域时有出现;环境行政诉讼审理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如2017年法院审理的环境行政诉讼二审案件中,“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与“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分别占比13.21与6.13,接近全年审理的二审案件的20%。
基于自由裁量权的“天使”形象,学者们总结出自由裁量权对政策执行、政府回应性、组织变革、组织和个人目标实现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主张“激励-引导”型责任控制机制。尽管这一派学者认识到街头官僚的“公众代理人”身份,但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街头官僚的“国家代理人”身份,过于相信街头官僚个人的品质、责任感等个人特质,忽视了他们“经济理性人”的面向。同时,街头官僚本身就面临着资源短缺、工作压力大、工作环境复杂等问题,他们很可能因此极力运作自身的自由裁量权以求自保,因此激励、引导等柔性方式在其责任控制议题上是否奏效,令人疑虑。
(三)责任控制路径论争小结
在街头官僚责任控制路径的议题上,研究者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分歧巨大,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沿袭李普斯基的观点,基于“国家代理人”理论范式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予以质疑甚至否定,因而强调“惩罚-规制”型责任控制路径;另一派基于“公众代理人”理论范式肯定了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价值,因此主张“激励-引导”型责任控制路径。不过,上述两派观点存在较大缺陷。前者偏于强调街头官僚理性、自利的一面,否定了其公共服务动机,且所依赖的“惩罚-规制”路径因增设规则和程序反而会扩大其自由裁量权;后者过分强调街头官僚的公共服务动机,忽视了其逐利的一面,且他们本身面临资源短缺、工作环境复杂等困境,以激励和引导等柔性方式实现责任控制目标,不具可持续性。时至今日,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依旧存在巨大争议。总体而言,企图全面描绘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的“轮廓”是困难的,但是该领域研究仍然呈现较为明显的脉络(见表2)。
外伶仃岛全年污水排放系数为0.320~0.498,其中7月份排放系数最高,4月份排放系数最低,全年平均值为0.425;东澳岛全年污水排放系数为0.267~0.519,其中7月份排放系数最高,12月份排放系数最低,全年平均值为0.386。海岛污水排放系数低于大陆城市生活污水排放系数,一方面由于海岛用水去向多,船上污水、海产品加工废水及娱乐废水难以进入管网收集;另一方面海岛地质为基岩,污水管网铺设困难,一些散户和偏远的商户产生的污水并未接入收集管网。因此在海岛污水处理体系规划中,要着重考虑海岛地质地形、居民区分布以及远期建设规划,合理布置污水管网。
dSPACE仿真系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实现快速控制原型和硬件在回路中的仿真,是由德国dSPACE公司开发的一套研发测试工作平台。主要用于控制系统的开发。
表2街头官僚责任控制路径研究脉络表
对自由裁量权的态度街头官僚工作“场域”责任控制路径传统公共行政时期(1955—1990)批判与否定为主面对面互动;处于相对强势地位 “惩罚-规制”型为主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1990—2000)肯定与否定对立并存面对面互动;强势地位开始削弱 “激励-引导”型为主治理理论兴起与扩展时期(2000—)避开价值判断,关注影响因素部分转向虚拟世界;公民与街头官僚相对均势逐渐强调“服务对象”控制型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六、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前景展望
经过数十年的持续研究与发展,尽管街头官僚研究主要围绕自由裁量权而非责任控制,但基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框架,本文构建了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体系。在对街头官僚责任体系与控制机制进行论述后,论文分别从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起点、争议焦点、以“自由裁量权应该有多少”为核心的责任控制程度、以“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和如何控制”为核心的责任控制路径等方面一一展开述评。本文发现街头官僚责任控制议题仍取得了丰硕成果:责任体系包含科层制中的“对上负责”的和民主政治中的“对下负责”;责任机制包括科层组织的“内部控制”和来自社会公众等“外部监督”两类;责任控制研究起点为自由裁量权,其内涵为“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空间”,产生于街头工作特性抑或制度、组织约束不足,本质是“自主选择权”,表现形式主要是“政策再制定”;责任控制争论焦点为选择“加强控制,以惩罚为主”还是“弱化控制,以激励为主”。
近年来,多数研究者倾向于避开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性质之争,也不再过分纠结于其自由裁量权的时代流变,而是致力于研究影响街头官僚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因素。这一派学者的逻辑是:只要确认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影响因素,便可“从原因找方法”,为街头官僚责任控制开辟有效路径(Buffat,2015;Hunter et al.,2016;Baviskar & Winter,2017)。这种避开“主义”之争,直击核心(即责任控制议题)的研究模式拓宽了街头官僚的理论与实践。
然而,回顾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依然存在着不足。为促进该领域研究“知识积累”和“理论突破”,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应重视以下方面。
第一,街头官僚责任控制机制及方式整合研究。目前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研究避开了“主义”之争,选择了“从原因找方法”的进路,产生了丰硕成果,并可把它们归结为六大影响因素:制度、组织、技术、文化与伦理、公共服务动机、外部环境。由此,形成了制度控制(Scholz et al.,1991;Hupe & Hill,2007)、组织控制(Harris,1996,1998;Maynard-Moody et al.,2000;Brodkin,2008;Evans,2010)、技术控制(Busch & Henriksen,2018;Bovens & Zouridis,2002)、文化与伦理控制(Loyens & Maesschalck,2010;Rothstein & Stolle,2001)、公共服务动机塑造(Lipsky,1980;Moynihan & Pandey,2007)和外部环境优化(Weissert,1994;Scott,1997)六类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方式。尽管如此,但是上述研究往往在某一关键影响因素之下展开更加细致的研究,无法厘清各种责任控制机制与方式的组合、匹配关系,缺乏整全的理解和分析,遑论整合性理论框架(Tummers & Bekkers,2014)。刘焕等(2016)指出,综合考虑体制、组织、公众参与等多种因素影响可以更好解决目标偏差、政策执行不畅等治理难题。鉴于街头官僚面临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公共管理难题,对其责任控制决非依赖某一要素可以实现,因此本文认为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综合多种学科视角,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另一方面则需要在上述六大影响要素之上发展出整全的理论框架,把诸要素纳入系统分析中去,从而进一步厘清不同责任控制机制与控制方式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公共管理实践中街头官僚存在着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才可能得到进一步治理,从而使基层公共服务质量得以进一步提升。
第二,屏幕官僚和系统官僚的责任控制。随着电子政务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街头官僚从现实走向虚拟。尽管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到屏幕官僚和系统官僚问题(Bovens & Zouridis,2002;Wastell et al.,2010;Buffat,2015),但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仍然远远不足。特别是当街头官僚化身为屏幕官僚和系统官僚后,其自由裁量权的发挥空间究竟如何发展,聚讼不已,并无定论。尽管屏幕官僚与系统官僚不再直接面对公众,其价值偏好与个人判断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缩小,但他们依然可能利用专业技术设计为自己牟利的信息系统(Bovens & Zouridis,2002)。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普及实现了对街头官僚实时监控,为其责任控制提供了更多可能。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成为未来趋势,有待深入探讨。此外,就实践而言,屏幕官僚与系统官僚越来越贴近公众的日常生活,承担着重要的政策执行与公共服务职能。只有在理论上厘清其自由裁量权的变化方向,才可能指导基层政府设置有效的责任控制机制,从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第三,治理理论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影响。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实质强调公民权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性。这一背景下,街头官僚与公众同时成为治理的主体,两者间的“街头互动”,特别是公民权如何作用于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虽然尚不清楚,但更加值得关注(Abbo et al.,2015)。社会和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其政治权利成为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重要依托(Hupe & Hill,2007),对象控制(即服务对象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成为值得研究的新路径。同时,还有研究注意到社会资本、工作网络等要素对街头官僚工作的影响(Rothstein & Stolle,2001,Scott,1997)。实践中,公众参与成为公共生活愈发重要的议题,确定公民权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促进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强化公众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从而鞭策街头官僚忠实地履职尽责。
[40] 罗肖:《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122-155页。
第四,对中国而言,街头官僚理论本土适用性问题决定了责任控制研究的严谨性与可行性。受街头官僚理论的启发,我国学者纷纷借鉴和引入,并对其责任控制展开了研究,在城管执法、基层政策执行、警察执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成果(刘鹏、刘志鹏,2014;韩志明,2008,2010;颜海娜、聂勇浩,2013)。由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引入发端于西方的理论时,必须首先讨论其本土适用性问题。遗憾的是,大部分研究未深入讨论这一议题(董伟玮、李靖,2017)。鉴于此,首先,必须厘清中西方语境下街头官僚概念上的异同,把握其内涵与外延。李普斯基指出了西方语境下街头官僚是“在工作过程中直接参与公众互动,并且在工作执行中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公共服务者”(Lipsky,1983),其涵盖的范围除了低级政府工作人员,还包括教师、医生、社工、律师等。在中国,街头官僚的外延究竟是否应该包括上述群体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我国往往设置了市长信箱、市长热线和市长接待日等制度,市长实际也直面公众,这类群体是否也应纳入街头官僚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是街头官僚的角色形象问题。李普斯基(Lipsky,1977,1980)所提出的街头官僚属于中性概念,而我国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暗含贬义,把这一群体视为“目光短浅,追逐利益,变通执行”的“坏人”。尽管这与我国政府人员构成(数量庞大的“临时工”“合同工”)的现实境况有一定关系,但这与西方街头官僚的中性定义相悖。最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主要是西方政治体制下政策执行的产物,而中国的一线官员往往在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执行政策,且还受到严格的政党纪律约束,这种制度差异是否造成了中国街头官僚的特殊之处,并未受到学界重视,理应在未来进一步澄清。只有澄清上述三方面不足,我国学界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严谨的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基层治理和基层干部管理实践,也才能更好地与西方学界展开理论对话。
参考文献
陈那波、卢施羽(2013). 场域转换中的默契互动——中国 “城管” 的自由裁量行为及其逻辑. 管理世界,162-80.
崔卓兰、刘福元(2009).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 中国法学,73-84.
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德博拉·戈德曼·罗森布鲁姆(2002).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张成福等校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董伟玮(2018). 建立一种街头官僚的政治理论:主题演进、概念愿景与理论整合. 云南社会科学,226(6)43-52.
董伟玮、李靖(2017). 街头官僚概念的中国适用性:对中国街头官僚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探讨. 云南社会科学,26-33.
韩志明(2008).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公共管理学报,5(1)41-48.
韩志明(2011). 街头官僚及其行动的空间辩证法——对街头官僚概念与理论命题的重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08-115.
胡怀亮(2005). 街头官僚理论与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 兰州学刊,227-228.
刘焕、吴建南、徐萌萌(2016).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目标偏差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评论,9(1)151-171.
刘鹏、刘志鹏(2014). 街头官僚政策变通执行的类型及其解释——基于对 H 县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案例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101-105.
刘祺、朱林彬(2018). 信息时代街头官僚及其自由裁量权的变革与挑战. 管理世界,179-181.
刘升(2018). 街头行政执法中的 “平衡” 机制研究——以城管执法为例.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63-77.
颜海娜、聂勇浩(2013). 基层公务员绩效问责的困境——基于 “街头官僚” 理论的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58-61.
叶娟丽、马骏(2003).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6(5)612-618.
尹文嘉(2009). 从街头官僚到街头领导:一个解释框架.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6-32.
张力伟(2018).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街头官僚素描——基于 L 省 K 市基层环境治理的田野调查. 地方治理研究,11-29.
周定财(2010). 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考察. 湖北社会科学,30-34.
朱亚鹏、刘云香(2014).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以C市城市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9-168.
Abbo, U., Bello, A. A., Bello, M. & Zain, Z. B. M. (2015). Street Level Politics, Local Governance and Local Power Structure in Northern Nigeria: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ublicPolicy&AdministrationResearch, 5(12)80-84.
Akosa, F. & Asare, B. E. (2017).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In Farazmand, A. Ed. GlobalEncyclopediaof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Policy,andGovernance. Lond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Bartels, K. P. (2017). A Relational Grounding for (Urban) Governance: Street-Level Practices of Responsive Improvisation and Practical Change. 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77(3)466-469.
Baviskar, S. & Winter, S. C. (2017).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s Individual Policymak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and Coping Behavior toward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Youth. 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 20(2)316-353.
Blau, P. M. (1955). TheDynamicsofBureaucracy:AStudyofInterpersonalRelationsinTwoGovernmentAgenc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vens, M. & Zouridis, S. (2002). From Street-Level to System-Level Bureaucracies: 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Constitutional Control. 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62(2)174-184.
Brehm, J. O. & Gates, S. (1999). Working,Shirking,andSabotage:BureaucraticResponsetoaDemocraticPublic.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rintnall, M. (1981). Caseloads, Performance, and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UrbanAffairsReview, 16(3)281-298.
Brodkin, E. Z. (1997). Inside the Welfare Contract: Discre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State Welfare Administration. TheSocialServiceReview, 71(1)1-33.
Brodkin, E. Z. (2008). Accountability in Street-Leve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 31(3)317-336.
Brown, M. K. (1988). WorkingtheStreet:PoliceDiscretionandtheDilemmasofRefor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uffat, A. (2015).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E-Government. PublicManagementReview, 17(1)149-161.
Busch, P. A. & Henriksen, H. Z. (2018). Digital Discre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ICT and Street-Level Discretion. InformationPolity,(Preprint)1-26.
Corazzini, K. N. (2000). Case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Go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Discretion and Client Interpretation. HomeHealthCareServicesQuarterly, 18(3)81-96.
Davis, K. C. (1969). DiscretionaryJustice:APreliminaryInquiry. Baton Rouge: LSU Press.
Dorch, E. L. (2009). The Implications of Policy Pre-Post Test Scores for Street-Level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JournalofHealthandHumanServicesAdministration, 32(2)139-163.
Dunér, A. & Nordström, M. (2006). The Discretion and Power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 Example from Swedish Municipal Eldercare. EuropeanJournalofSocialWork, 9(4)425-444.
Edwards, G. C. (1980). ImplementingPublicPolicy. 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Eisinger, P. (2002).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mong Street-Level Food Assistance Programs. NonprofitandVoluntarySectorQuarterly, 31(1)115-130.
Elmore, R. F. (1979). Backward Mapping: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Decisions. 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 94(4)601-616.
Evans, T. (2010). Professionals, Managers and Discretion: Critiquing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TheBritishJournalofSocialWork, 41(2)368-386.
Evans, T. & Harris, J. (2004).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Social Work and 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Discretion. TheBritishJournalofSocialWork, 34(6)871-895.
Fineman, S. (1998).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trol. OrganizationStudies, 19(6)953-974.
Goodsell, C. T. (1981). Looking Once again at Human Service Bureaucracy. TheJournalofPolitics, 43(3)763-778.
Hadley, R. & Clough, R. (1998). CareinChaos:FrustrationandChallengeinCommunityCare. London: A & C Black.
Hagelund, A. (2010). Dealing with the Dilemmas: Integration at the Street-Level in Norway. InternationalMigration, 48(2)79-102.
Hansen, H. T., Lundberg, K. & Syltevik, L. J. (2018). Digitalization,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Welfare Users’ Experiences. 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 52(1)67-90.
Harris, J. (1996). HardLabourinaColdClimate:DevelopmentsintheSocialWorkLabourProcess. In Fourteenth Annual International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ston, Birmingham.
Harris, J. (1998). Scientific Management, Bureau-Professionalism, New Managerialism: The Labour Process of State Social Work. BritishJournalofSocialWork, 28(6)839-862.
Harrits, G. S. & Møller, M. Ø. (2014). Prevention at the Front Line: How Home Nurses, Pedagogues, and Teachers Transform Public Worry into Decisions on Special Efforts. PublicManagementReview, 16(4)447-480.
Hill, H. C. (2003). Understanding Implementation: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Resources for Reform. 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 13(3)265-282.
Hjörne, E., Juhila, K. & Van Nijnatten, C. (2010). Negotiating Dilemmas in the Practices of Street-Level Welfare Work. 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19(3)303-309.
Howe, D. (1991).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hape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Davies, M. Ed. TheSociologyofSocialWork. London: Routledge.
Hughes, A. & Condon, L. (2016).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Nursing: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Experiences of Student and Novice Health Visitors. PrimaryHealthCareResearch&Development, 17(6)586-598.
Hunter, C., Bretherton, J., Halliday, S. & Johnsen, S. (2016). Legal Compliance in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 Study of UK Housing Officers. Law&Policy, 38(1)81-95.
Hupe, P. & Hill, M. (2007).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Publicadministration, 85(2)279-299.
Jones, C. (1999). Social Work: Regulation and Managerialism. In Exworthy, M. & Halford, S. Eds. ProfessionalsandtheNewManagerialisminthePublicSecto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Kaler, A. & Watkins, S. C. (2001). Disobedient Distributors: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Would-Be Patrons in Community-Base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Rural Kenya. StudiesinFamilyPlanning, 32(3)254-269.
Koch, C. H. (1986). Effective Regulatory Reform Hinges on Motivating the “Street Level” Bureaucrat. AdministrativeLawReview, 38(4)427-449.
Linder, S. H. & Peters, B. G. (1987). A Design Perspective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Fallacies of Misplaced Prescription. ReviewofPolicyResearch, 6(3)459-475.
Lipsky, M. (1980). Street-LevelBureaucracy:DilemmasoftheIndividualinPublicServi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Loyens, K. & Maesschalck, J. (2010).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Existing Models Reconsidered. Administration&Society, 42(1)66-100.
Lymbery, M. (2000). The Retreat from Professionalism. In Malin, N. Ed. Professionalism,BoundariesandtheWorkplace. London: Routledge.
Maier, C. & Winkel, G. (2017). Implementing Nature Conservation through Integrated Forest Management: A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Perspective on the German Public Forest Sector. ForestPolicyandEconomics, 814-29..
Maupin, J. R. (1993). Control, Efficiency, and the Street-Level Bureaucrat. 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 3(3)335-357.
Maynard-Moody, S. & Leland, S. (2000). Stories from the Front-Lines of Public Management: Street-Level Workers as Responsible Actors. In Brudney, J. Ed. AdvancingPublicManagement:NewDevelopmentsinTheory,Methods,andPractic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Maynard-Moody, S., Musheno, M. & Palumbo, D. (1990). Street-Wise Social Policy: Resolving the Dilemma of Street-Level Influence and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TheWesternPoliticalQuarterly, 43(4)833-848.
Maynard-Moody, S. & Musheno, M. (2000). State Agent or Citizen Agent: Two Narratives of Discretion. 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 10(2)329-358.
Meyers, M. K., Glaser, B. & Donald, K. M. (1998). On the Front Lines of Welfare Delivery: Are Workers Implementing Policy Reforms?. 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 17(1)1-22.
Meyers, M. K. & Vorsanger, S. (2007).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 Rabin, j., Hildreth, W. B. & Miller, G. J. Eds. TheHandbookofPublicAdministration. Boca Raton: CRC/Taylor & Francis.
Mladenka, K. R. (1981). Citizen Demands and Urban Services: The Distribution of Bureaucratic Response in Chicago and Houston. 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25(4)693-714.
Moynihan, D. P. & Pandey, S. K. (2007).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s in Foster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67(1)40-53.
Prottas, J. M. (1978). The Power of the Street-Level Bureaucrat in Public Service Bureaucracies. UrbanAffairsReview, 13(3)285-312.
Rothstein, B. & Stolle, D. (2001). SocialCapitalandStreet-LevelBureaucracy:AnInstitutionalTheoryofGeneralizedTrust. In ESF Conference Social Capital: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xeter, UK September15-20.
Sabatier, P. & Mazmanian, D. (1979). The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 Guide to Accomplishing Policy Objectives. PolicyAnalysis, 5(4)481-504.
Sager, F., Thomann, E., Zollinger, C., Van der Heiden, N. & Mavrot, C. (2014).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New Modes of Governance: How Conflicting Roles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wiss Ordinance on Veterinary Medicinal Products. PublicManagementReview, 16(4)481-502.
Satyamuri, C. (1981). OccupationalSurvival:TheCaseoftheLocalAuthoritySocialWork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cott, P. G. (1997). Assessing Determinants of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An Experiment in Street-Leve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 7(1)35-58.
Scholz, J. T., Twombly, J. & Headrick, B. (1991). Street-Level Political Controls over Federal Bureaucracy.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85(3)829-850.
Smart, A. (2018). The Unbearable Discretion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Corruption and Collusion in Hong Kong. CurrentAnthropology, 59(S18)S37-S47.
Tummers, L. & Bekkers, V. (2014).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the Importance of Discretion. PublicManagementReview, 16(4)527-547.
Wade, H. W. R. & Forsyth, C. F. (2000). Administrative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stell, D., White, S., Broadhurst, K., Peckover, S. & Pithouse, A. (2010). Children’s Services in the Iron Cage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the Spectre of vejkism.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19(3)310-320.
Weatherley, R. & Lipsky, M. (1977).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mplementing Special-Education Reform. HarvardEducationalReview, 47(2)171-197.
Weissert, C. S. (1994). Beyond the Organ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and Personal values on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Responsiveness. 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 4(2)225-254.
Wells, J. S. (1997). Priorities, “Street Level Bureaucracy” and 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Team. Health&SocialCareintheCommunity, 5(5)333-342.
Westley, W. A. (1970). ViolenceandthePolice:ASociologicalStudyofLaw,Custom,andMorality(Vol. 2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Van Maanen, J. (1973). WorkingtheStreet;ADevelopmentalViewofPoliceBehavior(No.681-73.).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Vinzant, J. C., Denhardt, J. V. & Crothers, L. (1998). Street-LevelLeadership:DiscretionandLegitimacyinFront-LinePublicService.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9)05-0176-22
甘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戴亦欣副教授和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海柱副教授的意见。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责任编辑:庄文嘉
标签:官僚论文; 街头论文; 自由论文; 裁量权论文; 责任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5期论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