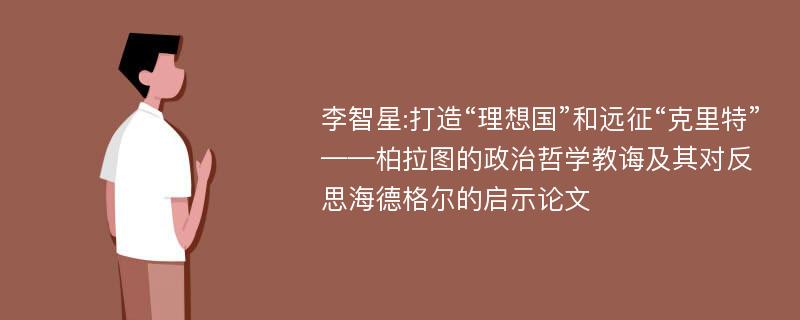
[摘 要]施特劳斯的柏拉图政治哲学阐释启发了关于海德格尔政治时刻的反思路径:海德格尔体现出《理想国》哲人王式的激进政治实践,即以哲学为原则对现实政治进行重新奠基,从而导致一种哲学僭政。为战胜现实中的虚假,保卫真理的哲人要求掌握权力是可理解的,但哲人的政治行动不应无视人类自然的道德秩序。《法篇》里的“克里特”立法展现了与大地上既有秩序相调和的哲人立法者。参照《法篇》的古典教诲,海德格尔政治审慎上的缺失将得到进一步揭示。
[关键词]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理想国》;《法篇》;僭政
海德格尔全集的最末三卷,即他写于1931年至1941年间的三册《黑色笔记本》(The Black Note)出版后,旋即在西方学界引起轩然大波。《黑色笔记本》的内容据称基本证实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与其纳粹反犹的政治立场之间的确具有学理上的内在关联。由此,就像意大利哲学家多梅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所述:“海德格尔的笔记被称为《黑色笔记本》,这是按照其封皮的颜色命名的;现在我们发现这些笔记首先在内容上是黑色的。”《黑色笔记本》的面世对海德格尔身后的名誉无疑十分不利,这一难题让学界内海德格尔的拥护者们感到相当棘手;但是在另一方面,《黑色笔记本》所揭示的问题,即海德格尔的思想跟纳粹及反犹之间存在某种难分难解的内在联系,对于施特劳斯学派的成员们来说却并非不可思议,根据他们的看法,沿着现代性政治哲学的思路,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其来有自,他其实分享了现代政治哲人思想史上共有的精神倾向,这一精神倾向据说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我们当然不必局限于施特劳斯学派的一家之言,在施特劳斯学派以外,人们仍然有足够的理论资源与能力去充分消化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不过对施特劳斯学派的意见加以必要的了解和分析,亦不失理论参考上的价值。本文的任务即尝试介绍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在有关海德格尔哲学与政治之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意见,对于丰富学界围绕《黑色笔记本》的辩论话语或许也是有益的。
(4)加强数据管理,实现信息共享。构建多级地下水数据库系统,包括:基础信息数据库、实时监测信息数据库、整编数据库、分析成果数据库、试验信息数据库、图形与空间数据库[14]等。同时考虑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对地下水环境治理工作也必然会加快步伐,多部门间联动磋商机制正在形成,建立一个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势在必行[15],不仅服务于国土资源部门,也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更好地为政府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也可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
受论题以及论述的目标所限,本文主要透过施特劳斯学派之眼对海德格尔思想进行阐发,因此并未能充分回应海德格尔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及展开其
他阐释的可能性,这也许是本文写作的某种遗憾之处(1)在施特劳斯那里,海德格尔哲学代表着极端虚无主义的哲学形式,与此相异趣,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中超克虚无主义的深刻的思想努力,可参见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285页;张志扬:《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底海德格尔》,载萌萌学术工作室编,《哲学、科学、神学诸意识形态》,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168页;贾冬阳:《“之-间”:海德格尔探问“诗的本质”》,载贾冬阳编,《思想的临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0-125页。。
一、作为“哲人王”的海德格尔?
跟施特劳斯一样,海德格尔也是一位古典学素养极深的哲人,通过诠释古典文本,他向世人传达着他对存在(Sein)迷踪的追思。柏拉图的《理想国》同为施特劳斯和海德格尔所诠释过,二人当然是采取截然有别的运思路径。根据海德格尔:
罗璨璨(1994—),女,福建仙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岩土工程数值模拟、大坝与基础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不过,对苏格拉底来说更为迫切的是,如何利用和转化这种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来引导青年走向哲学,因为苏格拉底知道,灵魂正义只有在哲学的生活中(而非在政治的生活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在修辞上,苏格拉底首先匆忙地在个体的灵魂生活问题和公共的政治生活问题之间建立联系,以顺应谈话对象当下的政治关切意向。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类比关系,即个体灵魂与城邦秩序之间平行对应的关系,以此让灵魂生活问题过渡到政治生活问题。这一类比为苏格拉底讨论其城邦政治学乃至探究理想的城邦政治形式奠定了出发点和基调,可是,这一类比本身是极成问题的。个体灵魂内部的各部分一一对应于城邦政制秩序内部的各部分,这导致城邦的形态呈现出机械的、几何学式的抽象变形,与城邦真实的政治生理学结构显然不相符。柏拉图有意为苏格拉底的这一类比论调在字里行间铺设了重重疑点,这直接暗示了灵魂生活与政治生活其实并不对称[11]2-15。对称性假设具有修辞策略上的考虑,因为苏格拉底意欲将灵魂正义问题最后引向哲学的沉思生活,但他此时则不得不照顾到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两位活在城邦中的青年公民的政治意向及政治关怀。这两位青年尽管对现实失望,但仍然对城邦政治本身怀有期求,两位青年对话者的政治意向是苏格拉底所必须直面与回应的。苏格拉底所认肯的灵魂正义的满足(即诉诸哲学沉思的生活)根本上超越城邦、超越政治,但是如果不首先充分顾及城邦政治的此在性,苏格拉底的教导便不易为身为城邦公民的对话者们所认可,这令人联想起城邦对他素来的怀疑倾向。因此,灵魂—城邦对应关系论相当于为他提供了某种修辞掩护。柏拉图更愿意留下线索以暗示自身真实的意思,即城邦政治学不外乎是其个体灵魂学的外衣(就其论述的最终目的而言,他终究要丢弃这一件外衣)。实情是城邦政治与个体灵魂根本不对等,苏格拉底所谈论的乃是一种被刻意扭曲了的城邦政治,“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理想国》,462d以上),可是国家根本不可能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个体人格,因而,苏格拉底探讨建立“最好的国家”,其真诚性相当可疑。这最终服务于苏格拉底的教育主旨,即个体灵魂生活正义的保证,应绕过对城邦公共政治生活的幻想,而回到灵魂生活自身,抵达一条真正的“灵魂之路”,即只能诉诸个体私人的内在生活,在纯粹的言辞活动里和在心中实现正义(《理想国》,592a以上;592a-b)。苏格拉底净化了青年们的政治理想主义激情,并将它升华为对哲学的爱欲。就此而论,《理想国》的教诲最终高于政治,关于哲人王为打造“最好的国家”而建立疯狂僭政的描述,实质只起到一种反讽修辞的作用。
洞穴的拱顶表示天空的拱顶。人们生活在这个拱顶下面,依赖于大地并且与大地维系在一起。在这里围绕和关涉到人的,对人而言就是“现实事物”,亦即存在者。在这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中,人们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在家中”,并且在这里找到了依靠。[1]247
柏拉图洞穴比喻中所叙述的故事描绘出现在和将来依然在由西方所烙印的人类历史中真正发生的事件的景象:人在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之本质意义上根据“理念”来思考一切存在者,并且根据“价值”来估价一切现实。唯一的和首要的决定性事情,并非何种理念和何种价值被设定了,而是人们根本上是根据“理念”来解释现实,根本上是根据“价值”来衡量“世界”[1]274-275。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尽管是反柏拉图主义的,但却继承了“从哲学上奠定政治”的“柏拉图式的要求”,后者在《理想国》中也就是哲人王式的缔造一个按照哲学建立起来的国家的要求(《理想国》,429a以上)(4)施特劳斯在一篇题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讲演稿中曾概要地梳理了现代性政治哲人的思想史脉络,其化用柏拉图《理想国》关于哲人建国的“三个浪头”这一比喻叙述,似乎是在暗示现代性的演进历史跟《理想国》中哲人当王、并以哲学作为根基的立法创制息息相关。施特劳斯还认为,第三波现代性政治哲学浪潮的实践结果被证明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参见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2-96页。。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施特劳斯思想的关键启示之一,在于揭示了哲学与政治二者间存在深刻的异质性:追随“绝对的”真理或知识的哲学与人类既有的文明道德习俗(nomos)在原则上包含冲突,前者属于知识,后者则属于意见,而一旦形而上学家(或哲人)以哲学作为基础展开建立国家的政治行动,就可能产生一种政治上激进的危险性,即对人类世俗的文明道德法则形成一种无视或公开挑战,从而演变为哲学的僭政政治(tyranny)。根据《理想国》,哲人王以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真理为标准宰制城邦的一切,为了净化城邦并永葆城邦的纯洁,他必须诉诸秘密驱逐与屠杀的残暴清洗政策(《理想国》,459e;460c-d;461c-d;501a以下),以僭越大地上人类基本的道德法则为代价。为哲人所统治的最理想城邦同时也成为流血最多的恐怖僭政。《理想国》中的哲人王实际上成了最危险、最狂热的大革命家。而对身处30年代的海德格尔而言,他的严峻的政治时刻在哲学上同时也是存在自身的一个真理时刻,存在真理的历史展开运动被认为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它派送出一个有望扭转现代技术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美苏为代表)的新的世界命运时刻,德国人应该无条件地或“无情”地担负起这一命运时刻……正如梅耶斯(Horst Mewes)所说:“施特劳斯同情海德格尔的哲学狂热,但指责他无力看到哲学审慎的必要性,尤其是假如其哲学直接导致他本人误把纳粹政治当作存在之展现的一个新阶段。”[2]500而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则正是通过重新深入古典政治哲学经典的内在教诲而阐发哲学审慎的意义的,这种阐发恰好能与海德格尔形成某种论战性关系。
惟在洞穴中“依赖于大地并且与大地维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中”,人方感觉到自己“在世界上”“在家中”,这些都是以洞穴以及人的洞穴生存为基本境域的。世界与大地之间的源初关联始终在洞穴的基本境域内发生,这与柏拉图脱离于这一洞穴境域的、作为纯粹被表象性的“理念”构成颠倒:告别“表象”式真理观而转向源初的存在真理观,也就是告别超离洞穴的“理念”而回归洞穴中的大地根基与围绕人的世界。
从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可见,285份IgM抗体阳性病例中,214例有病例信息,其中只有29例有免疫史,高达61.68%的病例无免疫接种史,无免疫史的病例中,8月~6岁组病例占53.03%(70/132),且均为非本县区户籍,这充分说明本地区麻疹免疫工作还存在较大漏洞,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的免疫接种工作,应该要加强对6岁以内儿童和22岁以上青年的麻疹免疫接种和信息管理工作,消除免疫空白地带,为早日实现消除麻疹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海德格尔将存在真理的视野从超越洞穴的“理念”转换到洞穴之中的大地与世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真理观。因为历史就是“连续的或同时存在的诸多洞穴”[4]458,存在之真理在洞穴之中显现自身,也就被“历史化”了。
施特劳斯谈及《林中路》时就断定,海德格尔哲学是“最极端的历史主义”形式[5]244(2)关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历史主义,可参见刘小枫:《海德格尔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而这和“海德格尔深深受惠于尼采”[6]424紧密相关。施特劳斯评论道:“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具有与马克思和尼采的历史哲学相同的结构……然而海德格尔离尼采比离马克思更近。”[7]101-102“最极端的历史主义”,意味着彻底删除超历史的永恒视角,存在之真理被迫在历史本身的纷乱运动中显现自身,因此,此在与“真理”显现的相遇就不得不立足在一个无根的境域里,“只有当我们真正地迷失——走入迷失中,我们才能撞到‘真理’”[8]13,5,23——“真理”是在无根据的历史生存境域中“撞到”的。存在真理在历史中的展现从而成为一种无端的命运性的派送,它以历史命运或特定历史时刻的方式而给予自身,而追随真理就意味着追随这神秘、深邃、不确定的命运,无条件地承受这种命运的被给予。对伴随存在真理涌现的历史命运的无条件承受必然导致“所有‘政治’观察便都成了存在自身出演的戏剧的方方面面”,而排除了“哪怕最为有限的人类责任”,包括人类对在世道德秩序的责任[2]507。对海德格尔30年代呼唤“无条件地”追随德国民族精神使命的号召,洛维特便指出,“这种历史使命的内容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方式才能使它变得显而易见,都不十分清楚。这种使命归根结底是由人们决心承受的‘命运’决定的。和这种命运的具体实质的不确定性相一致,海德格尔也强调了它的‘无情’”[9]77。此在需要学会的就是勇于真诚地、坚酷地直面这一无根据的历史化境域,直面“迷失中”的处境而勇敢地回应所遭遇的历史时刻,并做出决断,也就是冒险。存在真理的闪现闯入了历史与“世界”,在那里得到了开显,海德格尔鼓励人们踊跃响应存在真理在历史中的“示意”(Wink),它呼唤人们紧随历史事件(Ereignis)涌现的重大步伐,主动介入决断的振奋时刻……
海德格尔对历史行动的把握与动员,背后由其存在真理的形而上学本质所支配。因此,“在海德格尔及其努力中,国家社会主义就在他的基础存在论中得以确定下来”,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又称“弗莱堡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奠基于其存在哲学之上,是“借助于自身的基础存在论奠定”的[10]126-127;132-133。那便不难理解,“建立国家的活动”何以也会成为存在真理的一种开启自身之方式,一种关于国家建构的筹划也受存在真理自身的展开运动所规定了(3)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列举过存在真理的多种开启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国家的活动”。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45页。又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5页。。罗克莫尔(Tom Rockmore)在评论雅斯贝尔斯的《关于马丁·海德格尔的笔记》时进一步指出:
在紧张的复习阶段,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顺利或是不顺利的事情。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酸甜苦辣的期末复习之旅。
原本,苏格拉底企图为两位青年论证个人灵魂生活的正义何以值得追求,但是,格劳孔及阿德曼托斯之所以索求对灵魂正义的肯定性证明,乃是源于一种政治上特殊的愤懑情绪。他们厌恶雅典眼下庸俗的政治生活,在那里,正义者得不到幸福,灵魂不义的人却享受荣华富贵,为此,他们真正希望寻求的是一种合乎正义理想的政治生活制度,让灵魂正直的人在其中是有荣誉的和有福的,是受到肯定的,而不是遭受嘲笑的;这需要致力于改造眼下这一个为各种堕落趣味所败坏了的雅典。涌动在两位青年心中的是正直诚恳的政治理想主义志向。但苏格拉底却试图向他们证明,这样的理想恐怕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实际的政治生活几乎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摆脱它的不义。
以2016年3月~2017年3月准备接受放射治疗的首发头颈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病理切片确诊的头颈肿瘤患者;(2)患者全身状况良好、能完成治疗和研究;(3)新原发病例、无合并有其他恶性肿瘤及放化疗史。入选对象具有良好的依从性,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从《理想国》到《法篇》:柏拉图古典政治哲学教诲的复杂性
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健康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样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会走错的。
海德格尔提出了强烈的柏拉图式的要求,即从哲学上奠定政治,确切地说,借助于自身的基础存在论奠定国家社会主义。雅斯贝尔斯十分正确地把握了海德格尔(“让哲学变成现实”)这一要求的效应,但是,遗憾的是,他面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强调,海德格尔的处理态度与柏拉图的态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平行关系。[10]132-133
柏拉图的理念论以“表象之正确性”作为真理之本质,从根本上为西方日后的形而上学传统奠定了基础。它也被称为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对理念的正确意识与知觉,或关于理念之表象的陈述与断言的正确性,从此成了所有继起的西方理智、思维与理性的标准尺度。”[2]504在这种“表象”真理观的支配下,根据“理念”思考和解释一切存在者从本质上规定了基于“价值”(或意识形态)来表征一切现实和衡量世界的现代政治观,这一政治规定性在奠基于现代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世界政治体制中(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技术理性以柏拉图主义的表象观为基础,针对现代技术理性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批判其构建起世界的图像化,便溯源到上述柏拉图主义“表象”真理观:“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只要存在者没有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解释,那么,世界也就不能进入图像中,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图像。”[3]86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在集中于促逼着存在者之存在进入被精确表象化的状态中而遮蔽了存在本身的最深邃结构,柏拉图主义真理观以存在者的存在之被表象性作为真理的构成,整个世界作为被表象者而图像化,这都抑制了关于存在的真理的深刻内在性。而从海德格尔意义上源初的存在的真理之涌现出发,世界并不是“进入图像中”的,而是被保留在大地上,在大地之上开显自身。存在之真理通过世界和大地的相互关系而发生。世界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真理结构里命途殊异。但何为大地上之世界呢?海德格尔接过柏拉图洞穴比喻,写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理想国》(5)本文所引柏拉图著作汉译本均参见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理想国》的基本内容是苏格拉底与年轻人格劳孔及阿德曼托斯谈论如何构建正义的城邦政制形式,但如果从苏格拉底作为一名热爱纯粹沉思生活的哲人出发,他在何种意义上对于政治有兴趣则是成问题的。作为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在哲学上谈论城邦和在政治上谈论城邦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在苏格拉底的言辞中恰恰包含了一种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区分的自觉,而非简单肯定以哲学为基础去重建政治。
然而,如果认为“哲学超于政治”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含教诲的全部,却又并不准确。毋庸置疑,基于对现代种种政治乌托邦主义灾难的反思,我们更倾向于强调哲人相对于政治之外的思想独立性,但是,这一态度也可能影响到对《理想国》所反映的哲人的复杂面孔做选择性的呈现。《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固然调和并升华了年轻公民对政治现实的改良意向,即从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升华为超政治的哲学追求,可是,这是否就代表哲人果真对政治现实本身最终毫无激情?《理想国》详尽论证建立理想城邦所须采取的步骤与措施,如一概仅仅以服务于自我反讽的修辞目的来加以打发,恐怕也是非常不够的。在对《理想国》的诠释里,罗森(Stanley Rosen)就提醒读者不可忽视了苏格拉底的如下态度,即他“无一例外地承认他钦佩他的革命性政治建议,并以‘该城邦是可能的’这种极具保留意味然而又非常明确的主张结束”[12]5。也就是说,当苏格拉底尝试规划某种政治模型或政治计划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以一种认真的思想态度对政治现实试图进行某种干预。就此,苏格拉底对于介入政治的态度并非完全是不认真的,不认真与认真在他那里形成一种特殊的混合。
事实上,《理想国》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其内部始终包含着一种围绕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张力关系的微妙书写。苏格拉底一方面强调哲学生活相对于政治生活的优先性与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哲人并未回避自身对政治实践所具有的一种积极意志,且顺应此种意志,构拟了一场哲人充当立法者和统治者、并展开城邦缔造与治理的想象性实践。这表现出哲人既超越政治、又投入政治的双重性取向。在哲人那里,对纯粹真理的哲学爱欲和对实践的政治意欲实际彼此纠缠,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理想国》教诲中的复杂品质。问题在于,应该如何解释哲人身上的这种政治意向及其与哲学意向之间的相互并存呢?
哲人对纯粹真理的爱欲与其在政治上的意志虽然构成一种紧张关系,但二者间仍然存在一条内在联系的线索:既然从事哲学代表对自然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哲人便难免与周遭现实环境中存在的虚假之物形成对立,“哲人天性上想战胜虚假。对虚假的憎恨,是对真理之爱的另一面”,而真理要护卫自身并有效战胜虚假,就离不开掌握政治权力,“哲人作为哲人,其青睐政治权力,是战胜虚假的一种必要手段”,从而,“哲人为了真理而钟情权力”、而用心于权力的问题,产生哲学与权力结合的要求。就此,《理想国》详细展示和论证了哲人“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实行哲学僭政”,这被称为哲学的“男子气”[13]294-301。就此而论,“那些不为行使这种权力所动的人不是真正的哲人”[12]157。真正的哲人就像柏拉图在著名的《书信》第七封里所说,他不希望哲学仅仅局限于纯粹的言辞,不希望看到哲学“最终除了空谈以外将一事无成”(《书信》第七封,328d以上)。何况,凭借关于真理的爱欲与认知,哲人也比其他任何人更应当担当统治者。因此,“对真理之爱”使哲人对世俗之物无所用心,但又恰恰是“对真理之爱”支持和推动了哲人的权力意志。后者辩护和解释了《理想国》中哲人当王并建立城邦政权的政治冲动,以及需要偕同格劳孔这般具有政治理想主义血气的青年一同建立其城邦。
如联想到柏拉图本人曾三次奔赴叙拉古辅助僭主的政治经历,那就不难想象,哲人身上确实存在某种投身到属人洞穴中的政治参与欲,即怀有政治人式的实践意欲或血气。受这一股政治参与欲所驱动,哲人除在《理想国》缔造哲学僭政之外,又以雅典异乡人的身份开始了《法篇》里的“‘克里特’远征”(6)“克里特”远征这一说法参见王恒:《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法篇〉与希腊帝国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哲人并没有因为从政治走向哲学就放弃了政治上的谋求,他同时回头转向洞穴,转向“理想国”,也转向《法篇》里的立法改制。不过,与《理想国》气质相异,《法篇》的对话充满了绵密繁琐的针对实际政治事务的立法细节,被施特劳斯视为柏拉图著作里“最具政治性”[14]7的篇章。这一“政治性”的意思一方面是指《法篇》主旨之关于政治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指,相比于以哲学的自然知识作为尺度对政治进行再奠基,《法篇》已大大淡化了哲学对政治事物的直接干预,并更加尊重政治生活自身的法度与结构,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性”。也就是说,与《理想国》激进的哲学僭政迥异,《法篇》实际展现出哲人参与政治和立法实践的另一种路径。
在《法篇》里,雅典异乡人面对的是与雅典民主政制迥异的东方式政制,在那里,老年人占有绝对的权威,雅典异乡人的两位对话者克勒尼阿斯与麦吉罗斯就是两位德高望重的垂髫老者,可他们重视战争而不看重教育,不看重音乐、诗歌,更不消说哲学,以至于克勒尼阿斯对雅典异乡人关于“灵魂和头脑”或“理智”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生命有机体的优先性的教诲感到费解(《法篇》,961d-962)。这种不重视音乐、诗歌、“灵魂和头脑”或“理智”的政制类型在雅典异乡人眼中并不符合好政制的要求。雅典异乡人立法改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服克勒尼阿斯与麦吉罗斯接受它们,尤其是接受合乎理智美德的哲学。由此可见,即使《法篇》最具“政治性”,但对哲学的优越性的重视仍然支配着雅典异乡人从事立法改制的旨趣。在《法篇》及其续篇《厄庇诺米斯》里我们还会看到,由雅典异乡人在其改制纲领中所创立的最高统治机构是非常“哲学性”的,这一机构为从事知识性的哲学生活本身保留了某种空间,哲学也仍然以其对知识的接近而得以占据或参与到最高统治地位之中。这说明“政治性”与“哲学性”的微妙张力在《法篇》中同样存在着。
与《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两位对话者均属年轻人恰成对照,《法篇》里雅典异乡人的两位对话者均属老人家。某种意义上说,哲人更喜欢年轻人,他们更少受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所以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能够跟两个年轻人畅谈哲学,前提是年老的克法诺斯已离席。老者克法诺斯有意规避哲学,一如哲人苏格拉底有意规避老者。但是在《法篇》,雅典异乡人并没有排斥老者,而是与老者进行耐心的漫长对话,并一同合作从事立法。《法篇》里两位稳重、虔敬的老者代替了《理想国》中两位充满政治理想主义激情的青年人。
(3)在城镇化、信息化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城镇化发展不仅要快,更要好,要智慧,“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型城镇化不仅经济要智慧,建筑、移动、能源、规划、治理都要智慧。“智慧城市”有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综合协调政、产、学等各方资源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最终实现“智慧城市”服务于民生。
但是,既然哲学与青年更契合,那么,雅典异乡人如果要设法劝服两位老者接受哲学,就务必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重新“年青”,重新在他们心中注入青春的活力。这就是雅典异乡人首先谈论酒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意图所在。这是因为,关于酒的言辞探讨也会造成对话者在精神上一定程度的迷醉,从而帮助他们相应“恢复青春”,柔化他们的威严肃穆,立法改制所要推荐的新事物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接纳[15]34-35。在雅典异乡人所引进的新建制中,对哲学而言至关重要的便是夜间议事会的建立,它是最高的统治机构。这一机构是一个哲人的机构,在《法篇》续篇《厄庇诺米斯》中这一机构得到更详细的主题性考察,而“厄庇诺米斯”的希腊语原意即为认识者。不过,雅典异乡人既然选择与传统的权威老者共同进行立法统治,那么,在立法中对传统报以必要的虔敬和妥协就不可避免。事实上,议事会的内部构成并不完全是哲学的。议事会内部成员的组成状况包含一部分年轻人、一部分老年人(《法篇》,961a-b)。议事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法律审议,哲学之所以在议事会的这项工作中必不可少,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发达的理智以及对于政治事物拥有更好的知识(《法篇》,962c以上)。但与此同时,议事会成员中又包含有代表传统和惯例的“老资格的执法官”以及得到既有的社会公共舆论与意见所尊重的“其他所有拥有最高名望的人”(《法篇》,961a-b)——哲学和老资格者、有名望者在议事会内部是混合在一起的,因而,那些关于政治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更好的知识,也得以跟既存的传统律法和公共意见达成折衷。由此可见,议事会里的哲学要素须接受对其自身知识性的某种克制,并谨慎对待大地上世代相传的传统律法与公共习见,而不是以哲学的自然知识为基础强迫大地自身的秩序遭受革命性的重新规划。《法篇》中雅典异乡人跟两位正统老者一同合作进行的审慎立法,代替了《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跟两位政治理想主义青年一同打造的激进的哲学僭政方案。
三、结语:古今之间的政治哲人
从《理想国》到《法篇》,柏拉图为我们展示了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多重张力,也通过展示处理这一张力问题的不同可能与方式表达对于该问题的反思,从此出发,后世哲人们在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复杂斡旋几乎都在柏拉图那里存在某种共鸣。就此而言,这一张力问题实际贯穿了西方哲人的古今思想谱系,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问题正是一切伟大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16]39。与海德格尔相区别的是,古典政治哲人柏拉图的教诲包含引导哲人节制自身的癫狂,哲人在政治实践上的进取性应当得到审慎的克制。对于古典的政治哲学而言,节制、审慎以及必要的虔敬是哲人至关重要的政治德性,这既是保护哲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决定的,也是尊重政治生活自身的有限性决定的。古典哲人“退藏于密”(《周易·系辞》),《法篇》里的雅典异乡人便将哲学深邃地“退藏”起来。哲人固然渴求哲学上的“自然”知识能得到现世政治的接纳,这驱使哲人主动将“自然”的知识引入洞穴的政治世界中加以实现。然而,按照古典的教诲,哲人力图彻底满足这种欲求即便正当(从而是可同情与可理解的),但一旦正视人类道德生存的必然限度(即人不得不首先立足于大地的习常秩序而生存),则终究不可免除对这种欲求的合理自制与调整,而仅谋求其审慎的和有限的满足。
在施特劳斯同时代的哲人中,科耶夫延续了现代性政治哲学的路径,他所争取的恰恰是这一欲求径直地和完全地满足,从而以实现哲学为理由迫使现世政治秩序彻底重塑。“科耶夫的观点清晰而直接。哲学需要僭政,如果它想要成功地实现它的真理”,并在投身僭政的过程中,“像科耶夫解释的那样,哲学家更少被传统束缚,并且更擅长诉诸恐怖和其他或许被认为是‘违法的’手段”[17]243-244。从而,按照科耶夫,哲人(或潜在哲人)的生活重心应当被调转,应当被教导从热衷于静观沉思的生活转向现世政治生活,转向踊跃改造现世政治秩序的积极行动之中[5]244。这种教导一直可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后者暗示哲人必须“改变他的做法”“改变自己的性格”“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丢掉从前“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习性,并学会“采取迅猛行动”(《君主论》,第25章)。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施特劳斯无比渴望和科耶夫展开论战,其中一个原因是,科耶夫是一个清晰化的海德格尔,他没有海德格尔特殊的“怯懦”与“含糊其辞”[18]280-330,而更加坦率而直白地表达他结合哲学与政治(或僭政)的意图。因此,审视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论战,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施特劳斯的著作《论僭政》联系起他与科耶夫之间的论战性关系,但有线索证明,《论僭政》潜在的对话者也许包括海德格尔。在该著作中,施特劳斯通过解读古典哲人色诺芬的对话作品《希耶罗》,揭示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诲:尽管诗人西蒙尼德斯致力于站在僭主的位置上正面教化僭主希耶罗,而且表现得深谙僭主的生活与心理,还被希耶罗提防他企图篡夺其僭主之位,但是他终究没有打算当一名僭主,也不表示要与希耶罗达成任何政治上的联盟关系,他与僭主保持了距离。
参考文献:
[1][德]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学说[M]//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美]H.梅耶斯.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M]//刘小枫.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张新樟,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德]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M]//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美]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M]//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振,彭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5]Victor Gourevitch and Michael S.Roth eds.On Tyrann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including the Strauss-Kojève Correspondence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6][美]列奥·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M].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7][美]列奥·施特劳斯.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M]//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8][德]马丁·海德格尔.黑皮本[M].靳希平,译.P.13.5.23.
[9]张旭.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双重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02).
[10][美]T.罗克莫尔.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J].金寿铁,译.世界哲学,2013,(04).
[11][英]伯纳德·威廉姆斯.“理想国”中城邦与灵魂的类比[M]//娄林.《理想国》的内与外.黄俊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12][美]斯坦利·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M].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6.
[13][美]J.郝兰.评罗森《柏拉图《王制》研究[M]//娄林.古今之间的但丁.李向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14][法]卡斯代尔·布舒奇.《法义》导论[M].谭立铸,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5][美]T.潘戈.政制与美德:柏拉图《法义》疏解[M].朱颖,周尚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6][法]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7][加]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M].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8]刘振.哲人与僭政[M]//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4.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5-0080-07
[收稿日期]2019-08-15
[作者简介]李智星(1987—),广东肇庆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林祥]
标签:海德格尔论文; 施特劳斯论文; 政治论文; 哲学论文; 哲人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甘肃理论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