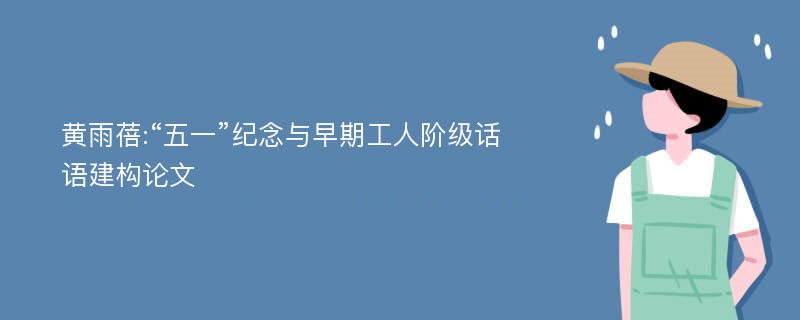
[摘 要]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早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组织通过“五一”纪念这一载体,传播革命理念,为工人阶级建立了一套融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一体的独特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他们以报刊和戏剧文学为传播载体,针对工人阶级的特点进行价值扩大和信念扩大,促进工人阶级形成自我意识,对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实际发生起到了动员作用。
[关键词]“五一”纪念;工人阶级;框架建构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人阶级由马克思所说的“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作为纪念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对于全世界资产阶级政府之反抗”[1]的节日,“五一”节所蕴含的阶级指向和主义依归,逐渐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并借助节日所传递的一些感受和统一、共同的情感,借助与旧制度的节庆截然不同的话语表达,通过多种形式,发动工人运动。在运动中唤醒劳工的阶级意识,在聚拢效应中使他们形成身份认同,其利益诉求也由物质条件改善向政治权益获得转变。
先进知识分子在“五一”纪念活动中唤醒劳工、促进身份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框架建构的过程。“框架”这一概念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提出的,指“使个体能够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在生活空间和更广泛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图式”,它“赋予事件和事情以意义,从而发挥着将体验组织化并引领行动的功能”[2]。因此,一旦特定的“框架”被成功塑造,就能够从价值观念、情感信念等多方面构建起追随者的信仰,从微观层面进行动员,有利于行动的开展。
本文基于1919至1927年间“五一”纪念的情况,从框架建构理论出发,试图挖掘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人阶级话语的建构历程和建构方式,透视早期工人动员的策略。
单侧闭合性NeerⅡB型不稳定锁骨远端骨折;受伤3周内手术;伤前患侧肩关节功能正常且术后随访>12个月者。
一、阶级与民族之间:早期“五一”纪念的话语主框架
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首次在中国纪念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此后,在蔡元培、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呼吁之下,“五一节”的影响逐渐显现。各地陆续在每年“五一”之际开展各种活动,报刊杂志也纷纷出版劳动节专号,纪念这个属于工人的节日。“五一”节的传入,不仅改变了劳工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也塑造着中国劳工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为中国工人阶级话语和行动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劳工与资本家的对立:阶级斗争框架。注意阶级关系,明确区分敌我,是“五一”纪念为工人塑造的最主要的话语框架。尽管早期“五一”纪念中没有明确出现“阶级斗争”的口号,但在1919年至1924年历年的纪念活动中,均出现了“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突出劳工与资本家对立的标语。1920年的一篇“五一”纪念文章则明确提到:“从前的战争是国与国或族与族的战争,以后的战争应当是被治者对治者的——平民对官贵族或劳工对资本家——战争。”[3]“劳工”向“资本家”要求权利的斗争开始在“五一”纪念中被鲜明地展现出来。
尽管这一时期对“阶级”划分的认识还较为简单,大多以是否劳动将人分为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或以是否拥有一定资本划分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但无论如何,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阶级概念已经成型,“阶级斗争”的影响力伴随着“五一”纪念日在中国不断扩大,使当时的工人形成了敌与我、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立观念。在这种话语模式下,“劳工”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享有共同生活经历和集体记忆、拥有共同利益诉求的集体变得真实可感,不断引起共鸣,使劳工逐渐建立起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从而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意识和动力。
(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融入民族解放的阶级斗争话语。在早期的“五一”纪念中,阶级是大于民族的,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不分国界、毋庸置疑,在“劳动者没有国家,劳动者只有世界”[10]的观念影响下,早期“五一”纪念中所宣传的阶级斗争方式也体现为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因而,强调“阶级斗争不能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遮蔽”的观念在当时并不少见。
阶级斗争话语框架实际上还隐含着“不公正”框架——曾经被认为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被重新定义为不公正的。伴随着“五一”纪念而来的“劳工神圣”潮流,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劳动者的价值,明白他们不应该处于当下的艰难处境,而应该拥有自己的地位和权利。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权利,并非是来自上天的“不幸”,而是源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你们的生活不安,破产,甚至于为经济所迫而犯法或自杀,也是受了欺压摧残工人农民那班恶势力所迫害。”[4]在这种“不公正”框架中,原本无法抗争的“上天”或“命运”,变成了可以抗争的现实对象,进一步激起了劳工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变的愿望,劳工与资本家的敌我身份对立也更加突出。
在“敌我”身份在“五一”纪念话语中不断被完善的同时,预后性框架建构也在进行。这一过程针对问题提出一个面对未来的设想,对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本运动发展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5]。李大钊曾指出,“五一”纪念的目标在于:“早日完成那‘八小时运动的使命’,更进而负起‘六小时’运动的新使命来。”[6]瑞彭希望中国的劳动界“用切实的工夫,做实际的运动,不要做资本家的奴隶。作工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务须极力,虽牺牲热血生命也不顾。”[7]郑振铎也提到,只有八小时的劳动、八小时的休息、八小时的教育的工作制度,才能让工人过上“人的生活”[8]。
b) 黑屏功能被启动时,当没有任何报警出现以及所有报警都恢复到“正常”状态时,操作站显示黑屏,此时操作人员可以处理报警以外的其他任务。
研究对象选用皖电东送1 000 kV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的SZ3021特高压双回鼓型钢管塔,建立输电塔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该钢管塔呼称高度为45m,整体塔高为101 m,塔底根开尺寸为19.71 m.输电塔主要由Q235和Q345两种钢管构件组成,只有塔头和塔腿的辅材使用了Q235角钢构件.如图1(a)和图1(b)所示为特高压钢管塔顺线路方向和垂直线路方向的立面图.
(一)以报刊构建话语传递公共空间。报刊是20世纪初期中国最重要的大众传媒,报刊的出现不仅构建了话题讨论的公共空间,也在这一空间中起到议程设置作用,主导着公众注意力的投向。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就通过报刊将对“五一”纪念认识的变化传达给工人,完成工人阶级的话语建构。
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五一”纪念不应仅仅满足于工作时间上的斗争,他们逐渐意识到,以八小时工作制为目的的抗争仍然拘泥于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要求资本家改良待遇的枝节上的努力并不能实现劳工真正的解放。“要想把社会问题根本解决,要想使劳动者完全由被压迫被掠夺的当中解放出来,非根本的改造社会组织不可。”[9]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工人应该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与“三八制”相比,这一预后性框架更为激进彻底,“五一”纪念的目标从物质利益要求转向政治利益诉求,“五一”运动的意义也从简单的要求运动上升到自求运动。
扒锅街的榕树下聚了好多人,唧唧呱呱地活像几万只鸭子在叫,我不耐烦地扯了片叶子放进嘴里嚼,脑子里想着下回要怎么才能亲到刘佳,最近他真的越来越滑头了,跟春天田里的泥鳅似的。
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迂萦,绵连斜亘,侧直齐平。[10](《谢灵运传》,P1757)
借助港口辐射优势,嗅觉灵敏的温商群体主动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截至目前,有68万多温州人在世界各地、175万多温州人在全国经商,形成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商网络”。其中仅在武汉创业发展的温州人就达17万,遍布商贸、物流、机电、服装、金融等众多领域的3000多家温商企业,带动近百万人就业。当地2017年底举办的全球温州商会专场活动中,温商企业家与武汉签约项目17个,总投资达1203亿元。在云南,12万温商同样开始布局新机会,云南敏大集团董事长陈教敏表示:“把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云南的浙商要做面向西南开放的排头兵。”
但是,谋求全人类幸福的世界主义革命更像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当时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迫在眉睫,呼吁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民族主义革命才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主旋律。在许多知识分子还寄希望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时,张国焘就指出,英美日三国对中国相互竞争式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群众极大的痛苦,因而,国际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11]。随着1924年国共合作的达成,以国内军阀为对象的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五一”纪念不再仅仅强调资本家与劳工的对立,而着重于宣传中国普通劳工在国际帝国主义及其援助的军阀蹂躏之下的痛苦,“五一”纪念的意义被引向阶级与民族解放的共同体。蔡和森曾深刻地论述道:“中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人阶级天然负有两种重任:一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12]
在这一阶段所构建的话语中,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帝国主义殖民者是中国境内占据主导力量的资产阶级势力,他们“侵略中国,一面援助中国军阀,延长中国内乱,一面用各种鬼计,压迫中国民众势力的发展”[13]。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剥削势力的扩大,是将对工人的剥削从本国向海外的扩展,从而形成国际层面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扩展海外市场,给殖民地的民众带来了痛苦与压迫,这又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同时,“中国的军阀,政府,与洋资本家勾结,压迫中国工人”[14],他们既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言人,又是国内反动阶级利益的代表,因而,国内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一样,是无产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的仇敌。这一话语框架之下,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对象合二为一,劳工大众针对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军阀的斗争不再仅仅是工人反抗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也具有了反抗侵略、实现国家与民族解放的意义。
“五一”纪念所宣传的阶级斗争对立主体在这时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而是包括农民、小商人、底层士兵、知识阶级等一切在内的被压迫的民众,而“他们”则变成了以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压迫阶级。阶级联合在这一阶段逐渐成为主流,虽然“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冲突的,但是他们并不用这种冲突而丧失他们的这种共同目标”[15]。“五一”纪念开始由单纯的工人阶级的纪念日,转变为“一切被压迫民众团结奋斗的纪念日”[16]。
同时,各种以《劳动歌》命名的诗歌也被创作出来,这些《劳动歌》不约而同地宣扬劳动者的价值与地位,将“劳工神圣”的概念融入字里行间,宣传“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此外,还有诗歌以更富本土化的形式对“五一”运动的目标进行阐释:“四海底人们皆兄弟!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21]中国传统的“均平”和“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念融合起来,从而使得源自西方工人运动的“五一”纪念能够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更好地生根发芽,引起“五一”纪念真正的主体——工人阶级的共鸣。
二、报刊、戏剧与文学:纪念话语与工人阶级的桥梁
尽管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反抗从“工人”这一名词出现就在不断出现。但近代早期工人的反抗与斗争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的地缘与亲缘关系,“阶级”的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工人斗争也没有同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联系起来。首先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是早期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们。第一个在中国喊出“劳工神圣”口号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主要由进步的知识分子构成,他们都与广大劳工之间存在一定的隔离。要将知识分子的呼吁传达到劳工中间,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和权利地位,就需要一定的制度、组织或者技术架构,将思想关切上一致但结构上不一致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连接起来,从而为“五一”纪念传达相应的阶级话语打通通道,这个过程称之为“框架桥接”。
劳动是为生存,休息是为个人的发展与乐趣,教育则是增进个人知识,推动人类进化。“三八制”的诉求不仅与五四时期要求个人解放、追求“真我”的人道主义潮流相呼应,更体现出“五一”纪念对劳工个人权利的关照,因而成为早期工人阶级运动的代表性口号。
更为复杂的政经逻辑隐藏其中,而这些逻辑和与之相配的操作路径,在未来,还将继续影响一个企业的产业路径与一个球队的竞技气质。
国内最先纪念“五一”的,是北京《晨报》副刊所出版的“劳动节纪念”专号;由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1921年对武汉、湖南、天津、大连、徐州等地进行了劳动状况调查,此后多年出版“五一纪念号”,刊登了许多关于“五一”纪念的文章,支持工人斗争;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编的《教育丛刊》刊登了当时“五一”纪念的情况。报界对“五一”的报道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五一节”的影响。
框架扩大是对既有价值和信念的美化、润饰、显化和激发。[22]在利用“五一”纪念对工人阶级进行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采用了一系列美化、润饰的话语策略来显化工人阶级的地位,进行情感动员,从而使工人阶级接受自己的观点。如果说报刊和戏剧文学是工人阶级话语建构的载体的话,框架扩大则是工人阶级话语建构的具体策略,是报刊、戏剧文学等载体所承载的具体内容。在早期工人阶级的话语建构中,主要采用了价值扩大和信念扩大两种框架扩大策略。
生活在北美沼泽地的灰鹤群每逢遇到死亡的同类,便会久久地在尸体上空盘旋。接着,“头领”会带着大伙落下来,默默地绕着尸体转圈,悲伤地“瞻仰”死者的“遗容”。而西伯利亚的灰鹤保持着另一种奇特的“葬礼风俗”。当某一只灰鹤不幸死去,它们便哀叫着守护在死者跟前,待“头领”突然发出一声尖锐而凄惨的长鸣,众灰鹤顿时肃然,默不作声,脑袋低垂,以示悼念。
无论是最初“劳工神圣”的启蒙,还是后期越来越多关切劳工情况的知识分子对“五一”纪念实际意义的呼吁,以至提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看法,都是以报刊为主要途径传达到广大劳工中间的。作为当时最主要大众传播工具,这些始终对工人境况表达关心并提出改善途径的报刊切合了当时工人阶级的需要,对“五一”纪念话语的传播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
(二)以戏剧文学简化话语表达方式。“五四”前后新文化的倡导,使文学艺术开始走向平民化、大众化,新文化人怀着启蒙大众的愿望,通过贴近平民的文学艺术创作,意图达到启蒙民众、解放思想的目的。这一新的文化环境,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在“五一”纪念中将自己的理念与观点传达到工人阶级中间搭建起桥梁。
不过,无论是“三八制”还是“劳工专政”,其实都离不开“阶级斗争”这一话语框架,它们都是工人阶级针对资本家的斗争,为工人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具体的行动策略与目标。“阶级斗争”的话语借由“五一”纪念被表达出来,使“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中国工人中更为广泛地传播。
1921年,《觉悟》的劳动纪念号上刊登了一部名为《五一纪念》的独幕短剧,这部短剧以主角阿方之口强调了“五一”的意义:“五一”是“我们苦工人的纪念日”,全世界要放假来纪念它[19]。1922年,《觉悟》上刊登的一篇《武汉庆祝五一节状况》中提到,在武昌的五一游艺大会上,除了学校及各团体的传单十几种在会场散发外,还演起了幻戏。这些幻戏大多描写工人的苦况,及鼓吹他们阶级觉悟。演“劳工血泪”一戏时,听众,尤其是工人,非常感动,有好些人甚至于哭了。[20]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直观地将工人阶级的艰难境况展现出来,从而消除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隔离,起到了极大的感染作用。戏剧这一工具在此后被中国共产党运用得炉火纯青,在苏区至抗日战争时期都成为框架桥接、情感动员的重要工具。
框架建构的过程和效果会受特定时期和地区政治结构的影响[17],“五一”纪念话语由单一的阶级斗争框架转向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的双重框架就是基于当时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特定政治情况提出的。理论上,为了扩大外界的支持,减少外界的反对,框架的边界就要尽量模糊一点,也就是要尽量提高与其他认同之间的重合度。[18]民族解放框架与国民党领导的追求民族解放的国民革命相契合,提高了两党认同之间的重合度。同时,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双重话语框架下,不仅工人阶级会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农民、商人、士兵、知识分子等其他阶级也会基于“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同情并支持工人阶级的运动,从而扩大外界的支持力量。很显然,由单一的阶级斗争框架向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的双重话语框架的转变,使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和其他社会阶级拥有了交汇点,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三、价值与信念的润饰:话语共鸣度的激发策略
同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组织也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报刊,专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理念与精神。1920年,陈独秀在自己以及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状况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此外,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也纷纷涌现,被誉为劳工兄弟刊物。1922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除了日常刊登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政论文章之外,还在“五一节”出版特刊,利用这一工人阶级的纪念日激励动员工人。
(一)从“自由平等”到“劳工神圣”。所谓“价值”,是指一个人群中被认为值得保存和提倡的行为模式和生存状况。[23]尽管辛亥革命以前,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多年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对“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几无概念,但并不能否认自由平等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五四”前后,在知识界流淌的“自由平等”思潮被引用到工人阶级话语建构当中,许多“五一”特刊上所刊载的文章都在强调工人应当享有应得的自由与权利,指出工人“是须要这种自由的”[24]。框架建构中的价值扩大是对关乎人类生存状态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反复修饰,是以社会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为核心,将人们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扩大。话语建构过程中能否与既有价值观念成功对接,是影响框架共鸣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五一”纪念为契机而针对工人阶级的启蒙与动员中,先进知识分子将“自由平等”这一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作为工人阶级奋斗的终极目标,提出以“劳工神圣”为代表的一系列口号和诉求,成功地将“五四”以后在社会中盛行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工人运动对接,不仅起到了转变工人阶级思想观念、建立“不公正”框架的作用,而且更能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为工人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
(二)从“敌我分明”到“舍我其谁”。“信念”是指关于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或其特征之间的一种假想性关系。[25]扩大工人阶级对于斗争的信念,也是成功提高框架共鸣度的重要手段。在进行价值扩大,将“自由平等”观念引入工人阶级话语体系之后,“五一”纪念话语针对工人阶级的特点,采用信念扩大的方式对工人阶级话语进行扩充。
第一,扩大固有信念,通过消极评价赢得正义性。在阶级斗争话语框架下,“五一”纪念话语对军阀、资本家等抗争对象的评价趋向于“罪恶”,将劳动者描述为“神圣”,而将资本家描述为剥削劳工生命血汗的“盗贼”[26],指出“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同是生活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大商绅士阶级的恶势力欺压摧残之下”[27]。
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资本家、军阀、大商绅士被喻为盗贼、恶势力,他们是靠着剥夺工人和农民的血汗来发展自己的。“惩恶扬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美德,劳动者的神圣与资本家的“罪恶”形成对比,再加上“劳工神圣”潮流引起的“不公正情绪”,工人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斗争便顺理成章地取得正义性,从而成功地调动起工人阶级对抗争对象的革命情绪,这一信念扩大是巩固“敌我”分明的阶级斗争话语方式的重要手段。
第二,改变的可能性或集体效力的信念。如果人们要集体行动,那么他们必须相信这样的行动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个变化是可能的,但是没有集体行动它不会自动发生。[28]在工人阶级话语建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采用这一方法,建立起阶级斗争效力的乐观情绪:“我们不要怕资本家和资本家政府的势力,只要我们一旦把我们自己的反抗力,觉醒起来,我们的势力就比他们的大得多,不但可以抵抗他们,而且可能推翻他们。”[29]“我们极相信我们这个阶级是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的,将来的世界必定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世界。”[30]
这种充满了“只要……就……”“必定”“极”等词语的话语方式,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它们强调最后胜利的希望,从而建立起工人阶级对于行动的乐观期望,在工人阶级心中播下“团结就是力量”“奋斗终将取得胜利”的种子,为后续行动起到动员作用。
《脊柱外科杂志》是一本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主办的高级学术期刊。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为统计源期刊。本刊对脊柱外科各个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热点、研究成果、技术与进展、经验与创新等进行全方位的报道,竭诚为脊柱外科医师、学者服务。读者对象为骨科及相关学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人员。
第三,关于“站起来”的必要性和恰当性的信念。这种信念中包含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强调只有自己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从而产生行动的必要性:“我们要粉碎掉这种残酷的东西,只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与牺牲”[31];“大家努力向前冲……创造劳动世界,责任在农工!”[32]“五一”纪念以文章、传单和诗歌戏剧等形式,不断地传达出“自己行动”“责任在我”的观点,强化了工人阶级发起行动的使命感,建立起“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的话语框架。
通过框架扩大的话语建构艺术,“五一”纪念使工人阶级话语在价值和信念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意识形态在革命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信念、信仰的建构来发动群众力量始终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一手段在利用“五一”纪念进行工人阶级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四、余论
“五一”纪念是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窗口。从最初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到后来向资本家和政府要求权利的实际运动,再到夺取政权的呼吁,“五一”纪念中体现了当时劳苦大众的真实诉求,以及关心劳工生活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组织以至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对劳工生活的关注。
在“五一”纪念以及对这一纪念的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以报刊、戏剧文学为载体的一系列对“自由平等”的价值扩大以及具有情感动员性质的信念扩大,一套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框架的工人阶级话语被建构起来,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开展革命斗争做了准备,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这一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以明确划分“敌我”的阶级分析法为特点,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始终。同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之下,阶级斗争框架中又被融入了民族解放框架,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方针。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些核心思想,在早期工人阶级话语建构中已经体现出来了。以“五一”纪念为载体的早期工人阶级话语建构,促使工人乃至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融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一体的话语框架,对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石.今年“五一”节与中国工人[J].向导,1924(63): 501.
[2][5][17][18][23][25]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09.219.240.240.223.223
[3]高尚德.“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J].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14):3.
[4][27]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五一”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J].向导(五一特刊),1925(112):1027.
[6]李大钊.“五一”May Day运动史[N].星期评论(上海1919) ,1920—05—01(A4).
[7]瑞彭.“五一纪念”促进中国劳动界的觉悟[N].民国日报·觉悟(劳动者纪念号),1921.5.1(4)
[8]郑振铎.“五一”的纪念[J].新社会,1920(19):4.
[9]江春.“五一”运动[N].民国日报·觉悟,1921—05—01(1).
[10]大白.劳动节歌[N].民国日报·觉悟,1921—05—01(1).
[11]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J].向导,1922(6):3.
[12]和森.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J].向导,1925(112):1029.
[13]越.五一劳动节[J].建声,1924(56):10—11.
[14]五一劳动节纪念[J].共进,1925(81):4.[15]大雷.国民会议与工人阶级[J].评论之评论(上海1924),1924(37):1.
[16]我们今后纪念五一节的任务[J].中国工人,1925(5):3.
[19]天底.五一纪念[N].民国日报·觉悟,1921—05—01(2).
[20]梦吾.武汉庆祝五一节状况[N].民国日报·觉悟,1922—05—11(4).
[21]苏宗武.劳动歌[J].国货月报(上海1924),1924(4):5.
[22][28]David A.Snow,E.Burke Rochford.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4): 469.471.
[24][30]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N].民国日报·觉悟,1922—06—08(2).
[26]亚子.劳动纪念特刊宣言[N].新黎里报(劳动纪念特刊),1923—05—01(6).
[29]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N].民国日报·觉悟,1922—05—01(4).
[31]亨.五一与五四[N].建声.1924(56):9.
[32]少陵.劳动歌[J].学汇,1923(96):5.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8-0024-07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周奕韵
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话语论文; 劳工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框架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8期论文;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