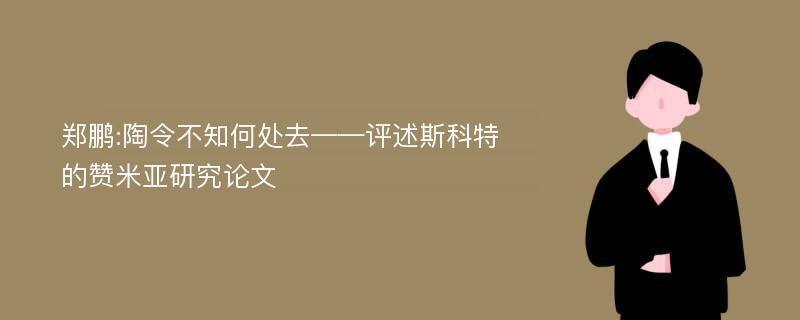
摘要:正如杜赞奇的溢美之词,《逃避统治的艺术》“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将对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评并指出其中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本文讨论“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其次,对斯科特为赞米亚研究设定的主题——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讨论赞米亚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关键词:斯科特;赞米亚;国家;非国家空间
一、引 言
著名历史学宗布罗代尔曾批评道:“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总是对平原流连忘返,而不愿意进入附近的高山。”①[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1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21页。与历史学家不同,山地是人类学家时常光顾的田野。晚年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武夷山、南岭、凉山、武陵山等南方山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将族群性与空间的视角贯穿于“富民”的社会问题之中,进而提问:“什么叫山区?它同平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山区同少数民族老是缠在一起?”他还提醒后来者,少数民族上山、下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靠一句话是解释不通的”。②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0-514页。
令人惊奇的是,另外一位在山地的人类学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就是斯科特。借助人类学的脚步与历史学的目光,斯科特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的偏执与线性文明进化论的偏狭,站在高地追问“文明缘何不上山”?这个问题承袭于布罗代尔和恩格斯。布罗代尔启发了山地研究的认识论。正如他的论述:“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在横的方向,这些潮流能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但在纵的方向,面对一道数百米高的障碍,它们就无能为力了。”③[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31页。恩格斯提供了山地研究的本体论反思。恩格斯追寻国家的起源,解构了国家的文化霸权。他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况”④[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意味着国家攫取了文明的定义权,因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⑤[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0页。。因之,如果考虑与山林“等量齐观”的江河湖泊以及更广大的海洋,那么,斯科特问题的本质就是——“国家之外无文明”?
为了使问题被解释得通。斯科特从马来西亚转战到了一个被称为“赞米亚”的山地。在“赞米亚”的图绘中,“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①[美]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终于被斯科特推向极致。他从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学辖域中逃逸出来,对德勒兹式差异、游耕、解辖域化的后现代政治学做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诠释。斯科特敏锐地洞察到山地垂直效应与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山地居民的能动性之间的亲和关系。所以,如果说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中建议人们尝试着审视国家建设中的种种极端,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中展示了日常政治及反抗的日常形式,那么,《逃避统治的艺术》②该书的英文标题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斯科特赋予了它两层意涵:一是避免被统合入国家体制;二是防止山地社会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中译本标题表现了“逃”是免遭统治的关键武器,它是“不被统治的艺术”得以展开的前提。日译本《ゾミア―― 脱国家の世界史》(2013)(直译为《赞米亚:逃离国家的历史》),也将“逃”作为关键词。“逃”字可以追溯到费孝通的观察。他曾指出,面对封建压迫,少数民族只有两条路或两个字:走,死。要生存就要走到更偏远的地方去,苗族、瑶族靠两条腿一直走到了泰国、东南亚等地区。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512页。(Seeing Like a Refugee)一书则将反抗形式升级为逃离国家的统治,并且论证了底层依托作为非国家空间的山地而应对国家建设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正如杜赞奇的溢美之词,《逃避统治的艺术》“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将对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评并指出其中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本文讨论“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其次,对斯科特为赞米亚研究设定的主题——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讨论赞米亚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二、作为方法的“赞米亚”:边缘、镜像与书写单位
我要阐明,赞米亚绝对有资格成为地区。③《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明实录藏族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3-554页。
通过对“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大篇幅论述,黑格尔归纳出山、水差异地理学的政治效应:“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国家不过是河川流注的区域……只有山脉才是分隔的。”④[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2页。山地的分隔性所导致的结果被古代中国政治地理学家总结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⑤《礼记·王制》。。赞米亚,便是一个被高山分隔的碎片区域。
赞米亚的空间,最早由荷兰学者申德尔构建。随后,让·米肖追踪了它的空间范围。赞米亚指称着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横括9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共计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的区域。其中,山地居民约800-1000万人,族群类型以百计,语系至少有5种。山地生态景观表现出了多样性,多元、多变的语言、服饰、生计、居住方式、族群认同、社会结构以及宗教活动,如马赛克一般,让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陷入困惑。因此,学者们在“赞米亚”的研究进路,如同赞米亚碎裂的地理/文化景观,往往是“分散和相互隔绝的”。虽然关于赞米亚内部各地区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它们只是“在赞米亚做研究”而非“赞米亚研究”,未能构筑出针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科学的新视角。
斯科特指出:“社会结构不应该被看作特定社区的持久社会特点,而应看作一个变量,其目的之一就是调整与周边权力区域的关系。”③[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54页。与农业技术的政治选择一样,社会结构也具有抵制监控与从属的政治功能。国家偏好稳定、可靠、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任何一个试图控制赞米亚地区的政权,都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打交道的权威,如果找不到就要创造一个这样的权威。为了避免被统合,赞米亚山地居民像水母一样,裂变为更小、更分散的社会单位,直到数个家庭无首领的聚合。裂变使政权只能面对一个无组织、无结构的人群,从而失去了政权建设的支撑点。
实际上,当谷地国家忙于构建整齐划一的社会景观时,“山地”则不断生产着差异性和边缘性,这赋予了山地居民的共通文化与历史。鉴于此,针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赞米亚状态,斯科特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尝试着提炼新的空间结构。
赞米亚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地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联合,这根本不存在。其相似的模式在于其多样的山地农业、分散的居住和迁徙,以及贫困的平均主义,与此相关,这里的妇女地位比谷地妇女地位高。⑥[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1页。
赞米亚地处低地国家中心的边缘,从而保持着“与国家相对的位置”。这种自主性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政治效应——即“其相对的无国家性”。因此,赞米亚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更具有着方法论的价值。
第一,就赞米亚区域内部的社会结构而言,赞米亚研究的主旨是摒除国家中心主义,在“中心—边缘”模式中赋予边缘自主性。如此,需要改变“中心”到“边缘”这种从上至下的线性思维,找出其中的断裂与不连续性。实际上,中国研究的变迁,叠写着类似的学术史转向。如果以费孝通、林耀华作为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起始,那么,以地域化的宗族结构为中心、依据弗里德曼模式构建起来的华南研究可以称得上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学者重返中国田野。与前两阶段执着于整体中国的归纳不同,这一时期的研究立足于乡土中国的边缘,志于寻求中国文化中的差异性。研究者认识到类型中国仅仅是汉人的单一族群投射,非汉人族群成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把钥匙。于是,少数族群聚集的中国西南成了学术的新增长点。正如华南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大卫所言:“我感觉到不能一辈子只研究华南,我的出发点是去了解中国社会。研究华南是其中必经之路,但不是终点。从理性方面来想,也知道现在是需要扩大研究范围的时候。”①华南研究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29页。相应地,从《想象的共同体》开始,东南亚研究的转向也大体循此轨迹。何况,中国西南本身就是被划入了赞米亚的田野空间。
我在这里试图描绘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对于我们所有的读者来说,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看起来距离非常遥远。在当今世界,我们未来的自由依赖于驯化利维坦式国家,而非逃避它,这个任务让人望而生畏。①[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04页。
1.4 组织病理检查 肾脏组织取材后置于甲醛中固定48 h,石蜡包埋,按8 μm厚度切片。Masson染色:肾脏组织切片脱蜡、水化,加入Bouin处理液过夜,用自来水冲洗;分别予苏木精染色液及碱性品红染色5~10 min,再予磷钨酸溶液反应5~10 min,最后予苯胺蓝染色。染色后在显微镜下(200倍)观察肾组织病理改变。
实然,赞米亚并非“文明-野蛮”“发达-欠发达”的二元结构中被压制与放逐的他者。在赞米亚山地所呈现的族群垂直分布模式中,每一层生态区都是山地族群精心设计以适宜山地生态与抵制国家扩张的结果。宗教、文化与族群性的认同,是自主选择的边界形成机制,旨在强化政治与社会差异。因此,逃亡的底层如何与山地的特殊地理环境相契合,以此生产和再生产非国家空间;它得以运行的物质与文化条件是什么;它内部的结构关系,都可以是单独的课题。
第二,山地社会是国家的反身物,构成了平原谷地国家的反写的“镜中我”。讨论国家建设的文献贯穿着从中心到边缘的平滑连续性的思维与等待归化的国家中心主义隐喻。但它鲜有关注逆向的去国家化与非国家性历史。所以,斯科特指出,剖析山地社会的形成史,就是在透视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
同时,山地与谷地之间保持着持久的共生关系。山地与谷地构成了互补的农业生态位。更重要的是,山地拥有一些价值量极高的产品,例如矿物、胡椒、稀有木材等。事实上,“谷地的政治实体,特别是小政权都被固定在特定的区域,严重依赖山地贸易,对他们来说,山地贸易伙伴的背叛是一个严重威胁”②[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27页。。
最激烈的空间竞争是人力资源的争夺。山地居民在不久前还是谷地国家的臣民,却沿着“逃亡走廊”进入山地。在新的生态环境中,他们策略性地改变了生计方式、社会结构、文化谱系,据此灵活地调整他们与国家的距离。所谓调整,实质是理性地对“进化序列”的再抉择。进化序列由“采集渔猎/游耕-农耕/灌溉稻作”“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分散与缩减-强制定居”“无文字-书写谱系”的递进关系组成。在国家的文明化框架里,前者构成了未开化的指标体系,后者则处于文明金字塔的顶端。然而,山地居民有针对性地解构国家文明、撤回到前者。流动、自然与社会景观的杂乱无章、社会组织的高度弹性与去中心性,让国家无法对山地空间“提纲挈领”。游耕或采集渔猎的生计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征用的成本,对国家财政而言几乎没有价值。如此一来,山地成为了耗噬国家财政人口的黑洞。于是,在国家建设的财政逻辑之下,“只有不断清洗其边陲地区,不断成长的水稻国家才能实现人口集聚的目标,从而才能统治和保卫其核心区”③[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99页。。由此,可以确认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建立在人口控制技术的基础之上,衡量国家能力的关键指标是在一个合理的统治空间内所吸引和控制的定居人口数量,领土则没有人口同等的重要性。
第三,“没有历史的人”与书写单位的重构。自19世纪开始,历史学家致力于打造民族国家起源与成长的脚本。以民族国家为书写单位成为历史学家的习惯性窠臼。书写使用了排除和纳入的双重机制。那些对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及其经历被纳入历史,而那些处于民族国家建设边缘的人群则被排除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变成了埃里克·沃尔夫笔下“没有历史的人民”。对此,在吸收汤因比文明史与布罗代尔区域史的经验基础上,斯科特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将赞米亚视为一个超国家空间的文化有机体。
赞米亚概念是要探索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在这里,划定区域的理由并非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比如老挝),也不是一个战略性概念(如东南亚),而是基于特定生态规律和结构关系,这些都会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如果走运的话,“赞米亚研究”的例子将可以激励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追随这样的实验并不断完善。①[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31页。
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这项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二月份到了,还是杳无音信。他们发去一封公函,要她到司法长官办公处去一趟。一周之后,镇长亲自写信给爱米丽,表示愿意登门访问,或派车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却是一张便条,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细小,但墨水已不鲜艳,信的大意是说她已根本不外出。纳税通知附还,没有表示意见。
赞米亚是“所剩无几”的一个透视非国家空间的窗口。赞米亚研究的实验意义在于,它将长期以来被国家的光环压制在阴影之中的“非国家空间”纳入书写的主体范畴。然而,重建“非国家空间”的历史总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多元的历史主体往往在制作国家连续性正统的神话过程中被削足适履。正如无国家的人很难被纳入到雇佣劳动或定居农业这样具有财政清晰性的经济中那样,非国家空间也不会被纳入到国家历史的书写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文明化的趋中性表达,将中央文明描述得充满文化和社会吸引力,加入中心文化圈被认为是一个进化与上升的过程。这种文明叙事会极力掩盖逃亡,或者将从中心逃亡到边陲的人们扭曲为土著的蛮夷。他们往往被抽象为统计数据,很少作为历史的行动者出现。
1.围绕岗位任职能力构建专业核心课程。核心课程是对学员专业能力素质起决定性作用的课程,对学员在部队的岗位任职能力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具有很强的军队特色和完整体系。核心课程的定位要建立在科学分析、准确把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任职岗位的主要工作任务,加强对不同岗位所需部队专业知识、技能的综合把握。优化过程中应坚持部队与院校相结合,强调核心课程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实践性。
随四季变换选择不同花卉,从而表达自己的审美情致,这是园林主人的共鸣,但具体花卉种类的好恶却因人而异。比如清代李渔自称“有四命”春之水仙、兰花,夏之莲,秋之秋海棠,冬之腊梅。“无此四花,是无命也”[3]。《花镜》中则用梅、柳、海棠、兰、梨、桃等花木喻春之繁华;用石榴、向日葵、荷花、竹、槐等花木喻夏之清凉;用桂花、梧桐、菊花、木芙蓉、枫、芦苇等花木喻秋之绮丽;用枇杷、腊梅、山茶等花木喻冬之寒香[8]。明清时,杏花的文化含义发生转变,少有园林使用,而文震亨对杏花却情有独钟。相反,向日葵被陈淏子认为是夏季代表,在他眼中则是“最恶”。
为了打破国家主义叙事框架的偏颇,考察山地历史的变迁,斯科特倡导“深度史学”(Deep History)。通过阅读东南亚史,斯科特“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差不多成为历史学家”。漫长的东南亚史,实际上长期为无国家状态主导,因而要用东南亚的真实历史来代替“帝国的想象”。对于无文字的山地社会,人类学有助于重建山地居民的社会结构。当然,这必须摒除线性进化论预设的偏狭。斯科特坚信“文字的劣势以及口述的优势”。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口述文化,成为了赞米亚田野调查的重要内容。正是口述而来的诗、传说、依据情势而编造的族谱,可以让山地居民灵活地调整族群认同与联盟。赞米亚田野过程中,斯科特尽力给予了山地居民更多的直接出场机会。
三、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流动性、空间阻力与结构性转化
山地居民被污名化的那些特征正是那些逃避国家的人群所提倡和完善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他们避免放弃自主权。②[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20页。
斯科特直言“贯穿我这本著作始终的逻辑将从根本上颠覆上述逻辑。”③[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1页。这种逻辑即在社会进化论的话语体系下,将国家统治状态与文明、将自我治理的人民与原始状态相混淆。这种逻辑的展开就是将赞米亚山地居民描述为“社会进化的活化石”或者是被文明遗弃的人。为此,斯科特担任起了为赞米亚山地居民去污名化的使命,将非国家空间的正当性与可行性设定为赞米亚的研究主题。斯科特的主要观点是,山地居民是为了逃避国家而“有意的野蛮”(Barbarians by Design),只有在“与国家相对立的位置”,才能够更正理解山地居民的历史。正如他所言,“山地人的历史最好不要理解为古老过去的残留,而是低地国家政权建设中‘逃亡’的历史。”①[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8页。
为了赋予非国家空间的正当性,斯科特将论述重点放在非国家空间何以可能的问题之上。如果能够揭示赞米亚山地社会无需国家便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山地社会就并非是社会进化的低端,而是为了保持自主性而精心设计的社会景观。在这里,斯科特将非国家空间再生产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项:
(一)流动性与“无处不在的逃亡”
“首先为激励医疗专业人才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要在职称评定、人员引进、待遇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其次要选派一部分年轻有潜力的医护人员到上级医院进行学习、培训,再次要柔性引进人才,与北京、上海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让他们定期到莱芜坐诊。”
然而,若将“不流动”的结果去历史化为“社会事实”,则难以理解“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不仅是底层的控诉,更是日常政治的实践。在这里,斯科特笔下东南亚底层与中国古代人民的行动逻辑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3.血清学诊断。包括补体结合试验、2-巯基乙醇试管凝集试验、乳胶凝集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方法。国际上公认的方法是改良补体结合试验,该方法可于感染后10 d检查血清抗体,可靠性比较强,但操作烦琐,目前认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较为实用。
东南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现在(殖民时代)还是以前,农民生活的主旋律是移动而非固定”⑤[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72页。包括水稻种植者在内的东南亚人口,迁移是他们的常态而非特例,这与原有“稳定地植根于某地的农民家庭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一旦“拾得”底层流动性的假设,逃离国家就有了发生学的机制。斯科特认为,底层逃离国家空间主要由两种原因驱动:逃避国家空间的赋役和拥挤,这在斯科特的论著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述。
(二)空间阻力与“山地公共避难地”
何处是归程?逃亡的归宿是理性抉择的结果,虽然此后他们便很难逃脱“野蛮”的标签。正如斯科特所言:
古代中国流行的政治思想一直就视民为“水”。它反映了人民所具有的流动性本质属性。“流民”的称谓,正是人民流动性属性的表现。流动性恰恰是人民面对国家建设时的能动性反应与构成这种反应的基础。作为流动性的政治表达,以逃离为反抗,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早已对“逃离”做出了高度评价。逃离作为“上计”一直被底层人民施展。作为底层人最早的“口述史”,在《诗经》中,人民对君主“嗇且逼急,不务广修德于民”②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深恶痛绝,以至视君为硕鼠,竟提出“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反抗方案。最终,“境内小民纷纷逃散。不久国亦旋亡”③朱熹集传、方玉润评:《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这种反抗行动被人民赋予了正当性,因为“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王风·兔爰》)。“诗经时代”之后仍有“士民亡窜山谷”的大量记载,到了清代依旧有人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去,视瘼乡如乐土。④江立华等:《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这不正好回答了斯皮瓦克“底层人能说话吗”的命题或如斯科特般“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吗?
最普遍的做法是逃避为皇家服务,转而也成为竞争人力的某一个名人或宗教权威的附属,这是最麻烦的方法。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另外的选择就是转到临近的另外一个低地王国。此外还有一种选择则是迁移出国家的势力范围,逃逸到内地和/或山地。⑥[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75页。
为何选择山地作为逃难之地呢?其重要原因就是山地的空间阻力。山地的崎岖地形使国家的脚步无法进入,山地密布的丛林与笼罩的瘴气导致国家的权力触角无法深入其中。增加空间阻力的地形还包括湿地、沼泽、沙漠、红树林等。在压缩空间的技术发明之前,权力的布局不得不绕开这类区域。即便是国家偶尔的军事征服,最终由于补给线和交通线的断裂而无法持久地控制这些区域。所以,“最陡峭的地区是自由的庇护所”。隐蔽的山地堡垒,对于山民而言是有利于隐藏和逃跑的地理环境,对于国家而言却是迷宫般难以习得的地理知识。因此,空间阻力作用下的国家隔离带,维护了山地居民的政治自主性。
赞米亚就是这样的“公共逃难地”。每当中央帝国或低地国家扩展国家空间时,首先会激发底层短暂的反叛,最后那些被国家建设挤出的人口沿着“逃亡走廊”,撤退到赞米亚。逃亡高地的人群根据各自的族群竞争力,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形成一种齿轮效应,使山地依据海拔高度而形成多样化的族群性垂直带谱。
(三)结构性转化:山地的生计、社会组织与族群认同
拉铁摩尔曾经观察到,人们日渐放弃农业资源的利用而专力发展牧畜资源,结果使得亚洲内地的边疆从“半草原”发展到整个的草原化。①[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在国家的进化序列中,从农耕转入游牧,或游耕-采集渔猎,是一种文明的退化。然而,斯科特坚持强调历史和策略选择的作用。逃亡的人群以不被统治为目标,以将自身置于与低地国家相对立的位置为原则,在赞米亚山地生态中“自我蛮夷化”,从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文化形态等方面进行结构性转化。
赞米亚山地居民的结构性转化——社会结构和日常生存策略的政治抉择——揭示了“非国家空间”再生产或者何以可能的问题。
通过协同设计使各专业在同一平台上预先进行可视化模拟建造,使建筑中各类管线铺设、结构高度和室内环境等相互协调,避免碰撞,提前打通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
1.生计转换:游耕与山地作物
重回自主的生存状态,首先需要替代生计的支撑。斯科特详细地考证出来山地居民的农业技术选择过程。以往,灌溉稻作被认为是高效的农作方式,而游耕则是低效的。斯科特指出,相对效率测评需要考虑要素禀赋与农业生态条件。灌溉稻作的高效率是人多地少的农业生态条件下对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标准的结论。但是,对于长期地广人稀的东南亚山地而言,游耕能够节约劳动力而使单位劳动力产出最大化。当然,山地居民的农业技术选择不只是经济逻辑,最重要的是政治逻辑。因为游耕内在地抵制国家征税并增强山地居民的流动性。所以,斯科特称游耕是“逃避农业”,并认为:“游耕有两个优势:它使人们相对自主和自由,以及允许农民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和享用劳动成果。二者的核心都是政治优势。”②[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36页。
一些特殊的山地作物增强了游耕的优势,它们就成为了山地居民的“逃避作物”。逃避作物有广泛的清单,包括山药、马铃薯、红薯、木薯、玉米等。15世纪引进的美洲作物有力地支持了底层向高地撤离。如果仅仅依靠东南亚本地的旱稻,山地居民会被限制在海拔900到1000米的地带内;玉米则让他们可以向上再逃300米。可见,逃避农业与逃避作物,扩展了非国家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正是这些传统养老模式不具备的优势使“互联网+养老”模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优势能否得到有效的发挥,将会对“互联网+养老”模式的顺利推广产生直接性的作用。
2.社会重组:裂变的结构
针对OPC UA TSN在控制器与现场层通信,贝加莱一直是其开发和标准化的核心参与者。在与之相应的标准化组织中发挥着主导作用:OPC基金会、IEC/IEEE和VDMA。贝加莱还积极参与了诸如工业互联网联盟(IIC)进行的测试平台。“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工业机械制造商和运营商能够尽快从协调统一的通信中获得实际利益。”贝加莱战略与创新副总裁Stefan Schonegger说道。此外,贝加莱的母公司ABB已被任命为OPC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3.族群认同:情境主义的实践
非国家空间的不被整合性,是斯科特赞米亚研究结论的核心要点。由此出发,斯科特的贡献不仅在于把空间环境要素带入政治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更重要的是他将被国家史观剥夺的底层能动性重新赋予给他们,从而得以全面地总结山地族群去国家化的策略组合。当然,高度自主性的山地居民不免让评论人使用“高贵的野蛮人”的套路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斯科特在书中声明:“我经常被指责为是错误的,但很少被指责为含糊不清或晦涩难懂的。”②[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页。斯科特思想的张力与想象力,足以让更多的“山地式”学人站在更高处继续前行。
四、讨论:山地政治学、斯科特议题与“赞米亚后传”
赞米亚的研究旨趣在于重建边缘的自主性与边缘人的能动性。作为一个“逃亡带”,赞米亚的形成“归功于”中华帝国的超前扩张,又被东南亚硕果仅存的低地王国强化。为了逃避国家的统合,山地居民从平原迁徙到低山地,又将更早的山地居民挤上高山。上山的人们并没有“移植”平原谷地的文明,否则山地最终不过是低地社会结构的复制品。因此,如果简单地以低地社会结构来框限赞米亚,或者以天下观、华夷秩序来审视赞米亚,赞米亚社会景观的异质性与多元性便一直“躲藏”在国家历史的阴影下。
山地的族群认同是多元的,认同的表达被特定的社会情境所诱发,像变色龙那样随着背景变化而改变颜色,也即群体间的界限可以相互渗透,身份认同灵活多变。斯科特质疑了关于族群认同的“原生论”与“文化论”,指出了这种情境主义的族群认同背后的逻辑“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手段”,用来调节与国家的关系。④[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302-348页。赞米亚山地居民的族群认同最本质的特征被斯科特称之为“反国家的民族主义”。它既排斥国家(使国家的统合难以进行),又防御国家(使得社会难以从内部发展出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而山地的口述文化则为认同系谱的制作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在口述文化中,每一次讲述都反映当时的利益、权力关系和周边社会的亲属结构。口述为山地居民提供了灵活多变的族群认同的可能性。相反,如果通过书写来传承系谱,那么山地居民的适应性会大打折扣。
由于工业、农业的发展和城镇建设等原因,浊漳河南源上游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总量日趋增多,其污染源主要是一些钢铁、煤炭和后续化产品企业,部分企业偷排偷放严重超标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致使浊漳河水污染加重,河道生态受损,其自净能力直线下降,浊漳河流域生态系统遭受到严重破坏,污染河水的渗透也造成了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浊漳河南源监测断面位于工程建设区下游,该控制断面能较好地反映湿地工程建设前的水质状况。
(一)山地政治学
研究非国家社会原本就是人类学的长项。但斯科特并没有停留于静态地对赞米亚进行功能论的民族志构画。斯科特超越了人类学关于非国家社会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山地政治学的“去”国家研究范式。
山地政治是国家建设的反身物。山地社会去国家化的历史过程包括两个维度:排斥国家(使国家难以征服和统合,难以加以控制,难以财政征用);防御国家(使得社会难以从内部发展出一个稳定的等级结构)。山地社会的去国家过程得到了三项技术的支持:一是流动性与地点的选择(逃得越高,空间阻力越大,国家的权力触角就越难俘获);二是社会结构的规模与分散程度(社会组织结构越是具有裂变与聚合的弹性,就越有调节与国家距离的能力);三是生计技术的调整(增强自身的流动性与降低国家的征用性)。
在构建了山地政治的理论框架之后,斯科特将“去国家化”的历史过程植入具体的空间结构之中。在分析层面上,自然生态地理的政治社会效应成为发掘的重点。空间阻力、山地垂直带谱的生计效应、山地垂直族群景观分布、山地垂直生态位都是理论构建的基石。山地为赞米亚难民、山民提供了逃避国家统治的政治掩体;不被国家统治的技术组合是基于山地生态环境的精心发明,表现出了一种选择性亲和。正是在山地空间的政治隔离带的作用下,山地民既有能力选择与国家发生交换关系,又不会丧失他们更为珍惜的政治自主性。
(二)斯科特议题
斯科特对赞米亚的研究成果可谓是一串璀璨夺目的珍珠。人们可以从赞米亚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视角中获得启示,除了前文已经涉及的议题,还可以从中采撷出一些可以拓展的议题。
然而,所谓“无历史的族群”并非处于时间之外。斯科特在开篇处引用了克拉斯特的论断,认为无历史的族群的历史就是反抗国家的历史,实际上,族群有多少历史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确定自己与强大的、有文字的邻居的位置关系,也为随时逃离国家时能够轻装前行。山地居民有着多重的历史,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任选一种或者组合使用。他们可以像阿卡人一样创造出悠久和精细的系谱,也可以像傈僳人和克钦人一样,只有最短的谱系和移民的历史。
1.山上住着野人,还是神仙?
由此之外,纵观整个艺术史,女性主题艺术的概念仍有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背景,所以并不是所有包含女性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女性艺术。这里所提到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它可分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山上是否有文明,山地居民是否是被社会进化序列所遗弃的野蛮人,是斯科特理论构建的主要关怀。该议题针对于布罗代尔关于文明不上山的论断。斯科特指出,有关文明的想象需要一个野蛮的未经驯化的对应物,它们往往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外,并最终被驯服和统合。可见,关于文明的议题,印证了恩格斯的论断。所以,在全书的结尾处,斯科特尖锐地提出,“如果用‘国家臣民’来代替‘文明的’,用‘非国家臣民’来替代‘不文明的’,那就差不多对了”。③[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21页。
山地族群被污名化的根本原因不过是他们坚持身处国家空间之外而已。而这些污名实指,其实是“自我野蛮化”,是那些逃避国家的人群在山地精心设计出来的技术操作。所以,斯科特指出,山地居民并非低地国家所想象的进化之前,而应该被理解为之“后”,后灌溉水稻、后定居、后臣民。“后”的政治效应表现为山地居民拥有低地国家臣民丧失的自主性。
(2)蛋白质膜。该类型保鲜膜主要是将动植物的分离蛋白作为原材料,并且具备有阻油性、可食用以及可生物降解等应用优势,因此具备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常见的蛋白质膜包含有大豆保鲜膜、小麦蛋白膜以及乳清蛋白膜等等。通过大豆来进行蛋白质保鲜膜的制作时,发现在干燥温度50℃下,大豆的分离蛋白质质量分数达到了2%,凝胶多糖的质量分数保持在1.2%,甘油质量分数保持在1%以下时,该保鲜膜的抗拉强度以及阻湿性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2]
2.国家构建的财政逻辑④进一步讨论参见拙文《财政空间的生产:“山川林泽”与国家构建的财政逻辑》,《求索》2019年第1期。
正如斯科特所言,山地社会与低地国家是一对黑暗双生子。透过山地社会的窗口也可以看到“镜像”中的国家。低地国家的建设核心是将人口集中治理技术可行的核心区域。人力与谷物是国家财政汲取的主要对象。如此,奴隶制与水稻生产都是技术发展的关键里程。斯科特发明了一个核心概念国家建设的逻辑——国家可获得生产总值(SAP)。
3.国家景观的制作⑤进一步讨论参见拙文《国家景观的制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2期。
稻田,意味着被适当组织起来的臣民和他们的产品所形成的文明景观。“国家景观”的概念承袭了《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的思路。与水稻国家景观对应的是繁杂的山地景观。采集、游耕、山地作物所构成的景观,不合适国家征收,因而被认为是不文明和野蛮的。所以,景观的国家性(stateness),即适合国家征收的农业景观,成为了判断文明程度的坐标。
4.农作的政治性
作物构成与配置、种植方式等看似技术中性,实际上在山地与低地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效应。逃避农业与灌溉稻作、山地作物与谷物相对。后者与国家及其征收相亲和,而前者则增强了山地居民的流动性。除了征收性之外,灌溉稻作的农艺特性,在时节周期上促进了社会景观一致性,增强了社会结构的整合性。而分散与多样的山地作物,则很少需要社会合作,因而也就内在地抵制着等级化的社会结构生成。
以上只是对斯科特议题清单的简要列举。正如斯科特期待用海上赞米亚及江河湖泊逃难所的研究,来拓展非国家空间边界那样,这个清单还可以不断地延长。
其政逆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他变异皆属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见适于天矣。[8]3266
(三)“赞米亚后传”
人类学家的田野分布在那些国家不在场而人们自治的空间。由此,人类学家或多或少做出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承诺,他们从那些正在与资本或权力相抗衡的人群中获得某种完全不同的实践和形式。然后,他们期待着以此在现代社会的大势中获得改善的可能性。赞米亚的故事鲜明地重申了人类学的承诺。即便斯科特关于赞米亚的研究内容保持了程序的价值中立,他的选题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价值立场。然而,在描写赞米亚地区长期以来的不被整合性的同时,他非常清楚,“在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
从19世纪开始,在国家之外生活第一次成为不切实际。如此,国家缘何上山(国家建设的垂直维度)以及被国家整合后的山地社会变迁,作为“赞米亚后传”的研究内容,或许可以成为学术增长点。①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拙文《禁山后国家缘何上山》,《社会发展研究》 2018年第3期。面对“大势所趋”与“避而不谈”,何处安置作为非国家空间的赞米亚山地研究的现实关怀呢?曾经长期存在的国家之外的生活机会选择与历史便被遗忘。这对学术研究造成了惯性。例如在华南研究模式中,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的惯性问题就是:“第一,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国家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应用什么办法?”可能,科大伟提出“告别华南研究”的原因也在于此。②华南研究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29页。因此,王铭铭提出了寻找东南与西南两大“学术区”之间纽带的呼吁。③王铭铭:《东南与西南》,《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除了学术导向之外,就现实关怀而言,赞米亚山地展示了另类的生存智慧。“群山造差异”。斯科特在文中明确地引用的德勒兹“千高原”的论述。显然,赞米亚山地居民的“游牧政治”是差异地理学与建基于流动性之上的底层能动性的复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将赞米亚山地居民视为德勒兹笔下的游牧战士,那就“不要将这种游牧主义设想为原初状态,而应将它看作惯于定居的群体突然发起的一次冒险,这些定居群体为一种移动魅力、一种外向性魅力所推动。”④德勒兹:《游牧政治》,载王明安等主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可见,逃入山地是躲避国家编码的解辖域化冒险,所生成的逃逸线预示着山地生活的自主性。
福柯曾言,古希腊以来一直存在着生存美学,“一种努力使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智慧。⑤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4页。赞米亚山地居民不被统治的艺术何尝不是一种生存美学。山地居民不关怀普遍性的历史主体,也不谋求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统治地位。他们的生存美学不仅是“关怀自身”,更导向族群的自主性与生活的多样性。即彼即此。
对于身处“后赞米亚时代”的我们,仍旧存在逃避新自由主义与极端现代性霸权的张力。高山上的乌托邦固然寄托着“高贵的野蛮人”的遐思。不过,一旦山地社会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或许它可以成为身处文明社会的我们的一副解毒剂。执此,如何谨慎地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之下守护差异,增强社会的自主性与自组织能力,应该成为“山地式”学人的新使命。⑥“山地式”学人的论述借鉴了叶敬忠教授在“农政与发展”论坛上对斯科特演讲的评述。(致谢: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斯科特作品的中译者王晓毅研究员与笔者的多次交谈,使我受益良多。)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3—0110—08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湘学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凝聚过程中的作用研究”(项目号:17AZX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 鹏,男,博士,湘潭大学碧泉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社会理论与历史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雪飞]
标签:斯科特论文; 山地论文; 国家论文; 米亚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湘学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凝聚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项目号:17AZX007) 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