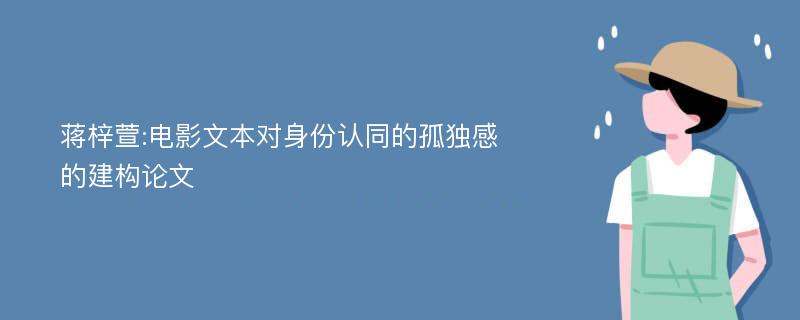
摘要:20世纪末的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独特的政治背景和即将面临全新转折的回归事实,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文化空间。于此背景下,在英国和中国两种文化之间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感成为香港人不可逃避的话题,一系列关于港人身份追寻主题的电影也由此被创作。本文以1995年在中国香港上映的电影《堕落天使》为个案,以电影符号学的视角出发,从文本的四个方面——电影对不同文化空间的再现、电影声音对身份认同复杂性的构建、电影对人物关系的再现和电影对身份迷失情感体验的表达进行分析,探究电影文本对香港人追寻身份认同过程中孤独感的建构。
关键词:电影符号学;文本分析;身份认同
一、电影对不同文化空间的再现
电影运用了大量的符号,通过各色人物的悲欢交集隐喻出两类生活状态——“不确定的、自由的独身生活”和“回归后的、安稳平淡的正常生活”。
阿明的职业是“杀手”,充满不确定的危险职业,隐喻着典型的“自由主义”。他的故事里有两个重要形象——“西装革履的男子”和“小学同学”。“前者在符号系统中所指的是一种世俗定义下的平稳生活;而“小学同学”向杀手递出的“婚礼请帖”即代表了对自由者发出平稳的家庭生活方式的邀请函。电影中,阿明将请帖扔出车窗外,画面随之变成黑白,再次强调一种与现实生活的背离,阿明“这种场合不适合我”的台词,并非指杀手不适合参加婚礼,而是意在他不愿接受婚姻,这种走向日常生活形态的选择。
志武代表着杀手的对立面,象征着渴求生活的人群。这一人物在影片中被定义为哑巴,他用强拉别人洗衣、强按别人洗头、强逼别人买茄子、半夜三更给猪按摩的方式与场景中的人事进行强行交流。夸张荒诞的肢体语言表征出迫切与他人沟通的心理概念,在符号系统中意指着人物渴求正常生活方式的强烈愿望,体现被高度现代化社会异化的港人内心深处无以排遣的孤寂。
我们将电影文本所隐喻的这两类生活状态带入回归前夕的香港文化语境中,它们分别对应着影响香港的英、中两国的不同文化——殖民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文化和回归祖国的、融入传统的寻根的文化。主人公们最开始都是在自由主义的文化下生长,随着回归式寻根文化的迫近,有的港人不愿改变原有的生活状态,他们为另一种状态惶恐不安,却也在自由的生活里感到麻木和疲倦;有的港人渴望改变,却因难以探寻融入新文化的方式而焦虑;有的港人似乎可以实现转变,却意识到新的状态也未必能带来心灵的归属和持续的幸福感,为此感到迷茫和困惑。
本期我们采访了法国摄影师Réhahn,他专注于拍摄世界各地的人文风貌,希望在这些文明消逝之前,用影像记录它们。
电影中声音的运用更突显出港人在世纪末的特殊时间里,追寻自我的孤独感。喧闹的都市背景反衬出人群的微弱,混乱的生活使他们无法认同自己都市者的身份;而冰冷的机器音和单向的自语阻隔了构建家庭关系的可能,回归家庭者身份的理想似乎也变得渺茫。都市者即是自由主义文化之下的身份,而家庭成员则是回归传统文化之后的人物象征,港人在两种文化之间迷失,他们逐渐怀疑自己自由者的身份,又无法在交流中完成为对家庭性的认同,这种在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复杂心理使他们感到更加孤独和无助。
二、电影声音的运用建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志武的故事里,有一位被他强迫买甜筒的长发男,他的生活即隐喻了以志武为代表的港人所追求的、“家庭式”的状态。长发男吃不下甜筒,本想叫妻子一起吃,却未料妻子将全家老小一起带了过来。长发男短短几句台词,却烘托琐碎且庸碌的家庭氛围。值得注意的是,长发男妻子的形象被塑造的满脸油腻、沧桑衰老,意指着一旦回归了日常的家庭生活,即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并且接受沧桑庸碌的人生状态。影片接近尾声时,志武已经过上了他一直追求的平淡生活,然而他此时的形象,全然没有了开始的神气,苍老和颓靡,对应的就是长发男妻子的形象。
*Liu Mingli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at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CICIR,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European economy,European integration,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指纹是指尖表面上交替分布的脊线和谷线图案。指纹图像有着许多不同于其它图像的特点,其纹理性和方向性比较强,而指纹图像的方向场代表了指纹的这种固有性质。通过原始指纹图像的纹理信息,求出每一个像素点的切线方向,就可以描绘出整幅指纹图像的方向场图,而方向场图又为后续指纹图像的滤波、特征提取奠定了基础,故该方向场估算十分重要[12-13]。
三、电影对人物关系的再现
电影文本通过人物间的互动构建出两类人物关系模式——“快餐式”与“家庭式”。前者象征着自由主义下的、无根的、易被遗忘的关系模式,影片中以阿玲与阿明的感情为代表,他们相识于麦当劳,“麦当劳”的意象即是代表快餐,意指着便捷而实惠的爱情,一种来去自由的人物关联。
《堕落天使》构建出一个嘈杂、喧闹、混乱的都市环境,与此相对比,影片中的人物大多时候是沉默的。
电影中主人公的生活大多是在与他人“快餐式”的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他们都是自由的独身者,很难与他人建构稳定的“家庭式”的关系,然而“家庭式”的关系也并非是孤独的解决办法,与他人稳定关系的建立也许会带来牵绊和禁锢,意指着回归家庭并不意味着找到归属感,港人也无法在这两种人物关系模式中找到真正告别孤独的答案。
四、电影对身份迷失的情感体验的表达
电影文本十分强调时间的概念,常以大限式的时间为人物提示出一种生存焦虑。“1995年6月22日,意大利的桑普多利亚队来香港打了一场友谊赛。他明天就结婚了。”对失恋的采妮而言,如果在期限之前见不到男友,就标志着他们感情的过期。限期的表达在香港文化的特殊语境里,是对1997年香港回归的隐喻,对大限式日期的反复提及,实际意指着对港人内心焦虑不安的强调。
电影对港人在身份追寻过程中的孤独体验的态度是悲观的,他们不断遗忘和被遗忘的过程隐喻着他们无法在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里建构自我,也无法说服自己接受任何一种文化,在此过程中,永恒的孤独感也因此被建构。
参考文献:
[1]张然.王家卫电影后现代主义影像风格下的现代主义作者观念[J].电影文学,2012 (15):40-41.
[2]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92.
[3]姚晓濛.电影符号学及其批评[J].当代电影,1989(06):6-14.
作者简介:蒋梓萱(1998.8-),女,汉族,江苏镇江人,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新媒体;广告;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标签:电影论文; 港人论文; 身份论文; 文化论文; 人物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20期论文; 苏州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