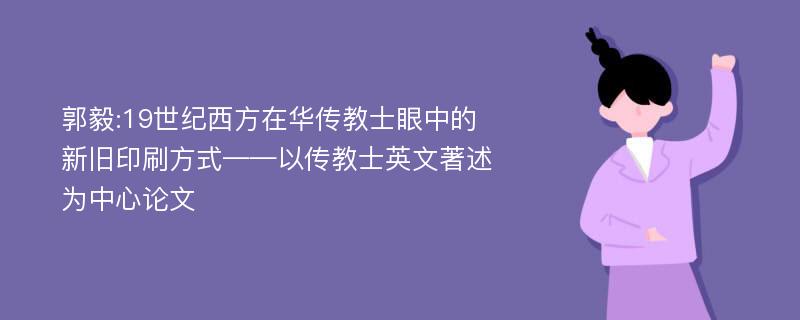
摘要:本文使用新发现的一手英文史料,通过梳理19世纪西方在华传教士对新旧印刷方式利弊的思考和评价,研究其引入现代印刷技术的动因。研究发现,19世纪在华传教士认为铅合金中文活字印刷术具有综合优势,特别是在提高印刷质量方面作用明显。
关键词:传教士 出版 印刷技术 雕版 活字印刷 石印
学界以19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来华并传入铅合金中文活字及机械化印刷技术为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发端标志,①叶再生:《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载《出版史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5—14页。这说明印刷技术革新问题关乎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以往研究证实了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后,重视印刷书籍,广布西学知识,是出于传教需要,②谭树林:《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然而传教士来华后为何不满足于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而要以机械化的铅合金活字印刷术取而代之?换言之,他们究竟如何看待当时中西印刷技术,③19世纪初中国出现的“中西印刷技术”包括雕版印刷、凸版印刷(主要是金属活字印刷)和平板印刷(主要是石印)。其中雕版印刷系中国传统印刷方式,为中国书刊印刷广为采用;凸版印刷与平板印刷均系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印刷方式。一般认为中国于11世纪已应用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但西方传教士传入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与之不同。关于中西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区别,参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5页。关于传教士引入中国的西方印刷技术述评,参见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著,张志强等译,郭晶校:《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又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取舍呢?
从媒介史角度讲,回答这些问题比考证何人于何时传入何种技术更为重要,因为这些传教士作为中国印刷出版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先锋,其行为必定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诚如传播史学家詹姆斯·W.凯瑞(James W.Carey,1934—2006)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文化史观时所说,“凯撒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穿越卢比肯河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重塑凯撒穿越卢比肯河时的感觉,即在这一行为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态度、情感、动机和期望”,④James Carey,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1 (1974): 3—5.因为这种“感觉”影响着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定社群的行为。因此,传教士在印刷技术新旧交替时刻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中国印刷出版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动因。
实际上,19世纪西方在华传教士已在国内外的英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西印刷技术得失的明确论述。这些文献不仅是传教士在技术革新过程中所思所想的直接证据,而且其作为话语实践发表在大众报刊而非日记、书信等私人空间,也势必在阅读社群中产生宣传作用,从而推动新技术观念在阅读社群中的普及。因此,对研究中国印刷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而言,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知价值。
一、对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的评价
熟悉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术的传教士们来华后,首先接触到的是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并在实际印务中对雕版印刷的缺陷有所体验。1833年2月,传教士主持的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总结雕版印刷的六个缺点:第一,“并不适用于讲求时效的印刷品,如号外、销售价目。因为在木板上刊刻字符需几日”,无法像金属活字印刷那样满足印刷时效性。第二,“木刻板尺寸较大难以携带”。第三,“印刷次数过多则刻板易损坏,印刷清晰度降低。即便上好的板材,也只能印刷一万至三万次”。第四,“若一个汉字在一本书中出现上千遍,也须反复刻制同一字符,而刻好的木板无法用以印刷其他作品”。第五,“中文雕版印刷不适用于印刷其他语言书籍”。第六,“若刻板破损则无法再印刷”。①“Literary Notices,” Chinese Repository 20.10 (1833): 414—422.
1834年10月,该报在对比雕版印刷、石印和金属活字印刷优劣时,又将雕版印刷缺点加以强化。其一,木刻板易受白蚁蚕食,难以保存,认为“如果一块刻板残损,除非工匠重刻,否则其余刻板也都没什么用了”。其二,刻板数量多,占用较大储存空间。“一本2 080页的八开本经书,如果每张木板雕刻两页,需制1 340个刻板。按每立方英尺储存20块刻板计算,需占67立方英尺”。其三,刻板完成后无法在不花钱和不影响页面美观的情况下对内容进行修改。其四,认为“经过二十年对语言知识的积累,传教士本应印刷一些更好的翻译版本,但因为用旧刻板印刷书籍比刻制新板容易,很多传教士习惯于使用旧板”。其五,“木刻板印制的作品版本单一,异教徒在收到这些印刷品时感觉司空见惯,他们渴望看到一些新东西”。其六,“刻字工人经常惹麻烦。为了维持秩序,传教士常常十分恼火”。其七,“刻字工人来自中国,若无通关文牒,他们无法离开中国。这意味着整个印刷流程仰仗中国供给。一旦中国中间人辞职或刻字工人遭受严格的出境控制,印刷工作会立即中断”。其八,“花费两倍于金属活字印刷”。②Typegraphus Sinensis, “Estimate of the Proportionate Expense of Xylography, Lithography, and Typography as Applied to Chinese Printing,” Chinese Repository 20.6 (1834): 246—252.对于这些有关雕版印刷的负面评价,当时在华传教士普遍认同。③如传教士马尔科姆(Howard Malcom, 1799—1879)和博纳(Andrew Redman Bonar, 1810—1892)均认为“十分公允”,参见Howard Malcom, Travels in Hindustan and China.Edinburgh: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1840, p.57;Andrew Redman Bonar,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Enterprise.London: Thomas Nelson, Paternoster Row and Edinburgh, 1852, pp.120—121。1820年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指摘,参见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p.239—243.
为了提升集成模型的差异化,Boosting算法是一个逐步递进的方法,每一个分类器都是前一个的通过调整样本权重的改进模型。
然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印刷术也并非一味否定。作为《中国丛报》的负责人兼传教士中富有经验的印刷工人,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对各种印刷技术的利弊有着清晰的认识。尽管他认为印刷大部头书籍时,雕版印刷具有明显缺点,④卫三畏认为《佩文韵府》的印制和保存令印刷工人犯难:“腐烂和蛀虫威胁着木刻板保存,更不能沾到丁点火星。”但仍然肯定其“最大优势在于制作材料的廉价。一块木板、几把錾子、一些纸墨、一位技术娴熟的印刷工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印刷车间”。此外,“传教士可以随身携带这些木刻板远行,并在需要时印刷书物”。在少量印刷廉价中文书籍方面也是金属活字印刷所无法比拟的。⑤S.Wells Williams, “Movable Types for Printing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5.1 (1875): 22—42.《中国丛报》甚至认为“除耐用性以及能够统一多个页面的字体样式外,雕版印刷术似乎拥有欧洲金属活字印刷的所有优点”。其理由有二:第一,“假设使用金属活字印刷带有释义和注解的科学书籍,正文使用大号字体,释义字体稍小,注解字体更小,再加上一些数学、天文和物理符号,这样算来至少需六种不同字符,即需要六种字模,花费巨大。而使用雕版印刷,所有的汉字无论大小字体都由一人刻制,速度、价格几乎一致,不必产生额外花销”。第二,“雕版印刷工序和仪器极为简单,无需铸模厂和复杂的机器来印刷装订。对于小规模印刷而言,一套桌椅足矣。刻板工具也可打包携带”,这对于印刷和传播基督教义意义重大。文章写道:
我们要正确看待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要对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在具体文章中的应用进行合理的评估,理论上不求甚解,则会影响翻译实践的应用效果。其次,在语言层面的异化或归化争论是可以被允许的,但这些研究的效果不能表面化,即根据一些例文、例句,根据简单的形象翻译就完成了文章翻译,这就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权威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再者,归化和异化的策略选择如何与文章实际做到较好的结合,这也是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要在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双管齐下的下功夫,构建完善翻译理论应用体系,从而让我国的整体翻译水平实现较好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丛报》对石印技术利弊的评价相对全面。在谈及优点时指出:其一,“可依据书籍需求量和纸张供应量印刷少量版本”。其二,“对每一个后续版本可以不同程度地修改完善”。其三,“一些为特殊目的而印制的宣传品可以低调进行印刷,尽可能少引起外界注意。印刷一份六页的小册子,只需两三天”。其四,“在只有一位传教士传教的穷乡僻壤,小册子的需求不多,活动经费不足以维持雕版印刷或金属活字印刷。这种情况下,石板印刷是最好的选择”。其五,“石印适合于印刷多种语言以及一些尚乏活字的图书。石印还特别适用于印刷图画以及任何语种的书法作品。如果没有石印技术,印刷日文和韩文字典几乎是不可能的。”⑥Sinensis,op.cit.,p.246.
一年后该报又补充:第一,“筹备雕版印刷的费用比筹备石印和金属活字便宜”;第二,“经典可按需求和纸张供应情况不时地印刷”;第三,“版面一旦刻成则永远保持相同版式”;第四,“传教士初到一个国家,可接管前人的刻板直接印刷”;第五,“整个印刷流程中国人可自己完成,无需借助欧洲的机器和工人帮助”;第六,“工人在筹备木刻板时也潜移默化受到宗教熏陶,变成基督徒,继而成为中国的福音传道者。虽然这并不是雕版印刷所特有的,但其功效强于其他印刷方式”。②Sinensis,op.cit.,p.246.
二、对石印技术的评价
尽管中文金属活字印刷也有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完全可以被克服。其一,“在建造活字印刷所时需要欧洲印刷工人的帮助,而聘用他们的费用高于中国人十倍。然而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传教士自己就懂得金属活字印刷知识”。第二,“总有一些字符是现有活字没有的,需另外铸造。但这些字符很少,而且可以简单地用锡刻制”。第三,“使用金属活字印刷需要昂贵的印刷机。但在印刷中文的间歇,还可以印刷其他语言的书籍,而且几乎在每个布道点传教士们都已拥有这样的一台印刷机”。第四,“普遍使用金属活字印刷后,已有木刻板怎么处理?我们的答案是雕版印刷当然可以继续存在,但是未来的经书和小册子应该用凸版印刷机印刷”。第五,“金属活字大小规格一致,无法在版面中插入评注,除非准备两套活字,一套大号的,一套小号的。对此我们认为马六甲和中国地区的小号汉字已经存在,可以用来印刷注脚”。④Ibid..
当中国的巡捕到处搜查福音书、缉拿基督教印刷工人时,工人们可在夜里悄悄溜到另一个城市,在那里重新开展印刷,就像什么都未发生。即便匆忙之下未能带上工具,也可在24小时内重新置办这些工具。”这种策略被当时传教士称为“巡回印刷(itinerant printing)。①“Literary Notices,” op.cit., p.414.
植株样品:将田间植株样本剪切成1 cm以下的小段或切碎,在不锈钢盆中充分混匀,用四分法缩分样品,分取2份200 g的样品,分别装入封口样品容器中,粘好标签,贮存于-20 ℃冰柜中保存。
三、对中文金属活字印刷的评价与思考
不同于鲍照诗歌中的抒情、议论或借重于繁复的用典,如《代白头吟》,或源于简单明净的意象,如《王昭君》。李白诗歌有许多创新处:围绕女性主人公展开完整的叙事、抒情,用典密度小,叙事线条疏朗单纯,情景交融,营造了凄美的意境,感染读者。
翻译:“我觉得你说过的,”老鼠说,“我接下去谈。“梅尔西亚伯爵艾德温和诺森伯利亚伯爵穆尔卡声明拥护他,甚至连那位热爱祖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梯干德也发现那个是适当的……”[12]
在华传教士对雕版印刷并不满意,对石印的缺点也有清晰认识,但是他们对金属活字印刷术却好评不断。1834年7月美国波士顿出版的《传教士先驱》(The Missionary Herald)写道:“这种技术被纽约许多有识之士广泛提及,他们几乎都提到用铅合金金属活字替代中国传统的木刻板”。①“Chinese Stereotype Printing,” The Missionary Herald 30.7 (1834): 268.在新教传教士眼中,当时西方世界已普遍流行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在印刷中文书籍方面,优势远胜于雕版印刷和平板印刷(石印)。1835年5月《中国丛报》评论道:第一,“铅合金活字切割费用小,还可以远距离运输”。第二,“所占空间仅是木刻板的一半。在中国的印刷车间,昆虫对木制字块蚕食严重。一个字块若久置不用,时间一长,表面塌陷,内部几乎被昆虫吃光。而应用金属活字印刷,白蚁等中国印刷车间里的常见昆虫对铅字损害不大”。第三,“铅合金活字的美观度也是传统木活字印刷术所不能比拟的”。第四,“这种印刷方式节省纸张,最大程度降低书籍厚度”。②“Chinese Metallic Types,” Chinese Repository 35.5 (1835): 528.
对传教士而言,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术优势明显。第一,“既适用于印刷大部头的书籍,也适用于印刷页码少的版本。适合印刷定期出版物和《圣经》”。第二,“如果金属质地较好,在活字损坏前可以印刷百万份之多”。第三,“相比雕版和石印,金属活字印刷节省成本”。第四,“从马礼逊的字典可以看到,金属活字印刷的成品更加美观,比雕版印刷更容易取悦中国人的眼睛”。第五,“使用金属活字印刷,不必再依赖中国印刷工人,马来西亚的小工同样可以从事印刷”。第六,“排版后可轻易修改版面内容”。第七,“首次制造金属活字费用很高,但这些活字可以不间断地使用20年,就算不能用了,也可作废品变卖”。第八,“在印刷字典时,金属活字可以与欧洲字母相结合”。第九,“印刷机在印刷中文印刷品的间歇还可以用来印刷其他语言的书籍”。第十,“中文金属活字占用的空间不大。每套活字箱只占据九平方英尺空间,三至四个活字箱可以容纳三万个汉字”。最后,“不必再担心白蚁和火苗的侵害”。③Sinensis,op.cit.,p.246.
虽然西方在华传教士并不否认中国传统印刷方式的优点,但总体而言他们对雕版印刷术不甚满意,诚如1844年印度一份传教士报刊评价道:“尽管中国人先于欧洲掌握了印刷的技术,但是在雕版印刷之外,中国印刷技术别无进步”。③“Spirit of the Indian Press,” The Bombay Times and Journal of Commerce 20.1 (1844): 22.而这种不满尤其表现在对雕版印刷和石印、金属活字印刷的对比中。19世纪30年代,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在华传教士也就其利弊与雕版印刷术进行了对比论述。比如卫三畏认为石板印刷较雕版印刷有一些优势,“一是它可以轻易地将多种语言混成在一个页面内,二是能够让作者直接印刷自己的作品”。然而,“石板容易损坏破裂,很少有传教士可以娴熟地驾驭,或是教授本地人如何使用。在热带地区特别难于防止油墨相互渗透,印出的文字非常模糊”。④Williams,op.cit.,pp.22—23.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也认为,尽管石印有其优势,但在马六甲一带的使用效果不如在较冷的地方好。⑤“Printing and Lith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25.6 (1829): 192—193.
金属活字印刷的种种优点以及那些“可以避免的缺陷”体现了在华传教士对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偏爱。这也使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对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普及充满信心。他们坚信中文金属活字印刷对于传统印刷方式的优越性好比欧洲火器之于中国刀剑,势必风靡。有传教士称“金属活字印刷术已被证明优于传统的中国木活字印刷,这就像欧洲商人优于中国摊贩”,认为中国人将像承认欧洲船舶的先进性那样承认金属活字印刷的优越性。⑤“Literary Notices,” op.cit., p.414.还有人在宣传金属活字印刷时称,“中国人喜欢守旧,但在过去与欧洲的战争中,他们对应用欧洲器物表现出极大渴望。在学习欧洲工程技术方面比其他国家都好”,⑥“Spirit of the Indian Press,”op.cit., p.22.借此印证中国人渴望学习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术。
传教士在文章中也提到石印技术的缺点:第一,“由于石印产生额外的工作(如每印一张就要湿润石板,每印十次就要清洗石板),印刷效率较低”。第二,“考虑到石板的腐败速度,在印制上万份作品时,每印一两千张后,就需重新在石板上誊写作画”。第三,“在印刷时可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如环境变化、材料问题、工人分心)”。第四,“由于每张页面的印刷有好有坏,石印图书的画面不规则”。第五,“首次印刷的花费高于雕版印刷”。⑦Ibid..
庚午,刑部尚书、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罢为工部尚书、知颍州。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论事烦数,或面折之。及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修,不许。孙甫、蔡襄遂言:“章懿诞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被诏志章懿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殊坐是黜。[1]3699
四、西方传教士改进中国印刷技术原因再认识
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作为中国印刷出版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环,19世纪西方在华传教士引入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术以其对多种印刷技术的利害思辨为前提。在这些考量中有三点值得进一步阐明。
其一,如何看待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方式节约印刷成本?学界传统观点认为中文金属活字印刷价格低廉。常列举的佐证是:据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估算,金属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节省三分之二的花销。①“Literary Notices,” op.cit., p.414—422.然而,这一观点在缺乏更多一手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似乎失之笼统。比如,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1892)认为两种印刷方式费用相似,甚至活字印刷成本略贵,因为金属活字印刷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昂贵墨汁,且雇佣外国工人成本高于中国人。②American Missionary Herald, “Amoy,” The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11.11 (1852): 83—85.从铸字角度讲,中文金属活字也未必便宜。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③Robert Morrison, “Chinese Type: To the Editor,”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asia 15.9: 48—49.和郭实猎(Karl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④“Letters from Rev.Mr.Gützlaff,” The Missionary Herald 30.8 (1834): 308.以及另外一些传教士⑤“Mission to China,” The Missionary Herald 29.12 (1833): 452.曾明确表示浇铸中文金属活字的花费太大,以至1833年马礼逊致信《中国丛报》,呼吁“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制造中文活字是在亚洲及其周边岛屿传播先进知识和基督教教义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什么比铸造廉价的中文活字更重要”⑥“Literary Notices,” op.cit., p.414—422.。那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士曼所称的金属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节省花销呢?从前文引证的材料可见,传教士们非常清楚中文金属活字印刷的综合优势,他们对这种印刷方式的偏爱也极可能是考虑到其在重复使用等方面的长远成本效益。对此,一个有力的例证是麦都思曾推算使用雕版印刷印制两千本中文《圣经》(Bible)的费用和所需时间,按马六甲和雅加达两地的行价,需花费1 900英镑并耗时三年。若由石印完成,仅需六名工人,耗时两年,花费1261英镑。使用金属活字印刷,需两名排版工,一名印刷工及一名装订工,耗时一年,花费1 498英镑。显然,金属活字印刷并非最为廉价,但麦氏特别补充道,“乍一看石印最便宜,但综合考虑印刷速度等因素,金属活字印刷占优势”。⑦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London: John Snow, 1838, p.561.
其二,推动传教士发动印刷技术革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传教士印刷业急需从对中国印刷工人的过分依赖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也是“节约印刷成本”的另一个方面。卫三畏曾回忆“当时在广东雇佣中国工人很危险”。1834年麦都思雇佣的三名中国印刷工人都因为传教士工作而被视为“汉奸”并被送进监狱。麦都思遂打算将印刷物料运往印尼和新加坡,并准备在那里聘请印刷工人。但这样一来印刷成本大增,“因此当时大家认为最便宜的印刷方式就是金属活字印刷”。⑧Williams,op.cit., pp.22—23.1836年传教士杜里时(Ira Tracy, 1806—1875)在给《传教士先驱》的信中也提到“寻找中国印刷工人的进展十分缓慢”,⑨“Letters from Mr.Tracy,” The Missionary Herald 32.5 (1836): 24.以至传教士们深感“在中文金属活字引入之前,中文印刷将完全由中国人操作”,⑩“Mission to China,” The Missionary Herald 32.1 (1836): 14.这已明显影响到宗教宣传品的印制。
其三,探索和引进中文金属活字印刷也有美学之考量,这一点现有研究鲜有提及。一是印刷品的清晰度。19世纪在华传教士渴望降低中文《圣经》厚度,提高便携性。既要缩小字号,又不能妨碍印刷质量,成为当时传教士社群中的现实需求。经过戴尔(Samuel Dyer, 1804—1843)等人的先后改良,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术已能够满足这种需求。⑪据传教士布朗(William Brown, 1823—1907)回忆,中文金属活字经过改良后,可将《圣经》压缩为一卷,其中《新约》少于90页。参见William Brow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London: Thomas Baker, 1864, p.258.1848年传教士戈达德(Josiah Goddard, 1813—1854)在《浸信会杂志》(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中写道:“各印刷方式均有优劣之处。可是目前对小号字体的需求尤甚,雕版印刷印制小号文字模糊得难以阅读,而金属活字印刷则有压倒性优势”。①Josiah Goddard, “Metallic Type and Block Cutting,”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28.3 (1848): 75.1852年1月《传教士先驱》也评价中文金属活字印刷“真是比最好的雕版印刷品更美观、整洁、更加清晰”。②“Recent Improvement,” The Missionary Herald 48.1 (1852): 18.直到1909年美国传教士师图尔(George A.Stuart,1845—1919)在上海演讲时,仍不忘称赞金属活字印刷“清晰的印刷效果可以很好地再现原典”,并认为这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优点”。③“The Press of China Today,” The North-China Herald, 6 March 1909.二是印刷品的美观性。《中国丛报》评价金属活字印制的《新约》(New Testament)样品“字体十分精美,以至最好的雕版印刷制品都无法比拟”,④“Religious Intelligence,” Chinese Repository 20.1 (1833): 376.又称“传教士们非常渴望中文金属活字。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要不是中文金属活字,马礼逊的字典根本无法像这样精美”。⑤“Literary Notices,” op.cit., p.414.然而,关于印刷之“精美”也只是见仁见智。比如米怜认为金属活字印刷的书籍“有某种夸张的僵硬感”,⑥“Chinese Printing,” The Missionary Register 14.7 (1816): 291—293.博纳认为金属活字“十分精美,但中国人却觉得怪怪的”,⑦Andrew Redman Bonar,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Enterprise.London: Thomas Nelson, Paternoster Row and Edinburgh, 1852,pp.120—121.马礼逊则担心金属活字印刷的美感是否只是“基于英国人的观感和偏见”。⑧Robert Morrison, “Literary Notice,” Evangelical Magazine and Missionary Chronicle 24.9 (1816): 352—353.
总之,19世纪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印刷方式的不满和对新印刷技术的偏爱,从本质上讲是从传教的需求出发。传教士笃信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是“传播基督教知识的最好方式”,⑨“Methods of Printing,” The Missionary Herald 28.5 (1832): 138.是“印刷《圣经》或其他优秀书籍”的最佳选择,在中国“会像欧美一样风靡”,⑩“Chinese Stereotype Printing,” The Missionary Herald 30.7 (1834): 268.实际上也是期望现代印刷方式能够在中国造就一场近代宗教改革。虽然西方传教士们最后未能如愿,但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毕竟在客观上翻开了中国印刷出版事业现代化的新篇章。
中图分类号:G210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13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19CDSKXYXW0038)的研究成果之一。
(郭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媒介史研究中心)
标签:传教士论文; 活字论文; 活字印刷论文; 金属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基督教史论文; 《国际汉学》2019年第3期论文; 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19CDSKXYXW0038)的研究成果之一论文;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论文;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媒介史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