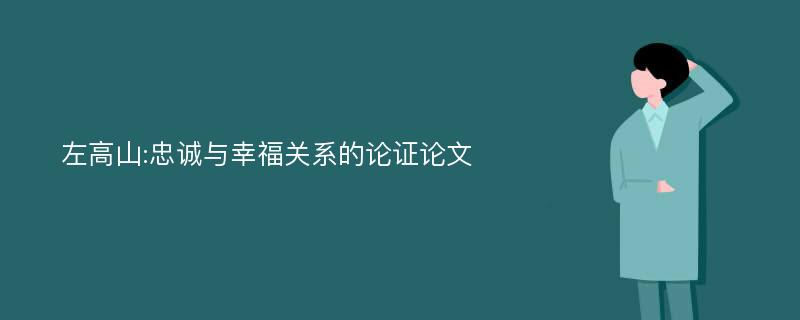
[摘 要]在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无法回避“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通过反思正义、智慧、节制等具体美德是否促进幸福来论证上述问题,但是鲜有人系统地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忠诚对幸福的影响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视为对幸福不那么重要。我们试图从儒家伦理、美德论、功利论、义务论和积极心理学等维度论证忠诚对人类幸福具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尚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忠诚与幸福具有因果关系。
[关键词]忠诚;幸福;美德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无法回避思考美德与幸福的关系,其实质是要回答“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正如伯纳德·威廉姆斯所言:“哲学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值得严肃考虑的事情。”[1](P5-6)古希腊哲学家试图通过反思正义、智慧、节制和勇敢等美德与幸福的关系来回答上述问题,然而,很少有人系统地论证“忠诚”作为一种具体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正如迈克尔·斯洛特指出:“在各种涉己诚实、可信、忠诚与涉他诚实、可信、忠诚之间的联系往往在道德理论的讨论中不被察觉。在这些讨论中,涉己的诚实、可信、忠诚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视为(不那么有价值的或不相关的)特例。人们这么做的理由,可能来自常识道德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他人不对称性。当不涉及对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时,对自己诚实或不诚实,可信或不可信,忠诚或不忠诚在直观上都不被看作道德赞扬或道德批评的基础。”[2](P167)我们在本文想初步论证忠诚作为一种具体美德能否促进忠诚者或者利益相关者的幸福。
超声波是诊断骨盆内脏器病变最佳的辅助检查。彩色多普勒超声下输卵管癌特点:①附件区腊肠型或不规则肿物,囊性伴乳头状回声;②附件区卵巢形态完整;③附件区实性回声内血流阻力指数降低[4]。超声检查在原发性输卵管癌肉瘤与其他输卵管、卵巢良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方面缺乏特异性。CT和MRI在判断输卵管周围脏器的浸润、是否有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指导选择手术方式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MRI在评估肿瘤浸润深度方面比CT更有优势。
一、忠诚与幸福的关系
在日常道德生活中,忠诚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甚至可以说没有忠诚就没有其他美德[3](P117)。人们倾向于肯定和赞美忠诚,否定和谴责不忠[2](P164-165)。但是,人们对忠诚的理解并没有达成共识。同样,人们对与忠诚相关的幸福观念的理解也不一致,因而对忠诚与幸福关系的认识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1.忠诚的现代内涵与古典意义
关于“忠诚”(loyalty)的思想观念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术语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在西方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的效忠誓言中,最初的内涵是忠于法律或忠于合法的政府,后来扩展为忠贞(fidelity)、效忠(allegiance)、忠心(faithfulness)、服从责任与义务等内涵。在实际应用中,“忠诚”的道德特性逐渐凸显出来,不仅含有忠顺(fealty)、顺从(homage)、忠贞、效忠、忠心等意涵,而且也具有尽心(devotion)、依附、不屈不挠、虔敬、信用、绝对可靠和真诚等意义。“忠诚”的意涵如此之丰富,以致于在英语中没有哪个词能够取代它的位置[4](P1-2)。1908年,美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在《忠诚之哲学》一书中把“忠诚”界定为:“一个人对一主义(cause)之自愿的、实际的及彻底的尽心(devotion)。”他进一步认为,一个人被称之为忠诚之人,首先是他有为之尽忠的某种主义,其次是他自愿、彻底为这种主义尽心,再次是他通过某些持久、实际的途径表现他的尽心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哲学教授特洛伊·乔利摩尔(Troy Jollimore)也认为真正的忠诚总是发自内心,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人才能忠于其所属的共同体[5](PX)。综上所述,忠诚既是一种涉己的美德,表现为忠诚者的尽心、忠心、真诚、虔敬等道德特性,同时它也是一种涉他的美德,体现为忠诚者对忠诚对象的顺从、效忠、忠实等方面。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忠”“诚”作为儒家重要的德目是分开使用的,很少看到“忠诚”合用,侧重从“忠”的层面来理解忠诚的意涵。但是,把“忠”等同于“忠诚”或者把“忠诚”等同于“忠”是有失偏颇的,会导致严重的误读[6](P165-174)。“忠”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分析。广义的“忠”是指“发自内心”“尽心”这一抽象的道德原则,体现在不同时期的文献中。例如,《说文解字》将“忠”解释为:“忠,敬也,尽心曰忠。”《忠经》载:“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载:“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孝经》疏引《字诂》曰:“忠,直也。”上述关于“忠”的理解体现了涉己的一面,主要从“忠”的主体来思考“忠”的内涵。而狭义的“忠”则是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具体化为政治伦理规范,主要涉及君、臣、民三者的关系,最初含有利民、利公、利国的意思。例如,《左传》桓公六年载:“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左传》僖公九年载:“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后来的儒家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忠”的内涵,将其扩展到了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范围。
综上所述,尽管“忠诚”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发展变化的,但它作为一种美德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其涉己性或涉他性都体现为某种具体的关系。
2.幸福作为最高的善
无论是美德伦理学还是义务论抑或功利主义伦理学都绕不过幸福问题,尽管它们的幸福观立论的基础不同,但它们关于幸福本质的理解大同小异,都离不开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7](P32)。因为幸福是一切行为的最后目的,它是以它自身而不以任何别的东西为目的,因此它是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可以从人的功能和活动方面来理解什么是幸福,人的幸福是在人的积极主动的现实活动获得的,是通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获得的[7](P25)。然而,人们对这个“最高的善”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把快乐等同于善或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区分三种不同的生活: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7](P9-10)。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人都会选择享乐的生活,他称之为“动物式的生活”,这种生活与放纵相关,只追求肉体的快乐,是不值得欲求的。另有一种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有品位的人”,则把荣誉等同于幸福,把荣誉当成政治生活的目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把荣誉当作目的未免太肤浅,因为荣誉取决于授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过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它持久,但这种生活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并不排斥快乐,不过快乐是指精神上的快乐,他也不否认外在善是幸福的补充,但是沉思的幸福只需要拥有中等财富即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多数哲学家并没有超越他的幸福理论。例如,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幸福指身体上的舒畅和灵魂上的安宁,幸福与人们美好的品德密切相关。然而,大多数人穷其一生都在追求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幸福观。约翰·穆勒认为:“幸福是一种善:即每个人的幸福对他本人来说都是一种善,因而公众幸福就是对所有的人的集体而言的善。”[8](P36)穆勒在此明确指出“幸福是一种善”,只不过他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则那样认为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而已。
根据亚里士多对幸福的分类,我们需要讨论忠诚与三种不同幸福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忠诚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即使区分不同类型的忠诚。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认为幸福就是物质享受和肉体的快乐,那么忠诚之士未必幸福,相反许多不忠之人比忠诚者更幸福,因为他们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如果忠诚之士的目的是实现物质幸福,那么这种忠诚将是暂时的、可变的、工具性的,因为忠诚只不过是实现物质幸福的一种手段。与政治生活或公共幸福相关的忠诚具有政治性或公共性,人们在实现这种幸福的过程中,需要对特定的领导者或组织表示忠诚,前者表现为对政治人物效忠,带有典型的人身依附性,倘若忠诚者仅仅效忠于某个领导者,可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带来更多的政治收益,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忠诚者,而是取决于效忠的对象,往往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而忠于某个政治组织,忠诚者通常认为组织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种忠诚带有人格物化性,忠诚者认为其行为是为了实现公共幸福或公众幸福。与第三种幸福相关的忠诚往往有一种理想或信念作为支撑,带有绝对道德性,它鼓舞和激励着忠诚者去追求和实现最高的善[3](P119-121)。就第三种幸福而言,忠诚无疑将有利于忠诚者本身,将促进忠诚者的幸福,而无论忠诚行为本身实际上可能给忠诚者带来损失甚或灾难。因为这种类型的忠诚者既然信奉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他们就不会重点考虑构成幸福的外在善。
除此之外,SEW还带来了从德国引进的最新的五轴联动并联机器人。这是在传统三轴并联机器人的基础上,增加两根平行旋转轴的从而推出的五轴机器人,通过一个轴转动,同时另一个轴使产品翻转,低齿隙行星伺服减速机保证机器人的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以上。据靳弃疾先生介绍,其通过SEW五个伺服电机,全新一代运动控制器,多轴伺服驱动器及高动态伺服电机,控制终端的五轴联动,实现五个自由度的运行。靳弃疾先生特别强调,SEW除了五轴并联机器人外,还能够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客户定制化数学模型,实现不同客户独特的的机器人运行。
3.忠诚与幸福的三种关系
我们要厘清忠诚与幸福的关系,首先要了解美德与幸福的关系。关于美德与幸福的关系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有益论”认为美德有益于人的幸福;“阻碍论”认为美德不仅无益甚至阻碍个人幸福;“同一论”则认为美德等同于幸福[9](P62-66)。我们认为“有益论”和“同一论”可以归为一类,都是认为美德能够促进人的幸福,而“阻碍论”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会妨碍人们获得幸福,而是认为某些具体的美德并不利于人们的幸福。那么,是否所有的美德都会促进美德拥有者的幸福呢?正如斯洛特指出:常识美德伦理学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是因为有利于其拥有者的利益或者有利于人类(或有感知的存在者)的利益才成为美德”[2](P163)。换言之,美德并不必然有利于其拥有者或者相关者的幸福,因为有些美德要求美德拥有者自制甚至自我牺牲才能称之为美德。例如,战士为国尽忠牺牲,就其个人的总体利益而已,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国尽忠显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但是他可能促进了其他人的幸福[2](P162)。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回答“什么是正义”和“正义的人是否幸福”来回应“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柏拉图的目的是要证明正义的人最幸福,而不正义的人最不幸。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的观点,著名的智者色拉叙玛霍斯认为,正义的人因为忠于法律和道德约束并妨碍了自己的利益,因而相较于不正义的人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不正义的人通常比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好。色拉叙玛霍斯以僭主为例,认为他是不忠和不义之人,但他却是最快乐的人。僭主作为大窃国者,掠夺人民钱财,剥夺人民自由,其暴政极端不正义,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17](P26-27)。僭主无疑是不忠诚的,他用暴力和欺诈手段获得政权,苏格拉底驳斥了色拉叙玛霍斯关于僭主不忠不义反而更幸福的观点。“正义者是否比不正义者生活过得更好更快乐”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应怎样采取正当的方式来生活的大事”[17](P39)。苏格拉底指出,灵魂的优秀或美德即正义,灵魂一旦达到正义,人就会生活得很幸福,因而正义的人才会更幸福。柏拉图认为,僭主的内心充满恐惧、困惑、贪婪和痛苦,其灵魂处于无序状态,总是担心别人也会像他一样不忠或背叛,因此他的生活其实是最不幸福的[17](P379)。
关于忠诚与幸福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为“无关论”,认为忠诚和幸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至少就常识而言,某些其他的美德作为美德也缺乏与其拥有者或其他人的福利之间的联系。”[2](P159)忠诚作为一种美德并不必然能促进忠诚者的幸福。第二种为“阻碍论”,即认为忠诚不仅不能促进幸福而且有害或者妨碍人的幸福。它们往往以忠诚者不幸福的特例或者以不忠或背叛更幸福等反例来进行论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把幸福等同于物质上的幸福,因而某些不忠者或背叛者反而比忠诚者更“幸福”。我们不打算在本文讨论上述两种观点。第三种为“促进论”,认为忠诚能够促进或者部分促进人的幸福。大多数美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家都持这种立场,我们也支持这种观点。例如,亚当·斯密认为,践行美德将会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的幸福。他指出:“当我们考虑任何个人的品质时,我们当然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第一,它对那个人自己的幸福所能产生的影响;第二,它对其他人的幸福所能产生的影响。”[10](P274)根据斯密的观点,我们需要全面考察忠诚对个人幸福和他人幸福的影响,从而论证忠诚是如何促进忠诚者或相关者的幸福的。根据约翰·穆勒的观点,美德是“促进公众幸福的首要条件,因而是头等重要的大事”[8](P38)。人们欲求忠诚美德的原因在于它能“产生快乐”“抵御痛苦”,而幸福也是趋乐避苦,二者具有一致性,人们如果只是追求钱权名利等物质幸福往往会妨碍或损害其他人的幸福,而践行忠诚等美德将有利于促进人的幸福[8](P38)。人们相信美德能够促进幸福是进行美德教育的重要前提。倘若人们认为一切美德或者大部分美德不仅不能促进反而妨碍美德拥有者的幸福,那么要在全社会倡导美德或者进行美德教育将非常困难甚至于不可能。我们接下来将从儒家伦理、美德论、道义论、功利论和积极心理学等多重维度进一步论证分析“促进论”的合理性,因为任何单一维度的论证都无法说明二者关系的复杂性。
二、忠诚与幸福关系的儒家式论证
我们一提到美德伦理学就会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许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具体观点,但是无法否认他们的美德伦理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因此,我们要分析忠诚与幸福的关系自然绕不开他们的美德理论,其核心观点正如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所概括的:美德是人为了实现幸福、兴旺繁荣或过得好而需要的品质特征,包括“美德有利于其拥有者”和“美德使其拥有者成为好的人”两种相关主张[12](P188-189)。这些观点又与“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密切相关。
她很开心,一路吹着口哨,买了一大盒德芙巧克力、一包抽取纸巾和一瓶诗芬直发营养水。到家的时候她忽然想,为什么要买直发营养水呢,她明明是卷发。对着镜子看自己,一直到腰的大波浪,毛茸茸的大眼睛,像极了蔡依林。可是她的下巴是圆的,没有尖,脸颊上也没有酒窝,没有照片上的女人那么美。
虽然洛必达法则是极限计算的一种有效的、常用的方法,但有时运用洛必达法则计算极限的计算量相对较大,且并不是满足型的待求极限都能够运用洛必达法则计算出极限值的。如下实例:
上述忠诚与幸福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规范性或评价性的层面,缺乏实证研究证明忠诚与幸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当代积极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践行美德能够有效地促进人的幸福,拥有美德的人更加幸福[22](P1521)。积极心理学家宣称运用古代智慧找寻积极心理学的源头,其目标是帮助大家找到幸福及意义[23](P3)。
三、忠诚与幸福关系的美德论论证
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美德伦理,强调品格的塑造和美德的养成,其核心是“仁”。“仁者不忧”(《论语·子罕》)意味着具有“仁”德之人没有烦恼痛苦因而是幸福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说的是一个人缺乏美德,即使他“富且贵”,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进一步说明拥有美德之人即使缺乏外在的物质条件依然幸福快乐。显然,儒家所理解的幸福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沉思的生活”类似,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幸福,而非“动物式的生活”。
苏格拉底相信践行美德的人都将获得幸福。苏格拉底之死是说明忠诚与幸福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它既提出了我们该如何理解忠诚美德问题,也提出了忠诚是否有利于忠诚者的幸福问题。在《克力同篇》中,克力同力劝苏格拉底逃跑,其理由是他们是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是忠诚仗义。而苏格拉底拒绝越狱逃跑的理由之一是,不能因为雅典人判处他死刑而逃跑,因为他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这里至少涉及三种忠诚:一是克力同与苏格拉底作为朋友的忠诚,二是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的忠诚,三是苏格拉底对信念的忠诚。显然,这三种忠诚存在严重的冲突,对苏格拉底本人和相关者的幸福都将产生影响。在忠诚的冲突中,苏格拉底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3](P71)。《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也肯定了苏格拉底的选择,他指出:“苏格拉底难道不是在毫不退让地拒绝其对鬼神的忠诚作丝毫让步的同时,以同样的忠实和平静来服从地上的主人即国家的命令吗?他是生则遵从其良心,死则服务其国家。”[14](P56)那么,苏格拉底之死所体现的对国家的忠诚有利于他个人的幸福或城邦的公共幸福吗?无论他人怎样看待这一问题,至少苏格拉底认为死亡其实是最大的幸福,因为灵魂抵达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可以见到由于生前正直忠诚而死后成为神的先贤和古代英雄[15](P30-31)。休谟肯定了苏格拉底的忠诚美德,他指出:“谁不钦敬苏格拉底,不钦敬他身处赤贫和家庭烦恼中却始终如一地保持平静和满足,不钦敬他在拒绝朋友和门徒的一切帮助乃至避免依赖于任何恩惠时表现出的对财富的断然轻蔑和对维护自由的慷慨关怀?”[16](P109)这些正是苏格拉底幸福观的核心要素。
最早论证美德与幸福关系的文献当属《尚书·洪范》,该书认为“福”有五种: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是“五福”之一,它既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幸福[11](P201)。尽管《洪范》并未直接论述忠诚与幸福的关系,但是后来的《忠经》多处引用《尚书》来论证“忠”与幸福的关系。《忠经》是论述“忠”与幸福关系最为系统的文献,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保孝行章第十》《证应章第十六》较为统地论证了“忠”与幸福之间关系。例如,《忠经·证应章第十六》指出:“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则福禄至焉,不忠则刑罚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长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征也,不亦明哉?《书》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根据上文所述,“作忠”即“作善”,而且是“最高的善”。“忠则福禄至焉”表明忠诚之人因为拥有忠诚美德和作出忠诚行为而获得幸福,同时通过引用《尚书》进一步论证“忠”将带来“百祥”即幸福。换言之,忠诚之人以忠示人,与人为善,上天必定以幸福来回报他,所以天降百福,所谓“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就是形容人们“作善”将得到无限的幸福。《忠经·保孝行章第十》指出:“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矣。”这里指出了“孝”与“忠”的关系,“忠”先于“孝”,“竭其忠”意味着君子只要按照忠道行事,自然会获得荣华富贵等幸福。虽然“忠”只是“善”的一种,但在《忠经》中“忠”是最为重要的美德。
在通化,像兴林镇一样用好红色资源的案例还有不少。被激活的红色资源不仅引来越来越多人的目光,也激发出当地人奋斗创新的干劲儿。在集安市,寻访抗联密营成为热度很高的体验项目;在辉南县,重走抗联路等项目吸引了很多参与者。在通化市靖宇陵园,每天都有各界群众前来参观,了解杨靖宇的战斗历程和英勇事迹。
亚里士多德通过区分互惠互利的朋友、共同娱乐的朋友和德性上相似的朋友等三类朋友来分析朋友之间的忠诚和友谊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第三类朋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忠诚是真正的朋友之间的一种品质[7](P253-258)。儒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忠”和“信”是朋友间友谊的核心问题。正如赫斯特豪斯指出:“相信忠诚是一种美德,就是相信那些采取忠诚行为的人正在以理性的方式行事,正在践行着实践理性。而相信某个人如此行动就是践行实践理性,则是相信,如果我在同样环境中出于同样的理由而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我也就是在践行实践理性。”[12](P260)赫斯特豪斯很好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上相似的朋友相信对方也会像自己一样相信并践行忠诚美德。她认为忠诚有助于促进社会群体的良好运转,有助于促进我们的快乐[12](P260)。根据美德伦理学的观点,忠诚之人不仅因忠诚行为而让自己愉悦,也让朋友或他人感到愉悦,因而拥有忠诚美德的人当然会感到幸福。
在义务论者看来,有德行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是幸福的,拥有美德的人才配享幸福。康德说:“幸福只有在与理性存在者的道德性精确相称、理性存在者由此配得幸福时,才构成一个世界的至善。”[21](P519)换言之,有德性的人应该获得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德福一致。当然,有德之人不一定得到福报,但有德的人获得了应得的幸福是最理想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道德与幸福的二律背反,忠诚的人应该配享幸福,但并非必然获得幸福。
四、忠诚与幸福关系的道义论论证
从康德义务论的维度分析忠诚与幸福的关系,我们先要厘清康德的幸福论和道德论各自的主旨,因为二者“赋予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的第一和最重要的任务”[18](P100)。康德通过“至善”来协调德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至善作为最高的、无条件的善,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追求的对象,是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康德指出:“既然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但与此同时,与德性(作为个人的价值和得到幸福的配享)极其精确地相比配的幸福也构成了一个可能世界的至善:所以至善意指整体,意指完整的善,在这里德行作为条件始终是无上的善,因为后者在自身之上不再有条件。幸福总是这样一种东西,虽然对于拥有它的人是愉悦的,但它自身而言并不是绝对地和在所有方面善的,而是在任何时候都以道德上合乎法则的举止为先决条件。”[18](P122)康德在此提出了“与德性极其精确地相比配的幸福”的统一构成“至善”,德行处于优先地位,追求幸福置于道德要求之下。人们对康德幸福论的理解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将有德性的人配享幸福等同于个人幸福的实现;二是没有区分康德所说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前一种幸福是指由于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而得到的快感,服从于经验原则;后一种幸福是指理性存在者因为行为符合善良意志而产生的幸福感,服从道德的最高原则[19](P91)。同样,人们对康德的道德论的理解也存在着误解,大多数人认为康德的伦理学是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完全不同的道义论,然而我们从康德的有关论述中发现其道德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其实是比较接近的[12](P104)。换言之,康德的道德理论也是某种形式的美德论。
我们对康德的德福理论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再回到“忠诚”问题本身。正如前文所述,人们认为“忠诚”既是一种情感、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义务,如果按照康德的道德理论,如何理解忠诚呢?康德认为,只有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其他内在品质都是有条件的善,忠诚作为一种内在品质当然属于一种有条件的善,因为它可用于行善,也可用于作恶,取决于一个什么样的意志支配它。根据康德的理论,忠诚显然不是一种道德情感,因为道德情感也是有条件的善,对于恶的忠诚会导致更大的罪恶。例如,对希特勒、恐怖主义、黑社会等越忠诚,其后果就越严重。而且,情感本身不具有确定性、普适性和客观性,不适于作为道德价值的起源。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当且仅当它是出于义务而做出的。据此,忠诚者的忠诚行为只有出于义务才具有道德价值。
史珂拉指出:“忠诚能够并且的确维持着义务。”[13](P44)她既看到了忠诚与义务之间的差异,也指出了忠诚能够确保义务。例如,“夫妻应当互相忠诚”表明,这种忠诚不仅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且是一种法律义务,忠诚作为一种义务具有强制性。根据康德的道义论,夫妻之间的忠诚是出于义务或责任,那么这种忠诚就是多余的,因为由义务或责任强加的忠诚是义务或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20](P19)。通常而言,如果夫妻彼此遵守并履行这种义务,无疑是有利于家庭幸福的。如果任何一方违背相互忠诚的义务,都可能导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异动,都可能影响夫妻双方乃至整个家庭的幸福。当然,也有不少现实案例表明,即使某些夫妻履行了相互忠诚的义务,然而彼此性格不合,情感冷漠,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这种忠诚能否带来幸福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了。
2#"Alzheimer's disease"or"Alzheimer's"or"AD"or"dementia";
五、忠诚与幸福关系的功利论论证
我们要进一步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功利主义是不可回避的一种道德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大多数人看来,功利主义的哲学家似乎只关心行为后果能否促进人的幸福或快乐,而不关心行为者本身的美德问题。即使功利主义关心人的美德,也只是把美德当作实现幸福的工具,它们把某些品格特质当作美德,仅当这些美德促进了其拥有者的利益或者促进了所有相关者的总体利益[2](P162-163)。显然,对功利主义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
功利主义主要从效用或者有用性来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例如,休谟认为,有用性具有强大的效能,它是给予忠实、正义、诚实、正直以及其他那些可敬的和有用的品质和原则的道德赞许的惟一源泉[16](P55)。休谟指出:“如果政府是完全无用的,它就绝不可能产生,忠诚这项义务的惟一基础就是它通过维持人类的和平和秩序而为社会所挣得的好处。”[16](P56)休谟指出了政府的产生离不开有用性,人们之所以忠于政府,是因为忠诚有利于促进公共幸福——维持人类和平和秩序、给社会带来福利。他又以养育子女论证夫妻忠诚的效用,他说:“人的漫长而无依无靠的幼年要求父母双方为了其幼儿的生存而相结合,这种结合要求贞洁或忠实于婚床这种德性。人们将容易承认,没有这样一种效用,这样一种德性就决不会被人们所想到。”[16](P57-58)贞洁或忠实的美德既是对夫妻双方彼此的道德要求,也可以避免幼儿无依无靠从而有利于他们的生存和成长。忠诚由于促进了社会利益,因而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忠诚对忠诚者本身也是有益的,“被当作是那种惟一能使人在生活中受到尊重的信赖和信心之源”[16](P90)。显然,忠诚作为涉己之德能够促进忠诚者自己的幸福,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作为涉他之德对他人和社会有用,可以促进他人和社会的福利,因而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德性。表面上看,休谟似乎认为忠诚是实现幸福的工具。其实不然,休谟只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验证或者证明某种品质带来的后果是否有用或者令人愉快,即是否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或者福利,他所理解的美德是对其拥有者或他人有用或适宜的品质特征。因此,与其说休谟是一名功利主义思想家,还不如说他是美德伦理学家,他是“美德伦理学的倡导者”[12](P32)。
古典功利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约翰·穆勒特别关注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他尤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认为美德不仅有助于增进人的幸福,甚至认为美德是幸福的有机组成部分。穆勒指出:功利主义认为应当为了美德本身去欲求美德。不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如何看待美德之为美德的原始条件,也不论他们是否认为美德只是因为其促进了美德之外的另一个目的,只要他们确定了什么是美德,美德作为首要的善将有利于实现终极目的,而且美德自身即为善,不依赖于其他任何目的。美德本身就值得人们热爱,即便美德在个别场合产生了不好的后果,它们仍然是与“功利”相符合的,最有利于公众幸福的。美德原本不是目的的一部分,但它能够成为目的的一部分,它不是作为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而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8](P36-37)。根据穆勒的观点,忠诚作为一种美德本身就是值得欲求的,忠诚不能仅仅被当作促进幸福的手段,它本身就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符合功利原则,而且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幸福。穆勒进一步指出:“那些为了美德本身而欲求美德的人,或者是因为,对美德的感受便是一种快乐,或者是因为,对没有美德的感受则是一种痛苦,或者是因为两者兼而有之。事实上,快乐和痛苦几乎不可分离而总是结伴而行的,一个人若因具备某种程度的美德感到快乐,那么他就会因不具备更多的美德而感到痛苦。如果这种美德不能使他感到快乐,那种美德不能使他感到痛苦,那么他就不会爱好或欲求美德了,或者,他会仅仅因为美德能给他或他所关心的人带来其他的福利而欲求美德。”[8](P39)根据穆勒的逻辑,忠诚者之所以忠诚,因为忠诚美德可以给忠诚者带来快乐,而背叛将带来痛苦,或者因为忠诚美德能够给忠诚者或者利益相关者带来福利。但是,功利主义伦理学论证逻辑的一个潜在风险在于,如果忠诚美德不会使任何人幸福反而会令某些人极其不幸,也就是说忠诚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那么不忠或者背叛很可能就是正确的或者道德的。
六、忠诚与幸福关系的积极心理学论证
《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德提到了“为国之本”的高度,“忠”因此突破了个人美德的局限上升为一种治国安邦的政治美德。《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指出:“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矣。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身一则百禄至,家一则六亲和,国一则万人理。”由此看出,“忠”与幸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忠”不再局限于促进个人的幸福,而是对个人(身)、家庭(家)、国家(国)的幸福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个人幸福是基础和根本,正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孟子没有空谈大道理,而是从天下、国、家和身的关系强调了“身”的根本性。就个人而言,忠诚能使个人安身立命,故为“忠之始也”;从家庭而言,忠诚能使家庭兴旺发达,故为“忠之中也”;从国家而言,忠诚能使国家稳定和谐大家幸福,故为“忠之终也”。总之,个人安身立命、家庭兴旺发达、国家稳定和谐都是总体幸福的题中之义。毫无疑问,《忠经》体现了儒家的忠诚观,其主体思想支持忠诚能够促进幸福,甚至认为忠诚是幸福的前提或者基础,没有忠诚就没有幸福。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等人通过阅读分析世界上主要宗教和哲学派别的经典论著,研究了整个世界横跨3000年历史的各种不同文化,归纳总结出六类各种文化和宗教都赞成的具有普适性的美德,即智慧与知识、勇气、仁爱、正义、节制与精神卓越。他们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发现,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践行这些美德,我们就能获得幸福[24](P138-139)。其中正义具体包括了公民精神、责任、团队精神、忠诚等美德。塞利格曼指出:“具有公民精神的人通常是集体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很忠心,有团队精神,他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使团队成功。”[24](P156)塞利格曼认为,忠诚是实现正义美德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幸福的重要源泉之一。美国另一位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学者乔纳森·海特以心理学家穆扎法尔·谢里夫1954年进行的一项社会心理学的实验为例,分析了忠诚的德性对两性的重要性,“对男孩们来说,忠诚的对象倾向于团队和盟友,对女孩来说却是两个人的关系”。乔纳森·海特进一步说明了忠诚/背叛对于部族主义和群体间竞争的意义,“能告诉你谁是有团队精神的人、谁是背叛者的任何东西都会是忠诚基础的原始诱因”。体育心理学表明,扩展忠诚基础的即时诱因,可以促进人们团结一致追求无害的战利品,从而获得快乐[25](P149)。
当然,正如乔纳森·海特指出,原本高贵的道德动机如正义、荣誉、忠诚、爱国,很多最后却变成了暴力、恐怖及战争,大部分人甚至还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23](P185-186)。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忠诚呢?这种忠诚还是一种值得称颂的美德吗?例如,“9·11”恐怖主义事件中恐怖分子的忠诚。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那群“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执行大屠杀指令的人,是忠于权威、忠于法律的守法者,貌似具有忠诚美德,然而他们却是一群缺乏良知的
人[26](P199)。正如阿伦特曾经指出,面对奥斯维辛,我们应该思考根本恶与平庸之恶区分的意义。艾希曼忠于恶本身,缺乏或者放弃了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位,取悦其上级,证明自己可以又快又好地工作,这就是平庸之恶[27](P268-269)。上述观点表明,忠诚作为一种美德与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密切相关,未经选择和反思的忠诚不能叫作忠诚,只能叫作愚蠢的“忠诚”,这种“愚忠”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灾难。
主动脉返流症状发生率为31.11%,肺动脉瓣返流症状发生率为55.56%,三尖瓣返流症状发生率为66.67%,二尖瓣返流症状发生率为38.89%。见表。
尽管积极心理学的实验证明人们践行美德能够带来幸福,同时大多数人也相信拥有美德的人更加幸福,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美德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我们只有在全面考察了人们在不进行美德实践或者进行恶德实践的情况下是否会感受不到幸福或者感受到不幸福,并且进行了充分的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美德与幸福的因果结论[22](P1521)。总之,忠诚与幸福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忠诚作为一种美德对人类幸福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是确定无疑的。
[注 释]
①正如《忠之哲学》的中文译者谢幼伟指出,Cause这个词很难找到合适的中文译名。它既可以译为“主义”,也可以译为“事业”,还可以译为“理想”“理由”“原因”“动机”,等等,他将其译为“主义”。Devotion一词具有献身、奉献、忠诚、信仰、热爱等多重含义,谢幼伟将其译为“尽心”,估计是受儒家“忠”观念的影响。Josiah Royce.The Philosphy of Loyalty[M].SophiaOmni Press,2017.p.18.参见Josiah Royce《忠之哲学》,谢幼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8.
胸腺肽α1可促使外周血的T淋巴细胞成熟,增加T细胞在各种抗原或致有丝分裂原激活后产生各种淋巴因子,增加T细胞上的淋巴因子受体水平。它同时可发挥对T辅助细胞的激活作用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因此在理论上可能提高抗结核药物的疗效[12],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胸腺肽α1明显提高了患者发热、盗汗、咳嗽、气短等的缓解率,而且加快了以上症状的缓解速度,明显缩短了病程,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同时提高了影像学的吸收率,因此临床上可减少患者复查的次数,节约复查费用,缩短治疗的周期,本研究为胸腺肽α1应用于结核性胸膜炎的辅助治疗提供了临床依据,有望提高结核性胸膜炎的临床治疗水平。
[参考文献]
[1]B·威廉姆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M].周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3]左高山,涂亦嘉.政治忠诚的核心问题[J].伦理学研究,2018(5).
[4] William Armstrong Fairburn.Loyalty[M].Nation Press Printing Co.,Inc.,1926.
[5]Troy Jollimore.On Loyalty[M].Routledge,Taylor&Francis Group,2013.
[6]Paul R.Goldin.When Zhong忠Does Not Mean“Loyalty”[J].Dao,2008(7).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8]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9]黎良华.美德与幸福:有益、阻碍抑或同一[J].齐鲁学刊,2011(3).
[10]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2]罗莎菻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M].李义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13]Judith N.Shklar.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1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5]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休谟.道德原则研究[M].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7]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杨秀香.论康德幸福观的嬗变[J].哲学研究,2011(2).
[20]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人类的18种美德[M].吴岳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2]喻丰,彭凯平等.美德是幸福的前提吗?[J].心理科学,2014(6).
[23]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M].李静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4]马丁·塞利格曼.真实的幸福[M].洪兰,译,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8.
[25]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M].舒明月,胡晓旭,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26]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7]理查德·J.伯恩斯坦.根本恶[M].王钦,朱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左高山,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段外宾,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忠诚及其实现机制研究”(17BZX023)
标签:忠诚论文; 幸福论文; 美德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的人论文; 《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忠诚及其实现机制研究”(17BZX023)论文;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