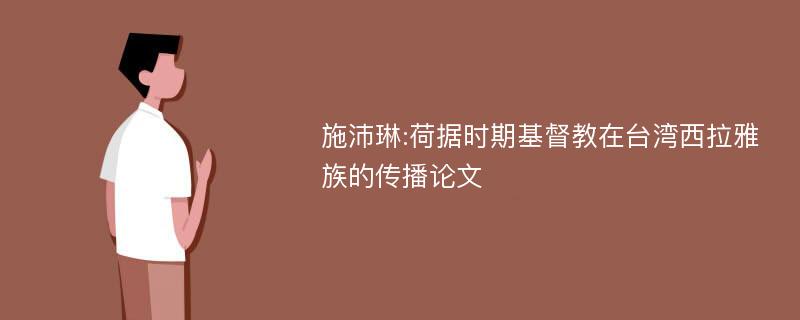
摘 要:荷兰占据台湾38年,初期目的主要是想争取一个对中国贸易的通商据点,企图以宝岛作为与葡萄牙、西班牙人竞争,进行转口贸易的基地。待脚步站稳,即开始扩大殖民统治范围,对岛内先住民及前来的汉人移民进行殖民统治。武力镇压与行政控制之余,还在岛内传布基督教义;恩威并重的宣教成为荷兰殖民统治当局的重点工作。1641年左右,台南地区以西拉雅族为主的先住民五个社,约有六成人口信奉基督教,开启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的首页。然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原信奉基督教的先住民纷纷恢复原来的信仰;荷兰人在台南地区传播基督教之举因而中断。
关键词:荷据时期;基督教;西拉雅族
17世纪台湾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先住民,在荷兰殖民统治当局的有计划传播下,通过荷兰改革宗教会宣教人员的传教而接受了基督宗教。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基督教一度几近消失;直到1865年英国医师马雅各与1872年加拿大牧师马偕,先后来台进行医疗宣教才又恢复。之后,基督教会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尤其在东部山区与纵谷地区的山地教会更是到处可见。
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2014年底基督宗教教会教堂数量合计3 280座,以基督教占76.7%最多,天主教占21.6%次之;各县市以台北市、高雄市及花莲县较多,合计占三分之二。其中,台北市462座最多,高雄市313座次之,花莲县289座居第三。至于山地教会数量,据相关部门统计,约有五百所。根据1995年底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都市先住民”的信仰仍以基督教占最多数,共计72.29%(基督徒44.848%,天主教徒27.18%);若以族群来分,又以泰雅族、鲁凯族、布农族、曹族(邹族)和阿美族信仰基督教者最多,而雅美族、赛夏族多信仰天主教。①其中,基督教派中以长老教会在少数民族传道最积极,资料显示,长老教会于1960年在太鲁阁族成立中会,1964年底有40所教会、9 644教徒;阿美族有教会103所、教徒20 804人;布农族有教会56所、教徒1 1630人;西排湾族教会有52所、教徒10 687人;东排湾族有教会26所、教徒2 622人;彪马族(卑南族)有教会9所、教徒1 184人;兰屿雅美族有教会6所、教徒809人;鲁凯族大南社教会有教徒474人,另还有邵族、赛夏族等教会。另根据20世纪60年代,某基督教杂志报道,当时台湾山地的长老教会有335所,会员人数17 469人,与其他教会合计有60 000以上,而台湾少数民族约150 000人,亦即有四成的台湾少数民族是信徒。1970年底,长老教会在全台的教徒人数已近200 000万,其中少数民族教徒人数约近70 000万,分布在10个少数民族部落。1998年长老教会教徒数有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教徒的流失,以2000年为例,该会各少数民族教会教徒减少3 451人。[1-2]32-142,144
一、荷兰改革宗教会
台湾基督教源自史上两次外来宗教在岛内的传播,最早是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荷兰据台初期,势力范围仅限大员及附近的新港(今台南市新市区)、麻豆(今台南市麻豆区)、萧垄(今台南市佳里区)、目加溜湾(今台南市安定区)、大目降(今台南市新化区)等先住民②村社,其住民主要为“西拉雅族”(siraya),多居于平原或丘陵,尚处原始社会,是最早与汉人往来的民族。
在岛内传播基督教的任务主要是由荷兰改革宗教会宣教人员负责。成立于1548年—1550年间的荷兰改革宗教会,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受到殖民者西班牙政府无情的压制,在对抗西班牙的独立运动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荷兰脱离西班牙统治后,改革宗教会就形同国教的地位,与荷兰政府间关系密切。[3]15-61改革宗教会采取长老制,总会下有“小会”“中会”(北荷和南荷)两“大会”,一般两大会属联谊性质,教会组织权力在小会和中会。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即选派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传道人担任海外宣教工作;可以说,17世纪荷兰海外宣教运动和海外殖民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荷兰改革宗教会是17世纪荷兰人来台后,与先住民最直接接触的组织;在台传教人员虽在身份上归东印度公司职员,改革宗教会却不属东印度公司,宣教人员除向巴达维亚城的印度总督和评议会或荷兰总部的十七人会议报告台湾一般事务之外,也会向荷兰境内的阿姆斯特“中会”报告有关台湾的教会事务。入岛的荷兰改革宗教会名下与先住民教化有关的神职人员,大致分几个层级:牧师、候补牧师或教师、疾病慰问使或传教师以及其他在荷兰人所设立学校担任教职的学校教会。其中,关键人物的牧师由巴达维亚小会任命,派遣来台领导传教事务;又分机关牧师或军中牧师、俗吏、宣教师;而给先住民传播教义的主要是宣教师,学校教师也会担任协助传教的任务。
二、荷据初期的基督教传播
1624至1627年荷兰人来台湾建立据点的最初几年之间,并无太多心思与计划从事改革基督教的普传。在大员这块新有土地上首要目标是建设该地成为日后贸易中心。③在陌生不确定的新世界,把人数稀少的荷兰人困居于台湾本岛旁、大海中的荒凉沙洲上,如何将寸土之地发展成大贸易基地,进而能从东亚贸易的契机中获取巨大利润,确实是荷兰人斯时的当务之急。
从1624年荷兰人来到大员建立贸易站开始,该处的荷兰人便由探访传道负责的情况下,成立了教会。荷兰改革宗教会目的是为照顾大员地区荷兰信徒的信仰需要;事实上,这也是联合东印度公司与荷兰改革宗教会合作,雇用经教会推荐的神职人员到亚洲的重要原因之一。[4]1-30在这之余,首任台湾长官宋克博士也认为有必要为荷兰殖民者与台湾岛上居民提供宗教信仰的需要。1625年,宋克向巴达维亚当局请求:“……下回季风起时送若干妥当上级商务……以及适宜、良善之二至三名牧师,或读经员来此,以宣扬主之名,并可使为数可观之本
岛野蛮番人成为基督徒。若由若干适当人员辛勤耕耘,佳美果实可望预期到来。”[5]271-292两年后,台湾第一位牧师乔治甘迪留斯进驻台湾岛,初期是带领荷兰人基督教友。虽然巴达维亚城当局规定,在台湾本岛传福音,不宜过分张扬与奖励,所以初期仅在若干番社派驻探访传道,而没有雇用牧师。然而,由公司派来的甘迪留斯有着强烈企图心,希望在这大岛屿上施展抱负,这点从他每次给总督顾恩写信时都会在签名旁加注一句话:“往外邦人中传扬上帝之道”中可见他有意在岛内传播上帝福音的意图。甘迪留斯甚至努力地融入当地社会,学新港语、进行调研,并在抵台十六个月后写成有关的民族志。在甘迪留斯的心目中,大员和赤崁一带新港社先住民的聪明程度超过南洋摩鹿加群岛或爪哇岛上的摩尔人,他们脑袋灵活、记忆力强,一个星期就教会他们在南洋其他地区要两星期才能教会的东西;对神的信仰有很高的吸收力,也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因此,积极向公司及长官表明,他相信当地人会接纳基督教,而且会舍弃违背上帝律法的行为,而且他有信心能在本岛建立成东南亚地区最美好与最重要的教会,甚至可以与荷兰最繁华与光荣的地区相抗衡。[6-7]221-241,145在他担任牧师期间,从物资引诱着手,经常以好酒好菜招待“头人”(村社的长老、“村长”),但他也主张用严厉的法律手段对付辖下村庄内不服统治的居民。
三、宣教与统治相辅相成
据1641年《巴达维亚城日记》记载:新港、麻豆、萧垄、目加溜湾等社又有男女和小孩380人接受洗礼,从而受洗人数在四千至五千人之间。[12]129-1301643年第二位牧师尤纽斯离台时,接受他受洗的总人数已达5 900人,其中大部分在大员附近;另有1 000多人由他证婚,举行基督教婚礼。[13]101再据1659年的视察报告,新港有谙悉教理的信教徒1 056人、麻豆701人、萧垄697人、目加溜湾412人,分别约占各村人口的83%、51%、48%和76%。若再包括诸罗山及附近地区,共计20个村庄中,能祈祷谙悉教理者在6 078人以上,约占总人口10 109人的六成。[14]380-406
1630年前后,与中国大陆贸易渐趋稳定后,荷兰人心有余力向岛内进行征服的工作。除了最初接触的新港社,荷兰人开始出现在目加溜湾与麻豆等社;为了与岛上先住民建立友谊,以小礼相赠踏出友谊第一步。然而,由于各社的先住民及更往山区的高山先住民,各有不同的领地及需求,且多数强悍,使荷兰统治当局逐渐感受到先住民的压力。荷兰人虽然希望跟这几个社的先住民保持良好关系,但仍不时会面临着其他可能的武力攻击状况,在《热兰遮城日志》中[9],多次提到有“野人袭击”的事件发生。例如:在1629年10月1日至1630年2月22日中国沿海处理事务的日志摘录和在1630年2月23日至9月29日大员办公室所写的日志摘录内容:
传教与武力镇压是荷据时期统治政治的一体两面;武力扩张为传教开辟了道路。1636年,荷兰人镇压了麻豆等社的反抗,传播基督教即从新港扩展到周围的几个村社。1637年的《巴达维亚城日志》即记载着台湾长官伯格的报告:“在目加溜湾,住民们用6天时间就建起一座教堂和一座传教士住宅;萧垄、麻豆也开始传教,但因人手不足,当需传教士二至三人。”[10]298、324而往南、向北,均有荷兰牧师宣教的足迹。大员及附近的几个社村靠近政治中心,又是甘迪留斯和尤纽斯长期经营的地方,归服得早,传教事业甚为可观。据1638年的教会视察报告,在大员附近村庄已有约5 300人会到教堂听教,包括:新港人与目加溜湾各有1 000人、萧垄1 300人、麻豆2 000人。[11]73-74而受洗礼人数,根据1639年底的视察报告,新港1 047人、大目降209人、目加溜湾261人、萧垄282人、麻豆215人;五社人口总数8 647人,受洗礼人数2 014人,占总人口23.3%,其中,新港人口数1 047人,全社均受洗。④
“1629年10月8日,长官阁下(普特曼斯)再次派人去赤崁圈用一处可建房屋的地方,目的要能再次安全使用该地,避免再遭受野人的困扰危险,像以前发生过那样。”“10月9日,有一个新港(台南市东北,现新市区)居民奉新港议会,他们称之为Tackatackusach(新港社酋长会议,当时新港社最高政权机构,即先住民族口中的长老会议)的命令来此地通报,有目加溜湾人(Baccalouan,台南县安定乡)和麻豆人(Mattauw,台南县麻豆镇)共约五百人,已经来到他们地区南边附近,计划要在夜里攻击上述新开始建造的房屋,他们不愿意我们在那里又开始砌砖造屋,而且还计划要偷袭这城堡。”[9]2“10月14、15、16日,四五百个野人到上述房屋附近,但停留在射程外,士兵带回野人几个,野人群起追击,投射百枝以上的箭及标枪,但我方无人受伤,于是继续留在房屋附近,没有其他动作。”[9]3“11月23日,约两百三十个武装者包括士兵与水手,准备前往目加溜湾,要用火及刀毁灭该社;这些人于隔日返回,他们杀死几个人,放火烧毁该社大部分。”“11月28日,长官普特曼斯由五十个士兵陪同前往新港勘查可盖碉堡地点。普特曼斯主张,牧师乔治甘迪留斯要像战争之前那样,再跟几个士兵一起去驻在新港,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基督教,也希望目加溜湾和麻豆居民的情绪,经过这场战争将更加稳定下来,并且归向我们。事实上,他们已向我们表示要这样做了,麻豆人也已请新港人带他们最好的武器来交给我们,作为我们已经战胜他们、制服他们的表征。因此,将来也愿意承认我们是他们的主人,愿意服从我们的统治。隔日,长官阁下率领全部随从回到此地,他曾受到当地居民照他们的习俗殷勤款待,也踏勘了要建造房屋和碉堡的地点。”“12月2日,目加溜湾社和麻豆社居民来新港社,从那里派代表来向长官阁下请求,让他们自由地、不受迫害地来大员见长官阁下,以便缔定和约等等,长官阁下同意他们请求,并派牧师甘迪留斯去带他们来。他们来到此地时,像欢迎朋友那样,令步枪手鸣枪三响,经互相讨论后,提出以下条款令其遵守,如此便可获得并享受我们的友谊:第一,他们必须归还被他们谋杀时夺去的我方人员的所有头颅和骸骨;第二,他们也必须归还被他们谋杀时夺去的我方人员的所有武器;第三,他们必须每年献出感恩礼物。”[9]5
这是我在伞底下伴送着走的少女的声音!奇怪,她何以又会在我家里?……门开了。堂中灯火通明,背着灯光立在开着一半的大门边的,倒并不是那个少女。朦胧里,我认出她是那个倚在柜台上用嫉妒的眼光看着我和那个同行的少女的女子。我惝怳(现在写作“惝恍”),这里是迷迷糊糊的意思。地走进门。在灯下,我很奇怪,为什么从我妻的脸色上再也找不出那个女子的幻影来。
工程图的绘制绝不仅仅是一个绘图软件的学习。绘制工程图样的理论基础是投影原理,而其规则是《制图国家标准》。工程图学是教授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要不断地由物画图、由图想物。
面对强悍的先住民,荷兰统治当局备感压力与威胁,因此,荷兰改革宗教会辖下的宣教人员除了担负起海外宣教任务,也尝试以传播基督教方式,配合武力镇压同时进行威恩并重的统治策略。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属于喀尔文教派改革教会领取公司薪金的神职人员,他们直接向台湾长官和巴达维亚总督汇报工作;他们可以携带配偶来台居住。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先后有神职人员32人次在台湾传教(其中,有3人曾经两次来台)。[7]145
1629年,第二位牧师尤纽斯也来到台湾,他与甘迪留斯合作,以新港为基地,传教事业始有进展。在当时荷兰人对台政策以贸易为最大考量的情形下,无非也希望能在动用军事武力镇压之余,能有其他方式来处理岛内先住民的问题。因此,荷兰人把传教与行政结合起来,传教亦为行政的一环,行政为主,教化为辅,尝试以宗教教义弥补武力镇压的不足,而能在心性上起潜移默化的作用。[8]101
荷兰人为了传教需要,便于1636年起在新港等各村社设置学校,进行基督教文化教育;到1643年10月,新港、目加溜湾、大目降、萧垄、麻豆等学生人数达234人以上。这五社的先住民子女被迫每日到校学习,否则处以罚款;同时也对入学学生给予奖励,让他们安心就读。目的就是要让儿童与少年,从小接受基督教义,使他们能成为虔诚基督徒,服从荷兰人的统治。这中间,也希望在普遍培养的同时,能发现一些拔尖人才,让他们可在村中传教,以解决荷兰人传教人员不足与语言障碍问题。
关于识别模型的训练方法,该方法要求制作一个足够大的单步统计特征-速度数据集。即采集不同人员在不同速度下的惯性数据,利用加速度数据峰值检测单步划分之后,将从单步惯性数据中提取的65维统计特征与该单步对应的实际速度对应,利用该数据集训练速度识别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LS)分类器、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k近邻(KNN)分类器、线型贝叶斯正态分类器(LDC)4种常见机器学习分类算法对以上数据集进行训练并验证其识别准确性,寻找其中最佳的识别方法。
在这些语境中,与乔字组合的词语,均是“装模做样”的意思。“乔势”、“乔样势”、“乔驱老”、“乔龙画虎”、“乔张致”、“乔张做致”、“乔声势”、“乔腔”,虽然它们的用例不同,但是其核心义却是一样的。
四、设校协助教义传播
基督新教随着17世纪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扩张,从1627年传入了台湾,到1662年荷兰人战败离开,荷兰改革宗教会已在台湾建立了西拉雅、南路地方、虎尾垄与二林、鸡笼与淡水等四个宣教区,至少拥有7 000名先住民信徒。1643年是荷兰改革宗教会在台湾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个别牧师单打独斗转变为牧师群的集体共治;教会的发展也从信徒人数大幅度增加转为信徒信仰深化的阶段。⑤
利用教育推广教义的传教政策,更扩大范围到成年男女。1647年,在五社的少年班学生577人、成年男子班160人、成年女子班374人以上。成年人上课时间与少年儿童班不同。儿童是在天亮一小时后开始上课,连上两小时;成年男子班在天亮以前去上课,时间一小时;妇女则是在傍晚去上一小时。⑥授课内容采用荷兰人编译的教理问答书。成年男女学习各种祈祷和教理问答,儿童除祈祷和教理问答,还需要学习拉丁文拼写当地语言、朗读课文、写字、习作。[15]18
荷兰人在台湾的宣教可谓煞费苦心,因为学习教义之需,台南地区以西拉雅族为主的新港等五社先住民均学会用拉丁文拼写自己的语言,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直到清代,在荷兰人办过学校的一些村庄中,仍发现用拉丁文字书写契约的文书,后世称“新港文书”,为研究早期先住民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参考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推进系统的研究进展, 本文选取了在燃烧室内带有楔板及单凹腔结构的冲压发动机燃烧室模型[21]作为研究对象. 在该类燃烧室结构中, 楔板的作用为产生斜激波以对流动进行增压增温, 其目的在于激波点火或使燃烧室内流动参数达到燃烧条件的区域增加, 而凹腔结构则是为了形成低速回流区以增加燃料在燃烧室内的停留时间, 其目的在于稳定燃烧.
斯时,散居府城东方山区的西拉雅族人,已大致放弃曾热爱过的渔猎生活,像汉人一样仰赖农耕维生。受驯服的新港、目加溜湾等社,尤其受到荷兰人宣教影响,使得大部分西拉雅族人不得不抛弃祖先及偶像崇拜,成为基督徒,并在荷兰人建立的教会及学校定期集会。他们就像其他先住民一样,喜爱音乐,不但会唱自己的民谣,而且很快就学会传教士教的圣歌。[16]49-54
设计意图: 通过对尤溪科研成果的展示,引发对科研成果成功内在原因的思考,应用概念对事例分析理解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学生爱家乡的情怀,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传教人员同时通过宗教对先住民进行教化,并在没有文字的先住民地区设立学校,以教育推广宗教;首创书写文字,成为后人研究重要的史料。客观地说,从台湾文化历史发展看,亦值得一书。然而,荷兰人采取了奴化教育方式,强迫儿童、成人、妇女接受荷兰殖民者的文化与教育,企图让他们忘记自己的祖国,永远受荷兰侵略者的统治剥削是不可容忍的。在荷兰人的殖民下,其以一个外来政权对“遥远”领土的掌握,除了施展一些侵略者凶残暴虐手段,以军事武力镇压先住民的反抗之外,同时将宗主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也带进殖民地。荷兰人初至异地的宝岛台湾,其殖民者的首要动作非融入当地社会,而是企图以宗教改造殖民地的先住民,使之成为宗主国的缩影。殖民者突显自己政治上的优越感,自认为要以神的信仰培养出优秀的人民,他们正有义务教导那些他们眼中文化较次等的先住民,而被殖民的先住民本应接受其教化成为文明人。17世纪大航海时代,荷兰人在岛内传播基督教而呈现出殖民主义者霸权的心态下,台湾正当其冲。
3.5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社会支持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拥有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这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部分车祸患者,因其不能享受医保,经济压力也为患者本人及照顾者带来深深的困扰。重症颅脑外伤患者大多带有程度不等的后遗症,后期的康复训练和生活照料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责任护士在患者放弃治疗时,可积极调动患者尽可能多的支持系统,并联系当地2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患者进行后续治疗,并请医师告知对方医护人员治疗护理的重点。
但这种强制的宗教政策是否奏效?1645年10月28日,台湾长官卡朗向巴达维亚城总督报告说:“基督教的传布并不理想,只有基督徒之名的人很多。”甚至,1658年3月2 日,大员评议会也向总督报告说:“已经好几次严肃训诫,但大员许多先住民仍崇拜偶像、不义、奸淫甚至近亲相奸。”[14]1-20显然,强制性措施只能收一时之效,荷兰人尝试以基督教义对先住民进行彻底改变,并不十分成功。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当郑军登陆消息在岛内传来之后,各地先住民很快地就抛弃基督教信仰,恢复以往的祖灵信仰与习惯,甚至用轻蔑的言语对待基督教,为自己能从基督教和学校释放出来而欢欣。
《巴达维亚城日记》中记载:“好些居住山区和平原的居民及长老,还有几乎所有住在南部的居民,都投降了国姓爷。每位长老获赏一件浅色丝袍、一顶装有金色顶球的帽子和一双中国鞋。这些家伙如今辱骂起我们努力传播给他们的基督教真理,他们因不用上学而兴高采烈,到处破坏书本和器具,又恢复其可恶的异教风俗和习惯了。他们听到国姓爷来了的消息,就杀了一个我们荷兰人,像往日处理打败的敌人一样,把头颅割下,大家围着跳舞、狂欢。”[12]303甚至在荷兰人统治中心的萧垄、麻豆等社,先住民对荷兰人“怀着敌意”,“异常无礼,公然反抗”,以致使得荷兰人感到很不安全。[9]308-309
结 语
荷据时期,牧师等传教人员一方面代表荷印公司管理先住民,一方面向先住民传教,以宣教协助当局统治台湾,推广教义,开启基督教在宝岛的发展。从前人史料中记载牧师的活动、报告,可看出先住民原有的生活和习俗,是探讨当时先住民社会与生活习俗等的珍贵史料。
以大员为出发点,宣教的范围更往北扩散,譬如:彰化北方的巴宰族会到距离他们居住约一百五十里外的台湾府城教会医院治病,把在那里学会的基督教义带回部落(埔里社),大部分族人摒弃偶像与祖先崇拜,改信基督教。他们音感十足,很容易学会欧洲歌曲,也保存许多与汉族完全不同的本族音乐,还把圣歌编入自己的民谣吟唱。传教士在巴宰族村社成立了几所学校,很多儿童会说写用罗马字母拼音的白话。荷兰殖民当局以强制措施逼迫先住民接受基督信仰,凡无故不去做礼拜或到学校上课的都要被处以罚款,严重的受到鞭笞或流放;对于原来各村社中的尪姨(女巫)也采取强行流放措施。[12]354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可由《热兰遮城日志》中的记载见其一斑,例如:1644年9月9日记载:“若有与当地基督徒妇女结婚的汉人,也必须接受基督教信仰并在牧师认为满意的情况下受洗,否则就必须跟妇女分开;两人若生有小孩,分开后男方须负担孩子的生活费。”1648年3月4-9日记载:“已经接受基督教教育的村社长老,不仅必须谨慎地对牧师表示敬畏,也要对传道和学校教师表示应有的敬畏,不仅要自己认真上教堂,也要劝勉他们的小孩和青年上教堂。因为有时听教会人士抱怨说他们怠慢了,而且因这理由设立的罚款办法仍继续执行,该罚款将用以建立教会与学校。”1648年3月7日日志又写着:“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学校的设立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为要使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得以接受基督教的美德教育,进而认识真神的道理。”[9]11、190
荷兰人以强制的政治力量进行宗教与文化霸权,却不敌民心向背,由此可见武力虽能慑人一时,却经不起考验。郑成功复台后,整个基督教信仰顿时中断,直至1865年马雅各与1871年马偕各从英国与加拿大渡海到宝岛,以医疗为手段从事宣教之后,才逐渐恢复,也使得基督教信仰在台湾的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
注 释:
①阿布丝:《原住民宣教史篇》,http://www.pct.org.tw/article_church.aspx?strBlockID=B00007&str ContentID=C2014021900010&strDesc=&strSiteID=&strCTID=CT0016&strASP=article_church.浏览时间:2016年8月28日。
②台湾一般以“原住民”称呼各少数民族,然据各族传说其先人入岛时间各有先后且未知,本文谈及荷兰时期之土著民族则以“先住民”取代“原住民”。同时,文章以“西拉雅族”为研究对象,未使用“平埔族”一词,盖在汉人尚未大量移民台湾的荷据时期,并无“平埔族”之说。
③兴瑟(W. Ginsel)博士论文:《De Gereg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第一章译注;见翁佳音译注:《台湾基督教奠基者康德牧师——荷兰时代台湾教会史(一)》,《台湾文献》第52卷第2期,第271-292页。“康德”(Georgius Candidius)牧师又译“甘迪留斯”、“甘第丢斯”,本文采译名“甘迪留斯”。
产业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有效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工作,对有效识别并规避信贷业务风险,合理分配信贷资源,减少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损失,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④1639年12月8日,特派员尼古拉考克巴克尔的台湾视察报告书,见《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二册,第129-130页。
⑤查忻:《1640年代后期西拉雅语及虎尾垄语教理问答的比较》,《“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台湾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4。
⑥1647年12月教会视察报告,见《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三册,附录一之一。
参考文献:
[1]井上伊之助原.台湾山地传道记[M].石井玲子汉,译.台北:前卫出版社,2016.
[2]郑志明.台湾全志(卷九)《宗教与社会篇》[M].南投:台湾文献馆,2006.
[3]林昌华.“阿立”“塔玛吉山哈”与“海伯”——宣教文献所见台湾本土宗教与荷兰改革宗教会的接触[M]//刘堡.台湾风物(53卷第2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4]查忻.荷兰改革宗大员教会 在十七世纪台湾的运作[J].台湾学研究,2013(15).
[5]翁佳音.台湾基督教奠基者康德牧师——荷兰时代台湾教会史(一)[M].台湾文献(第52卷2期).台北:台湾大通书局,2000.
[6]林伟盛.荷据时期教会工作史料选译[M]//台湾文献(第48卷第1期).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7]汤锦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M].台北:如果出版社,2011.
[8]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9]江树生.热兰遮城日志[M].台南:台南市政府,1999.
[10]村上直次郎,译注.巴达维亚城日志(第一册),[M].中村孝志,校注.东京平凡社,1970.
[11]曹永和.明郑时期以前之台湾[M]//台湾史论丛(第一辑).众文图书,1980.
[12]村上直次郎.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二册)[M].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
[13]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14]中村孝志.荷兰人对台湾原住民的教化[M].赖永祥,王瑞征,译//台南县文献委员会.南瀛文献(第3卷第3期).台南:成文出版社出版,1956.
[15]里斯.台湾岛史[M]// 候家骏.台湾经济史第三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16]史蒂瑞.19世纪原住民部落样貌[J].历史月刊,2004(203).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91(2019)02-0001-05
收稿日期:2019-02-10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15BMZ037)。
作者简介:施沛琳(1956-),女,台湾台南人,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闽台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谢雪莲
标签:台湾论文; 基督教论文; 荷兰论文; 住民论文; 新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史论文;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15BMZ037)论文;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