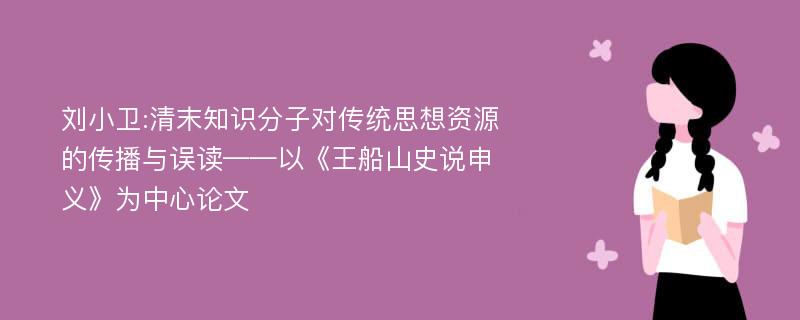
摘 要:章士钊的《王船山史说申义》是船山学说在近代影响的体现,是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传承传统思想资源的缩影。章士钊从“种姓之辨”、“辨败儒”和“振国魂”三个维度解读了船山学说,与此同时也存在学理性分析不足和感性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传统思想资源的合理运用为清末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清末知识分子在传播它时也存在误读成分。理性分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思想的理解与运用,能为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思想与促进它的现代性转化提供有益思考。
关键词:清末知识分子;《王船山史说申义》;传统思想;民族主义;清末革命
清朝末期革命形势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革命思想的宣传,而在知识分子所宣传的革命思想中传统思想资源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备受知识分子“青睐”的传统思想资源集中表现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观念以及明末遗民的思想学说,其中传统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船山学说尤其受到格外关注,并在清末革命发展中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以章士钊的《王船山史说申义》为个案,探索清末时期知识分子革命思想宣传中的内在逻辑与特征,并对传承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探讨。
1992年,在“全国第二届暗示教学法与沙塔洛夫教学法研讨会”中,我正式提出“两法合一”的问题,但当时还没提出“和谐教学”的概念,主要是利用暗示教学法的基本模式和课堂音乐,吸收纲要信号图示教学法的板书艺术,即“愉快教学法”。因当时上海已经有了“愉快教育”,为避免给人雷同的感觉,在与课题组教师反复讨论后,定名为“和谐教学法”。
一、“理论鼓吹”:清末知识分子革命思想的宣传与动员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的政治秩序、社会文化生活和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如何维护政治秩序和实现社会发展一直都是近代仁人志士思考与努力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求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也逐渐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共识。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腐朽的清末政权完全沦为洋人统治中国的工具,以激进的革命方式求取社会变革的呼声逐渐高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政治变革都需要相应的思想宣传。只有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民众了解革命团体的主张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进而形成革命的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相应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也离不开进步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介绍与宣传,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年间舆论工作。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年革命形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1年至1905年的 “理论鼓吹期”和1906年至1910年的“分途实行期”[1]182。 1901年至 1905年是进步知识分子进行革命宣传、抢占思想市场、制造革命舆论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革命理论宣传为后来的革命实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1901年至1905年间的革命发展形势来看,这一时期掌握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将革命理论灌输给民众,如何在社会上造革命声势,提升民众对革命的政治认同。首先,从革命思想的受众来看,普通民众是进步知识分子争取的重要对象,但那时民智未开,绝大多数民众对革命概念以及革命者的思想主张认知还不够准确。即使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他的革命思想也一度面临不被人接受的尴尬局面,在革命活动初次失败的时候,“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2]。庚子事变之后,同情革命的人逐渐增多,但在思想领域和舆论宣传方面革命派与保皇派等反革命势力之间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就是说,革命思想与革命势力在思想与社会领域并不占有主导地位,民众对革命的认同程度还不够高。其次,革命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性与学理性,在理解与认知方面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如果只注重革命实践而缺少革命理论的传播与宣传,就会重蹈太平天国的悲剧命运,因而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都特别注重革命理论的有效宣传。“今吾侪反其道而行之,先将革命理论集中在排满革命上,深入显出,解说明白,使全国之人视同饮食男女,怡然理顺。”[1]182为此,知识分子纷纷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有利于革命的思想资源,试图通过重述中国历史与重新解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达到影响民众的观念认知、鼓动民众和推动革命实践的目的。这一时期,“晚明抗清志士的著作被重新发现,成为后来排满种族革命思想的一个源泉”[3],其中王船山的思想学说被知识分子作为重点进行挖掘与重新阐释。
二、共同政治主题:章士钊对船山学说的解读与引申
早年的章士钊是个激进的革命者,《王船山史说申义》是他1903年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的、专门解读与演绎船山学说的文章,该文章后来被《皇帝魂》收录并在清末革命群体中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反抗清朝统治的时代主题与明末船山思想有着较强的契合性,使得清末知识分子在进行革命宣传、挖掘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时候都倾向于引用与诠释船山的思想学说。虽然同时代的不少学者都将船山的民族思想作为鼓动革命的工具,然而就对船山学说的诠释深度而言,章士钊所作的《王船山史说申义》在学理性、思想性上都是相对较高的,在众多革命宣传中独树一帜。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中引用了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原文并在其后附加按语,对船山思想进行了阐释与解读。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开篇即言:“王船山者,亡国之一国民也,故其言皆亡国之音,所说多亡国之惨”[4]160。既然王船山是亡国之人,他的学说抒发的是亡国之痛,那么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解读他的学说、体会他的思想,无论从情感还是时代需要来看,都是契合的。概括来讲,章士钊对于船山思想的解读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本试验的加载制度参考美国钢结构抗震规定(AISC—341—05)[15]。加载过程是以层间位移角控制的,层间位移角为梁端位移与加载点至柱中心距离之比。加载循环表如表2所示。
(一)种姓之辨:不可动摇之国粹
自从拓跋氏入主中原并“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慢慢地成了中国之民,以至于“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拓跋氏自知其文化不如华夏,通过冒用华夏文化、改良种姓的方式而融入华夏文明,这是中华文化强大向心力和同化力的表现。但是到了元朝,实行的是等级分明的人种制度,在文化、种姓上都表现出对华夏文明的“不肖”。在章士钊看来,胡元不像拓跋氏那样从风习、血液上改进种智、融入华夏文明而是采用相反的做法,应该称其为“将亡之虏”。章士钊认为,辨别种姓离不开“风习”与“血液”,风习与血液都是国粹,是万万不可变更的。在章士钊的论述中,“风习”指的是民族的文化层面,“血液”则是民族的生理层面。也就是说,章士钊是从文化与生理两个方面来认识种姓问题的。“夷狄”虽然入主华夏但必须在种智上进行改良,这彰显了华夏文明强大的同化力量和先进性。
此外,种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符合本国的种姓一旦丧失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论述梁武帝第十九条时,章士钊认为拓跋氏之所以亡国与其本身的种姓丧失是分不开的。“盖凡立国,必有其天然之国粹,不与人同。虽所遭之时世,逼之不得不然,而其所席之旧治之胚胎,究不可失;失之吾未见其能自立国者也。”[4]166-167拓跋氏本身“夷狄”,在文化方面不如华夏,却存在“由野至文”的文明演进路径,最终因“縻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精悍之气销,朴固之风斲”导致国亡。章士钊在按语中详细阐述了拓跋氏的覆亡原因,他实质上是在探讨华夏民族种族积弱的问题,想以此来唤醒民众对于种姓问题的认识。
此外,史学家“直心”已死也是心亡的表现。王船山认为,北魏崔浩因史被杀,却让后人知晓了夷狄的由来,“后世之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为君”;宋濂所著的《元史》则“隐其恶而扬其美”,掩盖元朝的丑迹,以至于“后人无所‘激’以‘创’其身”。章士钊指出,崔浩之后的史学家有的丧失了“直心”,“近时尤觉无此古道之人心”,混淆了种姓问题,以至于后世不能通过历史辨其正宗,“忘其本来,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乃曲为之庇,至于如是,此直心死已矣”[4]165。章士钊通过解读王船山的观点重现历史上受异族统治的历史,目的是以此激发国人的历史记忆,实现振国魂的主张。
在论述东晋成帝第十四条时,王船山将南宋与东晋进行比较。南宋与东晋虽然都偏居一隅,但南宋的官员“无不以报仇为言,而进畏懦之说者,皆为公论之所不容”,而东晋朝廷的官员则“侈敌之威,量己之弱”,“坐困江东”。在章士钊看来,这些畏惧异族、不思复国、贻误后世的官员都是“竖儒”,也属于败儒的行列。“竖儒之簧鼓,竟执小以遗大,勇私斗而忘国仇,以至于亡。”[4]163这类败儒不仅存在于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中,被章士钊称为“真汉奸”。“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4]158协助满清荡平太平天国、谄媚慈禧杀害中国义士以及协助满族官吏搜刮中国钱财的官员都是“真汉奸”,是汉族中的“异类”。在章士钊的论述中,华夏民族统治天下无论在治统上还是在道统上都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一脉相承的华夏文化自然而然是不可动摇的根本,而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则是对正统的颠覆,为少数民族歌功颂德、不思复国的官员、知识分子也就成了其笔下的“败类之儒”。
(二)辨败儒:从文化上肃清汉族中的异类
综上所述,结合本课例的教学实践,希沃授课助手的“桌面同步”“课件演示”“拍照上传”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希沃授课助手”新技术的支持下,课堂教学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达成了新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得到提升。
喂食动物鱼腥草能使受伤动物的脓液快速排出,促进新肉的生长。另外,鱼腥草可与黄芩、地塞米松、贝母、金钱草、桑白皮等进行配伍治疗动物疾病。
(三)振国魂:反对心亡与习安
第一,重点从“种族”与“文化”维度进行阐释是章士钊解读船山学说的鲜明特征。从章士钊对拓跋氏、胡元等少数民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特别注重对少数民族种姓与文化问题的考察与分析。章士钊强调从“风习”与“血液”的视角分析种姓,并认为汉族本身的文化与生理基础是不可动摇的国粹,由少数民族易主中原而引发的朝代变更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心亡而习安”是汉民族丧失原有种姓的表现,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重拾本民族的国粹,从文化上剖清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界限。从章士钊对船山学说继承与发扬的角度来看,他主要继承的是船山的“夷夏大防”思想,将船山学说中的种族观点扩大化了。章士钊的这一做法与当时的时代主题是分不开的,1901年至1905年间“排满”是革命者的重要主张,要“排满”就必须“剖清人种”,而从文化、历史上重新阐述汉民族与满族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章士钊解读船山学说并进行演绎,他对夷夏关系的认识受到王船山的直接影响。王船山认为,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种类,圣人“清其族,绝其畛,建其位,各归其屏”[5]。 圣人“绝其畛”正是对严明种类之别这一自然规律的恪守,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出现祸乱,这样的圣人才是“与天地合德者”。“自畛其类”这一规律在王船山民族观中具体体现为“保其类”的种族思想,“不可使夷狄间之”。在夷夏差别的认识方面,他们二人都特别注重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严格界定“中国”与“夷狄”,并以此严明“夷夏之大防”。王船山认为严明夷夏大防是“古今之通义”,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中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认为“隋之于周,虽其臂而夺之,而不得谓之不道,以其于驱逐之理得之也”,“此固历史之公例”[4]168。 但在种族问题的认识上,二者还存在差别:在王船山的民族观中,种族、地理环境、气质都是区分夷夏的维度,而在章士钊的解读中则重点强调的是种族维度。
《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是章士钊解读与引申王船山的学说、观念而撰写成的。章士钊对船山学说的解读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此外,官方代表是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要“发言人”,是阻滞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中坚力量。对于相关管理部门而言,履行管理职能、保证执政执法过程中的公信力是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精神资源,既是价值认同,也是责任期待[16]。官方代表发布的网络舆情信息是其他传播主体重点关注的内容,其言论恰当与否直接决定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集中爆发或趋向平息。相关管理部门应安排专人负责官方代表这一消息发布渠道的管理,坦诚、有效地与大众进行沟通,积极引导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合理传播。
王船山认为,天下最为重要并且不能被窃夺的是治统和道统。他认为治统如果被夷狄窃取就会“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统被夷狄窃夺则会沦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其妖妄”[6]339。夷狄盗取华夏文化并以圣贤之名居之,这是对道统的极大亵渎。王船山同时指出,石勒、拓跋氏等夷狄之所以能够成功窃取华夏文化,离不开趋炎附势的败儒。“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6]339章士钊对于王船山笔下的败儒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夷狄盗贼之所以敢于窃天下是因为有败儒歌功颂德,夷狄自知文化不如华夏而内生胆怯,但败儒则奏言通过“修宗庙,开鸿科”的方式笼络人才,使得夷狄之君成了被后世铭记的圣贤。“此败类之儒,罪岂胜杀!其长一二人非分窃国之想,犹可言也;其蒙蔽万世子孙不识太祖、太宗之即为夷狄盗贼,不可言也。”[4]162
王船山认为,“夷夏大防”原则是古今之通义与至高无上的“民族大义”,是否遵循与秉持这一原则才是判断掌权者贤良与否最重要的标准。“晋之所谓贤,宋之所谓奸,不必深察其情,而绳以古今之大义,则一也。”[6]346因此,“心亡”与“习安”是对“夷夏大防”思想的严重背离。在按语中,章士钊认为蔡谟之流讳言国事、宰相风流、将军儒雅、天子只顾青衣行酒,整个权力体系从上到下在“国耻弥天”的情况下“只谈风月”、“勇私斗而忘国仇”,最终只能是灭亡。在论述东晋穆帝时,东晋遗民迫于形势而服从异族,在礼法、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异族无异,以至于“心尽亡而习之也”。章士钊对于同为遗民的王船山报以极大的同情:“故总督而今仍总督,故尚书而今仍尚书,认敌作父,反颜噬人,新订会典,顶礼入朝,其所谓心亡而习安者,是船山之所及见也”[4]164。国亡数百年,子孙已经不知道其原来的国家与“正朔”,对加以阻止的人,则“必诋之曰大逆不道,则其心亡而习安也至于如是,是又何以独无冉闵也耶”[4]164。 从章士钊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东晋遗民心亡习安的阐释实际上是在论述清朝末期的汉族民众,清末的汉族民众同样面临心亡而习安,不知文化正统的问题。
第二,章士钊注重从民族情感、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论述国粹,感情因素较多,学理性分析较少。在章士钊看来,王船山是亡国之人,其学说也是亡国之语。那么在清末那个时局动乱、朝政腐朽的时代,解读船山学说首先要感知的就是王船山作为一个明末遗民的亡国情怀以及对于异族入侵的愤恨之情。章士钊使用“夷为中国之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沉痛也耶”、“吾船山其恫矣”等极具感情色彩的表述,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国人感知王船山丧失国家的悲痛之情,以此唤醒清朝廷压迫下民众的民族意识。从某个角度来讲,章士钊虽然解读的是明末的船山学说,其目的是让明末的王船山在清末继续发挥影响作用。从章士钊之前发表的文章来看,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对政治理论、革命思想的把握是较为系统而成熟的,但在引申船山学说时缺失了很多理性分析的成分,反而付诸较多的感情色彩。可见,章士钊在引申船山民族思想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学理性分析的视角,而是为了宣传效果、大众阅读方便而有意从“感性层面加以鼓动”[7]。
从章士钊引申的船山学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基本思路:以宣扬民族主义为目的,以史学为主体,阐释中国文化与国粹,重振国魂以强国民。章士钊将《王船山史说申义》作为宣传革命思想、附会排满的工具,在分析时涉及种族、夷夏之辨、新史学等以及那个时期革命派宣传的重要形式,可以说是当时革命宣传的重要缩影。
三、传播与误读:作为革命工具的传统思想资源
与这个时期的章士钊解读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王船山一样,孙中山也特别注重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以佐证自身革命思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孙中山曾指出,明末遗民如史可法、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严明春秋大义与夷夏之防,“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8]。在孙中山随后提出的十六字政治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鲜明的传统民族主义成分。春秋大义已经是深入民众骨髓的观念,需要激进的排满口号将其激发出来。当时的国民,对于民权主义或“平均地权”不见得就很明白,然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说,则能大大拨动心弦使之闻风而起”,加之革命者重新阐述历史上满清政府对于汉民族迫害的历史记忆以及传播具有鲜明“夷夏大防”思想的学说书籍,故此“排满革命、光复旧物便迅速成为国人的共识”[9]。从实际成效来看,知识分子的这一排满革命宣传策略是十分成功的,“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10]。不容置疑的是,这种基于中国历史记忆的传统民族主义宣传在普通民众中扩大了革命者的思想主张与影响力。清末知识分子将自己所掌握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源、历史记忆联系起来,从理性与感性两方面宣传民族主义,以达到宣传“排满”革命的目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清末知识分子在传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对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与曲解。其一,为了革命发展的需要,他们对于“民族主义”“革命”等政治理论的概念分析都具有学理性分析不足、激进色彩过于浓厚的特点。民族主义是清末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但知识分子在进行宣传的时候往往被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所裹挟。章士钊的《王船山史说申义》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正本清源”的分析,其目的就是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割裂开来,其实这是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以及文化发展相违背的。清末知识分子在进行革命思想宣传的时候,将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夷夏之辨”作为反抗清朝的思想武器加以运用。从思想本质而言,他们所宣扬的“夷夏之辨”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内容上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理解并没有太大出入,并且具有更加鲜明的“种族”意识。从革命的具体理念而言,王朝鼎革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它与引自西方的革命理念存在很大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鼎革更多的是政治革命范畴,而非实现民主、自由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然而,在进行革命宣传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都从中国传统革命的角度来理解与介绍西方的革命,以此来佐证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正当性。这种人为地将政治概念简单化、刻意化的解释虽然可以让普通民众快速了解自己的主张,进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种解释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其二,以笔端搅动风云的知识分子在挖掘传统思想资源的时候带有明显的工具性与功利主义眼光,他们为了达到“排满”目的甚至采用了不顾“手段”的做法:“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4]152。 可以说,清末知识分子这种似乎有些急功近利的宣传策略,将汉民族与满族二元对立的做法,不但不符合社会现实,也不利于先进思想观念的真正普及。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应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传承与发展传统思想资源,这是国家以及社会成员都必须担负的历史责任。我们在对待传统思想资源时,共同的社会政治主题和经典思想家对于基本政治、社会、伦理规范与理念的阐释、解读都是值得珍视的思想探索和历史经验。理性分析与客观看待中国近代社会中对于传统思想资源的分析与使用,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思想资源的价值和促进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章士钊.章士钊全集:卷八[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08.
[3]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J].历史研究,2000,(3):72.
[4]章士钊.章士钊全集:卷一[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5][清]王夫之.黄书 噩梦[M].北京:中华书局,1956:1.
[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 “排满”宣传为实例[J].社会科学研究,1996,(5):95.
[8]同盟会本部宣言书[N].时报,1911-12-23(2).
[9]冯天瑜.中国近世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4.
[1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98.
The Spread and Misreading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Resources by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Centered on Wang Chuanshan Shi Shuo Shen Yi
LIU Xiao-w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Wang Chuanshan Shi Shuo Shen Yi of Zhang Shizhao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Chuanshan theory in modern times,and is the epitome of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resources by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Zhang Shizhao interprets the theory of Chuansha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the discrimination of caste”, “identify confucianism” and “vibrating the soul of the country”.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analysis of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excessive sensitivity.The rational use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resources provided a certain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However,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so had some misreading when they spread it.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intellectuals'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ideas in this period can provide useful thinking about how to correctly treat traditional ideas and promote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Chuanshan Shi Shuo Shen Yi; traditional ideas;nationalism;revolu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D0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6-0021-05
收稿日期:2019-05-06
作者简介:刘小卫(1987—),男,河南睢县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张莲英]
标签:思想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清末论文; 学说论文; 这一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