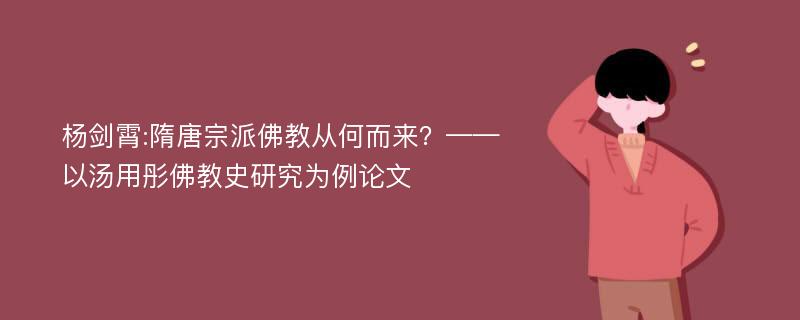
摘要:隋唐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然而,南北朝佛教如何过渡到隋唐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学术史中汤用彤对此的论述无疑是重中之重。汤氏借助中国佛教南北差异问题完成了对此问题的阐释。而在南北差异问题上其历经了三次不同表述,这也对应了其佛教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在赴西南联大之前的第一阶段,汤用彤以纯粹佛教史研究为本位,认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北统上承汉代经学,南统下接魏晋玄学,而隋唐佛教主要继承了北统。到第二阶段,汤用彤学术中心转向魏晋玄学。由此,他在南北差异问题中加入了价值判断,即魏晋玄学更为先进。所以汤氏将隋唐佛教继承北统的结论修正为前期受北方影响,后期则富南方风气。第三阶段,以对日本学界宗派问题论述的批判为契机,汤用彤将南北朝佛教如何过渡到隋唐佛教的问题从南北差异的论述中抽离出来,并最终通过从学派到教派这种宗教史内在脉络的梳理方式替代了南北差异问题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汤用彤;佛教史;南北差异
隋唐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然而,在佛教史梳理中南北朝佛教如何过渡到隋唐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汤用彤在佛教学术史上的位置毋庸赘言,其中国佛教史研究无疑是学界展开佛教史论述的基点。因此,从汤用彤出发检讨这一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成为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汤用彤一生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一个动态的多样化过程,这点在他对中国佛教南北差异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以此为中心,对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和隋唐佛教承何而来的问题进行一次重新梳理。
张志彤: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的第一年,也是全面推动水利改革发展的关键一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汛抗旱的部署,按照水利部党组要求,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供水安全,尽最大努力减轻洪涝和干旱灾害损失。
中国文化南北差异的认识古已有之,如《中庸》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北史·儒林传序》更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之语。有关佛教南北差异问题的讨论亦非汤用彤孤明先发,如汤氏本人便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引唐代神清《北山录》卷四后自言:“唐世已有分佛教为南北二系之论也。”[1]341而若就汤氏论说此问题的契机而言,便不得不提到梁启超。一是梁启超乃最早从现代学术立场讨论南北差异之人,开学界探讨此问题的先河。二是汤用彤对此问题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以梁氏研究为参照的交互关系,这点也是我们后文分析的一个线索。
高标清兼容的电视播出系统具有安全、统一、高效的特点,但同时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因此,需要在满足播出安全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成本。随着近年来数字电视建设完成后,高清信号的用户会越来越多,而通过高标清兼容的集群播出系统,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1902年,在接受西方和日本文化地理学理论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以研究地理对中国文化的决定作用。此后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等研究也均受此影响。概括言之,第一,梁启超是以考察中华文化这一整体为起点,由此确定中华文化地域差异(主要是南北差异)的成因为地理因素。如梁氏所言:“其在文学(即哲学、经学、佛学、词章、美术、音乐)上,则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2]705第二,梁启超对文化南北差异研究的归宿又落在深切的现实关怀上,从地理决定转向对“人力”的高扬。如其在分析文化南北差异在唐代瓦解后指出:“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今日轮船铁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治之矣,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2]708正是在从文化到现实的脉络中,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才得以“登场”而被梁启超等人言及。基于此背景,再进入汤用彤佛教南北差异研究的检讨。
一、第一阶段:佛教史为本位的独立期
早在因战乱赴西南联大(1938年)之前,汤用彤就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完成了《中国佛教史讲义》的撰写工作,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在1932年铅印成册。此《讲义》不仅是1938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下简称《佛教史》)的前一稿(即第三稿①),同时,今日我们所见的《隋唐佛教史稿》亦是由其中隋唐部分整理而成。汤用彤对南北差异的讨论也正肇始于这一时期。
11.关于陈宝生部长“三进”思想,其中,进教材是基础,建课堂是关键,进头脑是目的,实现理论体系— —教材体系— —课堂体系— —教学体系— —价值体系的有效转化,三进思想符合学生思想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
这一时期,汤用彤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论述:第一,南北佛教的不同之处;第二,分殊的原因;第三,南北差异的影响。第一个问题,汤用彤延续了传统的观点,即“南方偏尚玄学义理”而“北方重在宗教行为”[1]341。这不仅与梁启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3]9的论断一致,更是学界之共识。然而,以此结论为中心,汤用彤对佛教南北差异向上之原因和向下之影响的论述均表现出与梁启超以来学界理解的不同。首先,在差异成因问题上,汤用彤云:
南朝之学,玄理佛理,实相合流。北朝之学,经学佛学,似为俱起。合流者交互影响,相得益彰。俱起者则由于国家学术之发达,二教各自同时兴盛,因而互有关涉。[1]369
汤氏认为佛教北统之所以重迷信缘于汉代经学与佛学“俱起”。“北朝经学上承汉代,本杂谶纬。而元魏僧人,颇兼知术数,则亦汉世佛道与阴阳历数混杂之余绪。”[1]370与之相对,“佛义与玄学之同流,继承魏晋之风,为南统之特征”,因此“南统偏尚义理,不脱三玄之轨范”。[1]287而玄佛合流的中介,就是当时为“内学外学所共许”的“本末”思想。这也是汤用彤对南统佛学理解的独创之处,即不仅强调本末的思想史价值,更指出“五朝之所谓本末,略当后世之所谓体用”[1]328。如前所论,梁启超以来对此问题主要是从地理决定论角度进行分析。梁启超就明言:“同一佛学,而宗派之差别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响使然也。”[2]707刘师培更详细论云:“又南方之疆与赤道近,稽其轨道与天竺同,中国南方之地在赤道北二十度至三十度之间,印度北部亦然,故学术相近。”[4]736显然,汤用彤并未采用这种地理差异决定文化差异的逻辑,而是用思想史的内在脉络来勾勒南北差异,即汤氏所谓“学问演进之趋势”。
更尖锐的矛盾发生在南北差异的影响问题上。梁启超曾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指出:“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3]10即佛教南统开启隋唐宗派,且更代表“国民性”。与之完全相反,汤用彤明确指出佛教北统“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并进一步总结道:
及至隋帝统一中夏,其政治文物,上接魏周。而隋唐之佛理,虽颇采取江南之学,但其大宗,固犹上承北方。于是玄学澌尽,而中华教化以及佛学乃另开一新时代。[1]371
可见,汤氏的分析是从政治变革到思想变迁的思路,即因为隋代政治承自北朝,故佛教自然延续北方。
从双方论述可以看出,这种矛盾已不是地理决定论与思想史这种研究理论上差异的显现,而是研究立场的分歧。前文已述,梁启超的南北差异研究是以中华文化整体为本位,且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所以其讨论更多的存有对文化和现实的关照,而不是“就事论事”。由此,出现隋唐宗派继承南统与中国之“国民性”联系上也就不足为奇。与之不同,汤用彤《佛教史》的写作本就是以佛教史课程讲义为基础,主要是出于学术的目的。这点从1938年其《佛教史》跋中就可窥见。正因为此,汤氏的分析才会从佛教发展自身去考量,以政治史推进至思想史,再对思想脉络和变迁予以讨论。这是纯粹佛教史研究的立场。
二、第二阶段:魏晋玄学为主体的融合期
在赴西南联大之后,汤用彤对佛教南北差异问题的论述发生转变,可以说开始逐渐向梁启超靠拢。这一变化集中反映在1944年他在西南联大所作的讲演《隋唐佛学之特点》中。《隋唐佛学之特点》将隋唐佛学特征概括为四,即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或独立性、系统性。南北差异问题的论述主要在统一性和系统性部分。汤用彤也就此分别对差异的来源与影响两个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
哑巴也怔了。但哑巴把汤翠的愣怔当成是鼓励,一下子就抱住了她。哑巴力度强悍,汤翠感觉到其男性的威猛,身子哆嗦起来。汤翠一激动就要哆嗦,哆嗦得越厉害说明越激动。
南方受魏晋玄学影响、北方承袭汉代经学的论断在《佛教史》中既已有之,并非新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汤用彤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南北孰优孰劣价值判断,即南方比较先进,而北方相对陈旧。虽然,这种价值判断表面上延续着思想史分析的脉络,但已有了明显的价值导向性。
这里汤氏反思了以政治史主导宗教史研究的缺陷,明确指出佛教史的书写应先从宗教内部进行梳理,不能以政治变迁来“贸然断定”。但即便如此,在进入宗派问题以前,汤用彤还是不得不通过从政治史到思想史的路径来处理中古佛教史。这点在《魏晋思想的发展》中有明确的表述:
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南方)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觏也。若北方,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增加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无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希。[3]9-10
这与汤用彤“玄学本比汉代思想超越进步,所以南方比较新,北方比较旧”的结论相似,梁启超整个讨论充斥着南方学术先进而北方落后的思路。也正是在此逻辑下,才会有“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的结论。正因为汤用彤在此阶段有了与梁启超共同的价值判断,梁、汤二人在之后的论述上也就趋向一致:
(2)从业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竞争压力陡增。据统计,2017年初级会计职称报考人数高达186.68万,中级会计职称报考人数也达到110万人,均创历年新高。这一方面说明了身为会计人的危机感倍增,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会计行业竞争的激烈。另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高达820万人,比2017年多出25万,再创历史新高。当前会计行业的热门度丝毫不减,会计证取消后行业门槛被打破。身为一名会计人,如何守住自己的饭碗,是每一个会计人或准会计人必须直面的现实。
梁:隋、唐之际,宗风极盛。天台、法相、华严三宗,号称教下三家,皆起于北。陈义闳深,说法博辩,而修证之法,一务实践,疏释之书,动辄汗牛,其学统与北朝经生颇相近似。惟禅宗独起于南,号称教外别传。[2]707
汤:华严、天台、法相三宗发达最早。……它们原来大体上可说是北统佛教的继承者。禅宗则为南方佛学的表现,和魏晋玄学有密切关系。[5]10
不难看出,二人从观点到行文顺序都高度一致,即天台、法相、华严起于北方,诸宗之中唯禅宗起于南方。结合二人南方高于北方的价值判断可以推测,这种论述旨在突出禅宗在隋唐宗派中的殊胜地位。实际上,汤用彤在《隋唐佛学之特点》最后总结隋唐佛教时也确实指出:
(5) 填筑完毕后,从模型桶侧壁开口处开挖,开挖出所需模拟溶洞形状及大小。溶洞设置为底面直径30 cm、高为15 cm半球型溶洞,顶部埋深25 cm。开挖完成后将洞口用粉质黏土回填,关闭模型桶开口,形成一密闭土洞。
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汤用彤发生这次学术转变呢?我们先从1938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汤用彤给王维诚的一封信说起:
说到放贷者阿谬娜太太,我们总是能在文中看到阿斯科尔尼科夫称她为“虱子”而且就算是阿斯科尔尼科夫杀了她之后,内心承受着精神折磨和灵魂的拷打,也经常认为自己没有错。他总会想到阿谬娜是个虱子,我没有杀人,只不过是踩死一个毒害社会的虱子。没错,从文章中不难看出阿谬娜的劣迹。她对其亲妹妹如此苛刻,甚至可以说是折磨,同时又是一个剥削他的资本家。至于为什么称她为虱子,这就需要探究。
高二的期末考,我的成绩不出意外地让父母叹息。老妈说:“你原来很优秀的,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看着她忧伤的表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然,这种转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39年完成的《魏晋玄学论稿》第一篇文章《读〈人物志〉》中,汤用彤还没有对玄学产生前后的学术作出价值判断,仅仅认为这是“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7]12。之后又言:“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7]13可以注意到,此时所言的“演进”强调的是无优劣的“变迁”,而不是从落后到进步的“发展”。这也与《佛教史》的立场一致。
唐朝前期佛学富北方的风味,后期则富南方风气。……南方的禅宗,则简易直截,明心见性,重在觉悟,普通人都可以欣赏而加以模拟。所以天台、华严那种中国化的佛教行不通,而来自印度的法相宗也行不通,只有禅宗可以流行下去。禅宗不仅合于中国的理论,而且合乎中国的习惯。……由此也可见凡是印度性质多了,佛教终必衰落,而中国性质多的佛教渐趋兴盛。[5]10
彤到滇已三月,因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移设蒙自,遂复来此地。……彤去年本欲于今年休假期间进研五朝玄佛之学,但现值变乱,虽稍稍观览,然未能专心。……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但世事悠悠,今日如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故亦不求改削也。[6]511-512
各村要从村情、民情的实际出发,征求民意,认真调研,厘清经营思路。当地政府要帮助组建意向村把好组建关,避免为争取补助而“盲目推进”或为争取政绩而“好大喜功”的冒进现象。
早在1938年赴云南之前,汤用彤就对魏晋玄学有所涉及②,特别在完成《佛教史》的写作后,他已经意识到《佛教史》中对中国本土思潮反映得不够充分,只是出于“如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所以才在战乱中仓促完稿。正因为此,到西南联大之后,在1939年至1947年,汤用彤把全部学术精力都投注到玄学上,先后完成九篇相关论文,这也就是今日我们所见的《魏晋玄学论稿》。而实际上,汤用彤也是有意识地想用玄学来修正“前作之不足”。这自然就促成了他从佛教史内部向中国文化全体延伸的学术立场转变。
汤用彤基于南方玄学先进于北方经学的判定后认为,南方的禅宗更合于中国的习惯和理论演进潮流,也唯有符合此潮流才能兴盛,反之如其他宗派则终必衰落。可以看到,这里汤用彤走出了自己此前以佛教史内部脉络为主的论述,转而以中国思想史全体为考察中心。按其理解经学与玄学代表的不仅仅是理论演进的时间先后,而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优劣不同。如此,“和魏晋玄学有密切关系”的南方的禅宗自然是隋唐佛教的主体。这无疑与梁启超从立场到论断都如出一辙,却与自己《佛教史》时的理解有所不同。
1940年,汤用彤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一文中确立了其玄学研究的核心论点:“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7]42而此观点又是在他体会到本体论较之宇宙论更具“进步性”的情况下产生的:
……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魏晋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7]35
自此开始,汤用彤对玄学的理解加入了我们在《隋唐佛学之特点》中看到的价值判断,即从汉代宇宙论到魏晋本体论,不是学理的“变迁”而是从劣到优的“发展”。而其学术重心也随之从中古佛教史移向了魏晋玄学。这点在同年完成的《言意之辨》中彻底地反映出来。
玄学之发达乃中国学术自然演化之结果,佛学不但只为其助因,而且其入中国本依附于中华之文化思想以扩张其势力。[7]31可以看到,此时汤用彤已经与梁启超一样的以中华文化思想为本位。唯一不同或许是梁启超更多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而汤用彤主要是在学术研究内部。此后,汤氏的学术中心也就彻底转向探寻“汉代宇宙学说如何演为魏晋玄学之本体论者”[7]45。故在《隋唐佛学之特点》讲演前的两年(1942—1943年),汤氏完成了《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和《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的写作。③
作为“对自己玄学研究的总结”[8]244,1947年,汤用彤在西南联大的演讲《魏晋思想的发展》被整理成文发表。按照汤氏自言,此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一)玄学的产生是否受佛学的影响?(二)魏晋思想在理论上与佛学的关系如何?”而实际上结论很简单:“玄学的产生与佛学无关。……反之,佛教倒是先受玄学的洗礼,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我国人士所接受。”[7]92不难发现,汤用彤对魏晋时期思想的概括已经完全出于对中华文化思想全体梳理的用意,佛教自然被作为中华文化以外的“他者”来看待。可以说几经转变,此时的研究已与从佛教内部书写《佛教史》和之后用玄学补《佛教史》不足的初衷大相径庭。
三、第三阶段:宗派问题为中心的瓦解期
汤用彤对佛教南北差异的理解并未随着玄学研究的系统化而盖棺定论。1962—1963年,汤氏先后发表《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其学术中心开始转移到宗派问题上,而此前对南北差异的论说也随着对宗派问题的讨论而瓦解。
这一趋向体现在1962—1963年汤用彤写作完《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后为《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作准备而进行的《佛教宗派问题摘抄(戊类)》里。汤氏在阅读沈曾植所撰《法藏一勺》时于“总论诸宗”部分写下了以下按语:
……到了魏晋南北朝虽然日趋兴盛,但是南北渐趋分化。南方的文化思想以魏晋以来的玄学最占优势;北方则仍多承袭汉朝阴阳、谶纬的学问。玄学本比汉代思想超拔进步,所以南方比较新,北方比较旧。[5]6
禅宗、净土宗、戒律宗,为北方实际的佛教。三论、天台,为南方理论的佛教。北华严为缘起论宗,南法华为实相论宗。[9]475
汤用彤这里以禅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为北方佛教,三论、天台则属南方。这显然与《隋唐佛学之特点》中将天台、华严、法相视作北方佛教,禅宗为南方代表的观点相左。
宗派的南北区域问题本属历史考证范围,但如上文所论,这种判定的用意早已超出建立知识的范畴。在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研究中,对禅宗是南统仅有代表者的强调表达的是禅宗因吸收玄学思想而大获成功的隐性逻辑。汤用彤甚至就此将《佛教史》原本提出的隋唐佛教来自北统的结论修正为唐前期以北统为主,后期则受南方风气影响。这也与梁启超从立场到论述趋向了一致。然而,按引文所示,禅宗、天台的南北所属被汤用彤修正,这就让此前以进步的南方玄学为本位的佛教史叙述无法成立。
别呦呦把手伸到我腋窝,我怕痒,醒了。一睁眼,天早亮了,不知从哪传来几声鸟叫,有团雾从我眼前飘过,我伸手抓,抓住了,又让它溜走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冲突的呢?这就涉及汤用彤在中古佛教史研究中始终期望解决的一个问题:南北朝佛教怎样过渡到隋唐佛教。当然,这一问题从提出伊始就暗含了以王朝变迁来看待宗教发展,即从政治史推进到宗教史。就此,汤用彤对政治史与宗教史的关系作了谨慎地思考:
盖政治制度之变迁,与学术思想之发展,虽有形影声响之关系,但断代为史,记朝代之兴废,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而于宗教时期之分划,不必即能契合。……学者于区分佛教史之时代,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分划时代,乃臻完善,固非可依皇祚之转移,贸然断定也。[10]1
而此态度恰与梁启超如出一辙。梁氏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指出:
南朝北朝的名称,不仅是属于历史上政治的区划,也成为思想上的分野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不仅及于我国固有学术的面目,就是南北佛教因为地域的关系也一致的表现了不同的精神。[7]86
及至清朝末叶,海禁大开,国人往东洋者甚多,发现日本存有大量中国已佚的佛书,佛教学者一时视为奇珍。日人关于中国宗派的记载,亦从此流传。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刊行《新民丛报》,忆其中有文列中国佛教十三宗,约在同时,石埭杨文会(仁山)因凝然所著《八宗纲要》重作《十宗略说》,从此凝然所说大为流行。[11]368
宗派问题的产生源于汤氏对日本学界的回应,按其自述:
正因为此,佛教南北差异问题获得了更多的理论意义。如前所述,在第一阶段,汤用彤通过区分南北朝佛教南统与北统,建立了北统到隋唐佛教的连续性。而这种依托政治史的叙述也延续到了魏晋玄学为中心的第二阶段,所不同的是结论被修正成前期北统为主,后期为南统。可以看到,无论两个阶段的学术中心如何转变,以南北差异为线索来解决南北朝佛教如何过渡到隋唐的用意始终未变。汤用彤并未停留在这一政治史的框架内,而是通过对宗派问题的反思,将此问题的理解升华。
毋庸置疑,中国近代的佛教研究受日本影响颇深。无论是梁启超、杨仁山,还是蒋维乔、黄忏华,都主要是延续日本学界的问题与思路。汤用彤更自觉地意识到“中国近七十年来之记载系抄袭日本”[11]364。他对宗派问题的讨论也正是出于对当时日本学界观点的批判。汤用彤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佛教有宗派存在,而是指出传统的理解对学派之“宗”与教派之“宗”不加区分。从概念本身入手,汤氏梳理了“宗”的两个含义:
(1)“宗”本谓宗旨、宗义,因此,一人所主张的学说,一部经论的理论系统,均可称曰“宗”。
(2)“宗”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它是有创始,有传授,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11]360
按照汤用彤自己的说明,二者主要的分别在于学派之“宗”是就义理而言,教派之“宗”是就人众而言,“前者属佛学史,后者属于佛教史”[11]361、364。值得注意的是,汤氏强调了两晋以来盛行的是学派的“宗”,到隋唐时产生的是教派之“宗”,“它们是一个历史的发展”[11]361。换言之,从学派到教派的发展正好对应从南北朝佛教过渡到隋唐佛教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汤用彤在《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中对宗派的讨论主要围绕“为什么教派在隋唐兴起”展开。据其总结,教派兴起主要在于从师承到传法的演进:
在中国佛教的宗派历史中,传法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它在隋唐以后才盛为流行,前此不然。……但在汉晋之际,佛法初行,僧人有师徒关系而无传法之说。……仅是知识传授,与后来的所谓传法的意义不同。[12]394
如前所论,第一、二阶段,汤用彤还是通过佛教南北差异来建立自南北朝到隋唐佛教的连续性。但在经过宗派问题的讨论之后,他已经从南北差异问题上升至对“宗派”概念的分析。因此南北朝佛教过渡到隋唐佛教的问题开始与自学派到教派的宗教史内部发展脉络建立联系。基于此,南北差异问题的理论意义被宗派问题替代,宗派的南北归属也就失去了承载整个佛教史演进的功能。实际上,汤用彤就此便放弃对南北差异问题的系统性论述。那么在此背景下产生与前阶段表述不一致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总结
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并非一成不变,在中国佛教南北差异问题上历经了三次不同的表述,这无疑展现了汤用彤佛教史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早在赴西南联大(1938年)之前的第一阶段,汤用彤以纯粹佛教史研究为本位,认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北统上承汉代经学,南统下接魏晋玄学,而隋唐佛教主要继承了北统。到第二阶段,汤用彤学术中心转向魏晋玄学,所以其佛教史研究不再以佛教史本身为出发点,而是以中华文化全体特别是魏晋玄学为本位。由此,他在南北差异问题中加入了价值判断,即魏晋玄学更为先进。所以汤氏一再强调南方兴起的禅宗与玄学的关联,并将隋唐佛教继承北统的结论修正为前期受北方影响,后期则富南方风气。第三阶段,以对日本学界宗派问题论述的批判为契机,汤用彤改变了此前从政治史到宗教史的研究思路,将南北朝佛教如何过渡到隋唐佛教的问题从南北差异的论述中抽离出来,最后通过从学派到教派这种宗教史内在脉络的梳理方式彻底瓦解了中国佛教南北差异问题的理解意义。
大数据驱动下,信息融合的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图书馆的各类数据库资源、信息系统资源,还包括各类感知设备所采集的信息,以及图书馆用户行为数据等。将这些信息进行全面整合,最终实现终端应用、大屏展示和移动APP上的信息联动,是智慧图书馆信息系统实施的基础。
注释:
①有关《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成书过程,参考赵建永的《汤用彤与现代中国学术》,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8—163页。根据赵建永的分析,第一稿是汤用彤1926年冬在南开大学完稿的讲义《中国佛教史略》的前半部分。现存东南印顺公司代印中央大学讲义《汉魏六朝佛教史》(1927—1931年间讲授)是第二稿。
除了以上专家之外,会议还邀请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元清、核工业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副所长潘国伟、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总经理陈振明、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教授级高工靳红泽分别做了“基于断裂力学的含裂纹或类裂纹缺陷的钢构件安全性评定技术研究”、“核电站核岛安装施工管理软件焊接模块介绍”、“建筑钢结构中欧美标准焊接技术及应用”、“涉外水电工程采标情况”的演讲,演讲内容紧紧围绕主题,对各自行业的相关焊接技术、标准都非常翔实的报告,深受代表好评。
中国石油石化:王博士,您好!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农膜大国,农用地膜产量和使用面积居全球首位,但高端农膜比例仅占10%,大部分农膜仍是不可降解的。在您看来,不可降解农膜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②按照赵建永的考证,汤用彤早在1932年就已经开始了对玄学的研究。参见赵建永的《汤用彤与现代中国学术》,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
③其实早在1933年《癸酉(1933)读书札记》第一册中,汤用彤就对易学问题作过笔记,为此后易学研究进行了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G]//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G]//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G]//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G]//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
[6]汤用彤致王维诚信一通[G]//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4).合肥:黄山书社,1999.
[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赵建永.汤用彤与现代中国学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9]汤用彤.佛教宗派问题摘抄(戊类)[G]//汤用彤全集(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0]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1]汤用彤.论中国佛教无“十宗”[G]//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
[12]汤用彤.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G]//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
TheOriginofSectarianBuddhisminSuiandTangDynasties—Based on Tang Yongtong’s Study on the Buddhist History
Yang Jianxiao
Abstract: The Buddhist history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s in a period of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but the problem that how could Buddhism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ransit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s still unsolved. The discussion of Tang Yongtong in academic history undoubtedly is the priority among priorities. Tang used the Chinese Buddhism’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to elaborate this issue. In fact, the issu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experienced three different statements,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ree stages in the study of Buddhist history. In the first stage before going to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Tang Yongtong considered the pure study on Buddhist history as the standard, showing that Buddhism in the period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undertook Han’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north and linked Wei Jin metaphysics in the South. Buddhism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herited the northern order. In the second stage, Tang Yongtong’s academic center was turned to Wei Jin metaphysics, and then he increased value judgment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ctually, Wei Jin metaphysics was more advanced, thus Tang corrected the conclusion that Buddhism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herited the northern order as the northern affection in early stage. The later period was filled with southern custom. In the third stage,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discussing the sect issue in Japanese educational circles, Tang Yongtong came out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s analyzing how could Buddhism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ransit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finally used the systematic mode from the school to denomination to replac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Keywords: Tang Yongtong; buddhist histor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作者简介:杨剑霄,男,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佛教史、唯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项目编号:17ZDA233)。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9)01-0151-06
(责任编辑李华)
标签:佛教论文; 玄学论文; 隋唐论文; 宗派论文; 魏晋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史论文; 《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17ZDA233)论文; 清华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