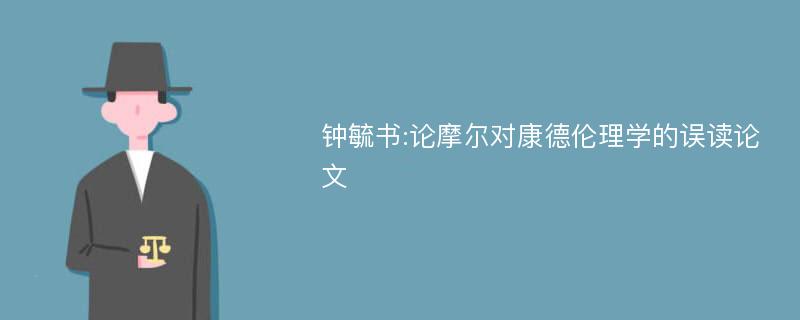
摘 要:元伦理学家摩尔认为康德伦理学由于混淆了“是善的”和“应以某种方式被思维的”问题,导致其所进行的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引发的全部汗牛充栋的著作一钱不值。 其实,摩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是有问题的。 首先,摩尔因为没有正确把握康德想突显“人的价值”的意图而仅在逻辑上进行推演,导致其彻底错估了康德伦理学的价值;其次,摩尔因为误读了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让自己的伦理学退回到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从“是”推导出“应该”的路径;最后,摩尔由于没有认识到“善”概念具备“依附性”,单独将“善”抽离出来研究是没有价值的,导致其在善的问题的探讨上彻底沦为了一场“语言游戏”。
关键词:摩尔;康德;善;意图;理性事实
一、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理论
摩尔认为伦理学必然是与“什么是善的行为”这一主题有关的。 然而,因为人们都非常清楚什么是“行为”。 因此,有关“什么是善”的问题的研究则应成为伦理学研究的普遍的主题。摩尔认为,如何给“善”下定义,是全部伦理学中的最根本问题。 除“善”的对立面“恶”之外,“善”是伦理学特有的惟一单纯的思维对象,对“善”的定义是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如果缺乏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虽然伦理判断仍然可能会有效, 但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伦理学的目的是给认为是“善”的某一判断提供正确的理由。
摩尔指出“定义”是陈述必定构成某一整体的各个部分。 在这个用法上,摩尔认为“善”是没有“定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若干组成部分。 他指出:“如果我被问到‘什么是善’,我的回答是:善就是善,并就此了事。 或者,如果我被问到‘怎样给善下定义’, 我的回答是, 不能给他下定义;并且这就是我必须要说的一切。 ”[1]善是不能下定义的无数概念之一。 类似善这样的概念是最后的术语,其他一切术语都必须参照它们来下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指出,他所谓的“善”不可下定义并不是指“善的东西”不可下定义,即“善者”不可下定义,而是指“善”这个单纯的概念不可以下定义。 他相信善的东西是可以下定义的,但是“善”本身是不可能下定义的。
基于“‘善’不可定义”的观点,摩尔指出许多哲学家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 “自然主义谬误”是指将形容“善”的某些性质的自然客体等同于“善”本身,并认为形容“善”的某些性质的自然客体是与“善”本身完全相同的东西。 摩尔指出:“这种方法就是用一个自然客体的或者自然客体的某一性质来代替‘善’。 ”[2]摩尔认为“善”本身不能跟任何自然客体如感情等同。 这是因为“善”本身并不是某种自然性质。 “善”并不因为某一自然客体实存而转移。 摩尔进而认为,“善”是一个单纯的,既不能下定义,也不可分析的思想对象。 而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参照这一思想对象来下定义。
摩尔认为, 在通常的伦理论证中因为没有将“善”的概念区分清楚,因而遭遇了许多困难。摩尔指出伦理学必须列举一切真实的普遍判断, 这种判断断言某事物无论什么时候都必然是善的。在有关伦理问题的论证中,往往有两种方式证明某种行为是否为善的: 一类论证试图证明某些行为本身就是善的, 另一类论证试图证明某些行为作为手段是善的。 只有这些问题才是任何伦理讨论所必须能够加以解决的;而且, 解决其中一个跟解决其中另一个并不是一回事。 摩尔认为,当我们认为某一行为“作为手段是善的”时,我们就是作一个有关它的因果关系的判断。然而,要找到具有普遍正确性的因果判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作为手段是善的”的某些行为,我们不能准确地去判断这些行为的因果判断都是真实可靠的。 人们甚至不能够确信类似 “恰好某些行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发生,并总能够恰好地产生某一种效果”这样的理论假说。 我们不可能知道某一行为在任何场合下发生所产生的效果。 在种种不同的情况下, 同样的某一行为可能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不一样的效果所依赖的事物的各个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有关“作为得到一种特定效果的某一种特定行为的手段来说是善的”所有的伦理判断里, 没有任何一个是完全真实可靠的。同时,即使许多伦理判断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是真实可靠的, 但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是极其不可靠的。 因此,人们需要谨记的是,不仅一个行为必须确信为能够产生一个极佳效果的行为, 同时要在因为这个行为影响而产生的接下来的所有行为中, 善的余额都要大于可能采取的任何其他行为。换言之,如果要判断某个行为是否作为手段是善的, 不仅要判断它产生了多少善的效果, 还需要去判断这个情况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中所允许的最大善。 这个工作无疑是巨大且困难的。不过,“作为手段是善的”仅仅意味着这件事物是达到善的手段——它会有些好的效果。“作为目的是善的”则是指这个行为的本身就具备我们所断定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仅隶属于它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和效果的那种性质。 但是,对类似“这样的行为正当吗”或者“什么是我们应当指望得到的”等诸如此类的命题进行分析,会发现这些命题内部都包括“什么行为本身是善的”即“作为目的的善”这个判断。 这样的一个判断仅仅意味着,所讨论的行为方针是最好的方法, 这样行动会得到一切可能的善。 并且, 无论它是真实或是虚妄的, 都包含一个有关论证的行为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善的程度的高低的命题。摩尔认为,一方面, 决定哪些事物具有善和在什么程度上具有善的这一伦理学的首要问题和任务在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另一方面,由于对作为手段的善和作为目的的善毫不相关的这一真理理解模糊, 也大大忽视了对手段作彻底的探讨。实际上,什么本身是最好的和什么会带来可能最好的东西,这两个问题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把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分得越清楚, 则正确回答二者的机会就越大。同时,在进行诸事物具有善的性质的不同程度的探讨时, 我们必须注意一整体具有善的程度可以不等于它的各部分的善的程度之和这一事实。
在探讨完“作为手段的善”之后,摩尔对过去哲学家就“什么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所提出的某些答案进行了考察。 摩尔将这些理论分为“形而上学的”和“自然主义的”,并认为这些理论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即将某种自然客体等同于善本身。
二、摩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最后,摩尔指出,如此这般被认为是应当去做的,通常被称为道德法则;而这一法则要么与自然法则相似, 要么与法律意义上的法则相似,要么与两者都相似。 而事实上,摩尔指出:“一条道德法则断定 ‘在所有情况下这都是善的’,一条自然法则断定‘在所有情况下这都会发生’,一条法律意义上的法则则断定‘这是一个命令,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去做,或者都必须不去做’。 ”事实上这三者是有根本不同的。摩尔认为康德把应当实存的东西与自由意志所必须遵循的法则相等同, 并通过这种等同,不仅断定了自由意志也要受其应做的事情的必然性的支配,而且意味着,它所应做的意味的只是其自身的法则。 其不同于人类一直的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它必然要做的。 在康德看来,道德律依赖自由比自由依赖道德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摩尔指出,如果一旦能证明能够去意愿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那么紧接着就可以说没有任何行为是应当去做的。 另一方面,摩尔认为康德也犯下了假定“这是应当做的”意味着“这是被命令的”错误。 摩尔认为之所以犯上述错误,就在于假定,当说明“你应当做这个” 就必定意味着 “你被命令着去做这个”。而事实上,断定“这是善的”并不同于断定“这是我所意愿的”。
摩尔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家的批判如下。首先,摩尔认为以康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家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即将属于善的性质的超感存在物归结为善本身,而这是错误的。 摩尔指出:“主张我们可以从任何断定‘实在具有这种性质’的命题推导出或确证任何‘这是善自身’的命题,这是犯下了自然主义谬误。 ”[4]
本刊讯 2016年4月9日至11日,由中国教师报主办、湖北省武汉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等单位协办的第二届全国名师工作室建设博览会在武汉成功举办。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雷振海、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刘华蓉、武汉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主任施火发、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黄玉峰、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成尚荣、台湾台北国语实验小学语文教师李玉贵等出席并参加了此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近1100名校长、教师、名师工作室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首先, 批判的首要工作在于捕捉作者的意图,而不是对内容作补充性的增加或修改。摩尔正是犯了没有认识、 捕捉康德的哲学理论想要解决的难题和康德哲学的意图的错误, 仅仅从理论逻辑上对康德伦理学理论进行添加和修正,从而忽视了康德哲学的合理性。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著作《路标》的一篇论文《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有关批判的方法论原则。 他认为:“批判应击中要害。 这就是说,批判不应面向秩序模式的确定的内容特征、个别判断,诸如对之作出修正,用其他特征和片段来替代他们;批判的意图并不是对内容作补充性的添加, 补上一些未被注意的‘类型’。 对这种哲学批判工作的方式, 需要着眼于它的基本态度并且联系于它企图解决的难题来加以规定。 ”[5]所以说,对一个理论进行批判, 首先应做到对其要解决的难题和其意图进行捕捉, 而不是面向其确定的内容特征和个别判断进行修正。
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一书“形而上学的伦理学” 一章中讨论了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家的谬误。 他指出:“这种伦理理论的伦理观典型地以斯多亚学派、斯宾诺莎、康德,以及特别是一些现代伦理作者为代表。 ”[3]摩尔认为这些伦理学家主张伦理学应该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 并用形而上学术语来描述至善。摩尔所定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涉及某些“超感物”的存在,这些超感物不隶属于任何“自然的”东西。 摩尔认为以康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关注的知识并不局限于经验事物, 他们更关注一些超出经验的不属于自然界与经验范围之类的, 甚至并不存在的一些事物。 摩尔认为“形而上学伦理学”体系的特征是认为一种不存在于自然中的超感实在为至善。
诗中“我”作为主体的第三次状态陈述,S3是“后来”的“我”,O3为价值对象“母亲”。这一阶段,即“我”的中年时期,“我”与“母亲”处于析取状态;
三、摩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误读
康德所处的时代是18 世纪,在经过了物理学等科学上的大发现之后, 宇宙已经被证明了不再是古代宇宙论中的和谐, 而只是一个物理规则作用下的力学场, 除了力与力的相互作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随着古代和谐宇宙观的崩塌,自然已经缺少了供我们沉思、凝视的神性。 而需要人类做的是,主动的规划与进行一些法则的构建。如同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在其著作《最美的哲学史》中所说“与视觉词汇紧密联系的‘沉思’和凝视的知识观,被精神工作、做综合判断的活动以及理智的‘联结’所取代。 ”[6]当自然界本身给我们任何答案时,我们如何才能重构世界秩序?如果我们只听从自己的欲望,那么就有可能会陷入满足私利而牺牲他人的利益的危险。 康德意识到“只有人的意志才是现代人文主义的道德观或者政治法律观的基础,并且,人知道这种行使意志的自由是受限制的,也就是说么每个人的自由必须在他人自由开始的地方停下来”[7]。康德把这个称作“目的王国”。“目的王国”的最高准则是对他人的尊重。 所以康德提出“善良意志”的概念,预设一个“意志的善”,这种“意志的善”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象征着人的力量。康德“善良意志”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标识出了“人”的力量与作用,从而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确立起人文主义的道德观,这也是为何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开篇便提出“善良意志”概念的用意所在。 摩尔由于犯了没有认识、捕捉康德理论所解决的难题和意图的错误, 仅仅从理论逻辑上对康德伦理学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忽视了康德伦理学理论在历史上的功绩, 使其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沦为了一场游戏。
其次,摩尔认为康德伦理学无法逾越“这是善的”到“这是应该做的”的这条“天堑”,而康德伦理学实际上跳出了摩尔的从“是”推导出“应该”的思路,提出了“理性事实”概念,认为作为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而直接被给予的法则本身就是“应该”,不需要任何前提[8]。 康德指出:“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之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能从先行的理性资料,例如从自由意识中(这个意识并不预先给予我们)推想出这一法则,而是由于它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强加于我们,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 不论是纯粹直观还是经验性直观之上的,虽然假如我们预设了意志自由的话, 它将会是分析的, 但这种自由意志作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就会需要某种智性的直观, 而这是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能假定的。 ”[9]从中可以看出,康德认为基本法则是作为理性的一个事实, 先于自由意识给予我们的。“纯粹理性的事实”概念发挥了“哥白尼倒转”的作用:道德乃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的定言命令, 而非任何外在事实及其属性的推论[10]。 摩尔对康德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和倒退, 是将开辟的一条新的道路倒退到传统的从“是”到“应该”的规范伦理学的思路。
其次,研究“超感实在”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家没有发现他们的形而上学和他们的伦理学是矛盾的。 首先,大部分形而上学与实践伦理学之间只有纯属否定的关系,甚至包括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一结论。这是因为形而上学试图告诉我们的是永恒实在的本性,而这种永恒实在的本性恰恰是我们无力改变的。而正因为永恒实在的本性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便可以由此推定,任何善都是由我不能有所作为的情况造成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只能改变未来,但是如果未来的事物是一种永恒实在, 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也无法造成任何善;因为一切已经被永恒实在所断言了。 接着,摩尔指出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断言“我们应该如此”的命题才会有几分真理性。 第一,作为我们向导的真实永恒实在,不是惟一的真实实在。 因为一条命令我们实现某一目的的道德规则,只有在该目的至少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情况下,才可能是合理的。 如果永恒实在是惟一的实在,那么其他任何善的事物都不能在时间上实存。 第二,永恒实在不可能是惟一善的事物。因为如果永恒实在是惟一善的事物,那么能增加这个世界的善总量的事物就不存在。同时,摩尔认为,形而上学伦理学家同时主张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即“唯一的实在是永恒的”和“它在未来的实现也是善”。但当我们断定一个事物是善的时,我们只能确定其存在或者实在是善的。一个事物的永恒存在不可能与必然是同一事物在时间中的存在一样地善。 因此,当我们认为真实自我的未来实现是善的时,这最多意味着一个自我的未来实现正像永恒真实与永恒存在的自我一样是善的。
摩尔认为康德伦理学由于混淆了“是善的”和“应以某种方式被思维的”问题,导致其所进行的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引起的全部汗牛充栋的著作一钱不值。 这一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
不过这种做法当时在图书馆界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定量管理只适宜于图书加工、图书上架等简单工种,不适于较复杂的脑力劳动。然而,我个人认为,即使在图书馆实现了从手工向自动化转变的今天,当时量化管理的思想和做法仍未过时,针对这些议题,业界仍有学者继续在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耕耘。
最后,纯粹的“善”的概念是有意义的,但将其抽离出研究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善”的概念具备“依附性”。 “善”这种观念的存在取决于其本身具有的两个属性, 即对物的依附性和与物产生作用的交互性。换言之,离开了对物的依附性和与物产生的交互性这两个属性,“善” 这个概念将不具有任何价值。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 一书中指出:“每当我们的语言让我们揣测该有个实体而那里却没有实体,我们就想说:那里有个精怪。 ”[11]从本质上来说,“善”就是一个有实体存在而又没有的地方。 我们日常生活中讨论的包含道德意义上的“善”的概念,实际上是在讨论一种“纯然性的善”+“某物”的“A+B”的东西。而日常生活中的“善”这个概念,正是因为物与物的交互作用而变得有意义。
综上所述:脑卒中筛查中采纳颈动脉超声,可有效诊断出颈动脉狭窄程度及其血流参数,并分析其超声特征,值得临床信赖并进一步推广。
“善”的概念因其依附性而有价值。 康德认为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善的,除非它是被命令的。而且,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命令容易出错,所以在终极的意义上,应该做的意味着“某种超感觉的实在权威所命令的”。 就此权威而言,它的命令不可能不公正。 而这种假定的前提所参照的超感觉特性是意志。 摩尔认为这是错误的。 “善是不可定义的,善就是善,并就此了事。 ”“这是善的” 并不与“这是超感觉的意志或者别的什么‘所意愿的’”这个断言等同。 但实际上,摩尔的批判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善”具备依附性和交互性,它必然依附于“超感觉的意志或是别的什么‘所意愿的’”有所指的东西。脱离了这些依附物,“善”的概念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以,脱离这些“善”的概念的依附物,而仅仅去讨论纯粹的“善”的概念,只会沦于语言上的探讨,不具有任何现实价值。
其次是在运营层面发力。企业要持续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提供越来越好的用户体验。这是实际产品质量与企业的品牌定位无缝对接的过程,因为用户通过实际的产品以及具体服务来感知和判断产品价值,从而形成自己对于相应企业产品的品牌定位。企业要清楚,真正在用户的实际消费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用户实际的品牌感知。因此,对企业而言,实现无形的品牌价值与实际产品的有效对接,是企业在自身品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摩尔对康德的批判仅限于逻辑与学理上,没有把握住康德哲学的意图, 误认为康德的理论“一钱不值”。他不仅因为误读了康德“理性事实”概念,从而退回到了传统规范伦理学从“是”推导出“应该”的路径,而且更因为忽视了“善”概念具备的依附性和交互性而导致其将“善”概念单独抽离出来研究的尝试沦为一场 “语言游戏”,成为纯粹学理上的探讨。 伦理学家们因专注于探讨道德术语的语义和逻辑关系, 而不太关心紧迫的现实问题, 使伦理学变成了道德方面的逻辑学,以至于被人讥为“书斋中的学问”“冷冰冰的伦理学”。 伦理学作为一门关注实践精神的学问, 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道德语词的分析, 更应关注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病症”,如此才能彰显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2]〔英〕乔治·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11,42.
[3][4]〔英〕乔治·摩尔.伦理学原理[M].陈德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24,128.
[5]〔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5.
[6][7]〔法〕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M].胡扬,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42,244.
[8][10]郁乐.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J].伦理学研究,2010(3):107.
[9]〔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
[11]〔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1.
G. E.Moore's Misunderstanding of Kant's Ethics
ZHONG Yushu LONG Jingyun
(School of Marxism,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G.E.Moore,a meta-ethicist,argues that Kant's ethics,confusing the question of"being good"and the question of"being thought in a certain way",leads to the worthlessness pile of epistemological works that resulted from his philosophical"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fact, G. E. Moore's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ethics is problematic. First of all, Moore completely misestimated the value of Kant's ethics because he didn't comprehend it correctly that Kant's intention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s" but only makes logical deduction.Secondly, because of misreading Kant's concept of "the fact of reason", G. E. Moore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al normative ethics and deduced "should" from"be". Finally, it's of no value that G. E. Moore study"good" independently since he didn't realize the concept of"good"i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thing".As a result,his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good are completely reduced to a"language game".
Key words:Moore;Kant;good;intention;the fact of reason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4-0064-06
收稿日期:2019-05-09
作者简介:钟毓书,男,安徽六安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龙静云,女,湖北英山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捷]
标签:康德论文; 伦理学论文; 这是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伦理论文; 《云梦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