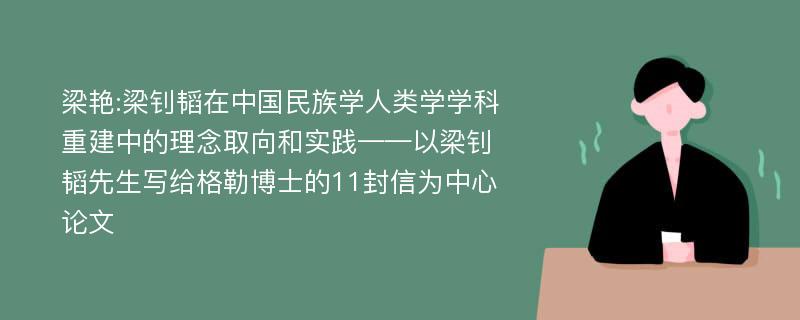
[摘 要]以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先生在1985年11月4日到1987年12月4日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写给他所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格勒同志的11封信为第一手材料,通过对信件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并进行分析,管窥梁钊韬先生对于“民族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民族学人类学的教材编写以及人类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和学科传承等关键问题的实践与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本土语境中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复建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议题以及这些实践与理念对当前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启发和反思。
[关键词]梁钊韬;民族考古学;中国本土语境;民族学人类学重建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建过程中,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梁钊韬先生可谓是最为关键的学者,他以罕见的胆略亲自组织筹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1](P600)从1978年开始,梁钊韬先生已经开始在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重建开始做铺垫,在他的亲自奔走之下,1980年,中山大学党委和行政部门的领导同意了梁的计划,成立人类学系。[2](P11)1981年4月教育部批准了人类学系复办计划,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正式建立,该系成为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最早复建的人类学系。1981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梁遴选为中国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为保证顶岗实习工作有序、高效、安全进行,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接受校内指导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的双重管理。对于不同层次的顶岗实习,对校内指导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及师生比也有所不同。
从1985年11月4日到1987年12月4日,在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梁钊韬先生为了指导他所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格勒的博士论文写作,总共给格勒写了11封信件,这11封信件的时间分别为1985年11月4日、1985年12月6日、1986年2月5日、1986年2月24日、1986年3月31日、1986年4月2日、1986年4月4日、1986年4月12日、1986年5月23日、1987年5月15日、1987年12月4日。这11封信件全部为梁钊韬先生亲笔手写,其中有六封是用毛笔小楷所写,剩余五封信则是用钢笔书写。笔者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访学期间对这11封信件全部进行了录文整理,其中1985年两封书信,1986年7封书信,1987年两封书信,11封信共录文8 391字。
这11封信中的许多内容牵扯到20世纪80年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建过程中一些非常关键的议题。笔者对这11封信的具体内容进行辨识阅读以后,对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录文,然后将其内容进行归类总结,从这11封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梁钊韬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恢复重建过程中所关心的主要议题。
一、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学科中“民族考古学”学科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梁钊韬教授倡导把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理论方法,用以研究社会历史,探索民族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解决了不少民族学和考古学方面的重要问题。[3]除了他最先发现马坝人头骨化石外,还表现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他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4](P3)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复建初期就忠实地实践了他的这一专业理念:“正式规定研究生可以申请人类学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都有一个确定的研究方向,即民族考古学。”[2](P14)梁先生在培养自己学生的过程中也格外关照这一点:“到了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的导师梁钊韬要求明确:第一,我的研究方向是民族考古学,因此必须运用考古、语言、体质、文献等资料和民族考古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复原和研究古代藏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5](P14)格勒按照梁所希望的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充分运用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以及民族学与语言学知识,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用民族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并发表的第一个代表作是《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属问题》(《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一文,在这项研究中格勒首次主持发掘甘孜州新龙县西北部谷日乡七座残墓的调查和抢救性挖掘,并撰写了相关的考古报告,并对这些墓葬的年代和族属进行了考证。
协同理论引入中国后,学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张刚(1997年)根据协同创新的路径不同,将协同分为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内部协同是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协同;外部协同是研究主体和外部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协同。陈光(2005年)根据研究主体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将外部协同细分为横向协同和纵向协同:横向协同是指同一大类产业中细分产业主体间的协同;纵向协同是指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主体之间的协同[8]。
这封信中所附的《屈家岭文化来龙去脉浅探》完全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考证苗族族源。在1986年2月5日在他给格勒的另一封信中也提到了苗族族源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其中关于苗瑶所属的民族系统,至今学术界仍有很大差距的不同看法。余与江应樑先生曾认为来自西北。余以为苗瑶文化与濮越向间无相同之处。一为佳山,一为习水;疑苗古与氐羌巴有关,远古时代新石器已徙江汉,屈家岭文化是其所创造者乎?迨后派生出瑶族,他们先后与濮越、羌彝系统族有密切关系,越、苗、瑶与彝、苗、瑶相融合,如都掌蛮便有越人的血统和文化成分,土家族亦有彝、越、苗的成分。此外,还在历史上与巴有关。当然还有些通过楚、越或直接与中原融合为汉人。此乃余一向存在之疑问,但未做深入研究。您所分之三大族系,是明确的,但苗瑶是否居于羌越之间的混合类型?适宜有所保留,暂不可归之于濮越系统之内,以其归于濮越,不如归于羌氐。仅布见,由您自行考虑处理,不可强随余见为要。”(1986年2月5日信件)
这封信当中所提到的“三大族系”就是格勒后来根据梁钊韬所倡导的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四结合”的研究方法写出的《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载《新华文摘》,1988年第3期)一文。在同一封信中,他随信寄来了《论“民族考古学”》一文,这是梁钊韬先生与张寿祺先生合写的一篇讨论“民族考古学”的论文,这篇文章被看作是“国内首次使用了这一学科之名,并对这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形成进行了论述”。[6]“另附来有有关民族考古一文,读后深悉大意与余相同。您整篇博士论文,遵循文化人类学、民族考古方向进行,已通篇体现了您的方法,似(无)在论文后作附录之必要。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是《民族考古》,而不是《民族考古学》。盖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便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1986年2月5日信件)
他在这封信中明确提到已经开始尝试和张寿祺先生合写论文提出“民族考古学”这一学科的概念,并意图深入讨论和发展这一概念。[5]在同一封信件中,他还提到了在《论“民族考古学”》一文发表后与容观夐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争论,同时提醒格勒作为自己的学生暂不要卷入这一争论:
梁钊韬对于自己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格勒寄予厚望,迫切地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学术衣钵留校任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早在1985年12月6日的信件中他就对格勒在专业上的发展做了极为周密的安排,认为格勒已经具备副教授的水平,尽快破格定为副教授:“关于您的职称,我已表示您目前已具备副教授的学术水平,即使按规定需要观察,也不需二年,尽快破格定为副教授。”(1985年12月6日信件)
领导干部在加班,下属就必须守在办公室,这在一些地方似乎成了“潜规则”。不可否认,领导干部开会、调研等可能挤占了办公时间,白天没做完的事情晚上加个班是正常的。加班过程中需要部属找一点资料、提供一些数据等也是应该的。但有些部属看到局长办公室的灯亮着,明明与己无关,却不敢离开办公室。即使在办公室玩手机、煲电话粥,也要保持加班的“姿态”,制造加班假象,其目的无非是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以辛勤工作的表现形式,赢得领导的关注和认可。这值得深思。
并意欲与格勒一起在三四个月后将有关这一场争论的所有文章看过以后合写一篇论文来表达关于“民族考古学”的观点:“故余意以为待三几个月后您把张、容等四篇文章看过,自有分晓,此时我同您一起写一篇文章发表(想见希望有一定分量)。”(1986年2月5日信件)
他在这些信中评价了当时学界有关民族考古学的一些学者,表达了除了林惠祥和冯汉骥先生作为文化人类学家能够在民族考古学的研究中名副其实外,对一些“历史学家”从未到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进行过实地调查的不以为然:“至于您在正文章内所提的学人,除林惠祥及冯汉骥两先生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家,并且身体力行,教过考古学、民族学课程及做过二者结合的研究著作外,其余一些‘历史学家’一生研究西北西藏史,但未到过新疆,一言片语,无济于事,有些(须看到)民族学考古学结合之重要,但他本身只从事其一,而不愿兼之,甚而客观上反对。此外,石兴邦先生确实受过一些的训练也重视二者结合,但解放以来毕竟是着重于考古实际工作了。故提那人,亦应严肃、宽事、求是。您以为如何?”(1986年2月5日信件)
实际上,梁先生对这一领域的长期关注以及对人才的培养,都促使了“民族考古学”这一学科领域的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从这个传统中得到重视的民族考古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重点研究方向。1992年中山大学的容观夐和乔晓勤两位先生出版了《民族考古学初论》一书,[7]周大鸣认为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成熟。[6]
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复建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教材的编写与“文化人类学教研室”的成立
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复建过程中,梁钊韬先生很早就在民族学人类学系列教材建设方面展开部署,《中国民族学概论》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部教材的编写也是他对专业发展规划的核心所在。尤其是《中国民族学概论》的写作及出版,解决了当时民族学人类学教学中的“教材荒”[8](P2)问题。早在1978年,梁钊韬先生就开始筹划《中国民族学概论》的写作:“余深感民族学人才有继续培养之必要,建议历史系和校领导,迅速恢复这个课程,并首先应以我国三十多年来民族调查研究的成就为讲授基础,培养我国民族研究人才,为建立我国民族学添砖加瓦,因而有编写《中国民族学概论》教材之举。”[8](P2)这部教材主要由梁钊韬先生的两个学生陈启新、杨鹤书编著,他们根据梁钊韬写成的《关于〈中国民族学〉教学内容的设想》作为征求意见稿,制定了编写提纲,并在1978年冬天在北京广泛征求了民族学界老、中年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领导的意见,回到广州后,由梁钊韬对提纲进行修订,印发全国各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广泛征求意见。1979年春,由陈启新、杨鹤书着手编写教材,经过半年的努力,编写出二十万字的《中国民族学概论初稿》,写成之后,梁钊韬又对全书进行了审定,在1985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专业教材非常有特色,它“主要是根据解放后国内民族学工作者的第一手社会调查报告及我们在1963年隆冬至1964年初夏在滇西民族考察材料编写的”。[8](P2)而且这部教材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等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整合了中国三十多年来学界所调查的第一手社会调查材料,这部教材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教材。编写的初稿在1979年秋天就开始出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历史专业、人类学系的民族学专业及考古学专业的课程中,在全国民族学界风头一时,“这门课程开了以后,国内兄弟院校(尤其民族院校)的教师和民族研究机关的同志纷纷来函要求交流教材”。[8](P2)后来,梁钊韬先生又亲自主编了人类学教材《文化人类学》一书。[9]“上月国家教委批准了我系博士点学科建设计划,要写一本《文化人类学》,我已写了大纲,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分工承担,共分七章,其中的一章‘文化区域结构与多重性发展’,希望您能结合博士论文去写。”(1985年11月4日信件)
在1985年11月4日的这封信中他提到了1985年10月国家教委对于中山大学博士点学科建设计划的批准,以及对于《文化人类学》写作的规划,这本人类学教材的大纲由梁先生亲自编写,在他所编写的大纲的基础上召集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以上的教师分工写作,共分七章。后来这本教材完成后也的确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和最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界所看重的专业参考书籍。虽然《文化人类学》的写作大纲在1985年底就已经编制完成,但实际上,直到1987年5月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成立以后,这本书的写作才作为主要任务提上日程,这些过程细节在他1987年5月15日写给格勒的信件中都有提道:“我们系已成立了‘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暂由我挂名主任,副主任为陈启新,所有硕士导师都是研究人员,目前主要工作是编写《文化人类学》这部书,暂不定编制,也不设办公室,待体制人类学方面发展成熟了,再成立一个体制人类学研究室,然后一起呈报国家教委申请成立人类学研究所(系一级的)……国家教委已正式批准我校成立人类学博物馆(系一级),目前人手大成问题。”(1987年5月15日信件)
对这个教研室的成立,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在书中也有所记载:“那一年年底,该系获准成立一个文化人类学教研室,进行人类学研究和著书工作,这个系的下属单位在次年春季正式成立。”[2](P14)从上面的书信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直到1987年5月,中山大学的体质人类学教研室仍然未能成立,但是梁钊韬先生已经对此有所深远打算。同时提到国家教委已正式批准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博物馆。而实际上“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收藏的近万件考古、民族文物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梁先生几十年来从事田野考察、考古发掘工作搜集来的”。[3]
再如他在1986年2月24日写给格勒的信中所提到的:“今天收到《考古》1986年第一期,内有《屈家岭文化来龙去脉浅探》一文,我认为颇有启发,请您参阅。古书记载‘左问庭右彭蠡’的江汉地区正是苗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活动地区,上承川东大溪文化,盛于京山屈家岭,后又融汇于龙山文化。整个过程与仰韶龙山有更大的关系,而与青莲岗等东南沿海地区文化,差距更大。上述意见供您参考。”(1986年2月24日信件)
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需从问题开始;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启发式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独立思考,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中国人类学的博士培养实践和学科传承
1981年底,梁钊韬先生成为中国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其时,中山大学为文化人类学博士设计的培养方案包括了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体质人类学。
(一)人类学博士培养实践
虽然在1983至1987年间梁钊韬先生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共带有四个博士,但是因为1987年12月梁钊韬先生就去世了,这也使得只有1983年入学的开山弟子格勒成为在梁先生指导下唯一完整完成人类学博士学业的学生。在1987年12月梁钊韬先生去世以后,直到黄淑聘先生在1992年获得博导资格,1993年在中山大学重新开始招收博士,从1986年到1993年这七年间中山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博士招生实际上是停止的。因此,梁钊韬对格勒的博士论文指导过程成为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学科博士学术研究指导难得的完整案例,也是最能体现梁钊韬先生对于民族学人类学专业体系人才培养思考的一个典范。
梁钊韬先生对格勒的培养完全按照他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四结合”的设想,以极高的标准,极为系统的训练试图培养合格的民族学人类学人才。正如格勒所回忆到的:“我考入中大人类学系后,首先经受了人类学各门课程的全面训练。所修课程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是一次高标准、严要求、极为系统的训练。”[1](P607)此外把自己家的藏书完全向格勒公开使用,并且提供书目,让他看书做笔记然后找出问题再与他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梁钊韬先生上课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着重运用:第一,提供书目,他家里面的所有书犹如我自己的书随时可以借阅,他叫我自己多看书,多做笔记,有问题再找他讨论。他说,有什么问题,找他。没问题就不找他。第二,主张上课讨论,不辩不明,有时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要讨论一个小时左右。一边翻书一边讨论,记忆深刻,收获很大。”[5](P81)
梁先生对格勒的培养严格按照自己思考的“民族考古学”学科方向进行,而格勒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也尽可能地遵循了梁钊韬先生对他在考古学上面严格的要求:“我为这篇论文花了不少心血,仅考古学报从解放以来的全看过,有关藏区考古资料一点一点积累达三大本。”[5](P86)他对格勒的博士论文的指导非常用心,他甚至不厌其烦地指导他怎么来写博士论文答辩时候需要准备的提要:
“请您按要求注意重点写800字。希实事求是写出您的创见。我认为:(1)您综合了人类学有关各方论述您论著的题目……是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2)以考古学和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论证了藏族是蒙古利亚种族,是中国人。(3)以考古学论证了藏族起源于卫藏,在历史发展中与羌族有密切的血统上和文化上的关系,而羌族则是中原华夏族(汉族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4)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内地后再传至西藏,与本地的本教结合而形成喇嘛教,它与印度佛教渊源有别……”(1985年12月6日信件)
“《前言》最后呈现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并非完全等同。我看后边应还有几句话才能结束。我认为二者既有关系但亦有区别,这样的认识有利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请您想想,可能会比我说得更好。我同意您这个《前言》,认为是开了个好‘头’。我读来也感动。一口气读了两遍。”(1985年12月6日信件)
眼镜、围巾、口罩等:如果在雨雪天出门锻炼,可以准备一个跑步眼镜,雨天避免雨水刺激看得清,雪天防止雪盲。脖子怕冷的话可以戴一个脖套式的围巾,不影响运动又能够保暖。如果对冷空气比较敏感,吸入过多会过敏或者导致上呼吸道问题等等,可以准备一个口罩,避免冷空气直接进入呼吸道。还有其他装备例如运动手环等可穿戴设备,就可以视个人情况而定了。
另外促使梁先生对格勒的研究特别上心的还有他始终如一的爱国心:
“我在美国旧金山参观一所博物馆的亚洲部分,竟把西藏文物摆在印度的陈列里,我十分恼火!!(已提出学术上的批评)……因为这是中国人类学对待外来野心的武器,也是捍卫祖国民族团结国家的统一的武器。”(1985年12月6日信件)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所言:“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终生都在为国家效力,没人会怀疑他号召中国人类学完全为中国人民服务时的诚心。”[2](P253)他对自己学生在研究中表现出的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爱国、爱民族的情怀予以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前天收到您十二月三日来信并附《前言》篇的稿子,阅后均感高兴。《前言》写的热情洋溢,学术性强,对前人所认识到的一点体会和尚未做到都综述(包括文献、考古、民族、体质、语言)过去。在方法论方向也充分发挥了文化人类学(并结合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优势,为建设我国文化人类学做了身体力行的开拓工作。也充分体现了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炽热爱国、爱藏族的研究目的和热情。”(1985年12月6日信件)
最后,总结本文基于二维结构稀疏信息的CFS ISAR成像方法主要处理过程如图3所示.其中调频步进信号的平动补偿方法可以参考文献[2],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再赘述.
整个系统的UI 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整个系统的外部引导UI,包括一些系统的基本配置和相关的参数调整、加载过度页面、暂停页面、保存页面等。另一个则是系统中提供给客户的介绍和提示消息,和提供个性化选择的相关调整页面,包括对家具的位置、配色、风格进行调整等页面。
“若论民族考古工作,您是80年代调查考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深入、牵涉学科最多的新秀。博士论文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1986年2月5日信件)
活性炭纤维具有大比表面积(1000~3000m2/g)和丰富的微孔,微孔体积占总孔体积的90%以上,其在空气中对有机气体的吸附能力比颗粒活性炭高几倍至几十倍,吸附速率快100~1000倍,同时耐酸、碱,耐高温,可再生循环使用,是近年来应用较多的一种吸附剂。
表2为不同施钾肥处理对甜玉米品质的影响,施用钾肥显著增加了甜玉米果实中硝酸盐、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的含量,与NP处理相比,增幅分别为 2.7%~29.9%、7.8%~21.5%和 11.0%~15.4%,等施钾量条件下,100%CF处理果实中硝酸盐含量高于其他施钾处理,增幅为 12.4%~26.4%。 30%OF+70%CF处理果实中可溶性糖含量略高于其他施钾处理,增幅为4.6%~12.8%。不同施钾处理果实中可溶性蛋白含量无明显差异。
“我认为您的博士论文在社会科学中,是站在国际(起码是)学术争论前缘的著作,堪称具有国际水平……您的论文已完成十万字(一半),章目和《前言》我都满意,有把握保证您的学术水平质量是高的,做了前人所未能做到的工作,发挥了我系‘四结合’的优势,加以您勤奋而又懂藏文就更加出色。”(1985年12月6日信件)
而这些他关注的研究点基本上都是考古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的结合点。
后来格勒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的第一部著作”。格勒2016年在跟笔者的口述史访谈中总结自己能够成功地完成博士研究的原因时也提到了梁钊韬先生所倡导的这种民族学、历史、文献、语言、考古综合研究的方法的重要性:“大概因为我实地田野考察一年半,时间长,收获大。论文新观点较多。运用调查资料多。再一个就是利用梁钊韬主张的运用民族学,历史、文献、语言、考古综合研究的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古代藏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5](P89)
图书浩如烟海,读者面临选择之困。《全国新书目》杂志携手全国出版单位,从海量的新书中精心挑选,向读者推荐出版人眼中的2018中国好书。
“我要求她:(1)请学校有思想准备,举行较隆重的答辩会,可能请北京、上海、云南的第一流的教授来当委员,准备接待费。”(1985年12月6日信件)
正如当时也参加了格勒博士答辩的顾定国所记载的梁钊韬精心选择了参加答辩委员会的高级学者,这些学者包含了来自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当时国内的顶尖学术力量:严学窘——著名的语言学家,武汉中南民族学院院长;李有义——中国社科院的民族学家;王辅仁——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系主任;江应樑——云南大学杰出的人类学家;曾昭璇——位于广州市另一隅的华南师范学院的地理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以及梁钊韬本人。[2](P14)格勒这本运用了梁钊韬所倡导的“四结合”的方法论最终写成的四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198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的确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梁先生甚至事无巨细的为自己学生的博士答辩会请中山大学教务处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和安排:
(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传承
梁钊韬先生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很注意留用那些优秀的学生补充师资,建设专业的人才梯队。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山大学人类学重建的过程中,“陈启新和杨鹤书是1981年前从北京调入中大历史系的民族学家,他俩都是梁教授以前的学生,考古学家李松生和语言学家庄益群也是梁教授的学生,他们自60年代初从中大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现在也调到新成立的系里”[2](P11~12)“被选出来担任系里重要的领导职务的也是梁教授以前的学生,两个副系主任,其中一个是李松生(主管教学),而另一个是容观夐,他是1942年梁先生教的第一届学生,他从北京调过来,负责系里的科研活动和学术资料的收集工作,以后几年里进入该系的教员似乎都与梁先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位是张寿祺,他是梁教授解放前的学生,可以说,到1984年为止,中大的人类学教员都是梁钊韬一手操办的)”[2](P11~12)
他对格勒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所做的实地调查的民族考古的调查工作极为满意,高度评价了自己学生的研究工作:
“年前,我与张寿祺先生合写的:《论‘民族考古学’》只不过作为一般合作,引起‘纯’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接受传统与训练。但容观夐先生速发两文(一见中大学报,一见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批评我们,我们当然要虚心接受,但其文章,似对《民族考古学》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学科有所误解,且论及一些问题,也有所失误。张先生已为文投中大学报(三月份出版)争鸣,另一文也投社会科学战线反驳。余因精神不够,置之度外。您作为我的学生,望亦持慎重态度,暂不卷入此中争论。”(1986年2月5日信件)
课堂规则制定了,但是学生个性迥异,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认真的遵守,这就要求教师要做好课堂监督,要预防和发现课堂中出现的一些纪律问题,教师要针对出现的纪律问题采取语言提示或目光的接触等方式提醒学生注意自己的行为。严格执行课堂规则,发挥规则的应有作用。
梁钊韬对于完全按照自己的学科发展思路培养的学生非常有信心,第一原则是中山大学要优先补充师资队伍,甚至提到希望格勒将来接替他的博士导师能够继续培养学科人才:
“中大培养您,希望你成大材,将来接我的博士导师。对中大来说,培养研究生有优先留用,补充师资队伍的权利,除非中央特别指定分配到那里,加之您自愿,那就没有办法了。”(1985年11月4日信件)
可198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调任格勒前往北京,打乱了梁先生原来的人才接班计划,他感到无限失落,提到自己“内心矛盾重重,失去一位合格的接班人”:
“接中央统战部多杰才旦同志的秘书黄华同志来函,现复印附上,阅后便知其详。余前向校长请示,并经同意留您在系任教,原希望您在系工作数年,待升为教授后,若中央调您,我们亦乐意为中央输送人才,并施展您为进一步巩固祖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作出贡献的宏愿。今党中央决定在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并由西藏自治区政府前任主席多杰才旦同志主持组建其事,自当有其重大的意义。多杰才旦同志需要您往京参加这个工作,我当顾全大局,服从中央对您毕业后的任用。未知您的意见如何?”(1986年4月2日信件)
在1986年4月2日的这封信中,梁钊韬已经跟中山大学校长请示,同意格勒留校,他本意欲格勒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数年后,将自己的职位与工作托付与他,尤其是博士生导师这一关键的专业职位。但是无奈接到中央统战部多杰才旦同志的秘书黄华的来函,这一年中央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需要调任格勒前往开创工作,梁钊韬先生希望格勒能够施展自己为进一步巩固祖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作出贡献的宏愿。随后两天,梁钊韬再次给格勒去信,仍然希望他能够慎重考虑自己的去向,希望格勒能考虑留校任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甚至谈到即使格勒去北京,中山大学仍然希望他能够两边兼职,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继续保持密切地联系:
“问于您是否毕业后到京工作问题,您仍须慎重考虑。学校是真心真意留您的,不须多此疑虑,主要是看您的意见,即使您去京,学校亦会提出条件的;‘两者兼任’,只是以那处为专职而已。学校不会让您今后与中大无关系的。在我来讲,已见致黄华同志函中所说,内心矛盾重重,失去一位合适接班人。在感情上更不用说了。”(1986年4月4日信件)
艺术作品往往带给人以美的享受,同理,具有艺术性的课堂提问也会为语文教学的开展增加美学特质,从而带给学生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具有艺术性的提问会增加语文课堂的美感,不仅为提问内容增加了科学性,同时也加强了问题之间的逻辑性,让学生了解语文教学中的核心任务。提问语言不仅具有上述的内在美,还具有以表达方式为主的外在美。语言使用上的简洁精练以及语句上的抑扬顿挫,无不为语言的使用增加了多样性的技巧,让学生感受到了语文学科中的张弛有度与自然韵律。
在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梁先生极为爱护自己的事业的接班人:“两年多来我处处为您的学业、名誉设想,想您树立自己的应有尊严和威信,使您为党为国家作出大贡献,我并无任何私心存在。”(1985年11月4日信件)
笔者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内心感动非常,感慨不已,他对自己的学生发自内心的着想和爱护让人泪目,对于学科发展继承者处于公心的爱护令人赞叹:“在过去两年多,我们相处都很好,我的意见您基本上都能接受。但我对您的鼓励、器重,希望避免产生副作用,使您‘骄傲’,当然您不是这样。”(1985年11月4日的信件)
格勒回忆到:“毕业后,他一定要把我留下来,安排得很好,我也愿意,但是考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刚成立,中央统战部干部局来了人,加上多杰才旦总干事诚恳邀请,最后决定还是为中国藏学做贡献可能好一点,所以就决定去北京。告别时导师抱着我眼泪都出来了,他不愿意我走,我走了没有一年吧,七八个月,他去世了。”[5](P87)格勒1986年毕业后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次年带领调查组去西藏调查,梁钊韬先生给他写信说:“望您到西藏后给我信,或到什么地方随便写几个字给我也好。”(1987年5月15日信件)笔者每读至此处都万分感慨。
格勒回忆与梁钊韬先生分别时的情景:“当时,梁教授伸开双臂紧紧拥抱着我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而奋斗。他期待着他所倡导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能在中国藏学研究的园地里首先开花结果,作出重大贡献,为此对我寄予厚望。”[1](P600)他在与格勒分别时完全是把他看做了自己事业的延续,希望格勒能够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而奋斗,期待自己所倡导的人类学方法在中国藏学研究的园地里开花结果,为国家和社会作出重大贡献:“我已过古稀之年,不能像中年时期亲力亲为的去搞文物馆了,相信现任领导班子总有办法的。我身体不很好,容易疲倦,这是衰老的必然现象,但愿你们的事业、贡献远远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得到的安慰!”(1987年5月15日信件)
The gate–drain capacity Cgd/L was calculated as below:
四、20世纪80年代中国本土语境中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复建的实践对当前学科发展的反思
从梁钊韬先生写给自己学生格勒的这11封信的具体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关注了“民族考古学”学科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民族学人类学教材的编写与“文化人类学教研室”的成立;博士培养实践和学科传承这三项焦点议题。这些在中国本土语境中民族学人类学学科20世纪80年代复建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议题,以及其形成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有重要的启发与反思。
不少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特别是深受外国功能学派影响的那一批,不大注重历史,对于这种作风,早在三十多年前,Freedman便提出批评,但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便开始注重历史的重要性。[10]今天我们阅读民族学人类学的大量论文会发现年轻的学者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热衷于用这些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社会,但这种对西方理论生产的背景和语境不能够深入了解,将之不加批判地当作全能的分析工具对今天中国社会和民族现实状况进行解释的这种取向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矮化和狭隘化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本身,查阅近十年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专业期刊,绝大部分研究内容只是在社会人类学这一个方向上用功,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民族学者所提出的阐释民族学,并没有把西方民族学带出困境。[11]这种狭窄化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取向对今天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是危险的,这些信件的内容提醒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学科复建时期所提倡的良好的学科传统在简单化和片面化,或者说没有有效继承这些具有胆略和眼光的学者对于学科长远而科学的规划,对我们文化中最有学科研究发言权的历史和考古的因素关注度明显欠缺和薄弱,而这却正是中国人类学自身的资源和特长之所在,也没有能够很好地运用好中国的文化历史资源来建设一个更有核心战斗力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丰富学科整体的知识和体系。
顾定国也观察到:“中国人类学家的理念取向我们看作是他们自己在看待人类学时十分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而历史在他们所阐述的人类学中的确也很重要,过去十年里中国人类学学科领域发生的很多事实只有放回到某些关键的地区类型或历史类型的框架中才能被理解。”[2](P3)“考古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三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理论上是相互贯通的,三者综合研究,得出规律性的理论,便是人类学的理论体系。”[4](P356)梁钊韬先生提出的“四结合”的方法论和“民族考古学”的体系对于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方法论“四结合”和“民族考古学”的重视可以让我们以补充现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足,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比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而要研究和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我们必须从复杂的社会形态入手,重视历史文献和考古学的作用,才能够对我们这种多文明社会进行有效的解读和认知。应该运用历史学方法、系谱学研究方法、考古文化地层方法、语言学的方法等,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化石”的理论,使其成为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内容。梁钊韬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建的理念取向和实践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学习和反思。
[参 考 文 献]
[1]格勒.格勒人类学、藏学论文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2]Gregory Eliyu Guldin.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M].M.E.Sharpe,Inc.1994.
[3]庄益群.博士生导师梁钊韬教授[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4]梁钊韬.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5]格勒,口述,梁艳,整理.格勒博士藏族人类学研究历程口述史(上)[J].中国藏学,2016(s1).
[6]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J].东南文化,2001(3).
[7]容观夐,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8]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中国民族学概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9]梁钊韬.文化人类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10]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11]杨圣敏.在方法论上超越西方民族学[N].人民日报,2018-04-02.
The Idea Ori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Liang Zhaotao in the Discipline Reconstruction 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Centered on the Eleven Letters by Liang Zhaotao to Dr.Gelek
LIANG Yan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610041,China)
Abstract:Centered on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of the eleven letters written by Mr.Liang Zhaotao,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Sun Yat—sen University,to Dr.Gelek,the first doctor whom Mr.Liang supervised,during the two years and one month from November 4,1985 to December 4,1987,this paper classifies,summarizes and analyses the contents of these letters,and studies on the practice and ideas of some key issues including Mr.Liang Zhaotao's conception of"ethnoarchaeology",textbook compilation 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doctoral training and academic inheritance of anthropology,etc..On this basis,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ocus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discipline reconstruction 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local context of China in the 1980s,and the inspiration and reflection that these practices and concepts bring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 as a discipline.
Key Words:Liang Zhaotao;ethnoarchaeology;local context of China;reconstruction 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2—0081—08
*收稿日期2018-10-10
基金项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00850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7M611968)。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张应强][责任校对 石彬筠]
[作者简介]梁 艳(1983~ ),女,甘肃兰州人,博士,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博士后,西南民族大学讲师。四川成都,邮编:610041。
标签:人类学论文; 民族学论文; 考古学论文; 中山大学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00850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7M611968)论文;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