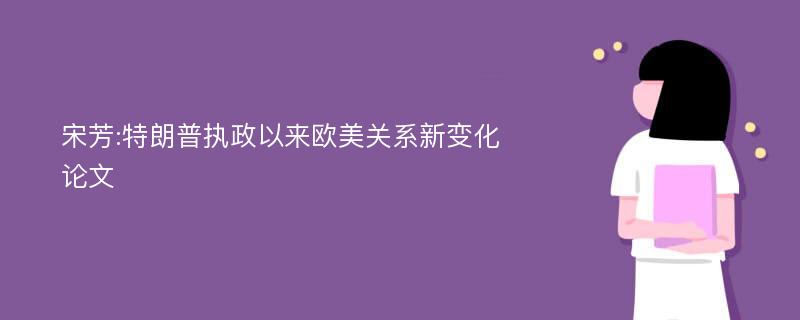
【内容提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方针,在一系列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对欧洲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外交举措,不仅提出“北约过时论”、质疑欧洲一体化,而且要求欧洲盟国为北约防务兑现更公平的预算份额,并在贸易问题上一再施压,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紧张,引起了世界舆论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欧美之间既存在原有结构性矛盾被激化的情况,又在新形势下产生新的矛盾,大体上反映了大西洋同盟内部围绕利益分配的博弈的新特征。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欧美合作的基础遭到一定的损害,欧盟及欧洲国家进一步意识到必须加强欧洲的自主性和“战略自治”,以应对美国对欧政策调整带来的各方面挑战,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欧美关系向着更为平衡合理的方向发展。应该说,欧洲自主性加强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它将有助于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然而,就中近期而言,大西洋同盟的既有基本结构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深层次共同利益的存在、欧洲防务能力的不足和安全上的“路径依赖”以及凝聚力的缺乏,决定了跨大西洋关系斗而不破的特征还将延续。
【关键词】欧美关系;特朗普政府;大西洋同盟;“战略自治”
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外交出现了不同于前届奥巴马政府的新格局。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更看重实际收益,即美国的国际行为的回报是否大于付出。因此上台后的特朗普刻意强调“美国优先”,退出多种双边和多边协定、国际条约,被认为是“向国际义务与合作宣战”。① Thomas G.Weiss,“The United Nation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Age of Trump,” Current History,Vol.117,Iss.795,January 2018,pp.10-15.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理念和外交还不仅针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且也毫不迟疑地对准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欧洲国家和欧盟,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在对美国的责任与负担进行“再平衡”的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对欧政策做出了重要调整,特朗普不仅提出“北约过时论”、质疑欧洲一体化,而且要求欧洲盟国为北约防务支付更公平的财政份额,更对欧盟和欧洲大国施加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要求它们对美开放市场和实现贸易平衡。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变化使正面临重重内部危机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欧盟难以适应,欧洲人感到欧洲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和平与安全,② Daniel S.Hamilton and Teija Tiilikainen,“Domestic Driver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Daniel S.Hamilton and Teija Tiilikainen,eds.,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nd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8,p.xii.以致欧洲领导人多次强调欧洲的命运必须掌握在欧洲人手中,欲推进欧洲的“战略自治”,欧美关系中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凸显。
特朗普上台后欧美之间分歧增大和关系紧张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对于当前的欧美关系态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着两种分析观点和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欧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大西洋同盟难以为继,如有学者力图通过事实和证据表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正在减弱甚至是破裂。里德沃尔(Marianne Riddervold)和纽瑟姆(Akasemi Newsome)认为,这是欧美在国际问题、国际制度和规范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等方面观点和立场日益分歧的结果。③ Marianne Riddervold and Akasemi Newsome,“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Crises and EU-US Rel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40,Iss.5,2018,pp.505-521.美国著名学者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等质疑特朗普的行为是否正在破坏整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跨大西洋关系本身处于危机状态。④ G.John Ikenberry,“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1,January 2018,pp.7-23; Gideon Rose,“Letting Go,” Foreign Affairs,Vol.97,Iss.2,March/April 2018,p.x; Fareed Zakaria,“FDR Started the Long Peace.Under Trump,It May Be Coming to an End,” Washington Post,26 Jaunary 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fdr-started-the-longpeace-under-trump -it-may-be-coming-to-an-end/2017/01/26/2f0835e2-e402-11e6-ba11-63c4b4fb5a63_story.html?utm_term=.a3b8e163ae02,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6日。夏皮罗(Jeremy Shapiro)和戈登(Philip H.Gordon)更是评论称“联盟已死”,认为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了致命打击,旧的联盟难以恢复。① Jeremy Shapiro and Philip H.Gordon,“How Trump Killed the Atlantic Alliance,” 5 March 2019,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how_trump_killed_the_atlantic_alliance,访问日期:2019年4月2日。俄罗斯《观点报》专栏作者彼得·阿科波夫认为,欧美分手已不可逆转,只 是“何时”“以何种形式”的问题。② Петр Акопов,«Европа обречена на союз с Китаем против США»,ВЗГЛЯД,27 марта 2019(彼得·阿科波夫:《欧洲注定要与中国结盟反对美国》,《观点报》,2019年3月27日),https://vz.ru/politics/2019/3/27/970174.html,访问日期:2019年4月16日。而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跨大西洋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厄尔代古伊(Rachid El Houdaigui)认为大西洋联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战略概念,现在只是需要围绕“北约分担责任”和集体防御达成新的战略共识。③ Rachid El Houdaigui,“The Atlantic Alliance: Between Revived Europeanism and Restless Atlanticism,” in The OCP Policy Center,Atlantic Currents: Overcoming the Choke Points,5th Edition of the Annual Report on Wider Atlantic Perspectives and Patterns,December 2018,pp.57-58.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台的政策报告称,欧美仍是不可替代的伙伴,“历史表明,将双方聚集在一起的问题的深度远远大于可能使它们分裂的问题的深度”。④ Patricia Lewis,Jacob Parakilas,et al.,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 Irreplaceable Partnership,Chatham House Report,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8.安德森(Jeffrey J.Anderson)认为“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策转变还只是表面的,尚未形成结构性变化”,并预计“它不会成功推翻美国70年来的外交政策共识”。⑤ Jeffrey J.Anderson,“Rancor and Resilience in the Atlantic Political Order: The Obama Year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ume 40,Iss.5,2018,pp.621-636.不少学者持和第二种观点相似的看法。⑥ Laetitia Langlois,“Trump,Brexit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The New Paradigms of the Trump Era,” Revue LISA / LISA e-journal,Vol.XVI,No.2,24 September 2018,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lisa/10235,访问日期:2019年3月3日; Ian Bond,“Has the Last Trump Sounded for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May 2018,p.15; Xenia Wickett,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onverging or Diverging? Chatham House Report,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8,p.30.
那么,特朗普上台后跨大西洋关系变得持续紧张甚至恶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特朗普欧洲政策冲击下,欧盟是否会更加独立自主?跨大西洋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欧美关系的变化和欧洲未来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嬗变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阐述特朗普上台后欧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表现和原因入手,进而重点分析欧洲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认知反应和政策调整,最后对特朗普持续施压背景下欧美关系可能的走向进行探讨。笔者认为,上述对欧美关系现状的两种认识都有其依据,特朗普对欧洲的抨击和施压确实给欧美关系带来了某些前所未见的新变化,但是,对欧美关系的结构性特点等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欧政策的调整及欧洲的反应尚不会导致近期欧美关系出现实质性转变。
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欧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及其原因
长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中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不对称的欧美权势结构及因其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平衡,但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方针和强硬的外交风格却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并产生了新的矛盾。相对于此前的同盟危机,从总体上来看,特朗普上台后欧美的矛盾和纷争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欧洲盟友甚至越来越质疑美国的领导力,并在是否保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派仍然支持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派则宁愿寻求新的地缘政治选择,以取代这个令人尴尬的同盟。① Younes Abouyoub,“A Perilous Legacy: From Trumping Multilateralism to the Demise of the U.S.Storytelling?” in the OCP Policy Center,Atlantic Currents: Overcoming the Choke Points,5th Edition of the Annual Report on Wider Atlantic Perspectives and Patterns,December 2018,p.51.
二战结束以来,大西洋同盟一直被欧洲视为其对外关系的基石,而美国也十分重视在欧洲的战略存在,有种形象的说法是,“美国一只脚站在美洲,而另一只脚站在欧洲”,没有欧洲,美国就等于失去了一只脚,无法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战后历届美国总统都将欧洲的安全和繁荣看作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他们一直对疏远欧洲、不顾欧洲人的感受持谨慎态度。相比之下,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既对自己在欧洲的传统角色不感兴趣,也无法履行自己的角色”。② Jeremy Shapiro,“Trump is a Mere Symptom of the Rot in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25 September 2017,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09/trump-is-a-mere-symptom-of-the-rot-in-thetransatlantic-community/,访问日期:2019年1月10日。特朗普只相信人造屏障(“筑墙”)和天然屏障(海洋)带给美国的安全感,所以他希望美国“能够而且应该置身事外,不去理会其他地区的问题”。特朗普的新政策虽然提高了美国的议价能力,但代价却可能是让整个大西洋同盟陷于危险境地。③ Jeremy Shapiro and Dina Pardijs,The Transatlantic Meaning of Donald Trump: A US-EU Power Audit,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September 2017,p.11.
忆从前,黑衣少年,红色镶边。手执随便,游荡世间。深邃眼眸中,尽现烟火人间。望天边,长发披肩,白衣若仙。指掠避尘,淡如止水。悠扬琴声间,尽悟世事难辨。
(一)原有矛盾的加深——利益分配的分歧加深
美欧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存在差别。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特朗普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来自中国的威胁。对美国来说,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联通了欧、亚、非,来自中国的挑战不断增加。同时,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崛起表明太平洋地缘战略重要性不断增强,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将其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亚太地区。相比之下,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很少有欧洲国家认同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看作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的观点。② Erik Brattberg and Etienne Soula,“Continental Drift?” Berlin Policy Journal,15 February 2018,https://berlinpolicyjournal.com/continental-drift-2/,访问日期:2019年3月20日。欧洲人虽然对于什么构成欧洲的最大安全威胁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一些南欧国家来说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而在东欧国家看来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威胁来说,“中国不是欧洲人的优先考虑”。③ Xenia Wickett,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onverging or Diverging? Chatham House Report,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8,p.30.在美国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时候,欧洲国家却纷纷加入了中国倡议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因为“欧洲一直在寻找适应中国崛起和亚洲增长的最佳方式”。④ Ulf Sverdrup and Bjørnar Sverdrup-Thygeson,“Transatlantic Troubles and the EU's Pivot toward Asia,” 18 July 2017,https://www.brinknews.com/transatlantic-troubles-and-the-eus-pivot-toward-asia/,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日。
1.特朗普对欧洲的经贸打压
欧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决定了欧盟加强自身军事和防务能力的需要。无论美国的战略重心是转移到了亚太地区还是美国本土,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不那么关心欧洲事务了。在丹尼尔·汉密尔顿(Daniel S.Hamilton)看来,从“马歇尔计划”开始,美国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欧洲大国”(European power),即全面参与欧洲事务,实际上它是欧洲建立的所有联盟中的一部分。而现在,美国不想继续做“欧洲大国”,而是要成为“在欧洲的大国”(a power in Europe),选择性地参与欧洲事务,这意味着分担和减轻负担。① David M.Herszenhorn,“Europe Thinks Trump ‘Hates Us',” Politico,15 July 2018,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trade-war-europe-diplomacy-nato-transatlantic-lamentations/,访问日期:2018年12月12日。特朗普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关注跨大西洋关系,并且在做决定时,他不会被传统、规范或需要尊重伙伴所困扰。② Laetitia Langlois,“Trump,Brexit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The New Paradigms of the Trump Era,” Revue LISA / LISA e-journal,Vol.XVI,No.2,24 September 2018,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lisa/10235,访问日期:2019年3月3日。
特朗普政府宣布从2018年6月1日起,向来自欧盟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惩罚性关税。这对于钢铝出口大国德、法、英等国来说,无疑是重创。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美国的这些单边关税是不合理的,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符。这纯粹是保护主义。”①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Commission Reacts to the US Restrictions on Steel and Aluminum Affecting the EU,31 May 2018,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4006_en.htm,访问日期:2019年1月3日。法国等国家希望“通过世贸组织对美国采取惩罚性措施”,而德国和其他国家“更愿意在冲突达到全面贸易战之前将其规模缩小”。② K.B.Kanat,“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Donald Trump,” Insight Turkey,Vol.20,No.3,Summer 2018,p.85. 2019年4月,特朗普更是加大了施压力度,宣称“欧盟对空客的补贴对美国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将对欧盟110 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③ Donald J.Trump,“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inds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Subsidies to Airbus has Adversely Impacted the United States,Which will now Put Tariffs on $11 Billion of EU Products! The EU has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S.on Trade for Many Years.It will Soon Stop!”Twitter,9 April 2019,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1115578769518018560?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115578769518018560&ref_url=https%3A%2F%2Fwww.rt.com%2Fbusiness%2F455973-tariffs-eu-products-trump%2F,访问日期:2019年4月14日。欧盟随后以美国对波音公司的补贴为理由宣布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00 亿美元的关税。
相比之下,欧盟是“多边主义”的信奉者和捍卫者。冷战后,欧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文化,即运用多边的和国际法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这种战略文化是基于欧洲人在军事选择方面的谨慎或犹豫,源于既“搭便车”又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怀疑、欧洲和平主义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欧盟民事/规范性力量的优越感。对欧洲国家来说,多边主义不仅预示着收益,而且能够遏制霸权国家。正如帕拉格·坎纳(Parag Khanna)所说,“欧盟越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就越能限制美国行使单边权力”。③ Parag Khanna,“The Era of Infrastructure Alliances,” in Mark Leonard,ed.,Connectivity Wars,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6,p.137.欧盟在多边体系中受益颇多,而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似乎是用双边协议取代多边主义。④ Maria Demertzis,André Sapir,and Guntram B.Wolff,“Europe in a New World Order,” Wirtschaftsdienst,Vol.98,No.13,2018,p.24.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单边退群的行为所体现的价值观与欧洲所坚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2.特朗普在同盟责任分担问题上的施压
几乎所有的同盟都会遇到“搭便车”的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支付超出其公平份额的费用。在大西洋同盟中,美国承担集体防务主要责任的传统由来已久,始于二战后美国的欧洲盟友经济重建时期。即使后来欧洲经济恢复且实力不断增强,美欧在北约军费开支中较大不平衡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在冷战期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试图让欧洲国家为北约付出更多,虽然都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但没有哪位总统真正去努力推动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因为其首要任务是保持同盟的团结以抵御苏联的威胁。① Michael Mandelbaum,“The New Containment: Handling Russia,China,and Iran,” Foreign Affairs,Vol.98,Iss.2,March/April 2019,pp.129-130.
实际上,早在2014年北约各国就达成共识,同意各国的军费开支应占到各自GDP 总额的2%,但目前欧洲盟国中只有个别国家达到了标准,北约的主要经费仍由美国承担。特朗普上台后对欧洲国家这种“搭便车”行为无法容忍,认为这样的经费分摊非常不合理,多次指责欧洲盟友“占美国便宜”,称欧洲国家接受北约安全保护,对北约的投入却太少。在2017年5月24日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批评欧洲领导人没有兑现对北约的开支承诺。虽然冷战结束后的前几任美国总统都表达了类似的抱怨,但特朗普以美国将不再继续对《北大西洋公约》作出承诺来威胁,将这种抱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朗普声称北约“过时了”,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为保护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国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他就让这些国家自己保护自己。② Elliott Abrams,“Trump the Traditionalist: A Surprisingly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Vol.96,Iss.4,July/August 2017,p.11.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大举投资于欧洲防务,而且在欧洲东部和南部邻国的稳定方面,美国的利益比欧盟低得多。③ Jeremy Shapiro and Dina Pardijs,The Transatlantic Meaning of Donald Trump: A US-EU Power Audit,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September 2017,p.10.因此,特朗普在北约财政责任分担问题上敢于向欧洲强硬施压的背后,似乎不仅是简单地对金钱投入后的回报的计算,更体现了其对欧洲安全的保护责任并不像其前任们那样的重视,乃至公开说出北约“过时”言论,这不能不引起欧洲人的忧虑。
(二)新矛盾的产生——特朗普的“另类”风格
1.单边主义退群——欧美价值观分歧加大
如果说在经贸和防务问题上的美欧矛盾是老生常谈,那么“单边主义退群”则是特朗普的“另类”作风,美国退出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不满。“唯利是图”的商人特质决定了特朗普的世界观“不是基于国际秩序的原则,而是更具交易性”。④ Laetitia Langlois,“Trump,Brexit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The New Paradigms of the Trump Era,” Revue LISA / LISA e-journal,Vol.XVI,No.2,24 September 2018,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lisa/10235,访问日期:2019年3月3日。如果某一多边机制与美国利益相悖,特朗普就选择单方面“退群”,正所谓“合则用,不合则弃”。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的单边行为表现为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保护主义”政策是指“在国际竞争中为国内产业提供不公平优势的政策”,始于15、16 世纪的重商主义(各国通过有利于本国经济的监管来增强自己的实力)时期,一直盛行到18 世纪。但是,随着贸易成为19 世纪和20 世纪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在英国的积极推动下,自由贸易成为基准和目标。① Alexander Tziamalis,“Explainer: What is Protectionism and could it Benefit the US Economy?” 1 March 2017,https://theconversation.com/explainer-what-is-protectionism-and-could-it-benefit-the-useconomy-73706,访问日期:2018年11月5日。二战后美国在建立、推动和监管国际贸易的机构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比如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等。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致力于国际机制创建与维护的大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退出了一系列多边条约和框架,回归“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最令欧洲国家担心的要数美国退出1987年与苏联签订的《中导条约》,因为任何中程导弹的重新部署都将使欧洲再次处于战略核武器的火力线上。② “The End of the INF Treaty? A Pillar of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at Risk,” 4 February 2019,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3175/EPRS_BRI(2019)633175_EN.pdf,访问日期:2019年3月5日。
美欧关税战的结果只会是双输,类似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当双方都选择自由贸易时,双方都可以获利;当一方进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实行贸易保护时,贸易保护方的收益可能会高于双方自由贸易的收益,而自由贸易方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但当双方都选择贸易保护时,双方都是负收益。如果单考虑一方,实行贸易保护增加关税是最优选择,能够通过禁止进口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但因为博弈是与另一方互动的过程,对于双方来说实行自由贸易才是最佳选择。然而,特朗普的眼中只有美国利益,所以选择了实行贸易保护增加关税。他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崇和对盟友利益的忽视给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伤害。
二是加强社区文明建设。制定社区居民公约,重塑乡村社会规范,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宿迁文明20条宣传、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将城市文明规范、文明理念、文明行为逐步向农村社区转移,推动城市和乡村文明对接,引导村民变市民。
特朗普与欧洲的矛盾还体现在质疑欧洲一体化的意义和前景。欧洲一体化是二战后欧洲人探索的复兴欧洲的道路,历任美国总统都支持欧洲一体化,并鼓励欧盟扩大进程。而特朗普却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结束了美国70年来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他还赞扬了试图瓦解欧盟的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者。① Ronald E.Powaski,Ideals,Interests,and U.S.Foreign Policy from George H.W.Bush to Donald Trump,Palgrave Macmillan,2019,p.239.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欧盟成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在贸易上打败美国”,所以,他不在乎欧盟是分开的还是在一起的。② “Full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Donald Trump,” The Times,16 January 2017,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full-transcript-of-interview-with-donald-trump-5d39sr09d,访问日期:2018年1月20日。特朗普将欧盟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英国脱欧对欧盟的打击将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并要求欧盟在经济上做出让步。③ Erik Brattberg and Nathaniel Rome,“The Limitations of the U.S.Approach to Brexit,” 28 November 2018,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8/11/28/limitations-of-u.s.-approach-to-brexitpub-77820,访问日期:2019年3月24日。此外,特朗普支持英国“硬脱欧”方案(即英国彻底脱离欧盟和欧洲单一市场),因为“硬脱欧”后伦敦将面临与华盛顿签署协议的压力,这将有利于美国贸易。④ Erik Brattberg,“What's in Store for Trump and Europe in 2019?” 8 January 2019,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1/08/what-s-in-store-for-trump-and-europe-in-2019-pub-78082,访问日期:2019年4月2日。这种对欧洲一体化的亵渎和对欧洲的漠不关心,触犯了欧盟的底线,着实伤了欧洲盟友的心。
在实证研究中,面板数据的常见处理方法有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这三种,而具体应该选择哪种模型,需要对数据进行检验后决定.首选运用F检验判断选择混合回归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通过stata14.0对样本数据的检验可知,F检验的结果为:F(15,143)=19.79,P>F=0.0000,故拒绝原假设,允许每个个体拥有自己的截距项,拒绝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其次运用豪斯曼检验判断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通过stata14.0对样本数据的检测得知,P>chi2=0,故拒绝截距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从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特朗普对英国脱欧的支持有着深层的原因。英国脱欧虽然体现的是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但很大程度上却反映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复苏,在大西洋彼岸与之遥相呼应的是特朗普对民粹主义的青睐。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对精英的敌视,因为外交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是精英活动。外交政策建制派倾向于美国在世界上扮演强有力的角色,⑤ Michael Mandelbaum,“The New Containment: Handling Russia,China,and Iran,” Foreign Affairs,Vol.98,Iss.2,March/April 2019,p.131.而民粹主义认为美国应该远离世界的纷扰,专注自身发展。同样在欧洲,一些欧盟领导人和民粹主义政客鼓吹,如果欧盟解体,他们的国家会变得更好。英国脱欧无疑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头增强的警示,它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场将重新定义政治范式的风潮。⑥ Laetitia Langlois,“Trump,Brexit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The New Paradigms of the Trump Era,” Revue LISA / LISA e-journal,Vol.XVI,No.2,24 September 2018,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lisa/10235,访问日期:2019年3月3日。
3.大国竞争中的欧美分歧
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大国竞争回归”,提出“要在竞争的世界中捍卫美国国家利益”,将中国和俄罗斯置于美国的对立面,称其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威胁美国的安全与繁荣”。① Donald J.Trump,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18 December 2017,p.27,p.3,p.25,p.2.
在冷战期间,虽然欧美大西洋同盟在防范苏联和西方安全等问题上能够保持一致,但是它们内部的分歧从来没有间断,合作与纷争并存成为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明显特征。冷战结束后,无论在军事安全还是在经贸等领域,欧美之间的利益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这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原有矛盾的延续与凸显。因此,冷战后的欧美关系本来就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冷战期间,即使面临着单一的来自苏联的威胁,西方联盟尚难保持团结,而如今面对多种威胁,建立和维持类似的联盟将更加困难。① Michael Mandelbaum,“The New Containment: Handling Russia,China,and Iran,” Foreign Affairs,Vol.98,Iss.2,March/April 2019,p.129.在维克特(Xenia Wickett)看来,“当外部威胁不再是主要利益时,就会出现分歧”。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欧洲常常难以维持密切关系,虽然“9·11”事件和恐怖主义威胁带来了更密切的合作,但“威胁的范围和处理威胁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比冷战几十年间更大的分歧”。② Xenia Wickett,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onverging or Diverging? Chatham House Report,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8,p.30.她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共同的威胁是凝聚同盟的重要因素,威胁的消失使得利益的分歧凸显。但实际上,无论是否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联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影响联盟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就像卡在联盟中的一根隐形的刺,当盟友的看法一致时,这根刺就像不存在一样不发挥作用,但当盟友发生分歧时,这根刺就会成为一把利剑。
4)自愈合效果最佳组合是微胶囊掺量 0.8%、微胶囊粒径200 μm、养护龄期7 d、养护温度40 ℃。
基于四川省38个气象站点 1970—2016年的气象数据,研究了在不同海拔 ET0及 4个最主要气象要素(相对湿度 RH、日平均温度 t、风速WS、日照时间S)的分布特征,采用敏感度分析以及贡献率分析不同海拔 ET0变化的驱动因素,得到结论如下:
面对俄罗斯,欧美之间也存在分歧。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任务是防止出现能挑战美国优势的地区霸权,俄罗斯实力的恢复以及在欧洲的强势使得美国加强了对俄罗斯遏制的力度,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更有美俄开始“新冷战”的说法。欧盟虽将俄罗斯看作威胁,但并不是非要将俄罗斯置于死地,相反,与一个安分的俄罗斯和平共存才是符合欧盟利益的选择,正如冯仲平所评价的那样,“与美国矮化、妖魔化俄,并高调反俄相比,欧洲国家倾向于就事论事”。⑤ 冯仲平:《当前欧美矛盾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5年第7 期,第7页。
欧洲对大国竞争的态度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欧洲的态度较为审慎,欧洲人对冷战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十分珍惜,不愿意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战场,更希望使用多边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另一方面欧洲希望利用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竞争,牵制中俄,甚至是它的盟友美国。欧盟与中俄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经济上相互依赖,欧盟与中国没有核心利益的冲突,与俄罗斯是邻居,担忧与俄彻底决裂带来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所以,欧盟不愿意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和俄罗斯。
二、欧洲的反应:掌握自己的命运势在必行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上台后的外交方针和欧洲政策导致了大西洋同盟关系的紧张和不确定性,欧洲人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显著下降。德国总理默克尔2019年5月中旬在德国媒体《南德意志报》上谈到对欧盟未来的担忧,称欧洲各国应联合起来应对来自中、美、俄等世界大国的竞争。人们对德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看作挑战并不感到奇怪,但德国总理将美国与中俄并列为欧洲的挑战者多少出人意料,以致多家西方媒体忽略了默克尔关于中俄的表态,而是强调,这表明欧洲已经不把美国当盟友了。① 青木:《默克尔:欧盟需应对美俄中挑战》,《环球时报》2019年5月17日,第2 版。确实,不少欧洲人持有同样的认识,即美国不仅在经济、政治上与欧洲渐行渐远,而且欧洲越来越不能完全依赖大西洋同盟(尤其是美国)来保护其安全利益,欧洲必须加强自主性,提高自身防务能力。因此,特朗普上台后,无论是默克尔总理、还是马克龙总统,都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欧洲的命运应该掌握在欧洲人自己的手中。正如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所说,“在这个危险的世界,5 亿欧洲人再也不能依靠3 亿美国人来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既需要投资于自身的安全,也需要转变思维。”② Mark Leonard,“The Era of 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 in Ulrike Esther Franke,Manuel Lafont Rapnouil and Susi Dennison,eds.,The New European Security Initiative,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December 2017,p.8.
不同金属离子对壳聚糖酶酶活性的影响,Mg2+,Ca2+,Zn2 +,Mn2+,K+,Na+和Cu2+等离子是该酶的激活剂,Fe2+,Hg2+,Co2+和Ag+等离子对该酶有强烈的抑制作用。例如Wang等在研究Serratia marcescens TKU011菌株中得出Mn2+,Cu2 +也可作为该酶的抑制剂。
(一)应对欧美合作的基础遭到损害、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特朗普对国际规则的挑战,促使欧盟加大力度维护和支持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同时,欧盟从内心不情愿与一个其领导人质疑欧洲一体化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美国政府进行合作。欧盟将尽可能使合作伙伴多样化,减少对一个反复无常的合作伙伴——美国——的依赖。③ Daniel S.Hamilton and Teija Tiilikainen,“Domestic Driver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Daniel S.Hamilton and Teija Tiilikainen,eds.,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nd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8,pp.xviii-xix.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德国与俄罗斯合作建设“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针对特朗普对该项目的敌视,默克尔在2019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美国摒弃冷战思维,并反问美国,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联邦德国甚至可以大量进口苏联的天然气,为何如今的德国却不能与俄罗斯进行天然气管道项目合作。① Angela Merkel,“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Dr.Angela Merkel on 16 February 2019 at the 55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16 Feb 2019,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bkin-en/news/speech-by-federal- chancellor-dr-angela-merkel-on-16-february-2019-at-the-55th-munich-security-conference-1582318,访问日期:2019年3月16日。
一些欧洲人担心,欧洲对美国采取独立甚至挑衅的立场,将会危及大西洋安全同盟关系。但特朗普的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其政府的安全政策主要反映了其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回报盟友的忠诚,这将破坏盟友间友好合作的基础。欧盟只有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战略行为体,并据此采取行动,才能更好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② Anthony Dworkin and Mark Leonard,Can Europe Save The World Order?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y 2018,pp.25-26.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华盛顿的变化使欧盟陷入困境”,“欧盟的解体并不会使成员国恢复某些虚构的、完全的主权,而会让它们真正和实际地依赖于超级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③ “‘United We Stand,Divided We Fall': Letter by President Donald Tusk to the 27 EU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n the Future of the EU Before the Malta Summit,” European Council,Press release,31 January 2017,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7/01/31/tusk-letter-futureeurope/,访问日期:2018年12月6日。他呼吁欧洲人团结起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保持欧盟整体影响力的同时,欧盟应具备扩大外交接触所需的灵活性和敏锐度,做好英国脱欧的准备,协调欧盟与英国的关系。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欧盟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合作,但需要对美国展现更独立的姿态,“应将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置于追随美国领导的传统本能之上”。④ Anthony Dworkin and Mark Leonard,Can Europe Save The World Order?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y 2018,p.25.
(二)加强自身军事和防务能力的需要
经贸关系一直是影响美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行为体互动越频繁,发生摩擦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经济上相互依赖的欧洲和美国难免发生经贸摩擦。20 世纪50年代末欧洲经济复苏后,欧洲就逐步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经济竞争对手,冷战结束以来美欧贸易纷争甚至贸易战也并不鲜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重新引发了围绕保护主义和全球化未来的激烈辩论,加剧了美欧同盟的矛盾。例如,德国是欧盟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欧洲经济的发动机,与美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然而,美国对德贸易逆差引起了特朗普的强烈不满,他说:“我们对德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加上他们在北约和军事上的支出远远低于应有水平。这对美国来说非常糟糕,这将会改变。”③ Donald J.Trump,“We have a MASSIVE Trade Deficit with Germany,plus they Pay FAR LESS than They should on NATO & Military.Very bad for U.S.This will Change,” Twitter,30 May 2017,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869503804307275776,访问日期:2018年12月5日。
⑶在地下害虫轻,玉米丝黑穗病发病也重(发病率大于5%)的地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干中直播地区,可选择2%的立克秀拌种剂或25%的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按种子质量的0.3~0.4%拌种;催芽坐水种的地区,可用“千斤顶”兑水进行种子催芽后,将种子晾干后,再用2%的立克秀按种子质量的0.3%拌种。
综上所述,对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目标性护理服务有助于降低手术风险事件发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预后康复效果,保持血糖稳定,应用效果良好。
而欧洲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对欧政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因为70年来欧洲已经习惯于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欧洲人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进行防务建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事家巴兹尔·里德尔·哈特爵士(Sir Basil Liddell Hart)曾试图推动英国军队的改革,他说:“处理公开的反对意见比原则上达成一致的专业意见要容易得多,后者掩盖了不愿将其付诸实践的根本原因。虽然明确的反对意见是可以克服的障碍,但犹豫不决的默认态度是对进展的不断破坏。”③ Basil H.Liddell Hart,The Memoirs of Captain Liddell Hart (Volume II),London: Cassel,1965,p.73.他的这番话恰好可以用来描述欧洲目前的防务状况,成员国对于国家主权和共同安全的权衡各有盘算,不明确反对共同防务的提案,却又不积极推动,往往导致各种防务计划流产。
2.特朗普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触犯了欧盟的底线
或许是特朗普对欧政策的转变点醒了欧洲人。为了提高欧洲的军事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战略自主权,2017年12月11日,欧盟理事会确定了《里斯本条约》所设想的“永久结构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简称PESCO)的框架性协议。该防务合作协议旨在共同发展防务能力、投资防务项目及提高军事实力,签署国有义务定期增加国防预算、投入一定比例资金开展防务技术研发并联合对外派遣军队。“永久结构性合作”一经提出就受到欧盟各成员国的热烈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在一个被认为是国家主权堡垒的政策领域——将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使欧盟能够保卫自己的安全。④ Kyriakos Revelas,“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Not a Panacea but an Important Step for Consolidating EU Security and Defence Cooperation,”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Formation Européenne,2016,p.1.斯文·比斯科(Sven Biscop)对其抱有极大的信心,因为与以往的协议不同,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拥有奖励机制,更重要的是,这项倡议是由成员国发起的,而不是欧盟。这些国家自己承担起了增强防务的责任,而没有受到美国、北约或欧盟的敦促。① Sven Biscop,“European Defence: Give PESCO a Chance,” Survival,Vol.60,No.3,June-July 2018,pp.162-164.但批评人士指出,软弱的承诺和官僚主义的增加不会带来任何附加值,反而有可能完全抹掉欧盟防务项目的信誉,这将又是一个雄心勃勃但终会令人失望的计划。② Nick Witney,“EU Defence Efforts Miss the Open Goal again,” in Ulrike Esther Franke,Manuel Lafont Rapnouil and Susi Dennison,eds.,The New European Security Initiative,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December 2017,pp.10-13.然而,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识到,在过去几年里,国内、地区和全球安全环境显著恶化,要求采取政治行动的压力从未像现在这么大。③ Kyriakos Revelas,“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Not a Panacea but an Important Step for Consolidating EU Security and Defence Cooperation,”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Formation Européenne,2016,p.1.
(三)英国脱欧背景下欧洲内部整合的需要
特朗普的欧洲政策和行为刺激了欧洲人寻求更大的自主权,但是摆脱美国的控制并不简单,当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如何应对英国脱欧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英国是欧盟中的军事和经济强国,英国的离开无疑是欧盟的巨大损失。欧洲人要思考的,一是在英国脱欧后,某种新的、自主性的欧洲安全结构应该如何建立,二是如何发展一种新的欧盟—英国安全伙伴关系,以增强欧洲的综合安全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④ Susi Dennison ed.,Keeping Europe Safe after Brexit,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018,p.2.
对于欧盟的未来,欧盟高层有两种不同的思考。由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相信,欧洲需要通过更多的一体化进程来实现其目标,这意味着应该赋予欧盟机构更多权力。但是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更多的中央集权将使民众反对欧盟,他说:“痴迷于当前和全面一体化的想法,没有注意到欧洲的普通民众不像他们的领导人那样对欧元抱有热情。”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批评“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的机构过于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公民失去了联系。”⑤ Charles Grant,“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EU,”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24 June 2016,https://www.cer.eu/insights/impact-brexit-eu,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2日。在欧盟考虑如何应对英国脱欧之际,图斯克的实用主义而不是容克的联邦主义理想占了上风。
英国脱欧将削弱欧盟内部那些支持进一步一体化的力量,并将使德国更具优势,而对德国更大主导地位的担忧是欧盟政界人士对英国脱欧前景如此恐惧的一个原因。近年来,法国的疲弱和英国的半独立地位,都使德国成为欧盟的主导国家。在欧元区危机、难民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德国在决定欧盟的反应。同时,德国也非常不希望英国退出欧盟,一方面德国将英国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欧盟预算缩减事业的盟友,英国的离开将使它缺少在欧盟中推行改革的有力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德国担心其他欧盟国家对德国主导地位的担忧会导致它们结成联盟反对德国。① Charles Grant,“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EU,”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24 June 2016,https://www.cer.eu/insights/impact-brexit-eu,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2日。
2018年6月25日,旨在建立一个独立于北约和欧盟的干预机制——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启动,九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爱沙尼亚、葡萄牙和英国)参与其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将英国包括在内的西欧俱乐部(爱沙尼亚除外),尽管英国脱欧,但英国仍是欧洲防务的重要伙伴,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不管英国脱欧与否,与英国的深层次战略关系将继续深化。”② Rachid El Houdaigui,“The Atlantic Alliance: Between Revived Europeanism and Restless Atlanticism,” in The OCP Policy Center,Atlantic Currents: Overcoming the Choke Points,5th Edition of the Annual Report on Wider Atlantic Perspectives and Patterns,December 2018,p.63.
三、欧美真的要分道扬镳吗?
欧洲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而当下这一话题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为欧洲人所重视。“物理上,大西洋正在以每年20 厘米的速度变宽;政治上,欧洲和美国面临着加速分裂的风险。”③ Ian Bond,“Has the Last Trump Sounded for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May 2018,p.10.但是,问题在于,目前跨大西洋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紧张状态会不会导致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种状况,即欧美之间出现分道扬镳的大变局,换言之,大西洋同盟关系会不会真的终结?抑或如另一些学者所言,尽管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欧美之间弥漫着对立情绪,但欧美关系并没有脱轨,跨大西洋盟友关系还将维持下去。本文认为,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的紧张关系和博弈乃是美欧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又一次强烈爆发之表现,是同盟内部围绕利益分配的又一次痛苦的争斗。不同于以往的欧美纷争,特朗普的欧洲外交具有明显的先发制人的主动性和粗鲁直接的强硬性特征,损害了欧洲人的利益和感情、恶化了欧美关系,促使后者更加坚定了“战略自主”的信念,并在争取更大自主权以致“掌握自己命运”的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而今后欧美关系的某种调整不可避免。然而,总体来看,跨大西洋关系的现有框架在一段时间内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欧美关系合作与纷争并存、合作大于纷争的状况还将延续下去。具体来看,这种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跨大西洋关系的权势结构难以改变。欧美的结构性矛盾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欧美实力对比的结构,这是一种稳定的客观物质因素,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欧洲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差距甚远,同时,虽然欧洲的经济总实力不弱,但欧盟各国实力差距太大。德国是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历史原因,军事实力不强;法国和英国有一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缺乏活力;意大利、西班牙和北欧几国都差不多;剩下的欧盟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都很弱。欧洲人不是没有人才和技术,而是缺乏意愿和野心。第二个是外交或战略层面的结构,即美主欧从的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构是可以改变的,欧洲人也一直努力试图改变对美从属地位,表现为欧洲对该结构的不满,不服从美国的指挥。比如20 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对美国的挑战(退出北约、建立独立核力量、缓和与苏东国家关系等),以及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老欧洲”的强硬态度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危机等。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大西洋同盟面对危机时会表露无疑。然而,历史上的这些挑战终究没有成功,欧洲人仍然生活在美国人的霸权阴影之下,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综合实力不敌美国,这不仅造成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而且当双方发生矛盾时,欧洲对美国霸权的抵制只能是有心无力,最后以铩羽告终。
设计意图: 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社会责任意识不可缺,通过对艾滋病在全球、全国发病的现状分析,使学生对艾滋病有更多的了解,同时认识到艾滋病发展的严峻形势和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在课堂上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责任意识,鼓励学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培养学生责任意识。
其次,欧洲内部的团结难以达成。从理论层面解释,国家在制衡霸权或威胁问题上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克服由于行为体过多而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集体行动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首次系统提出的。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一个存在共同利益的大集团中,除非存在独立的激励,或者外部强制力,否则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是不会自动采取行动以达到它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① 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从实践层面解释,第一,由于欧盟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其各部分的总和,欧盟动员大量资源的能力取决于成员国在具体问题上协调政策的能力。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欧盟的动员往往是困难的,因为不同的欧盟成员国有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优先项。例如,面对特朗普对欧洲的挑战,德国等“老欧洲”强调“要加强欧洲的韧性和团结”,而波兰等“新欧洲”的反应是“接受新的政治现实机遇,并加强与美国的双边伙伴关系”。① Piotr Buras and Josef Janning,Divided at the Centre: Germany,Poland,and the Troubles of the Trump Era,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December,2018,p.1.第二,欧盟并非军事同盟,虽然欧盟确实有一定的能力推动其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但各个主权国家对自身军事力量的调配拥有决定权,而一直以来,它们自身安全防务主要依赖北约的集体防务体系,欧洲人也并不想增加军费开支,所以欧盟不具备与美国硬碰硬的能力。第三,欧盟缺乏一个可以在国际危机中担起责任的明确的领导国。即使德国和法国有意愿担负起领导欧盟的重任,但在涉及成员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没有国家会服从其他国家的领导,故而导致共同政策的流产。
再次,欧洲在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上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欧洲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关于欧洲的“战略自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后大西洋主义者”(Post-Atlanticists)认为,“战略自治”是必要的,因为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该理念在法国尤其流行。“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cists)则担心欧洲“战略自治”将加剧美国脱离欧洲,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欧洲自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继续依赖美国。② Hans Kundnani,“The Necessity and Impossibility of ‘Strategic Autonomy',” 10 January 2018,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http://www.gmfus.org/blog/2018/01/10/necessity-andimpossibility-strategic-autonomy,访问日期:2019年1月20日。但现实是,正如库德纳尼(Hans Kudnani)和普格里林(Jana Puglierin)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的“战略自治”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③ Hans Kundnani and Jana Puglierin,“Atlanticist and ‘Post-Atlanticist' Wishful Thinking,”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3 January 2018,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atlanticistand- post-atlanticist-wishful-thinking,访问日期:2019年3月16日。这正是欧洲人在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例如,中东、北非地区对欧洲的安全至关重要,欧盟在其2016年全球战略中也提出要加强在欧洲相邻地区的“韧性”,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甚至主导,欧洲是很难单独在该地区有所作为的。
程凤萍介绍,80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坐飞机的,能够坐飞机的一般都是领导干部或者改革开放初期最先富裕起来的人,那时候乘机还需要开介绍信。那时的飞机也很小,她执飞的机型是安—24,容纳乘客48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水箱、没有烤箱,也不配餐,就是登机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纪念品和一盒饮料,纪念品是一个有飞机标志的钥匙扣或者是一把折扇,饮料是纸盒装的冬瓜茶,那时算是非常高档的饮品了。”程凤萍说:“那时在飞机上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服务工作,旅客上机后都在睡觉,一直到降落。”
最后,欧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共同利益,美国也需要维护跨大西洋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维护霸权需要欧洲的支持,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崛起的问题上,美国需拉上欧洲盟友一起应对全球和地缘政治的挑战,一个强大的大西洋同盟能够为美国在与中俄竞争中取得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伊肯伯里早就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必须加强与欧洲以及其他盟友的团结,才能真正维护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① 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 /Feb 2008,p.34.二是美国和欧盟仍然是彼此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二者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维系大西洋同盟的纽带。三是美国的建制派和主流社会对美欧关系的基本认知没有改变,支持美国维持与欧洲的传统政经合作和安全同盟,这表现在美国国会对加强北约的压倒性的支持。② Von Naz Durakoglu,“Don't Let Late-night Tweets Distract You,” 16 February 2019,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sicherheitskonferenz/trump-and-nato-don-t-let-late-night-tweets-distractyou-16037832.html,访问日期:2019年3月28日。其实跨大西洋关系是一种持久的战略关系,很难因为某一任总统的言辞作风而发生根本性转变。对美国来说,即使是特朗普执政,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欧洲这个重要的战略盟友,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欧洲始终没有、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成为美国的大国战略竞争对手。前美国国务院欧洲及欧亚事务局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A.Wess Mitchell)曾这样谈到欧美关系:“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我们都找到了走到一起的方法”,原因很简单,“在价值观、利益、贸易和安全方面,团结我们的力量远远大于分裂我们的力量”。③ A.Wess Mitchell,“Remarks at Carnegie Europe,” 21 June 2018,https://www.state.gov/p/eur/rls/rm/2018/283432.htm,访问日期:2019年2月24日。
尽管促成大西洋同盟成立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针对欧洲的强硬而不友好的言论,但大西洋同盟仍未解体,跨大西洋关系的纽带仍然具有韧性。然而,它的变化还是清晰可见的。按照拉希德·厄尔代古伊(Rachid El Houdaigui)的分析,“这场游戏在复兴的欧洲主义和躁动不安的大西洋主义之间展开”,“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和以它为基础建立的欧洲秩序(欧盟、北约)现在似乎正在失去动力。”这种局面是由三个相互独立的因素(按影响力排序:特朗普效应、欧洲主义的复兴以及欧盟、北约之外的制度安排的扩张)共同推动的,这三个过程最终将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新的格局。④ Rachid El Houdaigui,“The Atlantic Alliance: Between Revived Europeanism and Restless Atlanticism,” in The OCP Policy Center,Atlantic Currents: Overcoming the Choke Points,5th Edition of the Annual Report on Wider Atlantic Perspectives and Patterns,December 2018,p.65.这种新的格局可以称作是“后西方世界”(Post-Western World)——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逐渐脱去“国际警察”的制服,在多边机制中越来越后撤;欧盟努力迈向战略自治,将变得更强大、更自主;同时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崛起带来了一系列反映其经济能力的制度安排。下一个问题在于,大西洋两岸将如何适应这种“新的格局”。
结语
在当今世界中,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和走向十分重要,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强硬的政策无疑是导致其上台后欧美关系紧张的主要变量,在欧洲人看来,昔日“仁慈”的霸主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已经变得明哲保身和自私自利了。这是否会使美国“重新伟大”还有待观察,因为领导者的影响力不仅需要自身实力的维护和增强,更需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接受和支持,遑论欧洲这样的盟友了。在特朗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欧洲痛感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一方面,跨大西洋关系中也确实存在着如责任分担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看来,他们的总统对欧洲的一些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另一方面,欧美双方共同利益迄今仍是主要的,而欧洲的实力不足和凝聚力的缺乏又决定了欧美外交关系的斗而不破,甚至欧洲最终不得不又一次屈从美国的要求。因此,今天欧美关系某种程度上的恶化,看上去就如同戴高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法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公开反对美国那样,乃是同盟内部围绕利益分配的又一次复杂的博弈。不过,不同于上两次,这次是特朗普向欧洲的主动发难,既涉及双方长期缠斗、关乎美国人钱袋子的老问题,又踩到了长期以来美国对欧战略的红线。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是为了后者而对前者并不很较真,现在却是既不谨慎维护后者,又对前者抓住不放,因而不得不让人对其意涵多加思考:随着长期的矛盾累积和欧洲实力的不断增长,跨大西洋关系是否真的逐渐发展到了实质性变化前的某个节点?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笔者并不认为当今欧美关系已经或将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显然欧洲自主性加强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这将有助于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
针对纸病检测系统中多纸张缺陷提取的实时性要求,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块思想的多纸张缺陷一次提取算法。算法结合包围盒和连通域标记的特点,采用“先分块、后合并”的思想,在实时数据流处理的分支中完成纸张缺陷目标的检测,并以包围盒的形式给出位置坐标,从而准确地提取出常见各类纸张缺陷区域。与目前常用的缺陷区域标记算法相比较,该算法具有以下优势:①可以针对不同场合缺陷的出现概率以及检测精度,灵活控制分块的数量,从而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②占用硬件资源少,且算法结构简单,易于硬件的并行实现;③运行速度块,在本文实验测试环境下,该算法的运行时间仅仅为其他算法的1/100,有效地保证了纸病检测系统的实时性要求。
【作者简介】宋芳,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4 级博士研究生;洪邮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 邮编:210023)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5.004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9)05-052-19
【收稿日期:2019-05-23】
【责任编辑:程多闻】
标签:欧洲论文; 美国论文; 欧盟论文; 关系论文; 北约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论文; 《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论文;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