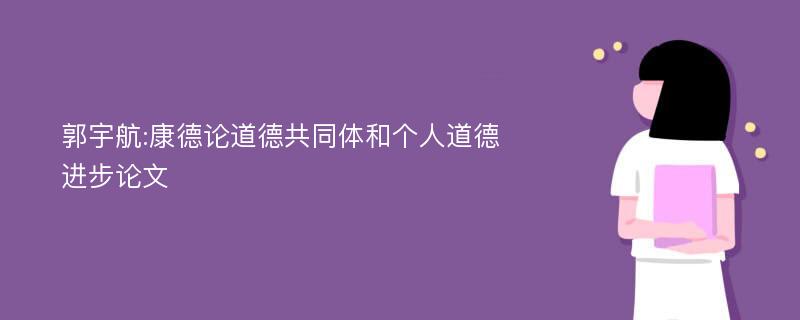
摘要: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康德将理想道德社会共同体论述为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目的保持一致。当代学者批评康德理想道德共同体的概念忽视了对个人道德发展的考察。因此,将试图重新审视在整个康德体系中的共同体概念,指出康德在道德、美学和政治著作中寻找并做出共同体同个人道德进步协调发展的论述。康德运用语言学方法阐述个体如何在共同体中相互作用,个体逐渐具备道德素养,愿意遵守与他人目的和准则相一致的准则。康德对道德和宗教关系的系统论述,指明了一条趋近实现理想道德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道德共同体;康德;道德进步;道德目的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康德对理想道德社会共同体做出了最早的批判性描述,社会共同体作为一种代理人系统,目的是与社会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目的保持一致。康德将道德代理人按照责任内在动机(即尊重道德法则)行事的理想王国称之为“目的王国”。[1]4:433道德法来源于人的自身目的,但康德似乎没有解释为何代理人之间会产生同样的责任观念的内在动机。类似于之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模糊阐述,[2]A810同样地,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似乎仅给出这种内在动机或者责任的不完全解释,即目的王国要求所有人都要尊重道德律,这种普遍遵守不会被胁迫。[1]4:438然而,这个道德人类共同体或目的王国究竟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困扰了康德,他试图在以后的道德、美学和政治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做出论述。
康德的共同体概念遇到的根本难题在于,他提出各种形式的道德发展不能被外部(其他代理人)强迫,因为这会违反他的自我概念: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明确阐述,迫使代理人“自由地”设定她所“意志”到的目的,这样的说法自相矛盾。[1]386-387康德似乎希望代理人独自改进自己,既然如此,共同体在理想代理人的发展中是否还有作用,或是仅仅作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目标?
根据以上问题,本文将阐述康德确实认同共同体包含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发展。具体来说,个人的道德进步将把实现道德共同体(目的王国)作为目的,反过来,道德共同体的目的是道德实践,其中包含了个人发展。康德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提出共同体的形式以及具有的道德价值,康德的共同体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即强调个人受到道德发展的“驱使”。虽然“驱使”只适用于个人自由的外部使用,但不违反个人自主发展和行动,如何解释这种“道德驱使”成为理解康德哲学的关键。
本文提出:康德通过语言学的手段来阐述个体在共同体中相互作用,使自己逐渐形成道德素养,愿意遵守与他人目的和准则相一致的准则。这是康德绝对律令中目的王国公式表述的目的观,我认为康德采取的语言学方法对道德宗教的系统论述,作为趋近实现理想道德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迪奥斯认为对康德政治和道德哲学体系的研究绕不开语言学背景。迪奥斯称康德希望“政治应将道德作为目的,因为政治不能对自身进行反思”。[3]239他引用了康德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引语,理想的道德愿望共同体产生于个人意志不可能的实际合作。[4]对此,康德将“道德共同体”或“看不见的教会”视为一种个人意志相互间合作的共同体,能够促进人类道德发展。康德的引语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辞,它反对宗教共同体(看得见的教会)鼓吹提高个人修养和‘尊重道德法则’的言论,它们仅仅是强迫(不考虑个人自主)个人行为的手段。
对康德的维护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在狭义上提出康德认同道德共同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具体阐述道德共同体如何能够促进个人发展。具体可以分为四部分:(1)康德引入道德共同体是为了解决“驱使问题”,“驱使问题”给人带来一种无望感,它产生于一方面人自主希望实现目的,而另一方面引入这种目的(道德进步)或许只是徒劳。(2)康德交流性策略更强调宗教共同体成员是否能够进行认真沟通。宗教信仰似乎不允许自由主义秩序,宗教面对争论(“驱使问题”)将如何发挥积极的组成性作用,即强制性的个人道德改善。(3)本文将试图找出康德道德共同体同个人之间的联系,积极的共同体作为道德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最终康德没有说这种共同体实际上起到这种作用。(4)康德论证道德共同体的意义是基于理性说服,即尊重道德宗教下的公民理性沟通。
一 为何引入道德共同体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第51节“道德学说”中,康德通过“道德教理问答”(moralischer Katechism)讨论教导道德的有效性。这种由教师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以学生已经给出并将详细记住的答案结束)对学生理解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将(学生的)普通理性开发出来”[1]6:479。这种教学技巧出自对教师话语的真实性的认可(这是经过学生的同意而回答的)。这种道德教理问答不同于宗教教义,康德坚持认为德性(道德)教义先于宗教教义,[1]6:478道德必须先于宗教。因为,如果宗教先于道德,那么将导致宗教信仰被滥用,后者通过恐惧或承诺来操纵参与者,而不是帮助人民产生自由同意的概念和判断。具体来说,康德道德宗教观表现在以下方面:
目的王国公式表达了康德绝对命令的目的概念,以及理想主体如何作为自身目的体系的一部分。因此,目的王国公式中的目的王国似乎是自由行动者的理想道德目的。[1]4:462-463康德认为,实现这一目的不需要任何条件,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代理人遵照自己的准则产生的共同(道德)行为,康德似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早已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目的?[2]A810/B838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论中(Rechtslehre),康德认为先产生公民国家,它确保个人的外部自由成为和谐的整体。强制性法律(Zuangsgesetze)确保代理人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1]6:237康德称之为“法则”(Recht)或“普遍正义原则”[1]6:230。政治条例规定人去遵守法律而享有权利,而道德目的则是人自由地将其作为自身目的和动机。那么,问题在于,如果外部(政治)条例本身不足,那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从外部自由状态(Recht)发展到愿意履行责任理念的代理人系统之一本身(“目的王国”公式中的目的)?
考虑到农地是否转出是家庭层面的联合决策,因此实证部分也将着重考察同属一个层面相应非农就业时间的成员群体差异,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这里便产生了“驱使问题”,道德改善的情况似乎行不通,如果人没有积极的事情可以做,这种无望感将会产生。一方面人自主希望实现目的,而另一方面人这种目的(道德进步)或许只是徒劳。为了摆脱这种无望感,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引入道德共同体。
2.道德共同体成员考虑个人准则时,应将尊重道德法则至于自爱之上。具体来说,人类必须做的是他们实际上可以做的事情,除了尊重道德法则的个人道德行为,还可形成“有形教会”(sichtbare Kirche),普遍教会或“无形教会”(unichtbare Kirche)。[4]6:48这里,无形教会作为一个理想的道德共同体,不考虑成员的国家,种族或社会地位,它包含所有代理人,因为他们自由意志形成道德法则。康德将无形教会形容为道德神圣的所有正直人类联合的纯粹理念,有形教会(sichtbare Kirche)是向普遍教会或隐形教会(unsichtbare Kirche)发展的必经阶段。康德将无形教会作为一个理想目的(普遍教会),并在历史发展中,通过有形教会达到这个目的。康德认为教会的真正标志是它的普遍性(根据每个成员的道德法则自由)及其法则内容,有形教会的核心是法权(政治,外在和谐理想状态的个人自我管理自己理想的状态),而无形教会的核心则是从自己内在出发的道德发展。
二 康德道德共同体试图解决的问题
本文论述了一般共同体所遇到的问题在于,它不依赖于个人选择,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缺乏互动,这使得康德引入道德共同体的概念。本节将重新审视康德试图解决的问题,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宣称必须创建一个道德共同体来对抗人性邪恶来源,这种性恶主要表现在社会环境中,对于社会问题,必须采取社会解决方案。[4]6:94康德提出的道德共同体有以下两种特征:
一般来说,罗西关注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如何沟通。然而,需要澄清有形教会对道德发展的积极作用。罗西认为道德共同体的社会权威是消极的,认为这种权威不是强制性的,但没有考虑道德共同体的社会权威的积极作用(即公民反对什么,公民支持什么?)。事实上,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论述了四种宗教共同体的意义和用途,由此可以确定康德并非认为有形教会不合理。康德批判有形教会在于作为一种共同体,它没有提供在非强制性下,关于促进个人进步的进一步解释,我相信康德更加侧重于将无形教会作为理想,来促进个人道德发展。有形教会是一个重要机构,它可以作为自由公共话语的场所,它朝着目的王国公式和无形教会所指定的理想道德共同体迈进,罗西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观察组35例患者中显效21例、有效11例,治疗总有效率为91.4%, 而对照组35例患者中显效11例、有效15例,治疗总有效率为74.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仪式由李光红副校长主持,济南大学社科处处长张守凤宣读了“关于成立济南大学旅游文化创意研究院”的批示文件,刘建波院长分别与山东兵圣孙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山东旅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和共同发起成立山东研学旅行研究中心的协议。
三 共同体秩序以及社会权威
如何解释教会中的个人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能够相互沟通?我认为应围绕共同体秩序展开论述。在论述之前,先论述当今学者对康德教会概念的指责。罗西提出,因为无形教会既培养人的道德目标,也将人视作自身权威。他认为康德对真正教会的描述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外部秩序中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和制度的说明,而仅仅体现政治权威的那些国家可以下令,以便使得国家内的人民为道德进步而努力”[5]81。罗西称,康德给出的是消极的标准,只是将道德界与任何强制性共同体区分开。道德共同体的作用是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公共关系,以便维护我们自由的社会条件,并且承担相互责任。[5]63-86道德共同体体现了理性的社会权威,但这种权威是非强制性。社会权威的强制形式是通过旨在创造外部权利状态的法定措施而适用的理性力量。这是外部权利状态非强制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权威的非强制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依赖于公民之间的自由沟通。
罗西认为,社会权威依靠自由沟通。道德共同体其成员相互承认对方为负责任的公民,这种关系在其话语实践中显而易见。罗西称,康德关注到了这种理性之间的辩论,因此,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康德所说的“批判性说服”进行真理辩论[4]73。它要求所有各方都理解或者试图理解自己和他人立场,未经沟通就不能对某件事情做出评价,沟通是产生“共同行动的基础”[5]73-74。这里,论证和沟通是行动的基础,但它自身并不是一项行动,[5]81为了表明对其他参与者自由的“尊重”,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满足批判性说服的要求[5]77。
健全反腐败法律体系,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惩治和防范结合的有机整体,既要凸显程序规定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性,又要强调其实体规定的惩戒性、约束性、激励性和保障性;既要包含从严治标、惩防并举的措施,又要注重预防、着力治本的内容;既要适合中国依法反腐的现实需求,又要能与国际反腐法律接轨,从而从源头上夯实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厚实法制基础。
1.道德共同体成员产生道德动机应优先于激情的动机。康德表述到,一种道德共同体产生自对其成员开始进行道德教育,以使得成员拥有一种倾向性(Gesinnung),这种倾向将道德律视为同激情的动机相比更加优先的动机,[4]6:48这种道德动机将在社交中妨碍恶性竞争或不良沟通。道德动机建立在“本身(德性)的特殊统一原则”上,它是对“邪恶的制止和对人类的善的促进,一个永久可持续的社会,通过完全联合力量来对抗邪恶并维护道德”[4]6:94。
随着建筑工程给排水施工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在给排水施工过程中的问题被解决,但也有很多新的问题涌现出来。给排水管道材料的种类越来越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施工的难度。通过细致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许多施工中出现问题的共性。要提升设计单位对给排水施工设计的重视度,根据项目工程的特点,选取最为适合的工程施工材料。设计方应该提出一个综合设计方法,使施工方在施工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有据可依,通过优秀的设计,完美的工艺,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建筑给排水系统的问题。
1.预设上帝存在。这里,上帝存在是从自身出发,而非被外在力量所操纵。康德严厉地警告任何类型的操纵,比如在《所谓‘在思考中定向’》中,他既反对那些阻碍人身体自由发展的行为,也反对任何强迫他人做有违良心的行为,这些行为完全无视人的自由和理性同意。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物理上强制于人,更是人们对“自己信仰对所危险思想的焦虑和恐惧”的病态动机[4]8:145。
四 道德先于宗教
康德在政治著作中考察共同体,较多的是强调共同体的构成形式。对康德来说,共同体应该有更高的发展阶段(即道德阶段),唯有在那里,人与人之间构成共同体的目的。道德共同体具有双重价值,这既有利于组成更好的共同体,也体现共同体本身作为道德行动的目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用自治公式将普遍法则公式和人类自然目的公式推广到自身。自治的公式可以被理解为过渡到“目的王国公式”所表明的理想道德共同体,即个人意志的准则与可能的目的王国准则相协调,它有助于引导以自治公式为代表的个体自治的系统使用,成为一个和谐的代理共同体。[1]4:433
康德对真正教会的解读实则是为了提出促进尊重个人的论点,并使其赞同真理。这样的话语概念维护了康德道德动机的内在性,因为个人积极地认识对方所说的事实的真相。这在他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中的道德教育的讨论中也很明显,这是教育和培养人类代理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道德问答的必要性。在德性论(Tugendslehre)中,康德认为决疑问题(casuisticalische Fragen)是道德问答和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6:483-84共同体有利于话语的宣传:道德法则越多,我们同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上帝就越亲密[4]6:151,制度和目的最大限度地将代理人协调一致(目的王国公式)。在道德教理问答中,康德将注意力转向道德教育学的实例。这些实例的使用不是用来教导任何既定的道德规则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规则是交易的与“不可思议”的内部状态通过非谨慎的道德法则来判断),而是“证明它确实有可能按照义务行事”[1]6:480。这个“证据不是严格意义上,因为我们总会欺骗自己”[1]4:407,或被别人欺骗。康德注意到,最好的宗教是基督教,耶稣在基督教里代表了“不变的纯粹意志”[4]6:64。
2.理性讨论。尽管我们没有实际的自由(没有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动机),但我们可以基于理性来讨论,例如这些道德概念,包括尊严,以及支持它们不朽的推论。所有人都可以就某种问题展开讨论,但这种讨论并不是随意的,它是基于人们自己获得其整体概念和观念的理性可接受性的依据。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康德似乎赞成“自然宗教”而不是“有学问的宗教”,或至少坚持认为“一个宗教可以是自然的,人类只靠理性自身可以而且应该到达它”[4]6:155。宗教共同体可以建立在启示之上,但这只能是一个历史的“怪癖”,从根本上它仅加速了理性发现的信息传递。没有“学问的”神职人员可以“欺骗”人去相信这样的信仰,没有任何奇迹可以让人们意识到某些经文的真理。
4.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可以讨论道德和论辩义务。康德认为,一个“历史”特定信仰的不能被如此崇高或具体化,以至于它们会超越理性。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有形教会之外(尽管所有都包含在无形教会的理想目标中); 相反,人们敬畏耶稣的话并不是因为外在任意神圣权威,而是因为他的纯粹的意志使他能够“真正地说出自己,仿佛善良的理想被展现在他身上”[4]6:65-66。通过对实例的说明,康德试图呈现人类代理中已经存在的目的来源。像耶稣这样的象征以及宗教叙事本身,作为道德改善的说服性话语是有用的。后来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宣称宗教提供的生动描述旨在表明改善人类的道德行为是一个艰难的事实,即人对美德的追求总是一场斗争,无论何时,这种努力不会完全停止。[1]6:409
在康德看来,共同体不会把代理人当作纯粹的机器或自然物体来操纵,它不同于权利状态(政治/民事联盟)的强制性约束。在1793年康德的秋季讲座中,他解释到,他人的“强迫”导致代理人自由自主的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说服”。康德解释到,当另一个人有权利履行他的责任时,也就是说,义务给代理人留下印象的道德规则,通过他的理性创造了先前在他内部的概念,而且仅仅是按照道德规律发展自我。[6]27
因此,相互代理人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容易受到道德共同体(有形教会)的影响,这里强调的是人通过内部动机进行道德培养,共同体内的人的内在力量并不是消极的,它与所有人的目的兼容。正如帕玛奎斯特指出,宗教不是通过言语欺骗人,“神职人员的真正任务是培养一种教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所有成员都可以自由探索任何信仰和行为,而出于责任的个人最有可能促进这种道德目标”[7]235。有形教会的真正权威来自于理性。它包含了罗西对道德共同体分析中提到的理性可接受性概念,借鉴理性力量,源于个人对自己理性力量所产生动机和概念的认可。有形教会的实质活动回答了什么类型的力量是非强制性的,个人的道德进步就是人的目的。
康德清楚地指出,为实现这一目的,宗教需要发挥作用。伍德写到,道德共同体的重要性,并强调其在克服不良社会环境的作用。[8]489-511他的基本论点如下:(1)人天生邪恶(例如,一旦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条件,他们倾向于降低道德法则)。其中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我们的“非社会的社交性”,人的自然秉赋终究是要充分地发展在时间过程中,它还必须有现实的手段将它实现出来。这种现实的手段是以人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然状态需要与其他人的对抗来融入社会。(2)共同体可以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自己与他人组成一个试图打击邪恶根源的共同体。(3)使自己完全与他人隔离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对他人的完全/不完全的责任。(4)因此,我们有义务去形成特定类型的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或有形教会)。[9]503-505
伍德的论点排除了基于道德理性的个人独立。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清楚孤立自己是否违背了对他人的义务。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者和指导者,这个“不友好的社交性与他人联系在一起”[9]8:20,因此,非社会的社交性是一种紧张,它的价值在于如何将自己从霸权社会状态中分离出来,后者从人的邪恶根源中产生。相反,《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提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人的真正选择,是道德共同体。因为它能够在“冷峻的敌意”下开始打破个人的态度,从而保证自己能够理解对方的意图(而不仅仅是自爱)。道德共同体牵涉到内在,这个内在根据自己的实践理性。
如果说康德的有形教会具有调节作用和组成性质,它表明了康德道德共同体概念的第一个维度,从更深地讲,是要挖掘道德共同体如何起到程序性的或调节性作用。因此,罗西正确理解了康德道德共同体中的说服含义,这里的说服是一种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物理/感性压迫的话语形式,坚持所有参与者都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在康德的人类学中,人们不应从相互自由行动出发来欺骗或者操纵他人,而应给予他们相同的尊严如同给予自己一样。然而,这种对自我的特权,也被认为是对自我的爱,会在我们的非社会交往中出现自我孤立的倾向。
表5所示试验3组血清中IgG和IgM含量显著高于试验1组(P<0.05),其他三组血清中IgG和IgM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四组血清中IgA的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总体来看,试验2、3、4组血清中IgG、IgM和IgA含量都高于试验1组。
五 理性交流互动——道德共同体 难题的解决
从根本上,康德如何解决道德共同体难题?康德的回答将是,从“听众”中获得动力,通过维护其成员的自由和促进这种自由,来维护并发展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是由理性交流互动构成,而理性交流互动是自由地对真理或谬误进行批判,而不是根据任何权威不可捉摸的法令。
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通过类比家庭的运作来暗示这种非强制性。宗教与家庭相似,其中“在一个无形的道德父亲之下,圣子知道父亲的意志,但与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血缘关系”,他的父亲就是人人都爱戴并拥护的公认权威,以及由理性给出的对道德律的爱。理性说服的动机来自我们自己的属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理性与感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即便它并不总存在于我们所处的共同体中,它无时无刻加强了我们自己和他人价值的联系。正如盖耶指出,康德在开始和结尾都强调一点,即个人认识到他们的自治能力与尊严的联系。[10]28这是人类作为共同体成员(即自由的先天权利/能力)认知的标准要素,也是康德整个哲学体系所追求的目标-维护和促进人类自由。这最后的表述可能导致一些关键的问题,有形教会是否需要朝着理想形式的(良性)共同体迈进?伍德指出,“任何判断的合理有效性都取决于其普遍的传播能力”[9]202,这似乎排除了纯粹的共同体强制性使用,但似乎并不需要将“神学包袱”强加给“有形教会”的成员。正如伍德指出,康德努力避免强迫式或家长式的极端宗教崇拜,以及极端的“个人宗教”运动。[9]214
2.2经过治疗后,介入组治愈患者54例,治愈率为100%;输卵管通畅患者48例,通畅率为88.88%;腹腔镜组治愈患者54例,治愈率为100%,输卵管通畅患者49例,通畅率为90.74%,组间各项指标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我相信,善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会促进人际关系,也会见贤思齐,促使自我不断成长,会让自我的幸福指数提升。这也是我真切关注学生真实内心的一种方式。
然而,关键问题是,如果完全离开宗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达到道德共同体(目的王国)?我相信康德将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两方面的。首先,对宗教的信仰是由道德所预设,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预设上帝存在那样。其次,人类理性似乎需要对实践理性及其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合理的表述,而这可以通过宗教学和经文解释的方式提供。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抽象的普世信仰似乎并不能指导“普遍的信念”,因为“人类需要最高的概念-理性的同时,人类的感官还应对理性和经验进行确认”[4]6:109。这感性的天赋不应将康德的道德共同体中的堕落和道德进步视为“绝对正确”,因为这是康德希望从任何向社会理想类型迈进的共同体中排除操纵和胁迫因素。某种宗教共同体确实在历史上起到开化人心的作用,但不应过分强调其历史信仰。
六 结 语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康德将理想社会共同体论述为社会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目的保持一致。康德道德共同体的核心是个人的道德发展不能被外部(其他代理人)强迫,因为这会违反他的自我概念,当代学者批评康德对这种强迫或者自主概念模糊,因此道德共同体似乎与个人道德发展很难共存。为此,从整个康德体系前后逻辑出发来审视康德共同体概念,指出康德在道德,美学和政治著作中努力做出道德共同体难题的回应,个体在共同体中相互作用,使自己逐渐具备道德素养,愿意遵守与他人目的和准则相一致的准则,道德共同体与个人道德发展并不相悖。
参 考 文 献
[1] Kant,Immanuel.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Translated by M.J.Gregor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Translated by P.Guyer and A.Woo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Dostal, Robert J. Kant and Rhetoric[J]. Philosophy & Rhetoric, 1980(13).
[4] Kant, Immanuel.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M]. Translated by T. Greene and H.Hudson New York: Harper Row, 1960.
[5] Rossi,The Social Authority of Reason:The ‘True Church’ as the Locus for Moral Progress[J]. 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nt Congress, 2013(3).
[6] Kant, Immanuel. Lectures on Ethics[M]. Translated by Louis Infield. New York: Harper, 1963.
[7] Stephen R. Palmquist. Kant’s Critical Religion[M].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2000.
[8] Wood, Allen. Religion, Ethic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Evil[J]. Faith and Philosophy,2000(17).
[9] Louden, R., & Kuehn, M. (Eds.).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 Guyer, P. The Value of Reason and the Value of Freedom[J]. Ethics, 1998(1).
OnKant’sMoralCommunityandPersonalMoralProgress
GUO Yuh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In “TheFoundationofMoralMetaphysics”, Kant regards the ideal moral social community as the consistency in the social community.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criticize the concept of Kant for the negligenc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 moral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in the entire Kantian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at Kant seeks out and develop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moral,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writings. Kant explains through linguistic means that individual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community and gradually become morally literate. They are willing to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and norms of others. Kant’s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moral and religious relationships indicates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achieving an ideal moral community.
Keywords:moral community; Kant; moral progress; moral purpose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81(2019)01-0045-06
收稿日期:2018-08-02
作者简介:郭宇航(1986-),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康德哲学和西方哲学。
标签:康德论文; 共同体论文; 道德论文; 目的论文; 教会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十七~十九世纪前期哲学论文;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北京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