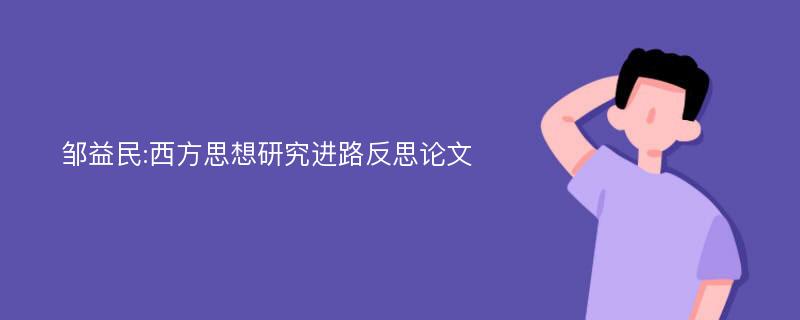
内容提要:国内外学界都对既有思想或者说思想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进行了争论,对思想研究自身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就晚近对西方思想的研究而言,国内主要形成了以甘阳、刘小枫为代表的“以西方观西方”和以邓正来为代表的“以中国观西方”两种进路。但这两种进路都没能阐明我们研究西方思想时所具有的多重意义结构。作者提出我们应当进行一种具有多维度的自主的西方思想研究。
关键词:以西方观西方 以中国观西方 意义结构
在当今的学术发展中,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既有思想或者说思想史的研究在哲学、历史、法律、政治等各领域都是成就斐然,而尤为可贵的是,思想研究者们也对自己的研究本身进行了反思。如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与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就思想研究方法展开的论战。(1)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60页。就国内思想界而言,应当说对思想本身的反思是一个传统,自孔子提出:“述而不作”(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页。,到当代汪晖、葛兆光等人的中国思想史反思及写作,(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这个传统尽管有种种变化、甚至断裂,但一直存在。这里更加值得反思的是自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思想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思想的研究与书写。当然,这种反思自我们开始学习西方时就存在,如清末洋务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是直到现在依然未停息的中西之争的一部分。但本文并非意在考察所有的争论与反思,而是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及其方法。
本文结合当代学界对西方思想研究的两种典型进路,即以甘阳、刘小枫为代表的进路和以邓正来为代表的进路,进行反思,以促进我们对西学的进一步反思和把握。
读杨鹏笔下的故事,你会发现,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承载的是一个小小男孩的英雄梦想。杨鹏自己也说,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影子,他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角落,永远是一个14岁的孩子,从未长大。
一、当代两种典型的西方思想研究进路:“以西方观西方”“以中国观西方”
甘阳、刘小枫在“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中,针对自近现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主张摒弃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4)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33.html。这种病夫的心态和头脑,要以健康的心态“重新阅读西方”(5)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33.html。。这种重新阅读西方的关键在于“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6)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33.html。,厘清西方文明中的差异、冲突、矛盾等。换言之,摒弃那种大而化之的概念化、标签式的做法,寻求“原汁原味的”、弄清西学的源流,并形成广阔的视野。这种进路可称之为“以西方观西方”。甘阳和刘小枫积极把这种主张贯穿于他们的学术实践,在继上世纪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文集后,在新世纪初至今仍主编“西学源流”等丛书,产生了广泛和巨大的影响。
邓正来则指出了学界对西方思想的四项误识和做法:其一,认为西方思想有自身固有的问题脉络,阅读或研究时应以这种脉络为前提或判准;其二,认为存在着整体的西方思想,以大而化之的“印象式”方法言说西方思想;其三,认为在不同的西方论者那里存在永恒的相同问题,从而以笼统的方式谈论一般“问题”;其四,认为能够不带前见、可以不以中国作为思想根据对西方进行阅读。(7)邓正来:《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57、657、660、590页。针对这些情况,邓正来提出“回归经典、个别阅读”(8)邓正来:《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57、657、660、590页。的方法,主张对西方思想采取“语境化的‘个殊化’研究方式。其中,依凭每个西方论者的文本,关注其知识生产的特定时空,尤其是严格遵循其知识增量的具体内在逻辑或理论脉络,乃是这种方式或方法的关键所在”(9)邓正来:《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57、657、660、590页。。在这种方式中,“中国”作为思想根据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潜在地作为阅读者或研究者的前见而引导对西方思想的把握。这种进路可称之为“以中国观西方”。邓正来同样以这种方式进行相关的学术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述甘阳、刘小枫以及邓正来的进路,是当代两种典型的对待西方思想的进路,可看作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思想研究方法的代表。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探讨人类行动所具有意义的复杂性时,引用吉伯特·赖尔对挤眼睛这个日常行动的描述,(12)Gilbert Ryle,CollectedPapers,Volume2:CollectedEssays 1929-1968,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p.494-510.指出赖尔精到地论述了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1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7页。,即我们常见的眨巴眼睛这种行为,可能具有眨眼、挤眼、假挤眼、模仿、模仿之练习这些丰富的含义,而到底具有何种含义,则依赖于具体语境下的情形。借用格尔茨的总结,我们可以说,人类思想本身一经产生即具有“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或者说多重的意义结构,而思想研究的任务即在于探究这种具有层级性的或多重的意义结构,或者说探究意义结构的多重的不同层面。而不同论者,如西方的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或国内的甘阳、刘小枫与邓正来,只是强调了多重意义结构中的一重或多层意义结构中的一层。那么,思想本身的意义结构到底有几重呢,或者说几层呢?
2018年4月至5月,我们在辽宁省盘锦市二界沟进行了中国对虾的苗种繁育,共培育出体长1~1.5cm的对虾苗种1.5亿尾。繁育技术总结如下:
其次,思想作为文化观念,固然有自己的独立形式与风格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传统,但思想表达的内容都是对某物的言说,这些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方面,而这些方面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除了上述能够从文字的用法及逻辑等角度对思想进行探究外,也可从特定历史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方面对思想进行研究,形成从这些方面出发的历史社会分析方法。如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从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变化;而福柯所倡导的谱系学以及知识考古学则是把马克思等所倡导的方法从经济基础的分析扩展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历史方面的分析,分析这些因素在特定时空下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这可归结为思想结构的第二重或第二层意义。
思想的多重意义结构表明,可采取多种方法对其进行探讨,因而只探究某一方面的意义结构并宣称自己的研究为唯一正确的说法,实在是管中窥豹。我们应当注意思想意义结构及对其研究的复杂性,尽量采取科学的方法对思想的多重含义进行揭示。即使对某种方法或某种结论比较偏爱,也不能认为自己所理解的意义就是唯一正确的、其余人的理解就一定是谬误。特别是那种以某某传人自居,觉得自己深得其神秘教诲的永恒精义,甚至拒绝讨论与批判,实在是本末倒置,不得要领,是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思维在现代思想领域的体现,值得警惕与批判。
二、西方思想研究中的多重意义结构
邓正来主张研究西方思想进路的关键在于从中国出发对西方思想文本进行语境化处理,以揭示出相关论说在知识传统或脉络中的知识增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突破那种只是“引进”和“复制”西方理论的做法,要求我们不能人云亦人,而是“必须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非反思性的盲目追随者,转变成反思性的、自主性的思想者”(10)邓正来:《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57、657、660、590页。。西方的思想与理论在邓正来那里只是观察与思考中国问题,进而建构中国自己主体性的一种可能的资源,而非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个殊化”研究方式正是在这种确立中国思想主体性进而确立起中国主体性语境下提出来的。它从中国出发观西方,既非病态亦非自大,而是力图对中国和西方都进行“个殊化”的情景式的真切理解。
首先,思想、尤其是以经典著作形式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是用文字以系统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思想的意义结构第一重或第一层,即在于文字的含义以及运用词法、句法、修辞、逻辑等在内的写作技艺对文字进行系统性运用与组合所生成的文本含义。需要指出的是,“写作技艺”这一用语由施特劳斯提出,(14)Leo Strauss,PersecutionandtheArtofWriting,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意在指出古代世界的思想家、哲人们为了避免显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招致政治迫害,而采用的隐微写作技巧。本文借用这一术语,不仅指施特劳斯的用法,更在一般意义上进行扩展,即泛指一切运用语词表达和呈现思想的方法、技巧。对于文字和文本的这种含义,我们首先能够借助于考古、考证、训诂等技术性方法考察文字的起源及其演变,从而能够揭示文字本身的含义;以文字本身的含义及变化为基础,再结合逻辑等写作技艺,我们可以探寻思想的字面和文本含义,或者说经典思想的表层含义;而结合思想历史传统中不同论者对文字或语词的运用等所形成的不同文本,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思想演变中的“永恒”问题以及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施特劳斯学派反对思想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进路,认为存在着亘古不变的先哲智慧,不同时代的思想只是对先哲所提永恒问题的不同回答,思想研究者的任务即在于运用各种解经法去拨开历史的迷雾,探究经典文本的精义,亦即那种至上的永恒智慧。(15)〔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洪涛译,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42页。甘、刘两位学者的主张,大体类似。他们的探究可归为这一层。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刑法和治安处罚法。如果犯罪,一般情况下已满七十五岁和任何情况下不满十八岁的人,是不能判死刑的,并且会被从轻或减轻处罚。例外的情况是已满七十五岁的老人以特别残忍的方法杀人,可以判处死刑。但“残忍”是个形容词,立法没有解释,不同的司法者评判的标准不同,对刺激的承受度不同,对同样的罪行是否“残忍”就会有不同的认知。从轻处理最典型的是治安处罚中的行政拘留,如果当事人不满十六岁或者七十岁以上,这个拘留是不执行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其实已经不能算“从轻”了,因为我们理解的从轻是降格处理,如从拘留降到罚款,从罚一千降到罚八百等,而“不执行”实质上相当于完全取消这个拘留处罚。
在这种进路中,我们的前见,即以“中国”为据,非但不是我们理解西方的枷锁与阻碍,反而是前提,是必不可少的与西方思想形成或明确、或潜在对话的抓手,是我们在西方思想面前坚定文化自信而不迷失自己的立足点。从中国出发观西方,也不意味着以“中国”为判准去切割“西方”,对西方思想进行断章取义,而是要在从中国所处特定时空下得出前见的前提下,理解西方在特定时空下形成思想及其传统的脉络和内在逻辑。
再次,尽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宏大的背景对思想观念的形成有影响,有时甚至是支配性的影响,但不管这种影响如何,它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思想者体现出来。思想的形成正如剑桥学派所主张的,是思想者在特定的语境中运用语言的行为。“文本即行动……理解过程要求我们复原作者行动所体现的意图。”(16)〔英〕昆廷·斯金纳:《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任军锋译,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由于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思想者的意图除了具有个人性之外,也具有社会性,即思想除了表达思想者个人的意图之外,还表达了有关群体的意图。这种意图不管是私人性的还是社会性的,都是相关个人或群体为了对付环境、克服外在环境对自己生活所造成的困厄的,用曼海姆的话来说,知识是“可以被某种具有生命的、处于某些生活条件下的存在加以支配的、用来对付各种生活情境的工具”(17)〔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这种看法表明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行动主义成分,即思想是思想者本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行动的体现,是他们行动的工具,或者说就是行动的一个方面或行动本身。正是这种行动主义成分,使得思想作为观念产生具体的历史效果或历史影响,突出体现在各种有关思想的历史事件中。这种作为意图的行动主义成分可看作思想具有的第三重或第三层意义结构。
总之,枳术宽中胶囊与埃索美拉唑联合治疗GERD具有较好的疗效,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炎症状态,安全性较好。
这表明思想本身的意义结构是多重或多层进而是复杂的。思想都是有感而发的,所谓“言之有物”即表明这一点,但这种有感而发首先都是由特定时空下个体所发、所言而形成的,所以个体的意图是出发点。其次,思想要引起共鸣必定不能仅是私人的,特别是要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个体有感,还必定表达了特定时空下相关群体生存与理想方面的重大关切,即要表达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重要情感、感觉、感悟、感想,换言之,要“文以载道”,这是根本。再者,思想不管是表达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感与道都要借助于媒介、以人们可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特别是经典作品,是借助于语言文字以符合语法、用法、修辞等相关的写作技艺要求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这些媒介以及语法、修辞等相关的写作技艺都是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都有自身的传承逻辑。个体与群体的感与道经过文字及相关写作技艺逻辑的升华,便具有了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意义;再经过人们以权力、文化、宗教、甚至经济等手段加以传承,变成了脱离所源发个体与群体及其所在时空的“永恒”经典,甚至成为后来者所膜拜的具有神秘性、神圣性的教义和圣典。所以,所谓经典、原典等体现出所谓的思想的“永恒”问题和精义,只是基于文字等媒介通过写作技艺传达的与特定时空相剥离的那一层含义,具有表面性,套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属于表层结构的含义。这些含义都包含在记载思想的文本中,重叠和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从而体现为思想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使思想一旦表达出来后,便成为不同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解释,甚至加以利用的对象。
思想研究是对思想本身的思想,是把思想作为具有一定客观性的物进行研究,套用剑桥学派的话说,思想是一种行动,具有行动意图,简要来说,研究者在复杂斑驳、异彩纷呈的各种思想中之所以选取某种或某类思想研究,是有自己的意图和旨趣的,这种意图与旨趣既具有个人性、也同样具有社会性与群体性。研究者不必讳言、也不必回避、更不必否认,不必假装或标榜进行所谓“科学的”“客观中立”的纯粹研究,从而自欺欺人;而是应当坦然承认,甚至是根据需要主动形成这种旨趣与意图,但也应当在研究中尽量克制自己的价值判断,用韦伯意义的“价值中立”(18)〔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方法论文集》,张旺山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481—538页。做到对相关思想的同情性理解,实现与论者的视域融合。当然,这里补充一点,如邓正来所言,通常是作为前见以隐微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甚至是在研究者根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三、多维度的自主的西方思想研究
以此观之,这与上文甘阳、刘小枫对待西方思想的进路有一致之处,即都要求我们抛弃那种以中国为病灶、以西方为药铺的病态心理,以自主的健康态度面对西方。然而,他们还是有差别的,即甘、刘两位所提的“惟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11)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这种进路,实际上受到邓正来的反对,是他所认为的误识西方的表现,即能够以为不带前见地按照西方自身理解西方,尽管他没有明确作这种归结。但显然,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进路是把握西方思想精义的最好方式,进而我们可以追问,西方思想到底有几种含义能供我们把握;或者进一步一般化,思想本身有几种含义供我们理解和探究?
笔者对思想多重意义结构的揭示,并不意味着否认邓正来的“个殊化”研究方式,毋宁看作是对那种大而化之的和“以西方观西方”的进路的进一步批判和对“个殊化”研究方式的补充和完善。综合观之,笔者认为,对待西方思想应当采取这样一种研究立场或进路:以中国为根据、从中国的语境出发,形成我们自己的前见或旨趣,然后在西方知识脉络与传统中选取与我们的前见或旨趣有共鸣的思想,揭示其在西方智识史与传统中的普遍意义和在其所出现历史语境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意义。这并非“以西方观西方”,并非“以中国为病灶、以西方为药铺”的病态心理和实践,也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以自觉自信的主体态度对西方以及我们自身的思想和处境进行深度把握。简言之,我们应当进行一种具有多维度的自主的西方思想研究。
这里再有必要补充强调一点的是对西方思想的自主态度,亦即一种自觉自信的主体态度。按照通常的说法,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影印,第19页。,在自那时开始的救亡图存危机中,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漫长过程。而甲午中日战争则导致传统中国世界观的解体,中国人开始彻底失去对自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从“器”到“道”等各层面的信心,(2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0—550页。当时学生师法西方,向西方学习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选择。“西化派”自然不用说,即使就保守的“西学中源说”“国粹派”等派别而言,表面上是热爱、保存、甚至发扬中国传统,认为西方有的那些先进的技艺和观念等源于我们中国,或者我们老祖宗其实早就有了,但如余英时所总结的,都以西方为标准对中国自身进行判断,要求中国人认同西方,“‘西方’永远是中国现代认同的核心部分;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能在民族的认同中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这种情况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改变”(21)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7页。。
这种认同西方的背后是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中国人一直没能找回或重建对中国的自信,即使相信中国能与西方做得一样好、甚至超越西方,也同样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以西方的标准为归宿,所以骨子里依然有由西方集体性侵略造成的自卑感,或者夹杂着怨恨、嫉妒、攀比等复杂情结。其实,如果简要回顾中国同世界、特别是同西方的交流史,不算同印度佛教交流的话,可发现,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很早的,大规模的学习最早可追溯到明末阶段,但那时的中国人丝毫不自卑,也不是完全盲目自大的,而是立足于自身的基础的自信。那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文化。“利玛窦采取了平等的手段传教,这对中国士大夫而言,是一次平等的对话机遇。这种方式被后来的‘康熙大帝’称作‘利玛窦规矩’。”(22)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647页。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士敞开胸怀,和传教士们平等地理性交流、探讨、辩论、学习,以取长补短。这种平等理性的交流对双方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与影响。但可惜的是,这种平等理性的交流,在随后的历史中异化为如上述的自我贬低式的“师法西方”,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改观。
2.2 重视人文基因传承,全力打造一支具有深厚人文知识功底和人文精神素养的教师、政工干部和辅导员队伍。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赢来了就世界游戏规则的创制和修订发言、影响世界命运的机会,有论者称之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23)高全喜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在这样的时刻,需要重建我们的自信,改变那种以西方为判准对我们自身进行评判的自卑的观念与实践,抵抗西方的包括文化在内的霸权,世界历史并没有终结,西方的历史从来都不是普遍历史;但我们也不需要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对西方与世界进行拒斥,更不需要以自大的君临天下的姿态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进行统治。我们要打破那种根深蒂固的大而化之的中西二分观,放眼整个世界,以上文所论多维度、自主的态度对包括西方思想在内的各个文明的思想进行探究,平等、理性地同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个文明进行交流,汲取各种有益成分,促进我们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丰富和发展,使包括我们在内的整个世界在丰富的多样性、多元性中以自信而又有尊严的方式存在。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9)03-0009-06
作者简介:邹益民,法学博士,河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河南开封 47500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法治建设中多元价值冲突解决机制研究”(14CFX003)、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法治思维中的公民权利质量保障研究”(2017BFX006)、河南大学科研种子基金(CX0000A40748)的阶段性成果;另:感谢刘鹏、杨松涛、杜启顺、张延祥、王勇、任瑞兴、汤沛丰和孙国东对本文的批评意见。
责任编辑:耿旭光
标签:思想论文; 中国论文; 进路论文; 自己的论文; 意义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法治建设中多元价值冲突解决机制研究”(14CFX003)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法治思维中的公民权利质量保障研究”(2017BFX006)河南大学科研种子基金(CX0000A40748)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河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论文; 河南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