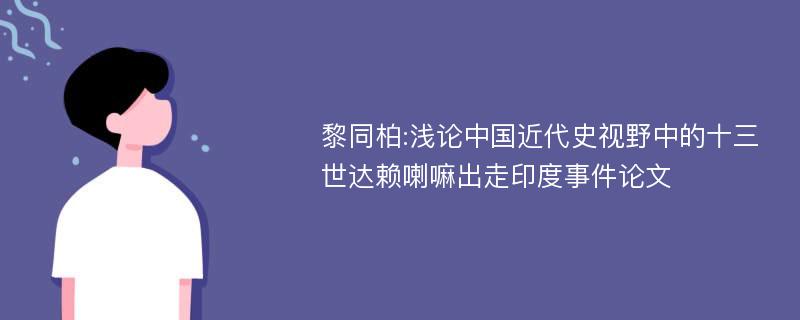
摘 要:1910年初,刚刚回到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逃往印度,此事件对西藏地区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评价此次事件的原因和性质,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把此次事件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下研究发现,清王朝的日益衰败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重要原因,而清末在西藏激进推行的“新政”则是其直接的导火索。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只是晚清各社会主体对于社会剧烈激荡做出的众多自发或自觉反应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1910年2月12日,因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而被迫离藏流亡祖国其他地方近六年之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刚回到拉萨,又因其与清朝政府及驻藏官员之间扑朔迷离的矛盾纠葛而出走英国殖民下的印度。此事件造成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再次被清朝政府褫夺,而他与昔日宿敌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种种事态对后期西藏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因为这一事件,成为一些学者笔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铁证”。其实,就西藏言西藏,或者用“放大镜”的效果来审视西藏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确实能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但也有可能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往往很难准确把握其全貌和本质。相反,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在清王朝加速衰败的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来观察就会发现,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其本质只是晚清社会风雨飘摇之中,众多社会主体做出的自发或自觉反应中的一个。
一、清王朝的日益衰败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重要原因
从鸦片战争前后直到1912年清王朝灭亡的近八十年时间里,封建专制社会的加速衰败是晚清社会发展中一个最明显的趋势。这里说的“衰”主要指社会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日益衰落,体现在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和腐朽,经济上的日益停滞和落后,社会结构上的等级僵化,文化结构上的迷信封闭,人民群众的贫困破产和整体发展趋势的沉沦垂死等方面。“败”则主要指在内外冲突中的不断失败,体现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以及应对国内革命和运动中的束手无策等方面。衰和败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底色。社会的衰败使早已暮气沉沉的封建王朝朝不保夕,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给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
清王朝的衰败在西藏地区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便是其引起的众多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首先,西藏地方的整体衰落相较祖国内地更加突出。在政治上,清王朝的腐朽不仅引起西藏地方民众的反抗,也引起地方政教上层的强烈不满。1908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礼仪上,清王朝顽固要求三跪九叩,这不仅违背世界发展大势,也引起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政教上层的严重不满。在地方事务上,清朝政府及其驻藏机构的腐败现象反而比内地更为严重。1906年,清王朝旨派以候补五品京堂赴藏查办藏事的张荫棠,在其奏稿中感慨,“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驻藏大臣“日形骄蹇,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废弃”[1](P1318-1319)。我们从清政府驻藏官员的派驻规律,以及派驻西藏的诸如有泰之流的具体官员的身份,就可以知道清王朝后期对西藏事务的重视程度和驻藏官员的恶劣影响。中央政府不重视,派驻官员腐败,而作为地方政教领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不能直接向皇帝奏事。在经济上,三大领主占有土地的封建庄园经济走向衰败没落,西藏经济的危机更加突出。从公元13世纪开始,在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以“谿卡”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封建庄园经济,一直是西藏的主要经济形式。进入近代以后,一方面由于土地和农奴的日益集中、封建剥削的不断加深和对农奴人身自由的禁锢,经济发展的凋敝之势愈发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和门户的洞开,西藏传统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差民和农奴为了躲避繁重的乌拉差役以及官吏的压迫,纷纷逃离庄园,流浪在西藏各处,很多人涌进拉萨,成为拉萨的乞丐和游民,直接导致庄园的衰亡”[2]。
当前,我国北京、广东、河北等省市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划针对个人消费端的、政府牵头的碳普惠机制。结合各地特点,它们涵盖的低碳行为方式、采用的核算方法、激励机制及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见表1。在民间层面,以支付宝旗下的“蚂蚁森林”为代表的各类碳普惠产品也受到公众关注。
其次,西藏在各种内外冲突中遭受的失败冲击更加明显。虽然西方侵略者对西藏的侵略相对较晚,但是侵略者的手法和目标并无二致。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都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在两次抗英斗争中都是如此。可是结果如何呢?抗英战争的失败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一波冲击,这种冲击给他带来如同内地面对鸦片战争失败时一样的挫败感和失望。使他对朝廷失望,对自身实力失望,在失望之余本能地选择出逃。第二波冲击则是中外交涉的结果。第一次侵藏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条约越过西藏地方政府,将在西藏的国家主权拱手让人。对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直是抵制的。这种抵制,既有无助中自立自强的成分,也有抵御外侮的性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清王朝政府的代表——驻藏大臣有泰认敌为友、“战后而和”的政策更是让人寒心。战后,清王朝在英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的态度,竟然是“旨令十三世达赖留驻青海塔尔寺,暂不返藏”[3],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处于有家不能回的窘境。面对这些冲击,作为地方政教领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其心中的挫败感和矛盾可想而知。
当国家处于风雨飘摇时,社会上的“风飘絮”和“雨打萍”都是常态,政治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综合分析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面临的内外处境,国家的加速衰败和英俄等大国的角逐,使他长期被迫小心地盘桓在俄国、英国和清王朝中央之间,这种无助感是他出走印度的重要动因。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更多表露的是对国家衰败的无奈、对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以及对自身前途的迷茫,而很难说得上就是对国家的背叛。
二、清末新政在西藏的推行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
如何看待新政在西藏地区的宿命呢?首先,清王朝的新政本身就存在如上文论及的种种缺陷,在全国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不满和反对,并以失败告终。这些缺陷在西藏地区同样存在甚至更加突出,因此,新政在西藏地区遇到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可以预见的。其次,在西藏地区推行的新政措施,由于没有顾及到西藏的区情和民族地区的特点,也没有获得藏族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它引起的抵制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由于特殊的民族、历史和宗教等原因,西藏地区的社会进化表现出自身的特点,社会改革的方式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然而遗憾的是,或者出于民族主义的心理,或者出于对民族特点的无知,亦或是出于对在藏施政挫败感的焦虑和反弹等原因,驻藏官员在西藏地区推行新政时采取了急功近利和简单化的措施。对于西藏“不改以行省之名而以行省之实治之”[5](P440),尤其是政教分离问题、川军入藏问题等改革举措都触动了西藏政教上层的敏感神经,进一步加剧了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对抗。此外,新政在西藏的推进过程更为“激进”,这对于积重难返的西藏社会是一时难以消化的。“毕竟西藏与其他藏区不同,与内地差别更大,把西藏与全国其他地方纳入统一步骤,问题自然凸显”[6](P437)。
两次英国侵藏战争之后,西藏作为一个非常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危机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从清王朝还是西藏地方考虑,变革已经在所难免。1905年,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清政府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推进“改土归流”政策,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控制。西藏的情形更为复杂,赴藏查办藏事的张荫棠感叹,“非大为更张,不足挽危局也”。张荫棠上奏朝廷,提出了以“政教分离”为重点,以“收回治权”为目的,和以“川军驻藏”为保障的建议,并提出了一系列在藏推行新政的措施。张荫棠对于西藏的看法无疑是有见地的,清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于1906年先后派联豫和张荫棠进藏推行新政。新政的推行,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西藏社会的变革,对西藏社会进步是有利的。同时,新政对于维护和加强清王朝对西藏的治权、巩固边疆以遏制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等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内地正在推行的新政相比,西藏的新政存在更多的缺陷。
首先,从新政的时机和条件上看,对新政的成功都是十分不利的。一方面,清末的新政错过了掌控和主动变革的最佳时机。清末新政是在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国外列强步步进逼的情况下登场的,清王朝中央已经无法掌控社会变革的主导权。另一方面,这一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权力和资源也极为脆弱。到了清末,清王朝的实力和中央的权威每况愈下。雪上加霜的是,作为晚清权力核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在两天之内相继撒手而去,皇室在继承危机中仓促的迎来只有两岁的溥仪勉强维持。清末的财政状况更是糟糕,根本无力为新政措施的推行提供起码的支持。其次,从新政的具体过程和改革举措上来看,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诸如改革措施不彻底、改革进程拖拉迟缓等等,国内学术界对于清末新政局限性和虚伪性的认识,多是从这方面的研究出发的。“对新政予以否定评价,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不但不可能导致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也无补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4]。实际上,这些缺陷都是在时间约束的背景下凸显的。相对于数千年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相对于极度脆弱的清王朝,新政的措施和进程可能并不缓慢,反而有些“激进”。历史留给清王朝的最后机会只有短短10年,它要么在顽抗中继续沉沦,要么在激进变革中走向覆灭。
进入20世纪,清王朝的内外交困接近了临界点。义和团运动的搅动、八国联军侵华的冲击和《辛丑条约》造成的危局,使苟延残喘的清王朝难以为继。为了摆脱内外困境,清政府在半推半就中开启了“新政”。1901年,慈禧太后在回京途中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实行“新政”,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措施;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使西洋考察政治;1906年,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对于清末新政的性质,学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改革运动和挽救大清王朝政权危机的最后一次尝试,清末新政的先天不足和内在缺陷确是十分明显的,这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完成前述的两项艰巨任务,最终只能在革命的炮火中偃旗息鼓。
综上,新政在西藏的推行摆脱不了失败的宿命,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必然对新政的推行进行抵抗。最终,新政不仅没有挽救封建王朝的生存危机,巩固清王朝在西藏的治权,反而加剧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以联豫为首的新政主持者的矛盾,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直接后果。
米家电磁炉,模拟传统燃气灶调控方式,轻轻一转,精密调节火力,准确到位。也可通过扭转直接选择烹饪模式,OLED显示屏,简单又直观,还可以根据内置菜谱增加常用烹饪模式。
三、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是晚清社会主体对于社会剧变做出的众多自发或自觉反应的一个缩影
清王朝的加速衰败,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社会危机。清末新政不仅没能如愿化解危机,反而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在这种背景下,晚清的中国社会瞬息万变,因为“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7](P61),纷纷努力寻找出路。李鸿章曾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今则……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是晚清社会唯一的确定性。面对风云变幻、急剧坠落的社会,各社会阶层和主体对社会的激荡做出了自发和自觉的反应,出现了众多社会运动和波诡云谲的事件。这些反应从大的方面看,有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有“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有地主阶级编练“湘军”以求自保,也有以“自强”、“求富”为名的洋务运动;有资产阶级维新派救亡图存的“百日维新”,也有革命派浴火重生的辛亥革命;有皇室当权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苟且,也有清末意兴阑珊的“新政”;有地方政权在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东南互保”,也有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总之,面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各社会主体都在以各种方式追求着国家、民族和自身的出路,身处西藏的政教人士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们认识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重要背景。
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是新时代全民普法的重要顶层设计和重大制度创新。责任制明确了普法的责任主体,转变了普法的理念和方式,拓展了普法的格局,提升了执法的效果。“谁执法谁普法”既是“七五”普法与“六五”普法的根本区别,也是“七五”普法工作的“牛鼻子”,只有紧紧抓住,才能推动新时代全民普法工作进一步转型升级,更好地助推新时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当然,面对乱世,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做出出走印度的反应,还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十三世达赖喇嘛有一定的自强心理,不愿意受到胁迫。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成长环境比较复杂,在他亲政后的几年里,西藏的政治形势依然十分险恶。除了英俄帝国主义争夺侵略西藏的野心日益膨胀,西藏上层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激烈,1899年发生的“第穆妖鞋”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经历这样的磨炼,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渴望有所作为,不愿意受到胁迫,逃亡是他逃避胁迫的方式。所以,在1904年英军进入拉萨之际,他选择北上内地;而在川军进入拉萨之时,他又选择了南逃印度。虽然川军入藏在性质上与英军入藏截然不同,但是个性要强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强烈感受到川军入藏带来的力量变化。面对有可能受到的胁迫和个人伤害,他再次选择了出走。只是这次他投奔的是昔日的宿敌。其次,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不惜选择以出走的方式对抗清王朝。清王朝治边政策的转变,特别是激进改革在西藏的推行,极大地损害了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封建领主阶层的利益,本就对清王朝非常失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极力采取措施加以对抗。当对抗失败后,他又选择以出走的方式拒不接受。
总之,单凭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推导出他谋求独立的思想,恐怕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此一事件更多的是他在应对清末变局中的一种被动选择。1912年1月1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8]。虽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走事件与一年多以后的各省独立不可同日而语,但《宣言书》的逻辑也足以说明,起码在革命者的视野中,此时对清廷的背离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实上的倾向“独立”。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后西藏形势的发展,应该另当别论。
(3)细化社会分工。融资租赁中,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在社会分工中其作用也不容小觑。从生产、加工到消费这一系列过程中,将销售流通业和租赁业分隔开,而这一过程,延长了社会分工链条长度。通过融资租赁,使企业分工更加细化,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各类社会资源得到了更好地应用,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吴丰培辑.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2]张晓明,金志国.百年西藏——20世纪的人和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
[3]周源.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英属印度事件考辨[J].清史研究,2000(11).
[4]崔志海.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J].清史研究,2014(8).
[5]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喜饶尼玛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8]宋月红.孙中山“五族共和”之治藏策略[J].中国国情国力,2001(9).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9)03-0065-04
收稿日期:2019-03-08
作者简介:黎同柏(1973-),男,河南信阳人,现为海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民族学。
[责任编辑 顾祖成]
[校 对 梁成秀]
标签:达赖喇嘛论文; 西藏论文; 新政论文; 印度论文; 清王朝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佛教史论文;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海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