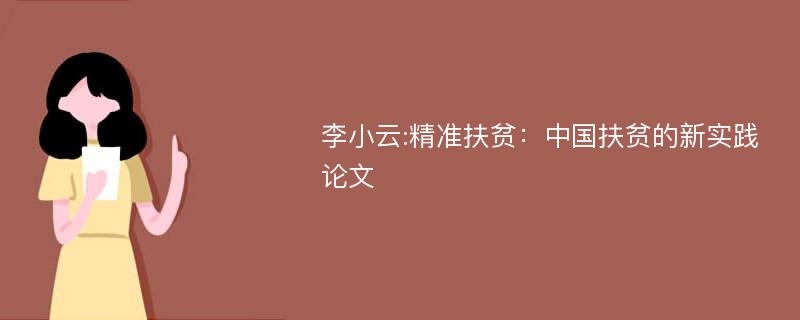
[摘要] 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中国扶贫政策仍在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建立,同时,为应对21 世纪以来特别是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经济社会转型所出现的挑战,在扶贫领导体制、贫困治理机制、扶贫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在扶贫体制方面,创新使用政府行政主导、五级书记挂帅、第一书记驻村等方式;在贫困治理机制方面,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回归部门专业技术理性,建立考核评估体系;在扶贫方式方面,因地因人因需制宜创新和扩展多元化扶贫方式。在政策的引领下,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是中国扶贫的新实践、中国减贫叙事中的新故事。
[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新实践;领导体制;治理机制;扶贫方式
在2012 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工作中,通常使用两个术语,一是精准扶贫,二是脱贫攻坚战。这两个术语形象地代表了这一阶段农村扶贫工作的基本特征。精准代表了扶贫的方式,脱贫攻坚战呈现了扶贫的机制,两者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农村扶贫工作的新特征。进入21 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社会分化日益明显是这一阶段扶贫工作所面临的新挑战[1][2]。与以往不同的是,进入新阶段以来,贫困人口的比例并不算很高,然而绝对数量依然很大,因此,难以通过全面实施保护托底式的脱贫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也难以通过一般的经济开发实现脱贫,扶贫工作面临双重压力。
贫困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贫困治理也始终是一项世界性的议题[3][4][5]。贫困的治理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调“个人努力进取”的脱贫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个人在市场中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计,并主要通过个人收入在市场机制中保障自身福利,如将个人收入用于投资商业化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机制以确保个人未来福利的维持或改善。尽管美国政府有扶贫救助计划,尤其是社会慈善救助,但从总体上讲,美国的贫困治理并不依靠收入转移[6]。第二种贫困治理模式是北欧和西欧的福利国家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通过高税收抑制收入差异,再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相对公平的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机制[7]。美国的贫困治理虽然具有很强的个体效率激励效应,但由于其无法应对处于贫困陷阱中的贫困人口问题而备受诟病[8]。欧洲模式虽然从制度上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兜底作用,但背负巨大的福利负担,形成了福利陷阱[9]。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沉重的福利负担曾促使德国尝试将社会保障政策引向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却因得不到民众支持而告终,福利政策进入进退两难的局面[10]。很多后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其经济发展以后基本采用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模式[11][12][13]。部分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则尝试创新性地采用收入转移模式[14]。这一模式一度取得喜人效果,但难以解决贫困者的收入问题,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整体贫困问题。
中国政府自21 世纪初就关注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在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扶贫战略中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实现两项制度的衔接,推动一系列针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与落实[15]。这一时期,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开始面临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的双重压力,但开发和保护有机衔接的贫困治理机制却未能得到完整发育。到了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压力日益突显,在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达到较高程度的情况下,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挖掘开发式扶贫的潜力,以避免直接的收入转移,另一方面,需要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建立有效的保护和托底机制。在精准扶贫阶段,最终走向两项制度的有机融合,而且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开发式与保护式扶贫相互结合的扶贫战略。不仅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农村扶贫的新格局,同时也为国际减贫实践提供了新经验。
新时期我国设定了到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精准脱贫攻坚战是我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精准脱贫攻坚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则是为应对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挑战而形成的。本文不是针对精准扶贫工作的系统评价和总结,也不是对这项工作进行理论归纳,而是基于以往的扶贫开发实践,从贫困治理机制、扶贫领导机制和扶贫方式创新等不同方面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比较性的解释和说明,从而为这项工作提供更多思考。
春季遇到阴雨寡照天气,要小心灰霉病和霜霉病,闷热天气小心白粉病和蓟马,尤其是夏秋季,霜霉病可能更难防控。
根据旅游统计公报显示,2013-2016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和国内居民出境人次均保持增长,其中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增长率稳定在10%以上,并有持续增长趋势。2016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和国内居民出境人次分别达到44.4亿人次和1.2亿人次,随着用户旅游经验的积累,对于个性化和深度旅游需求不断增加,为在线自助游奠定发展基础。
一、精准扶贫的成绩简要
中国贫困地区地域广泛,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较大,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需采用不同的扶贫方式,即使同一类别的致贫原因也无法采用单一方法来加以解决。在全面消除、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政治压力约束下,在扶贫质量的监督考核机制下,中国各地创新实现各种扶贫方式:
(四)旅游线路少,竞争力弱。市中心区的启新1889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等旅游景点,近年来主要接待了各级来唐参观的领导,居民和外地游客很少参观游览,叫好不叫座;由于旅游线路少、特色不突出、业态结构简单、再加之运营模式老套、缺乏竞争力,游客参与性不强,旅游收入也不乐观。
下面例子左边代码段表示:父类=人类(字段有name,age和学习方法),子类=学生类(字段有学号和学习方法),主程序类中学生类调用父类中的字段和说话方法。
同时,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条件改善等方面,也可以看出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成就。在住房质量改善方面,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为58.1%,比2012 年上升18.9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户均住房面积也比2012年增加21.4平方米。在饮水安全方面,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为89.2%,比2013年提高了8.2个百分点;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为70.1%,比2013 年提高16.5个百分点;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为43.7%,比2013年提高13.1个百分点。
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为92.0%,比2012 年提高8.6 个百分点;92.2%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比2013 年提高7.8 个百分点;拥有畜禽集中饲养区的行政村比重为28.4%,比2012 年提高12.4 个百分点;61.4%的户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比2013年提高31.5个百分点[20](详见表4)。
应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所有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实验均独立重复3次,计量资料以± s表示。2组之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首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两两比较用Bonferroni校正的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准确瞄准贫困群体是确保贫困者真正受益于扶贫政策的基础。在以往的扶贫实践中,除了针对贫困群体的瞄准偏离导致扶贫效益低下以外,扶贫措施未针对致贫原因精准实施更是影响扶贫效益的重要因素。针对整村推进扶贫措施的研究发现,虽然贫困村的农民平均收入比非贫困村的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改善,但在贫困村内部,非贫困户的受益程度依然高于贫困户[42],原因主要在于到村扶贫项目设置的约束,反映了过去常规的扶贫项目在对接真正贫困群体需求中的弊端。从国家角度出发,将扶贫项目聚焦到每一个贫困者的需求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成本非常高、实施困难。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在客观上要求不仅需要知道谁是贫困者,还必须做到精准施策。
传统气象观测由于相关业务人员对农业知识了解不足而使得气象观测的内容缺乏针对性。要实现地面气象观测工作在现代农业中应用效果的提高,就要加强同农业部门的联系。利用农业部门的人才有时同相关气象业务相结合,建立起一整套针对农业生产的气象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在进行观测过程中要依据当前农作物生长可能受到影响的气象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气象观测。气象部门应该同农业部门加强沟通,了解农业部门的实际需求,使得在进行地面气象观测过程中有的放矢,提高应用效果,保障农业生产。
表1 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17]
年份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万人)16567 12238 9899 8249 7017 5575 4335 3046 1660贫困发生率(%)17.2 12.7 10.2 8.5 7.2 5.7 4.5 3.1 1.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5919 6977.3 7916.6 9430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人均增长率(%)14.86 17.88 13.46 19.12 11.23 8.9zx 8.24 8.65 8.8
表2 2013-2017年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51.2指标名称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93.3 93.3 95.2 97.6 98.2 98.5 69 70.7 75 79.3 81.3 86.5 38.3 41.5 48 56.3 63.4 71——59.9 64.7 73 77.9 81.1 38.8 42.7 47.8 49.9
表3 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文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指标名称16 岁以上成员均未完成初中教育农户比(%)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重(%)2017年2012年2017年比2012年提高(百分点)15.2 18.2-3 84.7 17.1*88——10.0*89.2 74.5 14.7
表4 2013-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指标名称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拥有畜禽集中饲养区的行政村比重(%)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2012年83.4—2013年88.9 84.4 2014年90.9 86.8 2015年91.2 90.3 2016年90.4 91.4 2017年92 92.2 16 23.9 26.7 26.9 28 28.4—29.9 35.2 43.2 50.9 61.4
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16 岁以上家庭成员均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农户比重为15.2%,比2012年下降3.0 个百分点;84.7%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88.0%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分别比2013年提高17.1和10.0个百分点;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重为89.2%,比2012 年提高14.7个百分点[19](详见表3)。
口头述职完成后,李兴军的神情又紧张了起来,手不自觉地攥紧了一些,对在上一届已参加了两次述职的“老”代表来说,他知道下一个环节就是选民提问和评议。“乡镇卫生院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效率不高、活力不足、医疗服务质量不高的状况还没得到根本改变,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选民代表、寺头村村民张玉庆开门见山地问道。“我镇是山区乡镇,条件落后,近几年院里年轻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你是否向上级部门反映过?”选民代表、医院职工冯永红接着提问……李兴军代表脸红冒汗,一边听,一边用笔快速地记录问题,向选民一一作出答复。“现场回答选民的提问,压力很大,也感受到了人大代表为选民代言、为选民办事的责任。”李兴军感慨道。
对于松山湖开发区政府出资的留学生创业园、创新科技园,应该把视角放远一点,思路拓宽一点,率先开创出一些新的工作思路和孵化路径。
自中国20 世纪80 年代有组织地实施扶贫开发工作以来,精准扶贫工作在领导体制上实现重大创新。这一体制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克服了政府主导作用发挥的不足,为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打破扶贫工作中的部门利益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也是自2012 年以来贫困人口数量能够迅速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中国扶贫新故事的重要内容之一。
委托执法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将其执法权的一部分依法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或组织执行的法律行为。委托执法作为专业行政执法的补充和延伸,在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难题,降低行政执法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8年上半年,笔者对重庆市涪陵区行政委托执法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摸清了现状,查找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和规范行政委托执法工作的建议。
二、扶贫领导体制的创新
(一)“政府行政主导”扶贫模式
中国消除贫困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下的“政府行政主导”扶贫模式,。从国家法制角度讲,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治理,并非分权制的国家法治治理。这是中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实践在宪法条件下的合法性基础。1986 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至此,农村扶贫工作正式成为了中国政府的专项职责。正是这样一个机制孕育了中国在发展中摆脱贫困的“政府主导”扶贫模式。同时也需要看到这种模式依然属于政府序列下的行政治理。这一模式虽然在战略统一和实施效率上优于技术官僚的治理,但是当扶贫工作需要超越政府部门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主导”依然显得力不从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门利益所致[21],体制安排仍有一定局限性。
(二)“超越行政”的贫困治理——五级书记挂帅
如前所述,到2020 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任务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项目,而是涉及到如何突破结构性制约和资源再分配机制的重大政治议程。一方面,必须基于“政府主导”的原则统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这一议程的落实如没有超越行政就很容易陷入政府部门行政结构的约束之中,引发了公共服务的碎片化[22]。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虽然能避免碎片化扶贫,但难以避免行政层面分割扶贫的局面。而扶贫工作需要在社会和行政两个层面实现高度集中统一。很多针对精准扶贫的研究认为,中国现行的扶贫方略属于行政治理和运动式治理,并就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23][24][25][26]。事实上,精准扶贫虽具有较强的运动式和行政式特点,实则是“超越行政”集中治理的政治实践。首先,在精准扶贫开始实施之时,中国共产党就将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作为党的重要工作,实施“五级书记挂帅”,特别是党的总书记将扶贫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展开部署。这在领导体制上超越了以往的“政府主导”,将政府主导转变为党主导、政府落实;其次,通过双首长负责、压力层层传递和考核问责等机制将领导机制具体化,极大地强化了“政府主导”机制。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权威性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得以加强,工作效率得以提升。并且,总书记亲自深入贫困地区,带动各级党的书记直接参与扶贫行动。
传统的成本管理理念认为,成本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企业的成本,节约可以说是企业降低成本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但盲目控制成本会导致产品品质和业务收益下降,因此可以说传统的成本管理是一种负面的成本管理。
(三)外部组织资源落地——第一书记驻村
“五级书记挂帅”的领导包括党在中央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以及党对扶贫工作第一线的领导,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的措施将扶贫领导体制从战略政策层面贯穿到实践层面。截至2018 年底,全国共派出45.9 万名第一书记,目前仍有20.6 万人在岗[27]。向贫困村派出第一书记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在过去几十年中,农村地区组织人力资源极度匮乏,贫困地区则更为严重,而扶贫措施精准到每一户,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将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年轻人以第一书记的形式派驻贫困村,极大地补充了贫困地区的组织人力资源。扶贫工作是一项复杂的政治社会工作。中国的乡村是一个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扶贫工作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比如贫困户识别、扶贫措施的到位,虽然这些工作都有明确指标和程序要求,但即使规定非常客观科学,在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如果仅依靠村干部来推动实施,则很难展开工作[28][29]。村干部本身就是村里人,在实际操作中确保公平面临一定困难。外部组织资源的介入可以有效地协助村干部更为有效地展开工作,事实上,从建档立卡工作的开展到各项扶贫措施的落地,正是在派驻第一书记的条件下展开的。
贫困村派驻的第一书记不仅是乡村利益的社会调节器,同时也是扶贫的重要资源,他们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所在工作单位的社会网络,能有效利用社会网络将信息和技术引入扶贫工作中,不少扶贫创新来自于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精准扶贫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在贫困治理的场域中实事求是地把握了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在政府“扶贫责任—识别贫困者—打破贫困”的制度性约束下,为整合不同的扶贫资源,创新扶贫方式,向贫困者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凝聚社会的扶贫共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创新,构成了中国扶贫历史过程中的新实践和新经验,是中国减贫叙事中的新故事。
三、贫困治理机制的创新
(一)竞争性政治下的激励失灵
贫困治理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的难点,因为扶贫的议程涉及到利益调整和资源配置,需要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共识。在竞争性政治的条件下,行政官僚治理体系是这些国家的治理基本结构。政治议题纳入行政议程也需要基于法律。因此,在这些国家中,除非执政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否则执政党提出的建议容易成为政党斗争的牺牲品。解决贫困问题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部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因此很容易成为政党和行政官僚博弈的工具。从1601 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开始到现在,英国的扶贫法案已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全民医疗法案从提出到终结,更是现代社会“一个社会正义议题是如何被竞争性政治条件下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牺牲”的典型案例。
2.2.3 不同分娩方式对盆底肌力治疗前后的影响 不同分娩方式之间相比较,盆底肌力在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故认为产后盆底肌力减退治疗前后的变化与分娩方式无关。见表12。
在行政体系下,各个部门均会按照自身的技术官僚理性来确定工作重点。同时,专业行政部门的治理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即使行政治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政党政治议程对其影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30]。与此同时,专业行政部门的治理又很容易在行政独立运行的体制下优先确保其部门利益[31]。部门利益来源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专业部门的治理往往遵循专业技术主义的理性和逻辑,如农业部门和水利部门遵循自身的农业生产技术或水利应用技术的专业理性逻辑。部门划分越细,由于技术理性所形成的隔离也会越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发展规划的整体性,就会出现部门的反复划分、合并与循环,这也体现在中国历次机构改革方面。另一方面,部门的治理也是人的治理,人是政治化和社会化的,这就是治理的人格化[32]。各个部门在部门业绩的激励下,需要呈现各自独立的业绩。然而,按照部门合作的逻辑,有时很难区分业绩是哪个部门做出的贡献,从而使业绩比较出现困难,造成激励失灵。
(二)精准脱贫攻坚新机制打破部门壁垒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通过党的集中领导,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部门专业治理的弊端,特别是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所形成的“五级书记挂帅”体制下,各部门之间围绕脱贫攻坚的任务,可以做到统一协调和部署。但是过去在强调行政法治治理的过程中,部门专业治理已越来越法制化,比如部门的发展项目从论证立项到目标区域的选择,以及具体的产出,都需要在相对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考核和审计均基于已经批准的文本来展开,资源的统一部署依然受到行政部门专业治理的影响。例如,中央要求按照脱贫攻坚的任务对资金进行统筹使用,但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对资金的使用方向进行调整,因为可能面临严格的审计问责。在此情况下,中央对扶贫资金的管理进行改革,将资金使用与管理的权限下放到县一级,同时在计划、审计等基础性制度方面进行调整,要求涉农项目按照中央精准扶贫的战略安排,尤其是将深度性贫困地区的需要作为重点,进行资源的统筹[33],涉及到农业、林业、水利、教育、卫生、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部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扶贫开发确立了整村推进的战略,将贫困村作为扶贫的基本单元,由此出现了资金投向贫困村的具体问题,而在仅依靠财政扶贫资金,对整体贫困则是杯水车薪,因此当时就提出了资金整合使用的问题,在以后的十多年中,这一问题由于上述各种约束条件始终未能解决。随后,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确立了“五级书记挂帅”领导机制,并迅速通过该体制打破了行政专业治理的结构性制约,使摆脱贫困这一政治议题超越了行政治理的界限,形成了扶贫资源筹措使用的新机制。在此机制下,有助于农村发展的各种资源迅速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集中,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在某种意义上,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扶贫资源的供给强度。
(三)贫困再瞄准——建档立卡与贫困户精准识别
扶贫是一项涉及贫困人口的系统工程,衡量扶贫效益的高低始终围绕着贫困人口能否受益这一问题[34]。如何瞄准贫困人口则是全球扶贫工作的难题,除了极容易识别的特殊群体如残疾群体等以外,用发展和福利性的指标来识别贫困群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过程。一方面,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具有无偿或优惠资源转移的性质,在识别贫困群体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挤入现象,干扰扶贫的公正性,增加资源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在权力关系的制约下,会发生对贫困者的排斥,扭曲了扶贫的基本原则。从技术角度出发,仅仅依靠收入贫困线很难准确地瞄准贫困群体。中国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开始关注贫困群体问题。大量研究表明,以县为单位的区域性扶贫瞄准机制无法有效地瞄准贫困群体,592 个国定贫困县仅覆盖了50%的贫困人口[35]。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扶贫开发战略中,中国政府继续以贫困县为对象,并将扶贫工作的基本单元下沉到贫困村,基于收入、基础设施等指标,在全国共识别了148500 个贫困村[36]。之所以把贫困村作为基本单元,主要在于聚焦贫困村可以关注更多贫困人口,然而,将扶贫基本单元下沉到村一级,尽管覆盖了更多的贫困人口,但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群体瞄准机制[37]。
长期以来,在如何直接瞄准贫困者的问题上,扶贫瞄准机制一直存在着客观上或技术上的困难。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基本策略,即通过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向贫困地区的人口提供技术支持,以便他们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其次,开发式扶贫战略中的很多具体措施很难直接瞄准贫困群体,因为这些扶贫措施首先是开发性的,要求有经济效益,贫困户申请这些项目也需要一定条件,如在“八七扶贫攻坚”和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中许多养殖业、种植业的扶贫项目,往往要求有配套资金,承担项目的主体需要有劳动力资源以及掌握相应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因此,开发式项目一定程度限制了向真正贫困群体的瞄准[38]。最后,从扶贫瞄准与扶贫方式的关系上讲,保护式的扶贫,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本质上更容易瞄准贫困者,因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缺失的群体容易识别,如谁是辍学儿童,但在接受一定帮助后通过市场竞争增加收入则非常困难。
随着贫困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贫困的特征也在发生变化。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多具备了相对容易识别的特征,但是从技术上讲,即使2011年确定了贫困标准,依然难以确定究竟谁是贫困者。而到2020年要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客观上需要识别扶贫对象,这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考虑如何瞄准贫苦者。2014 年,我国开始在全国展开贫困户建档立卡制度[39],该制度通过行政人力资源展开贫困人口的普查。为准确识别农村贫困人口,政府采用了2011年不变价格2300元的收入标准,同时附加“两不愁、三保障”的非收入性贫困指标,既把握了收入标准的维度,同时克服了利用收入维度难以识别贫困者的缺陷,将容易识别的衣、食、住房、教育、医疗作为瞄准的指标内容,从技术的角度解决了识别贫困者的方法问题。这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贫困者瞄准的机制。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了许多创新方案,如贵州广泛采用“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进一步丰富了识别贫困者的方法。按照这一方法,2014年,全国共识别2948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40]、8962万贫困人口[41],为了确保精准性,政府要对建档立卡的贫困对象进行反复核查,技术上的可识别性以及相应的核查机制,最大程度确保了挤入和漏出的减少,为精准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四)对症施策,回归部门专业技术理性
截至2017 年末,贫困地区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从2012 年的93.3%上升到2017 年的98.5%,提高5.2 个百分点;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为86.5%,比2012 年提高17.5 个百分点;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为71.0%,比2012 年提高32.7 个百分点。2017 年贫困地区村内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为81.1%,比2013 年提高21.2 个百分点;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为51.2%,比2013 年提高12.4个百分点[18](详见表2)。
于是,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之上,我国对致贫原因进行了分类。2014 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和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分别占38.5%和9.1%,除此之外,缺资金、缺技术和缺劳力也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因而,中国政府作出“五个一批”的具体部署。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样的分类未必科学,一个农户或个体的致贫的原因往往是综合性的,简单地归结为某一因素可能是片面的,例如某一农户存在因学致贫的现象,另一个农户可能是因病致贫,但最初两者可能同样因为收入低下、无法支付教育和治疗费用而致贫,其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社会基本服务的不平等。
因此,从防止贫困的角度,整体脱贫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政府也在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体系中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服务均等化的内容,增强精准扶贫体系设计的严密性。而从扶贫的角度,分类施策则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扶贫的目标是解决现实中贫困群体的问题,在健全防止贫困发生机制的同时,需要直接瞄准已经发生的问题,在社会公共服务还没有实现均等化的条件下,需要首先解决儿童辍学和医疗救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对产生贫困的第一层原因进行分类,从而实施及时性的扶贫救助,这是扶贫战略必须首先面对的技术问题,否则容易导致扶贫资源使用的偏离。精准施策的意义还在于可引导通过扶贫机制整合的资源进入最需要的领域,并且更为科学地投入到扶贫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归了部门专业技术理性的权威,调动了部门积极性,同时也为部门回应业绩考核和审计提供了合法依据。针对致贫原因的分析和分类,不仅直接服务于扶贫的需要,同时指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诸多方面,为国家发展战略和计划工作提供了诸多案例。
(五)建立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效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对脱贫攻坚的各个环节都设置了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对于建档立卡、精准施策等实行了定期的核查,对脱贫攻坚工作采用了严格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2016 年我国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要求从2016 年到2020 年针对精准扶贫的成效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全面推出建立分省交叉评估制度、全员培训认证制度、APP 全数据采集系统、评估大数据平台系统、标准化统计分析系统等。精准扶贫中建立了系统和严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主要内容是:贫困瞄准和精准施策是否到位,特别是围绕着“两不愁、三保障”的具体指标,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展开评估,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情况,会对领导干部和相关人员进行问责。比如,安徽阜阳市委书记以扶贫搞形式主义撤职问责就是典型的一例。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不仅是确保扶贫资源使用效率的制度性约束,更是实现到2020 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制度性保障。
四、扶贫方式创新
(一)因地因人因需制宜——扶贫方式多元化
如果考虑到这个阶段减贫的难度,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000万以上应该是中国减贫历史上最好的业绩。如表1 所示,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 年的16567 万人下降到2018 年的1660 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从2010 年的17.2%下降至1.7%。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0 年的5919 元增加到14617 元,贫困地区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到10371元,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60 元,均高于全国农村上年增速[16],远远高于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详见表1)。
“扶贫车间”便是众多产业扶贫模式中的一个典例。在贫困人口集中的村庄,建立扶贫车间,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贫困村。这种模式从根本上瞄准留守人口和城镇返乡人口无法就业的问题,同时又规避了劳动力外出离家、在外生活成本高昂等问题,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光伏扶贫是产业扶贫中的另一种创新模式,光伏扶贫将贫困人口无法实现增收的土地资源,以入股的形式与能源企业相结合,通过能源收入获得股份收入,从而实现资产的增值。
土地流转扶贫也是扶贫方式的创新,在很多贫困地区,农户有大量的荒山荒地,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信息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等,农户没有充分开发利用这些土地资源。通过帮扶计划,企业与农户签署土地流转协议,将土地从农民手里长期租用,不少地区单个农户流转荒山荒地多达五十亩以上,每年可获得数万元的租金收入,基本实现脱贫。
电商扶贫影响力较大,直接满足了以农产品生产为主体的贫困群体需求,长期以来,如何让小农对接市场一直是开发式扶贫难以逾越的障碍,曾有多方面的尝试,但均无法越过中间层次多、成本高的问题,面临着农户农产品出门价格被不断挤压的困境[43][44]。大型农业电商平台在这方面进行了众多的技术创新,比如淘宝村、淘宝直播、多多农园等项目,有效地对接了小农生产和市场的需求,社交农商模式可通过瞬间凝聚巨量需求信息,有效衔接了鲜活农产品需要及时消费的特点。
旅游扶贫是产业扶贫实践中引人瞩目的创新,随着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逐渐成为贫困地区的优势资源,各种乡村旅游模式不断出现,其特点在于让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资源转化成经济资源,同时,可以直接吸纳贫困农户的就业,可以产生比农业更高的收入。云南勐腊县河边村原是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4000 元的贫困村,经过4 年的建设,如今成为了知名的小型会址和自然教育基地,农民收入实现了倍增。
保险扶贫模式聚焦了贫困农户脆弱性的核心特点,将涉及到的农业生产、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风险融为一体,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探索了可持续的脱贫方式。比如,河北省的社会保险扶贫从防止贫困的角度在国内率先进行扶贫创新。
(二)脱贫方式的扩展——定点帮扶与社会参与
定点帮扶与社会参与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中开始采用的扶贫方式,一是通过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对国家扶贫资源提供相应的补充,丰富扶贫方式。二是通过定点帮扶将社会帮扶行动具体化,激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定点扶贫和社会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央各项政策的激励下,大量的社会资源进入贫困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正式立项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共686家,共开展扶贫项目1536 个,扶贫项目总支出约323 亿元,受益建档立卡户约63 万户,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581万[45]。
与此同时,定点扶贫和社会参与的模式得到进一步创新。按照扶贫主体进行分类,这一扶贫模式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党和国家机关与高校、研究机构等事业单位的定点扶贫,其特点是使用公共财政资金进行扶贫,各单位均可按照自身的专业特点实施帮扶工作,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和专业特色。第二类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定点帮扶,如北京帮扶内蒙古和青海,上海帮扶云南和贵州,其特点是既使用地方财政的公共资源,又动员发达地区的国有和民营企业资源。第三种类型是企业和其他类型行业的帮扶,主要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施,其中国有企业会在政府统一部署下进行帮扶,民营企业则会根据地区要求和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展开帮扶。
例如,大型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在贵州毕节大方县投入40 亿元人民币进行扶贫工作,通过易地搬迁于2017 年实现12.73 万贫困人口脱贫。全国工商联发起“万企帮万村”行动,截至2018 年6 月底,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5.54 万家,精准帮扶6.28 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3.99 万个),帮助了755.9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产业投入597.52 亿元,公益投入115.65 亿元,安置就业54.92 万人,技能培训58.31万人[46]。同时,上海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4 州市的26 个县及德昂族、独龙族聚居区实施定点帮扶,截至2014 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7.87 亿元,援建各类帮扶项目6182 个,其中整村推进项目3942 个,逾60 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47]。另外,上海在贵州遵义的定点帮扶,2013-2015 年间共投入援助资金10400 万元(不含捐赠3000 万元),实施项目59 个,尤其是在教育帮扶方面,投入了帮扶资金2870 万元,用于遵义市、县两级5 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实训配置,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教学条件[48]。北京市在青海玉树定点帮扶工作中,2018 年累计安排支援资金45855 万元、项目65 个,其中累计投入7359 万元支持医疗教育事业发展,“院长+改革+团队”的医疗援青模式惠及群众40 余万人,产业就业扶贫项目资金3800 万元,间接助力3000 余人实现创业就业脱贫[49]。北京对内蒙古的定点帮扶实现了结对帮扶全覆盖,2018 年帮扶资金投入共计9.3 亿元,2013-2017 年间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3 年底的157 万人减少到2017 年底的37.8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4.7%下降到3%以下,定点帮扶的脱贫成效十分显著[50]。
定点帮扶和社会参与扶贫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较为充分地补充政府扶贫资源的缺口,尽管中央和地方两级的财政大量投入扶贫资金,但精准扶贫工作资金需求巨大,这一方式所动员的大量资金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社会资源的使用具有灵活性,补充了政府资源的不足,如浙江新湖集团,在云南深度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相关政策下,发起了怒江学前教育全覆盖的扶贫行动,使云南地方教育扶贫的政策得到落实,及时弥补了政府在学前教育方面的资金短板。第三,促进了大量的扶贫方式创新,以企业为主体的定点帮扶行动充分发挥了企业的市场经营能力,通过建立各种益贫性的产业,既为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又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定点帮扶行动中,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帮扶贫困地区的行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慈善捐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最近几年中,社会企业的实践在西方渐渐成为企业回归社会价值的创新模式。在中国,在企业参与扶贫的行动中,政府一直强调企业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通过企业自身在贫困地区的发展带动该地区的发展和脱贫,这从某种程度上引导了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更有效地回归社会价值的轨道。
结论
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建立,同时,为应对21世纪以来特别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经济社会转型所出现的挑战,扶贫政策在扶贫领导体制、贫困治理机制、扶贫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在扶贫体制方面,创新使用政府行政主导、五级书记挂帅、第一书记驻村等方式,既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行政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并通过引入外部组织资源缓解扶贫人力资源的不足;在贫困治理机制方面,打破部门壁垒、促进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的集中,通过建档立卡等制度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同时,针对致贫原因分类施策、回归部门专业技术理性,建立考核评估体系、确保扶贫政策实施到位;在扶贫方式方面,因地因人因需制宜创新多元化扶贫方式,如“扶贫车间”、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并进一步拓展定点帮扶与社会参与等扶贫方式。
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000万以上,几乎是减贫历史上的最好业绩,这主要得益于建立在精准扶贫新机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精准扶贫政策在贫困治理的场域中实事求是地把握了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经验,是中国减贫叙事中的新故事。同时,实践中仍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如何把握贫困发生的规律并逐步建立符合规律的扶贫制度安排,扶贫资源投入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建立一个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贫困治理机制等问题。
未来,需要通过系统的科学评估对上述问题进行总结,并进一步加强对贫困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在宏观层面,既需要继续发挥贫困人口的能动性,又需要正视贫困人口自身努力的局限,既需要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又要防止福利陷阱等相当多的政策选择困境。在微观层面,需要关注贫困发生机制、有效扶贫的机制以及防止贫困发生机制等方面。
[参考文献]:
[1][34]李小云.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2013(07):101-106.
[2][15]汪三贵,曾小溪.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18(08):40-50.
[3]Brady, D.The welfare state and relative poverty in rich Western democracies, 1967-1997[J].LIS Working Paper Series,Luxembourg Income Study(LIS),Luxembourg,2004,(390).
[4]Spicker,P.,Leguizamon,S.A.,Gordon,D.An International Glossary,Second Edition[M].New York,2006:1-19.
[5]Pogge,T.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J].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19(01):1-7
[6][8]Rank, M.R.One nation,underprivileged: Why American Poverty Affects Us All[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4:10-16.
[7][9]Korpi, W.Palme, J.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8,63(5):661-687.
[10]Nullmeier,F.Changes in German Social Policy,1990-2018[J].SocialWork and Society International Online Journal,2018,16(2).
[11]Kim, T., Kwon, H.J., Lee, J.,Yi,I.Poverty,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mixed governance”and welfare in south korea[J].Journal of Democracy,2011,22(3):120-134.
[12]NG, I.Y.H.Being Poor in a Rich“Nanny State”: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Social Welfare[J].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15,60(03):1-17.
[13]Ravallion, M.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J].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0,26(1):71-104.
[14]Ferreira, F.H.G., Leite, P.G., Ravallion, M.Poverty reduction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93(1),20-36.
[16]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http://www.tjcn.org/tjgb/00zg/35758.html,2019-03-10.
[17]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0-2018.
[18][19][20]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EB/OL],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2018-09-03.
[21][31]孙立.“政治正确”与部门利益——一种泛政治化现象的分析[J].中国改革,2006(08):18-19.
[22]何艳玲,钱蕾.“部门代表性竞争”:对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一种解释[J].中国行政管理,2018(10):90-97.
[23]许汉泽,李小云.“行政治理扶贫”与反贫困的中国方案——回应吴新叶教授[J].探索与争鸣,2019(03):58-66+142.
[24]陈义媛.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与基层治理困局[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06):42-49.
[25]何绍辉.从“运动式治理”到“制度性治理”——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范式转换[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33(07):95-99.
[26]魏程琳,赵晓峰.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5):58-69
[27]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EB/OL],人民网,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8/1204/c117092-30440661.html,2018-12-04.
[28]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08):156-162.
[29]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9):109-113.
[30]Gherghina,S.,Kopecký,P.Politic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an introduction[J].Acta Politica,2016,51(4),407-412.
[32]Ma, L., Christensen, T.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Structural Factors and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Reform in China[J].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10):1-21.
[33]关于印发《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cpad.gov.cn/art/2017/3/24/art_1747_761.html,2017-03-23.
[3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6]李小云,唐丽霞,李周等.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系统的开发与运用[J].林业经济,2007,(01):74-76.
[37]汪三贵,Park,A.,Chaudhuri,S.,Datt,G.中国新时期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J].管理世界,2007(01):56-64
[38]贺雪峰.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03):147-153.
[39]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24 号)[EB/OL],http://www.cpad.gov.cn/art/2014/4/11/art_50_23761.html,2014-04-11.
[40]十八大以来中国每年超1000 万人脱贫扶贫精准有力[EB/OL],中国青年网,http://cunguan.youth.cn/jjsn/201707/t20170713_10286825.htm,2017-07-13.
[4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147-150.
[42]王姮,汪三贵.整村推进项目对农户饮水状况的影响分析——江西省扶贫工作重点村扶贫效果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2008,(06):42-47.
[43]王春光,单丽卿.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3):38-47.
[44]蒋永甫,莫荣妹.干部下乡、精准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基于“第一书记产业联盟”的案例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6(05):162-168.
[45]民政部:去年全国性社会组织扶贫项目总支出约323 亿元[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6-28/8877658.shtml,2019-06-28.
[46]高云龙同志在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表彰大会暨扶贫日论坛上的讲话[EB/OL],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http://www.acfic.org.cn/wqbwc/ldjh/201811/t20181107_69523.html,2018-11-07.
[47]上海对口援滇工作基本情况[EB/OL],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http://www.shzgh.org/node2/node4/n1021/n1023/n1031/u1ai105777.html,2015-06-29.
[48]上海对口帮扶遵义工作情况[EB/OL],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http://www.shzgh.org/node2/node4/n1021/n1023/n1031/u1ai105206.html,2015-06-17.
[49]“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升对口支援成效[EB/OL],玉树州新闻网,http://www.yushunews.com/system/2019/04/01/012844591.shtml,2019-01-15.
[50]北京今后三年帮扶内蒙古增加支持资金近20 亿元[EB/OL],中青在线,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07/10/content_17369751.htm,2018-07-10
The Fight against Rural Absolute Poverty:China’s New Practice of Poverty Reduction
LI Xiaoyun CHEN Banglian TANG Lixia
Abstract:Although th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dopted in current campaign against rural absolute poverty is largely based on previous ones which has been based on“development oriented approach”,the present policies actually were designed to meet the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for reducing poverty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The whole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tackle the remaining rural poverty including the leadership model, poverty reduction approaches and others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constitute new form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approach.
Key Words:Poverty Reduction,New Practice,Leadership Model,Governance Mechanism,Approaches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9)05-0080-12
[收稿日期]2019-07-30
[作者简介]李小云(1961-),男,陕西定边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邦炼(1992-),女,广东潮州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唐丽霞(1979-),女,安徽池州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厚 和)
标签:贫困论文; 精准论文; 中国论文; 贫困地区论文; 工作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