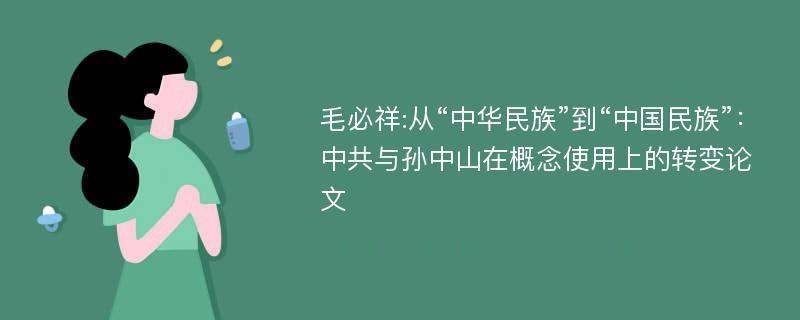
提要: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概念在孙中山的作用之下,逐渐具有了“民族同化”的含义。由于“民族同化”与中共主张的民族自决理论相冲突,所以,1923年11月左右,中共领导层认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始用“中国民族”替代“中华民族”来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而“中华民族”则仅仅指汉族。无独有偶,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为了获得苏俄的援助,也发生了同样的概念转变。在这之后,中共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进行诠释与再建构,使之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然而,孙中山的概念转变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所以,国民党一大刚结束,孙中山即发表民族主义演讲,开始通过灵活的处理方式来排斥世界主义思想,并试图重回民族主义阵营。中共与孙中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其实是双方意识形态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博弈。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苏俄;概念史
“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都是近代中国产生的两个概念。根据黄兴涛教授的研究,它们最初都有表示汉族的意思,只是“中国民族”有时还被用来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随着民国的成立与“五族共和”观念的提倡,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得以形成和确立,并成为表示国内各民族以国民身份平等融合为一大现代民族共同体的符号。[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5、89页。与此同时,“中国民族”概念却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关于这两个概念,中共与孙中山都使用过,而且都先后经历了一个概念转变的现象,在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时,用“中国民族”替换了“中华民族”。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说,“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这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这里的“中华民族”其实是指“中国各民族”的意思。但是,1923年11月左右,中共在正式文件中把“中华民族”换作“中国民族”,并且中共领导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多数都用“中国民族”,而不用“中华民族”。在这之后,中共所谓的“中华民族”,则仅仅是指汉族。无独有偶,1924年后,孙中山也发生这种情况。在此之前,孙中山所谓的“中华民族”是指中国各民族,但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在表达“中国各民族”意思的时候,一改往常的用词习惯,不用“中华民族”,而用“中国民族”。
由于孙中山的概念转变是发生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与中共此前的概念转变是一样的,这不得不令人怀疑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至于二者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其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可惜的是,这个现象,并没有引起学者注意。黄兴涛教授在其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也只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反映中国各民族整体性认同的词汇,除了‘中华民族’一词广泛传播之外,‘中国民族’一词也仍然很常见”,只是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华民族”才成为极度流行的固定词汇,绝对压倒“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164页。没有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一词流行的原因,也没有提到中共与孙中山从“中华民族”到“中国民族”的概念转变。而这个现象,恰恰在黄兴涛教授新著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中华民族’符号认同的强化与深化”两个章节之间,是处于一个过渡的重要阶段,是近代“中华民族”观念演变的重要过程之一。因此,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描”,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华民族”观念演变的过程,而且还能窥察到中共与孙中山在各自意识形态——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在我国输变电工程实际施工中,传统的成本控制方式主要是采用事后控制的方式,然而事后控制对施工成本起到的控制作用微乎其微,要想节省工程成本,就要加强成本的事前控制,要在工程开始之前了解相关资料,对施工成本进行预测和设计。施工企业一般不具备成本控制的能力,也不能对成本有一个准确的预测,过分依赖于个人经验,而没有一个完善的资金使用规划,也不能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施工成本,这就造成在施工过程中资金的滥用和浪费。再加上输变电工程施工过程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在施工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假如在施工前期没有一个合理的成本规划,就无法对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
一、中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
中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与外蒙古独立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外蒙古独立问题始于1911年底,当时,国内爆发辛亥革命,部分蒙古王公以“民族自决”为借口谋独立,沙俄在背后操纵,支持外蒙古独立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俄政府被推翻,北洋政府趁机派兵重新控制外蒙古。1921年7月,苏俄赤军以追击俄白军为由,进入外蒙古库伦等地,扶助成立了蒙古国民政府。[注]转引自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6页。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远东国际新秩序,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外蒙古独立问题,但呼吁保全中国领土,其义不点自明。这得到广州南方政府部分政治家的响应,并提出“归还蒙古”。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呼声,给苏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注]王柯:《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1922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注]这次大会原名为“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原计划于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直至1921年底,苏俄决定将大会改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在莫斯科召开,并以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1月23日,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耶夫针对广州南方政府有人提出的“归还蒙古”问题,进行了攻击。在1月26日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和群众中进步分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采用一种单一的所得税”[注]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1922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基于此,有学者指出,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于中共来说,不仅是在关于民族的思想和理论上直接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一次机会,同时,也面临着外蒙古独立问题必须向其上级(苏俄)表态。[注]王柯:《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第129页。
出席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国代表团39名代表中,其中有14位是中共党员。会议结束后,中共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体会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认为中国“应该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回国之后,他将会议的基本内容“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受。中共中央在1922年6月10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7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具”[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正因为如此,中共二大《宣言》中的“妨害蒙古等民族的自决自治的进步,不会给中国本部的人民带来任何利益”等内容,与大会报告内容的思路都是完全一致的。[注]王柯:《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第130页。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作的报告中,谈到中共将来的计划,其中有一项为“联络各革新党派,作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4页。。毋庸置疑,这是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苏俄)的指示。“计划”的出台,标志着中共承认外蒙古独立运动正式开始。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民族政策。[注]中共二大《宣言》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5-116页。但是,在运动之初,中共仍然使用“中华民族”。例如,中共二大《宣言》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5页。。9月,《向导》创刊,在《本报宣言》谈及“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注]《本报宣言》,《向导汇刊》第1集第1期(1922年9月),第2页。显然,引文中的“中华民族”,是指中国各民族,而且是一个沿用的概念。
所谓的沿用概念,是指民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具有“民族同化”含义的“中华民族”概念。民国成立之后,“五族共和”论开始盛行,并引发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思考,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同源共祖”,提倡“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同化之”,形成“大中华民族”。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基本确立,并广泛传播。[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91-109、133页。从而,“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同化”含义得到强化。
但是,“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同化”含义,在中共发起承认外蒙古独立运动之初,并没有被察觉出来。10月11日,《向导》周刊发表了一篇以“蒙古及其解放运动”为题的文章。文章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世界各弱小民族,大多都压迫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或宰制之下;我中华民族不幸也是这中的一个。本报拟以后多介绍国人关于弱小民族情形或运动的文字,一者俾我们借鉴和参取,二者也可得知一部分世界大势。”[注]记者:《蒙古及其解放运动》,《向导汇刊》第1集第5期(1922年10月11日),第43页。首先,这篇文章是中共所主办的期刊中首次全面而具体的以外蒙古独立为内容。它的发表,说明了陈独秀此前所计划的承认外蒙古独立运动已经开始。但是,相关的概念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改变,而文中所谓的“中华民族”仍然是沿用的概念,是包括蒙古等少数民族,指中国各民族。10月18日,张国焘在《向导》周刊发表《中国已脱离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说:“要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依然存在,他会让民众势力发展和中国民族独立么?”[注]国焘:《中国已脱离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向导汇刊》第1集第6期(1922年10月18日),第50页。文中用的是“中国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而11月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张国焘的另一篇文章《还是赞助新蒙古罢》,开篇就说,“蒙古国民革命党领袖登德布曾有一篇演说,题为‘蒙古及其解放运动’在本报第五期和第七期上发表过,算是极有价值和真切的叙述,很足以沟通中华民族和蒙古族的亲密感情”[注]国涛:《还是赞助新蒙古罢》,《向导汇刊》第1集第8期(1922年11月2日),第67页。。其认为“中华民族”与“蒙古民族”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中华民族”不包括蒙古族等少数民族。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评估在完成跨职业教育(Int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IPE)课程前后药学和护理学生观点的变化;学生复合技能的准确性与保留性分析;多学科沟通课程对护士、药学生和医学生沟通技巧自我效能的影响;逐步开展跨专业在线全球健康课程;学生的自我测试提高了药学课程的表现;在六年制药学博士课程中评估学生的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入门药学实践课程中学生互助教学的评价。关于课堂教学5年来研究的重点是翻转课堂、主动学习以及跨职业教育合作。
而恰恰在张国焘使用“中国民族”之后,1922年11月,中共的官方文献中,也用“中国民族”替代“中华民族”,来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0页。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写到“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称“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注]分别参见《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39、166页。
不过,关于孙中山的概念转变,可以说是孙中山与苏俄、中共之间的“秘密约定”,其他人并不了解详情。否则,对于蒋介石、戴季陶等国民党高层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使用“中国民族”的现象,便无法解释了。[注]蒋介石在1924年之后多数使用“中华民族”,偶尔也会使用“中国民族”,而戴季陶一般只用“中国民族”,不用“中华民族”。
陈独秀大致也在这段时期发生了概念转变。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一般用“中华民族”表示中国各民族。例如,1919年6月8日,其在文章中说,“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1922年9月13日,他指出,“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9月20日,他用“中华民族”解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但是,在1923年5月16日,陈独秀在文章中却用“中国民族”来表示中国各民族,“北京政府如此懦弱昏聩,真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注]分别参见《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1919年6月30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1922年9月13日)、《国民党是什么》(1922年9月20日)、《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1923年5月16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280、286、362页。
可见,中共领导层已经察觉到“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了,而且有意识地将二者区分开来,用“中国民族”来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后来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存在的问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0页。。转变概念之后,中共所谓的“中华民族”则一般是指汉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注]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第49页。
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概念转变完全是一种概念的自觉,而且,在概念发生转变之前,没有专门的文件对此问题作出规定或者说明。这导致中共党内出现概念使用比较随意的现象,或者概念转变滞后的情况。概念使用比较随意的,是以蔡和森为代表;概念转变滞后者,以李大钊为典型。
二、孙中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
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开始频繁地使用“中华民族”。如1919年9月,孙中山在《〈战后太平洋问题〉序》说:“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10月10日,他在《八年今日》中说,“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三民主义》中的“中华民族”不只是名词的使用,更是概念的诠释。文中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的目的也”。[注]分别见于《〈战后太平洋问题〉序》(1919年9月)、《八年今日》(1919年10月10日)、《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132、187-188页。孙中山以“民族同化”来解释“中华民族”,使之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并且占据着一定的话语地位。孙中山这种具有“民族同化”含义的“中华民族”观念于1919年正式形成,一直延续到1923年。[注]郑大华教授认为自1923年到孙中山病逝,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见于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64-69页。黄兴涛教授则认为郑大华教授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就内容而言,孙中山1919-1922年间的民族思想固然有潜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文化上也确有一种明显的汉族中心的优越感,但却很难说他在主观上即认同理念上,已经全然放弃了以往一贯声称的‘民族平等’原则,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143-144页。而笔者认为,郑大华教授所引用的第一则材料是1923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二则是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两则材料时隔一年,而期间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则材料中使用的是“中华民族”,第二则材料中使用的是“中国民族”。所以,相较之下,笔者更认同黄兴涛教授的观点。所以,在这个阶段,孙中山所谓的“中华民族”是指中国领土范围的各个民族在“民族同化”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大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等民族。
2) 教学功能.教学平台支持视频、音频、PPT等多格式课件上传,支持真实翻译项目导入,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可匹配、调用自建的多模态体育类语料库.就教师层面而言,教师用户可以在【课件管理】模块中添加课件,【素材管理】模块中添加素材并且可以将自己的课件与素材分享给学生.同时教师也可以改变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在教学中采取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依托多模态体育语料库大数据平台,从文字、图像、音频以及视频等多维度进行情境教学,从而凸显体育专业特色,促进体育院校专业人才的培养.学生层面,学生不但可以提前预习上课课件与教学内容,还可以利用多模态语料库进行查询与检索,彰显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然而,1923年底“关余交涉”事件发展到高潮,孙中山对外转向苏俄。1923年12月31日,孙中山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上演说,表示“我不再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我的脸转向了俄国”。[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80页。这种对外转向不仅是外交政策的变化,还是意识形态向苏俄作出妥协的开始。所以,在对外转向苏俄之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裂变”。[注]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30页。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发表《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注]《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而1月16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口头报告访苏情形,提出对“联俄”的担忧。孙中山则觉得他“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并对“联俄”充满期待,设想今后“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注]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099页。。
而恰恰在决定“联俄”之后,孙中山也发生了概念转变,用“中国民族”替换“中华民族”来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1924年1月13日,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欲救中国,须提倡民族主义,方能发挥民族精神。中国民族的四万万人,除蒙、满、回、藏等四种人外——不满千万”[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1月23日,孙中山在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宣言,频繁地使用“中国民族”,达5次之多:“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孙中山在这里使用的“中国民族”所指称的对象与之前的“中华民族”并无差别,都是指中国各民族。用“中国民族”代替“中华民族”,虽是一字之“变”,却折射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巨大变化。
孙中山思想与以往的表达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孙中山谈到“中国民族”的时候,会连带着使用“独立”一词,形成“民族独立”之类的话语,而这恰恰是承认国内各民族具有自决权的直接体现。孙中山既在概念上发生转变,又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提出“民族独立”,显然,这与中共的概念转变“路径”则是一致的。且概念转变之后,其中的世界主义思想便“呼之欲出”了。
这种种原因标明,利用Fizpatrick-Pathak皮肤分型来预测MED值是不可靠的,缺乏客观依据。
其次,孙中山除换用“中国民族”,没有直接地表达“民族同化”之外,还提倡民族平等观念。虽然,孙中山在1923年初已有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提法,但他所谓的“大中华民族”仍不免有“民族同化”的影子。而实际也如瞿秋白所说,“也许是逼于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命令”,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才未提“民族同化”问题,而将“国内民族一律平等”写入政纲。[注]《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1928年2月5日-1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毋庸置疑,孙中山的概念转变与中共一样,和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不同的是,中共是自觉的,而孙中山是被迫的。因为孙中山在1922年坚决地表示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认为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或自主权”[注][澳]梁肇庭著,贺跃夫译:《越飞使华及苏俄与孙中山关系的由来》,《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88年第3期,第180页。。苏俄为了改变孙中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看法,在国民党改组之际,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必须接受国内民族自决的原则,不与国内少数民族建立组织联系,也不允许在这些地方使用武力。国民党一大前夕,虽然鲍罗廷与国民党在国内民族自决问题上达成谅解,但由于国民党仍然坚持与国内少数民族建立组织联系,便对国民党进行严厉地指责。[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49-450页;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国民党与中俄交涉(1922-192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8期,第166页。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有关孙中山的概念转变并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明是苏俄与中共的要求,但是根据现有的文本与孙中山行文特征,再结合当时“联俄、联共”的背景,基本可以判断孙中山的概念转变与苏俄、中共是存在一定关联的。而将中共与孙中山的概念转变事件串联起来,基本可以得出整个事件的内在逻辑:中共领导层通过发起承认外蒙古独立运动,察觉了“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同化”含义,认为这与民族自决理论有矛盾之处,并发生概念转变。苏俄为了进一步推进外蒙古独立运动,于是通过共产国际(鲍罗廷)要求孙中山承认民族自决权。恰恰在这期间,中共领导人把概念中的“民族同化”问题向鲍罗廷进行说明,并得到他的认同,然后再由鲍罗廷对孙中山提出换用概念的要求。
至于是谁向鲍罗廷提出建议,其可能性最大的是瞿秋白。因为,一方面,瞿秋白十分了解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当初在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党员中,瞿秋白就是其中一个。会议期间“分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是“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183页。1923年1月,瞿秋白回国之后,与张国焘一样在文章中用“中国民族”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注]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瞿秋白最初使用“中国民族”概念是在1923年1月17日发表的《最低问题》,“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1923年1月17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11页。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宣言》是由瞿秋白翻译的。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张国焘后来也回忆说,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鲍罗廷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的助手和翻译……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292页。。无疑,文本中的“中国民族”是瞿秋白翻译的,而且由于工作关系,瞿秋白与鲍罗廷有日常的接触与交流。所以,孙中山在“联俄”之后多次使用“中国民族”概念,与瞿秋白和鲍罗廷不无关系。除此之外,上文也提到了瞿秋白所说的,孙中山迫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压力没有在《宣言》中将“民族同化”思想表现出来。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孙中山的概念转变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关于鲍罗廷和瞿秋白向孙中山提出转变概念要求的时间,由于史料的局限,目前只能得出一个大致的范围。根据孙中山在1月13日演讲中所用的“中国民族”,再结合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的《三民主义》演讲中使用“中国民族”的规律,可以断定时间下限是1月13日。而时间上限可以定在瞿秋白来到广州的时间,即在1924年1月5日。[注]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所以,孙中山被要求转变概念的时间是在1月5-13日。
2 生物标志物的类型 生物标志物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为检查器官功能或其他身体健康状况而引入生物体的物质,如氯化铷用于同位素标记检测心肌灌注情况;可以是用来表明特定疾病状态的物质,如受到疾病感染时抗体的出现;也可以是特异性细胞、分子或基因、基因产物、酶或激素,复杂的器官功能,生物特性或生物结构等。
新疆秸秆发电的燃料主要以棉花秆为主。作为我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新疆棉种植面积大,分布广,主要棉产地区包括喀什、阿克苏、巴州、塔城、昌吉州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棉花秸秆资源量非常富饶[16]。
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博弈
中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既是为了处理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也是为了使概念达到去除“民族同化”含义的效果,使之与主张的民族自决理论不再冲突。孙中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是在“联俄、联共”的背景下,选择了妥协,接受了苏俄、中共的民族自决理论,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增添了一些世界主义的色彩。[注]关于孙中山所受苏俄意识形态的具体影响,可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页。这在“西山会议派”看来,是“借口民族自决、世界革命,以破坏民族主义”[注]《伪二届中央第三次临时会议》(1927年4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页。。
因此,孙中山发生概念转变之后,中共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理论性的诠释与再建构。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进行了解释,称民族主义是要实现“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世界各民族的平等”[注]《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孙中山逝世之后,中共将1925年3月21日发行的《向导》周报定为“孙中山特刊”,发表了多篇悼念孙中山的文章,而其中也不乏对孙中山作出评论的话语,如“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标帜”。[注]分别见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和森:《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向导汇刊》第3集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第889、895页。从这些评论中可看出,孙中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再有丝毫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而是“焕然一新”地成为了具有世界革命理想的民族革命者,是一个领导中国民族获得自由独立的精神符号。
而在孙中山看来,“联俄”终究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注]李杨:《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97-113页。,意识形态上的妥协,亦是如此。所以,最初在决定“联俄”之时,他也没有顾忌太多,并自信能够从容处理与苏俄、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自国民党一大闭幕,这种思想就表现出来了。孙中山在致闭幕词中说,这次大会是“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1924年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79页。。而在演讲期间文稿、讲话中的很多细节,都流露出孙中山对世界主义思想的排斥心理。
但是,传统线性协整模型仅反映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平均响应,由于条件均值只是概率分布的一个特征,如果希望知道在更多的分布特征上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上述方法则无法胜任。一个改进的办法是在不同的分位点上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基于此,Xiao(2009)应用Koenker和Bassett(1978)的分位数回归方法,提出分位数协整模型(Quantile Cointegration Model)。记εt的τ分位数为Qε(τ),It={xt,Δxt-j}∀j,则对于式(5)中的条件分位数为: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期中共领导人中,最先用“中国民族”表示“中国各民族”的是张国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共产国际指导下关于外蒙古问题所应采取的“民族自决”政策深有体会。由于张国焘当时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比较特殊,“仅次于陈独秀”[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202页。,所以,他意识到“中华民族”概念有不恰当之处后,不仅自己率先换用了“中国民族”,而且很有可能就这个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
因此,神话除了是原始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同时更是一种现实生活的折射,其人物、情节、内容等,也往往会在社会文化沟通及对话的过程中,不停地转化其原有的意涵,或扩大其原有文化范围所赋予的意义范围。
再者,孙中山再次表达“民族同化”思想。一方面,使用“国族”概念,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页。对此,瞿秋白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有一种“精义”,“将满蒙回藏四民族,同化于汉族,以造成中华民国的国族”。而事实上,“这种同化异族的民族主义,实在是民族主义的很呵!”[注]《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1928年2月5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280页。另一方面,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中说:“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孙中山讲这段“民族同化”的历史,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表达被压抑的“民族同化”思想。
其次,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但是,就在当天,孙中山发表《致全党同志书》,其中使用的却是“中华民族”概念,“民族主义亦不止推翻满清而已,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而后可告成功”[注]《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1页。。3月16日,他在讲演中,再次换用“中国民族”来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称“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页。可见,孙中山在概念选择上看似随意,其实不然。在苏俄、中共的要求下,孙中山发生概念转变之后,意识到“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明显区别,且各自体现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思想。基于此,他在两个概念之间进行随机应变地选择,其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抗拒世界主义。
首先,在演讲期间,孙中山虽然一直使用“中国民族”,但是,不再像一大《宣言》中混合使用“国家独立”和“民族独立”话语,去除了“民族独立”,而只讲“国家独立”。[注]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只讲“国家独立”,1924年3月,孙中山在与黄季陆的谈话中说,“现在的情势与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们要谋国家的自由独立”。7月14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对〈中俄协定〉宣言》中说,“本党领有历史的使命,为中国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9月18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说,“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11月10日,在《北上宣言》中又重述了这句话。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观念形成,一方面主张将中国各民族融为一个“中华民族”,另一方面提倡实现国家独立。正因如此,在这种观念下,“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以至于孙中山在1923年1月29日发表的《中国革命史》中说:“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注]《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而且,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提出“国族”概念,而这正是五四运动以来“民族国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其实,依据这个脉络,孙中山在提出“国族”概念之后,可以在“国家独立”与“民族独立”两种话语之间任意选择,但是,他只选择了“国家独立”,其原因就在于“民族独立”是一种世界主义话语。显然,孙中山不讲“民族独立”,表达了他对世界主义思想的拒绝态度。
因此,关于苏俄所强加的世界主义思想,孙中山在心理上并不接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内在理路”,由于双方的思想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矛盾,这使得他对世界主义的拒斥,基本成为主观意愿上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外缘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赤化”谣言的兴起,也是促使他作出这种选择的重要因素。
培训评价阶段:培训教师借助网络技术,采用教师打分法、学员互评法等具有可操作性与与公信力的评价方法给出学员培训成绩,并利用网络平台对成绩进行公布。培训成绩将计入在案,作为学员是否有资格继续接受培训,或者能否获得政府有关乡村旅游扶植补助资金的参考依据。同时,培训学员也要通过网络平台对培训教师进行评价,作为进一步改进旅游院校培训工作的依据。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赤化”的谣言甚嚣尘上,是孙中山所没意料到的。1924年2月间,香港有报纸认为国民党已经“赤化”。对此,孙中山与国民党不得不发布辟谣通告,以洗脱“赤化”的罪名。[注]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赤化”谣言兴起后,国民党“右派”和海外国民党员,更是按捺不住,反对国共合作的情绪犹如火上浇油一样,越发高涨,并多次向孙中山抱怨,请求不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只好解释说,“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成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并劝慰他们要精诚团结,不要再非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事。[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第5200、5218页。虽然孙中山并不认为国民党改组是“赤化”,但是,外界的舆论很容易将其心理防线击溃。慢慢地,孙中山失去了此前的自信,开始对苏俄所强加的世界主义感到紧张了。但是,中俄协定事件的发生,更是加剧了这种心理。
1924年5月31日,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6月23日,部分国民党员方瑞麟、陈古廉等函请孙中山向苏俄抗议,取消《中俄协定》,张继也以该协定质问孙中山。[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第5471页。7月8日,《中俄协定》事件传至广州政府内,只有共产党员额手称庆,其余各方均有反对之意,孙中山则以“此为平常之事”来回应,并“不欲否认该协定”。[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第5517页。出乎意料的是,7月14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对<中俄协定>宣言》,予以赞同。
此时,孙中山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与“联俄”之前有着天壤之别,而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不得不令人怀疑。然而,细查从《中俄协定》的签订到孙中山发文赞同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一系列的细节尤其值得注意。6月25日,《香港华字日报》刊文称,鲍罗廷致电孙中山,希望他为之应声,促成《中俄协定》,早日完成。[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第5472页。7月初,鲍罗廷离开北京,重返广州,与孙中山密订条件。[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第5499页。7月8日,巴甫洛夫在广州考察,得出“军队的弹药武器十分缺乏,经费拮据”的结论,并在当天给苏俄拍了电报,请求立即给孙中山政府运送武器。次日,苏俄领导人做了批示,准备马上启运武器。[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第5516-5517页。7月11日,加拉罕致函孙中山,强调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重要性,并指出国民党所做的工作还不深入。次日,加拉罕又致信鲍罗廷,再次指出国民党在反帝宣传方面做的太少的问题,并希望他敦促孙中山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第5527、5529页。而事实上,加拉罕所谓的“反帝”,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口号,而是世界主义思想的一种表征。[注]正如瞿秋白也认为,反帝运动不仅有民族主义性质,还有“国际主义”意义。而且,中国青年党所认为的“打倒帝国主义……为世界革命(即共产革命)之口号”。参见《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五四——五一》(1924年5月4日),《瞿秋白选集》,第140-142页;曾琦:《蒋介石不敢复言打倒帝国主义矣!》,《醒狮》(1926年9月11日),第100号第1版。
可见,苏俄清楚,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会伤及孙中山与国民党。为了使双方此后的相处不陷于尴尬境地,苏俄给广州政府提供急需的物质,并且,一方面让孙中山平复国民党内甚至是社会各界的反对声音,另一方面让其加强反帝宣传工作。然而,孙中山已经看出了苏俄的阴谋,只是碍于“联俄”的需要,仅以赞同《中俄协定》作为换取苏俄援助的筹码。至于苏俄所说的加强反帝的宣传,孙中山只是在口头上敷衍一番。之后,孙中山的敷衍态度被中共察觉出来,并引起强烈不满。9月13日,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在莫斯科记者谈话时,严厉批评了孙中山及其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在南方的政策至今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注]《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1924年9月13日),《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在这个阶段,或许由于国民党实力还比较单薄,孙中山要将苏俄的世界主义完全抛弃,基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中止“联俄”。另一方面,孙中山仍然觉得苏俄的革命方法有其可取之处,认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否则,中国革命将“断无成就”。[注]《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基于此,在与苏俄、中共的世界主义的博弈中,孙中山容易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处境,既要坚持“联俄”的道路,又要防止来自苏俄世界主义思想的“侵蚀”。所以,在这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博弈中,孙中山从没有正面回击,更没有表现得激进,而仅仅是采取柔性地处理方式进行抵抗。这使得他在这期间所表达观点立场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几乎是处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
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国民党的实力逐渐增强,国共双方因意识形态分歧引起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并逐渐激化,最终走向了分裂。汪精卫在“分共”之后,就明确指出,“分共”不只是“要将共产党分子,从国民党里分出去”,更重要的是,“要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党里分出去”。[注]汪精卫:《分共以后》(1927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内部资料,1979年,第479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强调之下,孙中山一大前的“中华民族”概念能够概念转变之后得到深化。而“中华民族”概念的强化与深化,是孙中山抗拒世界主义思想的延续,其结果也明显,民族主义占得了上风。
违法药品广告一直是个顽疾,长期困扰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赣州市局创新监管手段,在全国首推违法药品广告治理的药品经营企业“扣分制”,对违法产品监督下架、刊播企业道歉声明,效果明显,该局也因此获得全国药品广告治理先进单位。
结语
虽然中共、孙中山的概念转变,都没有最直接的史料来证明是文中所叙述的那般,但是,缺乏直接的史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不存在。固然,有直接的史料作支撑,论证就更具有说服力,并称得上“实事求是”,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只能因循这种方法。清代学者阎若璩说过,“以实证虚,以虚证实”。余英时先生解释说:“‘以实证虚’固是‘实事求是’,‘以虚证实’又何尝非‘实事求是’乎?”[注]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3页。而以上对中共、孙中山在概念转变背后“历史真相”的发掘,正是借用了这种“以虚证实”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关键要素,在于“中华民族”概念在表示“中国各民族”之时所具有的“民族同化”含义。
由于“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同化”含义,导致双方先后发生概念转变,并且,在概念转变之后,双方为掌握各自的话语体系,展开了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对抗。按照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观点来看,中共与孙中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本质上是双方在国民革命运动过程中展开的一场幕后的权力斗争。由概念的含义,转到话语的争夺,再上升到权力的斗争。可见,中共与孙中山在概念使用上从“中华民族”转变到“中国民族”,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替换,一个非常细微的“碎片化”的“历史事实”,但在这“碎片”的背后却隐藏着宏大的“历史真相”。这不仅展现了双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意识形态的互动与博弈过程,而且,通过这个过程,表现的是各自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心灵史”。由于学界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等同视之,使这段“历史真相”几乎石沉大海。而对于这种类似的现象,余英时先生曾有感叹,“今之治史者已渐失昔人对古典文字所必有之敏感性。此诚令人不胜其今昔之感也”[注]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67页。。其实,岂止古代史学界存在这种对文字缺乏“敏感性”的问题,近代史学界又何尝不是呢?
总而言之,从“中华民族”到“中国民族”,不仅是中共“中华民族”观念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阶段,也是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念演变的重要历程,更是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孙中山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互动与博弈,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命运”。
From"ZhonghuaMinzu"to"ZhongguoMinzu":TheConceptualChangebetween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SunYat-Sen
MaoBixiangJiangXianbin
Abstract: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n Yat-sen, the concept of "Zhonghua Minzu" gradually formed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assimilation". Since "national assimilation" conflicted with the theory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dvocated by the CPC, the CPC leadership, after recognizing this problem, began to use "Zhongguo Minzu" instead of "Zhonghua Minzu"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around November 1923. And then the so-called "Zhonghua Minzu" generally referred to the Han nationality. Coincidentally, during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Sun Yat-sen also experienced the same conceptual change in order to obtain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Russia. Later, the CPC interpreted and reconstructed Sun Yat-sen's nationalism, making it cosmopolitan. However, Sun Yat-sen's conceptual change was only an expedient measure. After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Sun Yat-sen issued a nationalist speech and began to reject cosmopolitanism through a flexible approach and tried to recover his nationalism. The change in the use of concept between the CPC and Sun Yat-sen was actually a game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respective ideologies of the two sides.
Keywords:Zhonghua Minzu;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n Yat-sen; 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Soviet Russia; conceptual history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3.007
作者简介:毛必祥,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蒋贤斌,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责任编辑:黄 秀
标签:中国论文; 民族论文; 苏俄论文; 中华民族论文; 概念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