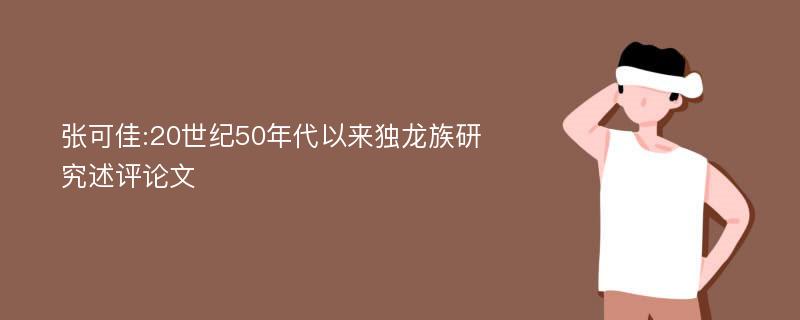
[摘 要]聚居于滇西北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作为为数不多的“边疆”“直过”“人口较少”民族,历来以其独特的地理、生态与人文而备受关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70年来关于独龙族的学术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通过对不同时期学者聚焦的源流与民俗、原生与传统、多元与融合、变迁与发展等主题内容的研究述评,呈现独龙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步入现代发展转型的历程。
[关键词]独龙族;独龙江;扶贫攻坚;整族脱贫
独龙族,旧称“俅人、曲人”,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流域,独龙江乡是其主要的聚居地。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为数不多的“跨境”“直过”和“人口较少”民族,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怀下,独龙族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性跨越”。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持续推进下,成为云南省率先实现“整族脱贫”的“直过”民族,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独龙族的发展繁荣与党和国家历来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怀、支持密不可分,也和学术界的研究关注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独龙族的研究体现出其特有的阶段性与时代性特点。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独龙族社会历史全面调查,聚焦独龙族的族源、传统社会与经济形态,奠定了独龙族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研究队伍逐步扩大,研究主题也更加多元化。1999年随着独龙江公路的贯通,外界关注力度加大,独龙族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21世纪开始,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反思独龙族社会发展的变迁和他们适应外部社会环境变化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问题意识。尤其是2010年至今独龙族研究持续增长,独龙江流域“扶贫攻坚与全面小康”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通过学界在不同时期对独龙族研究专题的综述与探讨,呈现独龙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步入现代发展转型的历程。
一、关于独龙族族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曾多次组织民族研究领域专家和民族工作者组成调查组,对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提供支持与保障。在这一背景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开展的对独龙族社会历史的全面调查及相关成果的陆续出版,奠定了独龙族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了独龙族社会在“直过”前的方方面面,成果非常丰硕。紧扣“直接过渡”与“民族识别”,这一阶段的研究焦点在独龙族的源流、社会发展阶段及经济形态。独龙族的族源成为了早期独龙族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在族源问题上,学界普遍认为独龙族先民属氐羌族群,肯定独龙族是云南境内怒江、独龙江一带定居的最早居民之一。有研究指出独龙族的先民族属与古代昆明族有关 ,[1]是从路蛮分化出来。[2](P11)有学者指出独龙族与怒族同源,[3]与僜人、景颇族同属氐羌族群。[4]高志英指出对于两个同源于古代氐羌系统且又长期共同居住于同一地域内的独龙族和怒族,需要综合论其源流。[5]刘达成通过对唐樊绰《蛮书》里所记载居住在察隅一带的“僧耆部落”或“侏儒民族”之地理分布、生产生活习俗的分析,指出其应当是今天独龙族和俅人的先民无疑。[6]21世纪初期,利用基因研究的最新成果来分析族群的起源在中国开始兴起。有学者结合遗传学的基因分析对独龙族的族源进行多重证据考究。周大鸣等通过对独龙族的基因分析,结合古羌人相关的藏、彝、白、哈尼、普米、景颇、拉祜族等的基因特征,推测独龙族的祖先和古羌人有渊源关系。[7]学界对独龙族源流的研究揭示了独龙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重要一员,是生活在滇西独龙江、怒江流域一带古老的居民之一。
二、独龙族的社会经济形态及语言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民族识别”,独龙族这一族称于1952年正式确定,由“半奴隶制半封建制社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跨越”。这一阶段紧扣“直接过渡”主题,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形态成为了早期独龙族研究的另一大重要论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范式,多数学者认为在“直过”前,独龙族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家庭公社逐步解体阶段。[8](P79)强调其社会形态属于父系家族公社晚期。[9]有学者指出独龙族社会处于家庭公社制与农村公社制之间的过渡形态。[10]在经济形态上,私有制及土地所有制(共耕制)成为了研究的重点。田继周指出由同一家族成员或具有姻亲关系的人组成的共耕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家族公社没落并向农村公社过渡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所决定的,强调共耕组占有和使用的土地不是私有而是家族公社所有。[10]许鸿宝认为独龙族的共耕关系主要是公社公有共耕及家族成员伙有共耕两种类型。[11]刘龙初则认为独龙族土地所有制形态经历了公有、伙有和私有三个阶段。[12]总之,在独龙族家庭公社基础上形成的“伙有共耕”反映了独龙族传统社会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制特点。而个体私有的形式也揭示了这一时期在私有制影响下“原始共产”制的逐步瓦解变迁。相关研究呈现了“直过”前独龙族传统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形态,也从中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龙族从最短的时间内由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开启崭新的发展历程。
独龙族的语言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早期的独龙语研究偏重于语言系属、语法词汇的研究。以语言学家孙宏开的《独龙语简志》为代表,对独龙族语言系属、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土语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呈现。他指出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景颇语比较接近,有划为同一语支的可能。[13](P2)后期学界则偏重对语言使用现状(母语能力)、语言生态、适应性变迁及比较研究,关注社会发展变迁中母语的掌握[14]和适应能力。[15]独龙族的教育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早期(20世纪90年代)的独龙族教育研究主要针对原始教育概况。陶天麟指出独龙族的原始教育与其生产生活融为一体,“皆木玛”与“皆木巴”皆是其最早的、相对固定的教育场所。[16]后期(21世纪初期至今)学者则对独龙族基础教育现状、乡村教师需求现状、教育均衡、双语教育进行专题研究。有学者对独龙族教育从原始、传统步入现代教育的变迁与适应进行了关注。高志英对20世纪独龙族的教育形式、教育观念从传统到近代学校教育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过程的回顾,探索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及其观念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存在的问题。[17]杨舒涵阐述了当前独龙族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强调教育在独龙族脱贫攻坚中的贡献,以教育发展筑牢独龙族脱贫致富的根基。[18]
三、独龙族传统习俗
在早期对独龙族社会历史全面考察基础上出版的一系列成果中,独龙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涵括其中,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呈现。20世纪末开始至今,独龙族文化专题研究成为热门,其中以李金明《独龙族文化大观》[19]与张桥贵的《独龙族文化史》[20]最为系统综合。张劲夫、罗波的《独龙江文化史纲:俅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则从生计活动、社会身份、族群关系等方面来阐述独龙族人与周边民族、中央政府建立和维持的多重动态关系。[21]学界对独龙族的习惯法、婚姻家庭、传统价值观、伦理观、禁忌文化等进行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独龙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传承与发展得到普遍的关注。杨文杰指出独龙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塑造了独龙族体育文化“水火交融”的特质,与中华民族传统“刚柔并济、内方外圆”等儒道文化和心理品质有着异曲同工的契合。[22]在文化研究中,独龙族的“文面”(又有称“纹面”)习俗尤为突出,得到了学界长期、普遍的关注。其中“文面”习俗动机与文化功能是研究重点,有包括美饰说、巫术说、图腾、标识说以及“为防止女性被异族抢掳为奴而强制文面说”[23]等诸多观点。高志英等学者认为“文面”是当时澜沧江、怒江流域多个族群久已有之的共有文化现象,尤其是与贡山北部怒族共享的区域文化,后仅在封闭于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中保留下来。[24]独龙族的文面习俗,应被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区域文化特征的延续和变化的过程。刘军也提到,文面习俗在独龙族村寨分布不均现象体现了特定时期民族间的互动与交往因素。[25]独龙族“文面”这一文化现象反映了特定时期民族互动关系网络,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独龙族文化的多元、融合特征。
在文化研究中,独龙族的文化互动与交融也成为关注热点。独龙族与周边民族,尤其与同是边疆“人口较少民族”怒族间的归类、比较研究较多。思索主流与边缘、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张驰、交融与互动,以及对独龙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意义。多民族互动关系如“族际通婚”“区域文化认同”等议题也成为探讨热点。赵沛曦等提到,族源、居住地域、文化生态等的共通性使得独龙族与周边的怒族、傈僳族等呈现出文化整合与区域文化认同现象,在长期的交流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多民族共生共荣、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26]张跃等也肯定了外来文化在独龙族生活地域本土化过程以及多元文化从排他性冲突到包容性并存并形成新的文化认同的过程。[27]相关研究呈现了独龙族与周边民族和睦共处、共生共荣的现实情境,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观念的形成。
四、独龙族变迁与文化传承、保护问题
事实上,为了提升本地患者的就医体验,区域内的医院也确实需要适当协调。经过一番国内外调查研究,医院管理层认为,这其实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最好是有一个公共载体,人人都使用,也可以跨院使用”,才能节约社会资源。
进入21世纪,对独龙族社会来说,传统与现代交互的时代特征日益突显,学者的研究视角聚焦到“变迁”问题上。学界针对独龙族生计方式、生存发展、教育、语言生活、传统文化、人地关系与聚落空间等的变迁与适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专题探讨。高志英研究了被高黎贡山阻隔的独龙江流域独龙族社会文化在20世纪以来发生的诸多变迁,指出传统因素及价值观念在不断受到冲击或否定的同时萌生、发展了与现代化变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28](P552~583)亦指出在独龙族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与外界主流文化之间,外源性发展动力与民族主体性作用发挥之间”存在的张力。[29](P269)郭建斌对独龙族村庄近60年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研究,围绕独龙族社会“制度变革、经济改革、体制改造”这三大重要事件分三阶段进行论述,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呈现“中心—边缘”的议题。[30]周云水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探讨了独龙族生计模式变迁与文化适应问题,指出传统文化对新的制度环境的适应障碍,提出应充分利用独龙族传统文化的拉力,使其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观点。[31]罗波将独龙族的生存变迁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联系起来,以考察变迁动力。[32]
(1)通过合理双切向入口和适当旋流速度设计,产生更大的旋转速度,离心加速度更大,旋流更为稳定,有利于气泡和油滴相互作用,加速气泡和油滴向旋流中间区域聚结,提高气浮效果,缩短停留时间,结构设计更为紧凑。
在对“变迁与适应”的思考之外,“如何保护”也成为了学者的关注热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关于生态资源,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的研究成果,表达了对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独龙族传统文化前景堪忧及文化自信与认同淡化危机的思虑,并积极探索保护与发展举措。独龙族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深厚的传统文化和重要的战略地位。20世纪90年代,何大明、李恒团队以跨学科方式对独龙江、独龙族的社会经济与资源开发进行了详尽调研后形成《独龙江和独龙族综合研究》,使得独龙族聚居区的自然生态资源与生物多样性得到全面呈现。[33]学者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中自然资源的流失与生态的破坏,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生活方式转变、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困境等,提出需要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构建基于独龙族文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并积极探索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总之,学者的研究从总体上呈现了独龙族传统社会在一系列“外源性动力”驱动下逐步融入外界与主流的过程,亦凸显了这一过程中变革与适应的种种张力,带出发展、变迁与保护议题。
五、独龙族发展与扶贫攻坚问题
作为边疆、特少、“直过”民族中社会制度跨越式发展的典型,独龙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历来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作为一个深居跨域峡谷的山地民族,独龙族与外界的交流互动与“路”密不可分。郭建斌指出,1960年是独龙江地区交通变化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建成贯通贡山县城与独龙江的人马驿道,成为独龙江连接外地最便捷的通道。[34](P7)而1999年独龙江公路的正式通车,被视为独龙江地区近60年来最重大事件之一及独龙族社会的第三次突变期。[35](P55)2014年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贯通,标示着独龙族与外界的交流互动进一步加强,对独龙江地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体现了政府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2018年底,独龙族从整体贫困实现了整族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2.63%,在住房、交通、教育、网络、医疗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3.1 加强协会建设,完善中介服务。加强种苗行业协会建设,建立健全各级林木种苗协会或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其在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协调、行业代表等方面的职能。行业协会要以当地龙头企业为中心,通过签订合同等方式,规定各方权利和义务,吸纳小型种苗基地和个体育苗户成立本地区的种苗协会或种苗合作社,收集对本组织有用的技术、市场、法规、政策信息,为组织自身及其成员使用。
在国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关注。云南省人民政府于2010年全面启动“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政策,“扶贫攻坚与全面小康”成为党和政府为独龙族铺垫的新时代新任务,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焦点。2010年开始至今,关于独龙族的研究文献呈持续性增长态势,“扶贫致富”成为了主要的关注主题。新闻媒体报道亦明显增多,如2015年“独龙新闻”中出现了16条与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的报道。相关研究探索剖析了独龙族的贫困现状、致贫因素,指出自然地理、区位、民族传统、观念意识等致贫因素复杂交织。[36]素质型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发展的内生性不足等导致扶贫任务繁重艰巨等。围绕独龙族的扶贫政策,尤其聚焦“精准扶贫”进行研究剖析。研究肯定了党和国家的帮扶政策促进了独龙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在衣食住行、教育及基础设施建设、媒体通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被媒体誉为“独龙江模式”。[37]但同时也反思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积极探索精准扶贫实践中更有效的模式。扶贫开发带给独龙族的是经济社会的巨大跨越。有研究指出,这一跨越并非仅仅是“外源性动力”的驱动性变革,而是在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下以及在独龙族自身“内源性”动力交互作用下实现的。[38]
六、结语
通观国内学界对独龙族的学术研究,以丰硕的成果从整体上呈现了独龙族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文化、信仰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在不同时期又基于源流与民俗、原生与传统、多元与融合、变迁与发展等主题焦点,呈现了独龙族社会文化特点及在新时代的发展变迁。总体说来,相关研究揭示了独龙族先民属氐羌族群,是云南境内最早居民之一,是中国56个民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独龙族文化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养在深闺无人识”,也不是“宛然太古之民”与世隔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在与历代中央政权的互动联系中产生了民族、国家意识。在与周边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区域性、多元性和融合性的文化传统,其文化认同中叠加了区域认同,国家认同中积淀了共生共荣、多元一体的观念意识。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中又不断地融入外界、融入主流、融入世界。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怀下、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持续推动中成为了云南省率先实现“整族脱贫”的“直过”民族。与国家、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连为一体,真正迈入经济社会的巨大跨越,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独龙族在新时代的发展变迁亦为未来的独龙族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思考议题。
[参 考 文 献]
[1]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2]编写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初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3]刘达成.《蛮书》的滇藏古道与“僧耆”“侏儒”的族属[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4]杨毓骧.藏彝走廊僜人、独龙和景颇的族体初探[J].民族调查研究,1985(1,2).
[5]高志英.独龙族、怒族源流考略[A].云南大学历史系.史学论丛[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6]刘达成.寻根溯源“释”独龙[J].大理学院学报,2009(9).
[7]周大鸣,梅方权.多重证据法与族源研究——以中国西南族群生物遗传多样性与区域文化研究为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8]编写组.独龙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9]吕光天.论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在民族学中的地位和作用[J].民族学研究,1981(2).
[10]田继周.略论独龙族、怒族、佤族和傈僳族的共耕关系[J].云南社会科学,1983(6).
[11]许鸿宝.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中间阶段——略论云南怒江少数民族的土地伙有共耕制[J].民族研究,1981(3).
[12]刘龙初.略论怒江地区土地制形态及其演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13]孙宏开.独龙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14]王晋军,黄兴亚.独龙族中小学生母语能力调查及对策研究[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2).
[15]覃丽赢.小茶腊独龙族语言生活的适应性变迁[J].贵州民族研究,2015(11).
[16]陶天麟.独龙族的原始教育与学校的产生[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17]高志英.20世纪中国边疆“直过”民族教育观念变迁研究——以云南独龙族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3).
[18]杨舒涵.独龙族:整族脱贫的教育典型[J].中国民族教育,2019(5).
[19]李金明.独龙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20]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21]张劲夫,罗波.独龙江文化史纲:俅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
[22]杨文杰.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圈特质剖析——以独龙族为例[J].前沿,2012(2).
[23]褚潇白.记忆·对话·真理性意味——由独龙族文面习俗研究现状引发的困惑与反思[J].云南社会科学,2007(5).
[24]高志英.独龙女文面的图案阐释与文化建构[J].民族研究,2015(6).
[25]刘军.独龙族文面初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26]赵沛曦,张波.独龙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27]张跃,舒丽丽.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怒江峡谷丙中洛地区民族宗教文化关系的变迁[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8.
[28]高志英.独龙族社会文化与观念嬗变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29]高志英.文化传统、国家力量与边疆人口特少民族社会发展——以云南独龙族、莽人为例[A].宋敏,主编.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区域民族卷(2010)[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30]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31]周云水.小民族的生计模式变迁与文化适应——人类学视野中的独龙族社会结构变迁分析[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32]罗波.关不住的门——19世纪90年代以来独龙江流域独龙族生存变迁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3]何大明,李恒.独龙江和独龙族综合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
[34]郭建斌.路与时空政治——以独龙江为个案[A].“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8):传播媒介与社会空间论文集[C].上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8.
[35]何大明.高山峡谷人地复合系统的演进[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36]谢屹.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贫困问题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37]杨艳.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8.
[38]杨艳.应变与思变: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J].青海民族研究,2017(3).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Dulong Ethnic Group since 1950s
ZHANG Ke-Jia
(Institute for Ethnic Studies of Sichuan Province,Chengdu610036,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few ethnic groups with a small population living in frontier areas and straightly entering socialism from a semi-slavery semi-feudal society,the Dulong people along the Dulong River Valley in northwestern Yunnan Province have alway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or the unique geography,ecology and humanities that they are endowed with.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Dulong ethnic group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Through analyzing the research themes focused by scholars in different periods,such as origin and folklore,aboriginality and tradition,pluralism and integration,as well as changes and development,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process of Dulong people's gradual development from being closed to being open,from singleness to pluralism,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Dulong ethnic group;Dulong River;poverty alleviation;poverty alleviation of the whole ethnic group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4-0106-06
*收稿日期2019-06-20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袁晓文][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张可佳,四川宜宾人,博士,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宗教理论。四川成都,邮编:610036。
标签:独龙族论文; 民族论文; 文化论文; 云南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