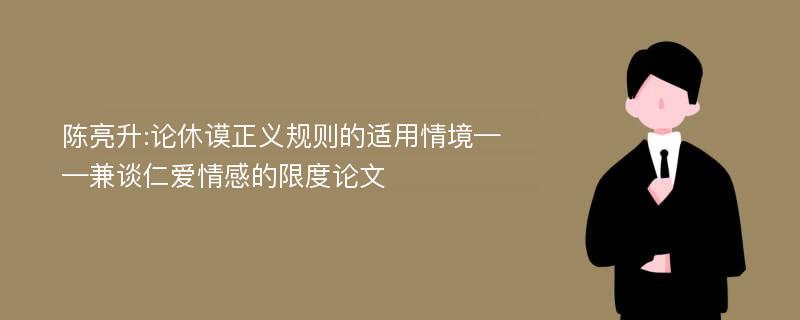
[摘 要]休谟在其道德哲学中建构了一种正义规则理论。然而,对这一理论的互利论、博弈论和契约论解读却让休谟的主张陷入争议——正义规则与仁爱情感如何相容?为了澄清争议,有必要考察正义规则的适用情境。休谟对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的区分表明一切合乎德性的行为可能发生于两类情境:“总体的行为规划或系统”与“单个的行为”。在前一类情境下,人们的仁爱情感是天然有限的,且不足以补救他们在财物占有中的贪欲。人们要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就须制定并遵守正义规则。在后一类情境下,仁爱情感仍然不可或缺。休谟在正义规则理论中论及仁爱情感的限度,其用意不在于彻底排斥仁爱情感,而是基于特定的情境要求,悬置它的作用,为正义规则的运用保留地盘。
[关键词]正义规则;仁爱情感;自然德性;人为德性;适用情境
对于休谟在其道德哲学中建构的正义规则理论,一些研究者们或将其解读为一种互利论(theory of mutual advantage),抑或把它视作一种博弈论(game theory)或契约论(contract theory)。然而,这几种主要解读方式却让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陷入争议。如果正义规则的建立和运行得益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博弈或者说契约,那么这样的人为规则又如何与休谟道德哲学中论及的自然的仁爱情感相兼容?本文认为,若把正义规则本身所适用的情境考虑进来,上述争议其实是可以得到澄清的。不仅如此,休谟正义规则理论中有关仁爱情感限度的论述也能获得更好的理解。为此,本文将考察休谟正义规则所适用的行为情境,以期阐明人为的正义规则和自然的仁爱情感在休谟道德哲学中的相容性。正文一共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笔者将梳理休谟有关正义规则的理论;第二部分将评述学界由解读休谟正义规则理论而引发的争议;在第三部分,笔者尝试从正义规则适用的特定情境对争议做出澄清。
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是对基本建设项目竣工结算编制,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计监督和评价的过程,工程审计是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建筑项目管理水平的内在动力,是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重要保障。
杠杆是能转动的棍子或板子,也可以是合页,它转动的中心点叫作“支点”。跷跷板就是一种杠杆。我不能用胳膊抬起罗克西,但我可以用跷跷板抬起它。其他杠杆可以帮助你把东西移动得更快或更远。
一、休谟道德哲学中的正义规则理论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有关正义问题的探讨占据着重要地位。按照研究者的看法,休谟对正义问题的哲学关注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正义是如何体现为德性的;另一方面,正义是如何体现为规则的[1](p80)。为更好地理解休谟的正义观,此部分将主要梳理正义在休谟那里是如何体现为人为的财产权规则的。
依休谟之见,人们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源于人的自私[2](p536,565)。人的自私和利己心的产生与人性的某些特点以及外物的状况有关。就人性的某些特点而言,每个人所具有的仁爱都是有限的,很少超出与他们最接近的亲朋好友和相识之外[2](p570,641)。在人们的原始心理结构中,最强的注意力都是专限于自身,次强烈的注意力才扩展到亲戚和相识,而到了陌生人那里,往往就只有最微弱的注意力。休谟认为,这一点从日常经验也能观察到。就外物的状况而言,外物并不总是无限丰富地给予人的,相对于人的需求来说,其供应总是显得稀少。不但如此,外物即便被人们通过勤劳和幸运所获取,也有容易发生转移的特点。一个人很可能通过暴力或欺诈等手段,把他人通过勤劳和幸运获得的财物占为己有[2](p524)。当上述的人性特点与外物状况相结合时,就会刺激起人的自私之心,使他们不可能不在占有财物的活动中区分“你的”和“我的”。休谟甚至说,在占有财物方面,人都有一种为自己和为与自己相接近的亲友获取财物和所有物的“贪欲”(avidity)。这种贪欲不仅是“普遍的”(universal)、“永久的”(perpetual)、“难以满足的”(insatiable),而且还是可能“直接摧毁社会的”(directly destructive of society)[2](p528)。正因为如此,如果任由人的贪欲横行而不设任何预防,那么势必会造成巨大的不便。用休谟的话说:“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入野蛮和孤立的状态。”[2](p534)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状态,人们不得不寻求补救的措施,这便有了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
如果说休谟从自私的层面阐述了人们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那么休谟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人们出于自私的原始动机而建立的正义为何要体现为人为的规则。对于休谟而言,正义既然作为补救性措施,必须能够对人身上可能危及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缺点予以有效的约束和调节。那么正义可能体现为某种自然的原则或情感吗?休谟对此持否定的看法。他说:“人类心灵中任何感情都没有充分的力量和适当的方向来抵消贪得的心理,使人们戒取他人的所有物并借此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合适的成员。对于陌生人的仁爱是太微弱了,不足以达成这个目的,至于其他情感,则它们反而会煽动这种贪心。”[2](p528)正因为凭借心灵中内在固有的自然原则或情感难以实现“使人们戒取他人的所有物并借此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合适的成员”这一目标,所以正义必须体现为与自然原则或情感有别的举措。依休谟之见,要达到使人自觉戒取他人所有物并使社会得以维系的目的,人们除了以缔结协约的方式制定有关财物占有和转让的规则之外,别无他法。休谟说:“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所缔结的协议,使那些外物的占有得到稳定,使每个人安享地凭幸运和勤劳所获得的财物。通过这种方法,每个人就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安全地占有的,而且情感的在其偏私的、矛盾的活动方面也就受到了约束。”[2](p526)
鉴于互利论、博弈论和契约论的解读使正义规则面临的指责,休谟的辩护者们试图指出休谟道德哲学中除了正义规则理论以外,其实还包含有其他重要成分。乔伊·索尔特(Joy Salter)就曾表示,以互利论去解读休谟的正义规则论并不能完整地呈现休谟的伦理意图[12](p302-321)。对于博弈论的解读片面性,威廉·克莱恩(William Kline)曾如此评论道:“通过进一步分析休谟的正义理论,就会发现博弈论的推理可能仅是休谟伦理学的一部分而已。”[13](p163-174)事实上,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除了有关正义规则的论述外,还包含有关仁爱和利他主义的论述①对此详见Rudolph V.Vanterpool.Hume on the“Duty”of Benevolence,Hume Studies[J].1988,14(1):93-110.Robert J.Lipkin.Altruism and Sympathy in Hume's Ethics,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7,65(1):18-32.Thomas Huff.Self-Interest and Benevolence in Hume's Account of Moral Obligation,Ethics[J].1972,83(1):57-70.Evander B.McGilvary.Altruism in Hume’s Treatis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J].1903,12(3):272-298.。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就曾批判单纯自爱的原则,也明确反对自私论的道德体系。仁爱和利他主义的行为在休谟道德哲学中完全能够得到支持[14](p18-32)。里科·威茨(Rico Vitz)就曾认为,尽管休谟在谈论正义时一再提及人们对陌生人仁爱的有限性,但是无论在《人性论》,还是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都一以贯之地认为仁爱的动机可以超出一个人的家庭、同胞或朋友这类狭小圈子之外[15](p271-295)。一个人的仁爱就其可能性而言,完全能够扩展到任何感性的生物上,只要其处境与我们足够接近并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而,不能因为休谟在其正义规则论中论及仁爱的限度,而忽视他的思想中同时包含的对仁爱情感可能超出“狭小圈子”的论述[16](p261-275)。
因而,从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中我们可知,人们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并非仁爱情感,而是自私。又由于人的心灵中没有任何自然的情感(包括仁爱)或原则足以抵消人们在财物占有方面的贪欲,所以人们所建立的正义必须对稳定的财物占有、根据同意转让所有物和履行许诺做出规定,也即是体现为以财产权为核心内容的人为规则。
二、正义规则与仁爱情感如何相容?
休谟道德哲学中所建构的正义规则理论在学界一直备受关注。一些学者在解读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视角:互利论、博弈论和契约论。然而,这些解读却把休谟的主张推向一种充满争议的境地。另有一些研究者则指出,一味地突出正义规则建立和运行中的互利、博弈或契约因素,不仅会让休谟的理论极易受到指责,而且还可能忽视休谟道德哲学中的其他重要部分,譬如对仁爱情感和利他主义的论述。在这一部分,笔者将评述学界由解读休谟正义规则理论而引发的争议。
对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比较常见的解读视角是互利论。依照互利论的解读,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本身可以看作一种极为典型的互利论。休谟有关人只具有有限仁爱的论述主要是为了突出利益的互惠性(mutuality of interests)在建构正义规则中的决定性作用。布赖恩·巴里(Brian Barry)曾指出:“依照休谟的看法,财产权制度所依赖的唯一基础只可以建立于互利之上。”[3](p163)与布赖恩·巴里的解读相似,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认为休谟正义规则理论背后的基础是互利。但是,努斯鲍姆并不以欣赏的眼光看待这种互利论的正义理论。在她看来,如果人性中的仁爱等自然情感因其有限而无益于建立正义规则,以至于必须诉诸互利原则才能达到维系社会的目标,那么这似乎也就暗示了我们不必同社会中那些较之于一般情况更弱的一类人开展协作。一个人在身体或心灵上愈是羸弱,他愈是不大可能成为政治社会的一部分,也难以成为建构社会正义的主体[4](p61)。对此,艾伦·布坎南(Allan Buchanan)也持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休谟作为互利性的正义(justice as reciprocity)根本上有赖于人的谋略能力(strategic capacities)。这种能力看似是一种与他人协作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损人的能力(capacity to inflict harm)。尤其是在讨价还价的商业竞争行为中,那些不能对他人构成损害的人实际上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别人值得商讨的[5](p227-252)。
从学界对休谟正义规则理论所做的互利论、博弈论和契约论解读以及对休谟道德哲学中仁爱、利他主义等方面的辩护中,我们可以发现三种解读视角所引发的争议点既非正义规则的建构主体究竟包不包括弱势群体,又非人的仁爱情感到底能否由熟人圈拓展到陌生群体,而是休谟在正义规则理论中论及仁爱情感的限度,为何却在正义规则理论之外又强调人的仁爱情感是可以扩展的。换言之,真正富有争议的地方在于人为的正义规则与休谟道德哲学中自然的仁爱情感到底是如何相容的。笔者看来,如果将正义规则本身所适用的情境考虑进来,那么上述争议便有可能得到澄清②虽然已有学者对正义的情境作了研究,但是笔者发现既有研究主要是考察了正义作为规则而产生的环境,即外部世界的相对匮乏和人的有限慷慨,而没有涉及正义作为规则产生之后所适用的行为情境。对此可见Andrew Lister.Hume and Rawls on the Circumstances and Priority of Justice[J].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2005,(26):664-695.Simon Hope.The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J].Hume Studies,2010,36(2):125-148.Adam J.Tebble.On the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2016,(9):1-23.。
除了上述两种解读视角之外,对休谟正义规则论的解读也被纳入契约论的视角下。基于这一视角,休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正义的基本含义是对社会契约的遵守和维护,而社会契约是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避免社会冲突的基本保障……正义和非义是相对于社会契约而言的,离开社会契约也就无所谓正义。”[8](p75-80)契约论的解读还认为休谟之所以认定正义需要体现为以财产权为核心内容的规则,乃是因为他明智地意识到人们对利益规约的兴趣。“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他的思想是契约论的,因为社会契约的本质是基于约束利益的互利上。”[9](p3-38)总的来说,契约的解读与互利论和博弈论的解读实质上大同小异。它们都认同正义规则的产生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人们心中自然的仁爱情感在此过程中没有发挥实质作用。
三年如同三个世纪一样长。我无数次梦到米米,梦到一浩,梦到哥哥张天明夫妇的甜沫和油条。在上大学以前,我所有的早餐都是甜沫油条。我从五岁就跟着卖甜沫油条摆水果摊的张天明夫妇长大,我们住在芙蓉街有八家住户的大杂院里。父母在记忆中已经面目模糊。从跨进牢狱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思念哥嫂的甜沫油条,像思念米米一样一刻不曾停止过。
尽管互利论、博弈论和契约论的解读也都能从某种程度上展示正义在休谟那里为何体现为规则,但是上述三种解读方式却让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陷入争议之中。经由这些解读后,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被呈现为一种有疏漏的理论。对此,从上文中努斯鲍姆和布坎南的互利论解读中就可见一斑。更进一步说,如果休谟的正义规则论完全可以归为一种互利论、契约论抑或是博弈论,那么这就意味着,若要求人们对老弱病残以及处在危困中的人们尽服务的责任,就成了一种超出责任范围之外的过分要求。正如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所指出的:“如果他人没有什么可提供给我们,或是绕开他们的决定或要求,我们就不能取得一些东西,那么严格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他们正义的义务。”[10](p165-170)如此一来,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就极易被人们批评为“无情的道德冷漠主义”(callousmoral indifferentism)[11](p93-110)。
在说明人们所建立的正义并不体现为某种自然的情感或原则,而是体现为人为的规则后,休谟还论述人为的正义规则是以财产权为核心内容的。对休谟来说,当人们明确正义起源于人为的措施,由此推论出财产权的起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休谟自视这种论证财产权的进路与先前自然权利论者们的做法不同。自然权利论者们往往不事先说明正义的起源,就贸然使用财产权、权利或义务等概念,这在休谟看来犯了极大的谬误,不可能在坚实的基础上进行推理[2](p527)。在休谟那里,财产权并不被理解为天赋的自然权利,而是“依据正义规则或人类协议而得来的一种稳定占有”[2](p542)。这就意味着人们要想享有财产权,就必须通过正义规则对“稳定的财物占有”和“根据同意转让所有物”做出明文规定。有了这两条基本规则,人们对外物的“占领、时效、添附和继承”才有切实保障。除了上述两条基本规则之外,人为的正义规则还要保证陌生人之间的互尽义务得以可能。因为人们对与自己不相熟的人往往只具有有限的仁爱情感,所以陌生人之间要达成互助合作原本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陌生人之间常常会因为利益争夺而做出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不义之举。休谟说:“人们不容易被诱导了去为陌生人的利益而做出任何行为,除非他们想要得到某种交互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只有通过自己做出有利于别人的行为才有希望可以得到……我们如果只是顺从我们情感和爱好的自然途径,我们便会很少会由于无私的观点而为他人的利益做出任何行为,因为我们的好意和仁爱天然是很有限的。”[2](p555)鉴于此,为了使陌生人之间的互相服务得以顺利开展,就同样需要借助人为规则的力量。休谟认为,这种力量源于“许诺的约束力”(obligation of promises)。许诺属于人为的发明物,以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2](p555)。对许诺约束力做出规定的正是正义的另一条基本规则——履行许诺。
在互利论的解读视角之外,还有研究者对休谟的正义规则论持博弈论的解读。在这种解读视角看来,休谟所论述的正义规则起源情形类似于“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当人们身处巨大的不便时,他们所能想到的出路不是如何仁爱地相处,而是如何寻求最有效、最一致的手段以使处境得到改善。因为不清楚他人心怀的意图,处在巨大不便状态中的人们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仁爱情感。安妮特·贝尔(Annette Baier)鉴于休谟在其著作并没有提及任何针对不履行责任的惩罚,因而并不认为休谟所谓的人为协约本身蕴含“囚徒式困境”。但是她仍然将人们不施仁爱,而选择制定正义规则的做法视作一种“保险型博弈”(assurance game)[6](p233)。另一位博弈论的解读者——彼得·范德施拉夫(Peter Vanderschraaf)曾指出,纯粹自利的商业活动是会陷入困局的,休谟对诚信的经济交换与自利的行为人之间所做的调和揭示了一种博弈理论。当休谟说人们对陌生人的仁爱太微弱,其中的真实含义是仁爱之情对于各方摆脱因单纯自利而陷入的困局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各方的博弈才可能使遵守道德规则与追求经济利益二者协调一致[7](p47-67)。
三、正义规则本身的特定适用情境
针对本文第1 节中归纳的数字化唐卡图像面临的未经授权的复制、传播和假冒、以次充好等问题,用鲁棒水印技术,将标识唐卡图像作品所有者的相关信息,如作者签名、企业Logo、图像序列码等作为水印,嵌入数字化唐卡图像中,将含水印的唐卡图像用于宣传展示。当该含水印图像被非法复制、传播或被假冒时,从侵权者非法复制或假冒的图像中能提取出合法拥有者的水印信息,就可以证明侵权者其侵权行为成立并可作为追责证据。
有研究者认为休谟对德性做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划分背后是对行为动机的区分,即休谟认为激发人们德性行为的动机有两类:要么是自然的情感,要么是人为的协约(humanconventions)[17](p373-388)。还有研究者则指出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的区分是“动机的善”和“结果的善”的区分[8](p75-80)。但是在笔者看来,上述看法虽然无误,但仅是对“自然的”和“人为的”注解,并不有助于我们理解休谟区分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的真正根源。因为当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激发合乎德性的行为的动机有两类而非一类,为什么对于休谟而言,行为的善有“动机的”和“结果的”两类而非一类,我们便会发现行为动机的区分以及“动机”和“结果”的区分本身并没有回答我们的疑问。为此,我们只能尝试从行为情境的差异去理解行为动机的差别,进而理解德性在自然和人为意义上的区分。进一步言之,假如一切合乎德性的行为,其发生不存在情境的差异,或者说天然地只有一类情境,那么休谟就根本没有必要区分出两种激发行为的动机,而在德性上细分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更无必要。因为一切行为情境既然在类型上都千篇一律,那么行为者完全只需要凭借一种行为动机(要么是由自然的仁爱情感推动,要么是受人为的正义规则约束)就足以在一切情境下做出令旁观者感到快乐和称赞的行为。如此一来,德性又怎么会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呢?
基于休谟对德性所做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划分,此部分将区分一切合乎德性的行为可能发生的两类情境。由此将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置于其中一类行为情境下加以审视,从而澄明正义规则与仁爱情感在休谟道德哲学中的相容性。
在《人性论》中,休谟认为区分德性(virtue)和恶行(vice)的根据既非道德教育,也非人的理性,而是人的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确切地说是快乐和称赞的情感。一种行为如果在旁观者心中引起快乐和赞许的情感,则该行为品格可被归为德性。相反,若一种行为引起旁观者的不快和谴责,则该行为品格应为归为恶行③参见[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26-327,507,615.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指出德性之为德性的标准在于效用(utility)。而效用包含有用性(usefulness,对自己或他人有用)和快适性(agreeableness,令自己或他人感到快乐)两方面。尽管较之于《人性论》中的论述有变化,但是休谟一以贯之地认为人的情感在有关一种行为到底是应受称赞还是应受责备的一切决定中起主导作用。。对于德性,休谟又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自然的(natural)和人为的(artificial)两类。其中,自然的德性指的是无需外在人为措施的干预,仅凭心灵中固有的自然情感或原则就能做出令旁观者感到快乐和称赞之举的那一类行为品格。例如,一个人出于仁爱情感,孝敬自己的父母或者给予乞丐以施舍,这些行为在休谟看来自然是令旁观者快乐和称赞的,因而可以被认为是合乎自然德性之举。人为的德性则意指只有借助人为举措才能做出的令旁观者感到快乐和赞许之举的那一类行为品格。例如,一个借了别人一大笔钱,债主就不能指望他出于仁爱之心而如期还款。但是借债人若在履行许诺的人为规则约束下如期还款,其诚信守诺行为则同样能够在旁观者心中引起快乐和称赞的情感,因而理应被视作合乎德性。问题是:上述两类行为既然都令旁观者感到称赞和愉快,那么休谟为什么还要将其划归到两类不同的德性目录下?他做出这种划分的根源何在?
笔者看来,当休谟对德性做出自然的和人为的区分时,他意在表明仅凭自然情感可能无法激发人们做出一些令旁观者感到快乐和赞许的行为。休谟当然清楚,仁爱作为一种自然情感可以驱使人们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这也是仁爱不仅能作为自然情感而且能体现为自然德性的魅力所在①与正义具有规则和德性双重性类似,仁爱在休谟哲学中具有情感和德性两面性。当人们出于和善、友好、慷慨、感恩等自然情感而行动时,所表现出的行为品格就是仁爱之德。。他说:“当仁爱伴随出身、权力和卓越的能力而展现于人类良好的政府和有用的教育中时,他们就似乎将那些拥有它们的人提升到几乎超越于人类本性之上的地位,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近乎神圣。”[18](p28)问题在于,在人生的一切人际关系中都怀有一种普遍的仁爱以至于在道德上接近圣人的人总是稀少的。人类心灵中天生缺乏爱一切人的纯粹感情②关于人为什么没有普遍的“人类之爱”(love of mankind,universal affection to mankind)的论述可见[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17-518.。大部分人的仁爱情感在具体的交互行为中还是会考虑“个人的品质、服务和对自己的关系”[2](p481)。这也表明人的仁爱之情并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在现实人际往来中,仁爱情感的流露是会视情境而定的。换句话说,总有一些行为情境是人的仁爱情感难以触及的。
碳交易促进企业改善技术水平,提高长期经济效益。碳交易市场是政府根据外部性原理强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市场,所以碳交易市场在诞生和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都是政策性因素;当地区生产总值较高时,碳排放数量也较高,但是碳排放数量高不一定导致碳交易金额高,一般来说,碳配额不足的企业会购买配额,碳配额多余的企业会出售配额,但是企业的碳配额充足与否与企业的碳排放数量无关,主要与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碳交易政策等因素相关;企业无法改变国家的碳交易政策,所以企业会不断改善技术水平,以降低碳排放成本,同时提高企业的长期经济效益。
实际上,休谟对不同类别的德性所对应的行为情境有专门的揭示和例证。在他看来,一切令旁观者感到快乐和称赞的行为,其发生的情境除了是每一“单个的行为”(every single act)之外,还可能是“总体的行为规划或系统”(general scheme or system of action)③参见[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17.关文运先生将“general scheme or system of action”译作“总的行为体系或制度”,笔者为了与“单个的”保持对应,将“general”译作“总体的”,又鉴于休谟论正义规则时对社会分工、协作和互助计划的论述,将“scheme”译作“规划”,将“system”译作“体系”。。前一类情境很典型地例示于人们对自己所爱的人、特别相识的人或者身陷苦难中的人所发生的“不计利害的往来”(disinterested commerce)中。人们在为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时,并不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任何实在的利益,也没有别的企图,而仅是出于慷慨友好,或者是知恩图报。休谟举例说:“当我拯救苦难中的人时,我的自然的仁爱就是我的动机。”[2](p617)后一类情境则鲜明地体现于人们为占有财物而开展的互助、分工和协作这一类“计较利害的往来”(interested commerce)行为之中。对于“总体的行为规划或系统”这类行为情境,休谟在《人性论》中列举过两个例子。其一是陌生的两个人之间互相帮助收割谷子:“你的谷子今天成熟,我的谷子明天将成熟。如果今天我为你劳动;明天你再帮助我,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我对你并没有什么好意,并且直到你对我也同样没有什么好意。因此,我不会为你白费辛苦。”[2](p557)另一个则是外科医生为受了重伤的病人治病:“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如果许给医治他的外科医生以一笔巨款,他一定就有践约的义务;这个情形与一个许给强盗以巨款项的人的情形本来没有那样大的差别。”[2](p562)休谟看来,在这两种具体的行为情境中,人们之间的互相服务都不带好意,一方都不肯为另一方无偿付出。正是履行许诺的人为规则使得他们最终能够做出合乎正义德性的举动①笔者看来,休谟举医生为受重伤的病患履行救治义务的例子来说明人为的正义规则发挥作用的情境并不十分恰当。尽管从病患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与医生非亲非故,也无往日恩情,那么确实无法在道德上苛求医生无偿为自己提供医疗服务。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医疗服务行为本身有其特殊性,很难说救死扶伤行为完全处在“总的行为规划或体系”中。医生固然不能被强求一直对他的病人行义诊,但是他对病人的医疗服务行为除了受履行许诺的规则约束外,至少还应受仁爱之心的驱动。。
通过引入两类行为情境的区分,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为的正义规则和自然的仁爱情感在休谟道德哲学中的相容性。确切说来,休谟的正义规则所面向的正是“总体的行为规划或体系”这一类行为情境。在这类情境下,仁爱情感因其天然有限而不足以驱使人们的行为合乎德性(如诚实、守信、正直和公道等)。正如休谟所观察到的,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助日益密切,自私的往来在社会中已然占据主导地位[2](p558)。鉴于此,一种道德理论若还继续向世人推崇仁爱情感的作用,则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②休谟表示,在“总体的行为规划或体系”下,人们如果还以仁爱之情去开展行动,则很有可能是“违反公益”的。例如对穷困者的救济,如果仅凭仁爱之情,那么很有可能纵容穷人的懒惰,助长他们放荡的恶习(参见[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17-618)。。在仁爱情感无能为力的行为情境下,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合乎德性,正义规则理应被安排出场发挥作用。由此,在“总体的行为规划或体系”中,人们要做出令旁观者感到快乐和称赞的行为,则需要严格遵守人为的正义规则。即便与自己相熟的人打交道,人们也要严格按照既定规则去行动。例如:一位正直而公道的法官不能因为自己的亲戚贫穷而把富人的财产任意判给他;子女要想继承父辈的财产,也必须依据父辈的同意;一个人借了自己亲兄弟或好朋友的钱,也要按借款时的许诺如期偿还,不得赖账。
就此而言,休谟在正义规则理论中论及仁爱情感的限度,其用意就应当被理解为他基于特定的情境要求,悬置仁爱情感的作用,从而为正义规则的运用保留地盘。这种悬置当然不是对仁爱情感作用的彻底排斥。因为休谟曾明确表示,即便自私的往来已然在现世社会中占主导,但是“这也并不完全取消更为慷慨和高尚的友谊和互助的交往”[2](p558)。毕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可能永远只发生在“总体的行为规划或体系”这类情境中。在“单个的行为”这类情境下,仍然召唤人们表现出仁爱之情。换言之,人们在“总体的行为规划或体系”中守规则,本身并不妨碍他们在“单个的行为”中讲仁爱。对于休谟而言,人们在“单个的行为”情境下展露仁爱情感的对象也并不只限于与自己亲近或相熟的人群上。他们完全可能不求回报地对素不相识的穷困者实施帮扶和救济,或者向身处苦难的陌生人伸出援手。以扶危济困为例,休谟认为虽然人们并没有被人为地规定这样一种帮扶他人的义务,但是他们心中的仁爱之情会驱使自己达到这种义务。因为置身于那样的情境下,如果不尽力伸出援手,人们就会由衷地感到那将是不道德的[2](p555)。
(3)采用技能竞赛激励法:为更进一步的提高学习的动力,可以将课程的学习与结构力学及结构竞赛紧密结合。把学科竞赛的内容搬到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因而,在解读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时,我们一定不能脱离正义规则本身所适用的行为情境。通过考察“单个的行为”和“总体的行为规划或体系”这两类行为情境,由互利论、博弈论和契约论解读视角所引发的争议——“人为的正义规则如何与休谟道德哲学中自然的仁爱情感相兼容?”也得到澄清。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休谟在其正义规则理论中论及仁爱情感的有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为的正义规则与自然的仁爱情感在休谟道德哲学中是不相容的。因为通过分析休谟对德性所做的人为的和自然的区分,我们可以发现休谟这一区分背后默认的根据是:一切合乎德性的行为除了可能发生于“单个的行为”情境之外,还可能发生于“总体的行为规划或系统”这类行为情境。依照休谟的看法,在前一种情境下,自然的仁爱情感足以促使人们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而在后一种情境下,自然的仁爱情感非但不足以驱使人们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而且还可能导致一些有违德性的举动。因而在“总的行为规划或系统”这类情境下,为了克服仁爱情感的有限性,正义规则不得不被人为地发明并加以运用。正因为休谟对正义规则的探讨考虑了特定的适用情境,所以他的正义理论本身有别于以往的个人正义理论(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切的个人如何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准确说来,休谟基于特定行为情境所建构的是一种社会正义理论(一个社会如何确立稳定的财产权)。这种建构正义理论的思路也深刻启发了当代政治哲学家们对正义议题的思考,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就曾明确表示他对社会分配正义的考察继承了休谟。就此而言,澄清正义规则的适用情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休谟所谓仁爱情感的有限性,而且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休谟正义理论本身的理解。
参考文献:
[1]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Brian Barry.A Treatise on Social Justice,vol.1:Theories of Justic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4]Martha C.Nussbaum.Frontiers of Justice:Disability,Nationality,SpeciesMembership[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5]Allan Buchanan.Justice as Reciprocity versus Subject-centered Justice[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90,19(3).
[6]Annette Baier.A Progress of Sentiments:Reflections on Hume's Treatise[M].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7]Peter Vanderschraaf.Hume’s Game-Theoretic BusinessEthics[J].BusinessEthicsQuarterly,1999,9(1).
[8]陈晓平.功利与情感之间:评休谟的道德哲学[J].哲学研究,2003(2).
[9]David Gauthier.David Hume,Contractarian[J].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79,88(1).
[10]Jonathan Wolff.Model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J].Novartis Found Symposium,2006(278).
[11]Rudolph V.Vanterpool.Hume on the“Duty”of Benevolence,Hume Studies[J].1988,14(1).
[12]Joy Salter.Hume and Mutual Advantage[J].Politics,Philosophy and Economics,2012,11(3).
[13]William Kline.Hume’s Theory of Business Ethics Revisited[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105(2).
[14]Robert J.Lipkin.Altruism and Sympathy in Hume's Ethics[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7,65(1).
[15]Rico Vitz.Hume and the Limits of Benevolence[J].Hume Studies,2002,28(2).
[16]RicoVitz.Sympathyand Benevolencein Hume's Moral Psycholog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04,42(3).
[17]James Fieser.Hume's Motiva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Virtues[J].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1997,5(2).
[18][英]休谟.道德原则研究[M].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9.008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9-006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休谟哲学著作翻译与研究”(17BZX012)。
作者简介:陈亮升(1990—),男,湖北广水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正义论文; 仁爱论文; 休谟论文; 规则论文; 德性论文; 《理论月刊》2019年第9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休谟哲学著作翻译与研究”(17BZX012)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